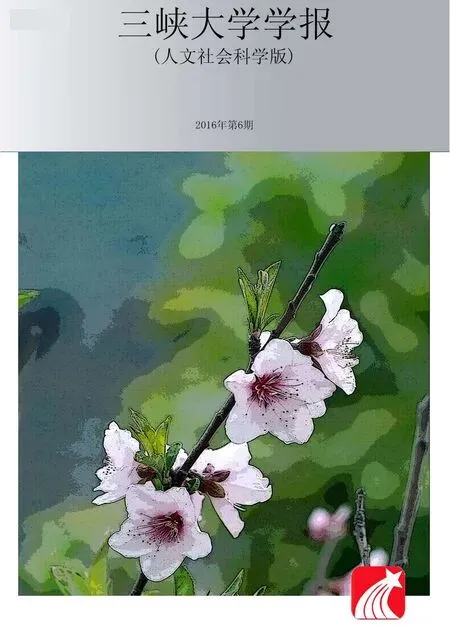论日本“精密司法”及其对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启示
2016-04-04单子洪
单子洪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北京 100088)
论日本“精密司法”及其对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启示
单子洪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北京 100088)
“精密司法”是日本学者松尾浩也教授首创的用于描述日本刑事诉讼特色的概念,其内涵是基于追求实质真实的目的,检察官与警察以彻底的侦查为核心,并以充足的证据为基础进行起诉,法院竭力调查案件细微的真相,最后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结果。“精密司法”现象暴露出了日本过于纠问化的侦查、过于严格化的起诉以及过于依赖案卷笔录的审判等问题。中国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日本非常类似,但是在程度上则更为极端化。日本的“精密司法”现象提醒中国未来的刑事诉讼改革,吸收借鉴当事人制度的精髓可能并不适合中国,应当探索一条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进路。
“精密司法”; 当事人主义; 中国刑事诉讼改革; 松尾浩也
自1996年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后,带有浓厚纠问色彩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开始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先进因素及经验,逐渐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运行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当事人主义特色的刑诉机制在正当程序理念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并越来越多地发挥保障人权的作用,以往许多带有中国刑事诉讼的痼疾得以初愈(如刑讯逼供),这些优秀的成果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订时集中体现。然而,二次修订后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却并没有因为借鉴了当事人主义的优势而彻底解决问题——以刑事庭审虚化为表象的“侦查中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以及司法工作者对案卷笔录的强烈依赖仍是中国刑事诉讼不可动摇的特征。这些特征顽固地将当事人主义的一些核心理念拒之门外。因此,二次修法后,中国的刑事诉讼学者仍在不遗余力地探寻如何在中国进一步确立当事人主义与正当程序的理念,探索对中国的刑事司法现状进行彻底性的改革。2014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这标志着执政当局终于发出了彻底变革现有刑事诉讼模式的声音,而中国刑事诉讼学界也“一呼百应”,纷纷对如何终结现有的“侦查中心”模式以及案卷笔录的依赖性,如何实现“以审判中心”的刑事诉讼新模式展开探讨。
实际上,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也存在着与中国类似的问题。自从二战结束后,借鉴法德建构起来的日本刑事诉讼制度受到了美国的深刻影响,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制度和经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混合诉讼模式”。1948年的日本《昭和刑事诉讼法》(日本现行刑事诉讼法)既保留了传统的职权因素,又引进了当事人主义的理念,开辟了刑事诉讼的第三种模式,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这种混合模式既实现了真实发现的诉讼本质功能,又实现了人权的保障,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日本的混合模式中的一些当事人主义的核心理念或制度在日本受到了强烈的排斥,甚至日本的刑事司法实践完全体现着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点。关于此,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论断莫过于松尾浩也教授的“精密司法”理论。他指出,基于“精密司法”,日本每年的定罪率均超过了99%,在这一数字的背后表现出了日本诉讼参与者对追求真实的极度热情,甚至连被告人都不隐讳对“精密司法”的偏好。松尾浩也教授认为这种“精密司法”的日本现状可能导致追求真实与程序正义两种理念之间平衡的崩溃,日本刑事诉讼可能会与真正的当事人主义渐行渐远[1]。
仅2014年,中国的刑事案件量有107万件之多,而法官宣判被检察官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仅为1000起左右,中国的定罪率可能在99.999%以上。松尾浩也教授的所谓“99%的有罪率让外国学者吃惊”的论断可能过于夸张了。然而,日本的99%的定罪率是基于所谓的“精密司法”,正是刑事诉讼过于“精密”,探求真相过于热情而牺牲刑事诉讼的对抗性过多,才会出现如此之高的定罪率。由此,从日本“精密司法”的刑事诉讼现状中引申出一个重要问题——一种大量留存纠问残余的刑事诉讼制度,到底能否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之精华,构建合理并符合国情的新机制?
一、“精密司法”理论的内涵
日本学者松尾浩也教授在观察了美国当事人主义并没有落实到本土的诉讼制度中这一现象后,提出了“精密司法”的日本刑事诉讼特色论。“精密司法”是指:日本实行彻底的侦查,在与正当程序不正面冲突的限度内,对拘禁的犯罪嫌疑人实行最大限度的调查。不仅警察,而且检察官也非常重视侦查,一般要在确定充分的证据基础上起诉,起诉要有完全的把握。在审判中,经常是在征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或者以证人丧失记忆、陈述矛盾为理由,使用侦查过程中的陈述笔录作为证据,排斥传闻证据规则的适用。在许多案件中,“口头辩论”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朗读证据文书。在需要开庭两次以上的案件中,开庭间隔时间很长。法院努力查明案件细微的真相,并根据这个结果做出判决。这种“以事实为中心”的“精密司法”理论可以被称为“拟似的当事人主义”[2]。
松尾浩也教授指出:日本刑事诉讼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均集中在“精密司法”,“精密司法”理论本身只是在描述日本刑事程序极端重视发现真实的特征,而并不包括价值判断[2]87-88。另外,松尾浩也教授也承认,“精密司法”的现状是受到了日本国民普遍追求事实真相的司法文化所支撑的。从理论角度上说,尽管实体真实主义与正当程序主义格格不入,但是这种司法文化承认并且崇尚实体真实主义,才形成了今天的“精密司法”现状。
对于“精密司法”的评价,松尾浩也本人认为这种“精密司法”确实有些过度“精密”了,也就是“精密司法”的司法现实可能已经成为了日本刑事司法的障碍。这种障碍体现在刑事诉讼机制的各个方面,具有架空日本刑事诉讼立法中的当事人对抗因素的可能。但是同时他指出那并未对日本刑事诉讼制度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也并未提出对现行的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作出彻底的改良。而是在认识客观存在的“精密司法”的基础上进行“微调整”,使得“精密司法”化的刑事诉讼模式偏向更具弹劾性质的当事人追行主义。一言以蔽之:“日本的精密司法让人感到有点像脸色苍白,弱不禁风的美女。需要刮点当事人主义活力之风。”[3]
对于松尾浩也教授的“精密司法”理论,日本的刑事诉讼法学者展开了广泛的争论。例如,田口守一教授阐释了“精密司法”的产生原因以及克服之道。他认为日本的“精密司法”现象是当事人主义受到日本实质真实传统的束缚所形成的日本特色的“当事人主义”,是过度重视追求案件真相的必然结果。若要破除“精密司法”之藩篱,则必须将其作为前提存在的追求绝对实质真实之传统“相对化”,寻找更多可以替代发现实质真实方能解决刑事案件之道,形成为多元化目的而存在的刑事诉讼制度[2]99-106。日本享誉盛名的刑事法学者平野龙一博士则认为现有刑事诉讼模式应当是尽量以案卷笔录突出侦查结果,而反之其他的庭审询问证人等程序与之相比则并不精密,日本的刑事诉讼与其说是“精密司法”不如说是一种以笔录调查为核心的“核心司法”[2]99。而与松尾浩也教授针锋相对的田宫裕教授则指出日本刑事审判并没有将控辩双方的事实攻辩发挥到底,就不能说明日本的刑事诉讼是以“精密司法”的模式运行[2]91。白取祐司教授则指出将“精密司法”概括为日本刑事诉讼特色言过其实,并且忽视了日本刑事诉讼改革的基本方向,当前日本刑事诉讼应当朝向将人权保障落到实处的方向前进,而并非总结现有的日本特色,改革刑事司法运行机制[4]。
二、“精密司法”刑事诉讼模式存在的问题
尽管持“缓和改革”观点的松尾浩也教授创设“精密司法”一词仅为客观描述日本刑事司法的现状,而并非将褒贬评价作为其理论的核心点,但是日本的“精密司法”的确为其刑事司法造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依笔者的观点,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过于纠问化的侦查、过于严格的起诉基准以及过于强烈的笔录依赖性。
1.过于纠问化的侦查
根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相对于侦查机关所处的地位之不同,可将侦查的形式分为纠问式的侦查观和弹劾式的侦查观,这一观点由日本知名的刑事法学者平野龙一首创。根据平野理论,纠问式的侦查观指侦查本质是调查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之所以能够对犯罪嫌疑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强制处分,原因就在于彻底调查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权力滥用,法律将强制处分法定化以及以司法权予以控制;而弹劾式的侦查观是指侦查仅为侦查机关单独进行的,与犯罪嫌疑人毫无关系的诉讼准备活动,强制处分行为仅是为将来法院审判而保全犯人和证据的行为,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是处于平等的地位[1]143。日本刑诉学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侦查构造理论,原因在于日本由借鉴法德的职权诉讼构造模式转为吸收美国当事人主义,由治罪偏向转为当事人追行主义这种别具一格的混合模式所导致的结果。
尽管日本刑诉学界普遍认为现在的日本刑事侦查构造是处于纠问式与弹劾式的中间阶段[5],但实际上在日本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其侦查阶段是相当纠问化的。除了国际通行的刑事司法基本人权保障机制(如沉默权)外,日本的犯罪嫌疑人并没有什么特殊防卫手段可以与控诉方平等对抗。而且《昭和刑事诉讼法》第197条规定日本司法警察可以采取非强制处分的任何必要的侦查措施,即任意侦查措施。警察完全可以利用犯罪嫌疑人律师不在场的前提下,利用一般性的职务询问,引诱其作出有罪答辩。此外,在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方面,《昭和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了“拘留”制度。尽管拘留犯罪嫌疑人需要法官签发令状得以进行,但是实务中确有相当比例的刑事案件实行第210条、第212条规定的重罪或现行犯无证拘留措施。并且在拘留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中,也没有规定国际通行的迅速带见法官的制度。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拘留,后面接踵而至的逮捕几乎一定会被适用,并且日本刑事诉讼法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保释制度,也缺乏对羁押的必要性审查措施。这些迹象均表明,在侦查阶段,看上去犯罪嫌疑人享受着种种权利保障,但从操作层面来说,犯罪嫌疑人明显是被当做警察挖掘事实真相所针对的客体。所以说在侦查程序中,日本并未形成控辩平等对抗的那种英美式的竞技机制。松尾浩也教授坦言:“迄今的日本侦查方法崇尚的是一种一味追求与犯罪嫌疑人、知情人之间沟通内心的略带情绪化的手法,随着获得有罪判决难度的增大,迟早要对美国式的侦查技巧进行认真的探讨,淡化精密司法。”[1]230
2.过于严格的起诉基准
日本刑事诉讼制度奉行起诉垄断主义,公诉要由检察官进行,这就意味着日本检察官提起公诉必须掌握一个明确的标准。对于提起公诉的标准如何界定,《昭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日本检察官在司法实践中奉行“慎重起诉”之原则,即必须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高度嫌疑”的情况下方能决定起诉。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标准,起诉必须以彻底的侦查寻找充分的证据为根基。基于《昭和刑事诉讼法》第193条赋予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在检察官的参与下,导致了侦查本身出现了尽其可能做到缜密、细致入微的侦查倾向,使得侦查与起诉特别“精密”。由此,日本的审判实践便前倾化,检察官成为刑事案件的实际处理者,而犯罪嫌疑人还要在侦查阶段承受巨大的负担,导致刑事审前程序的纠问化。对此,有学者认为,为使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的人权得到充分保障,必须降低起诉标准,引入“侦查终结”阶段,彻底割裂侦查与起诉之间的连接,使得侦查与起诉当事人主义化[6]。
此外,《昭和刑事诉讼法》第248条确立了日式的起诉便宜主义——起诉犹豫制度,基于此,垄断国家追诉权的日本检察官具有相当广泛的裁量权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这是以职权诉讼模式为根基的日本混合当事人主义诉讼特征的典型示例之一。然而,正是因为检察官基于起诉犹豫制度“可以不提起公诉”,反过来意味着检察官要提起公诉,那么就必须收集充分的证据,来判断犯罪事实的有无以及“追诉必要性”的有无,也就是起诉犹豫制度使得提起公诉的标准变得非常高。
3.过于依赖笔录证据进行案件处理
1948年,在《昭和刑事诉讼法》创设伊始,美国方面对《刑事诉讼法》草案进行了缜密研究,就一些与日本学者有分歧的问题进行磋商,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将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引入日本刑事诉讼的问题。经过讨论,最终《昭和刑事诉讼法》第320条确立了传闻证据规则。然而,第320条并没有“排除传闻证据”的明确表述;其后的第321条至第328条也为传闻证据规则设置了若干例外,其中最重视以文书为对象的传闻证据规则,并且特别处理了法官笔录、检察官笔录等文书,并且仅适用于日本刑事诉讼。也就是说,日本确立的传闻证据规则丢失了很多该规则的“原味”,成为了“改良式的日本特色传闻证据规则”。
《昭和刑事诉讼法》第321条第二、三、四款规定:关于记录在法官面前供述的书面证言,由于供述人死亡、精神或身体障碍等因素而不能在公审准备或公审日供述时,或供述人在公审准备或公审日作出与以前供述不同的供述时,该书面证言具备证据能力;若此供述是在检察官面前作出,且书面供述比公审准备或公审日的供述更可信赖时,该供述具备证据能力;而除此之外的书面证言,若在满足前述条件下,且为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与否不可缺少时,该书面证言具备证据能力。第326条第一款规定,如果检察官和被告人同意书面材料或供述作为证据使用,该书面证言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限制。由上述规定可知,尽管日本刑事诉讼确实确立了传闻证据规则,但是从第320条之后的若干例外实际上为传闻证据的应用大开方便之门。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应用的例外便是检察官面前作出的供述和证言以及经过当事人同意应用的证言。对于前者来说,由于二战前日本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有实行预审制度的历史,尽管日本刑事诉讼很早就废除了预审制度,但是检察官成为实际上的预审法官之替代者,因此几乎所有刑事诉讼的参与人对检察官都有一种信赖感,从而导致检察官笔录在证据法上具有优越之地位;对于后者来说,同意审前书面证言的应用实质上就是被告人放弃了反询问的对质权利,从辩护技术的立场出发,即便被告人拒绝同意而求反询问证人,也很有可能被控方提出其他符合传闻规则例外的证据或基于证明力的争辩制度而弹劾其反询问的效力,因此不如选择对书面供述先予以承认,然后再询问原陈述者引导其作出有利陈述,而对此策略恰恰符合控方想要利用笔录的方针,因此同意笔录的大量适用基本上左右着日本的现实审判实务[7]。
作为传闻证据规则例外的书面笔录证词被大量适用于日本刑事诉讼中,结果导致日本的刑事庭审演化成了笔录裁判的模式。检察官在提起公诉后,通过书面笔录证词交给法院完成证明责任。法官则依据详细阅读这些笔录证据形成内心确信、处理案件,因为大多数的日本刑事法官均认为侦查机关或者检察官调取的证词供述比公审日证人作出的供述具有更高的可信性以及证明力。被告人以及辩护人也对笔录内容多不持异议[8]。整个公审依靠着笔录证据挖掘事实真相,形成了所谓“拟似的”当事人主义庭审制度。案件的解决依靠着具有高度真实性以及细致入微的笔录证据进行“精密”的裁判。
三、“精密司法”刑事诉讼模式给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启示
从1979年到2012年后,经历了两次修改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引入很多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合理因素。然而,第7条规定的三机关配合原则始终是困扰中国刑事诉讼的魔咒,使其根本无法吸纳当事人主义之精髓。近期的四中全会的《决定》虽然掀起了“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浪潮,但是从诸如“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等表述可看出其仍没有突破旧有配合原则之藩篱,改革仍是在极度治罪偏向的诉讼机制舞台上演出而已。这种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独立并行的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演化为三个“极端”,实际上与立法中的当事人因素相行甚远。
彼岸的日本国比中国要早50年吸收当事人主义因素,并且更为彻底在立法层面确立当事人主义的核心制度。但是,日本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精密司法”却产生了诸多与当事人主义背道而驰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三个“极端”形式上看是极为相似的,但是从程度上评价中国的三个“极端”问题却比“精密司法”带来的每一个问题更为严重、更为突出。吸收当事人主义精髓的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仍旧出现“精密司法”的现状,这提醒着我们或许当事人主义极有可能不能扎根于诉讼机制以纠问主义为传统的中国,或许我们要对中国未来的刑事诉讼进行彻底改革的方向进行深刻的反思。
1.中国刑事诉讼机制的三个“极端”
第一,“极端”纠问化的侦查。
松尾浩也教授的“精密司法”论指出正是因为日本检察官享有极大的起诉裁量权,因此其必须要对涉案所有事实有一个精确的把握,从而导致了日本刑事侦查程序的纠问偏向。尽管如此,日本的犯罪嫌疑人似乎要比中国的犯罪嫌疑人“舒服”得太多。例如,日本的犯罪嫌疑人享有任意自白的特权,由此其享有沉默权并享有被告知沉默权的基本权利,并有辩护人在场制度保障该权利的行使。另外,尽管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并不享有受到保释的权利,但是羁押的期限最长为20天,特定的犯罪也不会超过一个月,并且在此期间犯罪嫌疑人随时享有申请撤销逮捕或提出准抗告的权利来对抗不适宜的羁押情形。反观中国的侦查程序,若比较起来,中国奉行的是极端的纠问式侦查观。支持这一结论的例证不胜枚举,但是重点突出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对于言词证据排除来说,尽管该证据规则确实威吓了长期存在的刑讯逼供行为,但是实践中的重复自白问题极为突出,若干份被告人供述,仅仅因法律规定排除了一份非法供述,另一份合法化的供述仍然可以作为定案根据,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意义。对于实物证据来说,“作出补正与合理解释”的规定治愈了极大多数的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而且很多实务工作者混淆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与实物证据鉴真辨认规则的内涵,使他们错认为排除了极多的不具备真实性的实物证据。相较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来说,中国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更是一具没有案例作为“内容”的空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实效,恰恰说明了犯罪嫌疑人没有寻求强力救济的手段对抗违法取证的侦查行为,反映了纠问式侦查的极端性。
其次,侦查羁押期限过长,替代羁押措施极为严酷。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羁押期限至多可以延长至7个月之久,算上实践中大量适用的最长的1个多月的拘留期限,整个侦查环节可以将犯罪嫌疑人羁押8个月,这在世界任何法治国家均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另外,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替代性强制措施,但是其在实践中这种措施表现出的完全是“以严代宽”的替代性。很多职务犯罪案件,基于证据的难以取得,嫌疑人的口供变得极为重要,为了获取口供,侦查机关往往将嫌疑人押往指定地点进行所谓的监视居住,实际上嫌疑人受到的痛苦要明显高于逮捕的看守所式羁押,人权保障完全得不到体现,而且这种措施也长达半年之久,嫌疑人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过长的侦查羁押期限以及严酷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出现,毫无疑问代表着办案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执著,强制措施的人身保全的性质完全异化成为方便办案的手段,更突出了中国侦查的极端纠问性。
第二,“极端”严格化的公诉。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起诉垄断主义以及起诉法定主义,并享有一定的起诉裁量权。同时,与日本类似,中国的刑事公诉并没有起诉司法审查机制,也就是说中国的检察机关享有绝对垄断性的公诉权力。然而,《刑事诉讼法》确定了提起公诉与法院定罪完全同样的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这就导致了实践中几乎所有的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时都将自己视为法官来处理案件,为此,在审查起诉环节中,检察官均不遗余力彻底地调查案件,争取提起公诉的判断与法院内心确信定罪的判断保持高度一致。为了能够彻底调查案件,《刑事诉讼法》也为检察官设计了补充侦查这一制度,检察官享有两次机会补足证据,完成证明责任。中国的这种现状极其类似日本“精密司法”中的起诉情况,提起公诉的标准极端严格化,结果使得案件在审前程序就已经得到彻底的调查和处理,导致刑事诉讼的中心偏向审前程序,并且加重了侦查程序的纠问化程度。
极端严格化的公诉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检法两机关对案件判断的剧烈冲突。由于公诉标准与审判定罪标准一元化,检察官与法官同样作为司法官对自己形成的内心确信均有一定程度的自尊心,并且提起公诉的准确性与裁判的准确性都与自身的利益挂钩。一旦两机关对某一案件的认定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那么双方均互不相让。实践中,检察机关因不服一审判决而提出抗诉的案例比比皆是,这样一来上一级检察机关与法院就又被牵扯进来,导致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降低诉讼效率。
第三,“极端”形式化的庭审。
“精密司法”的一项重要表现便是笔录式的庭审裁判,可以说,这种裁判模式是日本刑事诉讼纠问式残余的极致体现。笔录裁判的出现是由于传闻规则例外的存在,以及日本法曹界三方对于笔录作用的一致默认以及排斥以反询问为核心的竞技式庭审所造成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庭审是非实质化的。实际上,日本的证人出庭比率并不低,只是其没有受到像英美法系律师针对性极强的反询问罢了。另外,日本刑事诉讼的一大特色是奉行起诉书一本主义,该制度不仅排斥了法官对案件形成预断的可能,更排斥了法官庭后详细审阅案卷的情形,也就是说,即便是多次公审,法官的心证也只能在法庭上形成。
自四中全会“决定”出台后,绝大多数中国刑事诉讼学者均在探讨如何完善刑事庭审证人出庭制度,以解决证人出庭率过低,庭审虚化的问题。但实际上,中国刑事庭审虚化的真正极端表现在于法官的庭前预断案件或者庭后总览案件、以及审委会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定夺机制。如果法官在庭审外对案件形成预断和确信,那么庭审环节自然就成了解决心证中若干疑点的途径,对于简单的案件,法官心中对于案件的关键事实几乎是无疑惑的,那么这样的庭审定会流于形式,并且心证已在审判前形成,辩护人的庭审意见自然“不受待见”,庭审辩护也跟着流于形式,沦为作秀;对于复杂、疑难案件,因为错案追究的问责制度,承办法官不敢拍板定案,审委会的存在便成为了法官躲开追究问责的避风港,而审委会判者不审的性质自然排斥了庭审的作用。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表现,毫无疑问中国的形式化庭审与欧洲大陆中世纪的纠问式庭审并无差异。
2.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出路
第一,实现彻底的司法控制侦查措施机制。
形成中国极端纠问式侦查观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直接侵犯或高度威胁。虽然刑讯逼供等直接侵害的恶况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强权式的侦查给犯罪嫌疑人带来的压力,以及随时可能对其基本权利造成侵害的高度威胁仍旧存在。比较日本的“精密司法”中的偏纠问式的侦查,英美法系那样的审前程序两造对抗,司法机关居中裁决的形式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侦查程序改革。结合目前的情形,改革的重心应当放在利用司法权彻底控制强制侦查措施上。无论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落实,还是人身强制措施的不合理之处,这些问题均反映了侦查强制措施由于缺乏司法控制,因此可以被任意使用,从而造成侵犯人权的风险。欲实现司法权的彻底控制效用,首先,应当调整现有的司法控制机制。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其重点考虑仍在于尽力挖掘客观事实,极端重视证据的证明力,以确保捕后起诉必能获得有罪判决,从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今后的调整应将重点放在侦查机关的取证手段上;其次,应当严格依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彻底将侦查办案期限与侦查羁押期限相分离,并要严格监控羁押必要性的变化,加强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必要时还应通过听证会的方式,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公开、中立地审查对犯罪嫌疑人羁押的必要性。发现不具备羁押条件的,应当即时作出变更强制措施的裁断。然而,尽管要平衡侦查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加强犯罪嫌疑人对抗国家机关的权利,但决不能在审前程序中施行英美法系那样的竞技体制,否则将会贻误侦查取证,导致矫枉过正,实际有罪的嫌疑人逃脱法律制裁的后果。
第二,建构可行的司法控权式公诉机制。
从世界范围看,为了防止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不少国家确立了公诉的司法审查机制,如法国的预审制度、德国的中间程序、美国的大陪审团审查公诉等。而日本是为数不多的由检察机关完全垄断公诉权的国家,进而日本的检察官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公诉裁量权,这是造成日本“精密司法”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日本学者提出的公诉权滥用论,也正是为了限制检察官的公诉权的行使,调整当前“精密司法现状”的一种尝试。
中国与日本相同,检察机关享有完全垄断式的公诉权,其起诉可以不受限制的开启审判程序,而中国的法院却并不享有直接驳回公诉的权力。中国的检察官公诉的标准又与法院定罪标准同一化,结果造成了检察机关和法院因为案件争议而争吵、扯皮的现象。笔者认为,公诉标准极端严格化虽然并不合理,但是径行降低公诉标准可能也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当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检察官就几乎没有机会再对案件进行证据补充,从而影响客观真实的发现。因此解决之道应从控制角度出发,可以借鉴大多数国家对公诉施行司法控制的制度,对公诉进行形式和实质双重审查,不仅可以缓和检法冲突,有效控制检察官可能滥用公诉权的危险,还可以形成控方与审判方的缓冲带,缓解法官对案件的预断问题。从世界范围内观察,大多数发达国家公诉司法控制的主体均是法院中非审判官的司法官,如法国的预审官、德国的书记官等。因此,中国未来的公诉司法控制主体不能再局限于现有的“检法承办人对接制”,而要突破限定,以新的主体来负责公诉审查并向审判庭移交案件,确保中立性。关于构建新主体的归属问题以及人事待遇问题需要法学界的“鸿篇巨制”,笔者初步设想这一主体至少应当归属最中立超然的法院,并可让其负责主持庭前会议、判断程序分流等开庭前重要工作。
第三,建构具备中国特色的传闻证据规则。
就改革中国刑事审判之现状,实现庭审实质化层面而言,建构可行的证人出庭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在世界范围内,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与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是证人出庭作证的根本保障。最近,刑事诉讼学界多数学者都同意应当借鉴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构建中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然而,考虑到造成中国刑事庭审虚化的根源,笔者认为,构建具备中国特色的传闻证据规则可能更具实际意义。
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虽然确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二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就后者而言,传闻证据规则具有以下鲜明的特征:其一,与直接言词原则强调法官心证来源于出庭证人作出的证言不同,传闻证据规则更强调符合传闻证据条件时,证据不具备可采性的消极后果;其二,传闻证据规则由当事人进行操控与适用,并通过提出异议的方式申请传闻证据排除,而法官则作为中立方裁断传闻证据的排除;其三,传闻证据规则除了排除完全不能出庭作证的证言之外,还具有排除当庭证人作出的传闻性陈述的作用,这无疑要比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约束的范围更广。
上文已提出造成中国刑事庭审虚化的根源在于法官于庭外形成内心确信与审委会判而不审的决断效力,那么即便存在直接言词原则迫使法官履行庭审听证的义务,但是其内心确信或已形成,或出于对出庭证人的不信任,或规避基于庭审形成错误心证的风险,法官也会一如既往地在庭外依托案卷笔录决断案件。另外对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审委会是不可能直接接触证人的,会议的决断依据还是案卷,若如此,无论直接言词原则多么严格地约束法官也是于事无补。反之,以排除性为核心的传闻证据规则限制了不出庭证言笔录的使用,即便法官受到案卷笔录的影响,但是基于证据的排除,法官即便受到传闻证据的影响也不能将其作为判决依据使用,不能作为事实认定的推理前提,而且法官在排除了传闻证据后,审委会无法再接触到传闻证据,也就间接地削弱了审委会的认定能力,长此以往法官不得不“练就”庭审形成心证的能力,庭审将会更加实质化。此外,由于传闻证据规则是基于当事人申请或提出异议方能实现的证据规则,对于辩护人取证难的中国来说,赋予其申请排除传闻证据的权利对于庭审辩护权的保障,制约控方,以及监督法官基于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作出心证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相比较而言,传闻证据规则可能对中国庭审实质化发挥更多的作用。
然而,日本的“精密司法”也提醒我们,没有对抗制传统的国家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确实存在“水土不服”的风险。因此,中国应当确立符合中国刑事司法实际的传闻证据规则:首先,中国的传闻证据规则应当仅适用于书面证言式的传闻证据,而不能适用证人转述式的传闻证据。《日本刑事诉讼法》虽然作出了转述式传闻证据排除的规定,但实践中该规定很少被适用,辩护律师也尽量不会引用该规定限制证人陈述。转述式的传闻证据辨别起来极端复杂,而且更存在广泛的例外,这将会给控辩审三方对证据的判断带来巨大的麻烦。若一场庭审重点关注证人是否转述他人证言,那么刑事诉讼发现客观真实的价值将会被消磨殆尽,考虑中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转述性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不应被引入;其次,建构书面证言式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时应当谨慎。导致“精密司法”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刑事诉讼法》为传闻证据规则赋予的强有力的例外,结果使得例外成了原则,原则演化成例外,因此若要以传闻证据规则为媒介彻底使庭审实质化,构建例外的适用必须慎重,切忌不能出现类似日本使例外发挥代替原则适用的倾向,结果使得传闻证据规则虚有其表。
四、结论
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极其擅长博采众长并善于学以致用的国家。其刑事诉讼在历史上深受中华法系之影响,明治维新后,无论借鉴法国的《明治刑事诉讼法》抑或借鉴德国的《大正刑事诉讼法》,日本都打下了职权诉讼模式的根基。而二战后的1948年《昭和刑事诉讼法》(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在美国的帮助下大量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形成了所谓的混合式诉讼机制,因此日本刑事诉讼从立法层面上讲可以说是世界刑事司法经验的集大成者。然而,受本土神道教深刻熏陶的日本人却展现着挖掘事件真相、勇于承担责任、细致入微解决问题的特征。“耻感文化”形成了日本人的“义理高于一切”的教条与“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信念[9]。这种特殊的文化传统于日本刑事诉讼集中体现在对实质真实的极度渴求与对司法竞技主义的排斥,由此,“精密司法”便成为了日本刑事诉讼的特色。
从较为宏观的层面上看,通过日本的“精密司法”现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自1996年后被大量引入到了中国的当事人主义因素,其能不能很好地契合中国这样一个价值观既朴素又保守的国家,显而易见,从中国的诉讼参与者到社会公众远不能接受一名辩护律师为了自己委托人的利益而像英美庭审那样无所不用其极的弹劾证人的证明力,也不能忍受中国的司法者不顾客观真相,仅仅基于正当程序而对关键证据进行排除。如果在中国强推英美法系的竞技主义,可能会产生比日本的“精密司法”现状更为严重的后果。笔者的结论是,对于中国这样的纠问式传统过于厚重、并且形成了为追求客观真相而不惜牺牲程序正义的司法惯性的国家,完全构建当事人追行的诉讼模式并不合适,而对刑事司法局部问题作出符合基本诉讼规律以及突出人权保障的调整可能更为适宜。
[1] 松尾浩也.刑事诉讼法: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6-17.
[2] 田口守一.刑事诉讼的目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87.
[3] 松尾浩也.刑事诉讼法讲演集[M].东京:有斐阁,2004:284.
[4] 白取祐司.戦後刑事訴訟法学の歩みと現状[M]//川﨑英明,白取祐司.刑事訴訟法理論の探究.東京:株式会社日本評論社,2015:13-14.
[5] 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99.
[6] 石田論識.起訴基準の再検討[M]//川﨑英明,白取祐司.刑事訴訟法理論の探究.東京:株式会社日本評論社,2015:104-106.
[7] 松尾浩也.刑事诉讼法: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3-77.
[8] 汪振林.日本刑事诉讼模式变迁研究[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267-270.
[9]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
[责任编辑:马建平]
2016-06-20
单子洪,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D 925.2
: A
: 1672-6219(2016)06-007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