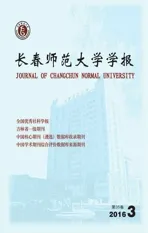《唐诗三百首》不收李贺诗原因新探
2016-03-29张宏锋
张宏锋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唐诗三百首》不收李贺诗原因新探
张宏锋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摘要]李贺诗未被选入《唐诗三百首》已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李贺诗未入选的原因并非孙洙学识浅陋,或没有严格按照标准来编选,也非李贺诗在观念上对君主不敬,而是因为李贺诗不符合孙洙定下的“脍炙人口、易于成诵”、“启蒙儿童、家塾课本”和“体裁完备、择其尤要者”这三条选诗标准。此外,李贺诗并非不符合“温柔敦厚”这一传统的儒家诗教,而是不符合“雅正”的文学观念。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李贺诗无法入选《唐诗三百首》。
[关键词]李贺诗;孙洙;唐诗三百首;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目前,关于李贺诗未入选《唐诗三百首》原因探析方面的论文有李德辉的《<唐诗三百首>为什么未选李贺的诗》(以下简称“李文”)和邹爽的《李贺诗未入选<唐诗三百首>原因探析》(以下简称“邹文”)。这两篇文章均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仍有缺失和有待商榷的地方。孙洙在序中提到自己的选诗标准:“世俗儿童就学,即受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期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城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胜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1]从中可以概括出孙洙选诗标准有以下三点:(1)选出的诗歌要脍炙人口,易于成诵;(2)选出的诗歌要有启蒙儿童之用,适合成为家塾课本;(3)选出的诗歌要体裁完备,择其尤要者。下面分别从这三点来分析李贺诗未能入选《唐诗三百首》的原因。
一
李贺诗多奇字异辞,内容荒诞诡谲,不易于成诵。对此,前人早有批评。如:唐代诗人杜牧《李贺集序》云:“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2]7明代的余飏在《家伯子李昌谷诗解序》中云:“唐人诗品,以杜甫为圣,李白为仙,李贺为鬼,故唐诗无注可读者,李、杜皆是;虽有注而终不可读,惟贺为然。贺之诗,险仄奇诡,无一字可调俗言,无一言可入俚耳。”[2]209批评李贺诗“险仄奇诡”,即使有注,亦很难理解。再如,明代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十六云:“后人学贺者,但能得其诡谲,于佳句十不得一,奇句百不得一也”[2]205。指出李贺诗因内容诡谲,后人即使效仿其诗,也很难取得突出的成就。要言之,李贺诗在内容上不具备“可接受性”。这一点在李文和邹文中皆有详细论证,不再赘述。这里谈一下两篇文章缺失和可商榷之处。
李贺诗大部分不符合“易于成诵”的标准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中符合这一标准的小部分诗作,如《马诗》(其五、其六)、《南园》(十)等,为何未能入选呢?李文认为:“编者在实际操作中,于具体的作品去取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的,至少他对待唐代诗人的标准就不一致,一宽一严,对待以奇取胜、不肯正道直行的诗人尤其苛刻,心存偏见。”[3]事实上,孙洙选诗的标准是很严格的,并无所谓“宽严”之分,也没有对“以奇取胜、不肯正道直行”有苛刻偏见之举。证据主要有三个:一是孙洙在《唐诗三百首》序中提到,其编书目的之一就是不满《千家诗》选诗标准不一,随手掇拾,故孙洙在定下选诗标准之后,定会严格遵守;二是孙洙将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等人的诗作大量选入,显然不是因为喜欢这些诗人,对这些诗人放宽标准,而是这些诗人确有较多的作品符合选诗标准;三是孙洙没有选择《马诗》(其五、其六)、《南园》(十)等易于成诵的作品,恰恰证明了其是严格遵照标准来选诗的。因为这一部分诗作虽然“易于成诵”,但尽是悲观消极之作,并不符合“启蒙儿童之用”的标准。再加上其他原因(下文有所论及),最终这小部分诗作未能被《唐诗三百首》所选录。因此,孙洙没有选录李贺诗,并非是对其有所偏见,而是李贺诗没有达到选诗标准。
二
孙洙选诗的第二个标准就是“启蒙儿童之用,成为家塾课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李贺诗无法被选入《唐诗三百首》。与这一标准相关的即为当时的科举制度。乾隆二十二年规定:“会试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才正式确立了试诗制度,从此诗歌成为学子仕进的重要阶梯[4]。孙洙的《唐诗三百首》完成于乾隆二十九年,具备家塾课本和应试教材之资,其主要对象是儿童。故孙洙所选录的诗歌应是积极向上、思想纯正的。在这一点上邹文认为:“李贺诗内容上的缺乏盛唐之音与讽刺性,观念上的目无君上,同《唐》成于康乾盛世,且推行文化高压的时代背景产生了冲突,这是李贺诗未能入选的第三点原因。”[5]这种说法是欠妥的。沈德潜在《重订唐诗别裁序》中云:“又五言试帖,前选略见,今为制科所需,检择佳摘篇,垂示准则,为入春秋闱者导夫先路也。”[6]可见,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是因为有“制科”的需要(“制科”在这里指的就是科举)。而在重订时,又偏偏收录了李贺十首诗作。这十首诗分别为:六首七言古诗(《高轩过》《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春坊正字剑子歌》《将进酒》和《美人梳头歌》)、一首五言律诗(《七夕》)、一首五言绝句(《马诗》(十))、两首七言绝句(《南园》其五和其六)。可知,这十首诗并不与当时的科举制度相悖。再者,沈德潜与乾隆皇帝关系非同一般,故沈德潜绝不会选录在观念上会触犯乾隆皇帝的诗作。
《唐诗三百首》和《唐诗别裁集》均是为了应试而编写的书,为何沈德潜选录了这十首诗而孙洙却没有选录呢?原因之一就是这十首诗要么在内容上为抒发怀才不遇之作(《马诗》(十)和《南园》的其五和其六),或为意境苍凉、颓伤情感之作(《高轩过》《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将进酒》和《七夕》);要么在风格上为构思奇特、想象力超常之作(《春坊正字剑子歌》和《美人梳头歌》),显然不适合启蒙儿童,更不适合儿童效仿学习。沈德潜在《重订唐诗别裁集序》中云:“第当时采录未竟,同学陈子树滋携至广南镌就,体格有遗,倘学诗者性情所喜,欲奉为步趋,而选中篇未之及,恐不免望洋兴叹而返也,因而增入诸家……”[6]从中可知,沈德潜所选择的读者对象并不包括儿童,而是爱好诗歌的学者,再加上这些诗又符合“温柔敦厚”这一诗教传统(下文有所论及),所以收录了这十首诗。因此,李贺的这十首诗没有入选《唐诗三百首》并不是因为其在观念上目无君主,而是因为这十首诗确实不符合“启蒙儿童之用,成为家塾课本”这一选诗标准。
三
孙洙选诗的第三条标准为“择其尤要者”。在这一点上,沈德潜亦云:“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录其所长,遗其所短,学者知所注力。”[6]要言之,二人选诗的标准皆为在某一诗体之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诗作。这解释了为何孙洙不选择李贺《南园》(其五、其六)、《马诗》(十)等通俗易懂的诗作而选择了韩愈《石鼓歌》那样难懂的诗作。《南园》(其五、其六)和《马诗》(十)分别是七言绝句和五言绝句,而韩愈的《石鼓歌》是七言古体诗,不能将其放在一起比较,故此问题应一分为三:在七言绝句之中,为何没有选择李贺的《南园》(其五和其六)?在五言绝句中,为何没有选择李贺的《马诗》(十)?在七言古诗方面,为何选择了韩愈的《石鼓歌》这样难懂的作品呢?下面分别论之。
首先,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凡例中评价七言绝句:“七言绝句,……开元之时,龙标、供奉,允称神品。外此高、岑起激壮之音,右压多凄婉之调,以至‘蒲桃美酒’之词,‘黄河远上’之曲,皆搜场也。后李庶子、刘宾客、杜司勋、李樊南、郑都官诸家,托兴幽微,克称嗣响。”[6]七言绝句首推李白和王昌龄,此外还有高适、岑参、王维、王翰、王之涣、李益、刘禹锡、杜牧、李商隐、郑谷诸家。其中,并没有提到李贺。虽然沈德潜选了李贺的两首绝句(《南园》的其五和其六),但李贺在这方面的成就显然没有超越以上的诸家。换言之,李贺在绝句方面的成就并没有得到时人的认可。孙洙选诗是“择其尤要者”,故没有选择李贺的这两首绝句。退一步讲,即使其得到了时人的认可,但从内容上来看,这两首绝句主要抒发怀才不遇之情,并不适合未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儿童。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其无法入选《唐诗三百首》。
沈德潜评五言绝句曰:“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淡,纯是化机,不关人力。他如崔颜《长千曲》,金昌绪《春怨》,王建《新嫁娘》,张祜《宫词》等篇,虽非专家,亦称绝调,后人当于此问津。”[6]五言绝句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王维、李白、韦应物、崔颢、金昌绪、王建、张祜诸家,其中亦未提到李贺,虽然在《唐诗别裁集》中选录了《马诗》(十),但其为抒发怀才不遇之作,故孙洙未选录此诗。
沈德潜对七言古体诗评价称:“《大风》、《柏梁》,七言权舆也。自时厥后,魏、宋之间,时多杰作,唐人出而变态极焉。初唐风调可歌,气格未上。至王、李、高、岑四家,驰骋有余,安详合度,为一体。李供奉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沉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泻,为一体。钱、刘以降,渐趋薄弱,韩文公拔出于贞元、元和间,琸厉风发,又别为一体。七言楷式,称大备云。”[6]在七言古体诗方面,初唐作家有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张若虚等人,盛唐有王维、李颀、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等人,中晚唐只有刘长卿、韩愈等人。韩愈在七言古体诗方面的成就很高,所以选择韩愈的《石鼓歌》实属正常。中晚唐诗人在七言古体诗方面的成就不高,虽然选择了李贺的六首七言古体诗,但其成就远不如盛唐,再加上这六首诗不是消极悲观,就是想象力超乎寻常,故孙洙没有选择这几首古体诗。此外,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还收录了李贺的一首五言律诗,即《七夕》。沈德潜对五言律诗的评价如下:“五言律,阴铿、何逊、庚信、徐陵已开其体,唐初人研揣声音,稳顺体势,其制大备。神龙之世,陈、杜、沈、宋如浑金璞玉,不须追琢,自饶名贵。开、宝以来,李太白之秾丽,王摩诘、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扬镳,并推极胜。杜少陵独开生面,寓纵横颠倒于整密中,故应超然拔萃。终唐之世,变态虽多,无有越诸家之范围者矣。”[6]在五言律诗方面,李贺仍没有超越文中所举的诸家,而且其主要为抱怨社会黑暗腐朽之作,孙洙自然也不会选择这样的诗歌。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有些学者认为李贺诗没有入选《唐诗三百首》,部分原因是有“三百篇”的数量限制。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李贺诗一首都没有入选《唐诗三百首》,是因为其诗确实不符合孙洙的选诗标准。孙洙在序中只提到“共三百余首”,并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故孙洙没有选择李贺诗并非是受到“三百篇”的数量限制。
四
除了李贺诗不符合前文提到的三个选诗标准之外,孙洙在选诗时亦会受到自身文学观念的影响。在清朝儒学复苏的背景下,统治者把儒学教化奉为国策,学者们亦推崇儒家诗教。沈德潜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其推崇儒家传统诗教的文学观念在《唐诗别裁集》原序中已有明确的表达:“既审其宗旨,复观其体裁,徐讽其音节,未尝立异,不求苟同,大约去淫滥以归雅正……”[6]在《重订唐诗别裁序》中又提到:“至于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而一归于中正和平。”[6]原序中沈德潜的文学观念是以“雅正”为标准的,而在《重订唐诗别裁序》中又把归“雅正”改为归“中正和平”,其文学观念转为“温柔敦厚”。换言之,沈德潜的文学观念前期以“雅正”为主,而后期以“温柔敦厚”为主。“雅正”与“温柔敦厚”是两种不同的儒家诗教。孔颖达《毛诗正义·周南关雎诂训传》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正义曰:雅者训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齐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还以齐正为名。”[7]可知,“雅”即“正”,“雅正”即为“齐正”。李天道《“雅正”诗学精神与“风雅”审美规范》一文将“雅正”一词从美学的角度来理解:“雅”为“正”,“雅言”为“正言”,“雅声”为“正声”,提升到美学理论高度,“雅”就意味着正规、正统、纯正、精纯、雅正[8]。要言之,“雅正”即思想要正统和纯正。“温柔敦厚”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礼记正义·经解》云:“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教厚,是诗教也。”[7]可知,“温柔敦厚”作为传统的儒家诗教,体现的是中庸原则,即讽谏要“怨而不怒”。在重订《唐诗别裁集》之前,沈德潜没有选择李贺诗,是因为“长吉之荒诞”显然不符合“雅正”这一标准;重订之后选录了李贺的十首诗,是因为沈德潜的选诗标准变成了“温柔敦厚”,“认同诗歌中所体现出的诗人性情,更广泛地包容了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9]。所以,李贺的这十首诗符合“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但不符合“雅正”这一标准。孙洙的文学观念以“雅正”和“温柔敦厚”为主,其文学观念受到沈德潜的影响。据学者考证,“《三百首》收诗三百一十一首,见于别裁者二百四十四首,为百分之七十。”[10]显然,《唐诗三百首》是以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为蓝本。而孙洙推崇“温柔敦厚”这一诗教在《唐诗三百首》中有着更为明确的表述。在《唐诗三百首》卷八选录的郑畋的七绝《马嵬坡》下批注道:“唐人马嵬诗极多,惟此首得温柔敦厚之意,故录之。”[5]虽然没有直
接证据证明孙洙推崇“雅正”这一诗教,但没有选录李贺符合“温柔敦厚”的那十首诗恰恰可以证明孙洙是以“雅正”和“温柔敦厚”这两条标准来选录诗歌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孙洙不选择李贺诗并不是因为其诗不符合“温柔敦厚”这一特点,而是其诗不符合“雅正”这一传统诗教。这也是李贺一些“通俗易懂”的作品未能入选《唐诗三百首》的原因之一。一些学者认为李贺诗不符合“温柔敦厚”,实属冤枉了李贺。
五
经过上面的论证,孙洙不选择李贺诗,实属李贺诗不符合其选诗标准,而并非李贺诗的艺术成就不高,也并非孙洙没有卓识,忽略了李贺诗。李贺大部分诗歌的内容皆以神仙鬼魅为主,有时又消极悲观,揭露社会黑暗,在艺术风格上想象力超乎寻常,同时还喜用奇字异辞,导致其诗缺乏“可接受性”,不适合作为启蒙读物、家塾课本。虽然李贺有一些“易于成诵”和“温柔敦厚”的诗作,但其艺术成就并未得到时人的完全认可,再加之内容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李贺连一首诗都没有被《唐诗三百首》所选入。
[参考文献]
[1]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M].北京:中华书局,1955:3.
[2]吴启明.李贺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李德辉.《唐诗三百首》为什么未选李贺诗[J].古典文学知识,2010(3):54-60.
[4]邹坤.《唐诗三百首》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8.
[5]邹爽.李贺诗未入选《唐诗三百首》原因探析[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14(1).
[6]沈德潜.唐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1368.
[8]李天道.“雅正”诗学精神与“风雅”审美规范[J].成都大学学报,2004(1):28-31.
[9]韩胜.从《唐诗别裁集》的重订看沈德潜的诗学发展[J].山东文学,2008(8):106-108.
[10]马茂元,赵昌平.关于孙洙《唐诗三百首》及其编选的指导思想——《唐诗三百首新编》前言[J].文学遗产,1985(1):77-84.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3-0129-04
[作者简介]张宏锋(1989- ),男,硕士研究生,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