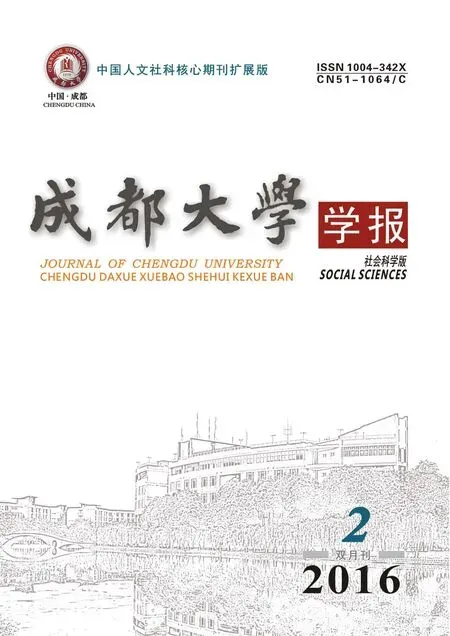广告硝烟中的《新青年》和《小说月报》*
2016-03-24李直飞刘晓红
李直飞 刘晓红
(1.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2.成都大学 期刊中心, 四川 成都 610106)
·文艺论丛·
广告硝烟中的《新青年》和《小说月报》*
李直飞1刘晓红2
(1.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650500; 2.成都大学 期刊中心, 四川 成都610106)
摘要:《小说月报》的革新,被视为是新文学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但是从广告的角度来看,却是《新青年》等新文学杂志与早期《小说月报》广告博弈的结果。在这场广告硝烟中,《新青年》采取多种广告手法,特别是对古文大家林纾的批评,使《新青年》得到了“广而告之”的机会,最终赢得了读者市场,迫使《小说月报》进行改革。
关键词:广告;《新青年》;《小说月报》
茅盾革新《小说月报》通常被看作新文学战胜旧文学的一个标志。这种较量首先表现在销量的此起彼伏之中。一般认为,《小说月报》在王蕴章编辑的最后几期达到了新低两千份,而茅盾革新后不久就达到了一万,在这场争夺读者市场的较量中,除了不同文学观念冲突外,其他外部的因素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小说月报》最早透露出要革新是在1917年10月张元济在日记里提到的“不适宜,应变通”,而败象则是在1918年之后才渐渐显露出来的。[1]衰败的主要原因自然是由于新文学的崛起带来的冲击,但销量达万余的《小说月报》在两三年内销量就大减为两千份,“衰败”的速度还是令人吃惊的。如果我们考虑到文学观念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文学战胜旧文学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促成《小说月报》销量快速下降的就应该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掺杂在里面。《小说月报》当时所处的大环境,新文学的宣传开始崭露头角,旧文学依然大行其道,文学的较量就从宣传开始,在其中,隐性或显性的广告宣传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一份刊物来说,想要迅速被读者接受,广告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广告的手法众多,并不是所有的广告都能立竿见影,特别是在大众传媒形式单一信息传播还远远谈不上便捷的时代,要真正引起业内的认可,一般的广告宣传更是难以一时奏效,对文学期刊这类带有文化性质的宣传来说更是如此。似乎从现代文学期刊诞生的时候开始,文学活动家们就找到一条能让文学期刊宣传快速奏效的方法,那就是与已经成名的其他期刊或者名家论争。闻一多就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了一个社团或一个杂志如何崛起的一系列策略:
我们若有创办杂志之胆量,即当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故你的“批评之批评”非做不可。用意在将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杀而代之一正当之观念与标准。……要想一鸣惊人则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足轰动一时。[2]
“挑衅”或“挑战”无疑可以看作是一种广告宣传,拉开了广告战的架势,特别是对名家或者是权威性报刊的挑战,其起到的效果就不仅仅是迅速提高在读者中的知名度了,往往还能在专业领域奠定相当的影响力,获得成名人士的关注。当《新青年》崛起于文坛,面对着强势的老牌杂志《小说月报》的时候,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打开了广告战。
《新青年》刚刚创刊时,寻找卖点来扩大知名度至关重要。陈独秀最后找到的卖点就是对白话文的提倡。从《青年杂志》创刊时采用文言文而不是白话文我们不难看出陈独秀等人是将白话文作为刊物卖点来进行宣传而不是切实将其作为一项事业来进行建构。重新梳理《新青年》采用白话文的过程能让这条线索变得更为清晰。《新青年》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新青年》的销量在两三千份之间,这样一种不尽人意的销量差点让这份刊物难以维持下去,面对着这样一种办刊困境,要提高刊物的销售量,寻找买点刺激读者将是其必然之路,如果还是按照一般刊物的做法,老老实实地用文言办刊,老老实实地一点一滴地提倡国学,面对着众多的强势刊物,可以想象就算《新青年》后来能形成一份有影响力的期刊,但成名绝不会那样迅速。在当时各家文学期刊尤其是影响力已经巨大的《小说月报》都还用文言办刊的时候,《新青年》不落蹊径,提倡白话文无疑就有了标新立异之举,而将胡适与陈独秀之间的通信刊登在刊物上,特意突出了胡适留学美国的身份,无疑含有利用胡适留学的特殊身份来为自己做广告的成分在里面。可以想见的是,在当时中国读者都习惯了几千年来用文言文来阅读的惯例,新办的刊物如果继续用文言文来办刊,无论其观点如何的新颖,读者都将其视为是一份普通的刊物,而刊物很难刺激起这些老中国的旧式读者了,早期《青年杂志》销量不好刚好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新青年》采取了在现在看来较为符合宣传之道的手法:一是改文言文为白话文;二是提倡新的观念,举起“科学”、“民主”的大旗;三是利用胡适等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来为他们呐喊。这三个方面,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都是标新立异之举,从视角到思想上都能刺激到古老中国已显阅读疲惫的读者。
按照陈独秀他们的心理预期,上述这些广告应该能将《新青年》的销售量提升上去的,但没想到的是中国读者的反应还是很平淡,《新青年》的销售依然故我,《新青年》在业内的影响力依然没有得到提高。也许不是读者没有反应,而是《新青年》的编辑与作者嫌这种反应太慢,他们需要的是快速提高影响力,而不是踟蹰而行。这时候,《新青年》能做的宣传手法就是选取名家来进行挑战了。选取一个已经成名的大家进行一番论战,将名家痛批一番,借名家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是《新青年》在提升影响力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广告宣传策略。那么,选取什么人做对手呢?于是林纾出现在了《新青年》编辑和作者的视野里。林纾无疑有着作为提升影响力、扩大刊物知名度“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林纾已经对他们有所反应,就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不久,林纾已经注意到了他们,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当废》来反驳他们的观点,能受到名家的青睐,就当时的《新青年》所处的情况来说是实属不易的;二是林纾是古文界的大家,通过1899年翻译的《茶花女遗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严复曾经评价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随着林译小说在全国引起的极大反响,林纾不啻成为了当时文坛的文化名人。林纾的名望之高,市场号召力之大,就连当时称为“杂志界的权威”——《小说月报》也不得不借助他来进行宣传,成为《小说月报》的一块“金字招牌”,翻开当时《小说月报》的广告,只要是提及林纾的,都是将其重点突出:
社会小说 金陵秋 冷红生著 定价四角
闽林琴南先生以小说得名。即自称冷洪生者也,先生著作等身,惟小说以译述为多,此书乃其自撰,以燃犀之笔,描写近时社会,述两军战争,则慷慨激昂,叙才士美人,则风情旖旎,尤为情文兼茂之作。[3]“林译小说”、“名家小说”在当时的《小说月报》上的广告随处可见,这可见出林纾在当时读者中的影响力。
有了这两个条件,林纾无疑成为《新青年》用来进行广告宣传的最佳人选。《新青年》的同仁们紧紧抓住林纾对他们进行回复的时机,不断对林纾抛出“炸弹”,在《新青年》之后刊出的几篇论文中,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钱玄同的《寄陈独秀》、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都含有着批评林纾的影子。尽管有着指名不指名的批评,《新青年》对林纾的这番“轰炸”显然没有起到多少效果,林纾居然没有回应。这也显示了《新青年》诸位将林纾作为广告宣传道具的一面,林纾作为当时大名鼎鼎的文界领袖,是不大跟《新青年》这班刚出道的毛头小子们较量的。但是,林纾的越是不回应,越是显示出了林纾可利用为宣传资源的价值之大,正因为双方之间地位的悬殊,更显示出《新青年》借助林纾来抬高自己的必要。于是,为了让林纾出来回应他们,就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一对一答所演的双簧戏,将林纾作为古文大家的代表进行了一番“淋漓痛快”的批评。
这种大肆打上门的做法对于一个已经成名多年的林纾来说无疑是不可忍的,忍无可忍之际,林纾终于出面回应了,很快便有了《荆生》和《妖梦》两篇讽刺小说的出现,新文学提倡者的一顿猛批,终于引来了林纾以小说来发泄他与新文化运动“不共戴天”的激愤,从宣传炒作来说,林纾的回应正中新文学倡导者们的下怀,新文学提倡者们正希望林纾有着这样强烈的反应。林纾的反应还不仅如此,在接着特地在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致蔡鹤卿太史书》,在北京、上海两地刊发出来之后,其影响已经波及全国,而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又抓住林纾的这两篇小说和公开信一阵猛批,直到林纾写信给各报馆承认有“过激之言”为止。在这番骂战中,曾有人说林纾“斯文扫地”,林纾虽然“斯文扫地”,但《新青年》借着林纾这股东风,却一路销量直上,达到了之前希望达到的效果。
这是一场带有明显广告意味的论争,《新青年》同仁们借助林纾来进行广告宣传的意图在之后得到了印证。在林纾死后不久,就有了新文学作家们对他的宽容。郑振铎、胡适等新文学的倡导者都曾对林纾做出过正面评价,认为由于“五四”文学论争给林纾带来的评价是不公允的。这很好地验证了新文化提倡者的诸人对于林纾的批评站在宣传炒作一面的立场。也就是说,新文学倡导者在起先对林纾的论争本意原不是要驳倒林纾的,而只是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才出现对林纾的大肆批判。对《新青年》同仁来说,就提高刊物的知名度来说,论争的影响力才是重点,而观点的对与错倒反是其次的了。当然,通过这场论争,客观上也使新文学站稳了脚跟。
与林纾同时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们猛烈攻击的还有鸳鸯蝴蝶派的旧文学。从文学观来看,鸳鸯蝴蝶派将文学视为娱乐、消遣的享乐主义文学观自然与新文学提倡者视文学为启蒙大众、为人生的文学观大相径庭,两种对立的文学观发生冲撞是在所必然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就新旧文学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却是鸳鸯蝴蝶派的影响要远大于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文学,在《新青年》的销量才有两三千的时候,《礼拜六》等鸳鸯蝴蝶派的杂志销量已达万余,这种销量的高下之分,自然让《新青年》这种后来者分外眼红。面对着这样的文学市场,《新青年》要扩大影响力,通过批驳鸳鸯蝴蝶派这类阅读面极广的通俗文学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树立自己的新形象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鸳鸯蝴蝶派这类通俗文学就成了新文学倡导者口诛笔伐的对象。先后有钱玄同的《“黑幕”书》、鲁迅的《有无相通》、周作人的《论“黑幕》和《再论”黑幕》等,新文学提倡者对通俗文学的这一场批驳,一方面逼迫鸳鸯蝴蝶派等文学向“俗”定位,乘势抬高自己,将自己定位为“雅”文学,另一方面打击了这一派文学在读者中的良好形象,从而提升了新文学自身的影响力。《新潮》、《新青年》这类新文学期刊新起时,攻击旧文学及其刊物就是其大造声势的一个做法,在这种广告宣传的影响下,受之影响的青年学子们,转移读者阵地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新文学倡导者们对林纾、鸳鸯蝴蝶派的大肆攻击,一方面借助于这些当时文坛的主流派别、名人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力,一方面必然使林纾、鸳鸯蝴蝶派在读者心目中的影响力下降。使得这一时期的林译小说魅力远不如从前,如明日黄花般令读者提不起兴趣,甚至还令某些受新文学运动熏陶的青年读者们反感。[4]而新文学的攻击对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则是明显的,周瘦鹃主编的《礼拜六》1916年停刊,枕亚主编的《小说丛报》1919年停刊,李定夷主编的《小说新报》1920年停刊一年。于是,我们看到,就在《新青年》等刊物的销量节节攀升的时候,老牌期刊《小说月报》的销量则不断下滑。《新青年》的销量由1915年的2000多份上升到了1917年的10000多份,而《小说月报》则在1917年后销量不断下降,到1920年就只有2000多份了。在这一升一降的背后,虽然说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各自文学观念的不同,但是,通过广告宣传炒作的手法,新文学作家对林纾、鸳鸯蝴蝶派的大肆攻击不能不对他们的主要作品发表阵地《小说月报》产生影响。林纾是《小说月报》的“金字招牌”,与《小说月报》有着长期的合作,几乎前期每期《小说月报》上面都刊登了林纾的作品。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就一直有在《小说月报》上刊登的传统,特别是王蕴章第二次编辑《小说月报》的时候,《小说月报》成为了鸳鸯蝴蝶派发表作品的一个大本营。新文学阵营对林纾和鸳鸯蝴蝶派的批驳,降低他们在读者群中的影响力,无疑也降低了他们的主要发表阵地《小说月报》在读者群中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下降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小说月报》销量的下降,而正是这些销量的下降,促成了商务印书馆最终决定对《小说月报》进行革新。
尽管在革新之前,茅盾对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作了大量的宣传,比如在十一卷十二期的《小说月报》上,连续的广告让读者感受到了革新《小说月报》的声势:
本月刊特别启事一
爱读本月刊诸君子!本月刊自与诸君子相见,凡十一年矣;此十一年中,国内思想界屡呈变换,本月刊亦常顺应环境,步步改革,冀为我国文学界尽一分之力,此固常读本刊诸君子所稔知者也。
近年以来,新思想东渐,新文学已过其建设之第一幕而方谋充量发展,本月刊鉴于时机之既至,亦愿本介绍介绍西洋文学之素志,勉为新文学前途尽提倡鼓吹之一分天职。自明年十二卷第一期起,本月刊将尽其能力,介绍西洋之新文学,并输进研究新文学应有之常识;面目既已一新,精神当亦不同,旧有门类,略有更改,兹分条具举如下:
(甲)论评 发表个人对于新文学之主张。
(乙)研究 介绍西洋文学思潮,输进文学常识。
(丙)译丛 本刊前此所译,以西洋名家小说居多,今年已译剧本,自明年起,拟加译诗,三者皆选西洋最新派之名著译。
(丁)创作 国人自作之新文学作品,不论长篇短着,择尤汇集于此栏。
(戊)特载 此门所收,皆最新之文艺思想及文艺作品,从此可以窥见西洋文艺将来之趋势。
(己)史传 文学家传及西洋各国文学史均入此门,读者从此可以上窥西洋文艺发达之来源。
(庚)杂载 此栏又分为三:
(子)文艺丛谈 此为小品。
(丑)海外文坛消息。
(寅)书报评论。
以上各门之中,将来仍拟多载(丙)(丁)两门材料,而以渐输进文学常识,以避过形枯索之感。尚祈海内研究文学之君子有以教之。
本月刊特别启事二
本月刊自明年起加大刷新,改变体例,增加材料,已见特别启事一,兹本刊本年所登各长篇尚有不能遽完者,均已于此期内登完,以作一结束。
本月刊特别启事三
本月刊自明年起改变体例,增多材料,添立门类,参用五号字印,以期多容材料,并为增加读者购买力起见,减定报价为二角。
本月刊特别启事四
本月刊明年起更改体例,(请查照启事一所开各门),并改定报酬为:
一、撰稿 每篇送酬自五元至三十元
二、译稿 每千字送酬自二元至五元
三、小品 文艺丛谭内小品酌送报酬
如蒙海内君子,惠以佳篇,不胜欢迎。
本月刊特别启事五
本刊明年起更改体例,文学研究会诸先生允担任撰着,敬列诸先生之台名如下:
周作人 瞿世英 叶绍钧
耿济之 蒋百里 郭梦良
许地山 郭绍虞 冰心女士
郑振铎 明心 卢隐女士
孙伏园 王统照 沈雁冰[5]
连续的五则广告,可谓为《小说月报》的革新做足了宣传造势,这些广告无疑在努力扭转前期《小说月报》的形象,期望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奠定良好基础,但由于之前新文学阵营对《小说月报》对保持其销量的林纾、鸳鸯蝴蝶派的批驳大大降低了《小说月报》在读者群中的影响力,茅盾的这番广告宣传,显然在短时间难以奏效,要恢复《小说月报》在读者心中的良好印象需要一个长久时期,这也是为什么茅盾革新初期《小说月报》销量并没有一下子上去的原因之一。[6]
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月报》的革新,其实也是各个阵营之间进行广告博弈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M].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48页.
[2]刘纳.郭沫若与泰东图书局[J].郭沫若学刊,1998(3).
[3]小说月报[J].第五卷第十号.
[4]柳珊.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M].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50页.
[5]小说月报[J].第十一卷第十二号.
[6]段从学.《小说月报》改版旁证[J].新文学史料,2005(3).
(责任编辑:刘晓红)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42(2016)02-67-05
作者简介:李直飞(1983-),男,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刘晓红(1981-),女,成都大学期刊中心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5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民国经济视域中的《小说月报》研究”(项目编号:15YJC751027);云南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科研启动基金“民国经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研究”。
收稿日期:2016-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