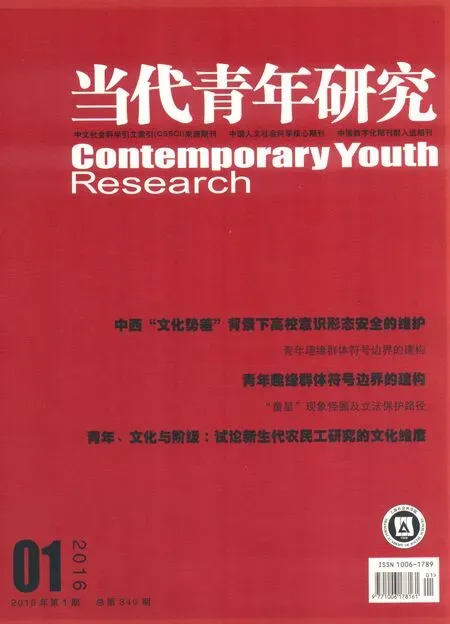当“女性”遇到“工人”
——以某机械制造业国企青年女工为例
2016-03-18高成新
高成新 刘 洁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当“女性”遇到“工人”
——以某机械制造业国企青年女工为例
高成新 刘 洁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
制造业国企中的青年女工是当代女性工人的有机构成。制造业车间场域在去性化的整体基调上,培育了青年女工彰显女性特质的工作惯习;在择偶和消费场域中,青年女工的惯习则并不受困于自己的女工弱势地位。不论劳动还是生活,制造业国企中的青年女工都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通过利用自身所特有的资本,发展出了轻视工人身份、重视女性身份的实践策略,这是结构与行动两种力量共同塑造出的。
青年女工;制造业国企;劳动;生活
自西方列强在晚清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工人阶级就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新中国的成立确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他们在资源分配和机会享有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幕启,所创边际效益低下的工人阶层逐渐在经济与社会等维度成为弱者,陷入了相对剥夺的地位。另一方面,关注并致力于铲除性别不平等的女性主义曾犀利地指出:“当我们在谈论‘人’时,只是在说‘男人’;而当我们在谈论‘性别’时,只是在说‘女人’。”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始终在男权制的统摄之下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种种瓶颈,如工作领域中的玻璃天花板效应、消费领域中的被物化现象等,女性工人亦不例外。就目前而论,在阶级分析与性别分析的交叉地带,女性工人是遭受双重困境的弱势群体,而青年女工作为女工群体的有机构成,对之进行调查分析,具有鲜明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回顾与对象选择
为“清除各种意识哲学所偏爱的‘主体’”,[1]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创立了以“场域”“惯习”等为核心概念的实践理论,向学界提供了洞悉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反身性思路。其中,场域是 “由附着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2]而“惯习则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其形式为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3]它与个体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相呼应,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场域与惯习的互生互动就导致了实践,实践就是“在一种习性和一种经人为改变以诱发该习性的情境之间建立关系”。[4]同时,受法国社会学主义传统的陶冶,布迪厄主张“客观主义的旁观在认识论上先于主观主义的理解”。[5]也就是认为场域中既成的规则与秩序“预先给定了行动的基本原则与限度”,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说惯习指导着实践,行动者“能按照惯习的系统策略来处理各种社会差别”。[6]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将运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概念工具与分析体系,对制造业国企青年女工的劳动与生活展开调查分析。
将研究对象框定为制造业国企中的青年女工,是基于如下的考量:不论从阶级分析还是性别分析的视角来看,女性工人都属于社会经济地位不高、面临生活压力与发展受限等多重困境的边缘群体,而女工中的青年(这里我们参照国家统计局的界定,将15-34岁的女性工人视作青年女工总体)作为女性工人的新生代力量,其自主意识、职业认同及人生规划等方面无疑均会对女工的整体面貌及未来走势产生巨大影响。回溯学界研究,对青年女工的考察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女性和改革开放后的打工妹这两类群体,如佟新的《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7]和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8]等作品。而针对当下国企制造业青年女工的经验研究尚属盲区,这一群体既与新中国成立后的青年女工具有某种历史的传承和变化,又同当代的打工妹群体有着某些共时的通性和特性——就这样,制造业国企中的青年女工走进了笔者的研究视线。加之当我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女性工人集中的纺织制造业及服务业等“女性化”产业时,机械制造业这一男性主导空间中的女工现状就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因此笔者选取了某市一家国有重型机械制造企业(Z厂),通过对其中的青年女工进行质性的非参与式观察,直观地了解了她们的劳动与生活情状;同时为了凸显当代制造业国企青年女工的特殊性,我们将辅以二手分析法,通过将机械制造业国企中的青年女工分别与纵贯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年女工和横剖的打工妹群体进行比较研究,以突出本文研究对象在时间(当代)和空间(国企)中的独特属性。从而在此基础上,运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作出分析。
二、青年女工的劳动:去性化与性化
在中国,女性工人是伴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而成长演进的一类社会群体。美国人类学家罗丽莎将现代性视为是“一个被延迟的本土渴望”,并认为社会性别在现代性想象中处于中心地位。[9]我们知道,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解放的一项成就,女性就业在国家话语体系中获得了合法性支持,当时“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性别意识形态“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否定和抹杀性别差异的存在意义;二是以男性为参照体系和样板的性别评判标准”。[10]在这样的性别模式下,佟新通过访谈发现受到“男女平等”理念的熏陶,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女性工人来说,“与技术相关的职业身份是女工特别看重的。女工不仅在经济上的独立成为一种常态,且工作本身使她们具有了独立、自强的精神。她们热爱集体生活,公共领域的生活成为其自我的一部分”。即便如此,那时女工的劳动也依然受着性别化的区隔,即使是受到推崇的女性劳模也不例外:“女劳模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突出了女性化的职业特性,如简单重复的机械劳动、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要求、职业晋升的阶梯较短等特点”。这样的劳动分工特点虽然旨在抹杀女性的传统特质,但是,对于无性的“铁姑娘”形象的塑造,其实是从反面固化了女性弱于甚至劣于男性的刻板印象——如果女性并不比男性差,又为什么要刻意鼓励女性模仿男性并为男性所同化呢?相应的,在改革开放后,“由国家主导的话语模型转变为市场导向的话语模型”,[11]市场经济的大潮一方面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并由此导致了越发极化的社会分层,这时女性工人的社会地位伴随着工人身份的被贬损也相应地下降了;另一方面女性则被置于消费社会的逻辑之中,其性别气质被不断地定型并放大,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女性在公共领域仍然遭受着不容忽视的性别不平等。“打工妹”的出现就是一个典范,潘毅指出,“‘打工’意味着个体变成劳动主体的过程,尤其是在为资本主义老板工作的情况下。‘妹’则进一步显示出这个劳动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性别身份”。[12]在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下,打工妹群体多集中在加工型企业、服务行业及色情等边缘职业,学界目前已对她们的群体特征、身份认同、就业路径、权益维护及城市适应等问题进行了关注与研究。通过将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女工与打工妹群体作为当代制造业国企青年女工的参照群体,我们就能够在纵横交织的谱系中获得对后者的深入理解。
(一)统一的工衣与个性的装饰
朱虹指出,“服装作为物化的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坐标,包含了文化范畴及其社会等级的复杂图式”,[13]这与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衣着呈现出一片“蓝(灰)色的海洋”的景观是相一致的。
走近Z厂,最直接的视觉感受就是所有工人都身着整齐划一的工作服装:土黄颜色、棉混纺布、宽松肥大。这种服装不分男女、无谓美丑,是去性化的,或者说是男性化的,彰显了以制造业为圭臬的工厂场域的特点:“做的都是苦力活儿”——这正如布迪厄所言:工人阶级的身体会有意地去展示男性的力量。其中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制造业国企为追求劳动效率,需要的身体形象是经受规训而驯服的、适应机器生产内容与节奏的身体,性感时尚的外形装扮并不适合车间这一前台。
但值得注意的是,Z厂中的青年女工往往会在头发与鞋子等方面精心打理,以通过个性化的装饰来体现自己的女性属性。即国企青年女工会基于自己的身体资本,采取一些性化策略来突出自己的女性身份与特质,这是她们与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女工在服饰方面的区别所在,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水平的提高与性别观念的变迁。也就是说,于衣着而言,制造业国企中的青年女工虽然在形式上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女工群体相近,但其在实质上则与当代的打工妹群体更加相似,这是因为后两者镶嵌在了同样的性别文化语境中——将女性客体化为被凝视的对象,同时它也可以看作是为布希亚提出的社会已从生产社会进入到消费社会的论点做了一个注脚:“这是消费主义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14]
(二)工作车间里的女性特质
之后,当我们深入工厂车间发现:在这一工作场域中,青年女工多集中在行车操作工和油漆工等岗位——青年女工占比为70%-80%,她们所从事的工作契合了女工的女性特质,也培育出了独特的工作惯习:操作简单,不费力,“听话”。虽然制造业的工厂车间整体上是男性化的,但是车间依然考虑并利用了女性的独特气质,如力气小、细心仔细、服从安排等,从而将青年女工安排在了特别需要这些特征的行车工等工作岗位上。
在工厂,青年女工通过发挥其性别资本特色,使自身适合于行车车工等工作角色。这样,工厂车间就用性别而自然化了工作分配,也就是生产并维系了劳动的性别分工。这一点,不论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青年女工、当代制造业国企中的青年女工还是私人企业中的打工妹群体来说,都是如此。我们发现,这三类女工群体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客观的工作内容,而在于主观的职业认同。具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青年女工赋予了工作以无上的高尚与荣光,“即使是在流水线上做一名装配工,女工们还是由衷地说:‘工作是美丽的’”;[15]而受“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以及家庭父权制的三重压迫”[16]的打工妹则“有着多重身份认同: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矛盾的族群身份认同以及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17]。对制造业国企中的青年女工来说,她们对“女性工人”的身份并不怀有强烈的归属感与自信心,“有啥热爱不热爱的,一份工作而已,挣钱养家糊口”;并且,前文提及的青年女工对身体资本的利用也从侧面反映出她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性别身份而非职业身份。这一事实与不再推崇体力劳动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分工细化与阶层分化导致的社会结构的层级化和消费社会的形塑等事实相关联。
调查表明,制造业车间整体上是一个去性化的劳动场域,但是一方面青年女工会基于自身的身体资本而策略性地显示自己的女性身份,另一方面特殊的车间岗位也会利用女性特质来引导青年女工完成工作任务。这意味着不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青年女工的性别属性都被强化了,这就导致了她们在工厂场域中的一种充满了张力的惯习和对职业角色的低度认同和对性别特质的高度追逐。
三、青年女工的生活:超越阶层与回归性别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从择偶和消费这两个与社会成员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维度来展开对制造业国企青年女工生活的调查分析。
(一)择偶期待:“我绝不嫁工人”
佟新通过访谈发现对改革开放前后的青年女工(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女性)来说,她们对配偶的选择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女工的婚姻主要发生在同一阶级或阶层内部……她们并不强烈地渴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阶层属性……女工们婚姻对象的选择途径主要是同学、同事之间的自由恋爱或由同学和同事介绍而成……对于女工来说,一方面,她们‘喜欢技术好的’工人;另一方面,有女工明确表示‘跟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人家大学生呀谁瞧得上你呀’。”[18]而对打工妹群体来说,叶文振等人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流入城市对外来打工妹的择偶观和择偶模式起到一定的再社会化作用,她们在农村形成的传统择偶意识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进步”,而她们的边缘性地位和生存压力“使得她们不得不把婚恋演变为一种尽快从经济上脱贫致富、从精神上排解孤独的工具,使自己的婚恋变迁呈现出‘二元’并存的状态,即交织着爱情与功利、自我与从众的综合变化”。[19]
制造业国企青年女工的择偶意愿是城市普通女青年的缩影,她们大多希望通过婚姻市场的成功来实现长久的阶层跃迁,“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嫁得好一点,对自己、对父母、对孩子,都好”。换言之,她们形成的择偶惯习往往并不是门当户对的“同类匹配”模式,而是“男高女低”的梯度偏好。一方面,与20世纪的青年女工相比,当代国企青年女工更加希望能够依托婚姻而完成向上流动,由此导致她们的择偶范围不再囿于工人阶层之内,有位受访的青年女工就表示:“我身边嫁给男工人的有,但是不多,也有的收入会比丈夫的高。但我坚决不找本厂的工人。(为什么?)又土又没钱呗。”这种纵向上的不同的根源主要在于宏观层面,包括男女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剩男”现实使得当代青年女工拥有了更加丰富裕如的选择空间、工人的弱势地位强化了当代青年女工对借婚姻来提升生活品质的期待;另一方面,国企制造业青年女工与置处不同空间的打工妹虽然具有相同的择偶意愿,但是前者无疑有着更多的资本与自信来实现这种择偶预期。这种横向上的不同的根源在于微观层面,包括制造业国企中的青年女工多为城市双职工家庭中的独生女,这就使其父母有意愿也有能力向她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婚姻保障而不是拖累束缚;同时,由于对现代城市文化的认同与熟习,制造业国企中的青年女工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更容易找到与理想伴侣的共同点。而家庭支持和自身素质这两方面却是在乡村长大、家庭传统重男轻女、身心图式带有“土气”的打工妹群体所可望而不可即的身份鸿沟。
(二)消费:是“工人”,更是“女性”
在资本、文化与政策等多元合力的作用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性和影响力与日俱增。《2014年女性生活蓝皮书》指出,“女性消费市场潜力极大。据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女性消费者有4.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48.7%,其中在消费活动中有较大影响的是中青年女性,即20-50岁年龄段的女性,约占人口总数的21%”。[20]调查发现:一方面,不同于崇尚“勤俭持家”“省吃俭用”的老一代青年女工和采取既“在局部领域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尤其是身体消费的欲望”,又因收入有限而“挤压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的两栖消费策略的打工妹,[21]在消费社会引发的“她经济”的规训下,制造业国企青年女工受到独生子女的身份、大众传媒的导引和同辈群体的参照等结构性因素影响,社会性地型塑出了她们追求新鲜、追求时尚、追求享受的消费习惯——这与当今城市青年的消费习性并无二致。另一方面,这样的消费习惯其实并不契洽于她们的女工身份,处于较低地位的女工职业并不能满足她们的消费热情。我们调查的Z厂青年女工每月收入在2000-3000元之间,她们普遍表示:“挣得多花得多,挣得少花得少,有把每月工资全花完的,有每月能攒下一些钱的,也有还要父母倒贴的。大部分人都能每月存下一些钱,以备急用,或是攒下钱去大宗消费,比如旅游。而且结了婚的大多会考虑攒钱,因为要还房贷、养孩子,但没结婚的就没有这些压力了。”那么制造业国企青年女工将如何应对并协调其消费欲望与支付能力之间的落差呢?调查对象向我们提供了几种途径:借助丈夫的收入或父母的补贴来对自己的消费给予支持,通过从事产品代理及打理网店等来赚取“外快”,在父母家吃饭以节省饮食开销,适当压缩自己的消费愿望……也就是说,当进行消费时,青年女工会受到自己“工人”角色的困扰,但她们也不会忽视满足自己“女性”属性的诉求。
四、讨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国企青年女工不论是在劳动场域还是生活场域中,均会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身体资本等而培植出独特的习惯。她们在丰富复杂的日常世界中、在结构制约与个体能动的交连互涉中,发展出了这样的实践策略:对工人身份的轻视和对女性身份的重视,这一方面说明性别变量仍然是主导资源配置与机会赋予的强有力社会建制,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女性在职业参与和发展维度上还有很大的作为可能。同时,将制造业国企青年女工与新中国成立后新女性和改革开放后打工妹进行比较研究,也体现了个体命运与结构安排的互动关系:唯有从特定时空情境出发,才能更好理解嵌入其中的个体生命历程;同时,唯有从个体生活实践着手,才能真切把握宏观因素的力量。
回溯历史,“近代产业女工的诞生,使中国妇女界崛起了一支生机勃勃的力量”[22]。我们有理由期待,随着制度的建立健全与观念的更新推动,当代国企青年女性工人能够在主体意识觉醒和政治生活参与等方面发挥出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1][3][5]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85、 17、11.
[2]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57-458.
[4]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3:143.
[6]潘建雷.生成的结构与能动的实践[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1):155-157.
[7][15][18]佟新.异化与抗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61.
[8][12][16]潘毅.中国女工[M].任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214.
[9]罗丽莎.另类的现代性 [M].黄新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10]吴小英. 国家与市场意识形态下的女性沉浮 [EB/OL].http://www.maple.org.cn/tabid/62/ArticleID/554/Default.aspx.2004-11-02.
[11]吴小英.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 2009(2):172.
[13]朱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J].社会, 2008(6):161.
[14]郑丹丹.身体的社会形塑与性别象征[J].社会学研究, 2007(2):159.
[17]严汇、高景柱.打工妹的身份认同:内涵、根源及影响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121.
[19]叶文振、胡峻岭、叶妍.外来打工妹的择偶意愿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6(6):40.
[20]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 2014年女性生活蓝皮书[EB/OL].http://www.womensurvey.com.cn/article-detail-id-1375.2014-05-30.
[21]王宁、严霞.两栖消费与两栖认同[J].江苏社会科学, 2011(4):99.
[22]郑永福.中国近代产业女工的历史考察[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4):15.
When“ Female” Encounters“ Worker”—Taking Young Female Workers in One State-owne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as an Example
Gao Chengxin Liu Ji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Shanxi University )
The young female workers in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significant composition of female workers at present.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ield of workshop which is based on de-sexualization shapes the habitus to embody feminine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female workers;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field of mate-sele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habitus of young female workers are not trapped to their vulnerable condition.No matter in labor or life, facing the restriction of objective condition, young female workers in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use their own capital and cultivate practice strategy to underestimate the identity of worker and appreciate the identity of female, which results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action.
Young Female Workers;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Labor; Life
D432.7
A
1006-1789(2016)01-0062-05
责任编辑 杨 毅
2015-11-27
高成新,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刘洁,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