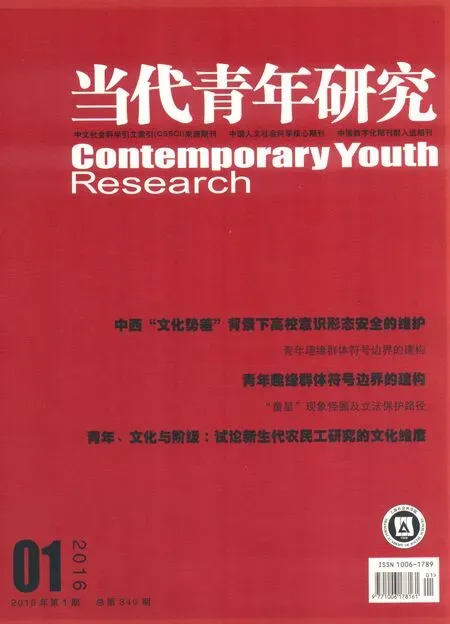儿童家暴社会工作介入的伦理困境
——基于深圳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的实践
2016-03-18张智辉蒋国河
张智辉 蒋国河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儿童家暴社会工作介入的伦理困境
——基于深圳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的实践
张智辉 蒋国河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近年来,儿童遭受或目睹家暴问题越来越突出,是社会工作亟须介入的重要方面,然而,社工在介入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伦理困境,主要涉及社会工作干预与法律、政策、文化背景及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相冲突的问题。基于深圳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的实践和案例,总结出社工在面临相关伦理困境时,需要扮演好政策倡导者、受虐儿童的支持者等角色,以期更好地保护儿童权益,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儿童家暴;社会工作介入;伦理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签约国,但儿童被虐待问题仍未被建构成社会问题,儿童被虐待现象还比较普遍。 全国妇联2013年出版的《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显示,中国家庭虐童的状况十分严重,10-17岁儿童遭到父亲和母亲家暴的比例分别为43.3%和43.1%。“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研究论文《农村少年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现象透析》一文指出,有51.0%的少年儿童被父母打过,经常被父母打的少年儿童占22.7%。在这些存在家庭暴力的家庭中,有18.0%-30.7%的子女遭受过父母的严重体罚,并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除了身体伤害,父母对儿童进行精神暴力的情况也较突出。该调查显示,在遭受家庭暴力的孩子中,父母对子女采取精神暴力(主要是威胁、言语伤害等)的比例达55.6%。[1]2015年以来发生了“南京养母虐童案”“毕节四兄妹生前遭受家暴”“猪栏小洪波遭母亲虐待”等多起典型家暴受虐儿童事件。结合数据和事实我们可以了解到目前儿童遭受或目睹家暴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中共十八大明确指出,保障儿童合法权益,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建立未成年人社会保护制度和使每一个孩子都有公平发展的机会,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通过了《反家暴法》草案,基于此,这对专业社会工作在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建设方面的开展是一种积极信号,为受虐待儿童的社会工作干预提供了法律基础。
据深圳市鹏星家暴防护中心所做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深圳市1600名受访者中18.9%表示在自己或亲友的家庭中存在家庭暴力。在家暴案例中,父母对孩子的暴力高达81%。[2]国务院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所称家庭暴力是指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对家庭成员实施的侵害行为。由国务院法制办面向社会的《征求意见稿》中指出,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神等方面的侵害,草案则没有涉及精神暴力。[3]国外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把语言暴力视为儿童虐待,甚至将儿童忽视也列为儿童虐待的一种。在国内倾向于认为忽视是一种独立于虐待之外的实体,国内相关学者认为儿童虐待就是指成年人采用暴力与非暴力的手段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心理、精神和其他权利并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4]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创意公益广告“今天的暴力语言会变成明天的凶器”,主要讲述父母的暴力语言是带来青少年犯罪的严重后果的重要因素,可见,父母的语言暴力对于儿童所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所提及的儿童家暴是指在家庭成长过程中儿童遭受到身体虐待、精神虐待(语言暴力和目睹家暴)。
二、理论基础
(一)依恋理论与家庭式儿童虐待
Bowlby一开始认为依恋就是年幼儿童对母亲的爱和陪伴的渴望、与他(她)因饥饿对食物的需要相当……依恋是一种“基本的动机系统”,独立进行运作并与其他动机系统相互作用。后来,Ainsworth和Bowlby运用关于人格发展的习性学方法,携手建立依恋理论。他们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假定依恋体系独立于喂食,指出依恋这种行为应该与哺乳及性行为作明确区分,性和食物无法主宰依恋,也无法派生依恋。[5]概言之,Bowlby将依恋定义为个体与生活中特定对象间强烈的情感联系。[6]这种牢固的情感纽带连接的是照顾者和孩子,并且影响着个体的一生,依恋关系对于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依恋理论中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型、依恋类型、强迫性自主、代际传递等核心理念帮助我们理解儿童是如何以及为何与照料者建立亲近关系的,并且为我们理解那些没能体验满意的关系甚至遭受糟糕的依恋体验的儿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7]它强调父母所引起的互动质量,以及互动质量对随后儿童人格发展的关联。
国外有学者把依恋理论列入《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一书,并且他提及了David教授1995的《依恋理论与社会工作实践》,以及1999年焦点于儿童虐待的《依恋理论:儿童虐待和家庭支持》。[8]依恋理论为社会工作在儿童家庭内受虐待领域的探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和方向,为社工介入提供了新的可能。[9]从依恋理论的视角出发,对于在家庭中受虐待的儿童,社工可以修复原有的非安全型依恋关系,或者是帮助他们构建一个安全型依恋关系。依恋理论充分解释了家庭暴力对儿童的不利影响、儿童后期出现各种心理与行为问题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进而可以帮助社工更好地理解家庭式虐待的问题及原因,从而更加有效地找到介入的切入点。社工可以促进父母与子女的良好互动,改善施暴父母与受虐儿童的内部工作模型。
(二)儿童权利理论与家庭式儿童虐待
一般认为,英国人汉娜 • 摩尔于1799年最早提出了儿童权利的概念。[10]她认为,“儿童权利是指儿童拥有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法律身份,以及不同于其父母的利益和需要”。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指出儿童有权享受特殊照顾和协助,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儿童在家庭中成长,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列举了一系列儿童权利,特别指出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受到保护和救济,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联合国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将儿童权利分为四种:生存权、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其中儿童受保护权主要是指保护儿童免受虐待。
就我国而言,学者结合儿童保护视角对儿童权利概念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有的学者提出儿童权利概念应包括下述内容:第一,必须将儿童当“人”看,承认儿童具有与成人一样的独立人权,而不是成人的附庸;第二,必须将儿童当“儿童”看,承认并尊重童年生活的独立价值,而不仅仅将它看作是成人的预备;第三,应当为儿童提供与之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生活,儿童个人权利、尊严应受到社会的保护。[11]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儿童权利是指儿童基于其特殊身心需求所拥有的一种有别于成人的权利,这种权利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可且为正当的,其范围包括受保护权和自主权两个相互依存方面,受保护权与自主权共同构筑了一项完整的儿童权利,两者缺一不可。可见,学者对于儿童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儿童的受保护权。[12]
我国历来重视儿童权利,但现实中儿童权利保护长期只惠及孤儿、残障儿童和流浪儿童,在儿童养育与照顾中,一味强调了家庭的养育与照顾责任,从而忽视了在家庭中受虐待儿童群体,在有的学者看来,他们是得不到家庭良好养育的“事实孤儿”。[13]笔者认为,家庭式虐待儿童问题的本质是监护人对儿童权利的剥夺。从儿童权利的受保护角度,预防儿童虐待事件的发生,及时保护受虐待儿童是全社会的共同义务与责任。
三、社会工作介入儿童虐待问题的伦理困境案例分析
案例1:案主TZE在遭受父亲绑在铁床,被小塑料袋蒙头威胁和闷住的经历后,对父亲产生极度恐惧,有一种“不愿意进家门或者留在家中”“死也不回家”的心理感受,从与他的接触中,发现案主有明显的急躁和低落的情绪,存在常见的自卑、胆小的心理障碍,就像一只躲在枝头的惊弓之鸟。还有他特别容易紧张和焦虑不安。社工基于“保护生命”“最少伤害”的专业伦理原则,如果发现受虐儿童,必须保护案主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以此减少案主的心理创伤。然而,社工介入可能面临的主要是涉及保密原则、专业关系和案主自决的专业伦理困境。比如,施暴者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虐待儿童行为,儿童也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被父母虐待的情况。[14]因为当社工是好朋友才将自己过去及现在的家暴受虐经历相告知,他从来没跟别人说过这些事情,并强调若社工跟任何人说他的事情,便不再当社工是朋友。社工与案主之间的关系是单一的有限关系,一旦出现朋友、伙伴等关系,双重关系便形成。而对于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而言,完全禁止双重关系的产生是不现实的。在中国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中,没有与案主建立亲密的 “朋友”关系是难以让案主信任社工的。但若放任这样的关系形成,则有可能在进一步的服务中产生伦理困境。使专业边界模糊,导致社工的专业角色混乱,或者过分关注案主,或者忽略了案主的实际需要。这样的双重关系无论对案主还是社工都会造成困扰。社工将因“保密原则” 和“专业关系”而陷入介入方式选择的困境。许多被虐待儿童即使受到了虐待,甚至生命安全已经受到了威胁,也不敢离开家庭,宁愿待在父母身边,不愿意去其他救助机构,社工一方面不能让案主身处险境,另一方面必须尊重案主自决,由此陷入伦理困境中。
现有的《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均有禁止虐待儿童的规定,但这是原则性和笼统的,执行法律责任不明确,也就是王思斌提及的“宣称型政策”。[15]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我国还缺乏专门的《反家暴法》和《防治儿童虐待法》 ,这样实际上没有把家庭式虐待儿童上升到法律层面,得不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和重视。饱受诟病的法律残缺往往容易导致执法困难,警察上门束手无策,只是一番批评教育。很多受到或目睹家暴儿童的实际情况是既不符合现有刑法的最低制裁标准,构不成犯罪,对于那些伤情轻微的受暴儿童,施暴者情节较轻,后果不是很严重,又构不成治安处罚,最终造成对施暴者无法采取强制措施,对受暴者无法提供有效援助的局面。还有就是我国《刑法》一方面规定儿童虐待属于自诉案件,也就是“告诉的才处理” 。即对此类犯罪,法律要求是“告诉才处理”,但儿童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几乎无能力自己告诉。虽然 《刑法》 第 9 条对此作出了补充规定,但基于“家丑不外扬”的陈旧观念,受虐儿童的近亲属几乎很少主动向有关部门告发。正是如此,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报案率非常低。在这种缺乏主动告知的情况下,还会涉及人情与法制及传统文化的冲突问题。其中按照社会工作专业守则规定,发现父母提供的环境不利于儿童成长,就立即对儿童施以援手。按照法律规定,在孩子主动寻求保护的前提下,才可将父母告上法庭,剥夺父母的监护权。但是从人情角度考虑,社会对“孩子状告父母” 的行为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孩子是“白眼狼”,会遭到其他人的责骂。社工倘若鼓励孩子状告有虐待行为的父母,往往会陷入人情与法制的冲突中。其中在中国儒家文化中,家庭伦理关系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可以说,儒家文化中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念深深融入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暴力支撑的秩序和权威不可避免地成为保持家庭和谐的必需。[16]不仅是施暴者,就是受虐者中也有许多人接受家庭暴力的存在。当孩子面对被虐问题时,若社工告诉孩子说“你的父母正在伤害你”,是否会强化孩子对父母的敌对情绪呢?在这样的问题上介入,实质上社工要面对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对虐待罪的量刑偏轻。虐待儿童虽然是一种严重的故意伤害行为,但对犯有虐待罪的侵害人仅仅处以最高不超过二年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甚至在出现致儿童重伤死亡的情况下,也只是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17]而同样情形的故意伤害罪,按照《刑法》第234条的规定,最低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最高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造成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在量刑上巨大的差异,在于立法者认为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暴力侵害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要小得多。法律有如此的规定,就意味着虐待儿童是法律所默许或认可的正常行为,本质上就是纵容虐待儿童行为。[18]
案例2:案主LZW经常遭受母亲的“没有用”“去死吧”等语言暴力,在他父亲的陪同下前来寻求帮助,父亲提及母亲对儿子的恶语频率相当高,儿子听到声音,都会害怕得发抖,社工发现这种精神暴力的教育模式,使得案主更多表现出学习散漫、无目标、敏感多疑等。社工的伦理价值要求社工需在改变亲子关系上作出努力。为此,社工尝试与该母亲取得联系,询问可否进行家访聊聊亲子关系,但遭到家长的拒绝。那位母亲甚至指责女儿不应参与儿童情绪教育、非暴力沟通工作坊等发展性小组活动,并以“学习为重”为由不让女儿继续参与,这让社工感到很无助。案主LJC在经常目睹父母之间以及打闹的家暴现象,长期生活在充满争吵和不愉快的家庭里,内心一直感到压抑和愤怒,并且把这种情绪转移到自己妹妹身上,处理手足不和往往采用打闹方式,发脾气恶骂或者推撞妹妹,既对家庭暴力有深深的恐惧和厌恶,又在失望和愤怒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社工分析,长期以来,不少人习惯于把儿童虐待单纯地理解为对儿童身体上的伤害,对精神伤害则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由于这种片面性认知,一些家长经常采取冷落、拒绝、孤立、恐吓的方式对待孩子,自觉不自觉地实施了精神虐待。但是,从上述案主LJC在目睹家暴后所产生的心理恶果,可见社工是很有必要而且必须介入的,然而却遭受到某些家长的各种拒绝。
除此之外,社工还会遭受不打不成材、棍棒之下出孝子、清官难断家务事和法不入家门等传统文化思想的阻碍。社工上门探访经常遇到诸如“我关起门来打孩子,是我家自己的事,外人无权干涉”“丈夫打妻子不对,但打孩子则天经地义,孩子是我生的,自古棍棒之下出孝子,没有家法那还了得”等封建语言的阻挠。更为重要的是,某些儿童不认同父母的体罚属于虐待,而是为了自己好。可见,儿童自身对拥有免受虐待的儿童权利一无所知。比如,妈妈曾经用衣架、扫把、鸡毛扫、皮带、拖鞋等打LZW,LZW当时觉得妈妈很过分;MWS说爸爸曾因他考试不及格而对他扇了几巴掌;HYL说父母曾因作业错太多让他在搓衣板上跪了半个小时,膝盖都流血了。这些非暴力沟通工作坊组员都认为,父母的这些体罚并不是虐待,自己当时的确做错了一些事情,父母是为了自己好。社工分析,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暴力,主要是由于孩子年龄小,在某些时候表现出顽皮或任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孩子不听话”。这时,有的父母可能在教育开导孩子不起作用的时候,当然也可能是在根本没有教育开导的情况下,就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于是孩子在屈从暴力的情况下不得不顺从了父母的意志。这些父母丝毫不重视保护儿童的免受虐待权利。社工工作必须介入诸如此类的儿童家暴,但是也会遭受某些家长或某些儿童的不欢迎。
案例3:社工基于专业伦理有义务、有职业责任将救助的遭受家暴的儿童受害者安置在安全的庇护中心。由于民政部在具体相关政策执行上存在问题,造成难以找到合适的地方暂时或永久性安置这一弱势群体。比如民政部于2014年12月24日发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其中明确了针对受虐待儿童,社工可以提供保护性服务和替代性服务两种类型。保护性服务即通过外部监督、干预性服务等方式,防止儿童被虐待。如儿童保护热线、儿童防性侵服务,为受伤害的儿童提供的庇护和心理干预等。替代性服务即当家庭照顾功能缺失时,针对儿童实际需要,将儿童安排到适当的居住场所,提供一部分或全部替代家庭照顾功能的服务。例如,家庭寄养、收养、儿童福利院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对儿童的安置服务等。笔者曾咨询该中心主任,她认为民政部这个指南发挥作用非常不明显,现在的妇女、儿童遭受家暴庇护站都设立在救助站,里面除了设置不人性化外,还鱼龙混杂,缺乏安全感,入住率不容乐观。在社工实务中确实存在这一伦理困境,无法为服务对象提供到必需的服务。例如案主LWH及其母亲前往中心寻求安全庇护,渴望暂住上一个星期以躲避案主父亲对这母子俩实施的家暴。我们只能尴尬地表示无能为力,深深觉得面对群众呼唤专门的家暴庇护中心时,我们无所作为。还有缺乏安全和人性化的临时保护住处,相当于纵容施暴者。还有民政部对《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宣传不足,比如东莞鹏星家暴庇护中心的F主任还不清楚有相关指南。
除此之外,在经费上政府没有将该项目纳入常规购买社会服务,缺少固定的资金支持,容易存在资金困难与人力资源欠缺问题,间接造成社工无法有效和及时介入服务对象。这也是有的学者指出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中的“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与资源缺乏困窘”伦理困境之一。[20]一方面,虽然先后有深圳市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国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深圳市幸福慈善基金会、深圳市慈善会的鹏星关爱基金、福田区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资助“儿童零暴力成长救助”项目,但是项目结项后,可能出现项目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缺乏继续做实做大该项目的具体规划和措施。另外,社会捐赠非常薄弱。深圳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总部每年要投入一定资金补贴该中心的日常运营和开展服务。另一方面,项目经费不足必然会引起人力资源欠缺问题。目前,该中心只有两名正式员工,其余三名已分别在2015年3月和6月离职,在最新的鹏星招聘中,暂时并无足够资金去新配置项目专员,显然将造成缺乏人力资源服务我们的服务对象。
四、社会工作干预儿童虐待伦理难题的角色思考
社会工作作为服务型治理,通过政策倡导和提供具体服务参与社会治理。[21]政策倡导作为一种社会工作实践,社工必须注重扮演政策实践这一角色,体现出社会工作的“社会”面。[22]社会工作在介入儿童虐待问题时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和原则,一是确保儿童在家庭中不受到伤害,二是确保父母在家庭中的责任和权利不受到损害。
(一)政策倡导
保护受家庭式虐待儿童的前提是国家层面树立公权力介入儿童保护理念,这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在此前提下,国家应该作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倡导。一是加紧制定与出台以预防和发展为取向的《儿童福利条例》,并且注重完善和具体化其中的防止家庭暴力、防止虐待儿童以及家庭支持政策中包括生活救助与家庭津贴等系列规制。二是加快《反家暴法》的征集,尽早出台《反家暴法》,并且未来的《反家暴法》应将目睹家暴儿童受害者纳入保护范围。三是制定颁布《防治儿童虐待法》专门性儿童保护法律。明确儿童虐待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提供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规范,比如强制报告制度。四是国家顶层设计上需要制定出与民政部于2014年12月24日发布的《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相配套的儿童保护制度,比如,建立和财政支持专门的人性化和隐蔽性的家暴庇护中心以及改革儿童收养与寄养法,将遭受家庭式虐待儿童列为对象。针对受虐待儿童,社工可以提供保护性服务和替代性服务两种类型服务。保护性服务即通过外部监督、干预性服务等方式,防止儿童被虐待,如儿童保护热线、儿童防性侵服务、为受伤害的儿童提供庇护和心理干预等。替代性服务即当家庭照顾功能缺失时,针对儿童的实际需要,将儿童安排到适当的居住场所,提供一部分或全部替代家庭照顾功能的服务,例如,家庭寄养、收养、儿童福利院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对儿童的安置服务等。五是加强政府购买反家暴社工援助项目,加大对儿童保护社工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力度。政府应该将“儿童零暴力成长救助”项目列入常规财政购买范围。这种方式可以让项目的资金来源更加稳定。同时,注重扩大和培训儿童保护社工专业人才队伍。
(二)具体服务
在减少法律和政策层面等面临伦理困境上的徘徊与挣扎的同时,注重为施暴者和受虐儿童提供具体服务。一是普及社会反对儿童暴力意识,宣传享有零暴力的儿童生活是每一个儿童的权利,保护儿童免受暴力伤害。鼓励儿童家暴受害者勇敢站出来,主动求助,改变现状,不让家暴陷入死循环。吸引到更多的公益志愿者资源加入到儿童保护中,进而使得反对儿童暴力衍化为社会常态。二是完善保护性与支持性社工专业服务,丰富依恋理论在儿童保护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与开发。在社工介入家暴受虐儿童的实务中,应首先帮助父母,通过对父母的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去帮助儿童。如果仅仅是给儿童增能充权,可能收效不大。[23]如果案主父母认为社工不是“笨蛋”就是“麻烦”,不是提供者就是剥夺者,不是柔软的就是强硬的,那么就要警醒地认识到,分裂正是这些案主的一个主要防御机制。发现案主的防御策略,有利于帮助社工理解案子的走向,尤其是那些有着矛盾依恋性体验的父母。分裂引起了专业社工的冲突性情感,按照Mattinson和Sinclair的说法,得到帮助的愿望与被征服的担心并存。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专业社工感到无力、愤怒,甚至放弃案主,而父母则将暴露社工的无能作为一种满足与成功。[24]David 指出虐待子女的父母表现出的特征:虐童作为他们自己混乱的关系史的结果,拥有焦虑、混乱的人格结构;缺乏社会与情感支持;遭受严重的物质和环境压力等。社工要更加去理解,理解具有强大的力量,称得上是接纳、尊重、同理心的前提和基础。下一步就是帮助父母发现和考虑过去怎样影响当前的情感、思想以及行为以及努力进行认知重构,将关于自我与孩子的世界重新模型化,重新加以理解。给予父母提升并支持养育技巧,显得尤为重要。社工的支持性服务可以协助父母解决问题,如社区可以定期组织父母互助小组和亲子互动小组,父母们交流管教孩子的经验和烦恼,寻求相互的帮助,发展良性的亲子互动模式。
对于被施暴者的儿童来说,他们不仅身体受到了伤害,更重要的是心理受到了不可磨灭的创伤。社工要重视帮助儿童建构有利于认识人与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型。采用依恋理论的语言来讲,就是用心理治疗中产生的新经验帮助儿童调整新的表征模式,改变原来关于自我以及与父母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型。为儿童提供关系服务,以此帮助儿童审视并调整与父母的关系。[25]
[1]王琛莹.面对家暴沉默忍耐会导致更多极端事件[N].中国青年报, 2015-03-23(07).
[2]刘永新.近两成深圳人身陷或闻睹亲人受家暴[N].深圳特区报, 2013-11-28(22).
[3]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草案), 2015-07-28.
[4]皮艺军.“虐童”浅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3(01):13-19.
[5][7][24]David Howe.依恋理论与社会工作实践[M].章淼榕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53-54,73-144,94.
[6]梁熙、王争艳.依恋关系的形成:保护情景中母亲和婴儿的作用[J].心理科学进展, 2014.20(12):1911-1923.
[8]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第三版)[M].冯亚丽、叶鹏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81-87.
[9]何姗姗、杨萍.依恋理论视角下家庭暴力受害儿童的个案研究[J].社会工作, 2015(01):66-73.
[10][12]吴鹏飞.嗷嗷待哺:儿童权利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实践[D].苏州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11]张爱宁.国际人权法专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333.
[13]程福财.保护儿童,国家监护责任不能缺位[N].环球时报, 2013-09-26(06).
[14]牛芳、张燕.社会工作介入儿童虐待问题时遇到的困境分析[J].社会工作, 2013(03):123-129.
[15]高翔.政策相关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以比较中美干预儿童虐待政策为基础的分析[J].东岳论丛, 2015(03):10-15.
[16]俞宁、陈沃聪.关于儿童虐待的文化思考[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1(02):125-129.
[17]吴鹏飞.我国儿童虐待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J].法学杂志, 2012(10):56-60.
[18]曹秀谦.关于家庭暴力的法治思考[J].政法学刊, 2000(04):24-28.
[19]民政部.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2014-12-24.
[20]张晓红.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中的伦理困境——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模式为例[J].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5(07):23-29.
[21]王思斌.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J].中国民政, 2015(03):11-12.
[22]马凤芝.政策实践: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工作实践方法[J].东岳论丛, 2014(01):12-17.
[23]乔东平.虐待儿童: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式诠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281-282.
[25]张智辉、蒋国河.儿童家暴的社会工作介入[N].中国社会报, 2015-08-31(03).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for Children of Domestic Violence——Practice of Anti 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Center of Pengxing in Shenzhen
Zhang Zhihui Jiang Guohe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In recent years, the children suffered or witnessed domestic violence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social work to intervene.However, social worker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vention are faced with many ethical dilemmas, mainly relating to the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laws, policie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 ethics conflict problems.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anti-domestic violence prevention center of Pengxing in Shenzhen, the paper found out that when social workers are confronted with ethical dilemma, they need to play a good policy advocates and the role of supporters for perpetrators abused children.I hope to better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ldren, and promote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Domestic Violence;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Ethical Dilemma
C913.5
A
1006-1789(2016)01-0103-06
责任编辑 杨 毅
2015-10-21
本文系江西省2015年研究生创新专项项目“依恋理论视角下受虐待儿童的社会工作干预研究——以深圳市‘儿童零暴力成长救助’项目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C2015-S204。
张智辉,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保护与社会政策、社区治理;蒋国河,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社会工作、农村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