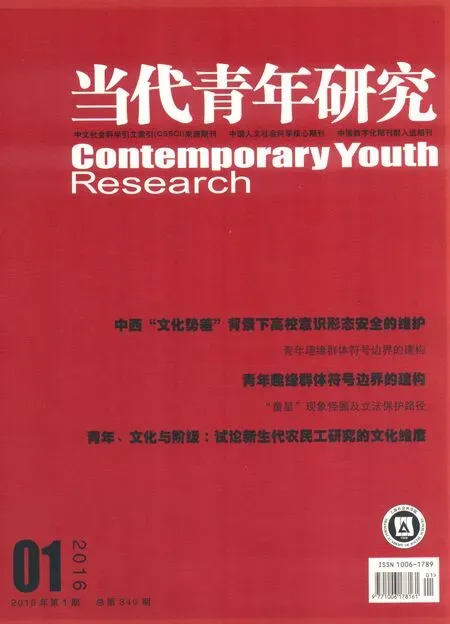网络社会中的愤青现象解读
2016-03-18郑唯
郑 唯
(中国戏曲学院学生处)
网络社会中的愤青现象解读
郑 唯
(中国戏曲学院学生处)
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愤青逐渐成为现实生活中愤世疾恶、个性鲜明的一个群体的代名词。愤青群体的成员构成都极其复杂,公众对其评价也呈现两极化态势。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在愤青现象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赋权作用。通过对愤青参与的热点社会议题的分析表明,政府在相关议题所引发的冲突中是否拥有制度化的解决能力是愤青表现为网络暴民还是积极公民的关键,而政府对于网络议程设置的差异也决定着作为愤青自我赋权场域的网络社会成为发酵场还是安全阀。
网络社会;愤青;愤青现象;赋权
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愤青用他们愤怒的吼声和偏执的话语吸引着大众的眼球,也因其与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关联受到学界的关注。愤青逐渐成为网络社会乃至现实生活中愤世嫉俗、个性鲜明的一个群体的代名词。有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微博上愤青扎堆的时代,也是一个必须保持微微的愤怒才能不显得和其他人太不一样的时代”。[1]尽管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地使用这一标签,传媒和学者也对愤青这一现象表示了强烈的兴趣[2],但对于愤青和愤青现象的学术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这也使得人们往往或是将愤青现象简单视为对于社会问题的愤怒与发泄,或是将其等同于网络社会民族主义的情绪表达。不论是网络社会中的愤青现象还是学界及社会舆论对于愤青现象的评论都呈现众声喧哗的图景。本文以聚焦于网络社会在愤青及愤青现象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对愤青参与的热点社会议题的分析,检视愤青在热点社会议题中的表现以及作为愤青自我赋权场域的网络社会的作用。
一、作为一种现象的愤青及其群体特征
愤青即愤怒青年(The Angry Young),最早指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左翼思潮中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中国的叛逆青年。1973年,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愤怒青年》讲述了一群不满社会现状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表明当时已存在“愤怒青年”这一称谓。后来愤怒青年被简称为“愤青”,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成为流行词。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尽管《中国可以说不》是一本刻意制造出来的粗糙之作,但它确实是合时宜的。“说不”,是表达愤怒的通行手段。国家可以“说不”,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说不”行为以合法性,而且,有可能将“说不”行为上升到民族国家大义的高度来予以肯定。这对愤青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撑。[3]
2002年7月,人民网刊发《“愤青”与“粪青”》。文章认为,“青年的愤怒源于对现有秩序及环境发出的质疑与不满,并非为一己私欲。不满是好事,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由不满而愤怒,由愤怒而鼓与呼,由鼓与呼而达群策群力,而最终达到改良的目的、进步的功效”。
2005年11月,《南方都市报》在《中国愤青:一个病态群体》一文中指出:“哪怕最为理性的‘中国愤青’,基本的精神气质也不脱‘仇恨’二字。最低水平的‘中国愤青’已经变成‘粪青’,只能以满嘴喷粪的方式来显示其爱与恨。”
为了展现中国愤青的真实状况,《瞭望东方周刊》做了“中国愤青们的真实生活”的专题;美国《纽约客》则以“愤青:中国新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为题对中国“愤青”进行了长篇的客观描述。这两篇报道共同反映了愤青群体的内在矛盾:愤青既会追求新闻的客观报道,也会充斥谩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
提及愤青,我们会想到以崔健、韩寒、罗永浩为代表的个人以及中国红客联盟、四月青年等为代表的团体。然而,不论是作为整体的愤青群体,还是某一具体愤青团体,其成员构成都极其复杂。以四月青年为例,这个脱胎于2008年反CNN运动的愤青团体聚集了大量民间爱国人士,已成为国内较有影响力的时政军事愤青团体。其四月社区拥有100余万活跃会员,UV访问量最高近43万,同时在线人数破3万。然而,正如四月网前总编辑胡亦南所言,“我们常被当作盲目效忠国家的民族主义青年,西方评论家也认为我们是理念一致的单一团体”,事实上,“四月青年的背景和想法十分多元,从儒家到基督徒,从托派到毛主义者①指从托洛茨基主义者到毛泽东主义者。,从信仰坚定的死忠人士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机分子,说我们是松散的联盟更为合理”。[4]
那么,愤青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为何而愤怒?对此,新加坡学者杨丽君和郑永年通过对“反CNN运动”“韩寒现象”和“六九圣战”等网络热门事件的分析,指出愤青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民族主义型愤青,这个群体是2008年反对CNN等西方媒体对华不实报道的主要力量;批判中国型愤青,这个群体主要是表达对国内社会问题的不满,韩寒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愤怒发泄型愤青,这个群体主要是网络黑客(如中国红客联盟)等网络群体参与的突发性的网络议题。这三个类型的成员构成、愤怒的原因和针对的目标都存在显著差异。[5]
二、作为愤青自我赋权场域的网络社会
愤青概念自产生以来,许多个体被自我或他人贴上了“愤青”的标签,而其被广泛地用于一个特定的群体则是伴随着网络的迅速兴起而流行的。[6]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与转型,其中,最为剧烈的领域和动力是网络社会的兴起与发展。网民的最大群体仍是青年,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30.7%。我国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数量为4.37亿人,网民中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使用率为70.3%。微博用户规模为2.75亿,网民中微博使用率为43.6%。[7]
虚拟的网络社会和互联网的发展是同步的。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在愤青现象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赋权作用。[8]赋权(empowerment,又译为“增权”)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用语。从心理学的个体动机角度看,赋权是“赋能”(enabling)或是一种“自我效能”,它源于个体对自主的内在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赋能就是通过提升强烈的个人效能意识,以增强个体达成目标的动机,它是一个让个体感受到能自己控制局面的过程。[9]网络社会对于愤青而言是一种自我赋权。愤青多数属于“无权”(powerlessness)群体,如少数群体、边缘群体等。他们利用网络社会的新媒体技术平台,在参与议题讨论中使个体心理和群体意识等层面实现了赋权。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以往被遮蔽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少数群体、边缘群体的声音得以表达。天涯论坛(1999年)、博客(2002年)、新浪微博(2009年)等新媒体的产生和迅速发展使得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和互动交流的机会。如2008年ANTI-CNN网站的创建者饶谨表示,其创建网站的动机源于“和网友聊天的时候萌生出一个想法”。“有网友建议我们应该进行反击,夺回话语权,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西方的民众了解事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0]
网络社会不仅提供了无权群体表达公共意见的机会,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而且增强了网民在虚拟空间建立社交关系型塑集体认同的能力。网站、论坛、贴吧、QQ群、微博、微群等新媒体都成为愤青沟通互动的平台,尤其是2009年以来微博的广泛使用,其自由的关注、转发与评论使得散布于不同地理空间的愤青通过网络互动而结成“想象的共同体”。愤青群体逐渐在网络社会形成一个具有与现实社会同等功能的虚拟公共论坛。天涯论坛、强国社区、四月论坛、博客中国等成为愤青发表公共意见,与不同意见者展开激辩的舞台。此外,他们还广泛借助QQ群、豆瓣小组、微群等新媒体加强互动交流,形成不同派别的愤青共同体。如QQ群“永年愤青@”拥有成员1023人,微群“愤青联盟”成员达3389人。
曼纽尔 • 卡斯特在其所著《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指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1]现实社会、虚拟空间、青年群体三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发生在虚拟空间的、受现实社会因素和群体特征渗透的行为。21世纪“愤青”以网络为依托,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发表自己对社会各种不良现象的愤怒。[12]他们的愤怒来自“不断积累的表达欲望”[13]。“他们认为自己的每句话都那么动听,以至于值得和这个世界分享。”[14]网络社会的兴起赋予网民以机会去表达对社会问题的意见,形成社会网络并组织线上线下的集体行动。于是,许多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不仅自己成为“愤青”,也吸引或者刺激着许多类似的青年人加入这个群体。
三、网络暴民VS积极公民:愤青现象的制度求解
对于愤青现象,《愤青史记》的作者缥缈认为:“只要进入了青春期,对现有社会秩序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满,感到自己的幸福愿望没有满足,愤怒了,就会成为愤青。”[15]对于如何界定愤青,维特根斯坦指出,“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16]从舆论对于愤青的讨论及其对于愤青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愤青可以分为由“奋青”、“愤青”和“粪青”所形成的光谱。在光谱的积极一端,是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气、有正义感和有责任心的奋青。因为有正义和责任在心,才会对不公有愤怒。在光谱的消极一端,则是一群“对国内或国际社会强烈不满,并长期保持一种渴望发泄的愤怒情绪的人”。“粪青”的种种无端的狂暴情绪,已经接近病态。[17]
可以说,愤青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产生以来就处于舆论的争议之中,理性与非理性、网络暴民与积极公民,对于愤青的评价也呈现明显的两极化倾向。一边是对愤青的肯定与鞭策,认为愤青是打破无所不在的社会困境的推动力量;一边是对愤青的担忧与反对,指责愤青滋长的不满情绪往往会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心理基础和驱动力。在一些社会议题中,愤青会成为激愤诋毁、打砸的网络暴民,而在另一些社会议题中,愤青却成为正直善良、勇于担当的积极公民。其间固然有愤青群体自身的复杂性的缘故,而政府在相关议题所引发的冲突中是否拥有制度化的解决能力则是问题的关键。[18]这种制度化解决的渠道包括多个层面,不仅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制度化表达、监督机制,也包括遭遇突发性、群体性社会议题时对网民诉求的回应机制,对网民的动员机制等。要通过宪法和法律框架下的制度化参与引导愤青言行,发挥愤青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如前所论,网络社会对于愤青而言是一种自我赋权,但他们的意见表达需要有制度化的渠道来倾听和反馈。由于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长期积聚的社会不满和愤恨在遭遇某些社会议题时被点燃,借机发泄,进而可能导致暴力行为。[19]“当人们在真实生活中无法表达自己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干脆就把愤怒发泄在其他人身上。”[20]因而,要以制度化的方式将愤青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纳入到问题的解决轨道,通过完善的制度来将他们的愤慨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而不是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以达到短期效果。在此,我们以2012年的保护钓鱼岛运动和2013年的雅安芦山地震为例予以说明。
2012年8月以来,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冲突不断,日本政府擅自将我国钓鱼岛宣布“国有化”的行迹激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很多愤青团体动员参与了以“抵制日货”为名的游行抗议活动,在抗议活动中出现了暴力打砸以至伤人等问题。而在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后,网民不仅第一时间发布救灾信息,还对灾区学校的建筑质量等问题进行了质疑。愤青在两次社会议题中展现出不同的形象。对于“抵制日货”的参与者而言,他们缺乏参与技能与规则意识,又没有得到及时的引导,当被动员参与抗议活动时就成为“乌合之众”,以至发生暴力问题。而在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政府对于如何引导网民发布救灾信息,如何回应网民质疑积累了相应的经验。在政府主导的参与、动员和反馈机制中,网民在芦山地震救灾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四、发酵场VS安全阀:愤青舆论与议程设置
网络社会作为愤青自我赋权的场域,在愤青现象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与公众对愤青的态度相似,对于愤青的网络公共参与是加剧还是缓和了相关议题以致社会紧张,网络社会是愤青现象的发酵场还是安全阀,学术界对此存在两种看法。一方将网络社会视为“发酵场”,认为网络使得愤青群体的观点与情绪相互感染,形成团体的极化现象,从而激化社会问题,加重对议题针对组织(政府、企业等)的不满,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则倾向于将网络社会视为“安全阀”,认为网络社会给予了愤青发泄不满和表达自我的机会,当他们表达发泄之后就不会再冲击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此外,网络社会将促进公民意识的觉醒,理性的公民将在现有社会秩序框架内推动社会的进步。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概念由詹姆斯 • 斯托纳于1961年提出。群体极化是指在群体决策中,经过群体讨论产生的群体意见比个体最初的偏向要更加极端。[21]研究表明,群体极化现象不仅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网络社会中的群体极化现象更加突出。凯斯 • 桑斯坦指出:“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22]愤青群体在网络社会就某一热点议题进行讨论时,为了使自己的观点得到他人的关注、转发、点赞、回复,他们会以夸张、渲染甚至扭曲事实的方式表达受到众人支持的观点,观点越是鲜明、激烈,引起的群体情绪就越高涨。而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民的言论与责任呈现非对等性,愤青敢于抛离现实社会的权威等级、道德规范等束缚,以极端的方式张扬个性、挑战权威。在群青激愤的氛围中,愤青群体将悬置事实本身,而聚焦于对事实的极端化解释,互动中的情绪渲染使得网络最终成为愤青讨论的发酵场。
愤青群体在网络社会中渲染和制造的议题冲突是否仅仅是一种破坏性的因素?对此,科塞认为,冲突对于社会团结、整合同样具有积极作用。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科塞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的概念。他认为,安全阀机制可以使社会不满情绪得到发泄,主动为社会冲突提供可控的、制度化的“出口”,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科塞还指出,“安全阀制度的使用会导致对行动者目标的替代:他不再需要将目标放在解决令人不满意的状况上,而仅仅是要求释放由此所产生的敌意”。[23]可以看出,网络的表达平台使得愤青得以宣泄自己的不满和愤慨,防止了矛盾的压抑和积聚,从而避免引发不良社会冲突的可能。此外,虽然“围观就是力量”,但围观的看客身份和心态使得这一群体缺乏稳定性。在短暂的宣泄之后,愤青群体的狂热情绪将恢复平静。2008年5月,在“四月青年”风起云涌后的短短一月内,“反CNN”的日均IP访问量即从顶峰的500万骤降到不及10万。
那么,网络社会在愤青现象的发展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愤青的网络公共参与是加剧还是缓和了社会紧张?我们认为,网络社会既可以是愤青现象的发酵场,也可能成为愤青现象的安全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在愤青所参与的具体热点议题中的议程设置。在此,我们可以对比“甬温7.23动车事故”和“北京7.21暴雨”两个案例中政府对于网络议程设置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结果。
7.23动车事故的最初信息源是由名为“sam_苗”的新浪博友发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微博个体是主要的信息传播主体之一。针对政府公布信息不及时、不透明,甚至通过删帖隐瞒事实的做法,愤青在“愤青联盟”“博客中国”“天涯社区”展开了激愤的讨论,网络上出现了大量负面言论,使得质疑政府公信力的言论在网络不断发酵。而在北京7.21暴雨事件中,以《人民日报》、“北京消防”等为代表的政务微博,及时、权威地发表灾情、路况、救助信息,为整个暴雨事件的舆论讨论设定了议程,尽管仍存在对预警信息发送等问题的质疑,但69%的“激动、愤怒”类微博在7月21号以后暴雨灾难并未过去的3天中几乎再也没有发布、转发过。[24]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微博政民互动典型案例分析报告》和《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的数据显示,动车事件中“批评铁道部救援(29%)”“反思总结教训(12%)”和“呼吁查清真相(12%)”的负面言论共占53%;而北京暴雨事件中“对北京排水系统不满(22%)”和“政府对暴雨预警不足(16%)”的负面言论共占38%。[25]
议程设置在舆论引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愤青在热点议题讨论中的观点倾向有着重要影响。当政府及时、透明公开相关信息,将政府决策及进展转化为舆论关注的议题,并就重要问题与网民展开互动,从而为议题讨论设定议程时,愤青的讨论则会受到网络上大量的关于已设定议程、议题的影响,尽管他们的讨论仍可能激烈甚至偏激,但在海量设定议题的讨论中呈现“沉默的螺旋”现象,从而不会造成矛盾激化。反之,如果政府拒绝公开信息,甚至删帖、屏蔽相关信息,那么,政府行为会在网民尤其是愤青中激起广泛的不满,愤青的激愤言论在网络的关注、转发等互动中将引导公众舆论,使网络舆论抗议以至挑战政府在该问题处理中的权威。
[1]大头.看:微博小愤青[N].申江服务导报, 2011-9-14.
[2]涂释文.中国愤青们的真实生活[J].瞭望东方周刊, 2005-11-07;卢波.和谐社会建设语境中的“愤青”“恶搞”现象评析[J].中国青年研究, 2007(6):69-70,87;山小琪.新世纪“愤青”与青年的爱国主义[J].中国青年研究, 2009(1):17-20;梁昕.理性与非理性之争——对网络愤青行为的社会心理学解读[J].当代青年研究, 2011(5):6-10,5;E.Osnos, Angry youth: the new generation’s neocon nationalists[J].The New Yorker, 2008.07.28;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Understanding China’s angry youth: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onference, 2009-04-29; Yang, Lijun and Zheng, Yongnian.Fen Qings (Angry Youth) in Contemporary China[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2:637-653.
[3]张闳.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J].南都周刊, 2007-07-20.
[4]杜强.四月青年维权记[J].南方人物周刊, 2013-10-14.
[5]Yang, Lijun and Zheng, Yongnian.Fen Qings (Angry Youth) in Contemporary China[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2:637-653.
[6]孙忠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愤青[J].职业技术教育, 2005(11):28-31.
[7]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4-7.
[8]G.Yang.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J].Asian Survey, 2003:405–422.
[9]丁未.新媒体赋权:理论建构与个案分析——以中国稀有血型群体网络自组织为例[J].开放时代, 2011(1):124-145.
[10]东方时空.正告CNN:网民为什么愤怒?[Z].CCTV, 2008-03-31.
[11]曼纽尔 •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569.
[12]山小琪.新世纪“愤青”与青年的爱国主义[J].中国青年研究, 2009(1):17-20.
[13][20]E.Osnos, Angry youth: the new generation’s neocon nationalists[J].The New Yorker, 2008-07-28.
[14]李林容、黎薇.微博的文化特性及传播价值[J].当代传播, 2011(1):22-25,34.
[15]缥缈.愤青史记[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封二语.
[16]路德维希 •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25-26.
[17]廖保平等.中国谁在不高兴[M].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9:6;廖保平.打捞中国愤青[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0.
[1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43-50.
[19]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9(1):1-5.
[21]Stoner J A F.A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Decisions Involving Risk[D].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1.
[22]凯斯 • 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50-51.
[23]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9:31-34.
[24]李路.微博的舆论集聚模式与反思——以“7•21北京特大暴雨”的微博传播为例[J].人民论坛(中旬刊), 2013(1):178-179.
[25]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微博政民互动典型案例分析报告[R].2011-8;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2 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R].2012-12.
Interpretation of Young Cynic Phenomenon in the Internet Society
Zheng Wei
(Student Department, National Academy of Chinese Theatre Arts)
With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ynic has become synonymous with a group of real life cynical hate and distinct personality.The group members of young cynic are extremely complex and the public evalua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polarization.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especially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young cynic phenomenon play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empowerment.The analysis of the cynics in the hot social issues showed that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institutionalized solving competence on related conflict is the key of young cynic’s choice to be network mob or active citizenship, and the government’s differences in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also determines the social networks as cynical selfempowerment field to be a fermentation or safety valve.
Internet Society; Young Cynic; Young Cynic Phenomenon; Empowerment
C913.5
A
1006-1789(2016)01-0056-06
责任编辑 曾燕波
2015-11-27
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高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传统艺术院校大学生深度辅导工作的目标管理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一般课题“传统文化政策发展趋势对艺术院校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BJSZ2015YB46。
郑唯,中国戏曲学院学生处,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校德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