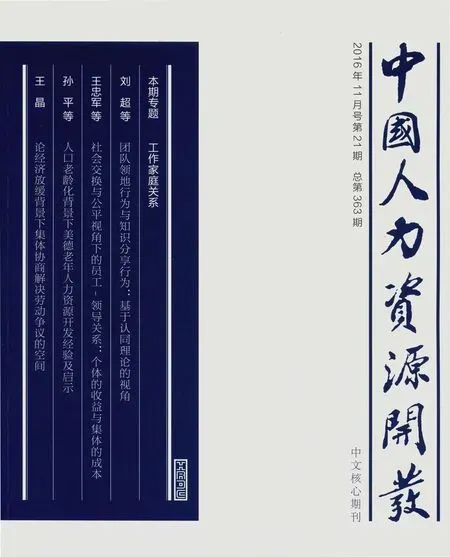国家、资本与劳工:中国集体协商制度发展的形塑力量
——基于文献的思考与启示
2016-02-13雷晓天
● 雷晓天
国家、资本与劳工:中国集体协商制度发展的形塑力量
——基于文献的思考与启示
● 雷晓天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集体谈判制度向来是产业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然而丰富的西方集体谈判制度研究并不能对中国情境下的集体协商制度进行完全有效的解释。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资本与劳工三股力量共同形塑着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的发展方向。国家确定了集体协商制度的基本框架,而中国集体协商的制度空间能否被逐渐拓展需要考虑工会实践、工人抗争行动和资本力量角逐等多重因素。
集体协商 驱动力 变革空间 文献综述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集体谈判制度向来是产业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自引入至今,经过30年的发展,基本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随着协商制度覆盖范围、集体合同签订率的不断提高,集体协商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经历了市场化洗礼后的中国集体协商制度发展至今,到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否仍然保持党政主导的形式化特色?影响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发展与变革的因素有哪些?围绕“中国集体协商制度如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对集体谈判研究领域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试图探寻中国集体协商制度发展的驱动力、变革空间及边界。
一、西方对集体谈判制度的经典论断
1.集体谈判是工会维持和提高会员工作条件的途径
集体谈判的实践活动是19世纪英国的产物(Hyman,2001)。近一个世纪以前,韦伯夫妇(Sidney Webb and Beatrice Webb)就在其经典著作《产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中提出了集体谈判的概念。他们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工会和集体谈判就不会消失。由工会代表具有集体力量的工人群体同雇主进行谈判,相较于单独的个别劳动合同,工人可以争取到较高的工资水平。集体谈判不仅可以避免劳动者之间的恶性竞争,还可以保护个体劳动者的权益不受雇主侵害(F. David,2008)。因此,集体谈判可被视为工会维持和提高其会员工作条件的手段之一。韦伯夫妇也认识到集体谈判是一个规则制定的过程,这为多元主义(pluralism)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渊源与基础。他们提出“共同规则”(common rules)的概念来描述工会的目标,而集体谈判是工会推动共同规则的重要途径与策略(Webbs,1914)。
2.集体谈判是缓和劳资冲突的手段
早期大量的集体谈判研究侧重其缓和劳资矛盾、规范劳资冲突的功能。这种研究为工会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使集体谈判成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双方解决冲突的主要手段。
“产业关系之父”康芒斯主张对经济过程持一种冲突而协商的观点。制度经济学家主张在劳动关系主体以及公众利益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问题(Commons, 1909; Perlman, 1928;Parsons, 1991)。他们认为既然劳资双方在进行着无休止的竞争,那么社会就应该建立规则制度来缓和这种冲突。这种规则制度的建立必须使双方都能接受,这就应该由劳资双方自己选出代表去制订,而不是依靠法律或外部规则。
3.集体谈判制度是规则制定的过程
集体谈判实施的背景是工业社会中不同利益的多元集合,产业关系多元主义者给出了集体谈判的经典理解。在多元主义者看来,集体谈判是规范和调整劳资之间利益关系的最佳选择(Dunlop 1958; Bell 1962; Galbraith 1972; Fox 1973,1975; Kerr et al. 1973)。Harbison(1951)在20世纪50年代讨论集体谈判的目标和策略时提出,劳资双方既存在利益冲突又存在利益一致,集体谈判实际上是将利益冲突协调为利益一致的一种结构化过程。集体谈判是多元主义社会中的一项关键制度,是产业关系中冲突与合作基本原理的产物(Mann,1973;Banks,1974;Fox, 1975)。
在多元主义的视角下,集体谈判并不等同于市场中的讨价还价,集体合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谈判,集体谈判的本质是劳资双方通过力量博弈最终制定规则的过程(Flanders,1968)。John T. Dunlop在1958年的《产业关系系统》(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中提出劳动关系系统中的主体——劳方、资方与政府,通过力量的对比与互动输出劳动关系系统的规则网络(web of rules),而集体谈判、调解、仲裁和立法则是制定规则网络的过程。他认为建立产业关系制度的目标就是将劳资冲突转变为一种有规则的程序,而集体谈判是实现这种规则程序的基础。
Fox将集体谈判以及工作场所的产业关系模式分为四种类型:传统模式(traditionalist)、精细的家长制模式(sophisticated paternalistic)、精细的现代模式(sophisticated modern)以及标准的现代模式(standard modern)。,不同类型的集体谈判类型既有差异又有相似之处。他们之间的差异受到劳动关系系统中多种变量的影响,如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从属关系、劳资双方的行动准则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还是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是一元论的还是多元论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独裁式的还是协商式的等(Storey and Sisson 1993; Purcell and Sisson,1983; Guest,1990)。他认为,集体谈判不仅是经济过程,还是一个政治过程,是组织之间力量比较的关系(Fox,1975)。
4.集体谈判是产业民主的核心过程
产业民主的概念被引入到集体谈判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赞同集体谈判是产业民主的核心过程(P. Ackers, 2007)。Hugh Clegg(1976)提出了分析产业民主的新途径。他的理论来源于澳大利亚、法国、瑞典、英国、美国和德国六个西方国家的数据。他认为集体谈判是工会参与企业管理的一种形式,集体谈判是一个类似“共决制”(co-determination)的过程,每一次的集体谈判都是为了达成联合决策。他通过分析工会与集体谈判发展了韦伯夫妇关于产业民主的理论,同时他强调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并不是与产业民主不相关的问题,反而能对产业中的民主社会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他认为集体谈判制度的种种差异造成了各国工会的不同行为,这些差异包括谈判的程度(即某一企业或某一行业中集体谈判的覆盖程度)、集体谈判层面(即企业层面、地区层面或国家层面的集体谈判)、国家对集体谈判的控制程度(即政府机构是如何监督集体合同实施的)。随后的产业关系研究者开始主张借由集体谈判走向产业民主,提倡工人与工会参与到管理决策的制定中(Derber, 1977; Ogden, 1982)。
5.集体谈判是企业管理者与企业工会的策略选择
众多美国产业关系学者认为微观的产业关系和集体谈判可以被看成是双方主体即企业管理层和企业工会的策略选择。他们强调工会对管理的认同与合作需要以工会在企业经营决策的参与为前提。因此,工会需要将新的利益表达和代表的形式与传统的利益代表方式相结合(Kochan et al., 1986)。Kochan一直倡“战略选择模型”,该理论模型更注重对企业层面上的劳动关系主体的选择行为进行分析。企业层级的劳动关系的制度化结构被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中观层面上的战略选择就是集体谈判,而宏观和微观分别是战略活动和工作场所活动(Kochan, 1980; Kochan et al., 1986)。
二、集体谈判制度研究的中国情境
西方文献对集体谈判制度已有丰富的研究与认识,然而这些研究并不能直接解释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的特点与本质。中国工人的利益代表工会具有独特性;而我国集体协商或谈判的内容也与西方的集体谈判存在较大差异;而协商或谈判中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也与西方明显不同(Ronld C. Brown, 2006)。对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的研究必须要考虑特别的情境因素。
(一)“国家主导”式的集体协商模式
自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确立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协商制度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集体谈判实践中,尽管劳资双方的行为要遵循政府所制定的规则与程序,但双方所选择的谈判决策与最后达成一致的谈判结果仍然由劳资双方通过力量博弈来决定(B. D. Mabry, 1965)。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集体协商的“国家主导”模式存在高度认同。
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的引入是一个充满行政化色彩的过程,党和政府才是推进集体协商制度的主要动力(M. Warner, Ng Sek-Hong, 1999;S. Clarke, Chang-Hee Lee and Qi Li,2004)。大量研究普遍认同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并不是劳资双方自下而上利益博弈的产物和劳资冲突的结果,也不是劳工运动制度化的产物,而是由政府先入为主,依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制定并推行的制度(M.Warner, Ng Sek-Hong,1999; S.Clarke, Chang-Hee Lee and Qi Li, 2004; 常凯,2009;吴清军,2012)。在中国的集体协商中,企业管理者和工会都要服从于政府的直接指导,工资和雇佣条件的最终确定亦受制于地方政府实施的准则。这种“国家主导”模式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的道路,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李琪,2003)。
在制度引入最初,党组织起主导作用,集体协商的程序与内容均要遵从上级政府、上级工会的干预与控制(Ding and Warner,2001)。集体协商主要是依据政府或上级工会组织自上而下的要求进行的,而不是劳资冲突的结果和制度化的过程(Chen,2007)。由于基层工会不能够完全摆脱企业管理层的控制,并且不能真正代表其会员的利益,所以,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无法为新的产业关系系统提供制度框架(Clarke,Lee and Li,2004)。
国家之所以要推行集体协商制度,是希望借助工会在越来越多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延续国家对基层劳动关系及产业秩序的干预和控制(Ng Sek-Hong and Warner, 1998)。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管理者和国家之间利益协调的行政管理框架。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这一行政管理框架逐渐消亡。随后而来的是单位制的解体,为了填补政府从企业中撤出后的空白,同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国家积极主动地推动集体协商(Warner and Ng,1999)。工会发挥政府政策沟通与执行的“传送带”(transmission belt)作用。而集体合同的作用不仅是规范和稳定企业中的劳动关系,还能够使工资水平避免巨大波动保持在稳定的状态,以预防社会出现不稳定。(Ng Sek-Hong and Warner, 1998)。国家推行集体协商制度一方面为了预防罢工等劳动争议的出现,另一方面希望培育新“一元主义”(neo-unitarist)来鼓励企业层面集体谈判的发展(Warner and Ng,1999)。
此外,国家推行集体协商制度的目的是党和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而建立起来的解决劳资冲突的合法化渠道(Clarke, Chang-Hee Lee and Qi Li,2004)。集体协商是建立在企业与劳动者“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提倡对法律规范的共同遵守。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将“民主参与”的概念引入到集体谈判制度的研究之中,他们认为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与推动集体协商工作的目的一方面是试图借助员工民主参与企业管理的手段来保证基层劳动关系的和谐(Zhu and Warner,2002),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为工会民主参与企业管理提供合法化的手段与途径(Clarke, Chang-Hee Lee and Qi Li,2004)。工会将集体协商看作是民主参与管理的延伸以及在逐渐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中规制劳动关系的主要手段(Li Qi,2000)。
然而,集体协商在规范劳动关系方面起到的作用却非常有限。在协商中,无论是企业管理者还是工会都不能自由地代表雇主和劳动者的利益,协商的双方均持续受到党政的指导,无论是直接的指导,还是通过上级工会。企业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最终确定都受到地方政府实施标准的制约(Clarke, Chang-Hee Lee and Qi Li,2004)。大部分集体协商并没有实际的协商过程,制定的集体合同照抄照搬政府部门提供的范本(Warner and Ng,1999;程延园,2004)。工会在集体协商中并不代表工人,也不能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及待遇,其作用仅限于基本劳工标准的监督者(Li Qi,2000)。集体合同条例中的表述也明确指出在我国通过集体协商的过程签订集体合同而不是通过集体谈判的程序(Warner & Ng,1999)。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无法“为新的产业关系系统提供制度框架”,除非基层工会能够完全摆脱企业管理层的控制,并且真正代表其会员的利益。如果上层工会不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提高基层谈判能力,那么很难有所变革(Clarke, Chang-Hee Lee and Qi Li,2004)。这样的一种集体协商必然导致集体合同陷入形式化的困境。由于雇主的反对,集体合同中并没有引入任何实质性的细节;集体合同的起草和制定过程中也没有工人任何形式的参与,工人被排除在集体协商的过程之外。在这样的制度中工人无法获得有效的沟通途径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和不满(Clark, 2002;Tsui, 2006)。而在劳资关系可能最紧张的非公有制企业中,集体协商并没有真正建立企业,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二)集体协商中的工会角色
虽然中国工会自身在不断进步并在集体协商制度的推进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Lee,2009),但是集体协商中工会的角色仍受到多方质疑。
工会虽被视作集体谈判的合法主体,但中国的企业工会通常仅是完成了作为劳动关系法律规制体系一部分的责任(Clarke, Lee and Li 2004),工会无法为会员争取更多的利益。Howell(2008)认为民主工会的模式很难在中国维持和推广,由于企业工会在代表性方面的结构性缺陷,在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谈判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上层工会不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提高基层谈判能力,那么集体谈判制度与工会很难有所变革(Clarke, Lee and Li 2004)。
一方面是由于工会对党政力量的依赖,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工会都需要党政力量的支持。工会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对企业施加压力,使企业同意工会在集体合同中提出的建议(Clarke, Chang-Hee Lee and Qi Li,2004)。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工会对企业管理层存在依附性,其在工作场所的功能局限于管理功能(Biddulph and Cooney 1993; Chan2000; Ding et al. 2002; Li Qi 2000; Zhu 1995; Zhu and Campbell1996)。工会将经济发展作为其首要职责,代表管理者鼓励工人提高生产力、监督劳动纪律并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保护员工的权益”仅仅体现在监控企业管理实践,以确保企业行为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实施员工福利,如看望生病职工、处理员工个人利益分配问题、组织野餐和安排庆典等。工会俨然呈了企业管理层的一部分(Cooke 2002)。在企业层面工会对管理层的依赖成为集体协商制度在规范劳动关系方面发挥作用的最大障碍(Clarke, Chang-Hee Lee and Qi Li,2004)。而工会的这一角色也阻碍着集体协商向真正集体谈判的发展(Ng and Warner,1998)。同时一元化的中国工会,其谈判能力也受到质疑。中国工会缺乏谈判资源的支持,谈判能力和技巧水平不高,急需专业化的技巧培训和支持性的基础设施。工会需要建立全国性的数据库,掌握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Warner and Ng Sek-Hong,1999)。
三、中国集体协商制度发展变革的驱动力
经过30余年的快速市场化进程,中国集体协商制度建立之初所面临的环境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劳动关系正经历由个别向集体转型的过程,工人群体的诉求出现由权利诉求向利益争议的转向(常凯,2013)。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意识、集体行动能力以及集体组织能力都在发生变化,集体劳动争议开始呈现高发态势。这一系列的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集体协商制度本身的变化。
(一)劳工抗争力量对传统制度框架的冲击
2010年以来,我国沿海多地发生罢工事件,这些事件大部分也是通过劳资谈判得到了解决(Chan , 2010;李琪,2011)。一种特殊形式的集体谈判出现,即通过工人集体行动的方式改变劳资对话的现状,通过罢工把企业带到谈判桌上。罢工行动被视为启动集体谈判的“潜机制”(李琪,2011),而这种类型的集体谈判被称为“事后协商”模式(任小平、许晓军,2008)。在这种模式下,工人选出了自己的谈判代表并提出了明确的谈判诉求;资方愿意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劳资之间的分歧并开始重视工人的诉求;政府在劳资双方之间进行积极的疏导与协调(冯祥武,2012)。与那些形式主义的数字化的集体合同相比,以工人为直接主体开展的集体协商,是一种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双方对等的集体协商谈判(常凯,2011;路军,孟泉,2011;谢玉华,2011)。
“罢工启动的集体协商”日益成为地方政府处理劳资争议的常见方式,进一步推动传统劳动关系意识的转变。劳动关系各方主体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劳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建立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对于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至关重要。而制度化的集体谈判是化解当前劳资冲突的有效途径。从工人集体行动到集体谈判的过程意味着集体谈判作为一种制度化机制已经取代了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机制(路军,2013)。
工人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压力促使工会角色转变。大连罢工潮迫使工会进行制度改良。在长期的劳资博弈中形成了“说和人”的工会运作模式:企业工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聚集工人意见并凝结力量,然后以中间人的姿态在劳资双方进行沟通(孟泉,2012)。企业工会一定程度上从既要代表工人又要严重依附于企业管理方的双重压力中解脱出来(Chen,2010)。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工人的罢工也迫使部分企业重建了工会,在汽车零部件业表现尤为明显(Chan & Hui,2012;吴同、文军,2010;汪建华,2013;汪建华、孟泉,2013)。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工厂体制中的迅速崛起以及工人集体行动的压力也成为推动基层工会直选的重要力量(闻效仪,2014)。
(二)集体协商制度变革的政策建构
同自下而上的底层劳工抗争并存的是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建构。全总开展的扩大集体合同覆盖面的运动和提高企业劳动关系“制度密度”(institutional density)的运动与政府推行的“重新平衡”经济政策是完全相符的。新型的集体谈判实践对工资和其他劳动条件的问题都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工会利用国家权力去提升了工资和雇佣条件。在这背后都是政府减少不公平和促进消费的宏观经济目标,它的政策性目标就是构建和谐社会(Chang-Hee Lee, William Brown and Xiaoyi Wen,2016)。当如何维护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的稳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时,工会因势利导地退出针对中小企业的区域性和行业性的工资集体协商,以配合政府解决稳定性的问题。全总力推的区域性和行业性的工资集体协商既可以通过集体合同对劳动法律的执行进行监督,又能够起到稳定区域劳动队伍的作用(谢玉华,郭永星,2011;闻效仪,2011;吴清军,2012)。为了配合产业转型,劳工政策也必须做出调整,提高劳工稳定性和责任感,以达到更充分的在经济上调动工人积极性的目的,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也构成了政府支持并推动工会直选背景(闻效仪,2014)。
新生代农民工发起的越发激烈的集体行动正在不断拓展着现存劳动关系制度的边界。集体行动的走向取决于政府的制度化能力(McCarthy & McPhail,1998)。地方政府正越来越多地尝试对罢工事件“去政治化”(常凯,2010)。政府力量以经济的逻辑解决劳资矛盾,劳资自治以及对等的谈判空间才会真正出现。集体谈判作为这样一种制度化治理机制,其有效性在我国已经得到很好的验证,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人集体行动制度化治理的空间和能力(路军,2013)。
(三)行业集体协商中的雇主
对集体谈判的研究普遍缺乏对雇主和雇主组织的研究。Flanders(1970)认为韦伯夫妇在其理论中忽略了雇主对集体谈判的兴趣,仅仅把集体谈判作为工会活动的一种手段。对于雇主而言,集体谈判所追求的稳定性、可预见性与一致性恰恰是雇主有效控制生产的先决条件,同时正式的谈判和争议解决程序能够有效化解工人的敌意(herding,1972)。
在中国已然出现了推动集体协商的雇主力量,这多见于行业集体协商的过程之中。一些实证研究得出了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对工人工资增长作用甚微的结论(谢玉华,2012),这是由于此类协商亦源于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其本质目的是完成集体协商的总体目标(吴清军,2012)。当然,也有许多学者通过对行业集体协商的案例研究探寻出了工会改革的线索(Lee at al, 2015; Pringle, 2011)。行业工会可以有效避免雇主在企业层面对集体协商的干预和控制,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代表性,从而可以发起多回合谈判的集体协商(Liu,2007)。浙江温岭羊毛衫行业集体协商是引起学者广泛研究的典型案例。有学者重点关注了该行业工资协商中雇主的角色与作用。雇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具备了寻求一种新途径来弥补市场失灵、避免恶性竞争和化解劳资矛盾的动力。集体谈判就是这样一种有效途径,它使工人从“无序抗争”转变为“有序遵守”(Wen & Li,2015;闻效仪,2011)。
四、集体协商发展的制度边界
在国家、资本、劳工三种力量的驱动下,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正在经历着变革。然而,这一系列深刻变化能否孕育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以上的集体谈判制度呢?“罢工推动的集体谈判”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协商模式呢?工会实践的改革是否面临乐观前景?
首先,“罢工推动的集体谈判”对集体协商制度的实效性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启动谈判的“潜机制”对工人、管理方和政府而言均带了高额的集体谈判成本。只有对现有的集体协商制度框架进行彻底的改革才有可能使工人的诉求与愿望得到制度化的沟通与表达渠道,进而才能对“潜机制”起到抑制的作用(李琪,2011)。“罢工推动的集体谈判”的显著特点是“先罢工后谈判”,这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先谈判后罢工”的逻辑截然相反(李琪,周畅,2011),因此虽然该模式日益成为地方政府处理劳资事件的常见方式,但却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这种方式转变为一种长期性制度化的集体协商模式并不具前景。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党政主导的集体谈判”,将与以前盛行的“形式化的集体协商”“罢工引领的集体谈判”共存,西方国家意义上“工人主导的集体谈判”在近期很难实现。(Chan & Hui,2012)。我国工人罢工行为实现了劳动关系中的各主体的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的重构,催生出“制度化效应”,但却未能形成“制度化结果”(孟泉,2015)。
其次,研究者对企业工会改革和政府推进集体谈判的实践持悲观论调。工人很难通过自身的团结行动进一步影响企业工会的日常实践和组织架构,即便选举了工人代表也并没有改变劳方代表性组织缺位的状况,工会仍然没有摆脱对地方政府和全球资本的依附关系,推动工会民主选举的社会力量也非常缺乏(Howell,2008)。政府及地方工会,仍然主导了企业工会的选举和集体谈判。政府重组工会、推行集体谈判的兴趣,与其说是为了迫使资本对工人让利,不如说是为了消除潜在的集体抗议行动,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政治上的有效控制。
最后,权利实现的政治空间。国家自上而下制度建构具有稳定性与牢固性。集体协商制度的发展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以何种机制使劳工三权得以实现。工人集体劳权实现的根本机制是有限的劳工意识和地方政府在经济、政治发展的原则之间的互动作用,导致了权利实现的政治空间的形成(孟泉、路军,2012)。现阶段,国家对于工人罢工权的谨慎态度导致集体谈判缺乏必要的压力手段,所以也很难有西方意义上的集体谈判。
五、结论
国家与民众、统治精英与底层的互动,共同塑造了社会转型的方向(Lee,2007;孙立平,2002;吴同、文军,2010)。中国的集体协商不是任何一个主体的“独角戏”,自下而上的底层劳工抗争、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建构以及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的资本力量共同形塑着我国集体协商制度的发展方向。虽然制度空间在反复的工会实践和工人抗争行动中被逐渐拓展,然而在中国情境下,孕育真正意义的集体谈判的制度发展空间并不是完全打开,国家、资本与劳工的力量格局与互动框定了制度空间的边界。
1. 常凯:《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2. 常凯:《罢工权立法问题的若干思考》,载《学海》,2005年第4期,第43-55页。
3. 程延园:《集体谈判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 冯同庆、王侃、闻效仪:《“事后协商”与“事先协商”——一种始于自发而被推广还可创新的模式和经验》,2012年第9期,第4-14页。
5. 李琪:《启动集体谈判的“潜机制”》,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年第2期。
6. 路军、孟泉:《过渡中的博弈机制——第二次“南海本田”集体协商的启示》,载《中国工人》,2011年第6期,第4-6页。
7. 孟泉、章小东:《制度化结果还是制度化效应?——中国工人罢工状况及其解决方式的启示》,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5年第19期。
8. 孟泉、路军:《劳工三权实现的政治空间:地方政府与工人抗争的互动》,载《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2年第3期,第89-93页。
9. 孟泉:《塑造基于“平衡逻辑”的“缓冲地带”——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劳资冲突模式分析》,载《东岳论丛》,2014年第5期。
10. 汪建华、孟泉:《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载《开放时代》。
11. 闻效仪:《集体谈判的内部国家机制:以温岭羊毛衫行业工价集体谈判为例》,载《社会》,2011第1期,第112-130页。
12. 闻效仪:《工会直选:广东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载《开发时代》,2014年第5期,第54-65页。
13. 吴清军:《集体协商与“国家主导”下的劳动关系治理》,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66-89页。
14. 谢玉华:《中国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效果的实证分析——以武汉餐饮行业为例》,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
15. 许少英、陈敬慈:《工会改革的动力与矛盾:以本田工人罢工为例》,载赵明华等(主编)《中国劳动者维权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6. Ackers P. 2007, Collective Bargaining as Industrial Democracy. Industrial Relations 45(1).
17. Brown, R.C. 2006, China Collective Contract Provisions: Can Collective Negotiations Embody Collective Bargaining?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16).
18. Chan, C. and Hui, E. 2013. The dynamics and dilemma of workplace trade union reform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Honda Workers’ Strike’.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4 (5)
19. Chan, C. and Hui, E. 2014.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From ‘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 to ‘Party State-led Wage Bargaining. The China Quarterly. 217. 221 - 242.
20. Chang-Hee Lee, William Brown and Xiaoyi Wen,2016. What Sor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s Emerging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4(1):214–236
21. Chen, F. 2003.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 China Quarterly, 176: 1006–28.
22. Chen, F. 2009. ‘Union power in China — source, operation and constraints’. Modern China, 35 (6): 662–89.
23. Clarke, Simon and Lee,Chang-Hee 2002. The Significance of Tripartite Consultation in China. Asia Pacifc Business Review. 9(2)
24. Clarke, Simon, Lee, Chang Hee and Li, Qi. 2004.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2 (2): 235–254.
15. Commons, John R.1909.American Shoemakers,1648-1895: A Sketch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4(November), pp39-81
16. David F. 2008, Beatrice and Sidney Webb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British industrial relations, Employee Relations 30(5)
17. Dunlop,John.1958. Industrial Relationship System.Cambridge, 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58
18. Flanders, Allan. 1968, “Collective Bargaining: A Theoretical Analysi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6(1).
19. Fox, Alan. 1973, “Industrial Relations: a Social Critique of Pluralist Ideology.”In Child J. (eds.), Man and Organizat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20. Fox, Alan. 1975. “Collective Bargaining, Flanders, and the Webbs”.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13 (2): 151–174
21. Harbison, F. H.1951,Goals and Strategy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New York: Harper
Howell, Jude. 2008.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s Unions beyond Reform? The Slow March of Direct Elec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 845–863.
22. Hyman, Richard. 2001.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as a Mechanism of Employment Regulation in Britain. In Alaluf, M.andPrieto, C. (eds.),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ployment. 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23. Kochan, T. A. 1980,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from Theory to Policy and Practice, INC: R. D. Irwin.
24. Kochan, Thomas A., Harry C. Katz and Robert B. McKersie.1986.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Industri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304
25. McCarthy, J. and McPhail, C.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eds. by Meyer,D.and Tarrow,S., US: Roman and Littlefeld, 1998.
26. Ng Sek-Hong and Warner, 1998. China’s Trade Union and Management. London: New York: Macmillan, St Martin’s Press
27. Pearson, M. M. 1991. Joint Ventur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trol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under Scoci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8. Perlman,Selig. 1928. 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New York: Macmillan
29. Pringle, T. 2011. Trade Unions in China: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Unrest. Abingdon: Routledge.
30. Tusi, A. and Carver, Anne. 2006, Collective Contract in the Shenzhen Economic Zone in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bor Law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22(4): 469-506.
31. Warner and Ng, S. H. 1999, Collective contract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a new brand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under market soci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32: 295–314.
32. Webb, S. and Webb, B. 1914, Industrial Democracy.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责编/ 孟泉 Tel: 010-88383907 E-mail: mengquan1982@gmail.com
The State, Capital and Labor: Shaping For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llective Consultation——Lessons from Literature Review
Lei Xiaotian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s an important adjustment mechanism for labor relation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rketed economy, collective bargaining system has always been a core issue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research. However, western collective bargaining research cannot be complete and effective explanation for Chinese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present that state, capital and labor forces shap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ese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system. The state determine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ollective negotiation. Whether the institutional space for Chinese collective bargaining can be gradually expand, there are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union practice, labor protest and capital power, need to be considered.
Collective Consultation; Driving Force; Literature Review
雷晓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集体劳动争议预防与处理机制的系统化建构研究”(14ZDA006)、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别委托项目“工业园集体劳动争议的发生、演化与预防机制研究”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