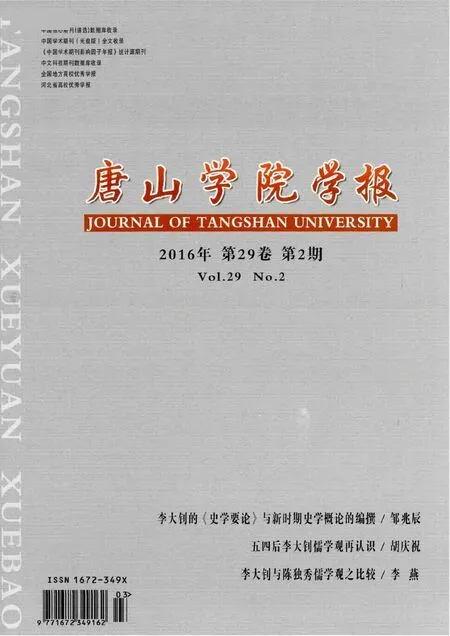凌叔华小说的情爱书写
2016-02-13邝利芬
邝利芬
(萍乡学院 文学院,江西 萍乡 337000)
凌叔华小说的情爱书写
邝利芬
(萍乡学院 文学院,江西 萍乡 337000)
摘要:在五四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女性作家凌叔华以一种客观、温婉的方式对“新闺秀”们的情爱进行书写,显示了与其他同时代女作家不同的强烈的历史感和深厚的文化感,其作品因而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关键词:凌叔华;小说创作;情爱书写
凌叔华是与冯沅君、冰心、汪静之等齐名的少数几个活跃在新文学初期的女作家之一,其文学生涯的开端可追溯到1922年加入燕京大学文学会,历时长达60余年,她的创作成就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在《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新月》《现代评论》等刊物上的短篇小说中,这些作品后大多收录在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中。借着五四时期欧风美雨的侵袭,应和新文化运动解放人的潮流,女性在时代的裹挟下发出了个体生命的呐喊,这个被中国几千年来父权机制扭曲、遮蔽了的生命体浮出历史地表。以冰心、凌叔华等为代表的知识女性,敏锐地抓住了时代的最强音,应我手写我心,将她们最熟知也是最擅长的婚姻家庭诉诸笔端。早在1930年代,学者毅真就在其评论文章《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中,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分为三大类来进行评述,即“闺秀派作家”“新闺秀派作家”“新女性作家”。很有意思的是,与其他两大类不同,“新闺秀派作家”大类中只列举了凌叔华一人。凌叔华的小说创作确实与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不同,除其创作的小说为短篇,这一既具有明显的中国古典文学痕迹,又深受西方现代小说熏陶的特点外,其“特立独行”之处还体现在她不像陈衡哲那样关注旧家庭中妇女事业与生活上的矛盾,也不像庐隐那样写觉醒后的新女性的痛苦和徘徊,相反,她的作品没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类的大张力,而是立足琐碎的日常生活,采用纯客观的叙事视角,书写新旧交替时代的旧女性的“新”或新女性的“旧”。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1]
长期被湮没的女性情爱,在冲破封建藩篱之后,将会呈现怎样的情态呢?女作家们的生活经验和写作方式不同,她们笔下的情爱书写也各异。冰心、苏雪林笔下的女性情爱,婚前往往体现为母亲之爱、同性之爱、自然之爱,婚后的爱则转向到对丈夫的爱。冯沅君、庐隐笔下的女性之爱是一种决绝、一种精神追寻,“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2]。而凌叔华则是从名门闺秀独特的审美视角,对女性生存方式以及生命价值进行追寻,对女性情爱意识的觉醒进行书写。
一、情爱死寂
凌叔华笔下集中描绘的是那些为时代潮流所忽略了的恰好又是她熟知于心的“常见不到太阳,地下满是青苔”(《有福气的人》)黑沉沉冷萧萧的旧式家庭,“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豪门巨族里的精魂”[3]。所谓“精魂”即为小说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太太、小姐、少爷,尤其是太太。她们或是贾母式的封建老太太,或是庸俗堕落的中年太太,或是寄生虫般无所事事的年轻太太。总的来看,这些“精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旧文化的牺牲品,一类是新文化的寄生虫。这两类女性的情爱完全是一种死寂的状态,在大环境的“变”与自身的“不变”中,她们本能地渴望幸福,却在现实中备受冷落,在封建礼教沉重的锁链下耗尽了青春和生命。
在《有福气的人》中,作者花了一多半的篇幅叙述章老太太是如何的有“福气”与“命好”:“凡认识章老太太的谁不是一些不疑惑的说‘章老太太要算第一名了’!”“她从年轻到年老没有忧过柴米,怪不得她的脸上皱纹不多,快七十岁的人了,皮肤还是非常得滑腻……”[3]三十岁时就做了“命妇”,四世同堂,儿子和媳妇都很孝顺她,刚过完一个体面的生日……看起来章老太太真令人羡慕。章老太太整日沉醉在自己以及周围人营造的“幸福”之中,瞧不起新事物,“她尤其的恨新式结婚……新娘的脸让人瞧个饱;新官人穿一身漆黑衣服,还要带一顶黑帽,那活像送丧的哀服”*选自请看小说网,凌叔华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第6节,http://www.qingkan.net/book/lingshuhuadaibiaozuo_zhongguoxiandaiwenxuebaijiaxilie_/18207635_2.html。。她生活在封建家长制的绝对权威下,“老太爷在京候差时讨过两个小老婆,她可是没有同他为这事吵过嘴,生过气,她对人说,大家人没有两三个侍妾是不成体统的,那争风吃醋是小家子气的人才做出来”*选自请看小说网,凌叔华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第6节,http://www.qingkan.net/book/lingshuhuadaibiaozuo_zhongguoxiandaiwenxuebaijiaxilie_/18207635_3.html。。像章老太太这类贾母式的封建老太太,是父权文化和男权审美下产生的典型,她们没有个体对情欲的基本追求,有家无爱,最起码的个人价值追求都是一片空白。牺牲自我,盲目保全家庭是她们人生的起点与归宿。然而有意思的是,她们“无私”的奉献得到的结果却是“虚假的温情”,“孝顺”的儿子和媳妇平日迎逢讨好她是为了她的私蓄,表面和睦的大家庭里兄弟妯娌彼此猜测怨恨。当得知这一切真相后,章老太太“命好”“有福气”的幻境瞬间坍塌了。
《中秋晚》中的敬仁太太也是一个愚昧、庸俗的典型,她迷信传统说法“不吃团鸭就不得团圆”。在中秋夜,当丈夫赶着去看干姐姐最后一面时,硬逼他吃下团鸭再走以致耽误了他们见最后一面,夫妻俩因此心生芥蒂,接连引发了一系列家庭矛盾。然而她把这一切都归因于没吃团鸭,她的无知与迷信历经四个中秋晚终于导致了家庭的破裂。逃回娘家后,敬仁太太还对她母亲说:“娘啊,都是我命中注定的吧。我出嫁后的头一个八月节晚上就同他闹气,他吃了一口团鸭,还吐了出来,我是十分不高兴的,后来他又碎了一个供过神的花瓶,我更知道不好了。”[4]弃妇敬仁太太是可怜可叹的,她悲剧的原因是那根深蒂固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她依附于男权文化,又最终遭到男权文化的抛弃。正是因为男权文化下,女性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才会有敬仁太太把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神灵。从敬仁对干姐姐的眷恋可以推测出,她与敬仁的婚姻是一桩包办婚姻,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残留,包办婚姻始终不是以人的解放和情爱的自由为出发点的。男权社会与封建文化心理构成了女性情爱诉求的双重阻力,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说:“他缺她照样能过得下去,而她没有他,日子则没那么容易过;若是他离开了她,她的生活便会毁掉。主要差别在于,女人的依附性是内在化的,即使她的行动有表面上的自由,她也还是个奴隶;而男人从本质上就是独立的,他受到的束缚来自外部”[5]。
如果说凌叔华对章老太太是客观地叙事,对敬仁太太是戏讽中带有一丝哀怜的话,那么在《太太》《送车》中则呈现的是纯粹的讥讽与嘲笑了。她们既不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又不具有新女性的素质。《太太》中所写的“太太”,终日只知外出打牌赌钱消磨时光,既不愿给女儿出钱制棉鞋,哪怕冬日里还穿着破鞋,也不愿意花钱给儿子买布做操衣,哪怕儿子遭先生责骂。她担心仆人买东西拿回扣,但一到牌桌上就把钱看“开”了,宁可当完了家里的东西也要赌牌。《送车》里的白太太和周太太,忙于蜚短流长,因嚼舌头而耽误了送车的时间。这两位太太拒绝传统礼教对妻子的规范,自诩为新女性,但又把名门正娶、门当户对的婚姻作为标准,“自由结婚,就是电影上看的紧紧相抱相吻的样子……那是不要脸的样子”*选自请看小说网,凌叔华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系列),第6节,http://www.qingkan.net/book/lingshuhuadaibiaozuo_zhongguoxiandaiwenxuebaijiaxilie_/18207635_2.html。。
二、情爱幻想
五四时期是一个转型时期,也是一个过渡时期,它既不是纯粹的新,也不是完全的旧,半新半旧才是它最真实客观的存在。在这个过渡时期,既有像上文所论述的“顽固不化”的拒绝情爱,蜷缩在死寂“囚笼”中的“太太们”,还有经不住“新文化”之风侵袭的“新闺秀”们,她们往往是少女或者少妇。她们在闭锁的闺阁中长大,接受了传统的“三从四德”“四书五经”教育,出落得贤德淑良。狭窄的生活空间以及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她们一方面认同了旧文化对自身的认定,另一方面又受现代文明的浸袭,她们蠢蠢欲动、亦步亦趋,试图追寻时代的步伐,渴望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期冀展现自己梦幻的美丽,进行她们独特的情爱幻想。
《绣枕》中的“大小姐”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闺秀”,她符合一切传统规范,温顺大方、优雅恬静,对待下人也温和之至,是一个典型的淑女。当她得知父亲因攀权附贵想将她许给白总长的二少爷时,她熬着酷暑,带着对甜蜜爱情和幸福婚姻的期待,倾心倾力地绣着一对靠枕,她幻想着她的努力与付出得到白总长的认可以及周围人的称赞。精致的绣枕承载了她美丽的梦,然而,梦终归是梦,当梦想碰到现实,就是梦想破碎的时刻。两年后,无意之中,大小姐从佣人小妞那里得知了两年前的那对绣枕的去处:“当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脏了一大片;另一个给打牌的人挤掉在地上,便用人拿来作脚垫子用。”[6]
现实总是残酷的,没人知道她花了多少心血在上面;没人知道她为了绣那对鸟儿还害了眼病;没人知道她做那鸟冠子曾拆了又绣,足足三次;更没人知道她洗完手都不敢拿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线……
《吃茶》中的芳影和“大小姐”一样,是一位温婉的闺秀美人,时代的新风,使得她有机会踏出闺阁,进入社交场所,并有幸结识了留洋归来的王斌。自第一眼看到王先生起,她就芳心暗许,做着“春秋梦”,她把原本是西方惯用的客套行为的“绅士般的微笑”“帮女士拎包”看成是对她的爱情暗示。她整日恍惚迷离、茶饭不思,在幻想中构筑着自己的爱情罗曼蒂克。某天,有人送来了一大束玫瑰花,她误认为是王先生来求爱了,于是尽显少女期待爱情时的腼腆与羞涩,甚至跑到阁楼里害羞地躲起来,当最后打开请帖得知是王先生邀请她去参加他与另外一个女子的婚礼时,芳影整个人都晕了。
《茶会以后》可以说是《吃茶》的姐妹篇,阿英和阿珠不再像《绣枕》中的“大小姐”那样苦苦等待,也不会像刚踏出闺门的“芳影”那样做“白日梦”。在时代新风中,她们拥有了一种全新的社交生活,但她们对恋爱自由、自主意识还一知半解。她们幻想着成为派对的对象,对男女在公开场合卿卿我我,表现出一定的向往,对“同男朋友那样起劲的说笑”的小姐们倾心羡慕。她们内心对情爱充满了幻想,但又在行动上鄙视“越出雷池”。
在《等》中,令读者好奇的那个“好女婿”始终未出现,其实,凌叔华所要表现的并不是这个“好女婿”的形象,而是母女两人对未来美好情爱生活的幻想。两个善良的苦命女人本想把改变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好女婿”身上,却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她们宁愿苦苦等待,做着美梦,也不愿意有所行动。
这些处在现实与传统缝隙中的“新闺秀”们,一只脚走出了闺门,另一只脚还在闺门中,新旧文化的冲突,旧的文化心理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她们那点刚刚兴起的可怜的情爱萌芽必将胎死腹中。按照时代标准他们是没有拯救价值的,而她们本人却需要被拯救。她们要想挣脱封建礼教的禁锢,冲决传统思想的藩篱,成为一个自主意识的女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情爱诉求
随着“新文化运动”以及“人”的解放的深入,五四时期的知识女性大多能够挣脱包办婚姻的枷锁,自主走向婚姻殿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娜拉出走后,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走向堕落,要么回归家庭。”[7]《伤逝》里的涓生与子君就恰好诠释了这种命运。处在同一社会语境下的凌叔华也对这一主题进行了不懈的探求,与鲁迅不同的是她笔下的“娜拉”物质上一般还比较富足,起码没有经济上的负担,与上文中提到的前两类走不出闺阁或者仅一只脚跨出闺阁的女性也不同,她们“新”的成分更多。
《酒后》中的女主人公采苕有一个十分爱她的丈夫,有甜蜜的婚姻生活,然而她却对丈夫柔情蜜意的表白充耳不闻。在一次晚宴过后,当她看到他们共同的朋友子仪醉倒在自己的沙发上时,便心生爱恋,竟然借着微醺的酒意当着丈夫的面大胆提出亲吻子仪的要求。虽然丈夫永璋迟疑后答应了她的请求,但她内心却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她想顺从内心追求爱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又想遵从作为妻的道德要求,她大胆地走到了子仪面前,最终又快速走回丈夫永璋的身边。《春天》中的霄音,婚后想给病痛中的昔日恋人写信以表安慰之情,在写信之际,丈夫的突然出现让她手足无措,怕被丈夫知晓,只好将写好的信搓成团扔进纸篓作罢。采苕的大胆要求是自我个性张扬的表现,霄音也意识到了作为女性应有的自主权利。这和前文提到的芳影、阿英、阿珠绝不相同,虽然在行动上采苕和霄音最终还是回到现实的规范中来,但较之前者进步的是,她们内心潜藏着一股情爱的律动,萌动着沉睡已久的女性自我意识,试图寻找女性作为妻子这一性别角色之外的价值主体,彰显了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自主的精神追求。
《花之寺》中的燕倩婚后生活也很幸福,但作诗人的丈夫却不满平静的生活,不想重复平淡的每一天。某天他收到一封匿名的爱慕信,心理万分激动,并接受了信里的约定,第二天便抱着不妨就做一次“奇美的梦”的心理,赶到花之寺赴约。等了许久不见人来,以为是谁开的一个玩笑,没想到等来的竟是自己的妻子,最后两人都不揭穿真相,共游秋景。这篇小说有意思的是,面对平淡的生活,燕倩运用自己的智慧,用类似“恶作剧”的小游戏来经营平淡的婚后生活。面对丈夫的“精神出轨”,燕倩为捍卫爱情而主动出击,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追求独立的自我价值。但是,在燕倩身上仍旧能见男权文化的控制,“情书”中的“我”就是燕倩渴望达到的“理想的我”,而这个标准仍是按照男性的标准,为了满足男性的需求设定的。这表明了只有获得丈夫的认同,女性才能获得在夫妻关系中的自我位置。《绮霞》中的绮霞酷爱音乐,也有相爱的丈夫,但婚后为了全心伺候爱人就再也没有摸过琴,后来在友人的鼓励和音乐会上外国小提琴家演奏大获成功的刺激下,经过了多次的内心挣扎后,留下一封家书,离家到国外学琴去了。五年后从国外学琴归来的绮霞虽然琴艺有了很深的造诣,但丈夫却有了新欢且组成了新的家庭,无奈的绮霞只得独自拉琴,用琴声来陪伴自己熬过寂寞的长夜。这表明进入婚姻后的新女性在实现情爱诉求时仍旧困难重重。
凌叔华笔下的那些旧式太太也好,跨出半只脚的小姐也好,全身心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新女性也好,最终她们的生存模式还是传统的、旧式的,仍旧走不出依靠男人生活的既定框架。她们与新世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厚厚的隔膜,这也就注定了她们必将走向落寞或毁灭。这三类女性从横轴上看,并存在五四这个新旧更替的历史时期;从纵轴上看,则展现了女性生命历程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少女-少妇-老太太。凌叔华通过对“新闺秀”们的情爱书写,深刻揭示出要彻底扫除封建礼教和宗法制沉积在女性文化心理上的历史尘垢,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
四、结语
也许是现实的情爱与理想的情爱差距太大而让凌叔华极度失望,她甚至转到了精神领域去探求女性情爱的出路。在小说《他俩的一日》中,莜和与棣生是一对分居两地的新式夫妻,一年难得见到一两次,为了避免婚姻滑向平淡,莜和最终还是选择了以距离产生美,宁愿坚持着异地婚姻的痛苦,希求以久别来获取相逢的甜蜜,以缺陷来求得完满,通过压制肉体来契合精神。她在现实中失去的理想只能从梦境中得到补偿,她企求“在梦中也许就尝到了美满而真实的生活了”,或许这也是凌叔华对充满矛盾的现实世界的一种选择和精神追求。此外,凌叔华还尝试到女性之间的相恋中为情爱诉求寻找出路,《说有这么一回事》就写了一个女同性恋的故事。云罗和影曼两人朝夕相处,好到紧紧相拥同睡一张床,日子久了便产生了感情。后来影曼因家里的压力而选择了传统的异性婚姻,苦苦等待的云罗听到消息后便晕倒在地。1930年代后,凌叔华的创作转向了虚幻、怀旧的儿童小说和诗意的散文,在经历了情爱寻求之路的艰苦跋涉后,她转而到洋溢着人生之美的童真世界和大自然里去抒发艺术情怀了。
纵观凌叔华的小说创作,在其情爱书写中,尽管并未为女性该如何“现代地”存在于男权社会指明一条明确的道路,且最终陷入了困境,但就五四女性文学的创作而言,“女人究竟该什么样才能算现代女人”这个问题还真的只有到凌叔华的小说里才得到了明晰的探讨。在丁玲、冰心、庐隐、陈衡哲的女性表达中,反封建和斥责男权社会是主要任务,和这些女作家的自述式的写作模式不同,凌叔华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客观地审视与品味五四这一新旧过渡时期“新闺秀”们的悲欢离合,从而对女性情爱诉求的客观心理历程进行了探寻和反思,这使得她的作品与同时代其他女作家的作品比较起来具有了更强的历史感和更深厚的文化感。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M]//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8.
[2]冯沅君.隔绝[M]//冯沅君小说集·春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
[3]凌叔华.有福气的人[M]//绣枕.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78.
[4]凌叔华.中秋晚[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4:22.
[5]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38.
[6]凌叔华.爱山庐梦影[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168.
[7]于青,王芳.黑夜的潜流——女性文学新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71.
(责任编校:李亚平)
Depiction of Love in Ling Shuhua’s Novels
KUANG Li-fen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Pingxiang University, Pingxiang 337000, China)
Abstract:At the edge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the female writer Ling Shuhua depicted the love of “new young lady” in a objective and gentle way,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writers. She had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y and a keen cultural sense and her works are of unique literary value.
Key Words:Ling Shuhua; fiction writing; love depiction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教改课题项目(JXJG-13-22-14)
作者简介:邝利芬(1981-),女,湖南郴州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2-0060-04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