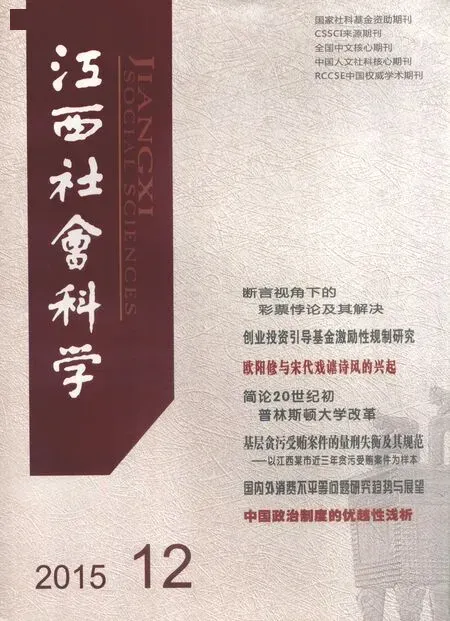“三言”与冯梦龙的“情教”观
2015-04-15丁佐湘蔡欢江
■丁佐湘 蔡欢江
“三言”与冯梦龙的“情教”观
■丁佐湘 蔡欢江
“三言”与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冯梦龙把情看作天地万物的本原,并力图以情为基础对封建礼教进行重新阐释。他以情为出发点,又以礼为归宿。这种思想在“三言”中那些表现男女婚姻爱情的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思想同时也给“三言”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
情教;冯梦龙;“三言”
丁佐湘,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蔡欢江,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西南昌 330013)
学者们以往对“三言”的研究往往过于突出其中所包含的反封建的启蒙意识,把冯梦龙当成一个大胆挑战封建传统思想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道理,却遮蔽了一些更为复杂的事实——与汤显祖等标举“以情抗理”相比,冯梦龙对于礼教的态度不但温和得多,也复杂得多。在“三言”之中既有对人的正常情欲的理解与赞同,也有对贞洁观念的推崇;既大力推崇人情,又不遗余力表彰忠孝节义,这一切都看似矛盾地统一在冯梦龙一人的身上。要解开这一团纠结不清的矛盾,只有从冯梦龙的 “情教”思想出发才有可能。
一、冯梦龙“情教”观的由来及内涵
(一)由来
冯梦龙的情教思想乃是针对晚明的社会思想状况而发的:一方面人们在疯狂地追求着各种欲望的满足,另一方面当时主流的封建礼教规范因为空洞僵化而失去了维系世道人心的作用。人们在心照不宣地疯狂追求欲望满足的同时,口头上却在大谈仁义道德。出于对这种现象的不满与批判,冯梦龙提出了他的“情教”论,他试图恢复人们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真诚信仰,以挽救儒家伦理教条化和空洞化的危机。
冯梦龙认为,要对社会大众进行教化就应该采用一些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而白话小说恰恰具备这样的特征。他在《警世通言序》中就根据自己的见闻指出: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1](P663)
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甚至对儿童都产生了巨大的教化作用,这不能不说小说在社会教化方面的确有正统的儒家经典所不及之处。因此,冯梦龙也想通过白话小说起到教化大众的作用,这也是他创作“三言”的初衷:
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者,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2](P3)
也就是说,创作“三言”的目的就是“导愚”、“适俗”和“习之不厌,传之可久”。
(二)内涵
在冯梦龙看来,宇宙万物皆由情所生,情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他在《情史序》中指出,“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3](P1)由此,冯梦龙进一步认为,情并不仅仅是人类的现象,情离开人依旧能够存在,相反人却唯有依情而生。“人,生死于情者也;情,不生死于人者也。人生,而情能死之;人死,而情又能生之。即令形不复生,而情终不死……情之为灵,亦甚著乎!”[3](P361)由此可见,冯梦龙的思想是以情为本体的思想。
对于冯梦龙的情本思想,历来的研究者往往首先注意到的是其对于自然人性的宽容与肯定。不可否认这的确是冯梦龙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方面。他认为人的欲望乃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也完全应当得到满足,人对于情爱的追求是人的必然权利。他编选《挂枝儿》《山歌》,即是出于“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4](P1)的目的,其所收也多为歌咏男女爱情之作。这些主张的确冲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礼教,肯定了人性的正当要求,在当时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但很多论者却因为这点而对冯梦龙产生了过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思想具有个性解放的性质和民主的倾向,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历史要求等等。但这不过是皮相之谈,并未真正理解其思想的实质。就冯梦龙来说,他提出以情为本的思想其实质在于以“情”来改造、充实明代已经逐渐僵化、空洞的礼教体系,以“情”来重新诠释封建礼教,把封建礼教建立在“情”的基础之上。冯梦龙说:“自来忠孝节烈之事,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妇其最近者也。无情之夫,必不能为义夫,无情之妇,必不能为节妇。世儒但知理为情之范,孰知情为理之维乎!”[3](P36)
在以情为本的思想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情教”的思想:“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3](P1)他希望以情立教,用情来感化众生,使他们合于君臣父子之道。而在署名江南詹詹外史述的《序》中,他进一步指出:“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流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情之功效亦可知已。”[3](P3)在此,他用“情”对封建礼教的一套三纲五常做了全新的阐释,把所有儒家的经典都归于情,并得出“情始于男女”的结论。由此可见,冯梦龙的“情教”思想,虽不同于宋明理学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但并不反对封建礼教所推崇的那一套忠孝节义的纲常规范。他其实是把情看作人的伦理道德的基础,从而把伦理道德看作是人的天然义务。
二、冯梦龙“情教”观在“三言”中的体现
(一)“三言”对人正常情欲的肯定
冯梦龙反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认为人的正当情欲无可厚非,理应得到同情和宽容。《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虽然在丈夫出外经商之后与他人通奸,但冯梦龙并没有把她写成一个像《水浒》中的潘金莲一样的淫贱荡妇。相反,作者把王三巧刻画成为一个重情重义、知恩图报的善良女性。在作品中,当王三巧的丈夫走后,她整日茶饭不思,一心思念自己的丈夫,可见她对自己的丈夫有着深厚的情感。蒋兴哥休弃了王三巧,王三巧非常自责,认为都是自己的罪过,辜负了丈夫的恩情。蒋兴哥遭了牢狱之灾,她又求后夫吴县令相救。她与蒋兴哥重逢的时候,禁不住相拥在一起,放声痛哭,可见王三巧与蒋兴哥之间的夫妻情深。看到这里,她的后夫也被他们的感情所打动,主动提出让他们破镜重圆。这说明,冯梦龙对人的正常感情和欲望持一种肯定和同情的态度。
《勘皮靴错证二郎神》中的韩玉翘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宠幸,孤独地居住在玉真轩,抑郁成疾。宋徽宗命杨太尉把韩夫人接到府中养病。一次,偶然到二郎神庙中还愿,遇到孙神通假扮的二郎神,韩夫人一见生情。后被人发现,孙神通被判凌迟处死,韩夫人被判改嫁良民。韩夫人终于实现了自己对正常人情感的追求。这种情节设计也表现了作者对封建时代女性追求正当情感和欲望的肯定。
在封建时代,男女自由恋爱不被允许,缔结婚姻必须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前提,对此,冯梦龙表现出大胆的批判精神。在“三言”当中,冯梦龙写了许多歌颂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卖油郎独占花魁》描写了一个妓女王美娘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妓院的生活已经让她丧失了正常人应有的尊严感,但是身份低微的卖油郎秦重,却用自己真挚的爱情,使她恢复了做一个正常人的乐趣与尊严,她被秦重的真情所打动,对秦重也心生爱恋,主动对秦重说出“我要嫁你”的心愿。作者通过王美娘争取自身幸福的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力量,肯定了青年男女对恋爱和婚姻自由的追求。
《卖油郎独占花魁》以大团圆告终,而《崔待诏生死冤家》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本篇小说的女主人公秀秀是一个大胆、热烈追求爱情的青年女性。秀秀本是王府的养娘。她趁王府着火之际,求崔宁带她到崔宁家去避火,并主动向崔宁表白爱慕之情,并怂恿他和自己一起私奔。与秀秀相反,崔宁则十分畏缩,只是被逼无奈才娶她为妻。秀秀不甘于被奴役和玩弄,而要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和婚姻。她用大胆的行动对封建礼教发起了勇敢挑战,这是她性格中最光辉的一面。虽然她的抗争最终失败了,但她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甘愿粉身碎骨的精神却极为光彩夺目。
除此之外,像《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宿香亭张浩遇莺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玉娇鸾百年长恨》等篇目也都对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行动表示了肯定与赞颂。
(二)对纵欲的否定与对贞洁观念的宣扬
冯梦龙虽然对人追求正常情欲表示宽容与肯定,但这并不等于对无节制的放纵欲望表示认同。事实上,在“三言”中有不少格调低下以至猥亵放荡的描写,但从其整体倾向来看,冯梦龙对人的纵欲行为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
在《郝大卿遗恨鸳鸯绦》中,尼姑空照、静真等人是“真念佛、假修行、爱风月、嫌冷静、怨恨出家的主儿”,将郝大卿强留在庵中淫纵,以至赫大卿淘空而死。而《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中的宝莲寺群僧,以祈嗣为名将良家妇女诱入寺中奸污。事败后又铤而走险,趁夜越狱谋反,几乎令全城百姓尽遭屠戮。冯梦龙对这些人的行为深恶痛绝,在小说中安排空照、静真等人依律被斩;宝莲寺群僧死于乱刀之下。
在《郝大卿遗恨鸳鸯绦》中,作者还论述了“好色与好淫不同”。将男女间正常的爱恋与倾慕视为“好色”;而将荒淫无耻的淫滥视为“好淫”。在“好色”中又有所谓“正色”、“旁色”、“邪色”与“乱色”之分。前三者包含了男女正常交往的基本内容而偷情淫乱则被归于“乱色”。这明显见出作者试图通过情欲的不同种类进行区分而寓之褒贬,以图在维护正常人欲的同时消灭过度纵欲引发的罪恶。
在写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样的宽容失贞者的作品同时,冯梦龙也写了不少宣扬妇女守节的故事。在《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刘宜春的父母设计抛弃她身染沉疴的丈夫后,她执意寻夫,投水殉情。当相信丈夫已不在人间后,她终日以泪洗面,誓不改嫁。冯梦龙把一个“节妇”的事迹写得如此动人,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在这个故事中,情是礼的基础,礼是情的延伸,情与礼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充分实现了冯梦龙的情教理想。
除此之外,“三言”中也有一些宣扬妇女贞洁思想的作品却没有做到情礼交融,而表现为礼对情的强制与压抑。在《蔡瑞虹忍辱报仇》中,蔡瑞虹一家在随其父上任途中遇上了强盗,除了蔡瑞虹,全家遇害。蔡瑞虹被强盗凌辱。为报家仇,蔡瑞虹忍辱负重,后来在丈夫的帮助下,终于报仇雪恨。她本来应该过上幸福生活,但她认为自己失节,配不上丈夫,因此自刎身亡。而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玉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她的丈夫莫稽得势之后甚至要置她于死地。按常理,金玉奴断绝与莫稽的夫妻关系,冯梦龙却让他们重修旧好,并通过玉奴之口说:“虽然莫郎嫌贫弃贱忍心害理;奴家各尽其道,岂肯改嫁,以伤妇节!”这其实是把贞洁置于妇女的生命价值之上。即使是宽容失贞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最后对王三巧也给予了惩罚,让她最后只能以妾的身份与蒋兴哥生活在一起。
从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冯梦龙“情教”思想的复杂与矛盾。他希望为日益僵化腐朽的封建礼教思想找到一个能为人所接受的情的基础,对之进行充实、改造。但封建礼教本身却与人们的情感有着天然的冲突,本来就是一种桎梏人性的陈腐思想,它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冯梦龙的这种调和情礼的做法注定只能是左右为难,最终导致为礼教而牺牲人情,这也正是冯梦龙“情教”思想的局限性所在。
三、冯梦龙“情教”观的历史意义
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是相当复杂的,我们不能以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去看待他的思想以及“三言”的思想倾向。无论是把他当作启蒙思想的急先锋,还是看作封建礼教的维护者都会有失偏颇。冯梦龙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与王学左派相吻合的一面。他提出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思想主张,表现出对封建大胆反叛的胆识和勇气。他对于广大人民对“性”、“灵”、“真”的追求,其实并不排斥,甚至有支持有鼓励。但矛盾的是,冯梦龙的思想还有一定的理学成分,他没有轻易地抛舍掉它,在这一方面,他又有思想的保留。可以说,他在思想上出现了矛盾、挣扎、困顿及该如何取舍、如何保留、如何划分重量的难题,显示出了在夹缝中生存的存在状态,这与他生活的社会时代和环境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从中看出,时代的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明显地反映在社会思潮上,借由世风民情表现出来了。通过他们的举止行为,我们可看到他们在思想上的挣扎和混乱。面对这个转型阶段,人们在思考,在进行着价值取向的判断和取舍。他受当时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认为“情”是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甚至提出要设立“情教”,使“情”成为一种宗教。因此,他要求小说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情真、事真、理真是冯梦龙至高的理论追求。因此,只有从其“以情立教”思想的得失的整体考虑出发,才能予以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三言”能“极摹人情世能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3](P324),这个评语是中肯而恰当的。这些作品的确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高峰之作。
总之,由于明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在明代始终占据着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受到封建礼教的桎梏。然而,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流行,尤其是王学左派的兴起,明代中后期,文坛出现了一股尊情尚性的文学思潮,对当时的封建礼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冯梦龙作为晚明时期倡导尊情文学观的杰出代表,他的“情教”理论肯定了人们正当情感和欲望的合理性,有力地批判了禁锢人心的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
冯梦龙高举“情”的大旗,认为“情”是世间至高的力量,没有“情”就没有一切。“情”是人们之间的黏合剂,“情”还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改变社会风气。他希望用“情”改造社会,教化大众,情与理在他的“情教”观中得到高度融合。
[1](明)冯梦龙.冯梦龙全集(第2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2](明)冯梦龙.冯梦龙全集(第3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3](明)冯梦龙.冯梦龙全集(第7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4](明)冯梦龙.冯梦龙全集(第10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彭民权】
I206.2
A
1004-518X(2015)12-0078-04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交通大学女性研究中心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