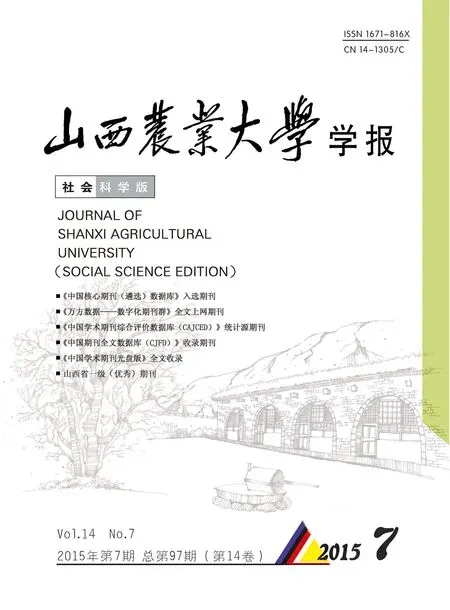虚假诉讼刑法规制及其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2015-04-02胡安琪
虚假诉讼刑法规制及其完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当前,虚假诉讼行为已经无法通过常规的民事、行政制裁措施来更深入的防控,社会对此严重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目前为止现行法对此并无专门规定,也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于是司法实践中在治理虚假诉讼方面频频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有按诈骗罪或妨害司法罪定罪的,还有按无罪处理但处以罚款和司法拘留的,有些地方法院还出台了规范文件,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已由浙江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但其不是有权的司法解释,不但在本地区不能起到强制作用,也无法辐射其他法院,全国对虚假诉讼的制裁仍处于无序的局面。[1]针对这类现象,新修订的修正案草案已经被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的第三十三条对于虚假诉讼在刑事立法上首次给予规制。但草案关于虚假诉讼犯罪罪状、法定刑的设置仍然存在着不足,有必要通过对新罪条文进行剖析从而对其刑法规制做出进一步完善。
一、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理由
(一)我国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必要性
犯罪的本质是要侵犯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某一违法行为上升为犯罪必然符合了法益侵犯性。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动用刑罚的谨慎性,只有虚假诉讼行为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才有必要给予刑法规制:
1.虚假诉讼严重破坏司法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和司法威信。众所周知,妥善解决纠纷的最后一扇门是司法,一旦失去应有的权威其公信力就会降低,其有效性和公正性将受到人们的质疑,削弱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和执行力。虚假诉讼恰是通过捏造事实或伪造证据等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漠视司法权威,将法院作为牟取自身利益的工具,使其做出错判,从而使人们丧失对司法的信赖。
2.虚假诉讼严重浪费司法资源。随着人们法律素养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诉诸法院解决纠纷,司法需求不断增大,但司法也是成本最高昂的解决纠纷的方法。而虚假诉讼正是通过一、二审,甚至不断的再审、申诉,极大消耗有限的司法资源,造成司法资源严重流失。
3.虚假诉讼对被害人的合法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虚假诉讼使当事人无端陷入诉讼,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侵财型虚假诉讼在侵犯正常司法秩序的同时还严重侵害被害人的财产;有的导致相对人因败诉而承受社会评价降低的精神痛苦;[2]更有甚者造成企业商誉降低从而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因此而破产。
综上,民事诉讼虽然是虚假诉讼犯罪的高发区域,但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应负刑事责任的程度,故修正案草案有必要对其予以刑法规制。
(二)域外立法例给我国的启示
虚假诉讼在境外亦是高发现象,大多数国家对于虚假诉讼都采取了刑法规制的手段,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模式:
1.诈骗罪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德日刑法为代表,二者均认为虚假诉讼是诈骗形式中的其中一种——“三角诈骗”,法院在其中“扮演”被骗者以及财产处分者而非财产损失者的角色,由于法院拥有执行生效判决的权力,故其具有处分相对人财产的权限,应认定为诈骗罪。我国的张明楷教授也对此观点持支持态度,他认为“诉讼诈骗是典型的三角诈骗,应认定为诈骗罪”。[3]然而根据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在2002年《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应谨慎对待用诈骗罪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定性的方式,诈骗罪不是对虚假诉讼犯罪的合适定性。[4]
虚假诉讼不宜以诈骗罪论处的关键原因在于其并不局限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侵财型诉讼,还包括为了获得驰名商标的认定、意图损害个人名誉、公司商誉等非侵财型诉讼;而诈骗罪侵犯的仅仅是财产所有权这种简单客体。如果笼统的将所有虚假诉讼均归入诈骗罪的行列,显然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基石,对于非侵财型虚假诉讼,诈骗罪的观点无能为力。
2.妨害司法罪模式。意大利和新加坡主要为采取这种模式的代表。《新加坡刑法典》第二百零八条就将“采用欺骗手段接受非应得数额的判决”行为的罪名认定为“伪证及破坏司法罪”的一种。[5]意大利则通过刑法第三百七十四条,明确将“诉讼欺诈”行为纳入“侵犯司法管理罪”规制的范围。[6]该二国基于虚假诉讼的法益侵犯、行为特征等因素而抉择出的“妨害司法罪”立法模式,符合我国刑法体系的协调性,值得我国刑事立法予以借鉴。
3.“侵财型”与“非侵财型”分别处理模式。该种模式以西班牙为主要代表,该国刑法将虚假诉讼区分为两种类型,对二者分别定性:一种是侵财型虚假诉讼,此种虚假诉讼作为“侵犯财产罪”中的诈骗罪的加重量刑情节来处理;另一种是非侵财型虚假诉讼,对于此类虚假诉讼按照“伪造罪”来定罪处罚。[7]
此次修正案草案针对国内外的立法形势,首次对虚假诉讼犯罪予以刑法调整,在三百零七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零七条之一:“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侵占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本次立法实际上采取的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分处模式”:其前半句是关于非侵财型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后半句是对侵财型虚假诉讼的刑法调整,二者分别按照“妨害司法罪”以及“诈骗罪”的从重处罚情节来处理。这种模式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其既保护了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司法秩序,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了侵财型虚假诉讼可能侵犯的复杂客体,具有较一般犯罪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而需要给予更重的刑罚,避免了将其放在妨害司法罪中量刑过低而导致的罪刑不相适应。这样的规定尽管在量刑上要远远高于妨害司法罪的其他罪名,但是存在一些弊端,笔者将在后文予以说明。
二、虚假诉讼犯罪之条文解读
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于虚假诉讼的裁判一直存在较大出入,这样的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虚假诉讼犯罪内涵不明晰所致,立法对于虚假诉讼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学界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也存在分歧,这样导致各地法院的司法裁判无法可依、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频繁出现。某一犯罪的内涵外延过宽会有损刑法的谦异性,外延过窄又会无法有效打击犯罪。针对这种现象,本次修正案草案就通过罪状的描述对虚假诉讼内涵予以一定程度的界定,即条文规定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然而“模糊性以及因模糊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是立法的基本特征”,[8]故笔者在此解读虚假诉讼犯罪条文,以更加明确条文内涵,对统一定罪量刑有所帮助。
(一)犯罪主体
虚假诉讼的本质在于行为人提起诉讼的虚假性,有时是双方诉讼当事人合谋损害诉讼案外人的利益(即双方虚假诉讼行为),有时是双方当事人中的其中一方与对方当事人之外的人,比如证人、勘验人员、专家辅助人等诉讼参与人,甚至与本案其他审判人员通谋,通过捏造事实,虚构民事法律关系给对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即单方虚假诉讼行为)。但只要该民事诉讼具有本质上的虚假性,无论是当事人双方还是单方恶意提起,均应纳入虚假诉讼犯罪的调整范畴,即诉讼当事人和当事人之外的人均可成为虚假诉讼犯罪的主体。同时,笔者认为虚假诉讼犯罪既可以由自然人来实施,还可由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但修正案草案没有将“单位”列作犯罪主体,这一点值得商榷。
(二)主观方面
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虚假诉讼行为可能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决从而有损第三人权益,但为追求自身利益仍希望并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具有故意,过失不构成虚假诉讼犯罪。并且修正案草案中将虚假诉讼犯罪的罪状表述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其中“捏造”行为亦体现出行为人主观上的严重恶性,故该罪只能以主观故意而实施。
虚假诉讼是民事诉讼的非常态表现形式,诉讼的提起是为了利用法院作为自己获取非法利益的工具。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虚假诉讼犯罪主观目的上是要“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提起,该主观构成要件在刑法典的其他罪名设置中亦有体现,最典型的如“行贿罪”法条中明确限定了只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才是行贿罪;若非为了非法利益而提起诉讼便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这样通过增加构成要件的方式提高入罪的门槛,更符合立法经验,但是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司法实践中检方对被告人主观方面的证明难度,有架空新法条文的危险性,不利于更好的打击犯罪。
(三)客观方面
修正案草案规定行为人必须“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该规定充分体现了虚假诉讼犯罪的虚假性本质。“捏造”是指凭空编造,包括对法院采取伪造证据、捏造事实以虚构民事法律关系等手段从而骗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故若行为人主观上准备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但客观上却误以“真实的事实”提起诉讼,就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因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犯,只有某一行为侵害到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才能认定为是犯罪,否则就有主观归罪的嫌疑。但是,这里的“捏造事实”是捏造全部事实还是部分事实,是否任何在诉讼中捏造的行为都能认定为犯罪也是值得商榷的。
(四)客体
罪名的归类主要取决于其侵犯的客体,若是复杂客体,则应放在具体的犯罪中来考虑,由主要客体所决定。本次修正案草案将非侵财型虚假诉讼放在“妨害司法罪”一节,说明正常的司法秩序是该罪主要侵犯的客体,同时将侵财型虚假诉讼作为诈骗罪的从重量刑情节,说明此时行为主要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一客体,并且此时虚假诉讼的提起同样会侵犯到司法权威,故该罪可能由复杂客体所构成。
然而,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威与公众的公私财产所有权到底孰更具重要性?这两种法益在刑法保护的不同层面上均占据重要地位,二者的迥异性质使司法实践很难通过单纯的对比得出答案。但一般认为,司法是维持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破坏司法秩序的危害性更大。而且妨害司法罪是行为犯,一旦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行为就必然扰乱司法机关正常司法活动的开展。然而诈骗罪与此相反,通说认为,要构成诈骗罪行为人必须非法获取数额较大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虚假诉讼行为最终都能实现侵犯财产的目的,对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一客体的侵犯是或然的,所以只有司法机关正常活动才是所有虚假诉讼侵犯的共同客体。从另一方面说,修正案草案中对所有侵财型虚假诉讼都依照诈骗罪的从重处罚情节来处理是不合适的,需要区分侵犯不同法益的情况予以考虑。
三、虚假诉讼犯罪之条文完善
(一)虚假诉讼罪状设置之构想
1、增加单位犯罪主体。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虚假诉讼案件中的典型一类就是单位资不抵债,作为虚假诉讼被告逃避债务的案件,即通常所说的“虚假破产”案件。虽然这类案件中虚假诉讼行为是由自然人实施,但自然人并非为了自身利益而是为单位的整体利益,经单位集体决定或者能够代表单位整体意志的负责人来决定而实施。然而我国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刑法分则条文未明确对虚假诉讼行为规定单位犯罪的情形下是无法对单位进行刑处罚的。然而单位实施虚假诉讼的现象愈加频繁,故我们需考虑在三百零七条之一中增加一款,作为单位虚假诉讼犯罪的处罚规定。
2.明确罪状用语。
如前文所述,修正案草案对捏造“部分事实”是否认定为犯罪没有规定,并且捏造事实是否一定需通过伪造证据,对仅口头编造虚假信息以虚构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是否又可以认定为犯罪也没有规定。笔者认为虚假诉讼入罪不代表对所有捏造事实提起诉讼的行为都一概予以定罪处罚,这是由刑法的谦抑性和补充性所决定的,并非任何侵犯法益的行为都应规定为犯罪,立法机关只有在其他手段不足以控制危险性时才能将某种违法行为上升为犯罪,在刑事立法时应严格遵循刑法的概念性思维和规范性思维。鉴于此,修正案草案在虚假诉讼犯罪中明确规定只有“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才予以刑事处罚,这就对虚假诉讼进行了必要的过滤,如果不以这一整体的评价要素来提高虚假诉讼犯罪的入罪门槛,将无法区分本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不同,使司法资源无法得到优化配置。对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相应的就按照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进行非罪化处理。
但是这一模糊性规定并无法明确界定何种行为达到了“严重妨害司法秩序”和值得刑法处罚的程度,这样极大的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不利于定罪标准的统一,且有些“审判人员有畏难情绪,对虚假诉讼进行刑事制裁意味着原诉讼案件要暂时中止审理,案件审理期限将大大延长,而审判人员在面临结案率与质效评估考核的压力下,往往会采取民事制裁措施,以求尽早审结案件。”[9]这样,法院便可能以行为未达到“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程度为理由拒不刑事裁判,而以民事或行政制裁来代替,这样的裁判便使草案的新增规定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
明确性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要求刑法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民众能够切实了解罪与非罪的界限,根据刑法的规定来认识自己行动的法律意义从而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10]否则立法的模糊性便会造成民众行动萎缩、限制自由。此外,不明确的立法用语还会给司法人员定罪和量刑造成巨大障碍,严重影响刑事审判。所以刑法条文应对什么样的行为达到“严重妨害司法秩序”的程度给予部分列举,在刑法修正案(九)正式颁布之后,我们也应当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此予以细致规定。
3.有区分的定性侵财型虚假诉讼。
首先,如前文所述,虚假诉讼犯罪是行为犯,诈骗罪是结果犯,修正案草案不加区分的将所有侵财型虚假诉讼定性为诈骗罪是欠妥的。若行为人非法取财数额达不到诈骗罪起刑点,一般只能依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做无罪处理;若行为被揭穿,就只能按诈骗罪未遂处理。这使法律在猖獗的虚假诉讼犯罪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难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不能有效预防和打击犯罪。相反,定性为妨害司法罪,只要行为人提起诉讼,即便没有骗取钱财,但案件经过一、二审甚至再审才揭穿虚假诉讼,仍浪费了巨大的司法资源,对司法权威造成侵害,也应认定为虚假诉讼犯罪的既遂。一旦行为人实施虚假诉讼,刑法便能给予及时有效的惩治,使公私财产和司法秩序免受扩大化损害,实现刑法一般预防的功能。
其次,即使侵犯财产的数额达到了诈骗罪的定罪标准,但没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时候亦不宜以诈骗罪论处。如前所述,罪名的归类应放在具体案件中考虑,由主要客体所决定。虚假诉讼行为之所以设定在“妨害诉讼罪”一节,是因为通常来说,其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权威,司法秩序比公私财产所有权更值得刑法保护,只有通过虚假诉讼非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时,其侵犯的主要客体才成为公私财产法益,才宜以诈骗罪论处。
综上,草案对侵财型虚假诉讼认定为诈骗罪应抱以谨慎的态度,应将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的第二款规定改为“有前款行为,侵占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数额特别巨大时,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从重处罚”,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以纳入妨害司法罪为宜。
(二)虚假诉讼犯罪法定刑设置之构想
1.法定刑配置过低,应适当提高主刑。
罪刑相适应原则不仅体现在刑事司法,还在立法方面有所体现。由于刑法的完善在性质上也属于刑法立法,故同样应遵守罪刑相适应原则,这样我们便可以从中发现刑法分则中哪些条文应予重新设置罪刑配对。[11]“刑罚应与罪质相适应。罪质,就是犯罪违法性与有责性统一表现的犯罪性质。不同的罪质,标志着各该犯罪行为侵害、威胁法益的锋芒所向不同。这种不同,正是表明各种犯罪具有不同的罪行程度、从而决定刑罚轻重的根本所在。”[12]
如前所述,虚假诉讼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对其设定更高的法定刑。并且在“妨害司法罪”这一节中,伪证罪、妨害作证罪中对于情节严重的行为法定最高刑可以判到7年有期徒刑,而虚假诉讼的主观恶性和对司法的危害性并不亚于前两罪,并且伪造证据的虚假诉讼行为还包含着伪证罪和妨害作证罪的罪质,但其法定刑最高却仅为三年有期徒刑。另外,司法实践中以侵财型虚假诉讼居多,具有侵犯司法机关正常秩序和公私财产权的双重犯罪属性,故无论侵犯财产的价值有多大,其危害性都不应低于“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危害性,法定刑应适当高于后者的法定最高刑3年有期徒刑。且当侵犯财产的价值达到数额较大时,侵财型虚假诉讼的危害性便不亚于同等数额的诈骗罪的危害性,故其法定刑便应高于同等数额的诈骗罪。因此,草案对虚假诉讼所规定的刑罚应予适当上调以校正现存刑法阶梯的不足。
2.设置罪刑阶梯,合理安排结果(情节)加重犯之法定刑。
修正案草案第三十三条忽视了对虚假诉讼的结果(情节)加重犯进行设置,从而使虚假诉讼犯罪的法定刑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考虑到虚假诉讼犯罪可能侵害的是复合法益,所以在设置该罪法定刑的时候也会相应更加复杂:在协调好该罪与妨害司法罪一节的整体量刑幅度的同时还不能忽视对虚假诉讼的其他严重情节进行评价。[4]因此,针对侵财型虚假诉讼犯罪的基本犯,即提起虚假诉讼但未造成财产重大损失的,其法定刑应比照妨害作证罪设定量刑幅度;针对结果(情节)加重犯,即因虚假诉讼给被害人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其法定刑应比照普通诈骗罪设定量刑幅度。并且对于非侵财型虚假诉讼,行为人也可能手段恶劣,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例如,被害人因名誉受损不堪重负而自杀、侵犯商业信誉导致企业破产等等,或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法律应对其适用升格的法定刑,针对不同情节设置不同量刑幅度,以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1] 卢建平,任江海.虚假诉讼的定罪问题探究——以 2012 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J].政治与法律,2012(11):3.
[2] 徐清宇,周永军.当今我国司法权威的缺失反省及重塑思考[J].法律适用,2009(4):86.
[3] 张明楷.论三角诈骗[J].法学研究,2004(2):99-103.
[4] 杨勇,缪慧琴,李正荣.虚假诉讼刑法规制的现实困境与立法构想[J].人民检察,2013(7):49,51.
[5] 柯良栋译.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57.
[6] 黄风译.意大利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12.
[7] 潘灯译.西班牙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94.
[8] 蒂莫西,A.Q.恩迪科特著.程朝阳译.法律中的模糊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9] 赵赤,李燕山.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J].江汉论坛,2010(2):118.
[10] 杜里奥,帕多瓦尼著.陈忠林译.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4.
[11] 马荣春.刑法完善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4-5.
[12] 张明楷.刑法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5.
(编辑:佘小宁)
Criminal Regulation and Litigation on False Litig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raft Criminal Law Amendment (IX)
HU An-qi
(SchoolofLaw,AnhuiUniversity,HefeiAnhui230601,China)
胡安琪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针对日益严重的虚假诉讼,《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第三十三条对于虚假诉讼在刑事立法上予以规制。在《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出台之前,欲于此探讨虚假诉讼行为上升为刑事犯罪之立法理由,对虚假诉讼犯罪之条文进行分析,并通过分析虚假诉讼犯罪立法设置在罪状、法定刑方面存在的诸问题,提出虚假诉讼犯罪的立法完善建言。
关键词:虚假诉讼;刑法规制;域外立法;妨害司法罪
Abstract:Since the false lawsu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the 33rd article of the Draft Criminal Law Amendment Bill (IX) regulates it in criminal legislation. Before the amendment bill is promulgated,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egislative reasons for formulating it as an unlawful act,and analyzes its existing provisions. Moreover,it also proposes series of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on in false lawsuit by analyzing th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facts about crime and punishment.
Key words:False litigation;Criminal regulation;Extraterritorial legislation;Crime of obstruction of justice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15)07-072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