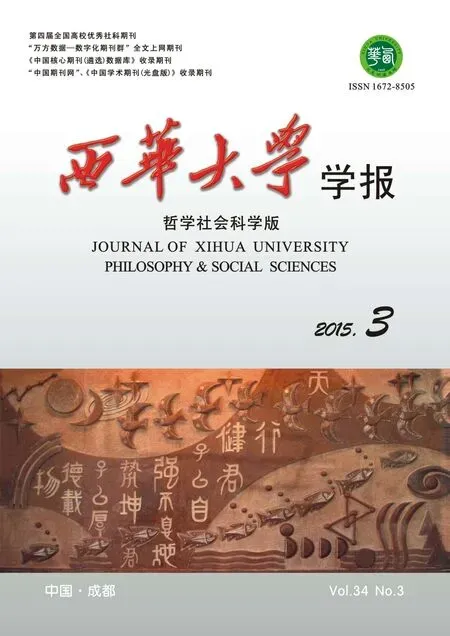入声“非声”,但入声“亦调”
——四川郫县话入声字韵母系统解析
2015-03-10纪国泰
纪国泰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语言文字·
入声“非声”,但入声“亦调”
——四川郫县话入声字韵母系统解析
纪国泰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文章对郫县话入声字韵母系统的解析,一方面用实际例证来阐明前贤“入声非声”的科学论断;另一方面,对有学者认为“一切方言都不存在‘保留入声调’的问题”提出异议。
郫县话入声字韵母系统;音节短促;保留入声;塞音韵尾;“特殊韵尾”
引言
自齐梁时代沈约等人发现汉语“四声”之后的一千四百多年间,“入声”一直被学界视为汉语的“声调”,把它同平、上、去三种声调等量齐观。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有人怀疑入声“声调”的性质。到了四十年代,岑麒祥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把入声仅仅视为汉语的声调,他在《入声非声说》一文中明确指出:
我国四声之中,平、上、去三声皆由于音高之升降关系,纯属声调问题;只入声由于音量(引者按:似指“音长”)较短及收音之不同,与其他三声绝不相侔,实不能混为一谈也……故吾曰:入声非声。若勉强以声类(引者按:实指“韵类”)视之,则极其量只能与平上去三声等量齐观。[1]10
五十年代末,王力先生曾经指出:
严格地说,促是音质的问题,不是音高的问题,不应该认为声调的一种。但是传统上总是把入声作为声调之一种。[2]102
按理说,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来考察入声的性质,“入声非声”的论断应当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声调”主要是指“一个音节内部的音高变化”,如:“妈、麻、马、骂”四个字的读音,就是由“ma”这个音节的升降变化——声调的不同形成的。而“入声”并不像平、上、去三声都是源于一个音节的音高变化,而是指韵母中含有“特殊韵尾”的一种韵类。很显然,“入声”跟平声、上声、去声是不同性质的概念,不应当混为一谈。
然而,尽管“入声非声”的科学论断已经问世近百年之久,但是关于入声性质问题的争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钟福邦先生发表《论入声性质》一文,继续讨论入声的性质,坚持“入声非声”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仍然有学者认为:“入声是否是一种声调,要针对具体语言或方言入声的语音特点来定,不能一概而论。”[3]25还有学者将入声称为“特殊的声调”,理由是:“入声与舒声的区别并不在音高,而在于音的长短,它具备的实际音高并不能区别意义。所以,可以说入声是一种特殊的声调,既称为声调却不具备声调的特征。”[4]
在众多讨论入声性质的著述中,夏中易先生的《入声献疑》[5]一书,后出转精,堪称研究入声问题的集大成者。该书关于“入声非声”问题的讨论非常深入,在很多问题上不乏创见,较此前讨论相关问题的论述前进了一大步,使“入声非声”的论断更加令人信服。
不过,在笔者看来,《入声献疑》第四章第四节关于“保留入声”的问题的有关论述,似有偏颇之嫌,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作为同行,作为朋友,为了让《入声献疑》臻于完美,也为了消除自己心中的疑惑,故不揣浅陋,撰成《入声“非声”,但入声“亦调”》一文,以就教于中易先生以及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其他同行师友。
为了避免空泛议论的流弊,笔者拟采用先例后议的结构方式,故首先将郫县话中常用常见的入声字读音一一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说明,最后针对中易先生的观点展开讨论。
一、老派郫县话入声字韵母系统举例
为什么要以郫县话为例?因为郫县话属于“古入声今读入声”的“岷江小片”方言,此其一;其二,研究方言语音,尤其是入声方言的语音,审音准确非常关键,有些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的语音材料也未必可靠,笔者是土生土长的郫县人,并且年近七旬,对掌握入声字语音材料来说,可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郫县话”前面为什么要冠以“老派”二字?这是因为: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推普”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人口大流动,今天的郫县人,尤其是郫县很多乡镇的年轻人,在他们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古入声今读入声”的已经很少了;只有跟灌县(都江堰市)毗邻的几个乡镇,如花园、友爱、安德几个镇的老年人(年龄一般在60岁以上),在他们的口语中,才仍然是“古入声今读入声”。要讨论“保留入声”的问题,必须以这些人的口语为语言材料,才有意义和价值。这些人的口语,就是本文所谓的“老派郫县话”。
“入声字韵母”这个概念,是陈淑静先生最早提出来的,她说:“入声字的韵母,指所有念入声调的字的韵母,不论韵母是否有塞音韵尾。”[6]92《入声献疑》采用了这个概念,并且给予了新的界定:“‘入声字韵母’指失去塞音韵尾的方言中,只包含古入声字或主要包含古入声字的韵母。这种保持着特殊结构形态的韵母,是入声韵阴声化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入声字韵母凭借其特殊音质发挥其别义作用。”[5]189夏中易先生的这个界定,不仅排除了“塞音韵尾”,而且摒弃了“入声调”的说法,这是需要注意的。笔者认为,称入声字韵母是“保持着特殊结构形态的韵母”,意味着这里的“入声字韵母”既有别于韵尾为[p]、[t]、[k]的中古入声字韵母,又是现代汉语普通话所没有的韵母。《入声献疑》还提出了“入声字韵母系统”的概念,并且说:“岷江小片在方言分区上的意义不是因为‘入声自成调类’,而是小片内各方言均有自己独特的韵母系统。”[5]205
以上是对“老派郫县话入声字韵母系统”这个说法的来历和原因所作的说明。它绝非多余的话,因为后面的讨论将涉及到与此相关的问题。为了称说的方便,后文提及这个概念时,均不再出现“老派”二字。
(一)郫县话入声字声、韵系统
1.声母系统
郫县话的声母,如果不考虑零声母和半元音声母,一共二十二个,它们是:
2.韵母系统
郫县话入声字的韵母,一共九个,它们是:
(二)郫县话入声字读音举例

说明:这是“划”在“笔划”、“划船”中的读音。
2.[o] [yo]
[po]:博搏缚膊薄不脖箔剥驳拨擘缽钵钹;[po]:卜(占卜)仆扑朴泼璞蹼濮瀑曝勃渤;[mo]:木沐末沫没殁莫寞目睦穆牧;[fo]:弗佛福幅幅蝠匐复腹馥伏茯袱服;[to]:读牍椟渎(亵渎)犊笃夺毒独咄戳;[to]:脱铎箨突柝秃凸;录绿禄碌鹿漉麓辘洛落络骆烙陆戮律乐(快乐);[ko]:谷骨鹄;[ko]:哭窟酷梏;[xo]:活豁蠚;[tso]:烛触祝筑粥酌作着斫捉瞩逐琢;[tso]:出掘促龊簇畜猝撮凿浊术戳;[so]:孰熟塾叔淑菽蜀属嘱说朔溯勺芍率蟀束烁铄硕缩索;[o]:入若辱缛弱肉;[o]:勿物沃兀屋握幄龌斡。
说明:①“戳”在表示“刺取”时读作[to],如“戳个腊肉来煮起”。②家禽家畜统称“[tso]牲”(畜牲)。③这是“术”在中药“白术”中的读音。④这是“戳”表示印章时的读音。表示“刺击”的意义时,既曰[to],亦曰[tso]。⑤这是“肉”的书面音,口语中曰[ou13]。

说明:①“略”亦曰[yo]。②“黢”又曰[ty55],如天色很暗曰“[tyo]黑”,也曰“[ty55]黑”。③“削”又音[yɛ]。
3.[iɛ] [yɛ]
[piɛ]:笔滗筚蹩壁璧碧必别鼻愎逼;[piɛ]:辟僻劈霹撇弼;[miɛ]:灭密蜜泌宓秘谧幂蔑汨觅;[tiɛ]:的得涤迪笛翟耋垤迭跌叠滴嫡镝敌蝶碟牒堞喋狄荻;[tiɛ]:铁贴帖惕踢餮倜;ɛ]:力列烈裂冽立粒笠历沥猎栗慄;[tiɛ]:即节疖鲫激迹寂接截集给绩积缉楫缉及极级吸汲笈吉洁结桔秸佶诘拮劼髻揭竭碣偈急杰桀击棘戟劫孑籍藉脊瘠疾蒺稷;[tiɛ]:七柒戚漆膝捷切窃怯乞迄讫惬妾挈;[iɛ]:血恤协胁夕汐隙歇穴勰析晰淅皙蜥悉蟋息熄媳昔惜锡楔泄亵袭习席蓆泣檄爕;[iɛ]:业匿溺逆涅捏怩聂蹑孽臬镍;[iɛ]:一壹噎乙叶亦弈奕益溢缢镒邑悒挹译绎页谒烨揖抑熠。
说明:①“逼”又读[pi55]。②“得”作助词时的读音,如“你做[tiɛ]受[tiɛ]”、“他走[tiɛ]太快,我咋个都撵不倒”。③“翟”表示姓氏时念[]。④“笠”在口语中音音“林”)。⑤这是“截”作量词时的读音,作动词时念[iɛ]。⑥“怩”的古音是泥母脂部平声,应当不是入声字,但在郫县话中,“忸怩”的读音与“扭捏”相同。⑦“揖”在口语中音[ʃ55](音“衣”),如“作揖”。
说明:①这是“搁”在“耽搁”中的读音,单独作动词时音[k13](与“课”同音)。②这是表示容量单位(十分之一升)时的读音。
说明:①“置”的中古音是知母志部去声,“炽”的中古音是昌母志部去声,并非入声字,但在郫县人的书面语中,都读与“织”同。②“吃”的古音是溪母物部入声,本义为“口吃”(说话结巴),现在郫县人仍把说话结巴叫做“结”,人则谓之“结子”。“喫”的古音是溪母锡部入声,本义为“吃饭”。后以“吃”代“喫”,遂致二字音义模糊。但在郫县话中,“吃”的两种意义仍保留入声读音。
(三)常用的中古入声字在郫县话中的“错读”
这里所谓的“错读”,是指中古汉语中的入声字在现代郫县话中,已经不再读入声的现象。“中古入声字”,以丁声树先生编录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7](中华书局1981年10月出版)所收入声字为准;所举例字,仅限于常用常见的范围,并且只讨论声调,不涉及声母的异同情况。例字声调的分类,以郫县话读音为标准,与普通话声调无关。例如:
读阳平的:笠、八、匣、膜、漠、篾、匹;
读上声的:撒、瘪、忸、饺;
读去声的:玉、術、述、黜、栅、压、诺、蛰、蔔、错、掖、液、腋、嚼、跃、桎、饰、式、轼、屹、肄、毅、憶、臆、亿、翼、翊、翌、弋、易、艺、裔、幕、笏、剧、尉、蔚。
这里一共55个。其中读去声的37个,占总数的67%。为什么读去声的会这么多?后面再来讨论这个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55个“错读”的中古入声字中,真正属于老百姓口语读音的,只有三十多个,其余的大多是书面语中的读音,尤其是读去声的许多中古入声字。
上文郫县话入声字读音举例共列举了677个入声字的读音,与这里的“错读”字相比较,“错读”的比例仅占百分之八。如果再除去书面语音的部分,常用中古入声字在现代郫县话中不再读入声的字,应该还不到百分之五。这就是所谓“古入声今读入声”或者“保留入声”的现象。
二、郫县话入声字韵母系统分析
下面拟从韵母系统、韵母结构、调位归属三个方面来分析讨论郫县话入声字韵母系统的特点。
(一)韵母系统的特点
1.韵部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广韵》有34个入声韵部,《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所列的中古汉语入声字,也涉及34个韵部。不难想象,中古汉语入声韵母的数量要远大于34个。现代广州话还有22个入声韵母,而郫县话的入声韵母只有9个。这9个入声韵母,如果按“韵部”来考察,实际只有[]、[o]、[ɛ]、[]、[]五个韵部。再把情况特殊、统字很少的[]、[]略去不计,则郫县话入声字韵部,实际就只有3个了。
郫县话中,入声韵部由中古汉语的34个减少到了3个或者5个,其变化之大不难想见。这种变化,应当是塞音韵尾[-p]、[-t]、[-k]消失之后,入声字为了继续保持其“音节短促”的音质特点,只好“另辟蹊径”——归并整合原来的韵部造成的。由于重新整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留“音节短促”的特点,原来的韵部无法顾及、完全被打乱,三个塞音韵尾[-p]、[-t]、[-k]被一个“特殊韵尾”[]取代,韵部数量自然就大大减少。这应当是郫县话入声韵部“以一当十”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根本原因。可见表示喉塞音韵尾或“紧喉动作”的那个[],对于北方话入声方言“保留入声”音质特点的作用多么重要。
2.声符极富于规律性
关于形声字的读音,清人段玉裁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同谐声者必同部。”[8]817据此,以相同入声字作声符的一组形声字,它们不仅韵部相同,而且都应当是入声字。这个语音规则在上古汉语中很少被破坏,如“昔”在上古为铎部入声,故以“昔”为声符的“错、措、厝、剒”在上古也是铎部入声;再如“卒”在上古为物部入声,以“卒”为声符的“萃、瘁、悴、淬、啐、翠、焠、綷、倅”也是物部入声。但是,由于入声字不断“阴声化”,到了中古时期,以上这些上古入声字便不再读入声而读作去声了。不过“昔”和“卒”在中古仍读入声。
“同谐声者必同部”的语音规则,在郫县话入声字读音中的体现是:具有相同入声声符的形声字,要么韵母相同并且都读入声,要么韵母虽然不同但是仍然读入声。例如“复”,《说文》段注为“房六切”,是个入声字;以“复”为声符的“復、複、馥、腹、蝮”,均读[fo]。至于“愎”,口语中少用,书面语读做[piɛ],与前面几个字的读音不同,但仍读入声。再如“賣”(简化作“卖”),尽管丁声树先生编录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和唐作藩先生编著的《上古音手册》[9],都将它标注为“去声”,但《说文》段注说:“卖或作粥、鬻,是卖、鬻为古今字矣……余六切。”[8]282取段玉裁说法,“卖”应当是“鬻”的古字,读“余六切”,是个入声字,而且《说文》也说它“读若育”,与“育”同音。郫县话中,“读、犊、牍、椟、渎(渎职)”均读[to];“续”读[yo],也是入声。又如“睪”(简化作“”),《说文》段注为“羊益切”,是个入声字。郫县话中,“泽、择”读[ts],“译、绎”读[iɛ],“铎、箨”读[to]或[to],“释”读[ʂ];这些字的读音迥异,但都读入声。还有“斥”,古音“昌石切”(昔韵),郫县话读[tʂ];在郫县话中,“拆”读[ts],“柝”读[to]。“诉”虽然今读去声,但在上古也读入声。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个别字在上古、中古和现代都不是入声,但是以它为声符的字,在古代有的读入声,有的不读入声;而在郫县话中,竟然全都读做入声。例如“亥”,上古是匣母之部上声,音“胡改切”,现代普通话和郫县话都读去声。在中古汉语中,除了“刻”(职韵)、“核”(陌韵)、“劾”(职韵)这少数几个读入声之外,其他以“亥”为声符的字都不读入声。[10]194但是,在郫县话中,“咳、骸、阂、骇”这几个字的韵母都读作[],都成了入声字。不过,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从整个韵母系统的情况看,“古入声今读入声”的现象,在郫县话中是普遍存在的。
(二)韵母结构分析
郫县话9个入声韵母中,4个单元音韵母,5个二合元音韵母。其主要元音的特点,“特殊韵尾”[]的作用很值得关注。
1.主要元音的特点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喉塞韵尾或者“紧喉动作”的形成需要主要元音的配合,主要元音发音时舌位太高或者太低、开口度太小或者太大,都无法形成喉塞韵尾或者“紧喉动作”,也就不能使整个音节变得短促。低元音[A]([a])发音时舌位太低、开口度太大,而高元音[i]、[u]、[y]发音时舌位太高、开口度太小。只有半高元音和半低元音,才有可能在发音时附带产生喉塞韵尾或者“紧喉动作”而使音节变得短促。换句话说,“特殊韵尾”[]只能附著在半高元音或者半低元音上使音节呈现出短促的音质特点。
广州话入声韵母的主要元音就不会是这样。广州话入声韵母,既有[ap]、[at]、[ak],也有[ik]、[uk]、[ut]和[yt],低元音[a]和高元音[i]、[u]、[y]都能充当入声韵母的主要元音。[5]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广州话中,入声字音节短促的音质特点,是靠塞音韵尾[-p]、[-t]、[-k]来实现的,跟主要元音的舌位高低和开口度大小没有一点关系。这应当是保留塞音韵尾的入声和塞音韵尾消失的入声之间的主要区别。
中古入声字被郫县话“错读”为非入声的时候,它们的韵母的主要元音,便既有低元音,如:拉、鸹、挖、八、匣、撒、瘪、栅、压;也有高元音,如:拭、篾、匹、蛰、桎、饰、式、轼、屹、肄、毅、憶、臆、亿、翼、翊、翌、弋、易、艺、裔、隻、術、述、黜、蔔、笏、玉、剧、尉、蔚。虽然也有半低或半高元音的,但是因为不带喉塞韵尾或“紧喉动作”([]),也就没有“短促”的入声音质,如:摸、膜、漠、饺、嚼、跃、错、忸。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郫县话入声韵母的主要元音,绝不由低元音[A]([a])和高元音[i]、[u]、[y]来充当。
郫县话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语音现象是:一些中古的非入声字,在普通话和成都话中,它们的韵母或者韵母的主要元音是[ɛ]、但在郫县话中却被念做[i],以致“些”和“西”、“野”和“椅”、“谢”和“细”、“爹”和“低”、“姐”和“挤”、“写”和“洗”、“爷”和“姨”、“茄子”和“旗子”都分别成了同音字。有人将这种现象视为一般的“音转”,笔者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在普通话和成都话中,韵母或韵母的主要元音为[i]的字,只有古入声字才会被郫县话将韵母或韵母的主要元音念作[ɛ],非入声字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一般的“音转”现象,那就不应该仅限于古入声字。因此,笔者认为:郫县话将有些非中古入声字的韵母[ɛ]念作[i],应该是一种自然产生的“语音规避现象”。“规避”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些非入声字的读音不至于跟入声字的读音相混淆,因为念作高元音[i],便无法形成“紧喉动作”使音节短促了。
了解郫县话入声韵母的主要元音的上述特点,至少对郫县人掌握古入声字会很有帮助。
其次说[o]。孤立地看,[o]和[o]的区别不是很明显。这应该是跟发[o]的时候,舌位较低,又要圆唇,使得“紧喉动作”的形成比较困难有关系。但是,当我们将“窝、鹅、我、饿、屋”放在一起用郫县话来念它们的时候,便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在念“屋”字的时候,喉头有紧缩的感觉,并且气流不是向外散发,而是向下沉降;更重要的是,前面四个音节都分别出现在阴、阳、上、去的调位上,只有“屋”的读音,以其短促的特点而与前面四个音节相区别。使“屋”音节短促的,是发[o]时发音器官自然产生的一种“紧喉动作”,这个“紧喉动作”具有节制主要元音音长的作用,从而使音节表现出“短促”的特点。“紧喉动作”的作用与喉塞韵尾相似,所以我们将它与喉塞韵尾一并拟作[]。
当我们用郫县话念“播”和“驳”、“磨”和“没”、“惰”和“夺”、“唾”和“脱”、“诺”和“洛”、“坐”和“捉”、“搓”和“撮”、“锁”和“索”、“火”和“活”、“我”和“沃”等各组字的时候,发音器官的感觉虽然没有念主要元音为[a]和[]的那几组字时区别明显,但是在念到各组后面的入声字的时候,仍然能够感觉到声带略微要紧一些;同时还发现,不管每组前面的非入声字是什么调类,各组后面的入声字都保持相同的调型,形成“千字一调”的现象。
再来说[ɛ]。三四十年前的老派郫县话中,没有单元音韵母[ɛ],今天被很多郫县人念作[tɛ21](德)、[tɛ21](特ɛ21](勒)、[tsɛ21](则)、[tsɛ21](泽)、[sɛ21](色)的各韵母[ɛ21],都念作[]。因此,只能用入声韵母[iɛ]跟非入声韵母[iɛ]进行比较。
[iɛ]和[iɛ]看似没有什么区别,其实差异很大,而且情况相当复杂。以“椰、爷、野、夜、叶”为例,在普通话中,这五个字的韵母都是[iɛ],“夜”和“叶”都读去声,它们跟“椰、爷、野”构成阴、阳、上、去的声调格局;但是在郫县话中,“椰、爷、野、夜”四个字的韵母都不是[iɛ],而是[i],只有“叶”的韵母是[iɛ],而且读作[iɛ]。“椰、爷、野、夜”在郫县话中的调类,跟在普通话中的调类一致,也是阴、阳、上、去。可见,入声跟非入声的区别非常明显。
是什么因素使郫县话入声字具有“千字一调”的特点?不是别的,就是那个表示“紧喉动作”的[]。应当说,[]不仅取代[-p]、[-t]、[-k]重新整合了郫县话入声字的韵母,而且使入声字在郫县话读音中具有了“千字一调”的调型特点。
以上分析应该能够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在郫县话中,“特殊韵尾”[]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且这个“特殊韵尾”只能附著在半高(半低)元音后面形成入声字韵母。
(三)调位归属问题
作为韵类,入声是跟阳声、阴声相并列的概念。中古及其以前的入声韵类,是以塞音韵尾[-p]、[-t]、[-k]跟阴声韵、阳声韵相并列的,足见“入声”属于韵类范畴的概念,自然不应当与平、上、去相并列,也就是说,入声不应当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声调”,“入声非声”是一个科学的论断。
入声不是“声调”,那么上文中多次提到的“千字一调”该如何理解?
汉语是声调语言,任何一个有意义的音节都有声调,入声字的音节自然不会例外。与非入声字,或者说与阴声韵类和阳声韵类的字在“声调”上的最大的不同,是入声字的“声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内涵不同。非入声字的“声调”,是指一个音节的音高变化;而入声字的“声调”,是指一个方言中入声字的音质特点。以郫县话为例,收音短促、调值中平(33),这就是郫县话入声字的音质特点,也是郫县话入声字的“声调”。在那些真正“保留入声”的方言中,入声字的调型一定是“平调”,因为入声音节的音长极其短促,不可能有音高上的升降变化——起音是多高,收音也是多高。可见,音节短促既是入声字音质上的特点,也是入声字总是“平调”的根本原因。起音有高有低,音节短促却是共性,于是“短平”成为所有入声字的“调型”,调值或55、或44、或33、或22、或11就成为各地入声方言入声字读音在调值上的差异。
第二,构成元素不同。非入声字的声调,是由音节的音高变化来实现的;而入声字的“声调”,是由韵母中的塞音韵尾或者“紧喉动作”来实现的。一般意义上的“声调”应该跟韵母的构成元素无关,而入声字的“声调”却取决于韵母中的构成元素,于是“入声”就成为兼有韵类和声调两种意义的“特殊声调”。
第三,运用对象不同。非入声字的声调“平、上、去”,适用于阴声韵类、阳声韵类的所有音节,而“入声”作为声调,只适用于表示入声韵类的字的调型或者音质特点。
第四,比较对象不同。“平、上、去”可以将所有非入声字按音高分为三大类,因此,平声、上声、去声是具有相同功能、处在同一层面的比较对象;而声调意义上的“入声”,只能表示入声韵类的音节在调型上的特点。由于“入声”跟“平、上、去”不是处在同一层面上的概念,因此岑麒祥先生说只能将入声与平、上、去三声“等量齐观”。
尽管“入声”跟一般意义上的“声调”在以上几个方面都不相同,但是,入声作为表示“独立调型”的概念,或者说用“入声”兼指入声韵类和入声调型,还是很有必要也是无可厚非的。传统音韵学将汉语作“舒声韵”和“促声韵”的分类,分明是不仅注意到了入声作为韵类的本质特点,也照顾到入声作为独立调型的特殊意义。
郫县话入声字“千字一调”,这正是“入声”作为“独立调型”的具体体现。入声是一种“独立调型”,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需要关注的,只是要将它同“平、上、去”的内涵和意义相区别而已。
三、质疑入声“非独立调位”的理论
在“入声非声”的命题出现之后,对于如何认识理解“入声调”和“保留入声”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意见。多数学者并不否认入声属于汉语韵类之一的本质,但同时认为:入声也是汉语的一种声调,为了与一般意义上的声调相区别,故称它为“特殊声调”。
但夏中易先生在其《入声献疑》一书中明确指出:
中古的声调系统只有“平、上、去”的对立;“入声”与“平、上、去”互补,因而不是一个独立调位。中古汉语就没有“入声调类”,那么“保留入声调”、“入声自成一调”之类说法即成为无意义。我们说,“入声非声”,一切方言都不存在“保留入声调”的问题。[5]225
入声的调位资格被否定之后,由于“入声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没有办法被否定的,于是《入声献疑》将入声称为“平、上、去”的“条件变体”。为了证明“条件变体”理论,《入声献疑》首先介绍了北方话入声韵历史演变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入声韵以带-p、-t、-k尾为基本特点;第二阶段,入声韵以带-尾为基本特点;第三阶段,入声韵塞音韵尾丢失,韵母主要元音不同程度地带有紧喉动作,并形成数量不等的入声字韵母;第四阶段,入声韵绝大部分与阴声韵合流。[5]226
接着,便宣讲了入声韵演变为阴声韵(简称“阴声化”)的过程和方式:
入声韵音节声调作为系统中某调位的变体,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演变条件与方式。第一、二阶段中,入声韵音节声调不同程度地带有自身个性,与系统内相应条件变体共存。演变进入第三、四阶段,伴随塞音韵尾的弱化、脱落,入声韵音节声调逐渐拉长音时、调整音高,最后达到与相应变体融合。[5]226
笔者按: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入声献疑》的意思是:“入声韵音节声调”从古到今都只是以“平、上、去”的“条件变体”形态存在的;入声韵在完成“阴声化”演变之后,入声韵音节除了演变为阴声韵音节之外,各个入声韵音节的声调,就分别变成与它们曾经“共存”的“相应条件变体”(平、上、去)的声调。
(一)“条件变体”说质疑
按照《入声献疑》阐述的“条件变体”理论,至少有两种现象不好理解也无法解释。
1.入声字“千字一调”现象无法解释
如果入声字的声调,从来都只是“某调位的变体”,那就是说,入声字的声调既有平声的变体、上声的变体,还有去声的变体。尽管我们无法理解这“变体”是怎样的读音,但是这“变体”既然在音高上各不相同,那么“共存”于各个“相应变体”的入声韵音节,在声调上势必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郫县话入声字音节,还是那些真正“保留入声”的地区的入声字音节,在声调上都具有“短平”而“千字一调”的特点,入声似乎总是以一个“独立调位”存在于这些入声方言中。
2.上古入声字“阴声化”现象无法解释
如果只是从中古汉语的入声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声调分布来看,“条件变体”理论似乎不无道理。因为中古汉语中的入声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它们的声调确实比较“均匀”地分布在阴、阳、上、去之中,似乎“最后达到与相应变体融合”。
然而,入声字的“阴声化”演变并非只有一次,不少上古汉语中的入声字在中古汉语中就已经“阴声化”了。而上古入声字“阴声化”的现象却并不支持“条件变体”理论的成立。因为上古入声字“阴声化”之后,其声调并没有像中古入声字的声调那样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普通话“阴、阳、上、去”中,而是绝大部分都读作去声。
笔者将唐作藩先生编著的《上古音手册》同丁声树先生编录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加以对比,对比的结果是:上古入声字到中古已经“阴声化”了的一共346个,其中读平声的4个,读上声的9个,读去声的333个;读去声的占96.2%,读平声的占1.2%,读上声的占2.6%。
按照“条件变体”理论,根据以上对比结果,那就意味着:在上古汉语中,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入声字的声调,都只是去声这一调位的“条件变体”。这说得过去吗?
很显然,《入声献疑》的“条件变体”理论是值得怀疑的。
(二)质疑衡量“保留入声”的标准
为了给否定“保留入声”或者“保留入声调”找到理论依据,《入声献疑》提出了衡量“保留入声”的标准:
论入声是否被保留,应以“韵尾是不除阻的塞音[-p]、[-t]、[-k]和喉塞音[]”的韵母是否被保留作为其确定的内容。根据这一明确的标准,说粤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南方言、闽东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晋方言之类“保留入声”;岷江小片各方言、长沙话、成都话、北京话之类“入声消失”,则无疑是正确的。[5]225
针对《入声献疑》的衡量“标准”,笔者提出不同意见与作者商榷。
笔者认为,“标准”衡量的对象有误。《入声献疑》提出的这个衡量“标准”,适用于“古入声韵母”“是否被保留”,并不适用于“入声”或“入声调”是否被保留。
诚如《入声献疑》所说:“大凡强调某方言是否‘保留入声’,往往更侧重指‘入声调’,比如说‘长沙话保留入声’即是如此。”至于什么是“入声调”,笔者已在前文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和介绍,“入声调”跟“古入声韵母”绝不是可以混淆的两个概念,自然不能运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
我们再三强调指出,“入声调”是指入声字在读音上的“音质特点”即音节短促的“短平”调型和“千字一调”。并且还分析了使入声字“音节短促、千字一调”的因素或手段并非只有“韵尾是不除阻的塞音[-p]、[-t]、[-k]”一种。像郫县话入声字这样,除喉塞韵尾[](如[])之外,还有“紧喉动作”这样的发音因素和手段。人们所说的“保留入声”或者“保留入声调”,都是针对古入声字是否还保留入声字的“音质特点”来说的,跟它是否还保留“古入声韵母”基本没有关系。
笔者认为,《入声献疑》之所以会在衡量是否“保留入声”的标准上产生“误解”,应该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客观上说,《入声献疑》的作者是道地的成都市区人,对一个不操入声方言的人来说,要真正深刻理解入声字的“音质特点”是比较困难的,至少是不够全面的。由于对入声字“音质特点”缺乏深刻理解,就很难正确理解“入声调”中的“调”的涵义,以致将“入声调”跟一般意义上的“声调”混为一谈。其实,如果换一个说法,“入声调”犹如“入声腔”。笔者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与某人初次见面,只要听他在谈话中把“直、吃、石”念作[tʂ]、[tʂ]、[ʂ],或者把“黑、白、特”念作[x]、[p]、[t],就不难猜测到他(她)是郫县人或者都江堰市的人;如果说话人把“急、切、息”念作[tiɛ]、[tiɛ]、[iɛ],把“直、吃、石”念作[tʂ]、[tʂ]、[ʂ],但是把“黑、白、特”念作[xɛ21]、[pɛ21]、[tɛ21],那么说话人很有可能是彭州市(丰乐、桂花、庆兴、君平、丽春几个镇除外)或者原新繁县所属乡镇的人。因为彭州、新繁虽然也是“岷江小片”方言区,但是“保留入声”不够完整,与都江堰市和郫县相比较,彭州、新繁话中已经没有入声字韵母[]、[i]、[u]。甚至即使是“老派郫县话”,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徐堰河以北的唐昌地区、郫筒镇以东的红光、犀浦等乡镇,[]、[i]、[u]就已经保留得不完整或者根本没有了。以笔者的经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郫县的花园、友爱、安德这几个乡镇是“保留入声”最完整的地区。古入声字在这几个乡镇的居民口中,都念的是入声字韵母,并且都是“千字一调”,我们姑且叫它作“入声腔”。入声字在“入声腔”中总是保持着一个固定的调型,这个固定的调型就是所谓“入声调”。这“入声调”跟《入声献疑》所理解的“声调”,应该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是《入声献疑》竟然将它们视为相同的概念,于是加以排斥,反对“保留入声”的说法。
其次,从主观上说,《入声献疑》坚持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似乎认为:既然“入声非声”,如果承认“入声调”,或者承认入声是一个“独立调位”,岂不是就否定了“入声非声”的科学论断?其实,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因为“入声调”跟一般意义上的“声调”并非同一层面上的概念,承认“入声”或“入声调”的“独立调位”资格,并不影响“入声非声”这一科学论断的成立。具体情况,笔者在前面已经详加分析和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入声献疑》用衡量“古入声韵母”是否保留的“标准”去衡量“入声”或“入声调”是否被保留,这样的做法是不恰当的。
结语
笔者根据郫县话入声字韵母系统对《入声献疑》“‘入声非声’,一切方言都不存在‘保留入声调’的问题”的观点表示怀疑。笔者的“怀疑”也只是一家之言,希望能得到夏中易先生以及其他同行师友的批评指正,这才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和目的。笔者所坚持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入声“非声”,但入声“亦调”。
[1] 岑麒祥.入声非声说[J].图书月刊,1942(2).
[2]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 门秀红.“入声声调说”浅析[J].和田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
[4] 国术平.从语言内部补偿看入声舒化现象[J].语文学刊,2006(5).
[5] 夏中易.入声献疑[M].成都:巴蜀书社,2009.
[6] 陈淑静.简论入声韵与入声字韵母的关系[J].河北大学学报,1993(3).
[7] 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K].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 唐作藩.上古音手册[K].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10]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
[责任编辑 李秀燕]
Entering Tone :“ Not a Tone”, But Still “ an Intonation”——The Vowel System Analysis of Entering Tone Words in Pixian Dialect
JI Guo-tai
(CollegeofHumanity,Xihua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39,China)
The vowel system analysis of entering tone words in Pixian dialect covers: to verify former scholars’ scientific judgment that “ entering tone is not a Tone ” by examples; to hold a different view from those scholars who think that “ ‘keeping entering intonation ’ is not a problem for all dialects.”
the vowel system of entering tone words in Pixian dialect; short syllable; keeping entering tone; tail vowel of glottal stops; “special tail vowel ”
2015-03-13
纪国泰(1948—),男,教授,主要从事古籍整理及四川方言的研究。
H172.3
A
1672-8505(2015)03-00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