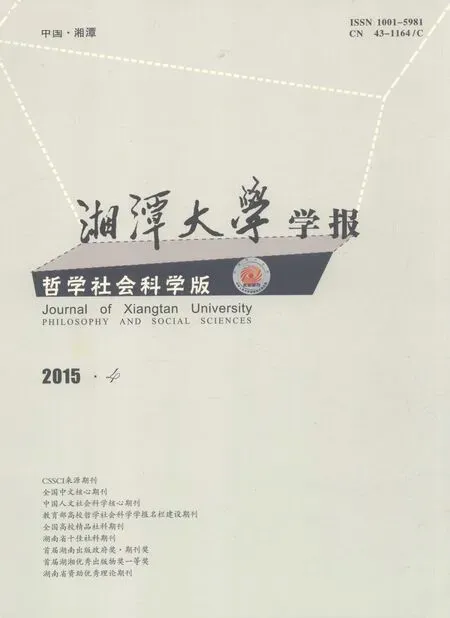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策略*
2015-02-22熊辉黄波
熊辉,黄波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策略*
熊辉,黄波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摘要:解殖民是后殖民时代的关键词之一,中国的解殖民化研究经历了从理论译介再到具体研究的过程,但至今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对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研究往往混合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而且专门探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成果十分稀缺。实际上,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浓厚的解殖民色彩,它主要通过以下翻译策略来达到解殖民的目的:中国文学主体身份的确立、弱小民族以及东方文学的翻译、翻译改写、被压迫阶层文学的翻译以及对传统的回归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文学的独立性。
关键词:解殖民;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翻译策略;后殖民语境
20世纪中期,很多民族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纷纷独立,宣告以武力控制和强权政治为典型特征的殖民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民族国家在主权独立之后开始寻求文化身份的独立,于是从被殖民文化内部生发出一股解构强势殖民文化的力量,这股力量并非后殖民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因素,它几乎伴随着整个西方物质和文化殖民的过程,只是在后殖民时代表现得更加突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半殖民地的状态,其文化和语言文字虽未被完全殖民,但在面对强势文化的压迫和侵略时,其解殖民活动依然清晰可辨。
一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最能够彰显出两种文化之间在交流中的地位和权力关系。因此,殖民地文学在寻求平等对话的后殖民语境中,就会将翻译作为解殖民的手段,由此引发人们对翻译文学解殖民的研究兴趣。由于译者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加上文学翻译在文化地位、文化身份和文化选择中的可变性,由此便在被殖民语境中赋予文学翻译解殖民的功能。
探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化特征,势必意味着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殖民化色彩,否则有何殖民需要化解呢?“晚清至今的现代中国文学,与其说是现代性的文学,不如说是半殖民与解殖民的文学。”[1]所谓“半殖民”文学即部分殖民化的文学,是指翻译文学在词汇和句法上接受了外语的表达方式,而在文字的书写形式和读音上却保持了中文的本来面目。文化交流始终摆脱不了权力关系的制约,中国社会文化自清朝末年开始便迈入老态,固步自封或夜郎自大的心态被外国强势文化撕扯破碎,国人纷纷反省民族文化,从此以弱势文化的身份走上了向西方学习之路。因此,中国人在翻译外国文学的时候,每当遇到中英文不对等的情况,就会采用“削足适履”的方法,让汉语屈从英文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这好比是在中国文学语言系统中开辟出一块领地,专门安放那些不合中国文法的西方语言要素,主动迎接西方语言对民族语言的殖民。比如清末白话小说翻译、五四白话新诗翻译以及后来各体文学的翻译,它们都是在背离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让部分西方文学词汇和表达方式侵入中国文学。而年轻一辈的新文学作家在否定传统的情况下,又只好向西方文学或翻译文学寻求创作资源。于是模仿这些新输入的表达和内容进行创作,或者以翻译进来的东西作为衡量中国的标准,便成为中国现代较为流行的做法,这样的文学环境无疑营造出中国文学主动接受殖民的土壤。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的部分殖民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一则因为中国语言需要承载并表达许多从国外输入的思想观念,再则因为中国语言自身的匮乏贫弱需要从西方语言中吸取营养。周作人认为思想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语言表达的更新:“假如思想还和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现在呢,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2]58-59因此,中国文学语言必然会在清末新思想传入的浪潮中发生改变,进而向西方寻求思想和形式来达到适应现实之目的。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的部分殖民化最早开始于清末时期,“梁启超用一种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之文,编撰各种杂志,号‘新文体’。”[3]114五四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都与西方文化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或者说自从翻译为中国输入了外国新思想和新表达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便有了新的参照对象,如若自身发展出现了困难就把目光投向国外,总认为外国文学可以医治中国文学的疾病,对外国文学的这种依赖思想自然会导致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殖民。“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情境中,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就转而向西方寻求解救之道,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同时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思维习惯,一种类似于下意识的反应”。[4]97翻译作为连接中外文化和文学的纽带,是最早被也是最容易被外文殖民的领域,部分借用外国文学的思想和文字表达当然会导致部分殖民现象,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还出现了鲁迅那样完全西化的“硬译”,那中文的殖民程度真是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对中国文学解殖民色彩的研究最早兴起于西方学术界和海外华人学术圈。但海外汉学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解殖民的研究主要基于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立场,没有充分且深入地对大陆半殖民化社会状态下的解殖民研究,当然更没有将解殖民化推延到现代翻译文学领域。目前国内解殖民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翻译文学领域的解殖民化研究更显滞后。专门探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的解殖民化特质的成果极稀,目前主要有两篇英语硕士论文涉及此题:一是《解殖民化与文学翻译: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新视角》(刘小玲,新疆大学,2006年),二是《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解析中国文学翻译中的解殖民化》(李峥,天津大学,2012年),此二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颇具创新性,但对解殖民因素的挖掘还欠深入,很多论述停留在个别文本或译者身上,难以勾勒出研究对象的复杂面貌。此外,还有多篇文章涉及到中国文学外译中的解殖民现象,与本课题探讨的解殖民化有相关性,但却是不同的研究对象。
由于特殊时代使然,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殖民化和解殖化特征十分明显,鉴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主体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其解殖民的研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如前所述,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半殖民化的特征,因此很多清醒的中国人发出了捍卫中国文学“纯洁性”的呼声,很多译者采取多种翻译策略来阻止外国文学的西化影响,凸显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化特征。具体而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通过如下策略或方法来达到解殖民的目的。
翻译主体身份的确立与解殖民。清末文学翻译主要以英法文学为主,彼时国人内心仍存有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对西学大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故选择何国何人的作品来翻译并不构成殖民化的威胁。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学随着海禁的强制解除涌入古老的中国,即便清末人士已经接触并了解了西方文化思想,但他们仍然认为中国文化要强于外国,唯器物之“末技”不如“夷人”。从南社会员的话中便可窥探当时知识分子自足心态的端倪:“言乎科学,诚相形见绌;若以文学论,未必不足以称伯五洲,彼白伦、莎士比亚、福禄特儿辈,固不逮我少陵、太白、稼轩、白石诸仙哲远甚也。”[5]31殊不知西方文学样式十分丰富,戏剧和小说的成就更是达到了中国文学难以企及的高度。清末国人的心态虽略显自大,但客观上却抵制了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殖民,使西方经典文学名著消融于中国近代文学的浪潮中。就小说翻译而言,林纾将英美小说翻译成章回体,并把不符合中国伦理和审美观念的内容加以中国化改造;在诗歌翻译方面,马君武、苏曼殊、梁启超等人的翻译采用文言和古诗体形式,其译作不会给中国读者带来审美的陌生感;在社会学翻译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采用古雅的文言,并用中国固有术语去翻译国外新兴的专有名词,后人对其译文的褒贬评价姑且不论,译文避免了西方社会学词汇对中国语言大面积的入侵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西方物质文明强势进入中土的清末时期,中国人秉着文学的主体身份和近乎不复存在的文化优势心理,用本土化的文体和内容阻止了英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殖民扩张。
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与解殖民。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可谓异彩纷呈:从时间上看,各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均被翻译到中国;从空间上看,强大的欧美文学与贫弱的东欧和亚洲文学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译介。然而,不同国家文学的翻译对中国影响迥异,面对被西方物质和文化殖民的强大压力,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只能借助翻译弱小民族的文学来增强自身对抗欧美文学的力量,成为近现代中国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重要手段。面对“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6]的不足,鲁迅从文学翻译之初就注重对弱小民族文学引荐,以对抗英美法德文学的翻译潮流,进而解构强势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殖民化。20世纪初叶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主要收录了东欧及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开创了中国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传统;五四时期《小说月报》推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是中国知识界在面对强势文学不断进入中国文学肌理的过程中,寻求平等和制衡心理的积极应对措施,表达了“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7];抗战时期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掀起了新的高潮,那些被法西斯侵占国家的文学以及弱小民族富于抗争精神的文学得到了大量的译介,比如西班牙文学、波兰文学以及苏联文学等是当时译介数量最多的文学,增强了中国文学对抗日本文学以及英美文学殖民的力量。除翻译弱小民族文学可以解构英法美德文学的殖民外,对东方文学的翻译则同样具有结盟以达到解殖民的目的,周作人等对日本文学的翻译、郑振铎等对印度文学的翻译、郭沫若等对波斯文学的翻译等等,客观上达到了用东方文学的审美观念对抗西方文学的效果,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重要举措。弱小民族文学和亚洲文学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而言,无疑形成了不言自明的同盟关系,推动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化步伐。
翻译文学的改写与解殖民。任何文学翻译都不可避免对原文有所改写,一是文学翻译本身的局限决定了译文不能完全呈现原文的风格和内容,二是译者出于某种翻译目的人为地对原文加以改写。而改写必然“要对文本作相当大的改动,以更适合特定读者比如儿童或特定的翻译目的”,[8]3因此改写的目的更有利于目标语文化的传播,其势必会有意隐藏或削弱原文的异质化力量,客观上起到解殖民化的效果。翻译文学的改写具有两种层次:强势文学对弱势文学的殖民化改写,以及弱势文学对强势文学的殖民化认同或解殖民化改写。改写比翻译学上所谓的“创造性叛逆”更具目的性,虽然一般意义上的创造性叛逆对弱势文学而言也具有很好的解殖民化功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对原文的改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或误译,译者在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对强势文学无意识的改写,客观上起到了解殖民化的效果;二是有意识的误译行为,译者出于某种翻译目的对原文的内容进行修改,使之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三是对译文的改编,此改写往往发生在戏剧领域,很多剧作家把翻译小说改编成戏剧,而且根据本国需要将译文的内容、背景、故事情节或结局加以改写。比如1941年在重庆公演的《遥望》是根据美国剧作家奥尼尔《天边外》的改写,赵清阁的戏剧《此恨绵绵》是对英国名著《呼啸山庄》的改写,马彦祥的《古城的怒吼》是对法国剧作家萨杜尔《祖国》的改写。译者对强势文学的改写以及中国作家对翻译文学的改写,均因译者或改编者主观目的和民族文学经验的渗入而具有很强的解殖民化效果,各种改写后的翻译作品均汇入到中国文学的行列,其原文所具有的殖民化力量也随之消失殆尽。
被压迫阶层文学的翻译与解殖民。从强势的殖民国家内部寻求反抗的力量,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解殖民化的重要手段。由此,我国翻译了大量反映欧美发达国家被压迫阶层人民艰苦生活的作品,以及他们顽强抗争强权政治的文学作品,借助被压迫阶层作品中的反抗精神来增强自身解殖民的力量。比如对黑人文学作品的翻译,对反映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革命斗争的左翼文学的翻译等,都体现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解殖民的主观意图。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是利用了被压迫阶层文学所蕴含的反抗资本主义强权的力量,但解殖民与反抗权贵之间存在本质差别,所以不能将西方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等而视之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努力。虽然二者所表现出来的状况均为对殖民国家政治和压迫的反抗,但西方被压迫阶层反抗主流政治的行为是一种阶级或种族对抗,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翻译文学反抗西方强权政治的斗争属于后殖民语境下的解殖民运动。
翻译文学对传统的回归与解殖民。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在经历了五四前后的喧嚣和杂乱之后,开始逐渐进入有序的发展阶段。新文学先驱出于“策略”或“创新”的目的而对传统文学加以排斥,导致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殖民中国的前沿舞台,中国新文学充斥着外国的句法、词汇、思想和审美,沦为强势文学的殖民地。在这种看似无法逆转的殖民化浪潮中,很多译者从捍卫民族文学主体性的角度发出了解殖民化的呼声,形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的顽固和守旧派。换个角度看,他们实际上捍卫了中国文学的独立性和民族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解殖民化的中坚力量。从翻译实践上看,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以“绝句”的形式对抗新诗的自由化,闻一多与徐志摩诸君的格律主张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诗歌审美的回归,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时用中国文学的方式置换外国人的思维和语言表达,这些翻译避免了英语对汉语的殖民。从翻译主张上看,卞之琳提出文学翻译应当捍卫汉语的“纯洁性”[9],林语堂主张文学翻译要有“国化”[10]60的过程等,也都是解殖民化的提倡。就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而言,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晚唐诗热”体现出中国现代作家对文学传统的回望与承传,同时借此对被部分殖民化的中国现代文学采取谨慎的修正态度;横跨20世纪20-30年代的“学衡派”被讥为保守分子,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观念将中国文学树为主体,西方强势文学则处于部分“给养”的辅助地位,这些创作和思想主张成为中国现代翻译解殖民化的有力声援。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翻译实践、翻译主张以及创作思潮对传统的回归和再现,具有鲜明的解殖民化色彩,其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有待重新估量。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在西潮涌动的变革年代,为中国社会文化输入西方进步思想和语言表达,并导致其自身和中国现代文学的部分殖民化,这是学界常识性的共识。但与此同时,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也通过一系列的翻译策略,来达到解殖民和建构民族文学的意图,这在今天同样应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三
中国社会文化自近代以来在与西方强势文化的遭遇中,自身的主体性不断地被削弱。西方思想、词汇以及表达不断地侵入文学的内部肌理,中国文学的殖民化已成为事实,翻译文学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中扮演着殖民与解殖民的双重角色。
在后殖民语境中研究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有助于重新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面貌。目前学术界多关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殖民化影响,而忽视了其具有解殖民的另一种面貌。透过解殖民的角度,我们在“现代性”、“欧化”、“进步性”等拥抱西方的价值体系之外,还应该体认到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民族立场和对强势文化的抵制,开拓出新鲜的翻译文学研究空间。而且,从解殖民化的角度出发可以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他者立场和多维视野,重新厘定各种夹缠的关系,比如欧化与现代化、欧化与殖民化、现代化与民族化、半殖民地与文学部分殖民化、保守与进步等。因此,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中国现代社会解殖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十分开阔的前景。
我们应该理性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策略。所谓“理性认识”,一是我们应该在声势浩大的西化浪潮中冷静观察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重新去认识昔日的“古今之辨”和“新旧之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保持民族文化的本位,不至于迷失在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中。二是我们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各种解殖民策略应该有全面的认识,不能仅仅看到其解殖民的优势而忽视了它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更不能在西化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语境中漠视翻译的解殖民策略,将之视为时代发展的逆流,从而否定这些翻译策略对民族文化主体身份的建构之功。
海外学术界在探讨世界范围内的解殖民运动时,很难将中国的半殖民化纳入研究范围,致使中国大陆的解殖民研究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事实上,尽管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仅具有半殖民的性质,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解殖民意图表现得较为突出,应该成为当下学术界和思想界深入讨论的话题。
参考文献:
[1]李永东.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J].天津社会科学,2015(3).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张星烺.欧化东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冯平.梦罗浮馆词集·序[M]//南社丛刊(第21集).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6]鲁迅.“题未定”草(1)[J].文学(第5卷第1号),1935(10).
[7]记者.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引言[N].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 号),1921-10-10.
[8]Mark Shuttleworth&Moira Cowie.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Manchester,UK: St.Jerome Publishing,1997.
[9]卞之琳.新诗和西方诗[J].诗探索,1981(4).
[10]林语堂.论翻译[M]//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海岸,选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万莲姣
“女性主义文学/性别研究”专栏(笔谈,3篇)
The De-colonial Strategie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XIONG Hui,HUANG Bo*(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Decolonization is a key word in the post-colonial era.From the theory translation to the concrete research,the study of decolonization in China has still stayed in the initial stage.The discussion to the decoloniza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s mixed with the post-colonialism,and the specific research on the decolon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has got little achievement.Actually,the 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has very strong sense of decolonization through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such as establishing the subject ident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translating the literature from the weak and eastern nations,re-writing during translation,translating the literature of the oppressed class and coming back to the tradition.To some extent,the decolon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maintained the independence of national literature.
Keywords:decolonization; modern Chine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strategies of translatio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作者简介:熊辉(1976-),男,四川邻水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文学、比较文学研究。黄波(1987-),男,重庆云阳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1-30
中图分类号:I206; 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5) 04-008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