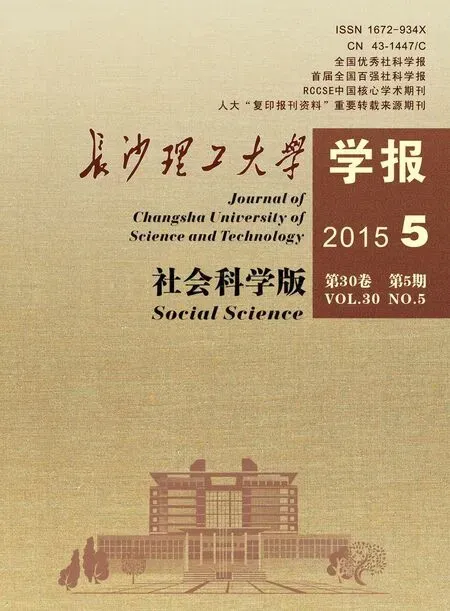潜隐的浪漫:穆旦40年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
2015-02-22马炜
马 炜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46)
潜隐的浪漫:穆旦40年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
马 炜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46)
穆旦40年代的诗歌创作自觉追求“思维复杂化、情感线团化”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表达方式。但其诗歌的主旨、立意和内在精神却与纯正的现代派风格有差异,表现出与浪漫主义的相通。穆旦诗歌中有明显的英雄崇拜,坚强的乐观精神以及对浪漫主义本质特征“自然”的推崇。这些浪漫主义因素成为他创作的深层精神资源,影响他诗歌风格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探讨穆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以及他的现代主义诗歌中包含浪漫主义特质的深层原因。
穆旦;40年代诗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
众所周知,穆旦是一个现代派诗人,他受英国现代派诗人奥登、燕卜荪等人的影响,自觉追求“思维复杂化、情感线团化”[1]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表达技巧。但只要细读穆旦的诗就会发现,他的一些诗篇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特别是早期和晚期的一些诗篇,从形式上看,完全是浪漫主义的吟唱。他现代意味最浓的诗作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40年代也是他最有意识地追求现代派创作技艺的阶段。诗歌具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情感的抒发趋向于“线团化”“复杂化”,有些诗篇甚至流于晦涩。但诗歌的主旨、立意和内在精神却与纯正的现代派有差异,表现出与浪漫主义的相通,浪漫主义成为他创作的深层精神资源,内化在他的诗歌文本深处。文章着重从主题思想角度探讨穆旦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因子,认为其诗歌中有明显的浪漫乐观精神以及对浪漫主义本质特征“自然”的推崇。通过梳理穆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心路历程,深入探讨其现代主义诗歌中内蕴浪漫主义的深层原因。
一、浪漫乐观精神
40年代,在民族危难,一切信仰、价值崩溃的时候,诗人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遭到破灭,敏锐地感受到自身以及所有个体人生存的悲惨处境,遭遇着严重的精神危机。他深深感到绝望,但又不屈地“反抗绝望”。他的诗作达到了深入苦难的品质,又给人希望。他在诗作中塑造了大量的浪漫英雄形象并对这些英雄给予了热情的赞美和歌颂。穆旦40年代诗歌中始终充溢着一种浪漫乐观精神。
(一)英雄崇拜
西方现代诗的一个特点就是抛弃一切信仰和理性,英雄、崇高、乐观这些褒义的字眼是被否定和嘲讽的。现代主义诗歌中是没有英雄的,或者说有英雄而没有英雄崇拜,英雄往往和常人同质化,并没有高出常人的品质。只是作者为了探讨形而上命题的一个符号,不承载任何现实意义的功能。英雄的命运是悲剧性的而且这种悲剧性往往是与生俱来的,是本根意义上的悲剧存在,就像西绪福斯神话中那个一次次把巨石推上山做着无始无终无用功的存在主义英雄一样。现代派作品往往给人彻底的虚无之感。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提倡英雄崇拜,充溢着乐观精神,浪漫主义的英雄通常有异于常人的非凡的智慧,过人的体力,坚强的意志,是常人的楷模,面对最困难的环境,英雄能凭坚强的意志去战胜和克服。即使英雄最后失败了,也给人以希望。
穆旦诗歌中塑造了很多“英雄”形象,在诗作中对他们给予了高度的赞美和歌颂,表现出浓郁的英雄主义和英雄崇拜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承接。40年代国家处于危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穆旦歌颂最多的英雄就是为国战斗的战士,把战士誉为“人民里有了自己的英雄”(《给战士》),当他们战死在战场时,是“最高的意志,在欢快中解放”“他把自己的生命交还/已较主所赐给的更为光荣。”(《奉献》)此外,英雄更是革命事业的先导,是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救星,“是英雄们的游魂活在今日”(《旗》)赞颂“伟大的导师们,不死的苦痛”“不灭的光辉”,导师是英雄式的人物,是永远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指向标,并表示要继承导师们的遗愿,“你们唯一的遗嘱是我们,这醒来的一群,/穿着你们燃烧的衣服,向着地面降临。”(《先导》)
在写印度“圣雄”甘地的诗中,穆旦对英雄的赞美和敬仰达到了顶峰。在诗中,穆旦毫不吝啬地将所有美好崇高的词语都给了“甘地”“一个巨大的良心”“因爱而遭受伤痕”“骄傲的灵魂”“勇敢的和上帝同行”“固守着良知而不转移”他是人民的救星,他牺牲自己而成就了印度人民“凡是他走过的地方,人民得到了起点,/甘地以自己铺路,印度有了旅程,再也不能安息。”穆旦甚至把甘地神化,称他是“一座古代的神龛”“是无信仰里的信仰”“在曙光中,那看见新大陆的人,他来了把十字架竖立,/他竖起的是谦卑美德,沉默牺牲,无治而治的人民,/在耕种和纺织声里,祈祷一个洁净的国家为神治理。”
在这些诗中,诗人对英雄以及英雄式的人物给予了高度的赞美。“穆旦的‘英雄’显然不是有着强烈个体意识和专断意志的古希腊英雄,更不是尼采式的信奉极端个人主义、视民众为群氓的‘超人’,而是为民族大义而英勇战斗的‘战士’,……像甘地这样救民于水火又有高尚道德人格的‘圣雄’。”[2](P258)英雄身后是广阔的现实大地,不像现代派作品中的英雄是为了生命本真的存在而战斗。英雄的失败,是现实的因素使然,不像现代派作品中英雄的悲剧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可改变的。穆旦诗中的英雄是浪漫主义的英雄,为理想而战,为信仰而斗争,即使失败了,也给人以希望。穆旦诗歌中浪漫英雄的形象塑造是他自身英雄崇拜的情感需要,他自己就曾投笔从戎,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和担当,所以说穆旦“对‘英雄’的景仰、称颂,与其说更多地表现了穆旦的个性主义精神,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了他强烈的济世情怀和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对儒家道德人格理想的深深眷恋。”[2](P258)
(二)反抗绝望
在民族危难,一切信仰、价值崩溃的时候,诗人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遭到破灭,自身的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使诗人遭遇着严重的精神危机。战争撕破了文明的虚假外壳,一切展现出本来的丑恶面目。诗人敏锐地堪破了现代文明的虚假神话之后,陷入了对自身以及知识分子的深深怀疑与否定之中,他将笔触对准自己的灵魂,进行不懈的拷问。他用拷问自己,将自己逼向绝境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特殊的反抗虚无、战胜自我的方式(《夜晚的告别》)。同时,他又以一己为出发点扩展到对知识分子阶层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探求。《被围者》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受难、精神搏求的坚忍品格。“每一秒白热而不能等待,/堕下来成了你不要的形状。/天空的流星和水,那灿烂的/焦躁,到这里就成了今天/一片砂砾。”诗中不断出现相互矛盾的意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希望与失望的纠缠。诗人在洞悉了悲剧绝望之后,并没有一味沉沦,而是试图“反抗绝望”,“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他完整。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被围者”以大无畏的勇气来彻底打破自己,在毁坏中求新生,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突围”,即使结果是牺牲。但“作为‘被围者’,忧虑、挣扎、突围是其精神与行动的特征。”[3]穆旦笔下的“被围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的一个侧面,是在逆境中求希望,始终没有放弃呐喊和搏求的一群。
穆旦显然不局限于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知识阶层的生存状况的反思,他的眼光始终是面对着现实生活中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活下去》创作于1944年9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当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如同暴露的大海/凶残摧毁凶残,”在绝望中“活下去”是失去一切之后的最后坚守。“希望,幻灭,希望,再活下去/在无尽的波涛的淹没中”,这里“活下去”已经不是一种呼号,而是上升到对坚忍的生命哲学的一种概括。应该说,这首诗基调是比较高昂的,有一种在绝望中呼号的深沉的力量。“穆旦像西方现代派诗人那样敏感着内心世界的剧烈冲突、生命的虚无与苦难,但他并未堕入彻底的虚无主义或宗教救赎之中,而是在最个人化的表达中与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血脉相通。”[4]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歌表现苦难,却并没有在苦难中不可自拔。穆旦的眼光始终是向下的,关注现实的人群,他笔下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现实的苦难是能克服和改变的,所以他的诗中充溢着乐观精神,给人以不灭的希望和信仰。“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任务是通过寻找他自身以外的足够宽广、能够包容他所有行为的实体来调和自己内部的矛盾。他再次成为一个信仰的思考者。因为信仰不仅仅是对未知世界的描述。它是一种能量的理论——鼓舞自然也鼓舞他自己的能量。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信仰是一种智力和情感的需要。”[5]穆旦诗中的信仰是一种反抗绝望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他的诗歌充溢着浪漫主义的乐观激情。
二、回归自然
对发达的工业文明的批判,是西方浪漫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议题,某种程度上是催生浪漫主义的一个原动力。浪漫主义兴起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一时期正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工业文明给人带来丰厚物质的同时,人也在机器文明下异化,人与自然日渐疏离,人类精神的“神性”和生存的“诗性”沦落。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认为:“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6](P7)所以,浪漫主义作家提倡“回归自然”,用自然的优美来涤荡人们被物质沾染了的心。正如刘小枫所说:“正是在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以为大功告成的17、18世纪,浪漫思潮在历史的沉沦中却应运而生了。它与以数学和智性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思潮拼命抗争,竭力想挽救被工业文明所淹没了的人的内在灵性,拯救被数学性思维浸渍了的属于人的思维方式。”[6](P40)在浪漫派笔下,多是对优美的大自然的赞美,“回归自然”不仅指回到自然中去,而更多的是回到一种未受世俗沾染的,自然人性能够自由发展的美好状态。穆旦诗歌中浪漫主义“自然”主题具体表现为:对自然风光的赞美和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对童心的钦慕、对理性的厌弃和对肉体的赞美。
(一)对自然风光赞美和对城市文明批判
在穆旦笔下,自然是美好的,当他面对自然时,是那么惊喜,发出赞叹“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从茫茫的天边把我们拥抱了”,“在我们的血里流泻着不尽的欢畅。”(《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多少年来都澎湃着丰盛收获的原野呵,/如今是你,展开了同样的诱惑的图案”。在《自然底梦》中,诗人说出自己的心声,“我曾迷误在自然底梦中,/我底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我是吹过林木的叹息,早晨底颜色,/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轻。”
此外,自然不仅表现为大自然的风光,也代表着一种没有压力的,回归自由人性的自然状态。所以,当诗人面对自然时,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在这一意义上,与自然相对的是城市文明,发达的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的不是舒适,而是压制和异化,使人成为机器文明下的一颗棋子,丧失主体性。在穆旦眼中,城市是这样的面目:“渔网似的”“那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城市是“工程师、企业家和钢铁水泥/的文明一手展开至高的愿望”(《城市的舞》),人在城市中是渺小的,成为城市文明的一个零件,高度运转,失去主体性,也失去希望,整天只能“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线上》),“八小时工作,挖成一个空壳,/荡在尘网里,害怕把丝弄断”(《还原作用》)。对工业文明带来的人类文明的负值效应的批判是西方浪漫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穆旦诗歌中对城市文明繁荣背后人性异化的透彻体悟显然达到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内核。
(二)对儿童的钦慕
“在西方浪漫主义者的文化构想中,天真烂漫的童真童心,较之野性未泯的生命强力和淳厚质朴的风俗人情,更具人类初民时代的原生性与纯洁性,它是一种未经文明社会和成人世界侵染的人的自然本能与自然情感。”[7]中西方浪漫主义都对童心推崇,西方借此表现为远离尘嚣,接近自然和田园生活的追求。而中国比如李贽的“童心说”认为童心是自然情感的完美状态。可以看出,不管西方还是中国,童心都体现为一种未被世俗沾染的自然人性。穆旦诗歌中对这种“自然人性”给予了高度的赞美。《摇篮歌》中把婴儿看作自己“心”的化身,为婴儿祈祷“别让任何敏锐的感觉/使你迷惑,使你苦痛。”诗人想回到童年时代,“我要回去,因为我还可以/孩子,在你们的脸上舐到甜蜜”“孩子,我要沿着你们望出的方向退回”(《阻滞的路》),童年里有成年人的一切“我们的童年所不意拥有的/而后远离了,却又是成年一切的辛劳/同所寻求失败的”(《隐现》),当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时,更是期待童年,“在阴霾的日子,在知识的期待中,/我们想着那样有力的童年。”(《控诉》)不能回到童年,诗人认为是最大的痛苦。孩子的纯真和童真在穆旦看来,是“已失迷的故乡”,他悲哀地唱出“我是永远地,被时间冲向寒凛的地方。”此外,对童年的赞美是和对成人世界的厌弃联系在一起的。“合起你的嘴来呵,别学成人造作的声音”“等长大了你就要带着罪名,从四面八方的嘴里笼罩来的批评。”最后说“为了幸福,/宝宝,先不要苏醒。”在诗人看来,成人的世界充满了罪恶、虚伪和矫饰,自然人性受到压制,而儿童时代以及童心的纯真是他抵抗世俗的一个武器。
(三)对理性的厌弃和对肉体的赞美
西方浪漫主义是继古典主义之后的一个思潮,是对古典主义的理想、规范的一个反叛,要求人们抛弃虚伪的压制人发展的理性,回到自然的人性状态。这里理性可以延伸为知识、哲理、规范、思想等概念。这些曾使人们摆脱野蛮,成为一个文明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浪漫主义者敏锐地感受到人们自身建立的知识体系,人们自恃的聪明和智慧越来越束缚人自身的发展。“零星的知识已使我们不再信任”“那些盲目的会发泄他们所想的,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控诉》)也意识到在战争年代,即使拥有知识、思想也得不到救赎,“那压制着它的是它的敌人:思想,/(笛卡尔说:我想,所以我存在。)/但什么是思想它不过是穿破的衣裳越穿越薄弱/越褪色越不能保护它所要保护的”(《我歌颂肉体》)。
在否定理性之后,穆旦热烈歌颂肉体。“肉体”在这里可以视为与理性内涵相对的概念,体现为自然未雕琢的状态。在40年代,一切信仰坍塌的年代,当穆旦发现理性并不能拯救自我时,转向对非理性的崇拜,企图从原始的生命强力中找到拯救自我以及人们的通道。“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岩石,/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大树的根。/摇吧,缤纷的枝叶,这里是你稳固的根基。/……我歌颂肉体:因为光明要从黑暗站出来,/你沉默而丰富的刹那,美的真实,我的上帝。”(《我歌颂肉体》)穆旦敏锐地认识到在现实中人们被理性异化,成为空虚无血的一群。穆旦“不是简单地在自然人性论的立场上,甚至也不是个性主义的立场上肯定肉体,而主要是在价值信仰层面肯定它,把肉体当作一种信仰来供奉的。”[2](P264)诗人认为只有肉体是真实的、可把握的,高度赞扬它是“光明”的化身,并能凭借它战胜黑暗。这里诗人把肉体当作文明的对立面,是扼杀人本性和本真的理性的对抗力量,以肉体的野性、原始性来抵抗文明的阉割,寻找失去的原始血性和生命强力。
三、从“浪漫”到“现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穆旦是深谙浪漫主义精髓的,他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实现了对浪漫主义思潮的继承。穆旦创作的初始,是沉溺于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在叶公超、吴宓以及英国诗人燕卜荪等的引导下,他接触了大量西方浪漫主义诗歌,深受雪莱、拜伦、惠特曼等人的影响。王佐良说穆旦早期是写“雪莱式的浪漫派的诗,有着强烈的抒情气质”[8]。同时穆旦开始创作诗歌的年代也正是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诗歌在中国得到大量传播的时候。赵瑞蕻在《南岳山中,蒙自湖畔》中回忆,穆旦当时非常喜欢惠特曼,时常大声朗诵《草叶集》中的诗作。他早期的诗作也有浓郁的浪漫色彩,比如《玫瑰的故事》(1937)、《我看》(1938)、《园》(1938)等诗篇,不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洋溢着浓烈的抒情气氛。应该说穆旦内心是倾向于浪漫主义风格的,那他40年代的诗歌为什么自觉摈弃浪漫主义的吟唱,追求西方现代派的艺术风格呢?
从文艺思潮的发展历程看,“在西方,象征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尾声,又是现代主义的开端。这意味着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是同一种文学倾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倾向,就是从浪漫主义思潮兴起以来,文学不断地向人的内面世界深入的趋势。”[9]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表现手法、风格情调等方面都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影子。同时,五四时期,在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思潮影响下,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中国的先驱者们企图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来对抗中国顽固的封建思想,建立自己的体系。西方经过几百年建立起来的前后相承的思潮体系在当时的中国以平行的方式传播。各种思潮之间往往彼此渗透,互相浸染。现代主义在当时被冠之以“新浪漫主义”,表明和浪漫主义亲密的血缘关系。这些相互渗透并经过本土化过程的思潮以平行方式来到中国作家面前,作家们往往根据现实和自身的需要来加以选择。当然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亲缘关系并不能说明穆旦一定会从浪漫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这只是一种大的环境,真正的转变在于诗人自身对现代主义思潮的切实认同。
穆旦最先接触浪漫主义,后又转向现代主义,这都是和他自身的文学追求和人生经历有关的。在西南联大时,穆旦师从奥登、燕卜荪,开始系统接触西方现代派的诗歌,阅读了大量艾略特、奥登、里尔克、叶芝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现代派诗歌不仅表达方式上与传统相异,传达的主题思想对穆旦也是一个不小的震动。“艾略特式的‘荒原’意识对穆旦的冲击极大——现实世界是荒芜的、没有生命力的,其中没有了正义、理性、人道、和谐,人被异化为受疯狂和盲目的欲望支使的动物。”[10]现代派诗人往往把现实人生的苦难上升到哲学的形而上的概括,他们的作品总呈现出本体意义上的荒凉,人生在他们笔下是彻底的虚无。现代派作品以其主题思想和表达方式的新奇深刻吸引着穆旦,但这还只是外在的影响。
随着外界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穆旦目睹了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大地上万千百姓的疾苦,他们生存无望,流离失所。早期的浪漫主义式吟唱已经不能满足穆旦这样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他是不会沉醉在自身喜爱的诗艺中,而全然不顾现实的丑恶和苦难的。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理想、追求幻灭,单纯、乐观的浪漫主义显然已经不适合时代和自身抒情的需要,而现代主义直面现实的苦难,表现人的生命的脆弱和虚无更契合他的情感表达需要。最重要的,穆旦自身的人生经历也有意无意地印证着现代派所描绘的人生的荒凉图景。日常生活的平庸、荒谬、虚伪和整个中国战乱中灾难深重的现实都在刺痛穆旦敏感的神经,使他对于现实生活中个体的人的生存有着深深的体悟和同情。最终促使穆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的原因不能不提到他在“野人山”的九死一生的经历。
1942年2月,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之际,穆旦投笔从戎,到中国“远征军”担任翻译工作。据王佐良回忆,穆旦所在的抗日远征军在缅甸撤退时,误入横亘胡康河谷的“野人山”。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身边的战友一个个死去。他在热带的毒雨里患上致命性的痢疾,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一次断粮八日之久[11]。这种对战争的亲历使他直接体验到饥饿、灾难、病痛、死亡。“存在主义认为,在这种向死而生的状态中,人往往能洞见常态世界所遮掩的非常态的真实,发现现存文化伪饰、虚无、阴暗等可疑性的一面,更深切地体认到自我生存的困境与难题。”[10]经过这一经历,早年在学校接触到的渗透在西方现代派诗歌中的存在的困境和虚无等主题在他所亲历的生存困境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与回应,使他真切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与虚无。正是从自身内在的精神困境出发,穆旦发现单纯乐观的浪漫主义吟唱是如此虚弱无力,从而在理智上坚决摈弃浪漫主义,而追求现代主义对形而上的本质的探索。穆旦“从一个热情、单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走向了一个被苦难的血水所激醒的现代主义者。”[10]尽管如此,他固有的诗歌审美理想是不会变的,也就是说,这种转变也是有根据的,不会从一种风格转到完全不相关的另一种风格。穆旦最终选择现代主义作为自觉追求的技艺,而不像40年代的晋察冀诗派那样把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直接传达现实;也不像七月诗派主张“主观拥抱客观”,着眼于对战争的抒情。而是将感情深藏起来,追求一种“现实、玄学、象征的综合”[12],就是基于这种原因。
正是以上的种种原因,穆旦从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深刻体悟使他的诗歌突破现实和时空的束缚,深入到形而上的对人的生存本质的探寻。但是他的诗歌并没有现代主义的那种洞穿人的生存困境之后的虚无和颓废,而是在洞穿绝望之后仍给人以希望,仍给人向上的力量,诗作的整体风格也洋溢着乐观精神。显然,穆旦在努力创作现代主义诗歌时,浪漫主义的因子仍不绝如缕地呈现在诗作中,这一点可能连穆旦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作家的创作总有一定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决定了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据英国学者波兰尼研究,人的精神资源第一个层面属‘可明言的部分’,为‘可说之奥秘’;第二个层面是‘未可明言的部分’,属‘不可说之奥秘’。前者为‘集中意识’,后者为‘支援意识’。”[13]按照波兰尼的说法,穆旦40年代的创作也有两个层面的“精神资源”的支撑,即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潮。现代主义很显然是他这一阶段的集中意识,使他的诗作呈现浓厚的现代主义特征;而浪漫主义就是他的“精神资源”的第二个层面,是支援意识。集中意识是作家自觉、刻意追求的,是不固定的,是会随自身或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而且这种集中意识对诗作的影响往往是停留在形式等比较浅的层次上,而支援意识往往是固定的,是内化在诗人“精神资源”的深层的,往往能更深入持久地影响诗作的风格形成。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是穆旦在40年代自觉选择的,而浪漫主义虽然被有意压制,但其思想却内蕴在他情感深处,对诗作的风格产生持久的影响。在穆旦创作的晚期(1975—1977),他的很多诗作(《理想》《秋》《冬》《老年的梦呓》等)都呈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情感。“热爱自然、欣然于时序变化的古典诗情既被泛政治化的时代长期压抑,也为他自己的现代诗学戒律所排斥,而在生命晚期的这一时刻,穆旦似乎为自己破除了双重的戒律,听任这种散发着‘过时’气息的浪漫主义情感的流露。”[14]穆旦钟爱的浪漫主义以别样的方式呈现在他的现代主义诗歌中,并以浪漫主义的对理想的坚守、乐观自信抗衡现代主义的虚无和颓废,使诗歌既着眼于现实的写照,又超越于现实之外,达到对人的生存本质的概括。从根本上说,穆旦的诗是一种“综合”的诗,浪漫主义对人生理想的不懈追求和现代主义对人生本质的洞穿在他诗歌中都有所体现。“也正是由于他自身具有的浪漫主义气质以及对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深刻理解,使他更好地把握了与浪漫主义有深层联系的现代主义的精髓,使他的现代主义诗歌摒弃了欧美现代主义的虚无,具有了一种深重的现实感和沉雄的力量美。”[15]
[1]郑敏.诗人与矛盾[A]//杜运燮,袁可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39.
[2]蒋登科.九叶诗人论稿[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李方.悲怆的“受难的品格”[A]//杜运燮,周与良,李方,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71.
[4]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6.
[5][美]雅克·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M].侯蓓,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50.
[6]俞兆平.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6.
[7]罗成琰.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41.
[8]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A]//杜运燮,袁可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
[9]陈国恩.浪漫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333-334.
[10]季爱娟.穆旦诗歌的“上帝”话语探析[J].学术交流, 2006(1):179-181.
[11]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A]//王圣思,选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308.
[12]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A]//王圣思,选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9.
[13]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17.
[14]耿占春.穆旦的晚期风格[J].文学评论,2013(5):203 -211.
[15]马瑞红,彭金山.穆旦浪漫主义情结的深层原因及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40-46.
The Hidden Romance:On the Romanticism in Mu Dan's Poems in the 1940s
MA Wei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46,China)
Mu Dan's poems in the 1940s pursues consciously western modernism school in writing styles:complicated thinking and intricate emotion.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his poems and the pure modernism poets in many areas including the purport,conception and intrinsic spirit.On the contrary,they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romanticism.Mu Dan's poems possesses obvious hero worship,firm optimistic spirit and admiration for the essence of"natural"romanticism.These romantic factors become the deep spiritual resources for his creation and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his style.Based on the discussed points above,the fundamental reasons why Mu Dan turned from romanticism to modernism and why there are romanticism factors in his poems of modernism are discussed.
Mu Dan;poems in the 1940s;Romanticism;Modernism
I207.25
A
1672-934X(2015)05-0103-07
10.16573/j.cnki.1672-934x.2015.05.017
2015-07-23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LX15_0015)
马 炜(1985—),女,江苏靖江人,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