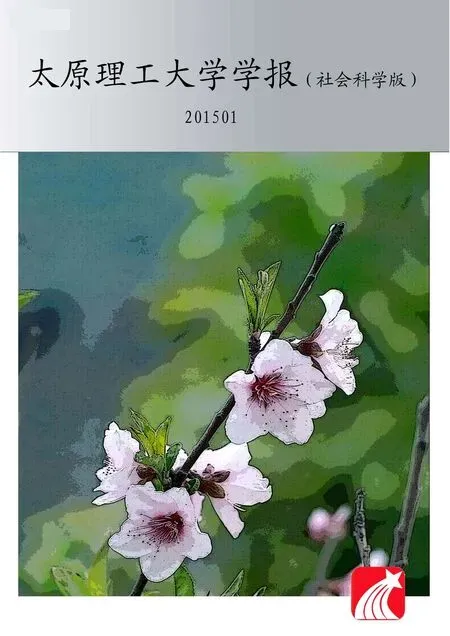救助义务法律化的美国路径及理论
2015-02-12成家全
成家全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救助义务法律化的美国路径及理论
成家全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保障人权是美国法庭化解救助义务道德困境的法律基石,捍卫生命是法官追求人性至善的道德情怀。文章在其实质合理性的基础上,否定自冒风险、区别真假不作为、解释可转嫁性过失,证明司法调整救助义务的形式合理性。
关键词:救助义务;不作为;可转嫁性过失
一般认为救助义务(a duty to rescue)是道德性义务,法律不能像好撒马尔人那样要求旁观者必须履行,但一百多年前的社会现实和公共政策转向,需要美国法庭支持救助者在救助行为中的伤害赔偿主张,并要求对救助义务的性质进行重新审视。如果救助义务是一个先验性的道德假设,法律能否介入这种个人道德实践行为?对此,卡多佐(Cardozo)大法官认为,危险期待救助,不幸渴望救济,壮举之为,良知使然,法律不可壁上观,因为法视生命之重,诺于护佑生命、无有过失本文所引用的全部案例均源自西方案例数据库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
一、美国法律中救助义务理论概述
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基于尊重生命和保护人权的原则,以保护潜在救助者的权益为主线,在1871年到1921年间通过判例对救助者赔偿主张的不断探索,逐步形成以保护救助者权益为中心的救助义务理论及相应的救助规则,实现了救助者权益保护的完全法律化和救助义务有限法律化。其内容主要指:面临迫近的危险时,一个谨慎的潜在救助者在帮助被救助者的过程中,只要不存在严重错误,则引起危险环境的第三方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中,即使被救助者自身存在过错,但该过错也具有不可转嫁性;在因果关系认定上,采用事实因果关系为主、法律因果关系为辅的原则,优先考虑由风险引起的自然和直接的结果事实;在抗辩理由中排除自冒风险规则。具体而言,救助义务理论包括如下救助规则:(1)救助者不存在过失,除非肆意行为;(2)救助者在救助行为中不应该承担判断失误的后果;(3)救助者的伤害责任应由危险制造者承担;(4)救助行为是必需的;(5)救助者的过失问题是一个法律和事实混合问题,应由陪审团根据证据来确定;(6)已经开始救助行为;(7)救助行为是自愿的;(8)救助者不一定与被救助者存在特定关系;(9)救助行为造成对第三者的伤害应由引起危险方承担赔偿责任;(10)风险制造者的过失是救助者损失的近因;(11)救助者不能故意加重被救助者的损失;(12)因天灾引发的救助损失不能向被救助者主张赔偿;(13)抢救财物的行为与救人行为不同;(14)风险是迫近的而不是虚构或者不当风险。
二、法律介入救助义务的逻辑前提
根据道德和法律分离性命题,一般认为在法律上不存在救助义务,法律也不能介入此类道德义务,救助者在救助行为中的损失自然不能获得司法救济;但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个案不公正的结果,违背了理性和正义一致性的传统理念,也不符合公共善对社会正义的要求。因此在危险环境、救助事实、损害事实等证据信息明确的情况下,根据道德和法律价值一致性命题,司法要裁决一个道德义务纠纷实际就是道德义务法律化议题,必须要证明其形式合理性和实质的合理性,并且不违背公共政策。从法律层面看,权利-义务分离命题更重视行为结果的正义性,普通法的基本原理也支持对权利伤害的救济,就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关联性而言,救助义务的道德性和法律性争议,不能否认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对人性的终极关怀是抑制个人道德实践对生命冷漠行为的有效手段。司法现实主义者认为,救助义务是道德性义务,属于先验假设命题,事实上没有任何绝对理由否定法律对此类行为的调整,社会现实也要求法律对救助者的权利主张实施救济,“法律是功利性的,它的存在是实现公众利益的合理需要”[1]。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阶层分裂化,个人道德冷漠,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受惠阶层的道德责任,发扬高贵人士应有的道德义务[2],罢工和经济萧条使很多人确信政府应该在调控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3]。由此,个人自由受到法律限制,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增加。同时,传统的宗教律令在合法命令前失去了效力,强制公民履行救助义务会面临法律制裁[4]。当个人的道德实践与法律的价值目标不和谐时,法官对法律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思考受到社会现实和共同善的影响,侵害行为法没有规定自愿救助义务,但不等于说救助者在救助行为中受到损失就不能获得法律救济。这个基本的法律逻辑前提使侵害之诉和间接侵害之诉不但有明显区别,也存在更多重合之处,因契约关系引起的损害可以通过间接侵害之诉获得赔偿。因此,从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上看,在不否定自愿救助行为合法性的基础上,实现救助者的损害赔偿就是法律上论证当事人之间存在契约义务的问题。
三、对救助者权益保护的司法论证
在救助行为中失去生命或受到伤害的救助者,其权利救济请求无疑受到了法庭的肯定,即使救助者的赔偿主张得不到法庭的支持,法官亦会表达对救助者的赞美、对生命的尊重。在吉布尼案中,法官认为“孩子面临的危险已经证明是州疏忽的后果,这种情景的自然后果就是父亲面临危险。如果父亲不跳入河中拯救自己孩子的生命,这与人类经验中的绝大多数事实不符”。
(一)契约理论对违反安全义务的证明
从对救助者权利保护的发展历程看,早期的救助义务案例基于对人性关怀、自然理性与正义的一致性作为法理基础,通过不严密甚至武断的法律推理实现对救助者遭受伤害的救济,后期的案件通过寻找“法律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张力”之间的平衡[5],以法的内在价值作为逻辑起点,通过论证被告对原告存在社会契约性的安全义务,以被告违反安全义务的形式合法性说明法律救济救助者伤害的实质合理性。这种论证路径在瓦格纳案中,由卡多佐归结成救助义务邀请说规则,以此说明救助者和危险制造者之间实际存在关于安全的契约关系,以此说明危险情境的制造者对救助者存在安全上的积极保护义务,从而克服救助者损失赔偿主张所面临的法律限制。如Thompson 法官所言:“关于过失的任何法律概念的必要要素涉及违反一个法律义务,而这个义务是被告和原告之间的关系所形成。”一方面,在很多诉讼中被告认为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特别是存在信赖利益的契约关系,因而不存在过失问题;另一方面,契约理论和市政管理模式为证明被告的过失提供了依据,而侵害行为法不排除对违反契约关系行为的救济。因此,只要证明救助者和危险制造者之间存在契约关系,救助者即可主张间接侵害之诉。黄金时代的科技进步远远快过立法速度,一些新技术的使用和市政建设管理的滞后,带来严重的速度和安全之间的矛盾。交通运输等企业追求效益的决心远大于公共设施对公众安全的承诺,造成公共设施如公共游泳池、公园、体育馆等的基本安全得不到保障。而得到广泛认可的契约理论认为:交通、公园、医院等是公共设施,这些设施的建设征得了公众的同意或授权,救助者是公众中的一员,因此,这些公共设施也是在救助者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建成的,双方就此形成了契约关系,彼此间应当存在相应的法律权利和义务。所有者在拥有获取经济效益权利的同时,承担不对公众造成安全威胁的义务。公共设施存在安全隐患,这显然违反了所有者承诺的安全义务,因此,这是一个假不作为。瓦格纳案中针对“被告没有邀请原告去救助被救助者”因而不能形成契约关系的说法,卡多佐直接以“危险邀请救助”来辩驳,其逻辑起点正是基于我们大众是公共设施当事人,我们之间又存在包括救助行为在内的更广泛契约关系,而间接侵害之诉并不排除这种基于契约关系的赔偿主张;另一方面,危机人们生命的交通安全风险是一种非自然的恶,而非自然的恶来自于人的行为,是一种人为的道德恶[6]。自然的恶是不可预测的,但人为的恶可以事先预见并采取积极防范措施,风险制造者没有积极阻止这种恶的发生,主观上存在过失。同时,对被告主观上存在过失的逻辑论证反映了司法现实主义者的主张,顺应了市政管理模式改革的要求,契合了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正义的呼声,符合当时的公共政策走向,也不会引起侵害之诉和间接侵害之诉的内在冲突[7]。
(二)对真作为和假作为的实践区分
侵害之诉中明确不承认因不作为引起的赔偿主张,但对不作为和作为的含义及区别存在法律认识上的混乱。对于个人而言,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分在本质上是一个法律下的自由选择问题,当处于危险状态的一方需要救助时,如果救助行为是出于本能或者经过功利性的计算后进行的,都是行为者自身意志范围内的自愿行为,法律不能干涉个体的选择权利。但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行使自己的权利,不能侵害他人的权利也是普通法的基本原则,只是这种侵害行为在传统上被界定为必须是积极的行为,即作为。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契约关系,对作为的语境考察前提明显不同于单独的个体,契约的平等性足以说明当事人对道德义务的自愿放弃,即被告对公众的安全义务超出个人自主范围,必须积极履行以避免伤害他人。这等于承认个人的道德义务可以通过契约关系转化成法律义务,从而放弃了作为和不作为区别的前提: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区别正是作为和不作为区别的正当性基础,正当性不存在了,法律自然介入道德义务[8]。作为潜在救助者的一方,其选择就建立在当事人对未能预防的作为和不作为及其引起伤害的清晰区分之上[9]。而作为和不作为的本质差异在理论上虽然很明显,但在实践上难以判断一个不当行为是积极作为还是消极作为[10],特别是在合同法和侵权法重叠适用的领域内,积极作为和消极作为区别容易产生假不作为而实际是作为问题,对此Wade法官指出:“不作为是代理人根本忘了或没有开始履行义务,而这些义务是代理人同意履行的;作为是不适当地履行了代理人应该合法承担的义务,或者以合法方式履行以免侵犯第三人的权益;如果代理人承诺为被代理人做某事,然后通过默示的方式予以拒绝或者没有开始履行,这是一个不作为;如果他一旦开始履行,但却疏于履行所承担的义务,由此造成对第三人的伤害,这属于假不作为……因为一些案件未能确切注意到这种区别,导致判决中存在混乱”。可见,对被代理人而言,代理人的不作为就是被代理人的作为,是一种以消极方式进行的积极侵害行为,是假不作为,市政管理机构接受公众的委托以提高公众福利为目的,代表公众授权铁路公司等社会组织从事铁路建设、管理事务,铁路公司自然应该积极履行保障公众安全的委托性义务。因此,在侵害行为法上,铁路公司的不作为实际上是消极的作为即假不作为,如果救助义务不存在于真不作为中,则假不作为中一定存在救助义务。
(三)重新解释可转嫁性过失
可转嫁性过失源自Thorogood v.Bryan案的判决,主要适用于类似主仆关系(或代理关系)并且主人作为原告的特定案件[11]。如果主人作为原告,即使被告存在更大的过错,由于仆人的过失,被告不能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仆人的过失是可转嫁给主人的过失。该规则假设司机和乘客利益一致,乘客因此应对司机的过失负责,其有效性是乘客在事故发生时能控制司机的行为,从而克服法律在司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12],以增加当事人之间的勤勉义务,保证粗心和不诚实的一方无法逃避懈怠行为的责任。美国一些经济法庭在涉及铁路公司的案见中适用此规则,但存在不同的解释,并且由于主仆关系并不存在于乘客和司机、乘客与车主之间,缺乏这种关系,司机过错就是乘客过错的规则与法律原则相违背。因此,有些州并不接受此规则,最高法院也拒绝适用此规则。所以,法庭从因果关系角度将可转嫁性过失解释为:危险制造者对被救助者的过失,就是对救助者的过失,因为救助者的伤害是危险制造者过失的自然的、直接的和最相关的结果。从侵权归责原则上看,这只是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区分的问题,对涉及公众安全的案件,只要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无错这个事实问题,被告就应承担无过错责任。对此问题,卡多佐大法官认为,社会现实要求过错与无过错严格区分,而涉及控制人类行为义务的法律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13]。
(四)禁止适用自担风险抗辩
救助者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他人,本身是否存在过失,古典自冒风险理论认为救助者具有明显的过失。但基于比较过错原则,特别是公共政策和人道主义考虑,法庭在审理此类案件中,一般排除该抗辩或者将此问题作为一个事实和法律混合问题提交给陪审团裁定。因为古典自冒风险原则在坚持当事人行为自主理念的同时,要求当事人之间在危险发生之前就认识和辨识风险的存在及可能的后果,并且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免除伤害责任的协议,救助行为中救助者行为虽然可以被推定为自愿承担伤害后果,但不是在危险发生之前,而且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认识和辨识风险,所以,适用自冒风险显然不符合逻辑。在Pennsylvania Co.v.Langendorff 案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没有法律义务去救助小孩,如果他允许火车碾过并杀死小孩,没有违反任何民事法律规则,因此其行为在本质上是自愿的。但Bradbury法官认为在类似情景中,除非一个谨慎之人对风险的判断具有严重错误,去救助他人时使自己遭受更大的危险。救助者本身有过错的说法即得不到道义的支持也不能获得公共政策的肯定,也不符合自冒风险的逻辑前提。
四、总结
综上,围绕救助义务法律化的问题,基于现实的公共政策选择,美国法庭以救助者义务和权利的不同为视角,将救助者权利保护作为途径扩展救助义务的法定化,对一个普遍重视公民“权利”的社会而言或许更为现实。
参考文献:
[1]James Barr Ames.Law and morals[J].Harvard Law Review,1908,22(2):111-113.
[2]John Lee Eighmy.Religious liberalism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J].Church History,1969,38(3):359-372.
[3]Jennifer Alexander. Efficiencies of balance:Technical efficiency,popular efficiency,and arbitrary standards in the late progressive era USA[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08,38(3):323-349.
[4]Aaron Kirschenbaum.The bystander’s duty to rescue in jewish law[J].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1980,8(2):204-226.
[5]李龙,汪习根.法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425.
[6]Marilyn Admas,Robert Admas.The problem of evil l[M].London:Ox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
[7]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common law[M].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48:81.
[8]Imputed negligence[J].Harvard Law Review,1910,23(4):299-300.
[9]Ernest J.Weinrib:The case for a duty to rescue[J].The Yale Law Journal,1980,90(2):247-250.
[10]Francis H.Bohlen.The moral duty to aid others as a basis of tort liability[J].U.PA.L.REV,1908,56(5):119-220.
[11]Imputed Negligence.Voluntary Exposure. Rescue.Pennsylvania Co.v.Langendorff,48 OhioSt.,28 N.E.Rep.172[J].The Yale Law Journal,1891,1(1):39-40.
[12]W.F.C.Power of a court of equity to appoint a receiver to wind up the affairs of a solvent corporation at the suit of a minority[J].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American Law Register,1929,77(5):676-678.
[13]M.Kime.The duty to control the conduct of another,Fowler V.Harper and Posey[J].The Yale Law Journal,1934,43(6):887-888.
(编辑:李红)
The American Path to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Duty to Rescue and Its Theory
CHENG Jia-quan
(LawSchool,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27,China)
Abstract:To protect human rights is the legal footstone for America to resolve the moral dilemma of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duty to rescue. To save a life is the moral feeling for a judge to seek the best human nature. Based on the virtual rationality, this paper negates risks by oneself, distinguishes the false nonfeasance from the true one, interprets the transferable negligence and demonstrates the form rationality of adjusting the duty to rescue by justice.
Key words:the duty to rescue; nonfeasance; transferable negligence
中图分类号:D99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5)01-0043-04
作者简介:成家全(1972-),男,陕西旬阳人,武汉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人权法、体育法。
收稿日期:*2014-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