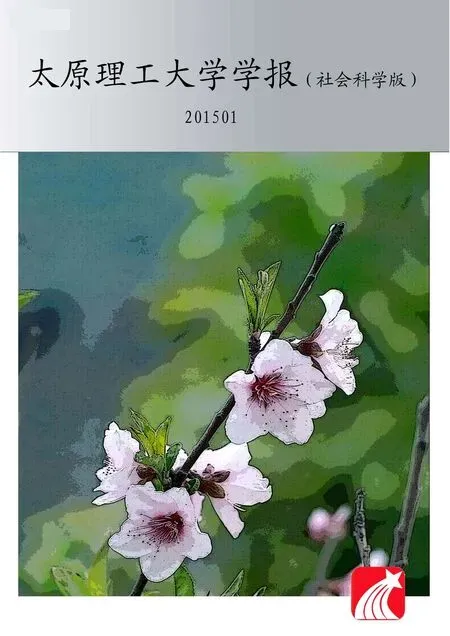论《管家》对家园概念的重构
2015-02-12乔娟
乔 娟
(1.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2.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论《管家》对家园概念的重构
乔娟1,2
(1.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2.北京语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自我身份的探寻始终存在于玛丽莲·罗宾逊小说《管家》的象征世界与符号世界的对话性叙述中。贯穿于事实和想象两个层面的复调叙述丰富了关于人物记忆、原初生活与未来选择的意义阐释,从而消解了居家与漂泊、留守与流浪的对立关系,修正了传统的家园概念。
关键词:《家园》;身份;象征性;符号性;复调叙述
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玛丽莲· 罗宾逊所创的首部小说《管家》于1980年出版,翌年获得海明威基金会/国际笔会最佳小说处女作奖,1982年获普利策最佳小说提名奖。小说关注人们面对生存难题时所做的心理探索,探讨了人类生活中所面临的永恒主题——遗弃与希望。小说叙事者茹丝简述了她和妹妹露西儿命运多舛的童年经历。在母亲海伦自杀后,她们先后在其多位女性亲属(外婆希薇亚·佛斯特,姑姥莉莉·佛斯特和诺娜·佛斯特,姨妈希薇亚·费雪)的照料下成长,最终茹丝跟随姨妈被迫离开外婆在爱达荷州指骨镇的家一起流浪生活,而妹妹露西儿选择与家政课老师洛伊斯过着稳定的居家生活。茹丝的叙述为家园概念的理解带来全新的视角:希薇亚和茹丝烧毁家的传统安全屏障——房子,被迫选择远离故土、流浪生活的行为是追逐自由心灵的勇敢之举,亦是对心灵之家的重构。
(一)理论依据
人从出生到发展成为独立的个体需要经历多个阶段。拉康提出了三个概念来对应人的三个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人类发展的三个领域——现实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与弗洛伊德一样,拉康认为:从婴儿的角度看,孩子出生伊始与母亲不可分离,在孩子与母亲之间完全没有自我和他者之分。婴儿识别不了自己与满足他各种需求(食物、安全、关怀等)的客体之间存在什么区分,他并没有关于“整体人”的概念。他与母亲(另外的人)之间完全不存在区分,这是“自然界”的状态。到婴儿成长到6—18个月的某个时候,他开始能够在自己的身体和环境中的其他东西之间做出区分。在此阶段的某个时候,婴儿会在镜中看见自己。自己的镜像与他人的反复交替出现赋予了婴儿一种整合了的存在感,至此,婴儿产生了“自我”的认知。拉康将此镜像阶段称为想象界。儿童一旦构建起关于其自身镜像的自我的概念,就开始进入象征界了。象征界的秩序是语言自身的结构,人类必须进入象征界才能成为言说的主体,让自己通过说“我”而得到表达,这一表达只可能发生在象征界。 克里斯蒂娃把尚未组织起来的无序的过程称作“符号的”过程,与拉康一样,将接受父权控制的、逻辑的、有序的句法过程称为 “象征的”过程[1]197。介于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是拉康所谓的镜像阶段,从这一时期,儿童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在符号化过程中,主体表现为某种欲动,它对于个体化的同一感(即作为协调统一的身体感)毫无觉知,此时,结构和意义均不存在。而到象征化过程时,成为言说主体的人必须屈服于语言的法律和规则。作为象征功能的语言,其最终形成要以压抑本能欲望和与母体的持续关系为代价。
《管家》的女性主义立场彰显于小说符号世界与象征世界之间的共存与对话中。以具体人名、地名、日期和事件为内容的传统、常态生活与茹丝在指骨镇的尴尬、失语状态相伴相随。复调叙述中简单事实性称述与泉涌般的符号性叙述并置。一方面,使用象征性秩序及组织常态语言的能力在茹丝的故事叙述中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叙述者运用大量比喻和虚拟性语句重构记忆,用诸如“梦想”“就说”“也许”等词汇构想未来,直至茹丝和读者都模糊了记忆、梦想和想象的界限[2]565。茹丝和露西儿在母爱庇护下逐渐步入差异性象征世界的步伐被母亲无情的“遗弃”[3]161而打断,戛然而止。海伦陪伴两姐妹在海滨公园愉快地游玩后,驱车到达外婆家,把茹丝姐妹及所有行囊丢在外婆家的玄关,独自开车飞进湖里。这一经历显然在两姐妹幼小的心灵留下挥之不去的困惑和期盼。对于母亲突然消失的原因,她们不得而知,读者也未能在文本中获得清晰的说明。无论如何,母亲未加解释的离开对茹丝和露西儿自我意识的形成造成危机。正如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所讲,自我认同包括了我们的个体感、唯一感、完整感,以及过去与未来的连续性,人在缺乏自我认同感时感到混乱和失望[4]80。茹丝热切地渴望回归、复原和再续,重获关爱成为她内心强烈的欲望诉求。这种欲望叙述暗含了茹丝在自我身份的认同过程中遭遇的迷失和滑落,对此,小说多处予以描述。“我期待一场到来,一个解释,一句道歉。”[3]232“…… 我一度信心满满地等待她回来, 这么多年以来, 还犹如当初她把我们留在玄关的时候。”[3]176“……但是她经常在就要溜过任何一扇门的时候,被我眼睛的余光瞄到,而那就是她,面貌如初,未曾逝去。……摆脱一切感官,但未曾逝去,未曾逝去。”[3]224
(二)重构的记忆
露西儿与茹丝采用不同的自我认知图式[4]299对关于母亲的记忆进行矫正性的干预,选择性地注意、解释和回忆某些事件,最终形成了融观察、期望和热情为一体的混合体。露西儿给回忆蒙上一层玫瑰色,她把一些细小的令人愉快的事件回想得比实际所经历的要美好得多。在她的记忆中,母亲海伦“有条不紊,精力充沛,通情达理”[3]161,而在茹丝的记忆中,“她对生活的任何要求毫不在乎”[3]161。小说中段,两姐妹在树林里过夜,但却对当晚的情形留有不同的印象。“露西儿对整件事有不同的说法。她说我睡着了,但我没有。我纯粹让天空的黑暗,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地触及我头颅我内脏和我骨头里的黑暗。眼前的一切都是幻影,是一袭覆盖这世界真实地运作的薄床单。”[3]168
茹丝以自传似的思维回溯其过往的生活经验,在叙述中赋予特定情节以新的意义和情感,设想出事件发生的理想状态,同时为未来的潜在发展设立路线。茹丝与露西儿迥然不同的记忆构想包含着两姐妹不同的人生期待。露西儿期望自己成为学校里其他女孩子的样子,通过像别人一样的行为,暂时逃离家庭遭受意外后留下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如弗洛姆所说,“个体……(通过)变成其他人希望的样子。……不再感到孤独和焦虑”[4]94。而茹丝与希薇亚建立的纯粹关系中,在彼此心灵相互敞开之际,蕴含着相互承诺的信任感逐渐出现。两人在湖边停留过夜后,这种信任感进而升华为一种信念,事件本身成为茹丝选择跟随希薇亚一起过漂泊生活的信号。小说中,人物心灵活动犹如在事实叙述与虚构想象之间艰难爬行一般,其心理通达性模糊了象征域与符号域之间变动不居的界限,随着时间的衍化,虚拟世界的星云终将变幻为“可能的自我”[5]30。
(三)原初的融合
如茹丝所说,“我从来就没办法灵敏地分别出,到底我是在想东西还是在梦游”[3]300。小说中,“符号性”与“象征性” 的双层叙述相互勾勒、持续融合。小说不是关于隔离或遵从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前语言时期的符号世界与秩序时期的象征世界的共融呈现。在传统家庭观念与社会约束力的调节下,原初的、不确定的冲动流有节律地交杂流淌,同时,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渴望促进着两者之间的融合。
晚间,踏进家门槛的茹丝和露西儿“从纯然的夜晚走进纯然的夜晚”[3]148,房屋结构中原本具有分隔内、外功能的窗户因希薇亚对黑暗的偏爱而暗示统一绝非相异。跟随希薇亚在河边度过一夜后,身处山谷中的茹丝分明感觉到自己和那些离群索居的野孩子并无二致。“没有任何门槛,他们几乎就靠在我脸颊上呼吸,几乎就在抚摸我的头发。”[3]219事实上,希薇亚、茹丝和露西儿在祖屋的保护下过着半流浪生活。即便祖屋本身,也并不确定拥有与父权和秩序的必然联系,甚而房子本身的结构特点亦包含着动态与漂泊的因子。“我外婆状似坚固的房子只是虚有其表……更何况,我们的屋子也不该有二楼,因为,要是屋顶在我们睡梦时塌下来,我们就会悲惨地直直坠入幽冥之中,我们所知大概不会多于梦猝然变得恐怖而且猛然结束。”[3]224另外,外公为二楼设计的活板门“只要轻轻一推就会打开,然后只要小力地关就会自行关上”[3]80。
茹丝与露西儿在指骨镇边缘化的半流浪式生活正是其内心渴望温暖和安全感的生动表征。两人冒险在树林里过夜,看似是与传统室内家庭生活的裂变行为,实则蕴含着两层叙述能量之间混合杂陈地融合。两人在努力寻找着两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即便在林中流浪过夜,她们依然保持了居家的习惯。“我们 ……用一块石头的一侧当墙,以浮木围成后墙和另一侧的墙,第三旁则对着湖敞开。把冷杉的枝桠扯下来盖了屋顶和地板。是个低矮而马虎的建业,盖得随性而且因地就简。”[3]167虽然只是“残破的碉堡”,但作为“临时小屋”[3]168,已然恰当地保持了象征世界中“家”的品质。
(四)互融的选择
希薇亚和茹丝在偷来的小船上渡过一夜,搭乘运货车回到指骨镇,这一行为公然对抗着小镇人们的传统居家意识,因此,小镇人试图保证茹丝安全地“待在门里”。警长与好事的女人们多次拜访,盘问打探,而有关茹丝监护权的听证会也即将召开,这标志着希薇亚与茹丝彼此相守的初步计划已然失败。“此刻”成为茹丝生命中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充斥着秉承僵硬正规的道德意味的传统与包含种种开放可能性的漂泊生活之间的对峙与抗衡。处在十字路口的茹丝需要一种特殊力量的体验,仿佛“豆荚里的一颗豆子”[3]226。“……这核心,这熟睡的胚芽,应该要膨胀延展。……接着,会以某种形式分娩……”[3]228茹丝在命运抉择时刻,在道德传统与自我存在的困境中,体验着第二次出生赋予的更多期许。在指骨镇居民异样的不无戒备的注视中,这种期许以微妙甚或赤裸裸的激荡方式与泛化的焦虑交织在一起,几乎被外在的侵蚀力所吞噬。为了在一个疯狂的世界中保持自我的认同,希薇亚与茹丝以轰响的爆炸给出一个响亮的解答。在指骨镇人们的喊叫声中,在群狗的骚动声中,在祖屋熊熊火焰的背景下,她们匆忙决定过桥。两人在桥头消逝的一幕,集中了符号世界与象征世界叙述的策略平衡,桥上的“我”迈着“缓慢、大步、跳着舞的步伐”[3]294,逃离其指骨镇家的传统世界,桥下却是让她回想起她母亲的湍急河流。茹丝与露西儿的选择仿佛桥的两头,分别属于符号与象征的视域,貌似不同方向,却存在持续的联系与沟通。跟随茹丝叙述的读者意识已经持续地从两个方向“跨越、再跨越这座桥,因为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真正地待在家中,也不可能全然到达超越所有父权制秩序的乌托邦世界”[6]103。
小说并没有在此停笔,茹丝依然持续讲述,仿佛她的逃离就是为了述说,连同希薇亚别在右翻领下侧的带有“湖夺两条人命”[3]297的简报一起标示着她们掌握了而不是抛弃了象征世界中的秩序。小说叙述始终贯通于事实和想象两个层面,以此消解了居家与漂泊、留守与流浪的对立关系。家并不意味着限制,漂泊也并不等同于无家,这正是传统家园概念的修正和重构。
参考文献:
[1]赛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King,Kristin.Resurfacings of the deeps:semiotic balance in Marilynne Robinson’s Housekeeping[J].Studies in the Novel,Winter 1996,(28)4:565-579.
[3]玛丽莲·罗宾逊.管家[M].李佳纯,林则良,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
[4]伯格.人格心理学[M].陈会昌,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5]迈尔斯.社会心理学[J].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6]Geyh,Paula E.Burning down the house? Domestic space and feminine subjectivity in Marilynne Robinson’s housekeeping[J].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93,34(1):103-122.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Home inHousekeeping
QIAO Juan1,2
(1.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ShanxiUniversity,TaiyuanShanxi030006,China
2.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BeijingLanguageandCulture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Seeking for Self-identity is a consistent issue existing in the dialogical narrative between symbolic and semiotic realms in Housekeeping by Marilynne Robinson. The polyphonic narrative well-versed in the two levels of fact and imagination enrich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s’ memory, the original life and the choice for the future, thereby dissolving the opposition between domesticity and homelessness, left-behind and transience and correct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home.
Key words:Housekeeping; identity; symbolic; semiotic; polyphonic narrative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5)01-0068-03
作者简介:乔娟(1979-),女,山西太谷人,山西大学讲师,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
收稿日期:*2014-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