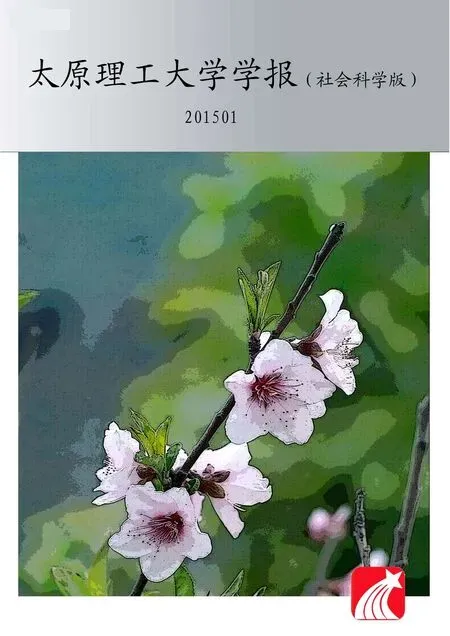红孩儿形象考论
2015-02-12车瑞
车 瑞
(宁波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红孩儿形象考论
车瑞
(宁波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西游记》中红孩儿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儿童形象,是在结合明前的文化原型基础上经过宗教互文、神话互文、文本互文再加工创造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形象发展中,先后经历了鬼子母、圣婴大王到善财童子的过程;红孩儿使用的三昧真火融合了佛教禅定摄心的教义和道教五行生克的理念,是印度血统中国化、中国形象本土化、本土人物神话化的成功典型。
关键词:西游记杂剧;红孩儿;鬼子母;善财童子;圣婴;
一、鬼子母期
红孩儿的形象在最初阶段比较单一,直至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之前尚未从“鬼子母”故事背景中脱离出来。“鬼子母”梵名,Hariti,音译诃利帝,意译为欢喜, “又被称作欢喜母、爱子母、功德天、天母等,因为她是五百鬼子之母,故称为鬼子母”[1]254。北魏《杂宝藏经·卷九》记载:“鬼子母者有子一万,其最小子,字嫔伽罗。此鬼子母凶妖暴虐,杀人儿子,以自啖食。人民患之,仰告世尊。世尊尔时,即取其子嫔伽罗,盛著钵底。”[2]732鬼子母为救嫔伽罗弃恶从善,皈依三宝,佛祖依言释其子。
《南海寄归内法传》曰:“施主乃净洗手足。先于大众行初。置圣僧供。次乃行食,以奉僧众。复于行末,安食一盘,以供呵利底母。其母先身,因事发愿,食王舍城所有儿子。因其邪愿,舍身遂生药叉之内,生五百儿,日日每餐王舍城男女。诸人白佛,佛遂藏其稚子,名曰爱儿。触处觅之,佛边方得。世尊告曰:‘汝怜爱儿乎?汝子五百。一尚见怜。况复余人一二而已。’佛因化之,令受五戒。”[3]50鬼子母最小的儿子“嫔伽罗”“爱儿”被世尊盛著钵底可以算作吴本《西游记》中红孩儿被观音困诸莲台的雏形,虽然他在这个故事中只是被简单提及,仍旧从属于鬼子母这一人物形象的叙述之中,但符号化的命名使他具有了无限可能的意义生成性。
红孩儿形象在宋代无名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入鬼子母国处》云:“逡巡投一国,入其殿宇,只见三岁小儿无千无万,又不言不语,法师问:‘臣启大王:此中人民,恁地性硬,街市往来,叫也不应。又无大人,都是三岁孩儿。何故孩儿无数,却无父母?’国王大笑曰:‘和尚向西来,岂不见人说有鬼子母国?’法师闻语,心如半醉:然我七人,只是对鬼说话。”[4]7-8此处,已有了对三岁小孩群体形象的具体描写,并点出了三岁小孩自成一国,与吴本《西游记》中红孩儿占山为王,受群孩儿拥趸的圣婴大王有相似之处。
元末明初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已经奠定了吴本《西游记》叙事的大致结构。杂剧《西游记》中的“鬼母皈依”折,虽然仍以鬼子母故事为蓝本,但与吴本《西游记》中红孩儿的故事非常相似,第十二出已有“红孩儿上哭科”的戏化唐僧的情节。唐僧云:“善哉,善哉!深山中谁家个小孩儿,迷踪失路。少刻晚来,豺狼毒虫,不坏了这孩儿性命?出家人见死不救,当破戒行。行者,与我驮着,前面有人家,教报问,送还他家请赏,也是好事。”[5]663悟空告诫师父山林中多妖怪,劝他不要多管闲事。唐僧不听终被妖精拿入洞中。行者就和沙僧、火龙同去见观音。观音也看不出妖怪的本来面目,又同去问世尊。世尊道:“那小孩唤做爱奴儿,他母亲我收在座下作诸天的,缘法未到,谓之鬼子母。我已差揭帝将我钵盂去把小孩盖将来,放在座下七日,化为黄水。鬼子母必来救他,因而收之。”并叫行者等回去,唐僧已经救出在那里了。鬼子母领了鬼兵来救儿子,但是不敌天降哪吒,终给哪吒拿住。鬼子母无奈只得皈依佛法,放出爱奴,子母团圆[5]663。爱奴儿智取唐僧一节与吴承恩《西游记》中“婴儿戏化禅心乱,猿马刀归木母空”的叙事结构非常接近,但仍保留了“鬼母揭钵”的结局。这里鬼子母的小儿子经由“嫔伽罗”/“爱儿”改名为“爱奴儿”/“火孩儿”,逐渐摆脱了对鬼子母故事的依附性,正如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所说“其鬼母皈依一则,则叙红孩儿事。此皆吴氏小说所有。惟鬼母揭钵事,则小说所无。盖小说以红孩儿为铁扇公主、牛魔王子,故遂不及鬼母事”。红孩儿不再是鬼子母形象的注脚,渐渐成为阻碍唐僧师徒取经故事的行动元,其妖魔化的“火孩儿”身份与红孩儿的形象更加接近。
二、红孩儿期
《朴通事谚解》中的一段文字值得注意:“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又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6]111《销释真空宝卷》曰:“正遇着,火焰山,黑松林过;见妖精,和鬼怪,魑魉成群。罗刹女,铁扇子,降下甘露;流沙河,红孩儿,地涌夫人。牛魔王,蜘蛛精,设(摄)入洞去。”[6]115《西游记》杂剧第二十一出“贫婆心印”中也有唐僧一行脱离了红孩儿,过了火焰山到达天竺国的记载。《朴通事谚解》《销释真空宝卷》《西游记》杂剧中以妖怪形象示人的“红孩儿”终于脱离鬼子揭钵故事体系,获得了自己的规定性。到了清代李汝珍《镜花缘》中红孩儿与道教各仙翁共赴昆仑为西王母祝寿,“只见福禄寿财喜五位星君,同著木公、老君、彭祖、张仙、月老、刘海蟾、和合二仙,也远远而来。后面还有红孩儿、金童儿、青女儿、玉女儿,都脚驾风火轮,到了昆仑”。
吴本《西游记》四十一回,孙悟空与红孩儿斗法时,红孩儿手拿丈八长的火尖枪,身上未着盔甲,只是腰间束一条锦绣战裙、赤着脚的小孩。只见他“面如傅粉三分白,唇若涂朱一表才。鬓挽青云欺靛染,眉分新月似刀裁。战裙巧绣盘龙凤,形比哪吒更富胎。双手绰枪威凛冽,祥光护体出门来。哏声响若春雷吼,暴眼明如掣电乖。要识此魔真姓氏,名扬千古唤红孩”。《西游记》中红孩儿使用的是连孙悟空、四海龙王都无可奈何的独门利器——三昧真火,这是释道二教结合的产物。“三昧”为佛教语,旧称三昧,音译“三摩地”,意为定、正受、等持,“谓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佛教以此作为取得确定之认识、作出确定之判断的心理条件,也有着念佛三昧的说法”[7]709。《观无量寿经》曰:“现身中得念佛三昧。……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8]1620《大智度论卷五》曰:“善心一处住不动,是名三昧。”《卷二十三》曰:“一切禅定摄心,皆名为三摩提,秦言正心行处。是心从无始世界来常曲不端,得此正心行处,心则端直,譬如蛇行常曲,入竹筒中则直。”《卷二十八》曰:“一切禅定,亦名定,亦名三昧。”《大乘义章卷二》曰:“以心合法,离邪乱,故曰三昧。”《卷九》曰:“心体寂静,离于邪乱,故曰三昧。”《卷十三》曰:“定者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言三昧者,是外国语,此名正定。”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三昧”也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包括对某事深有造诣或悟解其奥,可以说“深得个中三昧”。
道教认为“真火”有三,以身体的三个器官心、肾、膀胱对应上昧、中昧和下昧。《道枢》卷七《水火篇》曰:“人身有三昧之火焉。一曰君火,是为上昧,其心是也。二曰臣火,是为中昧,其肾是也。三曰民火,是为下昧,其膀胱也。”[9]71此三昧聚而为火,散而为气,升降循环有周天之道。《西游记》第四十一回红孩儿按金木水火土五行法布阵五车,也反映出“三昧真火”与道家的渊源。“那妖魔捶了两拳,念个咒语,口里喷出火来,鼻子里浓烟迸出,闸闸眼火焰齐生。那五辆车子上,火光涌出。……这火不是燧人钻木,又不是老子炮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妖魔修炼成真三昧火。五辆车儿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彻通灵。生生化化皆因火,火遍长空万物荣。妖邪久悟呼三昧,永镇西方第一名。”因此,四海龙王的私雨只能灭人间凡火,而圣婴大王的三昧真火只有被观音菩萨净瓶中聚集三江五湖、八海四渎、溪源潭洞的甘露真水所降,正是应对了道家五行中水火相克之理。
值得注意的是《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中,孙悟空给观音菩萨介绍红孩儿唤作“圣婴大王”时,李贽批道:“谁圣不婴?谁婴能圣?”[10]324《老子》第四十九章云:“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此章中的“孩”字,历来注家多以“小孩”“婴孩”之义为训。古人将新生儿称为“赤子”。《尚书·康诰》曰:“如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孔颖达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汉书·贾谊传》曰:“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颜师古注:“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发,其色赤。”满三月则为“孩”。初生婴儿皆为赤色,故圣婴大王名红孩儿,他的出现也总与红色有关,所居之地为枯松涧火云洞,现形前为一朵红云。“师徒们正当悚惧,又只见那山凹里有一朵红云,直冒到九霄空内,结聚了一团火气”;“却说红光里,真是个妖精”;“却说那孙大圣忽抬头再看处,只见那红云散尽,火气全无”;“妖怪即散红光,按云头落下,去那山坡里”;“他抖一抖身躯,脱了绳索,又纵红光,上空再看”;“却说那孙大圣抬头再看,只见那红云又散,复请师父上马前行”。因此,作者让红孩儿出场前在色彩上多角度映衬这个与众不同的英雄小战神形象。《老子》第二十章云:“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陆德明释为:“孩字又作咳”,意为“孩”是出生几个月后会咳咳而笑的小儿,婴孩与成人的区别在于婴儿刚出生知觉未有智识未开,还处于混沌无知的状态,尚未有善恶之分利欲之辨。老子以“圣人皆孩之”譬喻处在混沌恍惚婴儿未孩的状态,这样才能与“道”共存。或许,圣婴大王红孩儿原本就寄予了作者的一种人格理想,修行三百年依旧能够以“童神”的形象叱咤寰宇,《西游记》中诸多魑魅魍魉却无出其右。
三、善财童子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西游记》杂剧中《鬼母皈依》一出,即用揭钵盂救幼子故事者,其中有云,‘告世尊,肯发慈悲力,我着唐三藏西游便回。那唐僧,火孩儿妖怪放生了,他到前面须得二圣郎救了你’。而于此乃改为牛魔王子,且与参善知识之善才童子相混矣。”[11]133《西游记》四十二回中红孩儿被观音收服后,有作者的一段插话:“如今说,童子拜观音,五十三参,参参见佛,即此是也”。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故事见于《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在证果之前,不辞辛苦,经历一百一十城,前后参访菩萨、佛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天神、地神、主夜神、王者、城主、长者、居士、童子、天女、童女、外道、婆罗门等在内的五十三位善知识,故称五十三参。
如果论起师徒关系,善财童子首先是文殊菩萨的徒弟。《华严经》中文殊师利菩萨奉佛之命,渐次南行,教化众生,于福城东庄严幢娑罗林中说法。善财参与法会,在文殊教导之下,志笃精进,向南求法,经历百余城,最后入弥勒楼阁,证入法界。善财直到第二十九参方拜见观音菩萨。《华严经·入法界品》云:“(善财)渐次游行,至于彼山。处处求觅此大菩萨,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泉流萦映,树林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善财见已,欢喜踊跃。”《佛祖统纪》卷四十二载:“日本国沙门慧锷,礼五台山得观音像。道四明,将归国。舟过补陀山,附着石上不得进。……鄞人闻之,请其像归安开元寺……山在大海中,去鄞城东南水道六百里,即〈华严〉所谓:南海岸孤绝处,有山名补怛落迦,观音菩萨住其中也。即〈大悲经〉所谓:‘补陀落迦山,观世音宫殿,是为对释迦佛说大悲心印之所。其山有潮音洞,海潮吞吐,昼夜砰訇。洞前石桥,瞻礼者至此恳祷。或见大士宴坐,或见善财俯仰将迎’。”[12]268慧锷之事发生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以故最晚在晚唐时期,善财童子就已与观音发生牵合”[13]13。此外,在历代名画中,也有以观音与善财为题的画作,如宋代佚名《柳枝观音菩萨》善财童子于观音右下角单脚独立而起,手执莲蓬,足现莲花;故宫博物院元代阿加加、赵雍所画之观音画,左侍者也为善财童子[14]188。《西游记》中观音为收服红孩儿取出一个金箍儿“迎风一晃,叫声‘变’,变作五个箍儿,望童子身上抛去,叫声‘着’,一个套在他顶上,四个套在手脚上”。成都龙藏寺壁画现存明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像,其中图二十二明显可见善财童子脖颈、手腕、脚腕上的金箍儿。《八十华严》卷六云:“(善财童子)至伊沙那聚落,见彼胜热修诸苦行、求一切智。四面火聚犹如大山,中有刀山高峻无极,登彼山上投身入火。善财童子顶礼其足,合掌而立。(胜热)婆罗门言,‘善男子,汝今若能上此刀山,投身火聚,诸菩萨行悉得清净’。尔时,善财童子即登刀山,自投火聚,未至中间,即得菩萨善住三昧;才触火焰,又得菩萨寂静乐神通门三昧。善财自言,‘甚奇,圣者,如是刀山及大火聚,我身触时安稳快乐’。”两相对照完全符合,即善财童子第十参胜热婆罗门,得菩萨无尽轮解脱法门的表现。
民间信仰中,观音身边总伴随着一对童男女的形象。的确,善财童子并非观音身旁唯一的侍者。《西游记》四十三回菩萨助孙悟空灭三昧真火,孙悟空拿净瓶不动,观音说,“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观音出了潮音仙洞,着善财龙女去莲花池里劈一瓣莲花渡悟空过海,并吩咐善财龙女闭了洞门,方纵祥云离普陀。可见最终观音座下侍者有二,分别为善财龙女与善财童子。善财童子与观音虽在唐末有牵合之迹,然善财龙女为观音侍者似在五代宋初。宋延寿《宗镜录》云:“若就众生见解位看者。尚不见唯心即空。安见圆教中事。如迷东为西。正执西故。若诸情顿破。则法界圆现。无不已成。犹彼悟人。西处全东。是以善财龙女。皆是凡夫一生亲证。三乘权教信不及人。称为示现。如玄义格云。人谓善财龙女。是法身菩萨。化为幻技。一时悦凡人。令自强不息耳。”[15]594四川大足石刻保存了五代与宋时造像。五代窟中善财、龙女作为观音侍者的造像在佛湾218窟中有所体现[16]90。而在宋代石窟如118窟之玉印观音、119窟之不空羂索观音、120窟之净瓶观音,以及126、127窟中之观音的侍者均为善财与龙女塑像[16]43-49。虽然有学者考证“佛典中的善财童子与小说《西游记》中的红孩儿,其实毫不相干”[17]113,但文学形象与民间信仰之间经常发生常式与变式的更替交融,经过文人的加工再创造,“虽吸收外来故事人物,曼衍释典,能使之彻底中国化本土化,与中国固有之风俗习惯生活打成一片,佛法反因之而益弘,人民信仰反因之而益坚”[18]1061。善财童子/红孩儿之间与佛教形象/神话形象之间便构成了同类意指项,使这两个原本毫无关联的佛/妖形象却在民间符号的能指与民间信仰的所指中逐渐趋同。
作为鬼子母五百子之一的嫔伽罗/爱奴儿,其演化是随着鬼子母故事的演变而演化的。鬼子母嫁接为铁扇公主,火孩儿/红孩儿自然也就成了铁扇仙之子。从此,嫔伽罗/爱奴儿由印度血统转化为中国血统,实现了中国化。红孩儿形象由啖食人肉的鬼子母夜叉之子转变为攫取唐僧肉的圣婴大王,并最终以善财童子的身份被神化。红孩儿形象的中国化,为其形象的演变和神话化开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中华大藏经:第五十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宋)无名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年.
[5]杨景贤.西游记[C]//隋树森.元曲选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6]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C].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7]任继愈.宗教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8]李林,洪雅萍,译注.佛经精华(下):观无量寿经[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9](宋)曾慥.道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0](明)吴承恩.李卓吾先生批点西游记[M].李卓吾,批点.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2](宋)释志磐.佛祖统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3]冯国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故事的影响[J].法音,2003(8):8-13.
[14]徐建融.观音宝像[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15]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128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刘长久,胡文和,李永翘.大足石刻内容总录[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17]林冠夫.红孩儿、善财童子、齐天大圣庙——读《西游记》札记二[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111-115.
[18]柳存仁.和风堂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编辑:赵树庆)
A Study on the Image of the Red Boy
CHE Rui
(SchoolofHumanities,NingboUniversityofTechnology,NingboZhejiang315211,China)
Abstract:The Red Boy is one of the few child images in the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who is recre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cultural prototype before the Ming Dynasty and by religion, myth and text inter-textuality. In the process of character development, it goes from the Ghost Mother to Boy Sage King and the Page Sudhana. The True Samadhi Fire used by the Red Boy is integrated with the Buddhist doctrine of “meditation and spiritual regulation” and the Taoist philosophy of “generation-inhibition in five elements” and is typical of Indian lineage sinicization, Chinese image localization and local character mythologization .
Key words:the drama of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Red Boy; the Ghost Mother; the Page Sudhana; the Boy Sage King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5)01-0064-04
作者简介:车瑞(1979-),女,山西垣曲人,宁波工程学院讲师,扬州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文化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 “明清书坊对戏曲的影响研究”(13CB088)
收稿日期:*2014-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