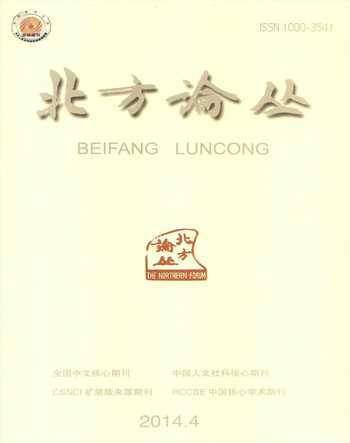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中的“跨界现象”
2014-04-29袁国兴
[摘要]清末民初新潮演剧对古今中外不同文化、文学、戏剧现象的“误读”和错位性理解,曾大面积发生,此即在文章中所述的“跨界现象”。跨界性思维虽然给当时戏剧类型意识造成了一些迷茫,但也给新潮演剧带来了少有的生机和活力,是中国现代戏剧文化转型的一种特有方式。
[关键词]清末民初;新潮演剧;跨界现象
[中图分类号]I207.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4-0001-06
清末民初的新潮演剧,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化转型的一种特有方式。对古今中外各种戏剧现象的“误读”和错位理解,曾大面积、多角度、普遍性地发生。本文所谓的新潮演剧中的“跨界现象”,指的就是这种对传统戏剧文化造成了系统性冲击,让人们的原有戏剧意识发生了震荡,以跨越戏剧类型意识和戏剧艺术边界的方式进行戏剧变革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
近代社会以前,中国戏剧基本是在封闭和半封闭条件下,在传统文化氛围中“独立自主”孕育发展起来的,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特别艺术观念,它们的“能指”和“所指”,都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与整体戏剧意识协调统一。可是,近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属于异己的另外一些文化系统的戏剧样态被介绍进来。此时,中国人用什么样的观念意识和词汇概念去指认和指称它们呢?当中国人把“国外的戏”与“中国的戏”看作同一的戏剧时,不仅在于昭示,人们已经发现了中外戏剧的相似文化特性和类似文化功能;还在于提示,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用“中国的”戏剧观念去看待外国戏剧的。也就是说,中国剧与外国剧原本是不同的,但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条件下,人们把它们的相似和相近因素放大了,把它们在戏剧类型意识方面的不同因素缩小了。这就造成了贯穿于整个新潮演剧过程中,中外戏剧无差别的“越界”思维和“跨界”理解的发生。
虽然到了五四时期人们才公开打出“文学并无中外的国界,只有新旧的时代”差别的旗号[1],但其基本意向早在近代之初的中国文学变革中就已经出现。然而,正因如此,在“大文学”层面去探讨问题,在具体的“小”事上就可能惹出一些麻烦。文学不是一个具体的称谓,古今中外不存在一种既不是诗歌、小说,也不是戏剧等其他文类的所谓“文学”,而一旦人们进入到这一层面来思考问题,就会发现,中国诗与外国诗、中国小说与外国小说、中国戏剧与外国戏剧,并不完全相同。新潮演剧意识所涉及的问题,虽然也比较“大”,但比起 “文学”要“小”得多,因为文学意念是由不同写作类型的作品构成的,当人们从戏剧表演艺术层面思考问题时,毕竟已经不同于从更普泛的“文学”层面切入论题,它似乎更容易接近于从不同艺术类型的角度来展开思考,这也许就是新潮演剧意识早于新文学意识兴起,也早于新文学意识消歇,话剧和戏曲更早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无论怎样说,新潮演剧所遵循的思路与“大文学”思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正所谓“泰西各国近改良戏剧,所以开通民智之基础也”[2](p551),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因为“开通民智”既可以用小说的手段,又可以用诗歌的手段,也可以用戏剧的手段,甚至还可以不用“文学”而用其他的社会变革手段。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去追求中国剧与外国剧的同质意向,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也比较好操作,当然问题也是明摆着的。新潮演剧崛起的基本理路是:国外的剧与中国的剧都是剧,借助描述国外剧的情形来为中国剧变革提供样板,让中国剧有国外剧的职能和身段;至于国外剧与中国剧在戏剧类型意识上的不同,国外剧的情形是否像人们描述的那样,中国剧在做戏方式上能不能与国外剧完全一样等,都不在新潮演剧意识的视野之内。蒋观云在《中国之演剧界》一文中,借用某外籍人士的话说,中国剧“其战争犹若儿戏,不能养成人民近世战争之观念”[3]。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第一,他从“养成人民近世战争之观念”的角度要求中国戏剧变革,与从“大文学”的角度要求中国文学变革的思维路径是一致的;第二,中国剧“其战争犹若儿戏”有相当部分是与其戏剧类型意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的核心是:在蒋观云的“戏剧意识”中,中国剧与外国剧不应该有差别,这一理论前提鼓励了他对中国剧的批评,这才使得他要求中国剧变革的意识——向外国剧靠拢的意识——有了更加“可靠”的理论支撑。
在新潮演剧意识中,既然外国剧与中国剧可以被人无差别地理解,那么,“新编的剧”和“新式的剧”也有了“跨界”指认和“跨界”理解的可能。我们知道,在新潮演剧风行之时,“新剧”这个概念是既清晰又模糊的。说它清晰,是因为所有被人称为新剧的那些剧作,都体现了一定的改革意识,比如,同被人们称为新剧的《铁公鸡》《官场丑史》《张文祥刺马》《黑奴吁天录》,等等,虽然它们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与传统戏剧比起来,都有那个时代人们体会到的“新潮”意识在里面,与“开通民智”、“养成人民近世战争之观念”的社会变革意识相一致,因此,都可以被人归为“新剧”的行列。但这样的新剧意识又是模糊的,因为被人看作“旧剧”的《金山寺》《打渔杀家》等,除了题材不够时尚,其思想意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落伍,自然也有某种“新潮”意味。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笼统的新剧意识中,有些新剧在演出手段和戏剧类型意识上与“养成人民近世战争之观念”又有相当距离,当人们把它们都称为新剧时,其“新”的意涵就不可能不发生某种模糊。
一旦人们从“大文学”变革意识出发去看待中国剧和外国剧,以及新编的剧和新式的剧,戏剧类型的“跨界”理解就必不可免。正因如此,在新潮演剧兴起的高潮中,质疑和辨析“新剧”的声音也随之而起。在当时有些人看来,“中国之戏与西戏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凡西戏未演之前先出告白贵客眷属均请往观……动不干非礼,静而能安,并无喧扰。至于捉狮擒虎胆智间优,踏索走绳变化不测,各种戏法尤令人不可思议,华人虽不能尽得其妙,而醒心快目,清兴正复不浅”[4]。笔者在《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一书中也曾探讨过,中国人最初企图对外国剧和中国剧的不同进行识别时,首先是从剧场、演员和演出手段等戏剧外围因素开始的[5](pp18-19)。为什么会如此?中国剧与外国剧的差别本来一眼就可以让人看出来,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它们都是戏,就像“捉狮擒虎”、“踏索走绳”,本来与演故事的戏剧是不同的,可它们都是“戏法”,也就是说,不是真实发生的事,站在“戏者戏也”的意识层面,都被人看做同一种文化现象了。如此一来,中国剧和外国剧、不同样式的剧,虽然差别明显,但站在特定立场上看,反倒不如剧场、演员和戏剧组织形式更容易让人识别。而用“戏”这种普泛化的艺术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社会追求,外国剧和中国剧、新编的剧和新式的剧也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也顾不得去细致辨析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从“养成人民近世战争之观念”的角度出发,不同的剧,比如,现实题材的剧与传统题材的剧,其作用大小又有所不同的。梅兰芳就认为:“我们唱的老戏,都是取材于古代的史实。虽然有些戏的内容是有教育意义的,观众看了,也能多少起一点作用。可是,如果直接采取现代的时事,编成新剧,看的人岂不更亲切有味?收效或许比老戏更大。”而他所编演的“《孽海波澜》,是根据北京本地的实事新闻编写的”[6]。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伴随着新潮演剧全过程的最大“理论”问题,一直都是所谓“什么是新剧”、“什么是旧剧”,以及二者的区别到底在哪里等问题。从整体上说,跨越了传统的戏和新编的戏的界限,把“新式”的戏与“旧式”的戏区别开来,是新潮演剧所能做到的最大“理论贡献”,而中国剧与外国剧的不同,新潮演剧还无暇顾及,不仅新潮演剧顾及不到,后来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中国戏剧理论界一直都对它显得没有什么热情。而这恰恰说明,在戏剧类型意识上“跨界”思维,是新潮演剧崛起的主要理论支撑,也是它的一个主要体貌特征,一旦什么时候人们认识到这个问题,转换了思维方式去探讨问题,新潮演剧意识也就开始消歇了。
二
在以上的探讨中我们感到,从文化功能上着眼,而不是从戏剧类型意识上着眼,要求中国戏剧变革,是新潮演剧跨界思维出现的主要动因。然而,这种变革策略也不仅仅发生在戏剧类型意识的“内部”,还在戏剧与其他社会活动“外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一再得到呈现。
在新潮演剧过程中,“演说”与“演剧”常常被人视为是同一种文化现象,经常被相互借用和跨界去理解。我们知道,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演说”有时也被人看作一种有论说性质的文体,比如,《遥吟俯唱戏会在昌平州演说》就是这样[7]。可是这样的 “报章演说”[8],与传统的“论说”也有不同。登在报纸杂志上只是它们的一种“副文本”,它们的原本形态是直接面向观众的口头讲演。因此,我们看到,在戊戌变法前,报纸杂志上有许多“演说”类的论说体式文章出现,而戊戌变法后,当大众讲演的演说形式得到吹捧之后,报纸杂志上的“演说”类文章就有些销声匿迹了,有时称谓也发生了改变,以“白话”或“论说”的称谓取代了所谓的“演说”。新潮演剧的兴起,与口头讲演的勃兴取同步姿态,所谓“开演说,聋自觉”,“言之不足而长言之”,求其“以声音笑貌之感人”[9],在这样的思考中,演说和演戏并没有什么区别。 “唱戏演说”被人并列起来理解[7],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沪上所演《铁公鸡》《左公平西》之类,发扬蹈厉,感人实深,声色并传,雅俗共赏,亦别开演说一生面也”[10]。在这里,“沪上所演《铁公鸡》《左公平西》”等就被人当作演说,而许多人倡导新剧也是因为他们觉得演戏可以“现身演说”[11]。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一方面用演说的方式要求演剧或者用演剧的方式要求演说。新潮演剧者被人看作“演说家”[12],观众“均以新戏为演说一流”就是这样[13]。另一方面,当人们用演说的方式要求演戏或者说用演戏的方式要求演说时,也看到了二者相互借用的可能,利用演剧来演说就是这种倾向的反映。“编戏曲以代演说”[14]或者利用演戏来“演光学电学各种戏法”、“练习格致之学”的主张就是如此[15]。而在我们看来,不论是把演说看作演戏,还是利用演戏去演说,都只有跨越演戏和演说活动的边界才能做到,它们都是跨界思维的结果,都是新潮演剧跨界现象的一种体现。
在新潮演剧过程中,演剧也常常被人视为与广义的社会教育具有同质。1914年公布的《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中指出,要以“通俗的社会之教育”来“补充群众道德及常识”,而所谓的通俗教育主要指“通俗讲演”、“通俗书报报章”,以及“改良小说”和“改良词曲”等[16](p247)。在《教育部官制》中更规定,“社会教育”管理的对象除了“演讲会”,还有“关于文艺音乐演剧事项”[17]。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新潮演剧倡导者所主张的“盖戏剧者,学校之补助品也”[18](p508)及“当世明达之士多以社会教育之荣名标作新剧之宗旨”的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19]。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这样一种“制度”的制定和文化倾向的形成,命意原本在于“社会教育”,而不在于演剧。其内在逻辑是:“中国文字繁难,学界不兴,下流社会,能识字阅报者,千不获一,故欲风气之广开,教育之普及,非改良戏本不可。”[20]把演戏看作社会教育的一种手段,除了在文化功能上让人们找到它们的相近因缘,还与传统教育方式的转型和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有一定关系。中国传统的教育展开方式是私塾式的家庭教育,近代开始引入西式的学校教育,即所谓“官办义塾”和官办学堂。“私塾”原本姓“私”,它隶属于某个私人性质的利益团体,即使是带有一定公益色彩的 “书院”,也没有完全脱离民间的“私有”性质。而“官办义塾”和官办学堂不是如此,“官办”是公共性质的,它隶属于整个国家和社会。这一教育性质的改变带来了与教育相关的其他一些方面因素的改变。在传统私塾教育中,教员受雇于某一私人性群体,而在学校教育中,“书院山长必由公举”[21](p72),“老成有品、能讲说者为师”[22](p89),教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公职人员,其公共性身份加强了。如果说私塾先生是达官贵人的“西席”座上宾,那么,官办学堂的教员就有条件地成为“社会教育家”。这样一来,被人“以社会教育之荣名”标榜的演剧活动,随其演剧目的的转移,其演员的身份也自然要发生转移,从搭班演戏的“伙计”,有条件地成为社会公共活动的一分子。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演新剧者何以不名伶人,而称新剧家”,它所遵循的思维路径与教育方式的转移相同步,新剧家不称伶人,是因为他们自恃“其智识程度足以补教育之不及,人格品行可以做国民之导师也”[23]。不论演剧者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资质,只要你把演戏与社会教育联系在一起,演员身份就会得到解放,就绝不是传统“伶人”意识所能归化得了的。官办学堂和学校,除了抹除了教育的私密色彩,还相应地增加了教育的公共空间意识,把剧场当作学校看待,既与新潮演剧兴起的社会目的有关,也与剧场和学校的相近文化特性相关。近代社会许多新潮演剧的举行,都发生在学校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不把演戏作为教育的手段,学校没有权利演剧;而学校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公共空间属性,也没有条件进行演剧。而不管是演员身份的转变还是学校活动空间意识的转变,都从一个侧面鼓励了演剧和社会教育的跨界现象出现。
“演说”也好,社会教育也好,在中国近代社会之所以受到社会舆论的高度正面评价,都是因为其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变革思潮在驱动。“演说”的风行,是这个社会变革思潮催生的结果,教育的新生也是这个社会变革思潮催生的结果。演剧与“演说”和社会教育被人认为具有同质性,它们之间的关系被人定义为:“社会家未必定为新剧家,而新剧家必得为社会家,盖新剧家对于社会上一切事业皆有提倡废革之责……”[24]。如果在有限的范围内这样去理解未尝不可,但在新潮演剧中,不论事实如何,新剧家和社会家的身份都被人过于凝固性地绑定在一起了。这样一来,一方面新潮演剧有时被人视作、等同于一般社会活动,“宣统年间所演的戏,几乎没有一出不是骂腐败官吏的”,“社会对于新剧的心理中,终有‘革命党三个字的色彩在里面”[12]。另一方面,新潮演剧者、新潮演剧活动本身也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作一般的社会活动。许多新潮演剧者都曾亲身参与当时的社会变革行动,有的还成为革命烈士“九月十三之役,月樵亦亲历炮火,稍尽义务,偶为敌弹伤足,不得不杜门养疴……”见《潘月樵致沪都督书》,《申报》1911年12月6日。“钱逢辛被举为水上游击队队长,深夜巡黄浦江,为十字军误击弹中,逢辛而卒。”见朱双云:《新剧史》,新剧小说社,1914。。一般说来,文学、文艺活动,本身就是社会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变革大潮中有某种激进色彩不足为奇。但像新潮演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活动与演剧活动的过于同质性追求并不多见,二者的跨界思维和跨界行为,已经超出一般的戏剧活动范围,因此,它也是不可能长久维系的。在新潮演剧高潮中,就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做;在新潮演剧高潮过后,更有一个戏剧不断“归位”的过程。问题是,在整个新潮演剧过程中,都不可能有人从正面去触及这一问题,而这恰恰是新潮演剧的一个重要特征,什么时候,人们开始思考演剧活动与普通社会活动还有什么不同,适当地让演剧活动与普通社会活动脱钩,新潮演剧意识和新潮演剧活动也就终止了。
三
新潮演剧兴起的主要推动力是外国戏剧的影响,举凡改良戏曲、学生演剧和早期话剧等都是如此,历来人们都不怀疑这一点。然而,这里的所谓外来影响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到底应该在哪些层面、何种程度上看待这种影响?前文我们谈到,中国人最初是在用“中国的”戏剧观念去看待外国戏剧,即把中国的戏和外国的戏都看作戏,如此影响才能发生;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戏与外国戏毕竟不同,在当时人眼里这种不同,除了我们上文分析过的戏剧外围因素,还有演剧形式方面的因素。如果说人们在一定程度的中外戏剧无差别意识中跨界要求中国戏剧变革的话,那么,当人们进入戏剧类型变革内部,在对中外戏剧类型进行辨析时,传统戏曲思维和戏曲意识又自觉不自觉地“被跨界”性地移用到新潮演剧中。
新潮演剧兴起之时,极端的言论以为“中国无戏剧”[25],因为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戏剧不应“唱与演参半”,而要全部以“科白说明之”[26](p107)。关于他们对“演”与“唱”的关系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去深究;可他们对不唱的“演”是怎么认识的却不能不引起我们注意。昔醉在《新剧之三大要素》中认为,不“唱”之“演”要“分徐疾高低抑扬顿挫,使声容并茂,而补表情之不足”[27]。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所谓“抑扬顿挫”、“声容并茂”,虽然不是“唱”,但并没有离开“唱”的“演法”多远,他是以传统戏曲演唱的方式去揣摩“新剧”演出的。在整个新潮演剧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新剧一直在追求“说”的戏剧效果,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又觉得“欲至以说白博观者之赞美,为事亦至难”[28],之所以有此种认识,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谈文字不能废诗,戏剧断不能无唱……做白之不尽,歌以振发之”[25]。这样一来,表面上看他们在追求新式的“真正的戏剧”,其实处处流露的还是传统戏曲情趣。《乌江》初演有所谓格斗的场面,编者要求演员“参以旧派俳优之扑斗”,也就是说,他希望能用京戏的“武把子”排演这段戏;至于“虞姬之舞则就歌中板眼而为顿挫进退,参以日本之舞,采用中国旧戏之动作”[29]。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种“有板有眼”的戏剧,除了不唱,与传统戏曲又有什么区别呢?正因如此,在新潮演剧过程中,“身披古时衣而口说新名词”的现象大量存在[30],女演员都学“贾璧云、梅兰芳、冯春航”[31],在这种背景下,新潮演剧艺术形态的“混搭”和跨界还不是自然而然的了吗?
前文我们谈过,新潮演剧与演说常常被人跨界理解,现在我们要说,演说和演剧的跨界,不仅仅是剧与非剧的区别,用传统戏曲眼光看或在某一层面上审视,演剧中确有“演说”的成分。1892年《申报》登了一篇文章,其中申明:“咸同以来,优人……其所演说无所谓故事遗闻也,大抵皆无根之谈”[32]。他所谈的事实如何我们不管,他把戏剧中的一种表演形态看作“演说”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招隐居》第二出为什么堂而皇之地要求“演者须台前朗诵”“戒烟歌”“此段正文,演者须台前朗诵”。钟云舫:《招隐居》第二出,载《钟云舫全集校注》(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朗诵”是一种演法,这种演法在中国戏曲中曾屡见不鲜;新式戏剧不唱,“朗诵”并没有被排除在外,不仅没有被排除,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新式演剧倚重的主要做戏手段,只要做到“千言万语均与本戏有关,间或引古征今,借题发挥,亦须引用符合不露形迹”[27],就完全符合新式演剧的规范了。而这样的新剧与旧剧不是在被“跨界”理解吗?
不仅在“曲演”和“说演”的理解上,“新剧”与“旧剧”存在貌似分离其实相通的问题,在其他表演方式上也是如此。比如布景,中国传统戏曲无所谓布景,有布景自外来影响的新剧始,可是当新潮演剧依样画葫芦,在舞台搭起了布景时,布景是被当作画片来理解的,取其好看吸引人眼球的一面,至于布景与剧情的关系,一时还不在大多数新潮演剧追随者的视野之内“泰西各种……油画点缀风景……所布置的都是世界景致……”见《戏剧进化》,载《顺天时报》,1910年1月1日。。布景是如此,服装道具也是如此,因为传统戏曲的服装是与任何朝代都没有关系的,它是舞台上的一种特有“行头”,当新潮演剧追求写实性的服饰时,在有些人眼里“写实”就变成了对另一种流行服装的追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戏,系古事,应服古装。而近日演此戏,有着新式装者殊不合”[33](p559)。为什么如此?戏剧服饰意识的跨界理解而已。在此种情形中,即使有了某种新型戏剧类型意识的出现,在具体理解和实现的过程中,也是逐渐才能被人领悟到的,在这个过程中就常常会出现一些戏剧类型意识的跨界现象。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事例,在《暖香楼杂剧一出》中,编者要求演剧者在“场上先设妆台一座”,演出过程中当戏剧场景发生了转换时,又要求演剧者 “场上将妆台撤去,改设酒席介”[34]。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传统戏曲根本不需要在“场上先设妆台一座”;而新式演剧既已在“场上先设妆台一座”,也就没有办法再临时“换场”了。当《暖香楼杂剧一出》的编者要求 “场上将妆台撤去,改设酒席介”时,此时已经在台上的演员干什么?干瞅着剧务人员换布景吗?他之所以有了这样一种费力不讨好的瞎“折腾”,是因为在他头脑中还存在 “切末”意识——“切末”是可以由“检场”人去临时处理的,在这里他还是用了传统的招法来处理“现实”问题。
行文至此,我们不能不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跨界能够成为新潮演剧的一种代表性形态?其意义和作用到底应该怎样评价?前文为了说明我们的主要观点,对新潮演剧中不同时期、不同演出团体的差异问题暂时都没有去顾及。其实,新潮演剧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同演出团体、不同剧作,对中外戏剧、对戏剧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系理解,都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在笔者看来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本质的区别。具体说就是有的演出群体和有的戏剧演出,比较早地认识到跨界的演剧倾向和跨界带来的演剧局限,有的演出群体和有的戏剧演出对此的认识相对晚了一些。我们所探讨的对象,包括对新潮演剧兴起和衰落的认定都是对整体趋向性的把握,并不排除个别和特殊情况的存在。而这种跨界的不同步,恰恰给我们提示了一个看待新潮演剧的特殊视角:不同的演出实践都是一个相对的有序存在,它们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显示了新潮演剧的一种发展趋向。从总体上说,跨界程度高的演出排在这个序列的靠前位置。在跨界程度低的演出排在这个序列的靠后位置。在新潮演剧刚兴起时,跨界程度高;在新潮演剧衰落时,跨界程度低。这就告诉我们:新潮演剧的跨界现象是中国现代戏剧转型的特有方式。这种转型有两种发展方向:一是对新型演剧的移植;二是对传统演剧的改造。不论是哪种转型都在新潮演剧中获得了足够的动能。如果没有新潮演剧的跨界现象出现,两种转型都不可能实现,跨界本身就是在重新定界。与跨界给当时演剧界造成的意识模糊比起来,它的发展方向是清晰的,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借用传统戏曲方式去跨界理解新型戏剧,用新型戏剧方式去跨界理解传统戏曲,是新潮演剧的基本行动策略,它们的混搭和混演虽然造成了戏剧类型意识上的一时迷茫,但也给新潮演剧带来了少有的生机和活力——当新潮演剧消歇的时候,新型演剧诞生了,传统演剧也迈上了新里程。
[参考文献]
[1]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J]新青年,1919,6卷4号
[2]慕优生海上梨园杂志·新剧闲评·年大将军:卷四[C]//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3]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C]//晚清文学研究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
[4]中西戏馆不同说[N]申报,1883-11-16
[5]袁国兴中国话剧的孕育与生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6]梅兰芳梅兰芳全集:一[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遥吟俯唱戏会在昌平州演说[N]京话日报,1906,669号
[8]论戏曲改良与群治之关系[N]申报,1906,922号
[9]尊伶篇[N]同文消闲报,1904-08-15
[10]春梦生维新梦·序[C]//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论风俗之害[J]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1)
[12]陈大悲十年来中国新剧之经过[N]晨报·副刊,1919-11-15
[13]义华剧趣·戏剧杂谈[J]民权素,1915,(4)
[14]编戏曲以代演说说[N]大公报,1902-11-11
[15]三爱论戏曲[C]//晚清文学研究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
[16]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C]//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7]教育部官制[C]//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8]慕优生海上梨园杂志·论说·剧场之教育:卷一[C]//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19]剑云新剧杂话[C]//鞠部丛刊上海: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
[20]箸夫论开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戏本为先[N]芝罘报,1905,(7)
[21]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C]//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2]小学义塾启:附规则[C]//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3]剑云晚近新剧论[C]//鞠部丛刊.上海: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
[24]豪士新剧角色与其资格[J]戏剧丛报,1915,(1)
[25]剑云剧学论坛[C]//菊部丛刊上海: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
[26]健鹤改良戏曲之计划[C]//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六.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27]昔醉新剧之三大要素[C]//菊部丛刊上海: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
[28]芳尘戏剧潮流[C]//菊部丛刊上海: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
[29]吴我尊史剧乌江二幕[J]春柳,1919,(5)
[30]正秋新剧经验谈[C]//菊部丛刊上海:上海交通图书馆,1918
[31]俳优琐言[J]俳优杂志,1914,(1)
[32]论酬神宜禁淫戏[N]申报,1892-12-04
[33]杜十娘应服古装海上梨园杂志:卷五[C]//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34]长洲吴梅暖香楼杂剧一出[J]小说林,1907,(1)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