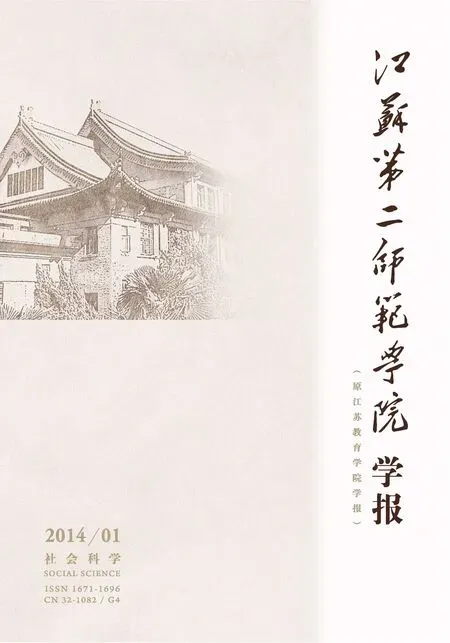理论纷争与经典的变迁:从先锋到后先锋*
2014-04-17周韵
周 韵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13)
理论纷争与经典的变迁:从先锋到后先锋*
周 韵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13)
先锋派对于20世纪文化艺术史来说是一个重要而又难解的谜。它在颠覆传统经典的同时,倾向于构建新的经典,因此先锋派总是处于理论纷争之中。随着现代技术、资本、文化的扩张,先锋派不断走向终结,经典边界也日益消解。在后现代转向中,理论在经典的批判和建构话语中取代实践成为当下的文化先锋。
先锋派; 艺术经典; 艺术理论; 后现代转向
先锋派是一个棘手而又引人入胜的问题。它总是以反经典的姿态出现,但几经周折后又常常跻身于经典的行列,戏谑地迎接着来自观众的困惑目光。杜尚的《喷泉》便是最典型的个案。在颠覆了关于美学和艺术的所有观念之后,这只签有假名的男用小便器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博物馆、艺术史和艺术研究著作,占据了它曾意图攻击的经典神龛。尽管理论家们对先锋派的这一悖论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先锋派以失败而告终,成为了它所极力反对的东西,有的则认为先锋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但是他们无疑都宣告了先锋派的终结,艺术从此进入了“后”时代:后先锋、后经典、后现代等等。本文试图首先对先锋派的理论化过程作一个简要的描述和分析,揭示先锋派内在的终结趋势,在颠覆传统经典的同时,倾向于构建新的经典,然后指出现代技术、资本、文化的扩张加速了先锋派的终结以及经典边界的消解,最后提出理论在经典的批判和建构话语中取代实践成为当下的文化先锋。
一
诚如贡巴尼翁所言,先锋派比任何艺术运动都依赖理论,倾向于利用理论来保障自身的未来,或者说自身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其理论总是导向新的从众主义。[1](P.64)更为重要的是,先锋派经历了双重理论化过程,一是先锋派的自我理论化,通过宣言、访谈、著述等方式提出新的审美规划,二是批评家和理论家们对先锋派的种种理论探讨和反思。这些理论的矛盾和纷争表明,先锋派及其理论都包含固有的悖论性。哈罗德·罗森堡的书名“新艺术的传统”恰到好处地点出了先锋派的这一特征。
在自我理论化过程中,尤其是在宣言中,先锋派总是摆出与传统决裂的姿态,推动一种新的审美规划。但是,在宣布与传统决裂之际,先锋派无一不表现出对伟大经典的怀旧。马里内蒂一再表示传统和经典对青年艺术家的毒害,发出摧毁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号召,但他也提出青年艺术家可以每年一次给《蒙娜丽莎》献上一朵玫瑰。[2](P.52)同时,先锋派对新的审美规划的推动,首先是通过自我命名实施的,而这为构建新的传统和经典提供了可能性。事后看来,宣言是先锋派确立和传播新的艺术观念、培育和生产新的观众的一条重要路径。布勒东甚至拟定了一个超现实主义名单,把萨德那样的作家和但丁、莎士比亚并置,构建出新的传统和经典。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伟大经典的矛盾态度得到了从先锋到后先锋的所有实践的证明。从《L.H.O.O.Q.》(1919)到《刮了胡子的L.H.O.O.Q.》(1965),杜尚对《蒙娜丽莎》的戏仿暗示了他对这一伟大经典的怀旧。沃霍尔以复制通俗影像著名,但他的晚期画作充斥文艺复兴尤其是宗教的题材,其中包括对《最后的晚餐》中的基督头像的复制。德波尔的情境主义实践走得更远,把伟大经典作为对抗警察和军队枪炮的工具,强调这是“让艺术返归生活,重新确立其优先权”的途径,也是对梵高和高更等伟大艺术家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3](PP.161-162)在这一意义上,正是对艺术的这种执着信念,先锋派从未能摆脱经典的幽灵。先锋派及其观念的纷争表明,越是挣扎,越是深陷其中。
可以说,对先锋派的理论探讨和反思,揭示出了同样的问题。历史地说,早期的先锋派理论探讨主要是围绕形式创新进行的。自奥尔特加到阿多诺和格林伯格,艺术的自主性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把先锋派的抽象化看作是一种模仿,阿多诺认为先锋派和异化现实处于模仿关系中,但它是通过对经验的模仿,制作出绝对客观的艺术品,而这一绝对艺术品和绝对商品趋向融合,[4](PP.31-32)格林伯格则把先锋派视为是“对模仿过程的模仿”,其目的是消除传统模仿的空间幻觉,回归绘画的“平面性”。[5](P.7)无疑,他们的理论为先锋派的经典化提供了依据,但也暗示了先锋派不断走向终结的命运。后期的先锋派理论探讨主要根植于体制批判。比格尔在批判了阿多诺的审美理论后提出,先锋派是对自主艺术体制的攻击,其规划是艺术和生活的融合,但是先锋派以失败而告终,以至于各种形式风格共存于体制之中,呈现出所谓的后先锋状况。[6](P.57)丹托在批评了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观念之后提出了艺术界理论,认为从杜尚到沃霍尔,正是理论的作用,他们的现成品才被界定为艺术,但艺术由此陷入终结状态。[7](P.34)从以上分析看,除了历史的差异外,先锋派及其理论也表现出地理的差异,在从欧洲到美国的旅行中就经历了去政治化的过程。
二
先锋派的终结不仅源于其固有的从众倾向,也来自现代技术、资本、文化的扩张的致命影响。这已经成为许多理论家的共识。威廉斯甚至认为,正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实现了先锋派的艺术和生活融合规划,先锋派也由此成为了历史。[8](P.29)德波尔也发现,对于先锋派,战后的资本主义改变了态度,从反对转向利用,把先锋派的创新变成无意义的消费时尚。[9](P.40)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功能主义建筑被同质化为“国际风格”推向全球,成为情境国际试图颠覆的景观社会的构成部分。以下将分别对此作简要的描述和分析。
首先是现代技术的影响
本雅明早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出,现代机械复制技术史无前例地改变了艺术的生产、传播、接受。从生产的角度看,现代技术摧毁了艺术的光晕,制作出去光晕的作品,艺术由此从仪式价值转向展示价值。从传播的角度看,现代技术摧毁了原作的独一无二性,将艺术品置于流动的时空里。从接受的角度看,现代技术把观众和艺术品置于集体的偶遇中。总之,现代技术带来了艺术的革命。但是,诚如胡伊森所言,“复制技术在今天的艺术中的作用已不同于20年代的作用。那时,复制技术对资产阶级文化传统具有质疑的功能,而今天它们肯定了技术进步的神话。”[10](P.155)这就是说,复制技术的发展本身没有了震惊美学和政治的潜能,而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趋向一致。胡伊森继而指出,波普艺术在复制技术的利用上尽管存在某种革命性,沃霍尔的技术创新——摄影和丝绸屏幕的合成利用——不仅促使艺术的无限传播成为可能,同时也摧毁了艺术品的韵味,但是波普艺术的技术创新并没有与社会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因此脱离了政治语境的艺术被博物馆和大众媒体所收编,以艺术家的韵味化即明星化而告终。[10](PP.155-156)即便是情境国际运动,虽然试图恢复早期先锋派的政治锋芒,但当艺术家们宣布拒绝工作、立足情境建构时,他们的情境主义生活依赖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因为只有在现代技术取代劳动时,他们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理想生活。
其次是体制市场的影响
20世纪后期的艺术家们对待市场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早期先锋派,后者通过反叛市场而为市场所接受,今天的艺术家不再费这个周折,对市场持完全接受的态度。克莱恩的研究表明,政府和企业对艺术市场的介入导致艺术体制的官僚化和市场化,先锋派所依赖的公共领域消失,文化产业处于支配地位,而且由于传播媒介的发展,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完全依赖这一传播系统。同时,艺术家数量的激增及其对市场的依赖导致他们对市场压力的服从,丧失了原有的反叛姿态和革新精神,多数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另外,由于市场和商品的作用,个体都被整合成只有虚假自主个性的消费者,观众完全受到市场的左右,判断艺术的标准不再是审美的了,而是市场价格决定一切。毋庸置疑,先锋派生成和发展的传统社会基础全面崩溃。今天,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和北京的798都成为了时尚商业区。
再次是大众文化的扩张
尽管后现代艺术实践对意义进行了更为激进的消解,但是震惊效果由于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扩张而日渐式微。胡伊森便持有这样的看法,认为在大众文化日益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艺术要保持其震惊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早期先锋派面对的文化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后现代主义所面对的是技术和经济方面得到尽情发展的媒体文化,这一文化掌握了融合、传播和推销最激进挑战的艺术。这个因素结合观众变化了的构成,说明了以下事实:较之20世纪初,要保持新艺术的震惊效果更困难,也许已经不可能。”[10](P.168)根据比格尔的看法,震惊本身也有自身的问题。一个问题是,震惊总是趋向于“无特殊的效果”,因为即便震惊打破了审美的固有性,它也不能保证接受者可以朝着既定的方向发生行为变化,相反,震惊常常生产出意料外的结果:对现存态度的强化。另一个问题是,震惊效果无法永远维持下去,它由于不断的重复而成为“期待中的”,或由于“体制化”而成为可“消费的”,从而丧失其震惊的效果。[11](P.80)贝尔也提出,由于不断的重复,震惊最终变成了大众消费的新奇时尚。[12](P.36)的确,由于大众文化的同化和收编,震惊和新奇都进入了消费市场,成为不择不扣的消费品。
三
如何摆脱这一文化困境?当代艺术如何能够承担起社会批判功能?先锋派作为艺术和政治的连接形式,其遗产值得艺术家和理论家们的重视。为此,有必要重估先锋派经典模型,重写先锋派的历史,以构建出新的先锋派谱系学。
在这一点上,女性主义运动和批评走在了探索的前沿。它不仅开启了对女性艺术家的个案研究,而且从性别批判的角度对经典模型加以抨击,对经典的历史加以重写。根据苏珊·苏莱曼的看法,这是因为女性艺术家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既远离艺术圣坛又远离市场,因而在当前发起对先锋派或现代主义的批判具有一种先锋性。[13](P.14)琳达·哈奇恩则提出,女性主义倾向于社会和政治变化,力图保持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距离,“使用后现代戏仿模式,同时确立和颠覆惯例,例如目光的男性特征,妇女的表征便可被非符号化”[14](P.151)。这就是说,女性主义对于恢复另类文化形式的政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原因在于女性艺术家在她们的艺术和批评中力图恢复封存已久的女性历史,在审美生产中对以性别为基础的主体性形式进行探索,对标准的先锋派或现代主义经典的界限加以拒绝。克莱格·奥温斯甚至认为,女性的文学、艺术和批评是后现代文化的重要资源,是衡量这一文化是否具有活力的标准。[15](P.84)简言之,女性主义从性别批判的角度为当代艺术和文化提供了新的政治维度。
另外,后殖民批评对欧洲中心论的知识生产发起了挑战,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遗产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文化表征形式及其所展示的文化身份、民族认同等问题。这其中,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尤其值得重视。他对“东方主义”这一艺术史术语的批评探讨揭示,东方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把非西方文化的同质化,生产出“东方”这个对立于西方的他者文化概念,且在文化表征中常常把非欧洲世界表征为落后的、非理性的、野蛮的,把欧洲表征为进步的、理性的、文明的。[16](PP.3-4)这一批评不仅为反思先锋派及其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而且为重新发明新的文化表征形式提供了参照。
最后,生态环境运动和批评也不失时机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从自然的角度对技术支配自然和社会的启蒙思想发起了挑战,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进行了广泛的批判。这一生态环境批评不仅出现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而且还出现在文学艺术实践和批评中。胡伊森指出:“正是这种生态感性的出现,现代主义的某些形式和技术现代化的联系受到了审视和批评。”[1](P.220)在某种意义上,生态环境运动扩展了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所发起的对启蒙现代性的批评,后者主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文化产业进行批判,而生态环境批评则是对人类中心论、唯发展论、科学决定论的激进批评,提出了生态伦理和正义思想、生态生活观和责任观,等等,召唤人类和自然之关系的整体重构。
总而言之,20世纪70和80年代出现了对边缘和他者文化的关注,不仅批判先锋派或现代主义艺术,而且对大众文化同样加以批评,提出了阶级、性别、种族和生态环境等问题。这些运动和批评都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即它们是通过集体反叛而构成的运动和批评,因而特别关注共同体的“表征”问题,倾向于后结构主义的解构策略,力图挑战主流文化的霸权话语。我们认为,这些激进的文化运动和批评具有相当的先锋性,尽管它们不同于早期先锋派和波普艺术,也不再关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而是强调“表征的政治”,一种以“他者性”和“差异性”为基础的微观文化表征。如果说早期先锋派试图以艺术之名颠覆传统和否定现实,那么这些文化先锋派立足于文化政治批判,倾向于重新建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在消费主义和文化政治之间制造出对立紧张。用胡伊森的话来说:“关键不是消除政治和美学、历史和文本、政治介入和艺术天职的紧张,而是要强化紧张,重新发现紧张,恢复艺术和批评中的紧张。”[17](P.221)可以说,对先锋派的持续理论反思,不仅使得我们对先锋派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立体化,而且也使得我们可以借助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来审视其经典化的脉络。
[1]Antoine Compagnon.TheFiveParadoxesofModernity[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2]Filippo T. Marinetti.TheFoundingandManifestoofFuturism[M]. in Lawrence Rainey, ed., Futurism: An Antholog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Guy Debord.TheSituationistsandtheNewFormsofActioninArtandPolitics[M]. in Thomas McDonough, ed., Guy Debord and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Cambridge: MIT, 2004.
[4]T .W. Adorno.AestheticTheory[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5]Clement Greenberg.Avant-gardeandKitsch[M]. in Art and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6]Peter Bürger.TheoryoftheAvant-Gard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7]Arthur Danto.TheArtword[A]. in Carolyn Korsmeyer, ed., Aesthetics:TheBigQuestions[M]. Oxford: Blackwell, 1998.
[8][英]雷蒙德·威廉斯. 现代主义的政治[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Guy Debord.ReportontheConstructionofSituationsandontheTermsofOrganizationandActionoftheInternationalSituationistTendency[M]. in Thomas McDonough, ed., Guy Debord and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Cambridge: MIT, 2004.
[10]Andreas Huyssen.AftertheGreatDivide[M]. London: Macmillan, 1988.
[11]Peter Bürger.TheoryoftheAvant-Gard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1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3]Susan Rubin Suleiman.SubversiveIntent:Gender,PoliticsandAvant-Gard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Linda Hutcheon.ThePoliticsofPostmodernism[M]. London: Routledge, 1989.
[15]Craig Owens.TheDiscourseofOthers[M]. in The Anti-Aesthetic, ed. Hal Foster, Port Townsend: Bay Press, 1985.
[16][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7]Andreas Huyssen.AftertheGreatDivide[M]. London: Macmillan, 1988.
(责任编辑 南 山)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视觉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2JZD019),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德波尔与情境主义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1WWB007)。
2013-12-10
周 韵,女,江苏溧阳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I01
A
1671-1696(2014)01-0109-04
主持人语:经典(canon)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已在不同学科领域得到广泛的探讨。近年来,在艺术学学科领域,针对这一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也日益增多。这其中,立足于文化建构主义立场,对艺术的经典化过程所进行的系统研究尤其值得关注。本次笔谈的三篇文章即以此为论题进行了彼此呼应的深入讨论:《理论纷争与经典的变迁:从先锋到后先锋》一文对先锋派理论所做的梳理,为我们审视先锋派在现当代艺术史中的位置提供了一个特有的理论视角;《作为“历史流传物”的艺术经典:阐释及其有效性》从作品的阐释问题入手,揭示出阐释活动在艺术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艺术史书写与经典建构——以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为例》则围绕艺术史书写的自觉意识,特别强调了艺术家参与经典建构的主体性地位及其关键所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三篇文章分别是从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维度出发,对艺术经典建构问题进行了既不乏理论深度、又极具对话意识的深入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代表了当前艺术学理论的三种学科形态关于经典问题的不同考察路径。因此,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来说,本组笔谈不仅在学理层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学科层面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