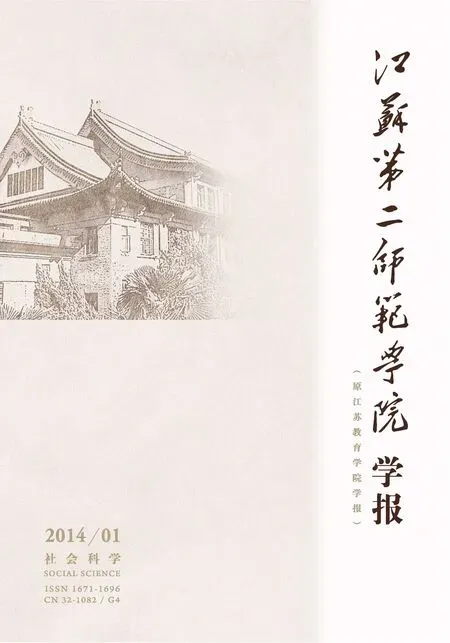艺术史书写与经典建构——以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为例*
2014-04-17李健
李 健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江苏南京 210093)
中国画作为特定的艺术史范畴,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画家及其作品所构成的经典序列,则是我们把握其演进脉络的重要历史线索。可以说,艺术史书写在客观上是艺术经典得以最终形成的关键环节之一。所谓艺术的经典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艺术史的书写工作最终得以实现。如果说传统中国画的经典序列已经在反复的艺术史书写过程中完全确立起来,那么基于社会转型语境对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状况予以剖析,将尤其有助于我们思考经典建构中的一些微观问题。对此,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对于经典建构过程的具体影响,其实是可以通过其艺术史书写的自觉意识被我们把握的。具体来看,近百年来,中国画一直在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中艰难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期间,不断有艺术家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张力中探寻中国画的现代表达形态。其中,以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等人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已经为我们开拓出现代中国画发展的多种可能路径。但与现代文学发展轨迹不同的是,中国画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并没有像前者一样在艺术语言上遭到釜底抽薪式的革命。事实上,即使是进入新世纪,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中国画创作仍然受大量艺术家以及欣赏者追捧。但是如果从艺术史书写的角度看,这种状况无法令人满意。近年来中国画的热度有所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种反思性的立场上实现的。唯其如此,中国画才可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进程中扮演更无可替代的独特角色,真正形成属于当代的经典序列,也才可更自觉地立足于现代语境探寻自己的未来发展之路。具体到艺术家对于艺术史书写的自觉意识,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探讨。
一
如上所述,近年来艺术界对于中国画的关注程度不断得到提升。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具有自觉历史反思意识的有影响的中国画画展日益增多。这里仅以自2012年开始启动的“重塑东方美”系列画展活动为例,无论以“水墨的现代诠释”为主题的首展画展,还是以“现代生活·水墨心印”为主题的第二届画展,无不体现出主办方参与艺术史书写的勃勃雄心。正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先生在首届画展前言所指出的那样,所谓“东方”不仅主要是指称中国,而且既针对西方,针对其持续太久的话语霸权,针对其依然事实存在的对世界的主导性;亦同时针对中国,针对中国的生存尊严,针对中国的文化尊严,亦针对中国对世界的责任和关怀。所谓“重塑”意在构建中国画的“当代性”,并以其“当代性”实现历史的延续。首届画展以“水墨的现代诠释”为题,一方面强调“水墨”仍是绘画的主要形式,其对历史的过去与未来都有更多的承担;另一方面亦关注“水墨”因“重塑”而必将遭际的困惑、思考和希望。这一自觉意识,不仅仅是一次画展及其相关系列活动的逻辑起点,更可视为艺术家参与艺术经典建构过程的重要前提。
我们知道,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节点上都有一些重要的变化。根据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诊断,西方社会现代转型集中体现在价值领域的分化上。艺术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一个完全依据自身游戏规则行事的独立价值领域。从学科的角度来说,艺术史书写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成为我们理解艺术世界的重要学术行为之一。而艺术史的书写作为一个由身处艺术世界中所有成员共同参与的活动,并不是由艺术史家独立完成的。这其中,艺术家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离开艺术家的存在,艺术史,尤其是现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艺术家而言,价值领域分化的直接后果是独立身份和自由职业的确立。艺术家随之对自身的职业定位也就有了更强烈的自觉意识。这一论断,在中国画的实践语境中同样是有效的。传统社会中从事中国画创作的文人或士的形象,在现代社会被角色相对单一的画家形象所取代。这意味着现代画家基本上只通过绘画即可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以此成为艺术史的主要书写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只能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参与艺术史的书写。因为一个由“艺术家(亦即画家、作家、作曲家之类)、报纸记者、各种刊物上的批评家、艺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等等”构成中坚力量的艺术世界,需要所有成员的共同参与,才能不停运转并持续生存下去。[1](P.111)正因为如此,艺术家在事实上始终都是艺术史书写的直接参与者。而艺术家有没有一种参与艺术史书写的自觉意识,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衡量一个艺术家的职业精神和艺术追求的高下。
之所以能如此理解,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在于:这种自觉意识,绝不简单是说一位画家首先要去考虑自己需要、应该或希望在艺术史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更基础性的问题是,艺术家应该考虑:我的绘画能不能带来真正区别于包括前人在内的其他画家的有价值的东西——当然更不是琢磨如何用最经济实惠的方式,让我的画每平尺卖更高的价格。综观绘画史的演进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随时代变迁而致绘画语言形式革新的逻辑线索是清晰可辨的。一方面,艺术家的艺术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种革新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他们的创作活动又是我们把握这一逻辑线索的基本途径。越是处于新旧激烈交锋的社会转型期,艺术家的艺术史价值就越是体现在这一点上。西方绘画史如此,中国绘画史亦如此。现代以降,关于中国画革新问题的争论几乎从来都没有停歇过。就艺术史的演进逻辑而言,在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传统中国画进行必要的革新,无疑是其得以进入艺术史视野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就现实来看,虽则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等诸前辈艺术家已经极大地开拓了中国画的表现形态,然其现代转型工作恐怕仍在继续当中。自陈独秀在《美术革命——答吕澂》中倡导革传统中国画的命以来[2],中国画仍始终在传统与现实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寻求平衡点,并不断展现其顽强的生命力。需要说明的是,在该文刊发之前,艺术实践领域的革新运动业已展开。不过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于其核心阵地上发布的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宣言式文本,它的意义远超出艺术活动本身,因此极具艺术史书写的标本意味。但作为艺术史的书写对象,身处中国现当代艺术之中的中国画又不得不一再面临被边缘化的境地。这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画经漫长历史积淀留存下来的遗产本身所具有的极大价值;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仍在路上,任重道远。至少,从更为宏阔的艺术史视野出发,诸如中国画的价值取向、语言建构及其与当下现实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仍有待于我们通过作品来回答。
二
以上述立论为前提,我们不难理解,要判断一个艺术家是否具有艺术史书写的自觉意识,就必须审视其艺术创作能否展现出一种区别于他人的存在价值。就艺术史发展的宏观脉络而言,这种价值又可以被指称为一种具有增值效应的文化价值。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以“文化增值”为尺度,对应的则是“技术性复制”。因此,这一尺度为我们书写艺术史提供了一个从“技术性复制到文化增值”的考察路径,再以此审视艺术家及其作品,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其在艺术史书写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这里所谓技术复制,主要不是在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的意义上使用的。它不特别指向因技术手段进步而遭际的艺术生产形式的变化,而指涉更宽泛意义上的绘画技巧、技能。以中国画来说,所谓技术性复制,主要是指在技术层面可以通过学习熟练掌握的各种绘画技巧、技能乃至情感、观念表达的常规化图式等。
毫无疑问,中国画经过那么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它走入现代之际,早已形成一套完整的创作程式。所谓“墨守成规”,大抵如此。任何事情,都是守成易,变更难。单就从事中国画创作的画家而言,因循守旧未必日子过得不滋润。甚至因为有了那么一套先人留下的遗产——不仅是艺术创作方面的遗产,也包括艺术接受方面的遗产,总可以把画卖出个好价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就是所谓“惯习”的力量。它不仅仅是艺术家的问题,也涉及欣赏者、批评家等。可以说,如果艺术家只是将绘画作为一种完全私人化的兴趣、一种表明个体身份的职业,那么这样一个积淀如此深厚的传统,已经足够玩味,足够让一个画家活得有滋有味了。当然他也就不会再难为自己,去琢磨什么传统中国画的现代转型问题。但对于有参与艺术史书写意识的艺术家来说,思考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技术复制”式的绘画创作,是很难进入艺术史视野的。但凡进入艺术史视野的,无疑都是那些具有文化增值意味的艺术家艺术品。韦伯有言,“一件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永远不会被超越,永远不会过时;每个人对它的意义评价不一,但谁也不能说,一件艺术性完美的作品被另一件同样‘完美’的作品超越了”[3](P.82)。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也指出艺术史与科学史具有非常不同的建构逻辑,因为前者建立在它的无穷可能的丰富性之中,构成艺术史的所有内容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这一论断是有前提的,即能够进入艺术史的艺术品无疑都具有其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独特性。简单点说,它必须具有某种文化维度的增值效应。所谓永远不会被超越,永远不会过时,就在于它的存在始终可以为艺术史增添价值。
如果中国画的演进史还不够令我们警醒,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文学史,作为一个参照。中国文学史一向有“体以代变”“一代之文学”的说法。综观中国文学史,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及至现代,尽管传统的诗词歌赋仍然有众多的爱好者,仍然有人从事诗词创作,但现当代文学史几乎已没有传统诗词的书写空间了。因为任你如何创作,也已很难摆脱技术复制式的创作窠臼,与文学史的“文化增值”效应基本无涉。中国画或许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在当前中国艺术界大致三足鼎立的态势下,“当代艺术”作为一个专属名词,几乎不关涉中国水墨。从艺术史书写的角度而言,这至少应是我们自觉反思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要反思这样一个相对宏大的艺术史问题,还需要从更加微观的现当代画家画作入手,思考我们时代的中国画究竟具有多大的“文化增值”效应,而不只是因袭前人的“技术性复制”的产物。
三
近年来,中国画持续受到关注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一批中国画画家开始自觉思考如何通过作品的创新来突破传统中国画的束缚,以拓展艺术表达的空间。仍以“重塑东方美”画展活动为例,无论首届画展的七位参展画家,还是第二届画展的15位画家,希望突破传统中国画创作程式的意图无疑是清晰可辨的。正如画展策展人兼参展画家、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林逸鹏教授在首届画展时所强调的那样:“水墨画的创作客观上进入转型期,但如果这个转型无限期拖延下去,就是艺术家的责任了。”这种责任感可以说是艺术史书写自觉意识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若从“文化增值”的角度再做进一步微观考察的话,这些作品带给我们的思考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视觉体验可以概括为:富于“韵味”的“陌生化”体验。
我们知道,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区分了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的根本不同。其中前者富于“韵味”,具有一种膜拜价值;后者带给人一种“震惊”体验,具有的只是一种展示价值。[4](PP.231-264)宽泛地说,传统水墨画与现代水墨画或可作此区分。但就个人体验来说,问题又并不如此简单。从观感来说,现代水墨画的现代意味,与本雅明以现代主义尤其是达达派延展而来的“震惊”体验,未必完全接洽。若说“震惊”,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早已一次次挑战我们视觉体验的极限。这种不同意味的现代体验,或许恰恰是把握“水墨的现代诠释”的一条有益线索。
具体来说,纵观两次画展的参展作品,给观者的一个突出印象便是既不乏“水墨”的传统基因所带来的“韵味”,又由于对“水墨”的现代挪用而造成特定的“陌生化”效应。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特殊的视觉体验,关键性的因素恐怕还是参展画家在其创作过程中,将自己的现代经验“融入”水墨世界的自觉意识。这种现代经验里面,既包含他们面对全球语境所吸纳的多元呈现的绘画表现方式,更有画家身处当下而获得的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生存体验。所谓“韵味”,在于作品并没有彻底遗弃传统中国画的精神内核以及表现形态。换言之,中国画的创新不是另起炉灶重新开张,重塑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基础之上。而所谓“陌生化”,则主要指涉画家通过对“水墨”这一传统绘画语言形式进行自觉改造之后必然带来的结果。“陌生化”作为文艺理论领域的一个专有术语,与“自动化”相对应。后者关乎“惯习”,意指我们的语言如果处于习惯成自然的状态之下,就会成为缺乏原创性和新鲜度的自动化语言;行为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则会变成自动化行为。如此,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将成为一个自动化环境中的无意识活动。“陌生化”正好与此相反,它以“新奇”体验为诉求,强调对自动化语言及行为的反拨。但其对“新奇”的追求,意不在新奇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手段,使人得以在社会生活的麻木状态中警醒起来、亢奋起来。面对仍习惯于传统中国画创作程式、批评模式、接受方式的艺术家、批评家以及欣赏者,这种“新奇”感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既是一种感官层面的“唤醒”,更是对艺术史书写自觉意识的一种“召唤”。[5](PP.1-10)
不失水墨立身于传统的特有“韵味”,又借助现代语汇给人以警醒意味的“陌生化”体验,这既是对真正面向当代社会生活进行中国画创作的画家作品的总体性把握,也是立于艺术史书写来思考当代中国画的价值取向、语言建构以及解读方式等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就经典建构而言,作品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无论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这些作品都带给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画未来走向的巨大空间。在作品背后,则隐藏着艺术家强烈的艺术史书写的自觉意识。也正是这种自觉意识,强化了艺术家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并不仅仅为艺术史的书写提供素材这么简单,他们本身就是这一书写过程的参与者,与艺术史家、批评家以及理论家共同建构起艺术史的经典序列。
[1][美]乔治·迪基.何为艺术(Ⅱ)[A].李普曼编.当代美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2]陈独秀,吕澂.美术革命——答吕澂[J].新青年,1919(1).
[3][德]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A].韩水法编.韦伯文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4][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A].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俄]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A].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