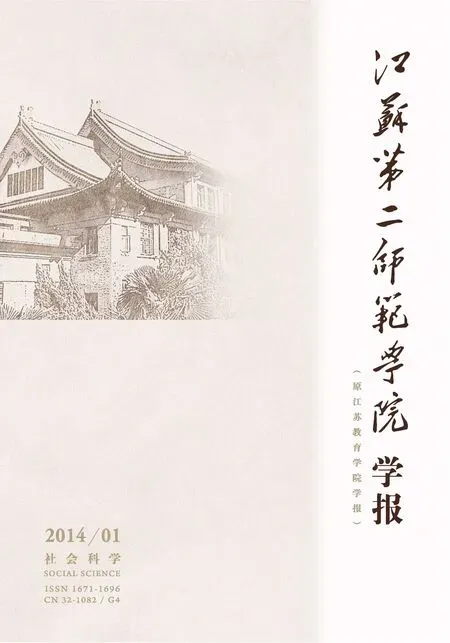作为“历史流传物”的艺术经典:阐释及其有效性*
2014-04-17翁再红
翁 再 红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13)
作为“历史流传物”的艺术经典:阐释及其有效性*
翁 再 红
(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13)
艺术作品得以流传并成为经典的过程,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其中,阐释作为一种带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文本遴选活动,既是艺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批评的基本职能所在,也是具体作品得以经典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作为“历史流传物”存在的艺术经典而言,有效的阐释意味着只有将文本与阐释主体都置于“历史意识”或“传统”之中,才能真正见出文本的历史地位以及批评家在文本经典化过程中的阐释效应。
艺术经典; 历史流传物; 阐释; 经典化
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1](P.3)。因此,人类所创造的任何文明成果,诸如文学作品,最终都必须通过传播活动才能延续。没有了传播活动,作为“历史流传物”的经典文本将失去留存下来的可能。于是“流传”作为艺术品传播的终极目的变成了经典文本重要属性之一。是什么使艺术品流传,原因当然是多样的,其中既有文本自身的深厚的审美张力,也有后世各种强大的文化权力,本文将着重探讨接收者的阐释之于艺术经典化的意义,并且试图从理论上回答阐释的有效性之于文本经典化的意义。
一
阐释(Hermeneutik,又译为解释学、诠释学)一词,来源于上帝信使的名字“Hermes”(赫尔墨斯),意指把上帝的指令翻译成凡人可以理解的话。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作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其阐释学观念也是从解释圣经的经验中发展而来的。在他看来,阐释的最终目的就是获取文本蕴涵的客观意义。为此,他把语法阐释和心理阐释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从理论上提出了“阐释的循环”观——即阐释从文本的部分开始到文本的整体,从认识整个文本意义的基础上认识部分。现代阐释学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施莱尔马赫的局限性,不仅把阐释学泛化为解释一切人文科学文本的学问,并且摆脱了阐释学仅仅作为方法论的命运。具体而言,在现代阐释学那里,阐释不再执着于文本的原义,而是借助文本进入到一个“存在”中去。因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存在”——一种独特的文化历史传统与境遇,每个人就会给文本的阐释打上自己的烙印。正如伽达默尔所言:
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和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2](PP.304-305)
这意味着,文本一旦进入历史,在历史中被传承,就必然处于一定的效果历史之中。换句话说,文本的“此时此地”性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当下”的文本,没有“过去”的文本,“理解必须被视为意义事件的一部分,正是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包括艺术陈述的意义和所有其他流传物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2](P.216)在这里,伽达默尔不仅是在说明阐释学的存在意义,同时也是在揭示这样一个真理:任何“历史流传物”正是在不断被阐释的过程中传播到今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阐释不仅仅只是对文本意义的简单追问,它还是一种带有明确价值取向的遴选活动。因为阐释者首先要遴选阐释的对象。尤其是对于艺术作品而言,阐释的对象不再只是对圣经或“六经”这样的文本,而是漫长的艺术史过程中所有历史流传的文本。正是阐释者独具慧眼的遴选活动,才使得“这一个”文本有可能脱颖而出。而历代阐释者的不断阐释,使文本的意义不断地叠加,带着先前的气息走向我们,成就了经典之为经典的命运。事实上,阐释历来就是艺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艺术批评的基本功能之一。甚至可以说,艺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同时滋生出艺术的阐释活动。比如《诗经》其实也就是文学批评家以他们当时的“存在”眼光遴选出来的。当它又被后世无数理论家不断注解,不断传承,才成为当之无愧的艺术经典的。艺术阐释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仅使文本的意义多层次地展现出来,更使艺术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及文学价值走向可能的经典之路。如巴特所言:“一部作品之不朽,并不是因为它把一种意义强加给不同的人,而是因为它向一个人暗示了不同的意义。”[3](P.101)
二
阐释打开了一扇通往经典的路,但是并非所有的阐释对文本本身都是适用的。比如歪曲的、错误的阐释,甚至脱离文本的虚夸阐释,这样无稽的阐释只能是无效的。尤其对于真正优秀的文本而言,这些阐释或许会起着阻碍或者延缓文本进入经典化进程的负作用。于是,阐释的有效性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了。那么什么才是有效的阐释?这种阐释活动的实现途径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明确什么是有效阐释的前提应当取决于我们预备阐释什么,或者说,我们认可怎样的阐释目的。这也是众多研究阐释学的学者发生分歧的症结所在。正如看似反对阐释的苏珊·桑塔格所说,“我并没有说艺术作品不可言说,不能被描述或诠释。它们可以被描述和诠释。问题是怎样来描述或诠释。”[4](P.14)一般而言,对于众多学者而言,阐释不外乎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作者意图、文本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文本的形式因素(即审美特质)以及当下存在的价值等等。以施莱尔马赫为首的传统解释学派大多都认为,阐释的有效与否就应该落实在是否与原义保持一致上。赫尔席在《阐释的有效性》一书中就认为:
阐释者的首要任务是以他自己身份重造作者的“逻辑”、作者的态度、作者的文化习俗;一句话,作者的世界。即使证实过程高度复杂与困难,最高的证实原则仍非常简单——重建叙述主体的想象。[5](P.15)
在他看来,作者意图就是有效阐释的标准。但是当我们不再以作者为中心转向读者的时候,我们分明发现了另外一种风景:文本作为一种审美客体,它同时也是一种对象化的存在。真正的审美对象,是由读者与文本共同建构的一种幻象而非实体。在此意义上而言,文本的意义绝非既定的,不变的。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恰恰揭示了审美除了“共性”(基于相对确定的文本意义),还应该有更深层的“个性”的审美感受。与以作者意图为中心的阐释模式相反的另一种极端观点则认为:“文本之外无他物”。在这里,作者独自主宰文本意义的“特权”被彻底取消了。正如福柯所言,“使得生产它(一本书)的人永远不能提出主权要求:既无权设立其发言意图,亦无权诉说其应然”[6](P.2)。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则正式宣判了作者的“死亡”。当然,这种观点并不能完全消解作者的声音。尤其对于古老的经典文本而言,正是作者赋予了文本独特的“韵味”,赋予了文本无法复制的“本真性”(本雅明语),才使阐释变得更有历史的余音,也更有文化的底蕴。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伽达默尔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总结作用,他指出了一条实现有效阐释的基本途径。如他所言,有效的阐释必须通过“历史意识”去寻找。这种“历史意识”强调:不光“历史流传物”本身是处于“历史”中的,更不要忘记阐释者自己也是处于“历史”之中的。在笔者看来,他的观点至少包含了两层积极的意义:一方面,阐释者所要阐释的文本已经不再是“原”文本了,它附加了很多前人的理解呈现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阐释者并不是一张白纸,他不仅有着对此文本及其赖以存在的传统有着先入为主的认识,还包含着个人独特的境遇。只有阐释者将两者的“历史”都理解进去,才能使阐释真正有效。无独有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也曲折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7](P.14)因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7](P.64)。事实上,无论伽达默尔所强调的“历史意识”,还是丹纳强调的“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与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强调的“传统”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对于艺术创作而言,传统是作为一种文本生产的“惯例系统”而存在的。而从阅读与阐释的角度来看,它则从另一个维度强调了一种“影响”或“关系”的存在:文本对文本的影响、文本隶属的时代对文本的影响、文本隶属的整个传统对接受者的影响以及接受者对文本的阐释所产生的后续影响等等。可以说,这样一种影响的“效应史意识”才是阐释学的真正核心,以至于当代批评家布鲁姆也把诗歌的发展史称为“影响的焦虑”史。其实对于一切文学样式来说,“影响”都是无处不在的。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对阐释的目的作一个简要的概括:对于作家而言,离开了“历史意识”,他也就不再具有隶属“体系”(艾略特语)的资格,更不用说,成为其中的经典;而对于阐释者而言,其阐释脱离了文本产生的依据——“历史意识”,那么其阐释也就不存在有效与否的说法了。
三
其次,要实现阐释的有效性,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因为无论是“历史意识”“时代情境”还是“传统”,阐释活动最终还是要由具体的人——阐释主体来承担。从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出发,所谓阐释主体,明确指向了“读者”这一群体。正如姚斯所指出的那样,艺术的生命不是来自作品自身的存在,而是来自作品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8](P.19)换句话说,最后所有的“过程性特征”——也即“影响”史,都要通过读者的阐释去获得:
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在阅读过程中,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评性的理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8](P.24)
可以说,在姚斯看来,读者在文学阐释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伊瑟尔在《阅读行为》一书中也直接宣称“本文只有当它被阅读时才能具有意义。……阅读是所有文学阐释过程中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并由此得出结论:“文学作品具有两极。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极和审美极。艺术极是作者写出来的本文,而审美极是读者对本文的实现”[9](PP.24-25)。虽然伊瑟尔所说的审美极,是读者通过“体验”的创造而非“阐释”去“接受”,但是却向我们传达出一种信息:阐释最终只能经过“读者”这一阶段才能完成。正如他所说:“是谁决定了标准的理想性、体现的客观性、或阐释的恰切性?自然是批评家。但他也是读者,他的所有判断都建立在他的阅读之上。”[9](P.29)
由此可见,一切阐释者首先应该是读者。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读者都在文本阐释的效应史中发光发热。“读者”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只要在与文本发生互为建构的审美关系的人都可以称为读者,它甚至也可以通过阶级、种族、文化层次、职业等等标准去划分。但是,可以作为文本经典化进程的历史分析依据的阐释史,则必须要有实际的印迹。比如,中国古典小说史中曾留下确凿批评文字的胡应麟、蒋大器、李贽、金圣叹等人,他们才是有效阐释所要求的读者。这也就是伊瑟尔所谓的“实际读者”——“在反应研究史中被提及”的读者,而非虚拟的“隐含读者”。基于以上对“有效阐释”的分析,笔者认为有效阐释的发出者必须是通晓文化与文本“传统”,并基于此能够具有“个人”声音的读者,而这个人只能是批评家。确切地说,“一般读者满足于也限制于准实用式的意义再现式阅读,只有批评家对文学的内在蕴意或人文意义的探究情有独钟”[10]。法国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曾经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把文学批评分为三种:
这三种批评,我将称之为有教养者的批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和艺术家的批评。有教养者的批评或自发的批评是由公众来实施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由公众中那一部分有修养的人和公众的直接代言人来实施的。专业工作者的批评是由专家来完成的,他们的职业就是看书,从这些书中总结出某种共同的理论,使所有的书,不分何时何地,建立起某种联系。艺术家的批评是由作家自己进行的批评,作家对他们的艺术进行一番思索,在车间里研究他们的产品。[11](P.11)
相形之下,专业工作者的文学批评工作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或者说,有效阐释的发出者主要是以专业批评家为核心的人群。因为这部分读者具有比自发批评家更专业的知识体系与批评视角,又有着艺术家所很难保持的客观与审慎的批评精神。确切地说,作家的批评不过是偶尔为之,多半出于爱或是出于恨,有时则是为了捍卫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而“一位专业评论家则真正投入,他要谈论很多书,不得不排出优劣顺序”,正是他们“因为对所处时代的作品的了解,亦因为对人文科学的了解,给予文学以更准确、更具技术性、更科学的描述与阐释”。[12](PP.3-6)
综上所述,有效的阐释只有把文本与个人都置于“历史意识”或“传统”之中才能真正见出文本的影响史。而有效的阐释最终又必须假借“专家”之手才能实现得更为全面和深刻。正如克莫德所言,“文本受到不断关注,特别是学者的关注是经典得以保存的最基本模式。唯有阐释才能维持一件艺术品的生命,使之代代相传”[1](P.36)。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本最终成为经典,是无法忽视专业批评家的有效工作的。而对处于不同艺术传统中的批评家而言,经典文本的阐释方式又是不尽相同的。
[1][美]威尔伯·施拉姆,[美]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英]安纳·杰斐逊,戴维·罗比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4][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美]戴维·霍伊.阐释学与文学[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6][法]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7][法]丹纳.艺术哲学[M].桂林:广西桂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9][德]沃·伊瑟尔.阅读行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10]汪正龙.论文学意义的存在方式[J].文艺理论研究,2001(6).
[11][法]阿尔贝·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2][法]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13][美]科尔巴斯.当前的经典论争[A].左东岭主编.文学前沿(第10辑)[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南 山)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艺术传播学视域中的经典建构与传承研究”(项目编号:12CA068),受2012年度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资助。
2013-12-10
翁再红,女,安徽淮北人,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J01
A
1671-1696(2014)01-01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