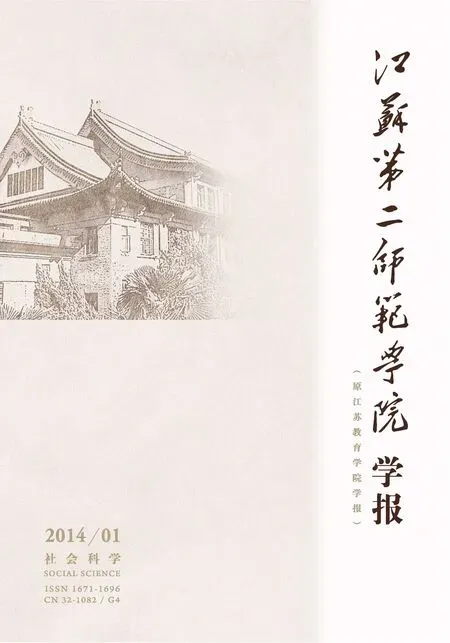浅析《无名的裘德》中女性气质的边缘化
2014-04-17曹磊
曹 磊
(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1167)
浅析《无名的裘德》中女性气质的边缘化
曹 磊
(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1167)
苏和阿拉贝拉是英国作家哈代《无名的裘德》中的两位女性。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气质往往被界定为温柔、优雅、善于抚养等角色特征,女性被看作是男性的附庸,是男性统治的对象。但这两位女性却表现得很独立,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她们身上,女性气质逐渐被边缘化,更多地表现出刚强、主动、支配性、侵略性等男性气质特点。女性气质的边缘化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也是女性追求女性自由、平等权利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无名的裘德》; 女性气质; 边缘化
“女性气质”通常用来指称对女性的形象和社会角色的建构。在父权社会里,女性气质由男人定义,为男人服务。女性气质往往被界定为温柔、优雅、善于抚养等角色特征,同时,它又被用来描述一些被视为女性有关的弱点,如柔弱、被动、情绪化等。女性气质被限定在家庭角色中,是男性统治的对象。
在《无名的裘德》中,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描述了裘德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及其短暂的人生际遇。裘德短暂的一生虽饱读诗书却求学无望,渴望爱情却婚姻失败,最终在病榻中悄然死去。如果说求学无望带给裘德的是事业发展的阻碍,那两段婚姻的失败则带给他生活的灭顶之灾,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小说中呈现的维多利亚时期,虽然是英国历史上极为繁荣的时期,科学、政治、经济都得到空前发展,但女性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女性仍旧被认为是弱势群体,附庸并顺从于男性的统治。而哈代在对两位女性阿拉贝拉和苏的创作时,颠覆了19世纪作品中女性柔弱、被动、安于家庭生活的形象,创造出两位反常规的极具鲜明个性的女性形象。
一、女性气质边缘化在苏和阿拉贝拉的具体呈现
小说中的两位女性性格迥异,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性情并不柔弱,内心里渴望主动地把握自己的生活。阿拉贝拉是裘德的妻子。她出生卑微,没有受过教育,是一个粗俗的女子,她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嫁一个可以依赖的丈夫,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当她第一次看到裘德时,就认定裘德是她理想的丈夫。她故意使计接近裘德,并不顾世俗的禁忌,利用自己的年轻美貌和裘德的单纯,诱惑裘德做出越礼之事。婚后,她发现裘德无法让她过上安逸的生活,立刻选择和裘德分道扬镳。当第二任老公去世之后,她又设计回到裘德身边,想要靠裘德过一种表面上“体面”的生活。阿拉贝拉的出现,改变了裘德的生活轨迹。原本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牧师的裘德,没能抵挡住阿拉贝拉的诱惑,不得不被迫成家。可以说,在这段结婚、离婚、复婚的闹剧中,阿拉贝拉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顺从”和“被动”,而是展现出“主动”和“权威”这种在男权社会中被定义为专属男性的特征。虽然她的行径有些令人不齿,但是她不受社会规则的束缚,一直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则生活,她想要通过主宰自己的身体掌控命运,表现出女性的觉醒意识。
相对于粗鄙自私的阿拉贝拉来说,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她谈吐不俗,气质高雅。苏是裘德的表妹,两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切感和依恋感。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渴望拥有男性所独有的学术自由。但不盲从所谓的权威观念,对世界、社会和宗教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信仰。她对裘德说:“我不愿干扰你的信仰。不过我一直渴望寻觅到一个知音,鼓励他追求高尚的目标。我见到你时,觉得你也想成为我的同志,然而你对那么多的传统观念都笃信无疑,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苏就读的梅尔切斯特培训学校,俨然一个门规森严的女修道院。对于她这样“一个不习惯受约束的年轻人来说,她感到满腹怨愤”。她用自己的方式反抗这种让人窒息的压迫:在一次和裘德外出晚归而受到的惩罚中,她越过“几乎齐肩深的河水”,逃出了这个桎梏她身心的场所。她的这种叛逆和反宗教的思想,在随后的共同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裘德对于基督教的认识,让他放弃了成为一名牧师的理想。
对于婚姻,苏的态度既保守又前卫。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尤其是已婚女子,被认为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是被排除在男权中心之外的“他者”,只能充当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和符号。而苏却表现得比较理性,不想沦为这种婚姻的牺牲品。她也曾犹豫过。为了获得教师资格,她以婚姻为筹码,接受了弗洛特孙先生的资助。被梅尔切斯特培训学校开除后,她处境艰难,迫不得已嫁给弗洛特孙。在和裘德的通信中,她内心挣扎地写道:“新郎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中我,而我却不是按我的意愿选择他。别人把我送给他,就像赠送母驴、母羊或旁的什么家畜。”婚后,她一直拒绝丈夫占有她的身体。相对于肉体的欲望,她更崇尚与爱人之间精神上的交流和碰撞。在和弗洛特孙离婚之后,苏勇敢地和裘德走在了一起,但她还是拒绝和心爱的裘德过真正的婚姻生活,直到阿拉贝拉的再次出现和舆论的压迫,才让她鼓起再次走进婚姻的念头。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她还是选择了放弃。她从心底发出叛逆的呐喊:“喜欢结婚的女人没有你估计的那么多。他们结婚,只是因为婚姻可以带来体面的生活,有时可以提供社交上的便利,而这种体面的生活和社交上的便利我都非常愿意放弃。”她“已经醒悟到了结婚的可怕性和严重性,如果执迷不悟再结一次婚,实在是不道德的行为”。在对待婚姻问题上,苏和阿拉贝拉的表现完全不同。阿拉贝拉是通过自己的身体结识男人,占有男人,通过对男人的占有达到自己个人的目的;而苏却企图通过抛开身体,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来抓住男人对自己的忠诚,实现自己心灵和精神上的圆满。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悦自己而非社会。尽管对待婚姻的方式和态度不同,有时似乎显得不合情理,两位女性却都将婚姻的选择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每段感情中,她们都处于主动地位,以自我的需求为中心,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生活,而不是一味地把服侍和取悦丈夫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这种对女性权利的追求无疑是对女性卑顺和附庸命运的强烈挑战。
二、女性气质边缘化与女性意识的觉醒
法国女性主义者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也认为:“性别压迫并不一定是生物的,还可能是文化的——生物性的男人受统治的影响根本和女人一样,但压迫她们的过程包括首先要她们降为‘低价值’的弱势阶层,即女性阶层。显然,女性特有的生理特点并不能使之成为女性是男性附庸的借口。在创世纪的初期,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的生存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行为独立于这个世界。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不同,男性逐渐掌控了社会权利,使女性陷于被动而附庸的处境。女性被迫与男人绑定在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中:“他”是唯一,而“她”就是他者。
但是,小说中的阿拉贝拉和苏却不甘于做男性生活中的“他者”。阿拉贝拉仗着自己的身体优势,她玩弄男性于股掌之间;她讲究实际,甚至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她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小“时光老人”的生死不闻不问。这完全不符合19世纪对“淑女”形象的定义:纤弱、爱空想、性被动、纯洁、顺从,是家中的天使。虽然身为女性,但在阿拉贝拉身上,女性气质却逐渐被边缘化,更多地表现出男性气质。
苏身体纤弱,气质高雅,充满母爱,表面上比较符合父权社会所规训的女性气质特征,但内心里,她所表现出的男性气质一点不亚于阿拉贝拉。她的思想和见解都超越时代的局限,处于时代的前沿。她勇敢地挑战宗教礼仪,敢于表达自己不同的见解;在她与追求者、她与丈夫弗洛特孙、她与至爱裘德的三段感情纠葛中,她始终掌控着主动权,她对基督教所崇尚的婚姻持有一种蔑视的态度,认为“加盖了政府公章的婚约的爱情太可怕、太庸俗”,“害怕婚约里的条件会扼杀他们的爱情”,因此她拒绝成为婚姻的牺牲品。阿德尔曼说:“苏是维多利亚文学史上敢于拒绝‘牺牲品’这一命运的最成功的代表。”
在这两位女性身上所表现出的女性气质的边缘化,是女性追求自由、平等权利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实际生活和众多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往往带有一种软弱性、被动性和悲剧性色彩。在古代中国,女性一出生接受的就是“三从四德”的儒家教育,被灌输的是“男尊女卑”的等级观念,女性承担的角色只囿于家庭范围,女性由于缺乏独立能力而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女性气质是由男人定义,为男人服务的。人类的文明成了男性的文明,女性全方位地“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在西方,女性也始终被教导要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否则会成为邪恶和危险的人。男性利用自己的特权将女性排挤出政治、教育、经济等本应两性共有的领域。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女性不断接受新的思想,试图颠覆和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女性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女性开始意识到女性气质不是由生理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女性逐渐走出家庭,摆脱父权制对女性气质形象的规训,踏入社会舞台,承担一定的社会角色。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比以往享有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女性和男性在智力上和能力上的差距也逐渐缩小。这些变化都促使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思想和行为重新进行社会和文化建构。女性利用自己特有的女性气质,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之中,女性比以往更自信,更独立,女性从事的职业范围也更为广泛,涉猎各种男性专有的职业,女性气质也因此越来越被边缘化,更多地表现出男性气质特点:刚强、主动、支配性、侵略性等。这一点在小说中的苏身上可以找到。苏虽然身体孱弱,内心却十分强大。她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她极力赞美《雅歌》中诗歌所表现出的“人与人之间欢乐的爱和自然的爱”,斥责那些企图为诗歌“涂上一层抽象的宗教色彩的”骗子行为;她对所生活的时代中女性地位低下的现实非常不满,想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虽然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使她感到痛苦、愤懑和隔绝感,但她仍然选择勇敢地面对而非逃避,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生活态度和不甘沉默的精神。这种女性气质的边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不满由男性或男性价值来支配和决定自己的命运,她们表现得越来越独立自主,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追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享有和男性相同的话语权,实现自身价值,为自己赢得尊严和平等的权利。苏也因此比同时代其他的女性更有可能成为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占据女性主义启蒙角色的前列。
三、结语
美国女作家吉尔曼在其1898年的著作《女性与经济》中曾经指出:男性以各种方式征服世界,而女性只有一种,她们的财富、权利、地位、名誉都只能通过一枚小小的戒指获取。她承认女性与男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代表优劣之分。
社会的发展依赖于所有人都充分发挥其潜能,当然也包括女性。过度强调女性气质特点,要求女性按男性所规训的女性气质生活,会将女性禁锢在家庭的牢笼中,主动内化传统的道德观和宗教教条,增加女性对新思想、新观念的负疚感,对女性的身心发展造成巨大伤害。女性,只有参与更大范围的活动,打破父权制对女性气质的界定标准,和男性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勇敢地寻求真正的自我,追求精神上的平等和独立,才能避免成为父权意识的附庸者和牺牲品,才能认识到自己生活的价值和重要意义。女性从来都是独立的个体。
(责任编辑 南 山)
2013-11-12
曹 磊,女,山东德州人,南京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
I106.4
A
1671-1696(2014)01-01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