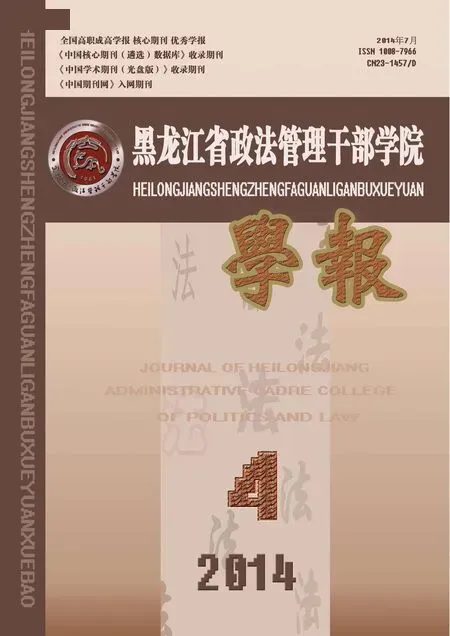民事二审新证据的界定与适用
2014-04-07汪文雨
方 俊,汪文雨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民事二审新证据的界定与适用
方 俊,汪文雨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有“新证据”是二审开庭审理的法定事由之一,但新法对二审新证据的规定阙如,导致二审法院对新证据如何界定与适用存在疑惑,现有司法解释也未能较好地解决此问题。民事二审的特殊功能决定了新证据仅应被有限引入,且其适用须遵循实体与程序的双重限制,以平衡实体公正、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
民事诉讼;新证据;程序正义;程序效益
新《民事诉讼法》以“新证据”强化二审程序的开庭审理,忽视了我国二审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与程序投机的现状,对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产生了一定冲击①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会以所谓的“新证据”提起上诉。而对我国二审法院来说,案多人少矛盾与法庭及书记员配备不足已十分突出,如果多数二审案件均以普通程序开庭审理,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对新证据进行理性界定与限制适用必然会减损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由于二审新证据本身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有必要从衡平实体公正、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紧锣密鼓地制定关于适用新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以下简称新民诉法司法解释),而涉及新证据的解释必是其中的重点与难点。因此,结合具体案例与证据规则对二审新证据的界定与适用进行探究适逢其时。
一、二审新证据之案例观察
上诉人琼海东展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展公司)因与上诉人广州市富航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航公司)、被上诉人许建明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口海事法院(2013)琼海法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提起上诉。二审中,富航公司向海南高院提交了其与贯隆公司(案外人)第一次运费支付清单卡号《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历史明细查询记录》和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黄埔支行开户名为许建明的《银行卡异地交易业务错账查询复查通知书》,结合与贯隆公司的运输合同,欲证明符兰英系代表贯隆公司支付运费。东展公司认为该证据已经超出了法定的举证期间,不应作为新证据采信,在证据内容上,该证据确系符兰英替贯隆公司付款,但该付款凭证是另一个航次的付款凭证,与本案所涉合同无关联。海南高院认为,该组证据属于《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1条规定的“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应认定为新证据②案例来源: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琼民三终字第99号判决书,http://www.pkulaw.cn,下载日期:2013年12月11日。案情及判决结果详见判决书。。
本案中新证据的界定与适用上存在的问题:(1)对富航公司提出的证据是否属于因客观原因而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没有进行严格审查与具体释明;(2)法院在认定该证据为新证据之前未组织独立的抗辩程序,使东展公司的异议权未得到充分行使;(3)引入该证据作为新证据对案件结果未产生重大影响,维持原判易引发富航公司对实体公正、东展公司对程序正义的质疑。考察司法实践中二审新证据的运作现状,我们会发现二审法院对新证据的界定与适用在不同程度上减损了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随着对程序独立价值的研究不断深入,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愈来愈被肯定与追求。为寻求实体公正、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的平衡与契合,对二审新证据进行理性界定与限制适用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二、二审新证据之立法解读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触及这一核心的改革立即就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1]。鉴于此,我国历次的民事诉讼法修订对二审新证据的规定都持回避态度,似乎是审慎而为,其实是无奈之举。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引入举证时限制度,确立了严格的“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并对二审新证据作出了粗略规定。《民事证据规定》第41条对二审新证据的解释:“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前述规定将二审新证据界定为因客观原因产生的新证据。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适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期限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举证期限通知》),以缓和举证时限制度与新证据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冲突。《举证期限通知》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新的证据’,应当依照《民事证据规定》第41条至第44条的规定,结合以下因素综合认定:(1)证据是否在举证期限或者《民事证据规定》第41条、第44条规定的其他期限内已经客观存在;(2)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期限内提供,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前述规定将二审新证据扩大解释为因时间原因产生的新证据和因主观原因产生的新证据。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对二审新证据的规定极其简单,仅第169条涉及。至于何谓二审新证据,民事诉讼法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长期以来,在“客观真实”的司法理念下,“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之流弊对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的实现产生了阻隔,二审程序尤为如此①参见李浩:《民事判决中的证据失权:案例与分析》,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
分析关于二审新证据的规定,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新证据的界定与运用偏向“实体公正”②我国民事诉讼法学者齐树洁教授曾精辟地论述“在经济发达、律师资源丰富的城市,二审新证据的界定与适用偏向‘程序’,相反,在农村、山区则偏向‘实体’”,齐教授的论点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司法实践中二审新证据认定存在的差异,值得思考与借鉴。但在“客观真实”的司法理念下,二审新证据的界定与适用偏向“实体”的总体现状是毋庸置疑的,只是经济发达、律师资源丰富的城市相较于在农村、山区而言偏向“程序”的可能性更大而已。,忽视了二审的程序价值,有动摇举证时限制度之虞;其二,认定多以时间为准,未区分“新证据”与“一般证据”;其三,新证据的认定程序与当事人关于新证据的异议程序的缺损。
三、二审新证据之理性界定
新证据的范围若太宽,诉讼通过裁判定分止争的任务就无法实现;若太窄,裁判的公正性就会动摇,严重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从司法实践与证据规则对二审新证据界定存在的问题出发,基于实体公正、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之权衡,应对二审新证据进行理性界定:
(一)突出新证据的“新”③本部分主要参见李喜莲、彭朝霞:《民事诉讼法中“新证据”的理解与适用》,载《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论文集(上册)》,第471页;李浩:《关注民事再审事由中的新证据》,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月1日第5版;郭接运《我国民事诉讼“新证据范围”研究》,郑州:河南大学,2010年第6-9页。
新证据最显著的特征是“新”,是既未经证据开示,也未经当事人质证,又未经法庭认证的事实材料或证据材料[3]。二审新证据应是当事人在一审中没有提出的证据,但当事人在一审中没有提出的未必构成二审新证据。实践中,应当从客观层面突出二审新证据“新”,包括“新产生的证据”、“新发现的证据”与“延时证据”三类。具体情形为:(1)一审庭审结束后至二审开庭前产生的证据、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产生并为当事人所发现但被一审法院错误排除在一审新证据之外的证据;(2)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就已经存在,但当时未能发现,等到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至二审开庭前才发现的证据;(3)证据形成的时间属于自诉讼开始以后至正式庭审活动由当事人提供证据之时,此类证据的特点在于其不断发展变化的延续过程中直接影响到对待证事实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最终及实质性认定,如医疗事故、人身侵权纠纷中,受害人人身受损的后遗症状在不断发生变化等情形④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原理与实务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363页;毕玉谦《试论民事诉讼上的举证时限》,载《法律适用》,2001年第1期。。
(二)限定新证据种类
二审新证据的种类是否应当与一般证据有所区别?有学者认为,书证、物证可以被认定为新证据,但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一般不得认定为新证据[4]。从证据的证明价值来界分二审新证据是可行与必要的,因为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证据主观性较强存在认定其客观性、真实性的较大困难,存在拖延诉讼程序的风险。若当事人仅以新的证人证言提起上诉,可能造成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受损的危险⑤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一中民终字第861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人郝某以3份证人证言作为新证据提起二审,二审开庭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虽然以证据种类来界定新证据确有合理性,但鉴于我国整体法治水平不高,不宜严苛限定新证据的种类。现阶段,至少应将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这两类证据排除在二审新证据之外。随着法治水平的提高,再将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这类主观性较强的证据剔除于二审新证据之外。
(三)细化认定新证据的主观因素
因主观因素产生的二审新证据,如果对主观因素不加区分,就会纵容当事人的随时举证行为,使举证时限制度形同虚设[5]。缓和因主观因素产生的二审新证据与举证时限制度之间的矛盾要求细化认定新证据的主观因素。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的主观因素可分为有过错和无过错两种情形,如果不存在过错,此类证据应当被允许进入二审程序,并且当事人无须对逾期举证承担任何不利后果;如果存在过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过错的形态。当事人的过错可细分为轻微过错、一般过错、重大过错和故意四种形态,然后根据不同的形态规定相应的制裁措施。根据《举证期限通知》第10条的规定,逾期举证的当事人如存在故意和重大过失,二审法院应当将该证据排除在新证据之外,但与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的立法精神⑥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对于逾期提交证据,法律首先给当事人一个说明理由的机会,这是法院处置此种情形的一个必经程序,也是一个符合正当程序要求的必经步骤。参见李浩:《民事证据制度的再修订》,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有所差异。故意逾期提出的新证据不是二审新证据当无疑义,争议较大的是重大过错逾期提出的证据是否属于二审新证据?笔者以为,从民事诉讼目的与司法实务现状出发,因重大过错逾期提出的证据应纳入二审新证据的范畴。现阶段对重大过错逾期提出证据予以费用制裁一般能实现程序正义。但毋庸置疑,将重大过错逾期提出证据排除在二审新证据之外是新证据制度发展的趋势。另需释说的是,如果认定逾期提出的证据会导致诉讼过分迟延,拒绝该证据进入二审亦是合理与必要的①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31条规定,因当事人过失而未于第一审提出的攻击或防御方法,当事人在第二审中不得提出。参见齐树洁编:《民事诉讼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277页。。
(四)明确新证据的提出时间
由于二审新证据大多由当事人自己持有而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调取的相对较少,当事人应当在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新证据,而不能在临近二审开庭或二审审理阶段再提出,俾第二审法院及他造当事人得于期日前尽早掌握上诉资料,进而整理争点,以充分准备言词辩论,以达到审理集中化之目标[6]313。《民事证据规定》第42条第二款关于二审新证据提出时间的规定对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的保障不够。因此,新民诉法司法解释应当对二审新证据的提出时间作出规定。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举证时限:一审程序结束,即法庭辩论结束之次日起至二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之日止,或者二审不需要开庭审理的,至人民法院指定期限的最后一日止。当事人在一审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的期限自一审程序结束之次日起至二审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止[4]。前述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的证据就不是二审新证据。需特别注意,《民事证据规定》第43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以视为新的证据”,本款是关于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不属新证据的除外情形的规定。但前述规定损害了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新民诉法司法解释不宜承袭该规定。
四、二审新证据之限制适用
理性界定二审新证据的范围后,为进一步衡平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对二审新证据的适用应附加必要限制。下文将从实体限制与程序限制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实体限制
允许新证据进入民事二审无疑是对举证时限制度的适度矫正,是一种理性地选择和有益的制度安排。但如果二审新证据的证明价值尚不足以动摇一审裁判时,引入并适用该证据可能会损害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根据新《民事诉讼法》第169条的规定,只要当事人提出新证据就应当开庭审理。该规定本意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确保上诉权的有效实现。然而,若恶意举证的当事人仅以对实体效果影响轻微的二审新证据请求开庭审理,既浪费国家司法资源,又枉增他造当事人诉讼成本,不符合程序经济的要求。近年来,我国的民事司法领域出现了局部性“诉讼爆炸”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样的,但二审新证据的随时提出与宽松适用造成的“一审空心化”与“‘无限上诉’诱导程序投机”②参见齐树洁:《民事上诉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为此,新民诉法司法解释可援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审监解释》)第10条关于再审新证据的实体重大影响之规定来限制二审新证据的适用。
(二)程序限制
1.证明与心证。为限制二审新证据的滥用,新民诉法司法解释应明确规定提出二审新证据的当事人的证明责任,由该当事人就逾期提出新证据是否基于客观原因、主观是否无过错及大小等加以证明。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未规定当事人以何种方式进行证明。不同于大陆地区,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44条之1第(四)项规定:“法院得命当事人以书状说明其逾期提出之理由”,以使当事人善尽其诉讼促进义务[6]313。因此,在二审审前程序中,当事人以书状说明逾期举证的理由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对于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是否属于新证据,法官只需具有较弱心证即可,无须完全确信,即当事人履行“疏明”义务。当事人以书状说明其逾期提出证据的理由即属“疏明”。鉴于一审已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举证机会,而且二审是建立在一审程序的基础之上,并更侧重于法律审,因而无论是法律条文规定的判断标准,还是法官的内心裁量尺度都应当较一审严格得多。
2.异议与抗辩。维护诉讼两造之武器平等原则是法治国家程序利益之重要保障。二审中,既然一方当事人可以提出新证据,也应当赋予他方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对二审新证据提出异议、进行抗辩。《民事证据规定》第45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述原则精神,可称之为新证据的抗辩规则。但《民事证据规定》未明确规定如何进行新证据的异议与抗辩。当事人提出反证或抗辩,一般是三种途径,一是对对方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进行纯粹证据上的防御,即从证据的形式、内容、证明力等方面发表意见,进行抗辩,否定该“新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二是自己提出相反的证据,达到推翻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新的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或者推翻该“新的证据”本身;第三,也可以从“新的证据”本身是否属于“新的证据”类型,是否具有“新的证据”特征上来说明该证据不构成“新的证据”从而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排除,不予适用,即不作为裁判的依据[7]。故,二审法院应及时将一方当事人提出新证据的情况告知他方当事人,因为这对其有效开展异议与抗辩尤为重要。此外,二审新证据的法庭抗辩的程序与规则有待新民诉法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3.费用制裁。当事人提交二审新证据一般会导致国家司法资源和他方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新增的支出应由提出新证据的当事人负担。《民事证据规定》第46条规定“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人民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以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规定对逾期提出新证据的主观因素未作区分。《审监解释》第39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再审人或者申请抗诉的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致使再审改判,被申请人等当事人因申请再审人或者申请抗诉的当事人的过错未能在原审程序中及时举证,请求补偿其增加的差旅、误工等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请求赔偿其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解决。”《审监解释》关于费用制裁的规定更具技术性,但《审监解释》规定费用制裁可另诉解决不符合程序效益的要求。关于二审新证据的费用制裁,由二审法院一并处理为妥,不宜规定当事人另诉处理。
4.释明责任。通过释明补充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的目的在于保护权利、实现实质正义[8]。在当事人诉讼能力差异较大的现实国情下,二审新证据之释明符合程序正义与程序效益的价值取向。笔者以为,二审证据释明问题主要涉及如何对新证据进行证明与抗辩以及由此造成的费用如何负担等问题。对这些问题,法官应当通过以下方式积极行使释明权:(1)一方当事人提出新证据,法官应先询问他方当事人是否同意对该逾期证据予以质证,并向其释明对新证据进行抗辩的方式,以保障他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同时使其对新证据的抗辩权行使得更加充分。(2)对于一方提供新证据而给他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和增加的费用承担方式的问题,法院有义务予以释明,可建议当事人就相关费用提出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合并审理,一并予以解决。
[1]齐树洁.《民事证据规定》的困境及其启示[J].证据科学,2009,(2).
[2]卢正敏.民事诉讼再审新证据之定位与运用[J].厦门大学学报,2009,(3).
[3]韦经建,李广军.论我国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J].当代法学,2006,(5).
[4]孙瑞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新证据”制度几个问题探讨[DB/OL].http://article. chinalawinfo.com.
[5]罗飞云.民事诉讼再审新证据的认定与运用[J].法律科学,2011,(5).
[6]许士宦.新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张杏喜.民事诉讼“新的证据”问题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07:35.
[8]严仁群.释明的理论逻辑[J].法学研究,2012,(4).
[责任编辑:王泽宇]
Defi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Evidence in the Second Instance of Civil Procedure
FANG Jun,WANG Wen-yv
According to the new civil procedural law, the existence of new evidence is one of the statutory circumstances of the second instance of civil trail.But the new civil procedural law has not regulated it, the existing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lso failed to solve this problem well. The special function of the second instance of civil procedure determined that the new evidence should only be introduced in a limited rang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evidence in the second instance of civil trail must follow the double restriction of entity and procedure,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entity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procedural efficiency.
Civil Litigation;New Evidence;Procedural justice;Procedural Efficiency
DF713
:A
:1008-7966(2014)04-0104-04
2014-04-12
方俊(1990-),男,江西乐平人,2013级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汪文雨(1989-),男,安徽舒城人,2013级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