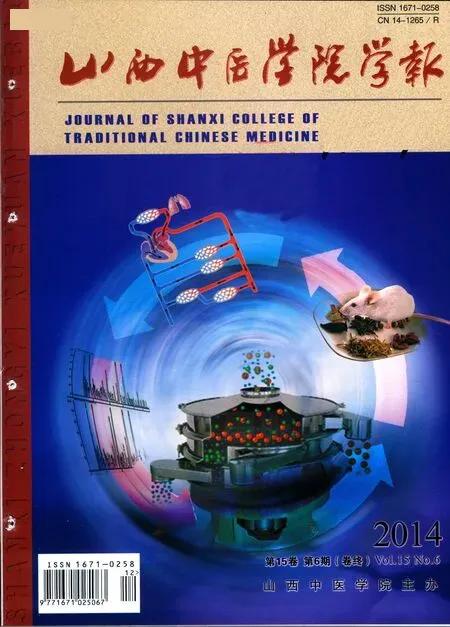基于气候因素探讨李东垣脾胃观与张仲景脾胃观的异同
2014-04-05张卫华王海军
刘 舟 ,张卫华 ,王海军 ,骆 殊
(1.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江苏南京 210046; 2.山西中医学院,山西太原 030024)
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仓廪之官,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金元时期的李东垣,钻研经典,结合当时的气候因素和社会环境,革旧创新,倡导首重脾胃,从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李东垣之脾胃观,溯源于《内经》,得益于仲景。然而,历代医家因受“外感宗仲景,内伤法东垣”的影响,往往忽略了二者之间的联系。本文将着重从两位医家所处时代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探寻医家学术流派形成的规律,并为中医临床提供理论指导。
1 张仲景和李东垣所处时期的气候特点
1.1 东汉时期的气候特点
张仲景(150-219)生活在东汉时期,那时候虽然没有气象报告,但是有物候的文字记载。根据竺可桢的研究记载,从战国到西汉的这段时期,中国气候总体比较温暖而湿润。但是从东汉开始,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而到了三国时代,寒冷更加明显。其中最著名的两个事件:一则是曹操(155-220)在铜雀台种橘,却只能开花而不能结果;一则是有关曹操的儿子曹丕到淮河广陵(今之淮阴)视察士兵演习的景象。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黄初五年(公元225年),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1]从这段文字可知,当时淮河因为骤寒而突然冻结,使得兵演被迫停止。这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淮河结冰,而这种寒冷的天气一直持续到了公元3世纪后半叶。
1.2 宋金元时期的气候特点
李东垣(1180-1251),生活在南宋北金对峙的混战时期。竺可桢报告指出:“历史上有两个阶段,即宋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的气候寒暖变化要比其他时期高。中国气候在唐代经历了和暖时期后,从12世纪初开始加剧转寒。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在冬天也同样结冰;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被派遣到金朝,他在重阳节(即阳历10月20日)抵京,当时北京的西山上到处都是雪。”[1]南运河冰封和北京在10月依然遍地皆雪,这种情况如今已非常少见,但是在12世纪的时候,却是常有发生。当然,12世纪刚刚结束,杭州冬季的温度又开始转暖。李东垣身处12世纪末13世纪初,正是寒暖变化频率较高之时。
2 张仲景和李东垣所经历疫病的特点
2.1 东汉时期的疫病特点
东汉较长时期的严寒引发了大规模的疫情。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2]全国多地连续暴发瘟疫,尤其是南阳、洛阳、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地的疫情更为严重。曹植在著名的《说疫气》中曾描述到:“建安22年(公元217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3]而裴松注《三国志·文帝纪》又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士人凋落。”[3]可见,当时的士大夫尚不能幸免,“建安七子”当中便有五子命丧于此。据研究统计:“在东汉180余年间,大规模的疫病发生频率极高,特别是在公元37-50年、公元161-219年的这两个时段。”[4]而后者正是医圣张仲景生活的时代,由此可见,仲景撰《伤寒杂病论》与寒性疫病流行有关。
2.2 金元时期的疫病特点
李东垣经历的开封大疫是中国历史记载的最为惨烈的疫情之一[5]。公元1232年,蒙古兵包围金朝首都开封,致使疫病大流行,汴京因此而死亡“迨百万人”。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中写到:“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故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6]从这段话可以分析出:第一,此次疫病从壬辰即公元1232年3月开始,绵延长达3个月;第二,开封大疫病死率很高,每天多达数千人;第三,发病率亦高,感染者约占98%。李东垣的脾胃学说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形成的。
造成这次疫病的原因,有学者将其直接归咎于战争[5]。但顾植山认为:“社会动乱并不是疫病发生的唯一原因,不能因存在战争因素而忽略了对自然环境因素的分析研究。”[7]此外,他还明确提出对于瘟疫、大疫适用“三年化疫说”理论。大疫发生在壬辰年,壬辰向前推三年是己丑年(1229年),按《内经·素问遗篇》“甲己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之论,发生在壬辰年的疫病正应该是“土疫”,即脾性疫病,而它与李东垣的脾土学说是否具有相关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3 张仲景和李东垣的脾胃证治观
3.1 六经发病与脾胃失常有关
仲景针对时疫,提出了“四季脾旺不受邪”的观点,在治疗上注重调理脾胃,这在其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中有多处体现。受篇幅所限,本文仅以易被世人忽略的六经辨证为例,说明六经病与脾胃的关系。
首先,营卫不和是太阳病的发病基础。太阳病病理改变的产生,在于外邪乘虚而入、营卫失和。而营卫二气皆受气于谷,虽清浊不同,却皆源于脾胃。倘若脾胃虚弱,则营卫二气化生无力,营卫不足则人体藩篱不固,而易使外邪乘虚侵袭肌表,发为太阳病。治疗太阳表虚,以桂枝汤外调营卫,内和脾胃为主。
其次,胃燥津伤是太阳病发展为阳明病的重要诱因。阳明燥土,得润则安,以降为顺。如果胃肠燥热、邪热内盛,则易致腑气壅滞、失于和降,终致燥实内结而成阳明病。
再次,血弱气尽是少阳病的发病基础。《伤寒论》曰:“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2]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虚弱则营卫羸弱,营卫弱则致腠理开。故少阳病的发病始于脾胃虚弱、营卫气血不充,最终致使邪气侵犯而得病。所以,仲景以小柴胡汤运转少阳枢机,调节脾胃升降。若兼里虚寒,仲景创有小建中汤;若兼气虚甚者,用黄芪建中汤。
最后,脾胃不足是三阴病发病和传变的关键。三阴之表为太阴,三阴被邪所犯,常首犯太阴,所以太阴脾的盛衰,往往对邪传少阴、厥阴有重要影响。由此可知:“六经病的产生,都与脾胃功能失常有关。倘若再有病理产物的潴留,如痰饮水湿食,自然会加重六经病发病的严重性,因此说脾胃失常在六经发病中具有重要地位。”[8]
3.2 脾胃为元气之本,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李东垣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将脾胃认作是元气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少,元气衰少则疾病所由生;同时,他重视气机升降,视脾胃为精气升降的枢纽,尤其强调升发脾胃的阳气。他又从“内伤”立论,倡导“脾虚气陷,阴火内生”。关于东垣论治脾胃病理法方药特点的具体内容,在他的代表方“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中有较为完整的体现。
李东垣所提出的补脾胃、泻阴火、升脾阳的治则,正是源于他对于脾胃病机的三个根本认识,包括脾胃气虚、阴火上乘和脾阳下陷。上述观点在他的代表作《脾胃论》中体现较为充分。东垣在书中揣仲景小柴胡汤之意,创立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该方也是《脾胃论》的第一方。通常认为,李东垣治疗“内伤病”的代表方是补中益气汤,而补中益气汤作为《内外伤辨惑论》的第一方,成书晚于《脾胃论》,且此方只具有补脾升阳之效用,它不足以完整概括东垣补脾、升阳、泻火的三大重要学术思想。所以,将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看作李东垣脾胃学术思想的代表方似乎更为妥帖。该方是由三组药配伍而成的,第一部分:黄芪、人参、炙甘草,可补脾益气;第二部分:黄连、黄芩、石膏,苦寒以泻阴火;第三部分:升麻、柴胡、羌活、苍术,可奏升阳除湿之效。
4 讨论
从两位医家生活的外在环境看,张仲景和李东垣生活在气候寒冷或气候多变的时代,都亲身经历过疫病大流行,这对他们的学术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由于两位医家所处气候环境的差异与经验积累的不同,二人在寒与温、正与邪、诊治原则等诸多方面,各有侧重。
仲景首重风寒外邪,这很可能和他所经历的寒性疫病流行有关。他较少提及灾荒或战乱等易使人元气内伤的因素,没有特别强调在发病之初必须培补正气。但是,他提出的“脾旺则不受邪”的发病观,注重调理脾胃的治则治法,以小建中汤为首的三建中汤等方剂,则贯彻了他的上述思想,仍然对后世内伤病的治疗具有较强的指导价值。学者普遍认为《伤寒论》六经辨证既适用于伤寒,也适用于内科杂病[9-10]。
李东垣擅长治疗脾胃病,倡导“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这一思想,治疗首重脾胃,创设了一系列补脾胃、泻阴火、升脾阳的名方。他的脾胃证治观,除了与个人的知识结构以及对仲景之方的继承与创新等内在因素相关外,可能和他身处南宋北金对峙混乱时期,战乱流离、人多元气内虚,以及人生经历的“土疫”(脾性流行病)有一定的相关性。他的学术观点常常略论外邪,比如说对疾病之初的恶寒发热,他解释为乃内伤脾胃、元气不足、“表中无阳”“阴火上冲”使然,即使用了升、柴、羌、防、葛根等“风药”,他也不认为是祛邪解表的,而解释为“升阳散火”[11]。又如,东垣在解释以补中益气汤化裁的诸方中加入风药的意义时,他或称引脾胃之气上行,或谓之引甘温气味上达,以实卫阳[12]。由此可见,东垣用上述诸药的出发点与仲景有异,理论阐释侧重面不同,但并没有完全否认外邪的存在,用药的实际效果依然可以祛邪解表。从这一层面来说,世医所言“外感宗仲景,内伤法东垣”之说也不是绝对的。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21-37.
[2]柯雪帆.伤寒论选读[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61.
[3]李德顺.古代气候变迁与麻桂剂产生的关联研究[J].现代中医药,2013,33(5):28.
[4]中国中医药研究院.中国疫病史年鉴[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03.
[5]赖明生.疫病流行的相关因素浅析[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0(11):32-33.
[6]李杲.内外伤辨惑论[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6.
[7]顾植山.疫病钩沉-从运气学说论疫病的发生规律[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3:31.
[8]梁华龙.六经升降学说原委[J].河南中医,1998,18(3):132.
[9]潘澄濂.《伤寒论》六经指要[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2(5):2.
[10]肖德馨.《伤寒论》六经探讨[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2(2):19.
[11]陈素娥.《伤寒杂病论》与《脾胃论》脾胃生理证治观的相关性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2:47.
[12]吴光炯.试论李东垣脾胃学说中的温热病学思想——东垣仲景学说比较[J].中医杂志,1999,4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