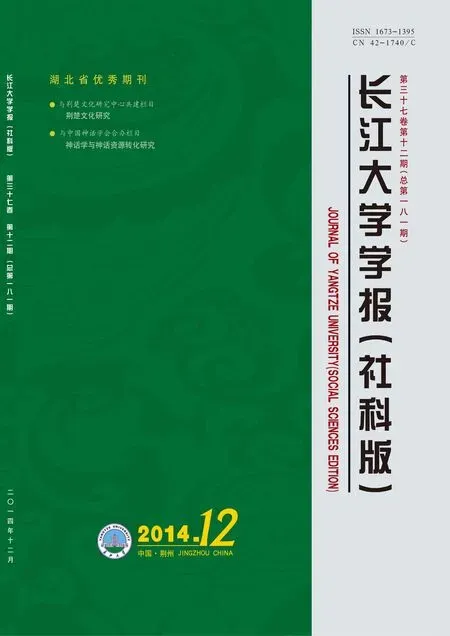芥川龙之介《酒虫》与蒲松龄《酒虫》对比研究
2014-03-25郭昱瑾
郭昱瑾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新思潮”派小说家,擅长创作题材新奇的短篇小说。其代表作有《罗生门》、《地狱变》、《鼻子》等。芥川龙之介早期的作品大都来源于民间传说,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典籍,意在借古喻今,针砭时弊。其《酒虫》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的同名小说,其标题和故事进展都与原作极为相似。芥川龙之介认为,自己的这篇小说,对原作几乎没有做出什么改动。但对比蒲松龄原作,芥川龙之介笔下的《酒虫》,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
一、作品结构
《聊斋志异》继承了史传文学“文约事丰”的叙事风格,文笔简洁明快,结构凝练。《聊斋志异·酒虫》的叙述方式为顺叙,而芥川龙之介的《酒虫》,则打乱了原作的故事顺序,将其重新编排成四个部分。小说由“这是近年来从未有过的酷暑”开篇,然后从房檐上的瓦“像铅一样反射着沉闷的日光”,联想到“屋檐下的燕子窝里的雏燕和燕蛋会不会就那么被热坏”;从农田里作物“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联想到农田上方的云“如在锅里煮的糯米点心那样漂浮着”[1](P57)。芥川龙之介笔下所描绘的社会风物、自然景色,以及其偶尔插入的联想,令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仿佛真能感受到那酷暑下的闷热和窒息。然而,就是在这炎炎烈日下,打麦场里一赤身裸体的男子,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附近站着一长相古怪,挥着扇子为其驱赶苍蝇的西域僧人,远处还有一位穿着黑布大褂的老学究。“狗也许都睡熟了”[1](P57)的夏日正午,三个沉默不语的男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作者用设置悬念的方式,激发起读者强烈的好奇心,为故事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交代完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后,芥川龙之介《酒虫》的第二部分,便交代出场人物和故事开端。原作《酒虫》只是说刘氏与番僧相遇,但对其是偶然相见,还是刻意为之,并无赘述。由于二人的相遇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芥川龙之介虚构了二人的见面契机:番僧主动寻来,刘大成在家中待客,因虚荣心作祟,促成了两人的见面。这样一来,既打消了读者的疑问,又使故事的发生更加合理。番僧与刘氏的对话,为读者揭开了小说第一部分中奇特光景产生的缘由:刘大成因好奇心驱使,接受番僧为其取酒虫治病的要求。这是整个故事的开端。但是,不单酒虫的存在与否令人怀疑,番僧的治疗方法也太过诡异。因此,在小说第二部分的结尾处,芥川龙之介添加了一段评论,嘲讽因轻易听信他人言论而接受治疗的刘大成的愚笨,并借古喻今,讽刺学校教育使人丧失了辨别能力。在故事进行途中插入自己的态度,并引导读者由此及彼,思考当时社会之弊端,以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这一做法,透漏出芥川龙之介改写《酒虫》的真实意图之所在。
芥川龙之介《酒虫》的第三部分,描写了治疗过程中刘大成的心理活动和治疗结果,是故事的高潮。此处小说的叙事视角,突然从小说开篇的叙事者视角转变为主人公视角,并由此切入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暴晒在烈日下的刘大成,汗珠渗进眼里,全身晒得火辣辣,喉咙发干;他甚至想到用望梅止渴的故事来自我勉励,但无奈身旁置有美酒,致其酒瘾难忍;长时间的治疗,让他开始产生剧烈的眩晕感……经由这一系列描述,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刘大成一人身上。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刘大成从最初的忍受,到其对接受治疗的后悔,继而转向对番僧的怨恨,最终发展为绝望,并企图放弃治疗;但就在此时,“一团难以言状的东西缓缓从胸口向喉咙爬上来”[1](P63),酒虫被排出来了。小说所描写的整个治疗过程安排合理,叙述节奏有张有弛,刘大成的心理变化脉络清晰可见。对于排除体外的酒虫,芥川龙之介并没有过度地强调其奇妙,而只是平实地描述了三人之所见:“一条肉色似朱泥,形状似小鲵鱼的东西在酒里游泳”,“长约三寸,有嘴有眼,好像一边游泳一边饮酒”。[1](P63)原作中,刘氏欲以重金答谢番僧,番僧不收,只是要求带走这酒虫;随后,番僧向刘氏揭示了酒虫的奥秘:“此酒之精,瓮中贮水,入虫搅之,即成佳酿。刘使试之,果然。”[2](P2423)原作的这段文字,充分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十分符合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目的。但是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却删除了这一部分内容。从篇幅上看,其明显将重点放在了对刘大成的心理描写上。这样的安排,也暗示着,芥川龙之介的《酒虫》,并非只是对原作的单纯改写。
芥川龙之介《酒虫》的结尾部分,与原作并无太大差异,其视角也回到了之前的叙事者视角,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记录了排出酒虫后刘大成的生活变化,并列举了人们对此事的各种看法。所不同的是,芥川龙之介用三种不同的答案,代替了原作中的异史氏曰。相较原作,这样的叙述方式,显得更为灵活自如,更有助于彰显作品的主旨。
二、人物安排
《聊斋志异·酒虫》中,主人公为好酒的有姓无名的刘氏。芥川龙之介在其《酒虫》则为刘氏取了一个名字——刘大成,由此,使刘氏完成了由文言小说人物向现代小说主人公的转变。“大成”即大成就。用这样一个极富美满寓意的名字,衬托主人公的生活状况,这是作者对其人生经历的一种嘲讽。改编后的刘大成形象,虽与原作刘氏并无太大出入,但芥川龙之介所更注重刘大成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心理变化,而蒲松龄则更强调一个普通人的新奇经历。原作对于番僧的来历只字未提,芥川龙之介的《酒虫》中,则对这一神秘高人做了详细的描述:这是一个“身着黄色袈裟,戴着小青铜耳环”,“皮肤黝黑,发须卷曲”的,来自“葱岭以西”的擅长医术的宝幢寺高僧。[1](P57)芥川龙之介《酒虫》对番僧相关信息的充实,使故事的进展更合乎情理。芥川龙之介笔下的番僧,虽然狂妄古怪,但治好了多人的异疾,颇负盛名。其主动寻找刘大成为其治病,表明了其善意。原作结尾处的异史氏曰认为番僧“愚”,而芥川龙之介的《酒虫》则将其塑造成一个除妖降魔式的卫道士形象。为了实现其帮人排出恶疾这一志向,番僧竟毫不顾忌强制去除酒虫对刘大成人生有何影响。如此一来,番僧的形象便更加鲜明和具体了。
除了原作中已有的两位主人公之外,芥川龙之介的《酒虫》中,还出现了刘大成的童仆、丫鬟,以及其酒友孙先生等人物。童仆和丫鬟的安排,很明显是为了衬托刘家的富足。刘大成“负外郭三百亩”[2](P2422),自然有侍从婢女。如此描写,才能使刘大成与其最终的潦倒形象,形成更强烈的对比。最有意思的要数这位孙先生了。小说中的孙先生,手持白羽扇,是位准学究。小说提到他无端地蔑视道佛两教。由此推测,这位孙先生应该是位儒者。孙先生的出现,促成了刘大成与番僧的相遇:“刘大成这人并不好客。不过有客在场,又有新客,一般都会高兴地接待。这样可以在客人面前炫耀自己贵客盈门,满足一下小孩子般的虚荣心。”[1](P59)如此,小说的情节展开就顺理成章了。
文学创作中,作者既可以让自己隐藏于故事背后,也可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在作品里,成为观察人物和故事发展的一双眼睛。芥川龙之介的《酒虫》中,孙先生始终在场。可以说,芥川龙之介正是借孙先生之眼,来观察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的。孙先生作为旁观者,是整个故事的见证人、记录者。同时,孙先生也真实地表露出旁观者那种事不关己的自私,以及对他人事情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好奇心。孙先生是刘大成的酒友,自然熟知刘氏日饮一瓮的习性,但其却对此不以为异。面对刘氏的求援,孙先生“故作姿态,只顾独自往棋盘上投子,根本不予理睬”;然而,他也并非对此全不关心,而是在“一直默默地听着两人对话”,甚至“担心自己肚子里是不是也有酒虫”,于是才突然插话问道“用什么药?”[1](P60)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孙先生后来的名为推不过去,实则为好奇心所驱使的见证人经历。如果治疗现场没有孙先生,旁人将无法知晓酒虫一事,世间的种种争论便无从而来。由此可见,芥川龙之介在小说中刻意添加的这位孙先生,可谓用心良苦。
三、创作目的
芥川龙之介的《酒虫》,较之原作进行了大胆的结构变动。其删除了原作的部分内容,加入了较多的虚构情节,从而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合理。这样的安排,致使原作猎奇式的主题已站不住脚。那么,芥川龙之介的《酒虫》究竟象征着什么,其创作意图又是什么呢?
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仕途蹭蹬,生活贫困。他创作《聊斋志异》,不单单是以之记录奇异事件,更是借谈狐说鬼,以揭露讽刺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现象,抒发其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想。《聊斋志异》中,酒虫是不为人所熟知的生物,是神秘的存在。有人说,刘氏因酒虫而嗜酒如命,贪得无厌,酒虫是其欲望的化身。也有人说,刘氏没有了酒虫就丧失了一切,酒虫是其天赐的福分,是命运。《详注聊斋志异图咏》评价蒲松龄《酒虫》云:“漫因贫富疑途穷,应悔当时去酒虫。何物番僧偏好事,未容长住醉乡中。”[3](P146)可见蒲松龄的《酒虫》,意在记录一段离奇经历,以讽刺人的愚蠢,感慨富贵之不常,表明人生的不可预测性,颇有些黄粱一梦的意味。
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并不是对历史的重述,而是对现实乃至未来的暗喻和借鉴。人是社会动物,必然会受到其所处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影响。芥川龙之介生活的大正时期(1912~1926年),日本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与思想的熏陶。同时,20世纪初,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少外商因此前往日本投资,带去了欧洲的新文化。一战结束后,日本国内民族自决浪潮兴盛,民主自由气息浓厚。一时间,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国民参政运动等各种民主运动,在日本风起云涌。在这种强烈的异文化和新文化的合力冲击下,日本文坛也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文学思潮:标榜真的自然主义,追求美的浪漫主义,向往善的白桦派文学。生活在如此时代的芥川龙之介,自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众多判断和抉择,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自己对事物的独特观察视角和判断标准。芥川龙之介所代表的新思潮派,站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交叉点上,虽然没有提出鲜明的文学主张,但其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其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却彰显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此外,芥川龙之介本人的养子身份和其早年的生活经历,也使其比常人更为敏感。这也是早期芥川龙之介作品着眼于人性思考的另一个现实原因。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因探求人性而揭露出人性之恶,但其并非为揭露而揭露。他的这种揭露,实际上折射出他对人性善的向往。其《酒虫》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芥川龙之介创作《酒虫》的目的,在于借此窥探主人公在经历一件离奇事件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并以此展现人性。刘大成在治疗前和治疗中所表现出来的傲慢、虚荣、好奇、隐忍、软弱和对自身的无奈,以及孙先生所代表的旁观者的自私冷漠,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心理状态。芥川龙之介深知人性的多面性,因此,在小说创作中,他让自己只做一个真实观察并记录世界的冷静的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笔,忠实地记录了人世间的丑恶与真善美。对人性的观察越客观,对人性的理解就越深刻。在《酒虫》中,芥川龙之介说酒虫就是刘某,刘某就是酒虫,其实是借酒虫指代人的个性,即人性;并通过细化番僧形象,以其为人治病的行为,比拟学校教育。番僧治病,是对他人自由的干涉;同样的,学校教育以单一模式培养学生,以唯一标准评价学生,亦是抹杀他人的个性,不尊重人性的做法。芥川龙之介借用《酒虫》故事,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表明了自己对学校教育理念的不认同。然而人性究竟是什么?对此,年轻的芥川龙之介心中也是充满疑惑,所以他才说自己“也不得而知”[1](P64)。
《酒虫》是继《罗生门》、《鼻子》之后,芥川龙之介另一部以冷静理智的态度,观察现实,认识现实,探讨人性的作品。《酒虫》的创作,体现出芥川龙之介这一主张:人性虽然并不完美,但我们仍应该尊重人们的个人自由。因此,芥川龙之介的《酒虫》,对于研究芥川龙之介早期的文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一卷)[M].郑明钦,魏大海,侯为,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2]蒲松龄.聊斋志异[M].济南:齐鲁书社,1981.
[3]吕湛恩.详注聊斋志异图咏[M].北京:中国书店,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