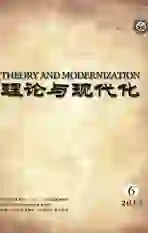文化结构分析:论马克思与钱穆文化结构论之异同
2013-04-29李承福周德丰
李承福 周德丰
摘 要:马克思与钱穆都从人的生活来认识文化结构。人的生活不仅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横向结构,人还生活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中,还有过去、现在与未来一同到场的历史向度,而实践作为人的类本性,整合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个体凝聚为民族,文化呈现为民族精神。分析马克思与钱穆文化结构的异同,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化与文化结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关键词:人的存在;文化;文化结构;实践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6-0045-04
梁启超、陈独秀、梁漱溟、殷海光、庞朴和余英时等都论及文化结构,但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与钱穆从人生活的横向结构、历史向度和类本性整合三重维度分析文化结构。其中马克思以人的实践为出发点,理解现实世界,理解人与世界的矛盾史,把自然、社会、人自身看作是开放的生成的存在,指明人在不断使世界人化的过程中,历史地扬弃自身的异化,将人的本质归还所有的个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1]而钱穆认为,“‘文化必由人类生活开始,没有人生,就没有文化”,[2]所以文化“是指的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3]由心性引发人文,以仁心为基础的道德精神指明历史前进方向,民族精神是现实文化的整合结果,天人合一是人类终极价值追求。总之,马克思与钱穆的文化结构分析,在形式上极为相似,但重心不同,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化与文化结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一、文化的横向结构:唯物论与心性论差异
马克思与钱穆都从人的生活谈文化,在此,人不只是单个的实体,更是关系性的存在。只有从人与世界的矛盾关系中,才能发现人的生活结构,进而说明文化结构。人与世界的交互关系中包含三要素:现实生活的人、人生活依赖的自然、直接操纵人活动的自我心灵。三要素两两组合,即是横向的三层矛盾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之所以称为矛盾关系,是因为这三层关系在主体性上展现为三类需要:自然性需要、社会性需要、精神性需要。这三类需要是人生活的动力,是一切文化和价值的基础。
马克思与钱穆都强调人是自然与超自然、个体性与社会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存在,三层矛盾关系相互关联交叉,互为中介,有机地形成人生活的横向结构,也即文化的横向结构。
1.人生活于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中
马克思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4]一方面人因生而获得躯体,由躯体而具有生理、本能等自然存在,这是人本身的自然存在;另一方面人以外的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与自然的矛盾就表现为人同这两方面自然的相互作用,矛盾越发展,人在矛盾中就越主动、越自觉。
钱穆也持同样观点,一方面是人离不开自然。他认为人性本于天性,即自然之性,“由天性中成长出人性,而更由人性来成长此天性”,[5]连人的身体与人性都为自然所演化,人的其他方面同样脱离不开自然,“人文兴建,依然是一种自然趋势,由自然中演出人文,而人文仍还在自然中,不能摆脱自然,更不能违反自然而独立存在。”[5](235)另一方面,人也改变自然,文化就是人性对自然的投射。“即就环绕我们的自然界而言,如山川、禽兽、风景气象,试问洪荒时代的自然界,何尝便如此?这里面已经有几十万年代的人类精神之不断灌注、不断经营、不断改造、不断要求而始形成。此刻我们之所谓自然,早已是人文化了的自然,而非为今人文化洗炼以前之原始自然。一切的‘物世界里早已有人类的‘心世界之融入。”[3] (12)
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中,自然是人生活的一部分,人也投射了人性在人化自然之中。这是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双重性质。
2.人还生活在人与人的矛盾关系中
马克思揭示人生活的第二重矛盾:“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6]他强调要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理解现实的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呈现为个体性存在,又以社会性存在为前提。人是互为主客体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这是人与人矛盾关系的双重性质。
钱穆也把人与人的交往作为人生活的第二层次,“其次是‘社会的人生,或称‘政治的人生、‘集团的人生。……在第二阶层里,人面对着人,即人生大群。这时的人生,主要在填进了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13)文化就是在人群交往中形成。他说:“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7]
正是这样一种人际交往实践,人突破了个体小生命形态,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融成大生命,才有了民族、国家等群体组织,在历史流变中,各种生活样态就成了文化。
3.人更是生活在人与自我的矛盾关系中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是自我意识的对象。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4]人是人自己的客体,是精神性与物质性的统一。这是人与自我矛盾关系的双重性质。
钱穆提出由心来认识世界和人自身,“心与物交,凭我们人心之灵,来改造自然万物,以备人生之用,此亦是自然。亦可说是一种天理,亦可说是一种天命,其事皆由天。”[2](35) 由口与手之合作产生语言文字,进而生成观念,使人类能保留旧记忆,产生新观念,引起人类极大变化,创造出一套真善美合一的精神文化,所以钱穆坚信:“宇宙生机,天地大德,永永无极之化育工作,其最后果实则为人,其最后核仁则为人之心,故唯人心乃可反映天心,而且承续天心,以开创新生机,展出新宇宙。”[2](85)
马克思与钱穆的不同在于三层矛盾关系中哪一方面为重心: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钱穆则认为人与自我关系有着根本意义。
马克思认为人是物质生产实践者,也是社会交往实践者,两种实践决定精神生产。他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升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外观。”[4](31)而且经济生活是思想最基本的方面,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而钱穆则强调人与自我矛盾关系是最高层次关系。他说:“必由第一阶层,才始孕育出第二阶层;亦必由第二阶层,才始孕育出第三阶层。第二阶层必建立于第一阶层之上,但已超越了第一阶层,而同时仍必包涵有第一阶层。第三阶层之于第二阶层亦然。”[3](15)钱穆认为心是文化的本源,文化的一切都是心的表现。钱穆批评道:“他(指马克思——作者注)却犯了更大的错误。他不晓得他所看重的经济人生,只尚在文化第一阶层中。此下第二、第三阶层,固然必须建立在第一阶层上,固然必须包含有第一阶层之存在,但却已超越了第一阶层。固然仍将为第一阶层所限制,但亦决非第一阶层所决定。……此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对人类文化演进通律所犯最大的错误。”[3](24)但是钱穆在阐释中西文化差异时,却是坚定的自然环境决定论者,用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环境说明人性与人心的差异,进而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钱穆并没有贯彻他的人生阶层论观点。
二、文化的历史向度:经济决定论与仁心生命论差异
马克思和钱穆都重视文化的历史向度。马克思说,某个需要被实现了,又产生新的需要,这些需要在历史中不断分化、深入,人类生活呈现需要系统的发展过程,这就形成文化结构的历史向度。钱穆认为人是期望的动物,人生只是一个向往,“人文科学里的时间,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过去穿过现在而迳向将来,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力量,就叫做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成了历史。”[8]
忽略文化的历史向度就意味着文化结构的解体。因为舍弃历史,即无文化,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这一点钱穆说得非常清楚:“文化是体,历史是此体所表现的相”,[2](129)“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7](115)所以文化与历史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在文化之中必然有历史向度。因为人的过去、现在、将来是一同到场,“历史时间过去的未过去,依然存在着。未来的早来到,也早存在着。唯在此时间中,必有其内容演变,而始成其为历史。”[8](4)历史本质上是融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一体的精神性的文化生命。
但马克思不同于钱穆。就哲学层面来说,文化的历史向度,体现在人与世界的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方面,体现在人不断创造、实现自我本质的过程,推动人化世界的演进,即文化的衍生。就唯物史观层面来说,文化的历史向度是由经济决定论主导的异化扬弃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文化的历史向度是由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的发展为终极力量决定,因为人类特定时期的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形式可选择的范围,进而决定社会精神面貌,当一定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精神面貌相适合并促进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发展时,文化就大踏步地往前迈进。相反,文化的进程就原地踏步,甚至产生紊乱与破坏。人类文化波浪式前进,从人的依赖关系到对物的依赖关系,最终达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文化结构的历史向度。
钱穆则把文化的历史向度看作是人原始本心不断流露的生命历程。钱穆认为,文化是一个大生命,也是一长生命,文化的生命历程就是历史,是由以仁心为核心的心性所决定。这同他把人与自我矛盾关系认定为文化横向结构核心相一致。
首先,文化产生于人的心性,心性决定文化的演变。“人文界一切,皆从人性展演而来”,[5](27)“人生大道,人类文化,必从各个人之自性内心人格动力为起步”。[5](105)心性是历史文化演进的领导精神,“历史文化之演进,其背后常有一抉择取舍之指针,此指针即人心”,“人心之长期指向,即是文化精神”。心性是社会、历史和文化演化的推动力,“人心变,斯历史亦必随而变”。[8](34)文化的进退升沉,虽然在现实上直接归结于政治、经济、军事的基础,但在根源上,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社会人心方面。因此,文化的历史向度为人的心性所决定。
其次,钱穆认为仁心是心性的内核。他说孔子提出“仁”为人心之同然,即孟子所谓人的原始本心,所以称为仁心。“凡人心必皆仁,仁即是人之特性标识” ,[8](33)把仁作为人类本质属性、人文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仁是人道不动真理,因仁是人类原始本心,此心上通于天,可谓是自然与人文之接寻处,亦可谓是人类生命之特性与本质。”[3](85)钱穆进一步认为天地之间只此一仁,“宇宙造化之本体,亦可谓之是一心,亦可谓之是一仁”。[9]万物的存在本身就是天地生生不息之大仁德的体现。天地生万物之时,万物便分有仁心,而人心之仁,是天地之仁的大用。因此,钱穆认为仁是心性之内核,说心性创造了人类文化这一长生命,实即是仁心缔造了文化的历史向度。
三、文化的类本性整合:自由回归与天人合一差异
文化的类本性整合就是按照人特定的类本性把文化的方方面面和各种要素整合起来,使抽象的文化要素凝结成现实的文化,使现实的文化有灵魂,有独一无二的特性。文化的类整合是文化成为有机整体,文化结构之所以称为结构的前提。
人类的类本性就在于人类区别其他物类,同世界打交道的生存方式。人通过生产、交往等实践,创造并满足人不断滋生的多层次需要,突破自然性存在,发展社会性和精神性存在,创造人自身和自己的本质;创造性的活动,产生和发展整个人文世界,不断将已经人化的实然世界推向价值上的应然世界,改变整个人与世界的矛盾关系。人实现需要的方式——实践,创造着人不同于动物的一切根本方面:动物是天生天养,被动适应世界,而人则自生自养,实现自我,创造新的世界。人类这一特性就是人的类本性。
马克思和钱穆对人类文化的类本性整合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的类本性整合的角度不一样。马克思是从人类的普遍性上谈文化的类本性整合,钱穆则是从文化史学特有的民族性看待文化的类本性整合。
首先,马克思从人类学视角,对人的类本性普遍意义作了哲学反思。他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0]可见,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才是人的类本性。
其次,钱穆认为文化创造了民族和国家。“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举世民族、国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后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随形,莫能违者。”[11]正是文化的异同,使得各个民族与国家有共相与别相,撇开文化,民族性就无从谈起。
具体说来,文化的个性就体现在各个民族内部的文化七要素(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与艺术)搭配差异。就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文化的类整合有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商业文化;人与人关系方面,有分权制文化、集中制文化;人与自我关系方面,有以宗教与科学为主轴的文化,有以道德与艺术为主轴的文化等。总之,“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就是历史精神。”[2](129)他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具体矛盾、需要取向、价值观念、意志韧性、理智系统、实践样式、文明成果。正因为各民族文化的类整合不一样,使得各个民族呈现不同的民族精神。
第二,他们定位人类的类本性基点和归宿不一样。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类本性在于自由自觉的生产实践,实现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终极价值追求;钱穆认定人类的类本性在于以仁心为基础的道德精神,提倡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首先,马克思把实践归结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0](131)他强调在经济生产中生产着真正属于人的自然界,这表现的正是人类的本质力量,即类本性。接着他用这一类本性说明社会和国家:“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4](29)再反过来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意义:“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而自然对人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12]而意识形态也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必然升华物”。
人与自然的物质资料生产实践,是人解决人与世界矛盾关系的活动基础,也是人与世界矛盾发展的基础,并且限定了所能采取的人与人之间交往实践方式,即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因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本质上是物质生产实践同社会交往实践交互作用的结果,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最终动力。马克思认为历史演进就是从对人的依赖关系到对物的依赖关系,最终达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从人与世界矛盾的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过程。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文化理念的根本价值和最高命题。
其次,钱穆以心性本体论为文化类整合的出发点,得出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内心的安乐与崇高成为终极价值关怀。他说:“文化本身是精神的,仅存在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7](120)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之中,“人类的心生命,乃寄存于外面之物质世界而获得其生命进展者,均在此宇宙界。凡寓人类所创造之新的物质世界中,则莫不有人类心的生命之存在。”[13](207)钱穆把人与自我的心世界认作人与世界最根本的方面,将不断进步的道德精神看作心世界的发展动力,“当知人类一切进步,决定在其最先的观念上。观念不同,便出发点变了。出发点变了,便一切都变了。人类的一切创造,主要在其观念上,其他的进程很简单,自然会水到渠成”。[14]道德精神源于人类生命的心性本体,人类从宇宙大生命走向文化历史生命,道德精神贯穿在人类生命历程始终。世间万物都生于天,因而有共同性,“此一大共通即是天,故曰天命之谓性”。“好生求生,此乃生命界共同之性”。[13](218)而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在于人心之仁,这是因为人心最灵最能表现出此性,即是最能表现出此天,虽然源于自然,却又是一种文化心,“人类以心交心,创出一套真善美合一调整之理想人类文化,而天地变色,宇宙翻新,其事更值重视”。[13](218)由此体现了心与性、人文与自然的融通合一。
钱穆从心性与道德精神角度谈天人合一是抽象的文化类整合,他还提出了更现实具体的文化类整合:各民族通过其历史文化的个性传承与发展,并且融通其他民族的文化精神,使个人的生活符合以仁心为基础的道德精神,从而求得安乐与崇高的心灵境界,实现天人合一。钱穆首先强调的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只有在不丢失以往自我的前提下,才能开出符合未来的新自我。因为每一个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文化方式,作为该民族的特定历史积淀下来,必然有需要传承的合理方面。其次是强调要融通其他民族文化精神。每个民族在人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追求安乐与崇高的终极价值方式各有所长,传承民族自身文化的优长,并按自身需要融通其他民族的文化优长,“据旧开新”,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天人合一,站在人类追求安乐与崇高的文化顶端。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钱穆都勾画出人与世界矛盾关系的横向结构、历史向度与类整合的文化结构层次,都是基于人的生活来解读现实世界的人文意义,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其中他们都认为人与世界矛盾关系的横向结构是相互交叉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层关系,并且人类文化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实然与应然的历史向度中不断向前发展,这种人类文化演进的驱动力在于人类的类本性,而且人类文化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无限接近这一类本性。
他们在文化结构观念上总体的差异在于:马克思对文化结构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哲学的普遍性与科学的客观性,而钱穆则是基于历史学的民族性与人本学的多元性。当我们讨论人类文化发展的道路问题时,具体到某个现实国家的发展形态就可能很不一样,这是因为人文演进有普遍性,也有民族性。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特殊性恰是钱穆所强调的,他认为各个民族人文的演进有其自身的历史惯性,一个民族适应时代发展的文化必然是在传统传承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生活现状、新的需要,借鉴其他文化样式,设计出符合民族性的文化类整合方案。譬如说社会主义制度的样式,历史发展到当今,世界存在苏联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甚至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世界上有一百多种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注意到了沙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欧资本主义的巨大差异,也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设想,但也只是试图探讨将世界各国历史与文化差异如何转换到历史向度的一般轨迹上来。而从钱穆的文化类本性整合侧重文化的民族性与延续性出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必然的,所以钱穆说:“然则今日大陆果有意推行中国社会主义,以代替苏俄所奉行之共产主义,岂不极为恰当。”[15]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遵循了人类一般人文演进的现代化之路,又是中国自身民族发展与历史延伸之果。但是马克思坚持了人类文化科学进程的客观性,而钱穆以仁心为基础的道德精神完全包容在马克思对人类文化进程的主体性之中,因此马克思的人类文化结构理论整体上比钱穆的更加严谨和全面。
马克思和钱穆的文化结构理论之中都包含了合理内容,我们把这些思想挖掘出来,加以发挥,形成更加完善的文化结构理论,必然会更加贴近文化本身。具体来说,这种文化结构理论有三个特点:第一,在文化的横向结构上,坚定物质生活的基础性地位,同时积极能动地寻求精神生活的安乐与崇高。以生产和交往实践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本身并不违背人类对安乐与崇高的精神生活追求,不管是修身养性的中国儒学,还是印度佛学和西方基督教,或者其他信仰,也都必须要通过各种方式求得内心安乐与道德崇高。第二,在文化的历史向度上,肯定人文社会变动的客观性,也明确心性对人文演进的指引性。心性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但人类并不能立刻跳跃到心性指引的理想世界彼岸,所以人类必须正视由生产方式主导的现实世界,只能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前行。第三,在文化的类本性整合上,现实的各个民族与国家在文化前进道路上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人类迈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不是征服必然王国,而是更加完美地融入必然王国,人类处在自由与必然之间,这正是心性合一、天人合一。这三点精神就是综合马克思与钱穆文化结构思想精华的大纲式结论。
参考文献:
[1]李承福.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人本学维度[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05.
[2]钱穆.中国文化丛谈(一)[M].台北:三民书局,1984.186.
[3]钱穆.文化学大义[M].台北:正中书局,1952.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5]钱穆.双溪独语[M].台北:学生书局,1981.26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79.
[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32-133.
[8]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钱宾四先生全集(29)[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6.
[9]钱穆.朱子新学案[M].四川:巴蜀书社,1986.24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6-97.
[11]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1-32.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5.
[13]钱穆.中国文化丛谈(二)[M].台北:三民书局,1984.207.
[14]钱穆.民族与文化[M].香港:新亚书院,1962.51.
[15]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