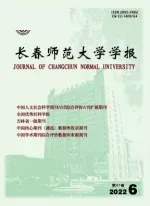论元好问对宋词的继承与创新
2012-08-15黄春梅
黄春梅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系,广东揭阳 522000)
论元好问对宋词的继承与创新
黄春梅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系,广东揭阳 522000)
元好问在词的词风及自然山水空间、情词审美范畴上的开拓,扩大了词的审美空间和审美趣味。在宋词基础之上的继承和创新,使元好问成为集金词之大成的大家,在宋词对金词的熏染以及金词对宋词吸纳过程中,起到了整合、创新甚至提升的作用。
元好问;词风;词境;创新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州)人,是金、元两代著名的文学家。元好问的词直承苏、辛,有豪放雄奇的一面,又能兼容秦、周、姜、史等婉约词人的风格,创造性地融合豪放与婉约两种词风于一体,在词的发展史上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本文从词风、词境等方面探讨遗山词对宋词的继承及创新,从接受传播的角度探讨遗山词对两宋词的继承与发扬,从更具体的角度研究宋词在金元的传播及宋词与北方文化结合之后的新变。
一、刚柔相济,含蓄蕴藉的词风
说到宋词词风,一般都会举“豪放”和“婉约”。“豪放”主要是就创作主体的内在人格、性情、心态而言,指作者气魄胸襟博大,追求人格个性的独立和自由,勇于突破传统和外在规范的束缚。而“婉约”则主要是就作品的表达方式而言,即不直接、坦率地表达主体的情思意向,而是以曲折的方式,委婉含蓄地表达情感[1]。简要地说,“豪放”是指创作主体内在的人格类型、情感模式,而“婉约”是指作品本体外在的表达方式。
宋代豪放词的代表,非苏、辛莫属。元好问身上北方民族豪健英杰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特定的人生遭际使他极为推崇苏、辛,创作上也继承了苏、辛的豪放之风,具体表现在抒情主体的豪健人格和博大胸襟上。而在情感的抒发方面,遗山并没有亦步亦趋地模仿苏、辛,而是转益多师,继承了宋词中的婉约手法,追求情感表达的含蓄蕴籍。情感表达的含蓄蕴藉使元好问词避免了苏、辛词派缺少含蓄、词无余味的不足,其情感表达方式具体表现在章法结构的回环往复和情感表达诉诸理性两个方面。
(一)回环往复的结构
元好问论词讲究含蓄,要有韵外之致,不仅如此,其在具体的创作中也实践其理论主张。比如元好问在词的情感表达方式上就不是一味追求豪放,而是以回环曲折的手法婉转地传达出主体的情感,表现在创作中就是有意打破晓畅抒情、直线发展的路数,转而采用回环往复、曲折跌宕的章法结构。如他的《青玉案》 (落红吹满沙头路),全词以描写晚春落花起调,导入感情的抒发,以人拟花,又借花写人。继而写春燕对春色的执着追求,以寄托个人的怀抱。然后由此写及自身境况,感叹之后又转而写花,感伤好花不常开,再转及自身的描写。词意层层转折,愈转愈深,外界自然景物的转移,与词人内部感情潮水的跳荡互为包容。回环式的结构准确地传达出词人蕴含心底的思绪和忧伤,以婉转曲折之笔写出了难以言传的幽怀。
小令如此,元好问的慢词在结构上也表现为情、景或时空交替上的回环。如其怀古词《木兰花慢·游三台》:
拥苕苕双阙,龙虎气,郁峥嵘。想暮雨珠帘,秋香桂树,指顾台城。台城,为谁西望,但哀弦凄断似平生。只道江山如画,争教天地无情。 风云奔走十年兵,惨淡入经营。问对酒当歌,曹侯墓上,何用虚名。青青,故都乔木,怅西陵遗恨几时平?安得参军健笔,为君重赋芜城。
这首词写词人游三台而怀古寄慨。此时金朝已亡,作为一位生活于蒙古统治下的金朝遗民,元好问凭吊魏都,必然触目兴感,但其感情又不便直接表露,因此促成了本词以健笔壮语写悲怀、寄深于浅、寄曲于直的艺术特色。一般怀古词都是先写眼前之景,然后追昔念旧,但是遗山此词落笔不是写眼前之景,而是先逆笔蓄势,以劲健的笔力极力渲染出邺城往日的王都气象,通过描摹追忆中的邺城繁盛画面发端,于雄阔高朗的意境中寄托了抒情主体的无限感慨,忆昔愈切,伤今愈痛。全词上片侧重写景,情由景生,末句又归结于情。下片则以叙事入笔,转而抒情,又继之以写景。情景交替出现,互相融合,空间上是由古到今,再由今到古,时空的转换主要通过“想”、“只道”、“芜城”等词加以提示。本词词意层层递进,犹如剥茧抽丝,缕缕不绝,借助于画面的今昔对比,在言与不言中表达了词人的难言之隐和对故国的怀恋,“疏快之中,自饶深婉”。清刘熙载《艺概》谓:“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味,倚声家得之,便超出常境。”
(二)情感表达诉诸理性
在情感抒发的表现形式上,元好问不是靠词的字面色调、音节韵味等感性因素来营造氛围,而是将情感表达诉诸理性,通过使事用典,利用意象将艺术感染力向内在拓展。如《玉楼春》:
惊沙猎猎风成阵,白雁一声霜有信。琵琶肠断塞门秋,却望紫台知远近。
深宫桃李无人问,旧爱玉颜今自恨。明妃留在两眉愁,万古春山颦不尽。
本词借咏史以抒怀,反映了词人内心的愁苦。词中白雁惊心,青山含愁,不仅是基于对昭君的同情,同时也是词人心态的外化。吊古与伤今,怜人与自伤,交织一体,不可分割。词中作者深广的忧愤和沉重的悲凉,不是靠夸张的叫嚣和感慨表现出来,而是借玉颜桃李、青山眉黛这些传统意象传达。在浏亮婉转的音节背后、绮丽温润的字面下,传达的是沉郁顿挫的情感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刚柔相济,变温婉为悲凉。特别是遗山晚年的作品,皆“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2]。
以豪放之济婉约,寓刚健于婀娜,形成独具一格的词风,这既是遗山词对宋词的学习和继承,也是遗山对词风发展的一个贡献。
二、雄浑深厚的词境
关于词的境界,清代论词名家都很重视,如王国维、况周颐皆在其论著中使用了“境界”的概念。金代元好问虽然在词论中没有直接使用“境界”这个概念,但其在词的创作中不自觉地继承了宋词在词意境方面的创造,并有所开拓,扩大了词的审美空间和审美趣味。
(一)雄伟壮丽的北国河山
唐五代词人囿于对词体的认识,词的审美空间一般安排在人造建筑空间,如画楼绣阁、庭中池畔,着意于享乐生活的描绘。宋词的审美目光已开始移注于自然山水空间、个体生活场景、人间悲惨世界与历史空间。元好问词除了继承宋词的审美对象之外,还开拓了两宋自然山水词的审美空间,将北国雄伟壮丽的河山引入读者的视野,在词中展现了一个有别于南方山水的北国风光。
元好问在自然山水词中纵情描绘北国雄奇壮丽、苍莽阔大的天地山川,在词史上留下不少风格雄浑、内容阔大的写景名篇。如在《水调歌头·黄河九天上》中以如掾巨笔描写了三门峡的雄奇景观,词中怒涛翻卷的黄河,在黄河激浪中巍然屹立的三门峡,均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又如其《水调歌头·滩声荡高壁》,以雄杰之笔,写阔大气象:
滩声荡高壁,秋气静云林。回头洛阳城阙,尘土一何深。前日神光牛背,今日春风马耳,因见古人心。一笑青山底,未受二毛侵。 问龙门,何所似,似山阴。平生梦想佳处,留眼更登临。我有一卮芳酒,唤取山花山鸟,伴我醉时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本词有序曰:与李长源游龙门。龙门,又称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市南二十五公里处,以有龙门山和香山隔伊河夹峙如门,故称龙门。龙门前水势峻急,水声郁怒,振荡高壁。面对如此雄壮的景象,词人用“滩声荡高壁”为首句,既用滩声先声夺人,点出龙门特有的景色,而且一个“荡”字如神来之笔,写出了龙门水急声喧的非凡景象。接着“秋气静云林”又用一“静”字描写出秋日风和、云止林静的特有画面。词人仅用短短的两句十个字,便形象地写出了龙门山水之胜。全词情景交融,令人荡气回肠。
遗山的其他自然山水词,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怀,都充满着一种不可抑勒的豪气,金石铿锵,落地有声。这些都有别于宋词中灵动秀美、充满诗情画意的南方山水,给词带来新鲜的气息。
遗山自然山水词中所展现的雄奇峻美的北方山川,是对两宋自然山水词审美空间的开拓。
(二)柔情中带骨气的审美情感
元好问现存的词中,情词约占六分之一,大部分继承了宋词情词的写法。但是,在抒写男女爱情的爱情词方面,元好问却独辟蹊径,开创了高远的情词境界。
唐以来至宋,爱情词一般只局限于描写个人艳情的狭小范畴。遗山的爱情词,突破了这个范畴,以讴歌那种轰轰烈烈的忠贞、纯洁爱情为主题,善于将阔大、深远的社会内容寄托于词境中,包举宏富,气格深厚,有别于两宋爱情词的柔肠软泪、苦恋悲思的情调。如其写情的名篇《双莲》,词人通过词序讲述了一个凄美悱恻的爱情故事:“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一对青年男女殉情而死,此后他们殉情的荷塘都开并蒂荷花。对于这样一个凄美的爱情,遗山在词中给予深情的咏叹,对这样一对以生命捍卫爱情的青年男女赋予了深刻的同情和哀怜。词中融入了唐人诗句,化用唐诗句意,使得这个爱情故事更显风情绰约、仪态高华。
如果说《双莲》是对男女青年纯真爱情的歌颂,那么它的姊妹篇《雁丘》则是对大雁坚贞爱情的歌颂及其对不幸命运的悲叹: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诗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该词有序,词人的情感为大雁殉情的事情所深深触动,于是驰骋其丰富的想象,运用拟人的艺术手法,紧紧围绕“情”字,对大雁殉情的故事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描写,塑造了一个忠于爱情的大雁的艺术形象,谱写了一曲凄楚欲绝、生死不渝的恋情悲歌,寄托了作者对殉情者的赞美与哀思。雁之殉情事实既悲壮又凄美,既美丽又缠绵,而它事实上就是无数青年男女为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而不惜献出青春甚至生命的投影。作者对雁的赞美,就是对无数青年男女坚贞、专一爱情的歌颂,也是对他们爱情遭受梗阻、破坏的叹息。全词以真挚的感情和沉重的笔调,寓缠绵之情于豪宕之中,字里行间跳动着清雄顿挫的高昂之音,使人读后自觉或不自觉产生荡气回肠之感,这是我们品读唐宋艳词时很难得到的审美感受。
元遗山笔下这种不惜生命、海枯石烂犹不悔的爱情,以及柔情中带骨气的审美情感,是唐五代两宋词史上罕见的境界。抒写人间真情而又不失雅正,是南宋张炎肯定遗山爱情词“模写情态,立意高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柔情中带侠骨的审美情感正是元好问对两宋词境的又一开拓。
三、善用领字发问
词的作法皆有一定的规定,遗山词在作法上大体依规定作词,但是在句首领字的使用上,却独树一帜,善于用领字发问,抒发词人的情感。
词中起句用领字,多是用于回忆题材或铺叙眼前景物,抒发感慨。而起句以领字发问,这在五代两宋甚至金元诸多词作中是较少见的。起句用领字发问,多是词人对所咏对象深有感触,情绪激动,要议论,要质问,酝酿再三,至不可按捺时便冲口而出。而发问的内容,往往是作者思考的核心问题,因此这一出口便如水决长堤,一发而不可收。遗山词便善于用领字发问来表达其强烈的情感,且看其两首经典之作《雁丘》、《双莲》。《雁丘》起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徒然发问,奇思妙想,破空而来。词人本要咏雁,却从“世间”落笔,提出“情是何物”这样一个似乎是人尽皆知的问题,事实上有许多人只是从形骸上看待男女之爱,并不懂得什么是“至情”。词人劈头提出这个问题,唤起了世人对“至情”的关注,震撼人心!这为下文写雁的殉情预作张本,同时也点出了贯穿全词的“情”字。古人认为,情至于极处,互相爱着的双方可以生死与共。情是何物而至于“生死相许”!这是大雁殉情一事引起的普遍的感叹,同时也是作者对“至情”力量的讴歌。在“生死相许”之前补上“直教”二字,补足了“情”的魔力。以此开篇,中心突出,气健神旺,犹如盘马弯弓,为下文雁之殉情蓄足了笔势。《双莲》同样以“问”字起句:“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一个“问”字,领起“莲根”、“莲心”两句。“丝”是殉情的青年男女爱情之“思”;“莲心”,亦即人心,他们生不得结为伉俪,被迫而死,其冤其苦可想而知。一“丝”一“苦”,是两句的核心,而且贯穿全词。劈头领字发问,表现了词人不可按捺的激动、愤瞒情绪。
金人入主中原后,北宋词和金词就有一个交会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交融与碰撞的过程。在这种交融与碰撞中,元好问以其博大的胸襟及勇于创新的精神,将宋词融会贯通,大胆创造,形成刚柔相济的词风,雄浑深厚的词境。在宋词基础之上的继承和创新,使元好问成为集金词之大成的大家,在宋词对金词的熏染以及金词对宋词吸纳过程中,起到了整合、创新甚至提升的作用,成为词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
[1]王兆鹏.唐宋词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况周颐.蕙风词话[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3]遗山乐府校注[M].赵永源,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4]傅璇宗,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刘锋焘.宋金词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I207.23
A
1008-178X(2012) 02-0093-04
2011-12-23
黄春梅(1978-),女,广东揭阳人,揭阳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系讲师,硕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