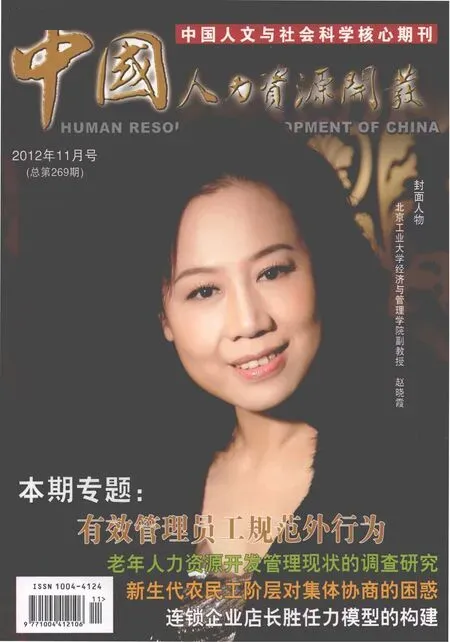试用期内辞职无须承担支付专项培训费用责任吗:兼论服务期与试用期之法律适用问题*
2012-01-28高建东刘金祥
● 高建东 刘金祥
■责编 王 晶 Tel:010-88383907 E-mail:wjtg17@163.com
董小姐于2010年3月进入上海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2010年3月至2013年6月的劳动合同,并约定试用期为6个月。同时,签订了《专项培训服务期协议》,协议中约定“公司根据员工的成长需要以及公司的相关培训计划为员工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员工接受公司提供的专业技术培训,应自觉遵守公司关于培训服务期限的规定,并按照规定的服务期限履行义务:服务期限从培训期结束次月起不少于一年”。协议中还约定:“若员工在服务期限未满的情况下提前向公司提出辞职的,则需要向公司支付为其提供的专项培训费用。”
2010年5月,董小姐在培训结束后到公司上班,但她发现公司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故在2010年6月中旬向公司提出辞职。公司不同意其辞职,要求她继续履行双方的劳动合同至服务期限结束,但她没有答应。董小姐离职后,公司要求她支付为其提供的专项培训费用共计一万元。董不同意,双方协商不成,公司即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她支付专项培训费用一万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劳动者试用期内辞职,用人单位可否要求支付培训费?
公司认为,双方签订了 《专项培训服务期协议》,协议中明确约定公司为董小姐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其应履行服务期义务。但现试用期还未结束,董小姐就已经辞职,其行为已经违反了双方所签订的《专项培训服务期协议》中关于服务期的约定。公司有权根据协议的约定,要求董小姐向公司支付为其提供的专项培训费用。
董小姐则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试用期内,劳动者只要提前三天通知用人单位即可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征得单位的同意;即使双方签订了《专项培训服务期协议》,其也无需向公司支付为其提供的专项培训费用。
仲裁庭认为,双方虽签订了《专项培训服务期协议》,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出资对职工进行各类技术培训,职工提出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如果在试用期内,则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支付该项培训费用。董小姐在试用期内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所以无需向公司支付为其提供的专项培训费用一万元①。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辞职,用人单位是否可以要求其支付该项培训费用。仲裁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认为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出辞职,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支付该专项培训费用。笔者对此裁决持不同见解。上述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是表面想象,深入剖析其实质则是劳动法上之试用期与服务期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试用期和服务期之法律适用的问题
有关服务期的规定,我国法律、法规仅见诸《劳动合同法》第22条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6条。由于立法技术的不足或者法律规范的自身局限,在有关服务期的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法律调整的空白区域,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局面。
关于劳动者试用期内辞职,用人单位是否有权要求其支付专项培训费用的问题,我国法律、法规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仅存在于原劳动部先前的规范性文件之中。原劳动部于1995年10月答复原浙江省劳动厅《关于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依据问题的请示》时,曾在复函《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依据问题的复函》(以下简称“原劳动部文件”)中指出:“用人单位出资(指有支付货币凭证的情况)对职工进行各类技术培训,职工提出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如果在试用期内,则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支付该项培训费用。”
该条文发布之时所依据的《劳动法》与当前的《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的规定,尽管有部分内容不一致(主要是试用期的期限和试用期内辞职提前通知期限)而适用于后者,但是试用期本身的性质及其意义未发生任何变化。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②这一规定,是否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有关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唯一且充分之程序?现有法律、法规对此尚无明文规定。但是从文义上理解,劳动法上之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并无其他程序之限制,原劳动部该文件与《劳动合同法》关于服务期的规定亦无任何明显冲突之处。
在《劳动合同法》或者《劳动法》尚无明确规定的条件下,能否当然适用原劳动部文件?原劳动部文件的规定是否有效?笔者认为,不能对此简单作出结论。欲解答本案中的法律适用问题,首先应当明确试用期与服务期在劳动法上做何界定;其次,两者在法律适用上是否遵循了法律的一般原理;最后,在上述法律适用中体现的法律价值,是否符合社会之公平正义。下文将循此思路展开分析。
二、劳动合同之试用期与服务期协议的法律界定
关于劳动合同的试用期,尽管有不同的理解,但其涵义则基本一致。笔者从彰显试用期法律特征的角度予以说明之:试用期主要是指在劳动关系建立最初阶段,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约定依法对劳动关系要素进行考察(主要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考察)而使得劳动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一段期间。这段不稳定的期间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是劳动合同的特殊条款。所谓劳动关系不稳定,主要是在劳动法上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比试用期之外的期间要更加灵活。《劳动合同法》对试用期中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用人单位针对“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劳动者,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也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这些单方解除的条件在试用期之外的期间则不能适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订立了期限为3年以上(40个月)的劳动合同,试用期定为6个月,并未违反《劳动合同法》关于试用期的规定。董小姐在试用期内提出辞职,只需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即可解除劳动合同,这一点并无不妥。
服务期一般是指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劳动者在特定条件下承诺为用人单位工作满一定年限的特定期间。服务期协议存在的基础是双方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劳动合同。但是订立劳动合同并不必然要约定服务期。约定服务期,往往以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供特定条件为前提。这种特定条件往往是以用人单位先履行或者承诺履行劳动合同以外的义务,并非是劳动合同内的一般劳动条件。在此条件之下,对劳动者履行劳动合同的期限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制,以违约金的法定形式保护了用人单位的利益。因此,服务期一般被认为是用人单位“用以保护自身正当利益的工具”。
服务期协议与劳动合同存在一定联系,但并不必然被劳动合同所包含。笔者认为,服务期协议是当事人双方订立的独立于劳动合同的民事契约。首先,从立法导向上看,基于“强资本弱劳工”之现实写照,劳动合同的立法侧重于劳动者利益的保护;而服务期协议注重双方利益的平等保护,其设立初衷是为了避免用人单位之利益受损。其次,从合同成立的前提上看,劳动合同的成立与否并无其他前置条件,只需双方有建立劳动关系的意向即可;而服务期协议则不然,其成立往往以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特定条件为前提,未提供特定条件而约定服务期则显失公平,有悖于权利义务对等之法律原则。最后,从法律责任来看,违反劳动合同义务的法律责任,主要是针对用人单位设定的,需要承担劳动法上之民事赔偿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而违反服务期协议的法律责任,主要是针对劳动者设定的,需要承担违约金责任仅仅是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试用期是劳动合同期限的一部分,而服务期协议则是独立于劳动合同期限的民事契约。尽管服务期协议与劳动合同期限会发生交叉或者重合,但从根本上讲,劳动合同与服务期协议是相互独立的不同性质的合同。
三、本案之法律适用意见
1.基于合同性质的法律适用
本案中的用人单位与董小姐约定为其提供专项出资培训,订立服务期协议。该协议建立在用人单位提供专项培训费用、董小姐接受专项技术培训之基础上,并对服务期限进行了约定。该服务期协议符合《劳动合同法》有关服务期之规定,已经成立且合法有效。董小姐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不不妥,但是因此而导致违反服务期协议之约定则是另一个合同责任承担的问题。该服务期协议并不必然包含于劳动合同之内。因此,董小姐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之行为虽然并无不妥,但是其解除服务期协议的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此,根据两者合同性质之不同,原劳动部文件认为用人单位不得要求劳动者承担违约责任即支付该项培训费用,并不合理。
2.基于效力位阶的法律适用
与劳动部行政规范性文件相比,《劳动合同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法律的制定主体,均为行使最高立法权的国家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其可行使国家最高立法权。两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其效力位阶仅次于宪法。劳动部作为国务院的行政部门,《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依据问题的复函》其效力是法律、法规、规章之外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明显低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相比较而言,前者属于“上位法”,而后者属于“下位法”,在两者发生冲突之时,理应适用效力位阶明显较高的《劳动合同法》。仲裁庭在本案中选择适用了与《劳动合同法》立法精神相悖之效力位阶较低的原劳动部文件,其法律适用不当。
3.基于公平责任的法律适用
《劳动合同法》第22条对服务期做了三项规定:(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法定权限;(2)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责任承担;(3)劳动者在服务期内劳动报酬的调整。此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6条对服务期违约责任的承担又作出了补充性规定。《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服务期违约的责任承担以违约方承担责任为主且兼顾公平,其归责原则体现了债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其原因是劳动者作为违约一方自身存在过错。在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下,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属于违反服务期的约定,其原因是用人单位存在过错。而在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法定情形下,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不属于违反服务期的约定,而此时劳动者作为过错一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有关服务期之违约金数额的约定,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也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应分摊的培训费用,这体现了违约金承担的公平责任原则。
本案中,董小姐以“工作并不适合自己”为由,在试用期内提出辞职,只需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即可解除劳动合同。这是其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的法定权利。但是,由于服务期协议是与劳动合同性质不同的民事契约,责任的承担并不完全一致。本案中的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和服务期协议过程中并无过错,董小姐不具备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之法定情形。作为服务期协议违约的一方,董小姐应当承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责任,向公司支付为其提供的专项培训费用一万元。如此,与《劳动合同法》之立法精神乃至法治精神相符。
注释:
①该案例源于2011年5月21日《劳动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试用期内辞职无须承担支付责任》,笔者对此文之案例解读持不同观点。
②根据《劳动法》第32条的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7条,两者相冲突而适用后者。原劳动部《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依据问题的复函》根据《劳动法》第32条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有关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约定应符合上述规定”。结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按其本意而言,“上述规定”应理解为《劳动合同法》第32条"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之规定,而未予以考虑其他因素。
1.王全兴:《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郑尚元主编:《劳动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成曼丽、王全兴:《服务期的法律定性和法律后果》,载《中国劳动》,2006年第2期。
4.郭文龙:《服务期制度是对现行劳动合同制度缺陷的合法校正》,载《中国劳动》,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