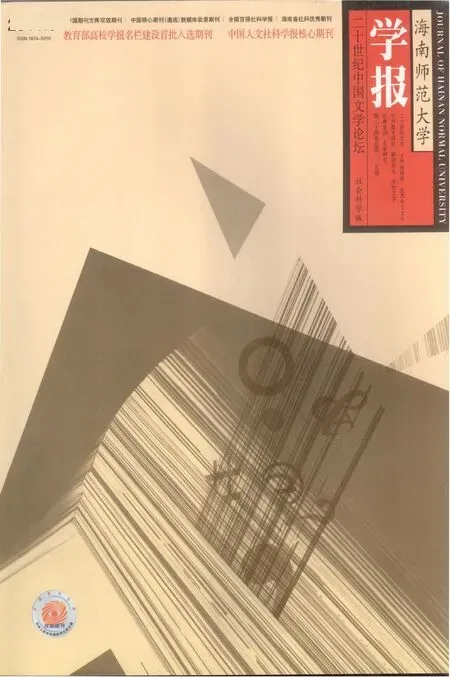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以《公案簿》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2011-12-27蒲晶,甘奇
蒲 晶,甘 奇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
——以《公案簿》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蒲 晶,甘 奇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她包括了中国去的新客、与华人通婚的番人、华人与华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和华人与番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吧城华人社会中,女性的观念和地位等都与中国国内有很大不同。文章根据对《公案簿》中相关案件的分析,来揭示这一特殊的群体。
吧城;华人女性;《公案簿》
一 吧城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吧城公堂
吧城即巴达维亚,1619年荷兰攻占印尼雅加达后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中国人称之为吧城或者吧国。中国古代史籍中称之为噶喇吧。
据《海岛逸志》记载,“华人自明永乐王三保、郑和等下西洋采买宝物,至今通商来往不绝,于冬至后厦开棹,廿余日可达。吧城连衢设肆,夷民互市,贵贱交易,所谓利尽南海者也。富商大贾,获利无穷……”[1]可见华人去吧城很早就开始了。明清两朝,在政治和生存等多种原因的驱使下,大量的闽粤琼人移民海外,其中就有很多人移民到了吧城。
荷兰攻占吧城后,当时居住在吧城的华人已经很多,为了便于管理华人,荷兰东印度公司用以华制华的手段,在华人中推行甲必丹制度,1619年首任甲必丹①也称甲必丹大、甲大甲太、甲丁,荷兰语Kapitein,本意是上尉军官,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始设华人甲必丹,以管理华人民事事务,1837年陈永元加“玛腰”衔后,一些雷珍兰也加了甲必丹衔。(简称甲大)苏鸣岗(明光)正式上任,1742年林明光任甲必丹时正式设立了专门处理华人事物的半自治机构——巴达维亚华人评议会(De Chinese Raad of Batavia),华人称为吧城公堂或者吧国公堂(Batavian Kong Koan)。
据吧城公堂内悬挂1861年与1893年木刻碑记云:“公者平也,平公察理;堂者同也,同堂论事。情有真伪,事有是非,非经公堂察论,曷以标其准!”“公堂者,所以奉公勤民,凡有利于公者,无不咨而谋之,举而措之,以笃庆壬林也。”简言之,公堂即同堂公平议事,是唐人议事厅,俗称为理事。海外唐人②唐人即华人。理事自有唐人聚居之后就已产生,是唐人谋求生存处理内外事务的自发组织。但公堂不同于海外唐人自己的理事组织,而系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管辖下并委任唐人首领以唐人律法与习惯处理唐人自己事物的机构。[2]
1742年,“红溪惨案”后第三年,吧城总督Van Imhoff决定恢复吧城的甲必丹制,甲必丹林明光买了闽人黄銮光的房屋作为甲必丹办公场所,名为“吧城公堂”,地址在吧城城北。但华人大多住在城南,为办事方便,1809年,甲必丹陈炳郎在城南就近备一公馆,作为日常办公之用,而重大事务仍在城北公堂举行。高长宗③1821-1828年任吧城甲必丹。任甲必丹时,在城南中港仔修了一座公馆,所有公事皆在此公馆举行,高长宗离任后依然如此。陈永元任玛腰后用公堂的资金买下了高长宗公馆,作为公堂日常办公之地,城北的公堂逐渐废弃,而城南的“公馆”则变成了“公堂”。
公堂的官员开始只有甲必丹一人,随着华人人口的增加,设立了雷珍兰④荷兰语Luitenant,意为中尉军官,1678始设,辅助甲必丹处理华人事务。一职协助甲必丹工作,并设立了达氏⑤荷兰语Soldaat,意为差役。一名。后来随着华人义冢、救济院、义学等机构的相继建立,逐渐增加了朱葛礁、①公堂书记官,荷兰语Secretaris,1750年始设,开始时只有一名,1766年增设一名副书记官,以后遂称书记官为“大朱”,副书记官为“二朱”。土公、②荷兰语Begrafenismeesters,管理丧事的官员。武直迷 、③荷兰语Boedelmeester,1690年始设,财产管理官员,负责救济院和遗产。默氏④荷兰语Wijkmeester,区长、街长。1655年始设,负责各华人街区的治安。等官职。
吧城公堂的主要职责是代表殖民地政府⑤殖民地政府1799年之前指荷兰东印度公司,1799年之后指荷印殖民政府。管理吧城华人,审理华人之间的民事诉讼案件,并定期向殖民地政府报告华人社区的情况。如果民事案件涉及的钱财金额过大,则需转交殖民地政府法院审理。此外,公堂还需审理殖民地政府法院委托审理的案件,如《公案簿》第四辑中出现了大量的承挨实嗹⑥挨实嗹:荷兰语,英语Resident,驻扎官,指东印度群岛各地荷兰商馆的代理人,其职责除了收购土产货物、推销产品、实行专卖之外,还可以代表公司同当地王公进行谈判及实施政治阴谋。1816年,荷兰人重新恢复对东印度的统治后,依据莱佛士改革的内容,吧城成为荷属东印度的一个州,行政长官是驻扎官,此外驻扎官还兼有检察官和法官的职责。命,承兰得力⑦地方法院。命。
二 《公案簿》的由来
吧城公堂从1742年始设到到1970年代取消,中间跨越了230多年时间,期间留下了大量公堂档案,现存世的档案涵盖了从1775年到1950年170年的时间(缺1791年2月8日之后到1824年6月25日之前的档案),现存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的图书馆。这批档案主要包括通告簿、公案簿、户口簿、新客簿、清册簿、婚姻簿、冢地簿、寺庙簿、金德院簿等卷册,以及为数众多的由公堂开俱的各种证件文书、收据、呈文、批复等文件的正本和副本,内容涉及有关吧城华人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司法、宗教以及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多数以中文书写,少量为荷兰文和印尼文,总字数约有2000万字。其中《公案簿》的内容,从1787年开始到1964年结束,计32卷,600万字,是公堂审理、判决华人居民诉讼案件记录的謄本,占公堂档案的1/4。其中1787-1920年《公案簿》用中文书写,共28卷,1920-1940年《公案簿》用印尼文书写。涉及有关吧城华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印尼华人社会不可多得的资料。[3]55
《公案簿》所记载从时间跨越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荷印殖民政府统治时期、莱弗士复兴时代、印尼民族觉醒时代、日占时期、民族独立运动时期、苏加诺时代和苏哈托时代。所以,“对记录这一时期的原始档案——《公案簿》加以考察和分析,一方面能使我们了解一个处在多种变革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行政管理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殖民地当局对华人移民及华人社会的政策演变及对当地华人社会的影响”。[3]55《公案簿》所载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有关华人的案件的审判记录;二是公堂的决议和重大事件的记载。按其性质可大致分为:经济类案件,婚姻家庭类案件,社会治安类案件和公堂规章及其他类型案件。几乎涵盖了吧城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吧城华人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公案簿》中所记载的每个案件第一部分记载审案的时间和出席的官员以及审案地点(有时在公堂,有时在甲必丹府),第二部分是原告被告双方和证人的姓名、控辩双方的供词、审问内容和最后的判决,第三部分是出席官员的签名。
三 《公案簿》中相关个案的分析
华人社会中的女性是个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按照吧城相关法律的规定,同中国移民结婚的当地妇女及其所生的子女,在人口分类时是不加区别的视同“中国人”的,而同荷兰人结婚的当地妇女则仍从属于原来的人口分类,不加以改变,其所生的子女归为“欧亚混血后裔”,不得视为“荷兰人”。根据这一规定,吧城的华人就包括了中国去的新客、与华人通婚的番人以及华人与华人或者与番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
《开吧历代史记》中记载:“康熙三十八年已卯,即和1699年正月,唐船来吧,有王界夫妇,潜搭此船来吧,登岸时唐番俱见,此信播扬通吧,直至大王⑧即巴达维亚总督。耳边。王界妻郑氏,伴态生成,仪范端庄,衣服与吧人迥异。大王询知备细,切意欲观中华妇人,即令人来请,王界夫妇齐到王府内相见。”[4]可见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大多是当地的土著女子,而从中国移民去的女性华人则较少。
《公案簿》第一辑,“甲大府中嘧喳唠。杨甲、陈甲当事。丁十月十三日,和1787年11月22日,拜四。雷珍兰高根官在吧⑨吧即吧城。做遗嘱字”[5]8条中,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高根官所里的遗嘱中,其家庭成员共有19人,涉及到的女性共有16人,除其母王连娘居住在厦门外,其余15名女性均住在吧城,分别是李荫娘、陈审娘、郭瑞娘、黄志娘(万兰人)、春梅(武讫人)、吗咚(巴厘人),春桂(逞罗人)、冬菊(逞罗人)、当寅(逞罗人),罗果(武讫人)、高清娘(已出嫁)、高意娘、高添娘、高变娘、碧桃(本地人)和另一个己忘记名字的人。其中李荫娘和已忘记名字者是其故妻,陈审娘、郭瑞娘、黄志娘是其现妻,春梅、吗咚,春桂、冬菊、当寅,罗果是女婢出身,○10高清娘、高意娘、高添娘、高变娘是女儿,碧桃是女婢。高根官有1妻6妾1婢共8人,是非华裔血统的人,其中1妻6妾被认为是华人。女儿高意娘系罗果(武讫人)所生,这种由
○10即妾。华人和当地土著女子所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在印尼被称为“帕拉纳坎”,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被称为“峇峇”,在菲律宾被称为“梅斯蒂索”。此案中非华裔的女性共有9人,比华裔女性还多2人。
高根官任吧城雷珍兰13年,其名下有大量的财产,在吧城是比较富裕的华人,高根官先后有6妻(3人已亡,1人出走,实际上只有2人在其身边)6妾。由此可见,一夫多妻制在吧城富裕华人中应该大量存在。
与中国国内相比,华人在遗产继承上吸收了当地(实际上是荷兰)遗产继承的办法。在中国国内,并没有立遗嘱的习惯。人死之后,如果儿子年纪尚幼,那么他的财产便由其妻代为掌管,如果其妻改嫁,便交由本族亲长掌管,待其子成年后,方交予其子掌管。而立遗嘱则是依据荷兰惯例。但由于高根官在遗产分配上的不公平,导致其死后家庭矛盾不断,这是后话,此处不提。
在吧城华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比中国国内也要高出一点。下面试举几例予以说明。
《公案簿》中涉及华人社会中的女性的案件较多,大概可分为两类。
第一是财务纠纷(主要是遗产争夺纠纷)。如《公案簿》第一辑中,“黄甲、林甲当事。戊(戊申,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五日,和1788年3月12日,拜三。廖新娘叫董祖韵”[5]31一案。
廖新娘供谓:“氏夫董君去岁正月初二日(1787年2月19日)弃世,做字付氏挂沙,董標贵挂沙惹难,氏夫有唐山子名董祖韵,向氏云欲回唐,要取多少银。氏因无钱,转向氏母借来钱叁百五拾文,将钱尽交祖韵收去。后来祖韵并无回唐,氏又因家母在万丹染病,即往省视,而祖韵将氏家内物器尽皆搬出。”
召问董標贵曰:“董君遗嘱字财产做几分均分?”答曰:“作对半均分,一半在唐,一半在吧”。
因董祖韵未到,当日公堂并未做出判决,在一个星期后,“黄甲、林甲当事。戊(戊申,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和1788年3月19日,拜三。廖新娘叫董祖韵”[5]33中,董祖韵因“财业分不平,挂沙人①遗嘱见证人。不肯的栖,②检查、察视。是以搬去物件”,公堂问廖新娘“丈夫初故,何无的栖遗业?”廖新娘回答说“为病缠身,是以未及暇也。”后董祖韵出示了其父所留的挂沙字,③即委托书。其父将遗产“作三分均分:一分遗唐山三男,一分遗在吧二男,一分遗吧妻”。
吧城华人大都有两个家,在中国国内一个,在吧城一个,这种现象被称为海内外两头家。在本案中,国内的三个儿子获得父亲1/3的遗产,廖新娘获得了亡夫1/3的遗产,相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儿子继承父亲遗产之后,母亲便丧失管理权,吧城华人对于遗产继承上,显示出与中国传统社会很大的不同。
第二是家庭纠纷(包括因夫妻纠纷、偷情和私奔案件、离婚案件)。
夫妻纠纷的主要原因有:家庭贫困导致夫妻不睦,妻子遭受家庭暴力,丈夫抛弃妻子,丈夫另结新欢,老夫少妻妻子嫌弃丈夫等。
通奸案件在《公案簿》中也占很大一部分比例,通奸原因主要有:丈夫收入太少,丈夫另结新欢,老夫少妻妻子嫌弃丈夫等。

1787-1790吧城华人妇女与婚姻案件统计图
私奔案件分为妻子私奔案和女儿私奔案。妻子私奔的主要原因基本与通奸案相同,而女儿私奔最主要的原因是被人诱拐。
离婚的主要原因有结婚多年无子,妻子出轨,家庭贫困导致夫妻不睦,妻子遭受家庭暴力,丈夫抛弃妻子,丈夫另结新欢,老夫少妻妻子嫌弃丈夫等。而离婚案件则是越来越多,比如1849年一年当中就有19起、21次离婚案件,而1849年3月16日当天就有6起离婚案件。
如《公案簿》第六辑中:
和1849年3月16日,拜五,玛腰府中嘧喳唠。值月公勃低陈甲启淮官、吴甲昭阳官。黄甲燎光官不在议,张谨娘、黄亚三离婚一案。
张谨娘叫伊夫黄亚三,据云:“氏与夫结发五年,生下一儿不育,④不能存活。讵料夫并无照顾衣食资费,乞判分离。”
“吊讯亚三,供云:‘晚於丁年(丁未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回唐,及戊年(戊申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到吧,宛如新客一般,而妻欲取费甚多,晚自顾不暇,安能肆其所欲?兹妻若要分离,愿从其便。’台劝二比须相和好,奈谨娘坚执不肯,决要分离。职等未敢擅夺,将情申详公堂大嘧内裁夺。
列台复讯张谨娘、张亚三,供如公勃低所详,二比决要分离。台曰:‘《交寅字》⑤即结婚证。何在?’二比答曰:‘已经失落无存。’
公堂准其分离,各花押为炤。”[6]
在本案中,妻子张谨娘因为丈夫黄亚三不能负担自己和儿子的生活费用,请求离婚,黄亚三回唐来吧之后,穷困潦倒,像他自己所说的“自顾不暇”。公堂调解无效,便准双方离婚。中国传统社会中,讲究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因为家庭经济状况不佳而离婚基本上不可能。而本案中,张谨娘是主动要求与黄亚三离婚,是张谨娘“休”掉了黄亚三。由此可见,在吧城,虽然未做到男女平等,但妇女的地位较中国国内还是比较高的。
四 结语
综上所述,依据吧城法律的规定,华人包括中国去的新客、与华人通婚的番人以及华人与华人或者与番人通婚后产生的第二代土生华人。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女性也基本上涵盖了以上几种人群。吧城华人社会中,一夫多妻制在富裕华人阶层大量存在;女性可以继承亡夫的一部分财产;女性的忠贞观念不及中国国内,通奸、私奔和寡妇再嫁在吧城比较普遍;离婚率要远远高于国内,男尊女卑的现象仍然存在,但女性的地位较中国国内高。
[1](清)王大海.海岛逸志[M].香港:学津书店,1992:4.
[2]〔荷〕包乐史.吧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75-77.
[3]聂德宁.吧国公堂档案之《公案簿》述略[J].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2(3).
[4]许云樵.开吧历代史记[J].南洋学报,1953,第九卷第一辑:35.
[5]〔荷〕包乐史,吴凤斌.《公案簿》第一辑[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6]〔荷〕包乐史,刘勇,聂德宁,侯真平,吴凤斌.《公案簿》第六辑[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37.
Femal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Batavia——A Case Study ofGong An Bu
PU Jing,GAN Q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571158,China)
Femal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Batavia are of a very special group,which includes new migrants from China,indigenous persons wedded to Chinese,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ranakans,descendents either of marriages between Chinese there or of marriages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genous persons.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Batavia,the concept and status of women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women living in China’s mainland.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this special group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relevant cases inGong An Bu.
Batavia;femal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Batavia;Gong An Bu
K342.41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674-5310(2011)-05-0060-04
2011-06-10
蒲晶(1988-),男,陕西宝鸡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南海区域历史文化;甘奇(1987-),男,河南驻店人,海南师范大学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
(责任编辑:李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