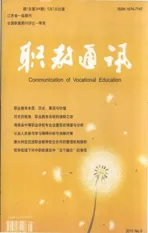围墙与立交桥
2011-02-20臧志军
臧志军
围墙与立交桥
臧志军
也许是出于天性,人类总是倾向于把自己封装在一个又一个有形的空间(如房屋、汽车)或无形的组织(如工厂、学校)中,因此,整个世界就被一道道有形或无形的围墙给隔开了。为了实现交流,人们经常会在墙上开门或窗,但门窗的出现并非为了墙的隔绝功能,因为生活常识告诉我们,门窗最常见的状态是关闭而不是开放。
为了实现沟通,人们设想过很多办法,古代的崂山道士的解决方案是学习穿墙术,现代的肖申克则通过挖地道,而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德国人所做的把墙推倒。在故事里,崂山道士是失败了,这大概隐喻着人在墙面前的渺小,以一已之力对抗一堵墙结果只会是撞得头破血流;肖申克就聪明多了,既然无法正面对抗,我就绕着走;柏林墙的倒掉则说明人们对墙这种东西的厌恶,也说明墙也是可以被彻底推倒的。
同有形的围墙一样,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之间的围墙也是各种信息流、知识流、资源流可以到达的最远边界。同样,为了实现沟通,人们也会对围墙的存在咬牙切齿,想尽各种办法挑战它。
在职业教育领域,也存在无数的围墙:职教与普教之间、中职与高职之间、不同学校之间、不同专业之间、不同年级之间……在这些墙的后面,大致站着两种人,一种是管理者,也就是围墙的修建者,另一种是被管理者,是一群对墙既爱又恨的人。随着管理分工的不断精细化,管理者发现如果不为自己的管辖范围设定一个边界将会造成与其他管理者的冲突,所以他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围墙的修造者,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不就乱套了”;而那些被管理者则是一个矛盾的群体,他们在受到威胁时希望围墙的保护,在感到被限制时则希望围墙的倒掉。
因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落差,在职教界,存在一种“立交桥共识”。人们一般设想通过架设超越高墙的“立交桥”形成不同教育结构间的互通:为中职学生搭建一座桥,好让他们能越过中职与高职之间的围墙,进入到高职;为职业学校学生搭一座桥,好让他们能越过职校与普通高中之间的围墙,进入到普通学校;为不同学校的学生搭一座桥,好让他们能越过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围墙,进入到其他学校学习……
显然,我们在学习肖申克的越狱方法,我们不想打破原有结构,甚至都不敢在墙上开一扇窗,只是想办法绕过现有障碍,我们与肖申克的唯一不同在于他只能在地下偷偷地干,而我们可以公开地在天上施工。
在去年的这个栏目里我们曾经讨论过,“立交桥”不仅隐喻着沟通,更表示规避,是一种在不打破原有结构的基础之上的沟通方案。在这一点上,“立交桥”的比喻是成功的,因为在现实中我们确实只看到了一条条面向特定群体的通道的建立,而不是不同教育结构之间障碍的消失。中职学生可以“三校生”的身份参加高考,进入高职,但比例受到一定限制;全国许多地方举办了五年一贯制的高职(有的地方采用的是中高职贯通的方式),但前提是必须是中高职都开设的专业;高职学生有专升本的通道,但似乎障碍不少……
就“立交桥”而言,这些桥已经形成了某种体系,已经有了四通八达的趋势,职业教育不可谓成就不大;但就围墙而言,一道道高耸的墙仍然矗立,能够走上“立交桥”的并不是所有学生。
我们不要忘记,在规避之外还有一种沟通的方式:把墙推倒。问题是,中高职之间、普职之间、不同专业之间能够没有围墙吗?在澳大利亚,中职已经很少以学校的面貌存在了,它可能是TAFE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能以社区教育中心的形式出现;在美国,众所周知的是其综合中学的职业教育架构。也就说,模糊不同教育结构之间的边界并非不可能。也许把墙推倒还难以做到,但应该看到墙的倒掉可能是一个趋势;也许西方国家的解决方案不适合我们,但我们不能完全无视这种可能性。
如果继续追问,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不同教育结构之间的边界可以被模糊,而在中国好像还是很遥远的事?这个问题的回答只需要考察一下双方的不同用语就知道了。中国人用“衔接”、“贯通”来表示不同教育结构间的连接,而西方人更喜欢用“过渡”(transition)。原来,我们重视的是通道,他们关注的是学生;我们的眼里是管理者如何管理,他们的眼中是被管理者如何发展。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墙的存在意义重大,从被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能够促进人的发展的制度才是好制度。
目前,中国教育再次扯起了改革大旗,我却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疑问:三十年来改革一直是教育发展的主题,为什么现在又提出了改革的任务?是说以前的改革不成功吗?还是说以前的改革造成了新的问题,又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也许兼而有之吧!希望设计这次改革的时候眼光长远一点,至少在中高职协调发展上不要为职业教育的后续发展设置更多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