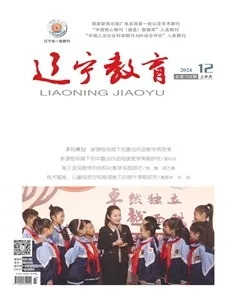新课程视域下初中鲁迅作品阅读教学策略研究
2024-12-27郭向东
摘要:新课标视域下的语文课程围绕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展开,强调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这与鲁迅作品中的“立人”思想是一致的。教师应充分挖掘鲁迅作品中的育人价值,将其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深度融合。新课标视域下的鲁迅作品阅读教学,可以从“以主问题为切入口,激发学生持续探究的兴趣;读写结合,引领学生深入解读文本;类文联读,拓展学生思维广度”几个方面入手,从而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关键词:新课标;初中语文;鲁迅作品;阅读教学
鲁迅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奠基人,其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鲁迅作品的教学价值和文化价值难以充分地体现出来。作者被神圣化,作品被政治化,教法、学法单一化,导致学生对学习鲁迅作品产生畏难情绪。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更好地挖掘鲁迅作品的育人价值,教师应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通称“新课标”)为导向,在教学实践中探索科学有效的教学策略。
一、以主问题为切入口,激发学生持续探究的兴趣
所谓“主问题”,就是语文阅读教学中能从课文整体的角度或学生的整体参与度上引发思考、讨论、理解、品味、欣赏的重要提问。鲁迅的作品文质兼美,各方面的解读细致入微。教师阅读的文献越多,课堂上越难以取舍,甚至觉得哪一句话都可圈可点、不容错过,课堂容易出现碎问碎答的现象。语文特级教师余映潮提出的主问题阅读教学设计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方法。主问题可以向下拆解成若干个多层次、多角度的子问题,也可以向四周延伸成若干个比照式、烘托式的辅问题,关键是这个主问题要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能激发学生持续的探究兴趣,能成为一节课或一个板块的课堂活动线索。
语文名家黄厚江的《孔乙己》教学案例是语文教师学习的典范。课上,黄老师先从阅读体验入手,问学生:孔乙己这个人物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有的学生说是“脸色”,有的学生说是“长衫”,有的学生说是“语言”。在肯定及评价学生的答案之后,黄老师提出第二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文中对孔乙己哪一方面的描写最多?”这两个问题作为辅问题,既是主问题的分析支架,又自然地引出了主问题:作者是怎样通过对孔乙己手部的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揭示文章主题的?通过分组活动,学生在文中找到了描写手部的动作和形状的句子。接着黄老师提出第一个子问题:“文中对手部动作描写最突出,大家看看哪个动作最能体现孔乙己的性格?”有的学生从“排”字上分析出孔乙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黄老师又提供了一个问题支架:“他是跟哪些人在一起喝酒?”(短衣帮)从而分析出“排”字还体现出孔乙己炫耀得意的心理。学生又找到“敲”和“罩”,分析孔乙己的自傲与贫穷,注意到两个动词前后对比。黄老师顺势追问:“还有哪两个动词可以联系起来看?”于是学生又找到了“排”和“摸”,通过前后的变化与反差,黄老师提出并分析出孔乙己由自命清高到自感卑贱的心态转变。黄老师提出第二个子问题:“你们觉得最能表现人物命运的动作是哪一个动词?”学生齐声回答是“走”,因为孔乙己被打断腿,用手走路,说明他命运悲惨。在被人们嘲笑中走下场,说明他社会地位低微。黄老师再深入挖掘:“能不能把‘走’换成‘爬’呢?”以简笔画为分析支架,引导学生区分本质差别:“爬”是手脚并用,“走”是只有脚动,而孔乙己则是只用手;“爬”的时候身体趴下,孔乙己用手“走”则是努力挺直身子,保持着读书人的清高和一点可怜的尊严。本节课中,黄老师以手为切入口设计主问题,以进阶式的子问题启发学生深入文本,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文本、学生与作者的多重对话,从孔乙己的畸形动作中挖掘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用黄老师的共生课堂理论来说,就是“一个点,一条线,分层推进,多点共生”。
经典作品都是挖掘不尽的宝藏,鲁迅作品更是这样。同样是教学《孔乙己》一文,欧阳代娜先生以“笑”为切入口,语文名师徐杰以“长衫”为切入口。他们以不同主问题提纲挈领,组织课堂活动,都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有时课堂上可能会出现主问题之外的旁逸斜出,教师要根据具体情境,顺势引导,既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又不脱离课堂教学的主线。钱梦龙先生在教授《故乡》一课时,有的学生提出:“鱼怎么会有青蛙似的两只脚呢?”这个问题中钱先生顺势引导:“是啊,鱼怎么会有两只脚呢?你们见过吗?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书上怎么说?”学生恍然大悟:“闰土见多识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儿”。在教授《社戏》一课时,笔者以书后思考与探究第三题为切入口,设置主问题:“豆儿是很普通的豆,戏也是让‘我’昏昏欲睡的戏,但是文章最后却说是‘好豆’‘好戏’,对此你是怎样理解的?”学生围绕“好”字展开探究,既然“豆”和“戏”都并不好,那么到底什么好?学生找到了景色好、民风好、人情好……忽然有个学生提出问题:“双喜叫阿发的时候,为什么前面有个阿阿”?这个问题瞬间引起了其他学生的兴趣,有的学生说是对阿发亲切的称呼,有的学生说是看到罗汉豆时的感叹,还有的学生说是双喜想叫“阿发”但是犹豫一下叫成了“阿阿”……课堂气氛非常活跃。为了不打消学生的积极性,师生一起分析理由。称阿发为“阿阿”,似乎说不通,如果想用叠词亲切地称呼阿发,应该称为“发发”才对。感叹也说不通,双喜又不是没有见过罗汉豆,不至于大惊小怪。犹豫似乎有理,为什么呢?学生继续探究,此处双喜内心犹豫,偷阿发家的罗汉豆是最佳的选择,由阿发提出来偷自家的罗汉豆,是最佳中的最佳。但阿发会怎么决定?根据阿发淳朴憨厚的性格,双喜猜测阿发应该会选择偷自己家的罗汉豆。双喜问阿发偷哪一边的,虽撇开了自己的责任,但又觉得自己有点狡黠,把球踢给了阿发,感觉对不起朋友,稍一犹豫“阿发”就说成了“阿阿”。结果却超出了他的预料,阿发并没有“高风亮节”地宣布偷自家的罗汉豆,“且慢,让我来看一看吧。”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之后才说“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阿发的表现打消了双喜的歉疚,阿发的憨厚超出想象,他没有按照罗汉豆的主人来选择的,而是按照罗汉豆的大小来选择,完全是为了小伙伴吃得好,没有考虑是谁家的罗汉豆,丝毫没有因为自家的豆在选择之列而为难。况且一声“且慢”,让阿发成了偷罗汉豆的领袖,“一声答应,大家便散开在阿发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抛入船舱中”。小伙伴们全体响应更给了阿发领导者的感受。双喜此时应该是内心释然的,之前是自己多虑了。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主问题的展开,教师顺着一个易被忽视的词语引领学生分析双喜的细心周全和阿发的淳朴憨厚,最后归结到江南水乡的“人情好”上,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回应主问题。
不同的切入口、不同的主问题、不同的引领、不同的活动,教师带领学生从不同的原点沿着不同的路径欣赏不同的风景。值得注意的是,以主问题为切入口,并不意味着以提问为课堂组织形式。主问题引领的是课堂实践活动,而不是简单的几个问题的组合。其显著特点是学生整体性参与,学生在具体真实的情境中完成具有挑战性、探究性、持续性的系列任务,主问题是将这些任务串起来的红线、提起来的抓手,能使整个课堂呈现线性结构或立体交叉结构。
二、读写结合,引领学生深入解读文本
读写结合是提升学生语文素养的有效方法。经典作品无疑是写作学习的典范,鲁迅的作品更是开展阅读和写作活动的源头活水。当然,读写结合不是简单地在阅读课上写作,而是使阅读与写作水乳交融,在阅读中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在写作中促进学生对文本的深入理解,从而实现读写共生。
鲁迅的文章中有很多经典的句式,比如“不必说……也不必说……单是……就……”两个“不必说”中,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有长吟的鸣蝉,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本是不必说的,却说了这么多;本是引出下文的略写,却写得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有高有低、丰富多彩。可以想象下文“单是”引领出的隆重登场的景色,会有怎样的“无限趣味”了。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仿写这个句式,学习先概括列举,宕开一笔,再进行聚焦式的描写。又如“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也许是……也许是……”从成人的视角看,一定知道为什么要去三味书屋,但从儿童的视角看,离开百草园是多么的不舍和无奈呀!如果没有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如果不拔何首乌,如果不抛砖头,能不能继续在百草园玩耍?当然不能,这些原因只是无端的猜测,是对百草园快乐生活的回忆和眷恋,是对即将进入三味书屋学习的无助和畏惧。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文本分析之后,应适时唤起学生的生活体验,使学生结合真实的情感仿写句子,既深入了文本,又反观了自我,同时积累了语言模型,阅读和写作能力都能得到提升。
学生除了依据句式仿写,还可以依据写作手法仿写。特级教师王君曾把《社戏》当作写作型文本教学。鲁迅采用多种写法表现心情,颇具独到之处,王老师抓住了这一点,先带领学生阅读、赏析、提炼。鲁迅写“我”因不能看社戏而着急,“我急得要哭”——直接写急。“我似乎听到锣鼓的声音”——通过幻觉写急,“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通过状态写急。三个角度,三种写法,各得其妙。得以看社戏后写高兴,与写着急异曲同工:“我高兴了”——直接写高兴。“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通过幻觉写高兴。“我们立刻一哄的出了门”——通过状态写高兴。写戏不好看时的疲倦与前两者同中有异:“我有些疲倦了”——直接写疲倦。“那五官渐不明显,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没有什么高低”——通过幻觉写疲倦。“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通过情节写疲倦。王老师带领学生读出了不同的心情,分析了不同的角度,提炼出丰富的写作方法。然后设置情境,给出题目,当场赛练,读写高度融合。
补写也是读写结合的有效方法。黄厚江老师在《孔乙己》一课的教学中,以手为切入口展开阅读实践活动,在深入挖掘文本之后,自然地引入写作训练,“文中写了这么多处的手,其实有些其他地方也可以写手的,而作者却并没有写,你能找出这些地方来进行再创作,补写出一两句,并说说自己为什么这样补写吗?”这个写作训练本身就是读写相融的,对手的补写活动,是阅读活动主线的延伸。学生找出可以补写的地方,需要深入文本,把握文脉;补写句子,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说出自己为什么这样写,需要分析补写内容与课文的契合点。而学生分享的过程,充分展现读写共生的优秀成果。读写共生既体现在课堂读写活动的互相促进,又体现在学生读写能力的共同提升。学生用“孔乙己双手用长指甲在桌子上掴来掴去”来表现他受人嘲笑后的尴尬,用“紧紧攥着拳头”表示他的愤怒。黄老师提醒学生补写应该既能表现人物性格,又要切合上下文。当学生补写的孔乙己手的动作能够符合语境、切合身份、表现性格时,黄老师又提示大家可以想象孔乙己手的形状。最后,黄老师引导学生想象并补写孔乙己死去的情景,当然必须写到孔乙己的手,并且创造性地为他的手安排两个道具。有的学生安排了“书”,因为孔乙己一心想中举,始终要显示自己是个读书人。有的学生安排了“碗”,因为孔乙己既想要吃饭,还想喝酒。书和酒是解码孔乙己的两把钥匙,学生为孔乙己安排书和喝酒的碗这两个道具,说明学生对课文的解读已经触及文章的本质。黄老师整合学生的补写:“冬天寒冷的夜晚,在村外的破庙里,孔乙己死了。他蜷曲的身躯像一个少了一个点的问号,一只手紧紧地攥着一个破碗,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一本又破又旧的书……”补写活动非常丰富,但黄老师并没有满足于此,又安排了一个创写活动:如果为孔乙己立一座碑,请同学们为他代写一句碑文,并简要说明理由。接着,黄老师以自我调侃的方式提供了支架:黄老师将来的碑文就可以写“这里躺着一个热爱语文的人”。学生在笑声中创写:“这里躺着一个可怜的人。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中,没有一个人同情他,打了他还嘲笑他”“这里躺着一个可笑的人。因为他自命清高,迂腐可笑,还给人带来笑声”……学生用一个词概括出孔乙己的性格和命运。补写、创写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逐层深入。
除了仿写、补写、创写,教师还可以设计缩写、扩写、短评、人物小传等多种写作活动。当然,阅读教学中设计写作活动的目的是引领学生深入解读文本,而不是把阅读课上成写作课,因此,教师要根据文本特质,在恰切的读写结合点设计适宜的写作活动,达到读写共生的效果。
三、类文联读,拓展学生思维广度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共选编7篇鲁迅作品,其中1篇为思辨性阅读,其余6篇为文学作品阅读。教师可以采用不同形式的联读策略,促进学生从整体上理解鲁迅作品的独特风格,全面认识鲁迅作品的思想内涵,拓展思维广度,提升语文素养。类文联读在选择文本时,要注意文本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同一性是整合的基础,差异性是分析的关键。教师可以从文本作者、时代、主题、题材、文体、结构特点、语言风格等多方面组合类文,引导学生对多文本材料进行对比、分析、综合、评价,在合作探究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两篇文章都是散文,都有对童年的回忆,标题也都能揭示行文结构,可比性较强,教师可设计类文联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分散着写事,即写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中的童年生活;《阿长与〈山海经〉》集中地写人,即写幼年的保姆阿长,但事件也是分散的。分别概括提炼主要事件对初一学生来说难度不大,但内在情感的差异与矛盾,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对立与统一则需要教师逐步引导。这两篇文章都有绝妙的神来之笔:“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这一句在文章中间起过渡作用;“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这一句在文章结尾起升华作用。两句神来之笔,在教学活动中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笔者以此为出发点,引领学生展开类文联读。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蟋蟀后面加“们”已经具有拟人色彩了,前面再加上“我的”,可见“我”与它们的亲密关系,“我”为什么这么留恋百草园,这么畏惧三味书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在《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作者为什么对阿长这样一个身份低微的小人物发出颂歌式的抒情?阿长买来《山海经》的前后,“我”的情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教师可抓住关键词语,引领学生体会文字背后的深层意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只有一些野草”是成人的视角,“确凿”因为百草园确实是荒园,这是客观的事实;“似乎”是“我”对七八年前模糊的记忆,是主观感受。“乐园”是儿童视角,表明百草园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快乐。百草园在户外,活动空间是相对开放的,景物是丰富多彩的,是儿童尽情展现童真童趣的自由空间。在三味书屋部分,教师要引导学生抓住“读书”这一关键词语。“我就只读书”,一个“只”字突出了作者选择性地忽视了读书以外的事情。三味书屋中的学习生活是单调枯燥的,生活空间是相对封闭的,即使有折蜡梅花、蒙了绣像作画的乐趣,也是不合规矩的。再回到神来之笔的过渡句,学生可以清晰地理解作者情感的变化过程。
阿长买来“我”渴慕已久的《山海经》,前后都有为结尾的神来之笔蓄势的关键词语。买来《山海经》之前,阿长的切切察察令“我”讨厌,繁琐的规矩让“我”不耐烦,谋死“我”的隐鼠让“我”憎恶,这是儿童视角的真实感受,至于对她有阻止大炮的“伟大的神力”的敬意,儿童天真的心理可能信以为真,成人的叙述视角就有了调侃、反讽的意味。在阿长买来《山海经》之后,“霹雳”“震悚”这样的关键词预示着“新的敬意”不再调侃,不再反讽,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抒情。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伟大的神力”消解了谋害隐鼠的怨恨,消解了所有的讨厌、不耐烦、磨难。多重铺垫之后,托出神来之笔:“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通过对关键词语的解析,教师引导学生体会到两篇文章中作者情感变化的过程,了解到童年的鲁迅对自然、对学习、对自己、对他人真实的人生态度,引导学生发现童年的鲁迅与自己相通的精神世界。
这两篇文章中都有阿长讲故事,分别讲了美女蛇的故事和长毛的故事。美女蛇的故事,无论作为迷信传说,还是正义战胜邪恶的童话,故事本身和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荒谬的。鲁迅却一本正经地写道:“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似乎还为自己名字不是美女蛇而庆幸。阿长讲美女蛇的故事,还可以理解成警告孩子要远离危险之地,学会自我保护。长毛的故事就完全成了反面教材,不仅荒诞,而且低俗。鲁迅却用“伟大的神力”来回应,并且以“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作为不必惧惮阿长的理由,把荒诞的故事纳入行文逻辑之中。再联系到鲁迅对老师的态度,“怪哉”事件中老师用简单的“不知道”回应学生的好奇心,显然失之偏颇。鲁迅却以儿童视角去调侃,并不以此否定老师的博学与方正。可见,鲁迅的批判是理性的,他批判的是教育制度,而不是教育本身,更不是教育者。对阿长和老师的弱点和局限性,鲁迅都能以幽默的调侃一笑置之,体会到对方的温暖和爱意并以此消解他们曾带给自己的不快。从成年回述的视角联结两篇文章,可以读出鲁迅的适度与包容。
鲁迅的作品不但在课程中具有整体性,在各单元中还起到定篇的作用。基于单元的整体性,教师可以根据单元的人文主题和语文要素设计类文联读。例如,《故乡》和《我的叔叔于勒》单元主题为少年成长,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少年视角、文章色调、对比手法等方面展开联读。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还涉及中外文化差异的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比较两位作者不同的思想倾向。两位作者在批判现实的同时都有对未来的希望,宏儿和水生是鲁迅的希望,若瑟夫是莫泊桑的希望。教师补充《我的叔叔于勒》原文被删减的开头和结尾,展示《故乡》的结尾。通过对两篇文章的比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挖掘出差异的实质:莫泊桑的希望寄托于保持善良的人性,鲁迅的希望寄托于前赴后继的实践。莫泊桑的思想倾向是人道主义,鲁迅的思想倾向是革命主义。
鲁迅作品联读要以语言运用为出发点,运用求同存异的方式,抓住多文本阅读对比和联结的关键点,在分析、综合的过程中促进学生思维空间结构化、系统化。
综上,新课标视域下鲁迅作品的阅读教学,教师可根据文本特质和学段特点把握教学重点,找准切入口,设置主问题,引导学生深入解读文本,通过读写结合、类文联读等教学策略,观照鲁迅作品内在的连续性与进阶性,将鲁迅作品学习融入学生生命成长,彰显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实现鲁迅作品单篇独特性和课程整体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余映潮.语文教学设计技法80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2]黄厚江.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3]王君.凭什么教好语文[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
(责任编辑:赵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