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电影中表演美学的本土特征探析:以“第二代”导演的实践为例
2024-06-18朱国昌窦嫣
朱国昌 窦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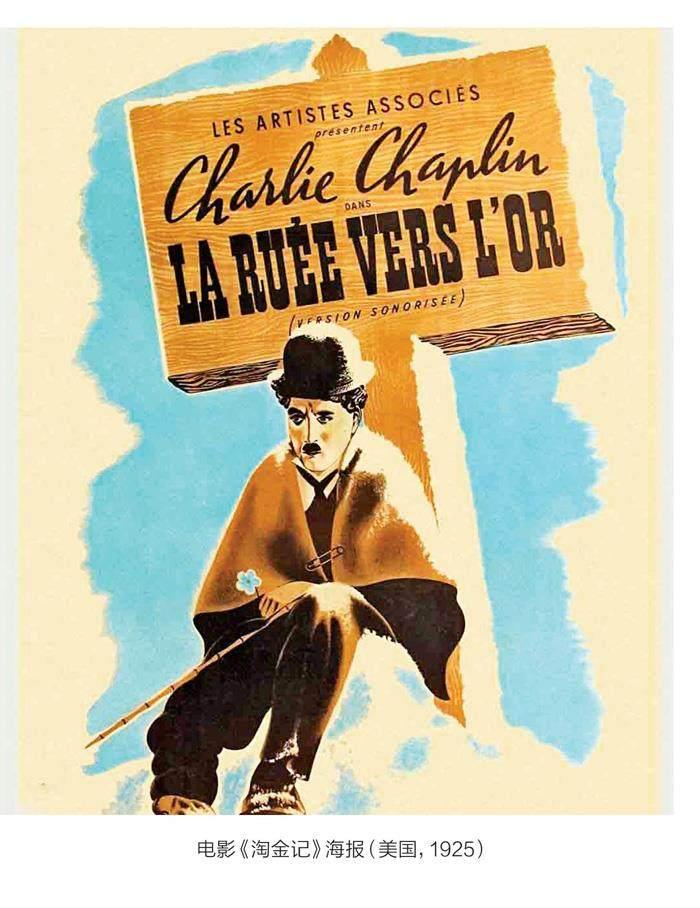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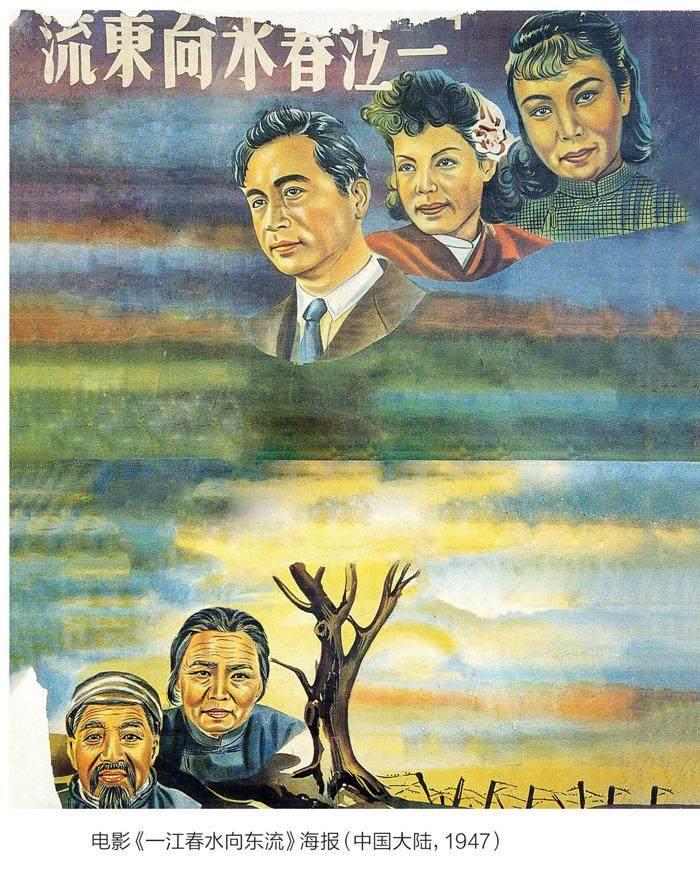

中国早期电影表演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的电影表演并不在同一个表现维度上,它们的判别标准也不同。中国早期电影表演形成了明显的中国式本土表演范式,凸显了鲜明的中国早期电影表演美学的本土特征,它集中反映在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的实践过程中,作品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一、表演风格与电影本体美学的确立
中国早期电影在探索和实践中从早期戏曲表演、滑稽表演逐渐发展出具有民族类型风格的表演,脱离了程式化、夸张化的戏曲风格而生成具有电影本体性质的写实风格,中国电影表演初步确立了电影本体的美学。
中国电影与戏曲是紧密缠绕的两个脐带,它一诞生就是电影和戏曲的双胞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任庆泰执导)就是戏曲中的京剧品类,电影主演是京剧界鼻祖谭鑫培。京剧的唱、念、做、打,京剧舞台上经常使用的“欲擒先纵”之法,简言之就是欲扬先抑,欲左先右,欲快先慢,欲进先退等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规律,不黑不显白,不低不见高,欲擒先纵之法是有意识加强矛盾对比,使需要加强的东西,用突出的手法来达到目的。譬如,台上做个指出的手势,要使观众看清楚手的指向,讲究“未曾动左先动右”,就是说当左手要指出时,先使右肩略稍启动(匀个小圈儿),用欲左先右之法来领台下观众,唤起注目,否则,观众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动作一掠而过,台上身段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内进行的,要让台下看清姿势圆顺完美,只有动作距离拉长,但拉长并不是简单地放慢,而是以相反相成的欲擒故纵法,做个装饰动作,使人看清动作层次,观其美而不觉其长,再配以锣经节奏,显得鲜明有力,更觉意味深长。例如,双臂展开,向前拥抱时,须先朝后一闪身(欲前先后)这和往前蹿跳时,先要撤步蹲腿(欲起先伏)是一个道理,哪怕是简单地撩个水袖,也得先朝下一放(欲高先低)再向上撩起来。因此,台上所有的前与后、左与右、高与低、扬与抑、上与下、快与慢、长与短、起与落、伸与缩、放与收、进与退、单与双、强与弱、大与小、正与侧、推与拉等。
在中国电影还没有可观可借鉴国外电影的当时条件下,戏曲范式首先闯入电影表演中来,而且早期的电影演员也多从戏剧舞台转移到电影摄影机前,这种认识上合理的、看似“有神”的表演功夫就自然被带入电影的镜头当中。
电影毕竟不是戏曲,为了使电影与戏剧分离,使电影电影化,电影理论家和导演都做了相当的努力,夏衍等一些电影理论家明确指出:“电影虽然和戏剧是最接近的亲属,但是,电影有它艺术上的特质,绝不是戏剧上的改装,也不是戏剧的延长……”[1]费穆的作品在一定程度开始了电影与戏剧分离的自觉尝试。1934年费穆的作品《香雪海》完成,他在总结这部作品的文章《<香雪海>中的一个小问题——“倒叙法”与“悬想”作用》中写道:“我有一个偏见:我认为戏剧既可以从文学部门中分化出来,由附庸而蔚为大观,那末电影艺术也应该早点离开戏剧的形式,而自成一家数。”[2]
随着国外电影的引进,最早是美国电影制作公司启斯东(Keystone)打闹喜剧传入,让中国观众接触到西方类型电影的滑稽片,尤其是默片时代查理·卓别林自导自演的无声喜剧短片《流浪汉》(1915)、《当铺》(1916)、《溜冰场》(1916)、《移民》(1917)、《冒险家》(1917)、《越狱》(1917)、《从军记》(1918)、《百万金钱》(1920)、《犬吠声》(1921)、《淘金记》(1925);美国导演巴斯特·基顿的自导自演的无声电影《倒霉》(1921)和《三个时代》(1923)等。
20世纪20年代(1921-1926年前后),受此影响和启发,中国出现了滑稽片的创作热潮。美国电影制作公司启斯东(Keystone)滑稽逗趣的喜剧观念、追逐打闹的滑稽场景和滑稽角色的外貌特征、形象类型与情节叙事等,都给中国早期滑稽片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它和中国社会人生与民间笑话故事融合一体,渐趋形成另有一番中国民族性特点的带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滑稽片电影风貌。
随着电影观念的发展和电影人的思考,以及国外电影生活化表演对比,中国电影的表演概念发生了动摇和电影本身的单独分类,它不从属于戏曲,表演当然也不能重蹈旧辙;同时,启斯东(Keystone)滑稽表演,一味地搞笑电影也没能对中国电影表演形成长期不散的影痕和盲从的模仿追踪。
电影在与戏剧和滑稽戏做出分离之后,走向了自我,凸显了电影本体,用声画在有限的时间长度中无限地伸展了有寓意的故事,确立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表演风格,彰显了主题,而且可喜地走向写实主义的美学范畴,释放出中国早期电影的绚丽光辉。
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是在对于现实的照相记录本性的连续中来凸显艺术精神和抽象意味。”[3]电影的写实是摄影机的功能,它把生活似动性地固定在银幕上,让生活“搬家”到暂时固定的时空中,它在这里开始,或是过着有炊烟升起的日子,或是展开一场波澜壮阔的事件,人的命运就在这里上演,社会的声响呼啸而来。
中国早期电影遵循工业文明的发展步伐,带入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风尚,不仅享有电影的娱乐因素,还自觉地把电影功能扩大到社会使命的发掘中,全功效地释放着第七艺术的能量,使电影成为广角性绽放文化的传播机。
中国早期电影还蕴含了许多哲学智慧的因素,道德、命运、历史的轨迹隐隐出现,有时高声呐喊、振聋发聩,或者隐晦、象征性表达,在艺术氛围的程度中引人深思。
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恰逢面临中华民族濒临危亡的特别时期,抗争的声音构成电影宣传的唤醒,在黑白、彩色或有声电影或默片中爆出。而且,在国家遭受侵略的背后,又繁生出各种世间情态,成为电影的鲜活题材和主题,人物形象生动感人,呼之欲出。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1947)男主人公张忠良(陶金扮演)本是个非常有民族气节的抗战英雄,却在周遭颓败环境的影响、诱惑下堕落成忘恩负义的变节丑角,大背景大主题照射出小人物、小家庭的悲惨命运,又回归以至升华了电影主题,从宇宙、人性的视野中萃取了生与死的典型,掀动了国家、民族后幕中的悲歌。
爱森斯坦说过“蒙太奇的力量就在于它把观众的情绪和理智也纳入到了创作过程之中”[4]。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正像电影题目所示——一江春水向东流,把观众的情绪和理智都带入滔滔江水之中。素芬(白杨扮演)这个曾经美貌天真、质朴善良的中国妇女典型也纵身投进它,付诸东流。影片另有可贵之处是把中国古诗词的经典诗句挪用于电影,顿生画面感和电影主题寓意,字幕同步呈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五代十国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中诗句)富有电影“才气”的感觉,而且电影音乐是凄婉、悲绝、苍凉的曲调流水似地送远。
麦茨则提出电影的“空的空间”本体特征,它与文学的意会特征有相似性,即“都体现了概括和传达人类抽象情感力量的艺术气质”[5]。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伊始,电影名就融入在一江春水的画面里,歌声唱出片名的歌词,大桥、烟囱、房子、车间在很多镜头中出现,后面的战争场面、过日子的家庭画面等映照出社会的无限繁杂和无助感,空镜头、实物以及人物随剧情出现和隐没,这些带有中国山水画、笔墨画特点的空间表述有实有虚,有留白,给联想带来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并构成了象征性延宕的遐想。
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1948)、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1937)、沈西苓导演的《十字街头》(1937)、蔡楚生和郑君里联合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史东山导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1947)、吴永刚导演的《神女》(1934)等电影作品,都堪称第二代电影导演作品的成功典范。
中国的电影表演也像其他事物发展一样,从模仿到发挥,从吸收国内各种艺术营养到借鉴国外电影样式,一步步发展,日趋成型,变成了它自己的模样。最为可取的是,它没有唯沿袭而沿袭,唯模仿而模仿,而是经过有效地扬弃,由此独创性地生长出一个具有本土特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诞生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中国早期电影表演美学,它在中国第二代导演作品中释放出绚丽多姿的色彩。
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中成就最大的是蔡楚生、郑君里、费穆、吴永刚、史东山、桑弧、汤晓丹、孙瑜等,他们经历了中国电影的默片和有声电影阶段。
脱离程式化、夸张化的戏曲风格而生成具有电影本体性质的写实风格并非只是表演单方面的认识能做到的,它与影片内容、主题、人物身份、国家形势、民族命运、电影本身特点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戏曲中多为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武生、小旦等这些角本身就带有与常人不一样的身份标志,出于舞台的表演,又要让观众看得清,看得懂,表演上的夸张、假定性、程式化、亮相、眨眼、表演、表情用力等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它直接冲击了电影的真实化和生活化表演。生动自然、心理世界更丰富的表现内核,应该是有血有肉地、质朴无华地流淌;可以把它说成是电影形象的塑造,但这种塑造是真情实感的流动,而非戏剧夸张变形的做作;可以说,人物角色的真实是生活的逼真、情节发展的必然和角色灵魂的化境展开。
1933年左翼电影在上海的发展,使带有浓烈的民族使命感电影加大了中国电影表演真实性程度,让电影本体性质的写实风格更具雕塑性的外型和流畅节奏。
二、表演观念与电影业界结构的形成
中国早期电影中表演美学的本土特征探索并非直线发展,一路无阻,而是经历了艰难的观念性阻止,其中最大的发展就是根深蒂固的戏曲历史和其中的表演经验带来的,它是来自电影之外的戏种的国粹级的横亘,是权威级的看似合理的、不容推翻的立说。
影戏表演观念和纪实表演观念的争论,电影家指责“新剧家”其银幕表演“做作”,甚至“乱动”。“新剧家”则反嘲电影演员只求“面目姣好,服装新奇”,上了银幕即以明星自居,有戏剧经验和风格者,反而成为“银幕罪人”。[6]彼此观念争执激烈,波及戏剧与电影表演业界的生态结构及其生存状况。
(一)影戏表演观念
影戏的观念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影戏又称影子戏,是一种优美的传统民间戏曲艺术,中国被誉为“影戏的故乡”,起源于唐、五代,繁荣于宋、元、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自形成以来,得到了上至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下至市民百姓的喜爱。中国影戏包括手影戏、纸影戏、皮影戏三大类,是一种集绘画、雕刻、音乐、歌唱、表演于一体综合的传统民俗艺术。
第二种说法,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人对电影的通用名称,实际上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电影创作特点和电影工作者的电影观念。[7]大多披着社会教化功能的外衣,创作原则以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在环境中重指示性轻再现性,迎合市民欣赏趣味。
本文指的是第二种说法的影戏。“影戏观”由影戏的表演形式发展成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的规定,进而成为电影表演的教范,曾一度形成电影整体创作遵循的标准,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走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现象也主要与中国早期的舞台艺术观念连在一起,由于电影是在舞台艺术之后诞生和发展的产物,这种遵循就成了自然的延续,更何况中国第一部电影拍的也是舞台戏的京剧,后期还有1948年费穆导演的京剧电影《生死恨》,剧中的主演是声震海内外的梅兰芳,这种影戏表演观念的建立和坚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电影《生死恨》的剧情是南宋时期,金兵大举入侵,大批无辜百姓被俘,成为金国官宦人家的奴仆。韩玉娘和程鹏举是宋国大臣后代,亦在兵荒马乱之中成为金将张万户的奴仆。张万户强迫二人婚配,新婚之夜晚玉娘劝鹏举寻找机会逃回宋国。张万户得知此事,将玉娘卖与瞿姓汉子为妻,玉娘将一副耳环留给鹏举,自己拾得鹏举一只鞋作为纪念。鹏举设法归宋,入伍建功,成为襄阳太守,并终于寻得玉娘,而此时玉娘已病入膏肓,憾然而逝。
这种国破家亡的故事主题具有劝诫说教的功能,由名导演、名演员演绎,形成观众的直接联想,在中国面对外敌侵略的特殊时期,能唤起爱国情绪。激发民间斗志的电影无疑具有宣传和鼓动作用,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不仅在电影内部,也在银幕之外获得艺术的实际功能。
文明戏的影响也倒向影戏观一方。文明戏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由天津曲坛上演十样杂耍演变而成。具内容不仅包括鼓曲和相声,而且有杂技、戏法和魔术。文明戏在“以研究新派为主”[8]的口号下建立一种新的语言表现形式,动作都是程式化的,延续了戏曲表演的根脉,是一种新的戏剧表现形式,人们称之为“新剧”,属于中国早期话剧,是改观后的文明戏,演出时无正式剧本,多采用幕表制,可即兴发挥,20世纪初曾在上海一带流行。
中国第一代导演中的张石川、郑正秋的电影作品,很多都是取材于以往较为上乘的文明戏。文明戏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主要材料资源,它强调“电影剧本是电影的灵魂”[9],一切按本子的设计、创作和规定演戏。早期的“影戏”理论不注重电影对现实的记录和复制功能,淡化纪录性表现成分,而强调教化的功能和成效,讲究剧情和剧作水平的提升,把演绎主题当作电影的主要呈现过程。
主人公历经磨难,角色类型化,行动轨迹不变。男主人公有自我镜像中的理想化特质,坏蛋、滑稽的傻瓜也成为角色类型的一种。整体观影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艺术形态煽情,能博取怜悯之心和同情。观众随剧情进入换我状态,在银幕前获得自我体验,提倡普及性,能通俗易懂,让影戏发挥“表现人生、批评人生、调和人生、美化人生”[10]的教化功能。
影戏的情节模式化严重,多见偶然性结构,戏剧性巧合成篇,又强调戏剧化冲突。故事情节越曲折生动越被看作是好作品,以此评价叙事能力的高低与否,而且有明显的好坏、善恶、美丑对比,立场鲜明,人物品质界限分明,正义和邪恶的对抗凸显,鲜明的道德感统领剧本,劝善的艺术指向明朗,教化的功能内化于中,价值评判多具伦理色彩,多以高大和凛然的戏剧姿态冲荡反动势力,形成撞击似的情节冲突,最终,正义战胜邪恶,在人们美好期待中进入高潮,以满足观众的心理预设作完满结局。
影戏的人物多被塑造为正义化身的有抱负和理想的典型形象,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牺牲自己。其他男子形象的矛盾多在家庭中展开,或金榜题名,或升迁后变质,此后,在爱情上喜新厌旧,另寻新欢,背信弃义,女性被抛弃,故而绝望,既而奋勇反抗,以强烈抗争命运的精神来凸显矛盾的冲击力。
影戏演员很多本身就是戏剧演员出身,一生都在银幕和舞台穿梭,表演痕迹终不褪色,甚至日益加重。影戏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创作风格,更是一种看待和把握电影的观念和思想方法。
(二)纪实表演观念
纪实表演观念对影戏驳斥,认为“新剧家”其银幕表演“做作”,甚至“乱动”。上文说到“新剧”是指文明戏的一个发展后的变种即影戏,“新剧家”是演影戏和创作影戏的业界之人。“新剧家”则反嘲电影演员只求“面目姣好,服装新奇”,上了银幕即以明星自居,有戏剧经验和风格者,反而成了“银幕罪人”。两者观念难辩是在影戏(戏剧的一种)表演的假定性上,纪实表演也有假定性。
影戏戏剧舞台具有假定性,电影也有假定性,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就是假定性的开始,但电影追求艺术真实,在打破假定性中求真。影戏戏剧舞台是在表演中求真实,演绎出艺术的真实,规定的时间、空间一看就是不真实的,但演员的表演过程结束时,要变换出一个真实而令人感动的故事,可是演员所用表演的夸张舞台效果就是通过做戏体现出来的。纪实表演是电影化的,场景不允许是假的,去掉了环境的、空间的假定性,演员化妆也不能看上去是化过妆的。一个多小时左右的电影观赏,时间具有假定性,但表演不能看出是表演,是假定性对真实性的建立,真实性对假定性的打破,这就是电影与影戏戏剧的本质区别。纪实表演观念要的是这样一种艺术,是区别于戏曲的艺术,是艺术幻化出的真实,越真实越属于电影本体。
戏剧表演受舞台的限制,远排的观众看不到演员的细微表情,演员的表演必须夸张、用力,布景指意不明确必须靠动作引导。电影则没有这些限制,摄影机可以任意调整、调换角度,可以推进演员,拍摄他(她)的特写。
纪实表演观念要还原生活的本真状态,演员进行本色出演,景物、服装当然都要真的,应该是去掉舞台的夸张、用力,当然不要舞台剧的程式化表演,戏曲中的“唱”“念”“做”“打”都不是电影里的做法,尤其是“做”的缓冲动作都不能有,那些欲前先后、欲起先伏等统统都不能出现,程式化、亮相、眨眼、表演、表情用力等都要去掉,因此,电影的纪实表演对一个习惯了舞台表演的演员来说,得时刻保持在真实生活环境里和非做戏的体验当中,避免一不小心就“演”了出来。当然,纪实表演也不是完全没有控制的表演,内心里的情绪按人物思想和性格需要,不可能悲伤就嚎啕大哭,喜悦便得意忘形,它依然属于准确的心理通过表情真实地传达给观众。
三、“情动”机制与民族电影美学的成熟
影戏表演观念和纪实表演观念的争论,并没有让一方绝对获胜,而是抽取和复显了双方有效的成分,在戏剧之“虚”与纪实之“实”之间,探索出一条中国电影在民族化道路上的发展之路,以“情动”为机制,走向中国民族电影美学的成熟。
电影呈现出“虚中带实,实中带虚”的美学风格,闪耀出民族性独有的电影美学色彩。中国的电影表演是在戏剧表演的基础上通过纪实性表演阶段,不断探索,逐步走向表演电影化的。在戏剧假定性的“虚”中规范进入纪实性的“实”的程序里,让真实意识更集中、更典型、更有表现力,以“动情”的状态进入更高境界。
电影理论大师安德烈·巴赞与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提出了“电影影像本体论”,巴赞认为,“唯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11]。克拉考尔的观点与巴赞相似,他认为“电影的特性可以分为基本特性和技巧特性。基本特性是跟照相的特性相同的”[12]。技巧特性应该理解为情动在基本特性中的表现手段,即表演的功力,它和只有感觉到却不会表演形成艺术表现能力的对比,这就要求演员除了理解到剧情、故事主题、人物个性和命运,还要有高超的表演天赋在镜头前驾驭这些属于电影表达的水准。
费穆导演的电影《小城之春》(1948)没有影戏的说教功能,表演完全是电影化的纪实表演风格。在南方的一个小城里住着一对夫妻,丈夫戴礼言(石羽饰演)和妻子周玉纹(韦伟饰演)。丈夫的好朋友章志忱(李纬饰演)来看他,到了之后才知道,丈夫的妻子周玉纹和丈夫的朋友章志忱是从前的恋人。其中最精彩的一场戏是,周玉纹和章志忱喝酒后似醉非醉地亲近之后,到了晚上周玉纹照镜子打扮了一番,身体的前后又照了照,嘴里说像做梦,走到门前又回过身,把桌上的蜡烛吹灭,她的旁白道:“这时候,月亮升得高高的,微微有点风”。悄悄地走近了章志忱的房门前,停住脚步,往后看,有没有被谁发现,又回过身,往章志忱的房间走。章志忱开门迎出来,他扶着她的双肩,往外推她,周玉纹:“你让我进去。”章志忱:“回去。”周玉纹推开门,章志忱:“别进去。”周玉纹闯进去,章志忱把门关上,镜头移到窗外的月亮,周玉纹拿出火柴划着,章志忱把火柴掐灭,月光照在屋里的盆草上。周玉纹凑近章志忱,章志忱先是冲动地把她抱起来,后自己把内心的欲火熄灭,他把周玉纹锁在屋里,周玉纹要出来,敲碎玻璃,章志忱赶紧进屋,给她玻璃刮伤的手服药,把她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场戏扮演周玉纹的韦伟和扮演章志忱的李纬都在“情动”中演得十分投入,没有半点演戏的感觉,让观众也看得心里怦怦直跳,长镜头的拍摄让一个“发乎情,止于礼”的爱情戏演绎得如此生动。
电影的表演镶嵌在这个小城的废墟之中,城墙的残垣断壁象征着破败,死气沉沉的屋中气氛笼罩着这里主人的内心,章志忱的到来像吹进了一缕春风。傍晚,周玉纹偷进了章志忱的房间,月光也照了进来,周玉纹送给章志忱的盆草也被月影抚掠。
让表演呈现出时空的流动感。中国抗战14年,章志忱和周玉纹的聚散也在这期间发生,男女主人公的悲剧与这小城的命运是重叠的,从完好到破败。“时间本身是荒诞的,空间本身也是这样。相对性和绝对性都是相互映射的结果,每一方都常常涉及到另一方,空间和时间亦复如是。”[13]
男女主人公韦伟和李纬的表演基调惆怅又委婉的,亦是时间的陈述,又是对时过境迁的追忆和感叹。时空是不在场的表演,人物复合在时空表演的外显逻辑里,演员的表演不仅是在镜头前,而且还必须在历史的幕后,这是一种印合丰富文化内蕴的表演功力,既像时间流水似地淌出,又框定在空间的桎梏里。“影片的含义就是通过这种融合,通过影片主题的逻辑思想和能够体现主题的最高形式之间的融合才能完整地显露出来。”[14]电影《小城之春》的表演不仅仅是一段故事的讲述,还是挖掘了爱的命运使然,即时间与空间框定的和不可更改的命中劫数和未来预测。“再现现实是摄影艺术的本体,而电影在这一点上与摄影相似,电影相对于摄影而言就是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摄影只能留存瞬间,电影能够再现事物的时间延续。”[15]
在后面的镜头中,章志忱离开了小城,周玉纹和戴礼言目送远去的旧友,这又是一个象征,画面中没有章志忱,周玉纹伸手把戴礼言拉到高处,他们和好还初。最后的一个镜头,演员的面部表情都没有出现,而是一个大概念的表演,是他们一如当年的背影,向着远方,也环扣了主题,小城之春才见曙光。
结语
本文以回顾的方式对中国早期电影中表演美学的本土特征做了探讨性分析,并以“第二代”导演的实践作为重点讨论对象,旨在从中国电影表演的历史过程中寻到一个可鉴性的经验。中国电影表演从世界范围内的观察上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不仅与西方的电影表演不同,与东方的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的表演也大相径庭,这正是艺术所该有的独特性所在,只有最具民族性的艺术才最能彰显魅力的光芒。
中国早期电影表演中蕴含的东方韵味拥有显著时代标志的历史痕迹,其实这正是它光辉的闪耀。从电影理论上看,它涵盖了对旧有表演的克服,尤其是对戏曲中程式化的除根改造是一种扬弃。这在一个时期笼罩的表演观念下进行其实是较为困难的,尤其是对权威观念的挑战和大胆的反向迈进,不仅要有实实在在的成就做导引,还要有对新观念的理解,并且最终能上升到哲学的认识高度。
建立中国早期电影表演美学,并付诸可喜的实践,是电影人,尤其是中国第二代导演积极思索、顽强探究以及大胆实践中获得的巨大成就,它不仅是那一个时期电影傲人的标志,也是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一面光辉的旗帜。
参考文献:
[1][2]周立萌.刍议费穆电影美学——影像本体现代性的自觉探索[ J ].视听,2018(11):79-80.
[3][5]王志敏主编.电影学:基本理论与宏观[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136,137.
[4]爱森斯坦.论蒙太奇[M]//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99.
[6][厉震林.中国电影表演美学的文脉与观念[ J ].当代电影,2019(08):23-28.
[7]钟大丰,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4.
[8]黄爱华.春柳社研究札记[ J ].戏剧艺术,1993(02):76-83.
[9]钟大丰.“影戏”理论历史溯源[ J ].当代电影,1986(03):77-82.
[10]周星.关于中国电影理论构架的梳理[ J ].当代电影,2004(06):103-107.
[11][15][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6,1-2.
[12][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206.
[13][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M]//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86.
[14][法]亨.阿杰尔.电影美学概述[M].徐崇业,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