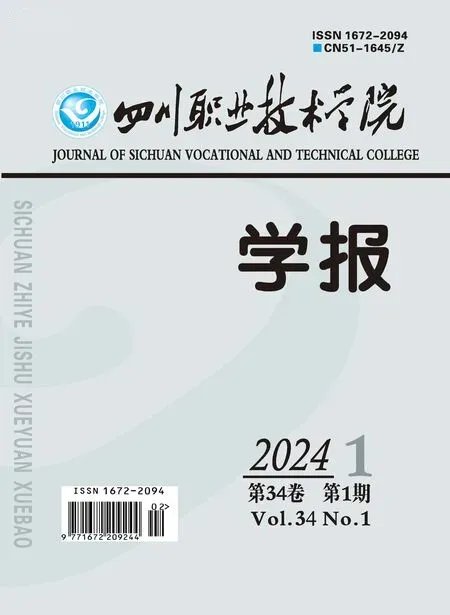鲁迅之“女吊”与女吊之“复仇”建构路径探析
2024-06-01陈琳
陈 琳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1936年9月21日,即鲁迅写完《女吊》的第一天,冯雪峰到他那里去,他对冯雪峰说:“这一篇比较的强一点,还有一个理由,是病后写得比较顺手了。病重实在懒散了。”[1]鲁迅去世的前两天,在与来自日本的鹿地亘、池田幸子谈论《女吊》时,“他把脸孔全部挤成皱纹而笑了”[2]。《女吊》作为鲁迅晚年极为自得的杰作,以其特殊的创作时间和风格吸引着读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以“民间”“复仇”和“女吊”三个关键词解读其中鲁迅的思想及中国近现代民俗文化。丸尾常喜以民俗学视野通过田野调查的形式考察了鲁迅之“女吊”与绍兴目连戏之“女吊”的精神差异。少数研究者关注了作为“非遗”之《女吊》与鲁迅之《女吊》的互动关系,基于文学“女吊”与绍剧“女吊”殊异,故而提出了“女吊”形象中“复仇”精神可能是鲁迅的一次“发明”。
事实上,无论从民俗学还是从“复仇”精神着眼借助绍剧“女吊”来解读文学“女吊”,其认识皆基于绍剧“女吊”为鲁迅“女吊”之底本,以及回忆散文式话语的真实性底色。而各种艺术之间具有辩证关系的复杂结构,这种结构通过一种艺术进入另一种艺术,反过来,又通过另一种艺术进入这种艺术,在进入某种艺术后可以发生完全的形变[3]。如果仅以绍剧“女吊”为形象资源,当代绍兴戏中又为何援引并借鉴鲁迅“女吊”的描述?那么,鲁迅之“女吊”作为文学性的差异存在,在两种艺术形变过程中,鲁迅的“女吊” 形象建构经历了哪些显性和隐曲的途径?他对“女吊”复仇精神特质的思考来源何处?其作为“鲁迅资源”的一种,在发展中对“复仇精神”是否有再次建构?
一、传统、民间与时代:“女吊”形象的文学化路径
鲁迅认为绍兴人“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4]87鲁迅写鬼于他自己而言并非新主题,他在与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的谈论中多次提到了对鬼的思考,认为中国的鬼,有更奇特之点,女子常常出来,常有与鬼亲昵的男人的故事,这是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的心理的东西。文人写鬼并不少见,宋代邵伯温的《闻见录》、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见中国古代文人与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不只是涉及迷信,而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周作人在三十年代有两篇谈鬼的文章,主要写落水鬼与鬼的生长,在引用中国古代文人笔下鬼的故事中,最后道出自己不信人死为鬼,却信鬼后有人,鲁迅在《失掉的好地狱》一文中谈到了地狱与鬼,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寓言,“鲁迅和周作人谈鬼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也就是鬼背后的人,理背后的情,所谓人情的东西,他们对鬼感兴趣,实际上是对鬼背后体现的人情感兴趣,因为所有鬼这样的东西,都是人的创造。”[5]24单从文人谈鬼历史路径来看,“女吊”作为“鬼”的共性象征与传统书写并无二致。不过鲁迅又谈道:“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罢。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4]89在提倡民主科学的环境之下,提及鬼的问题总是与反迷信有关,在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就“迷信”发表过文章,而在写作《女吊》这一年,即1936年,鲁迅说“绍兴的妇女,至今还偶有搽粉穿红之后,这才上吊的。”[4]89显然,科学与迷信问题仍然悬置着,鲁迅笔下的“女吊”又展示出科学与迷信问题处理的时代印记,与中国传统文人书写“鬼”的意图殊异。
在鲁迅写好《女吊》之后,冯雪峰从头看下去,而鲁迅指着“跳女吊”开场那一段让他看,鲁迅也多次提到吊死鬼照例是指女子而说的,而现在“女人自杀,近来往往吞金子等东西,因为金子是重的,停在肠里,引起肠炎,这种自杀,因为不是直接的,而是由炎症而来的死,很费时间,所以有的人弄得不愿意死了,医生用使金和排泄物一同拉出的方法救治。女人等到痛苦停了之后最先查问的事是,先生,我的戒指呢?”[6]无论是吊死还是吞金,鲁迅话语中都蕴含着尖锐的讽刺与深切的同情。从鲁迅的创作来看,他对女性问题尤为关注,在写作《女吊》期间,鲁迅与冯雪峰谈话中提到他要写一篇关于伟大母爱的文章,也成功塑造了农村妇女祥林嫂、城市女性子君、神话人物女娲、吴妈、小尼姑等女性形象,但与这些女性人物不同的是,“女吊”的面容、穿着、细节动作等如此入微的描写在鲁迅“白描”式刻画人物习惯中成为一个特例。投缳的女性厉鬼,正是数千年来封建伦理制度下女性的呐喊与控诉的具象化体现,这样的背景最具复仇的驱动性。作为一个“复仇者”代表,鲁迅却尤其强调“女吊”柔婉的一面,弱小又可爱可亲, “女吊”笔墨转向极度的柔弱一面,“这是以至柔表现至刚,形成极度的反差,这种反差,相距越远,力度越大。”[5]30鲁迅借助传统“女性特征”沉默的话语代言所有弱小者,以极度的反差隐藏“复仇”的力度,反而比显露的锋利更具爆发性及悲剧性。
鲁迅对“女吊”初印象来源于小时候对绍兴目连戏的实践体验,绍兴目连戏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自北宋沿袭至今,被称为“戏剧始祖”“戏剧活化石”。废名回忆说鲁迅几次给他们介绍他的故乡的“目连戏”,每次都乐道不已。绍兴目连戏中的“女吊”形象作为鲁迅之“女吊”形象资源源头,绍剧 “女吊”形象的原型考察显得格外重要,随着近年来对绍兴目连戏抄本的整理,“目前所发现最早的目连戏剧本,是郑之珍所撰《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7]鲁迅藏书中也有此本,自晚清到民国的绍兴目连戏抄本中,“女吊”故事流传是一个“妓女”经历的版本,鲁迅注释中所提却是 “童养媳/儿媳”经历版本,据学者考察,这并非鲁迅记忆之偏差,而是鲁迅记忆中的“童养媳”版本是流传于江浙地区的另一个女吊故事体系。郑本中所记录的便是“儿媳”经历版本,它作为女吊故事的雏形,后期众多戏本多从郑本中取材,从而演变出了各种类型的目连戏,尤其是江苏高淳阳腔目连戏中“讨替代”的“吊死鬼”形象就继承了郑本中受不了公婆气从而吊死的身世,绍兴目连戏的“女吊”“无常”故事雏形都来自阳腔本。从郑本到阳腔本,再到绍兴目连戏,同时借助柯灵的回忆可推断出鲁迅对这“女吊”的形象记忆并非失误,而是另一个女吊故事脉络的记忆。绍剧“女吊”虽为鲁迅“女吊”形象之来源,但在鲁迅创作《女吊》以前,女吊并非复仇者形象代表,有学者提及其中“复仇”可能是鲁迅的一种“发明”,而这种艺术形变中的“复仇”理念发明可能是直接来源于陶元庆的一幅画。
许钦文曾将陶元庆创作《大红袍》的经历讲给鲁迅,绘画设计保持悲苦、愤怒、坚强三种神情,穿着藏蓝衫、红袍和高底靴,添加来自武生的握剑的姿势。之后鲁迅嘱咐许钦文:“璇卿的那幅《大红袍》,已亲眼看见过了,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8]鲁迅虽然接收了绘画“女吊”的形象影响,但从《大红袍》的创作缘由和原作来看,鲁迅将《大红袍》复仇表象内化为一种精神表征。陶元庆在向许钦文阐释创作“女吊”形象过程中的思考时,言笔下“女吊”去除了些许病态因素,保持“悲苦、愤怒、坚强”三种神情,使用蓝、红、黑等较多的色彩渲染,更为重要的是加了一个握剑的姿势,具有外化的“复仇”意图,在诸多绘画元素中,鲁迅唯对“剑”印象更为深刻,《大红袍》中许多元素在鲁迅之后对“女吊”形象的想象中并未被采用,对“长舌”的取舍,对色彩的使用,以及女吊整体气质塑造等都与陶元庆的《大红袍》相去甚远,唯有“剑”之意象为鲁迅重新建构“女吊”形象中的“复仇”精神提供了隐曲的形成路径。不同于陶元庆对“力量”的外化,鲁迅的“女吊”是外弱内强,极其注重复仇力量的“沉默化”表达。女吊的出场先是 “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女吊为什么要走“心”字呢?鲁迅说道“我不明白”,与其说鲁迅自谦,倒不如说鲁迅想让读者自问:为什么女吊的行动轨迹呈现“心”字?浙江绍剧研究者朱燕认为“这是女吊提醒自己,心里念念不忘复仇”。作家李国文以中西方文化中“心”与“情”的密切关系为切入点,解读女吊的行动轨迹是为了诉说她悲苦的爱情。鲁迅文章开头便写到女吊是复仇者的化身,但写女吊形象的文字中未提到任何关于复仇的思想或者行为,仔细观察在走“心”字轨迹前后,女吊形象具有反差,换言之,女吊由柔婉姿态到刺目面貌的转变点就是 “心”,因为随心所以女吊面貌发生了变化,鲁迅并未直接将心中“复仇”外化,而是通过“心”的行动轨迹前后女吊面貌差异展开。
“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4]89女吊出场的形象非常缓慢,与男吊“闯”进场的方式对比强烈,紧接着女吊穿着“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地走一个全台。”[4]89对于作家而言,人物的出场十分讲究艺术,女吊出场已是文章高潮部分,鲁迅的描写是否完全符合小时候所观女吊依然存疑,单从出场的女吊姿态来看,其中长发蓬松、垂头、垂手也不像陶元庆的《大红袍》,倒与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寡妇》《格雷琴》有着相似之处。在1936年5月,中国出版的第一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便是由鲁迅自费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并请史沫特莱为其写了一篇序,史沫特莱认为珂勒惠支版画的主题一为反抗,二为母爱与死亡,在珂勒惠支的作品中弥漫着受难、悲苦、以及被压迫者的反抗意识。鲁迅十分赞同她的观点,并在版画集序中评论珂勒惠支的《反抗》:“谁都在草地上没命的向前, 最先是少年, 喝令的却是一个女人, 从全体上洋溢着复仇的愤怒。她浑身是力, 挥手顿足, 不但令人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 还好像天上的云, 也应声裂成片片。她的姿态, 是所有名画中最有力量的女性的一个。”[4]101936年4月7日,鲁迅的《写于深夜里》在英文刊物《Thevoiceof China》(《中国的呼声》)上发表时,他选发了作品《反抗》,1936年7月,鲁迅与许广平又一同整理了珂勒惠支的作品,可见鲁迅晚年对珂勒惠支十分赞赏,尤其是珂勒惠支对母亲、反抗主题的表达与鲁迅晚年的创作趋向不谋而合。“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4]89鲁迅自此揭开女吊的面纱,“白、黑、红”三种颜色的搭配非常刺目,在绘画中这是三个非常极端的颜色,刺激的色调与刚出场的女吊柔婉形成反差,鲁迅受美术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晚年对黑白版画的关注,在《影的告别》《死火》《铸剑》等作品中都是以黑、白与红三种颜色为基调,正如柯灵所言,《女吊》最刺目的,几乎可以说是对于视觉的突击的,是女吊的色彩[9]。不过鲁迅对刺目的色彩又转为了女吊可爱一面的描述,若越发极端很可能会降低女吊作为“弱小者”的反差强度,紧接着到了女吊自述她故事的情节,鲁迅却全部省略了,只留下女吊的些许呼喊。相比于鲁迅十年前在《无常》中对无常故事的详细书写,女吊故事却戛然而止,若单是鲁迅遗忘缘故还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鲁迅既有相关藏书,又有其弟的回忆,并且在鲁迅写完《女吊》后与许钦文讨论过女吊,许钦文对女吊也十分熟悉,因此女吊的唱词是可以写出来的。事实上,抛开女吊的语言,女吊形象已经十分立体,“至于她的悲惨经历,受了何种压迫,如何死的,这些细节都不重要,细节反而要削弱鲁迅希望达到的效果。”[5]31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7月,许钦文也曾写过一篇《美丽的吊死鬼》发表在《论语》1936年的第92期,其中对女吊出场的描写都和鲁迅描写得十分相似,张梦阳在《鲁迅全传》中提到鲁迅曾将《女吊》给许钦文看,与他讨论绍剧里的女吊是怎样表演的,据此可知,鲁迅的女吊也有可能会受许钦文的影响。
鲁迅有意对“女吊”的建构,综合了戏剧、绘画、文学、民间文化、传统思想、时代之症等资源融汇进“女吊”之生命,可以说“女吊”的立体化是多方路径的作用,而在这一形象之中,鲁迅为何会重点提及女吊的“复仇”?这种“复仇”精神是女吊本身具有的特征,还是鲁迅的重新发掘,抑或是解读过程中的一次次建构而成?
二、挖掘、发明与附加——复仇精神建构的复杂脉络
《女吊》发表后,有人将刊物《中流》给了郭沫若看,说这篇文章的末尾几句“分明是在骂人”,郭沫若看完之后也觉得与自己有关,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郭沫若的《蒐苗的检阅》确实隐含着鲁迅所批评的“犯而不校”与“不念旧恶”的观点,有研究者通过郭沫若的《戏论鲁迅茅盾联》及徐懋庸还击鲁迅的《还答鲁迅先生》两文,据此断定《女吊》中“人面东西”特指郭沫若。而鲁迅在写作《女吊》之前才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若将《女吊》的复仇概括为文人间因文学见解分歧而发起的一场“复仇”,这样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单化,同时也将鲁迅为人虚伪化。1936年9月5日,鲁迅在《死》一文中首次承认了“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死亡的趋近促使鲁迅晚年更想完成一部像《朝花夕拾》那样的散文集,当时已有几篇写“母爱”“穷”等主题的腹稿,《女吊》就思想上而言是接着《死》中第七条遗嘱往下写的,就行文路径而言又与《朝花夕拾》中的《无常》遥接,“因此这篇文章读来有死神唇吻的气息,像是他将所有剩余的生命力在这篇文章里燃烧殆尽。”[5]32不论从死亡心理影响还是从作家本身创作路径来看,《女吊》无疑是他对自己一生思想的又一次重要总结。作为鲁迅晚年极为自得的杰作,废名评论这篇文章是生活里正义无法伸张,便由艺术来创造一个冤魂的形象,犹之乎复仇的女吊,认为女吊是一个美丽的复仇女神,而据学者丸尾常喜的考察,绍剧中女吊并没有突出她的复仇精神,甚至找不到复仇精神表达的痕迹,而鲁迅又是如何将“女吊”与“复仇”结合起来的?
《女吊》开篇提到王思任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直接奠定了全文的“复仇”基调,时值“晚明小品文热”,王思任被众多学者推崇,周作人早期在《乡谈》中便注意到了王思任,后在《〈燕知草〉跋》中再次提到王思任的“反抗”精神,1935年施蛰存亦对其大力推崇并直接借用了王思任一文之名办刊。从创作的逻辑上来看,鲁迅引用充满地域色彩的名言意味深长。
越文化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具有尚武的民风和强烈的复仇意识。尤其是在明末清初更迭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风是清政府眼中危险的存在,王思任对马士英的责骂信中明确指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与此同时,绍兴民间对“朱天菩萨”的信仰愈来愈广,借这种对神话的信仰将吴越文化中的“复仇”精神进行外化,通过目连戏具象其民间文化中所蕴含的复仇精神,鲁迅在书写“目连戏”观众时,也特别提到了屈原的《国殇》,并叙述道:“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4]88鲁迅敏锐地捕捉地方民间的“复仇”文化,将女吊所代表的“厉鬼”信仰与地方反叛明确地结合起来,传达出一个充满“复仇”精神的中国民间文化世界。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10月5日出版的《中流》头条刊出了杂文《女吊》,还补白发表了鲁迅署名晓角的《“立此存照”(三)》。对于发生在上海的“辱华影片”事件,有人主张对美国导演予以舆论谴责,鲁迅则告诫中国同胞: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把中国的“舆论的谴责”放在心里,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有多大的权威。毫无疑问,女吊的复仇精神理念来源于一条宽广、纵深的乡土文化根柢,不过鲁迅并不认为“复仇”一定会成功,在女吊的行为中我们始终未见她采取实际的复仇,进而渗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感,正如鲁迅在“辱华影片”事件所评论的那样,表现出一种欲渴复仇,却又明晰地感觉到复仇的渺茫以及永不忘复仇的历史悲凉精神。源远流长的越文化,越地民间的鬼文化,以及表面柔弱的“装饰性唯美”的魏晋风格,使女吊的“复仇”显现出了与越文化及魏晋风度的一致性,而内心受到压制的阴郁、意念而饱含力度,极具中国化的唯美主义风格。
实际上,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到过类似的复仇精神,他有意提醒“复仇并非民族主义式的,而是为自由之战,或者说,不是利己的,而是利他的”[10]84。换言之,鲁迅并不在意是否复仇,而是在意一种去功利性的复仇,希望“无功利”式复仇,因此鲁迅唯一对女吊的批评便在于她的“讨替代”,这才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不过女吊的追求又无可厚非,她的目的性非常强,听见一个女人,在衔冤悲泣,准备自杀。她万分惊喜,可以去“讨替代”了。她丝毫不掩饰重新投胎的目的,相反,自称正人君子的人在暗地吸血,还满口仁义道德以掩饰自己的行为,“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4]90鲁迅才说“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女吊》是一个‘好鬼’, 是一个‘爱憎分明的鬼’, 有一张见仇人坏人的狠面, 还有一张见好人可怜人的善面。”[11]15堂堂正正的女吊虽是鬼魂,却有可敬之处,与假面之人相较,鲁迅至死对这些面具背后的卑劣越发透彻,由此无法控制地在文末书写了一段疾恶如仇的文字,最后一段文字与他在《死》一文中一条遗嘱照应:“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鲁迅晚年始终保持着一种“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的人生姿态,决绝又带有历史悲凉的复仇精神可以说是鲁迅晚年人生美学的重要部分。
作为鲁迅话语的一部分,《女吊》的复仇精神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不断延伸出新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提到戏曲表现新时代和继承传统都不能偏废,鼓励创作新剧目的同时也要继续整理改编旧有剧目,戏剧如何处理国家的现代化诉求与人民群众的文艺需求问题,地方戏如何反映现代生活,又能为群众所接受?鲁迅的《女吊》对绍剧《女吊》改编意义重大。当时章艳秋对女吊“复仇”精神的加重表演,达到呼唤建构民族精神的目的,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鲁迅《女吊》的评论多是围绕“阶级论”和“妇女论”而展开的,1953年,废名说“鲁迅的《女吊》等于屈原的《国殇》,是就他们对祖国的忠诚说的,其实鲁迅是人民革命时代的先觉,通过中国共产党,他已经知道了人民的力量,有意借这一个女魂写出被压迫者复仇的美丽形象,告诉人民要争取胜利。”[12]1958年,伊兵谈论《女吊》时,将王灵官看作是人民意志的代表,所有如同“女吊”这类被压迫的弱小者都会被官方的人民群体意志拯救,最终导向的是“反对压迫”的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如何应对西方文化冲击,寻找中国本土文化之根显得格外重要,2013年,陈清卿作为戏剧《女吊》的非遗传承人,在她理解《女吊》的内涵时,认为“她自始至终贯串着寻仇两字”[11]15。《女吊》作为绍兴目连戏的重要剧目,其文化内涵、民族风情、群众影响都极为广泛,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地方民间文化代表,绍剧《女吊》与鲁迅《女吊》两种艺术形式的沟通成就了《女吊》再改编的成功,使“戏改”之后的《女吊》兼具民间精神与时代精神。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这篇文章中提到他是学习民间艺术的,这是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鲁迅倾心赞美了绍兴地方戏中的“女吊”,“从‘地底下’发掘出美丽而强悍的魂魄, 正是为了承传民族文化固有之血脉, 以使中华民族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3]
相比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女吊》中“阶级性”“人民性”的解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更重视其中“传统文化”“民族精神”话语挖掘,在这转变中,“复仇”精神的内涵并非以固定方式存在,而是一种不断被重构的文化符号,在建构的途径中,以“女吊”形象为代表的民间并非一种立场,而是以一种方法成为可征用资源,不论是“女吊”形象建构,还是“复仇”精神建构,同属于民间资源再改编的逻辑,换言之,鲁迅对民间资源的频频征用与《女吊》不同时期的解读取向“殊途同归”。
三、民间、民族与文化——中华民族复兴精神建构
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与民间文化有着深刻联系,同时可见鲁迅对民间文化中所隐藏的中华民族之根的敏锐洞察。“《死》是鲁迅的‘遗嘱’,《女吊》可看做是对‘死’的衍义;《死》中论到中国人的生死观时,已提到‘鬼的生活’,《女吊》则是对‘鬼的生活’的描写。”[14]时至晚年,学贯中西的鲁迅为何对死的衍义和鬼的生活要通过故乡“绍兴戏”来说明?从前文可知鲁迅之“女吊”已经不同于绍兴戏中的女吊,而是集合多种文化资源综合而成,换句话说,鲁迅意不在于完美复制绍兴戏中的《女吊》,而是借用绍剧《女吊》这一民间舞台。如伊腾虎丸之言,鲁迅为何独独选择具有故乡特色的女吊,是由于鲁迅“从一般人看作是‘科学’的对立面的‘乡曲小民’们的‘迷信’中看到了可能性,正是从生命的对立面、排摒‘人’事的幽鬼死了还想切近人的那种复仇的怨念和火红的衣色中,找到了那内部生命再生的根据”[15]。鲁迅在被视为民间的故乡绍兴的文化资源中看到了“民族再生”的力量。
但从鲁迅的创作角度而言,只是将“民间”作为方法,而非立场[10]80-88。在鲁迅建构女吊形象过程中,他着重关注的是“民间传统”的独立性、自主意识,比如言说不幸使观众感到战栗,以“讨替代”的行为让世人恐惧,强烈的投胎意愿使“活着”显得如此珍贵,可爱的鬼魂之下有种生命力的迸发,相较于当时普遍存在的萎靡精神,鲁迅的“女吊”是一种生命精神的表征。而综观《女吊》全文,鲁迅潜意识上将女吊的复仇停滞在精神层面,很难采取实际的行动,这也符合当时他对如何回击“辱华影片”的思考,只能停滞在精神层面是鲁迅复仇观必有的困境。鲁迅主张无功利的复仇、纯粹的复仇,但是他在《女吊》一文中又暗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因为此前被损害了,接下来人物的所作所为就拥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和真理性?男吊和女吊实则都是被压迫的形象,而在讨替代的过程中,两个被压迫者之间也有内斗,最终只能动武,同样作为被压迫者,又如何去思考被压迫者内部争斗的问题?鲁迅回避了这一民间文化存在的问题,只能借助于王灵官去解决。
与鲁迅对绍兴民间的文化记忆书写一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回溯”皆是为了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之根,如果说鲁迅的《女吊》是一种个人记忆的艰难寻找,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更偏向于寻找集体记忆。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之下,文化认同危机日渐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如何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鲁迅的《女吊》给予了重要借鉴,发掘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化资源,以此对抗西方话语权威。
四、结语
行文至此,可见鲁迅之“女吊”形象形成的多方路径与“复仇”精神建构的历史脉络极为复杂,“女吊”形象来源考察未尽,从绍剧《女吊》到鲁迅的《女吊》,如复仇精神的“发明”、女吊形象的“浓妆重抹”等新变之处可能是深入了解鲁迅晚年思想的一把重要钥匙。由此,就这篇文章而言,希望通过“女吊”形象源考察、“复仇”精神解读分析两条路径为深入理解鲁迅作品增加一条新的路径,同时,借用鲁迅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征用方式,为当今时代如何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