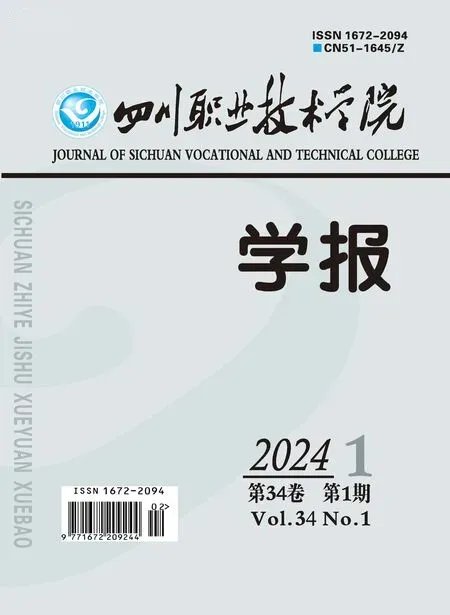汪曾祺短篇小说《八千岁》中的狂欢色彩
2024-06-01邹梦琦
邹梦琦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罗强烈认为:“民间意识作为一种主题原型,始终贯穿着汪曾祺的重要作品。”[1]汪曾祺的小说广泛吸纳社会中的诸多杂语,聚焦于时代中的“小人物”,展示市民朴素的生活,呈现出通俗质朴、充满谐趣的幽默风格。更深一步来看,汪曾祺小说的这种幽默谐趣的风格其实来源于其文学中的狂欢特质,他的小说注重民间叙事,以开朗豁达而非尖酸刻薄的方式讽刺、调笑人物,叙事中时而穿插着插科打诨和俗语表达,营造了狂欢节式的感受。短篇小说《八千岁》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一、绰号中的狂欢化形象
塑造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是小说谐趣风格的立身之本,人物形象是小说的灵魂,小说展开的过程往往也是人物形成、发展的过程。在塑造人物时,除了从外貌、语言、行动上来表现人物,人物的名字、代号本身就可能具有符号意义和情感倾向,有趣的名字自身即具有喜剧效果,它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能指存在,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蕴藏着象征、暗示的意味,能够将人物的性格、命运高度凝练出来,也能够揭示人物身上的矛盾属性。《八千岁》里的人物大多以绰号出场,而且这些绰号都带有民间自由而无拘束的戏谑调侃。不交代真实姓名,人物有如戴上了狂欢节的假面,被修饰了个体的真实面目,以一种戏剧性的姿态呈现,仿佛在进行舞台上的表演,这正是狂欢节的生活本身,“实际上,这就是生活本身,但它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游戏方式……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其中”[2]。
“八千岁”之所以叫“八千岁”,是因为他靠着两块七角钱从一个穷苦百姓发家成了米商。但即使发了家,他依旧保持着俭省的生活习惯,穿着过时的蓝布衫,吃着最简单的食物,因此被人戏称为“八千岁”。人们用一个极小数目的钱来称呼一位富商,是对“八千岁”身份的颠倒,在这种颠倒中,同时揭示了“八千岁”富有与节俭的带有矛盾的双重特质,因而诞生出了引人发笑的错位,造成带有狂欢意味的讽刺与欢乐效果。
和他性格大有不同的“宋侉子”是个浪子,也是个奇人,“宋侉子”不吝惜钱财,但也有来钱的本事,从黑心商人手里买骡子就是他的传奇。“本地人把行为乖谬,悖乎常理,而又身材高大的人,都叫做侉子”,“侉子”一词是带有当地特色的俗称。特意地把行为异常,离经叛道的人称作“侉子”,这其中自然就带有了与常人区分开来和贬低的意味,但这种贬低并非是完全否定的贬损,它是对人行为方式的揶揄,本质上也是对身份的重建。通过称呼其为“侉子”这样的调侃和贬损,来使其行为可理解化、世俗化并以此吸纳进俗世生活中,容纳进入狂欢性质的生活里,人们对他们的贬损也就成为了极具包容性的玩笑。
“小千岁”与“八千岁”一老一少,相得益彰,组成了一组滑稽怪诞的形象。在“小千岁”身上有“八千岁”生命的延续,“他的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只是比他小一号”[3]36,也穿着“蓝布衫”,过着与“八千岁”相似的生活。但“小千岁”又展现出少年人的童趣,在“宋侉子”的说情之下,“小千岁”得以养了鸽子作玩乐,看着儿子养的鸽子的眼睛转来转去,“八千岁”也觉得好玩,由此并引导出了“八千岁”身上原本所看不到的生趣,使得人物形象获得了更新,体现出继往开来、不断更新的开放状态。
“赵厨房”不叫“厨子”而叫听上去更加有格调的“厨房”,就类似于给狂欢节上的“愚人王”加冕了,一个原本卑微的身份职业,通过绰号的称谓将其拔高成了受人爱戴、尊敬的人物。相对的,“八舅太爷”的绰号则是对他的脱冕和“降格”处理。“八舅太爷”虽然是有权有势的军阀阶级,在小说中还是带上了民间化的绰号,关于他的名号,作者这样讲述:“这里的人不知为什么对舅舅那么有意见。把不讲理的人叫做‘舅舅’,讲一种胡搅蛮缠的歪理,叫做‘讲舅舅理’来源于当地人对‘舅舅’的偏见”[3]47。由此可见,八舅太爷绰号的来源同样来自于民间的玩笑,是带有贬损含义的,而非常人对权势阶级的敬畏。这暗示着“八舅太爷”在小说中他其实与其他角色无异,并非高高在上的掌权者,而是与他人混杂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且同样是众人调笑的对象。
不见其人,先闻其名,作者从幽默的绰号里切入对人物的描绘,赋予了其生动的狂欢特征,人物成为了狂欢生活本身,也让浓郁的市井江湖气满溢在了小说的每一个角落,充满生趣的众生百相跃然纸上。同时,用绰号代替对具体身份的强调将人物拉至了同一平面,这同样赋予了写作者俯视的态度,通过以绰号展示人物,汪曾祺已经构建了一个所有人物都平等地生活的小说世界,每个人物都有极强的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作者同等地给予了他们文学形象的鲜活性,使得小说的人物从来都非某一种个性的“独白”,在个性与精神层面实现了群体性的狂欢。
二、市井中的狂欢化生活
夏忠宪曾指出:“情节上一切可能出现的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的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诸如大街小酒馆澡堂船上甲板客厅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4]《八千岁》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与众多的市井场所,通过对“吃”“玩”的市井生活描写,体现了对形而下层面的即物质-肉体层面的关注。在描写这些好吃、好玩的事情上,作者以一种兴味盎然、积极乐观的态度仔细描摹,对于物质-生理层面的享受表现出肯定态度,这不仅仅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层面的,在小说的世界中,“吃”与“玩乐”展现出的是不单属于个人的、全民性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和生活情趣。
“吃”的描写在小说《八千岁》中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正如“八千岁”柜台一头竖匾上所写“食为民天”,《八千岁》中的人物几乎都带有“暴食者”的特质。“吃”能够将外部世界吸纳、吞食进肚子,是与外界融合、互动的重要行为,反映出人与世界之间的开放共生的生活状态,是狂欢色彩的重要体现。
宋侉子长得“人高马大”,吃相豪迈,他“一半是寻钱,一半是看看北边的风景,吃吃黄羊肉、狍子肉、鹿肉、狗肉”,“爱吃面食。最爱吃山东的锅盔、牛杂碎,喝高粱酒。酒量很大,一顿能喝一斤。”[3]39在这段表述中,作家列举了多种食物,仿佛摆酒宴一般将食物罗列出来,“宋侉子”爱好的食物之多、食量之足,以及他健壮的肉体形象就间接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小说中还展示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及众生对“吃”的喜爱。“八千岁”是卖米的,尽管节俭,从他吃晚茶、叫三鲜面的行动中也能看出他并非不爱吃只是不敢吃,“八千岁”的左邻右舍也都在卖吃的。赵厨房做的是满汉全席,排场大,讲究多,工序精,只有办酒席的时候才能吃上一回;草炉烧饼简单方便,配上一碗宽汤饺面也叫人撑肠拄腹,就着壶茶也能让人打个响亮的饱嗝。晚茶是个地方习俗,吃晚茶的茶馆里除了各式的香茶还有“包子、蒸饺、烧麦”,“吃晚茶”就好似一种仪式,是所有人参与其中、共同享受的,小说中展示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而且这是一种所有人参与其中,共同欢乐的活动。
小说中最会吃的还属八舅太爷,“他把全城的名厨都叫来,轮流给他做饭。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3]49,从“八千岁”那儿得了八百之后,豪掷百金,请赵厨房来了套满汉全席,在荷花亭子里从早上十点一直吃到半夜,显然是一场“盛宴”。但“八舅太爷”并非小说中完全的正面形象,其作威作福、欺霸一方的行为虽然在小说的狂欢氛围中一定程度地淡化了,作家却对其不乏嘲讽。“八舅太爷”的宴席并非全民性的,而是他个人的享乐,对于这一次宴饮,作者不曾直接描绘,而是通过“赵厨房”对“八千岁”的转述以及“八千岁”的视角来展现:“八千岁真是开了眼了,一面看,一面又掉了几滴泪,他想:这是吃我哪!”[3]52以“八千岁”的苦来消解狂宴的乐,对于压迫性质的权势阶级,作者保留了一份批判和挑衅,暗含了一种对非全民性的、个人主义的欲望的否定,反而确立起平等性的、无阶级性的狂欢愿景。
玩乐也是小说中的狂欢元素。宋侉子“花鸟虫鱼,无所不好,还特别爱养骡子养马”,他往北边去买骡马,还记得顺道看看风景,虞家母女搬出来时带了些字画,想必也是略通此道,只可惜两个不会营生又过惯了不用干活的日子的女子在那个世道实在难以生存,只好把字画都卖了。“赵厨房”的兴趣是做菜,看他如何对“八千岁”津津乐道那满汉全席上的菜点,就知道他对自己的手艺,自己的职业十分热爱。“八舅太爷”吹拉弹唱,古董字画,样样都要把玩。在这些玩乐中,展现了包罗万象、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而小说中的所有人都生活其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与之游戏。
这些爱吃爱玩的形象寄托了丰腴的乌托邦式理想,蕴藏着生命的活力。《八千岁》中的人物对“吃”很讲究,作家也乐于描写各种食物,因为“吃”是人民最为本质的需求,人与万物必须依靠摄入物质的养分才能得以生长,肯定了“吃”的地位便是肯定了民间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肯定了生长与发展的可能性;在对玩乐的描写中,也肯定了民间生活的创造性、包容性和广阔性,展现了充满笑意的民间生活。
三、杂语中的狂欢化语言
巴赫金主张,“小说中应该呈现时代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声音,即时代的一切重要的语言;小说应该成为杂语的微观世界。”[5]136杂语指的是小说中多元化、多声部的语言现象,反映出时代转型时期的文化特点。在小说中,出现了不止一种语言风格,而具有来自各个阶层、各类体裁、各种行业的话语声音,打破了文学语言的统一性,构建起语言的狂欢化。在这种狂欢中,不同类型的语言平等地发出声音,形成和谐对话的局面。小说《八千岁》的语言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首先是叙述声音的口语化和对话性。小说以“据说”两字开头,立刻就表明了叙述者道听途说的“不可靠”的身份。叙述者并非小说中拥有全知视角的上帝,而是读者面前一个讲故事的说书人,他的讲述是随意的、没有规范的,诸如“他如果不是”“这些人家的大少爷,是连粮价也不知道的”“这地方米店量米兴报数,一边量,一边唱”,这些句子中的“如果不是”“这”“也不知道的的”“兴”的使用,都使得叙述话语带上了鲜明的主观意识和口语的随意性,具有日常口语交流对话的特征。讲述者的在场鲜明了起来,读者也可以窥见其亲切的姿态。
关于叙述的对话性,还可以从讲述过程中叙述者不断使用疑问句向读者提出设问来考量。设问意味着提问却并不包含对回答的期待,小说中的设问强调了读者的在场,且肯定了读者与作者之间有一种相互理解的默契,因此问题不必由读者来确实地回答,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知根知底的对话关系。如:“按当时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银元,八吊钱还不到两块七角钱。两块七角钱怎么就能起了家呢?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这些,谁也不去追究,然而死死地认定了他就是八千钱起家的,他就是八千岁! ”[3]35“八舅太爷”喜欢“借”别人的字画,“他也不白要你的,会送一张他自己画的画跟你换,他不是上过一年美专么?”[3]49
其次,小说中混杂着许多行业内的话语及地方特色的俚语、俗语表达,也体现了小说语言的杂语特征。“二马裾”“油儿”是服饰行业的称法;“头糙”“二糙”“三糙”“高尖”,这是米商行业的术语;“相骡子”是做骡马买卖的“宋侉子”的行话;“扫榻留宾”,“洗妆谢客”是风尘女子专用的说法;“杂花色”“一壶三点”则是吃晚茶时的讲究……。此外,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也使用了大量的俗语和俚语,如“甭打听”“多谢你老”“乖乖”等日常话语中的俚语,“是儿不死,是财不散,看开一点”“包子有肉,不在褶儿了”,这些是同样来源于日常生活的俗语。在民间形成、来自各行各业的话语声音在小说中同时平等存在,被作者以恰当的口吻艺术性地组织起来。这些语言之间不存在相互间的争锋或贬斥,而是彼此交融构成小说的语言生活,吸收并纳了各行各业的独特风姿,赋予小说宽广的社会视野。
再者,在小说《八千岁》中,也不乏一些“高雅化”的表达,如将“八千岁”的儿子称为“令郎”,形容“八舅太爷”的宴席生活时使用了“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对仗表达。“八舅太爷”“他请人刻了两方押角图章,一方是阴文:‘戎马书生’,一方是阳文:‘富贵英雄美丈夫’——这是《紫钗记·折柳阳关》里的词句,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学里最好的词句。”[3]49在使用这些高雅、凝练且具有一定阶级性和文化深度的表达时,往往是作家讽刺、嘲笑的时刻,这些话语虽然高雅,却并非如表面般代表着雅趣,而是放在了可笑、野蛮的人物身上,“令郎”之后便接上“小千岁”与其父亲同样没有生趣的生活,“八舅太爷”的“高雅兴趣”更是作者对其仗着有权有势附庸风雅、欺世盗名的讽刺。作家对于“高雅”语言的运用,目的反而在于反抗、嘲弄权威,在于消解“高雅”,颠覆传统的语言秩序。此外,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小说中有一处仔细描写了“拴骡子的牲口槽”、骡子的屎味和骡子撒尿的场景。这类排泄相关的描写是对肉体-下部的关注,也是对物质-生理的关注。被“高雅”文学所不齿的粗鄙场景反而被作者以细腻而诗意的语言展现出来,极具挑衅与颠覆意味。
杂语的引入解构了传统文学的“文学性”,尤其反叛了文学语言可能具有的“官方影响”和“传统影响”,将文学从知识分子阶级高高在上的位置拉到与人民大众等身。在对文学的高雅神话祛魅之后,小说借使用“非文学”的杂交话语使得小说的语言对于社会面貌的吸收容纳更加森罗万象,应有尽有,也将文学作品本身“脱冕”到与大众读者同等的平面,通俗而容易让人亲近,更加诙谐而幽默。
四、狂欢中的危机与嬗变
狂欢化来源于民间的节庆活动,必须明确的是,狂欢节仅仅是生活的过渡时期,而非常态,是特定时期的一种颠覆与狂欢。“节庆活动在其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上,都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危机、转折关头相联系的。死亡和再生、交替和更新的因素永远是节庆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5]70狂欢节式的感受在激情、富足的欢乐背后,同时也存在着危机与变化,狂欢式的欢乐总是带有讽刺、颠覆的意味,这便喻示着另一股带来危机的势力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才需要以狂欢来与之对抗。在《八千岁》中,呈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处于危机与嬗变中的时期,小说中隐藏着时代的动荡与变迁,那些戏谑的人物绰号、丰盛的美食盛宴、夹杂着俚语、口语、诗文的杂语运用,其实都呈现了20世纪以来现代性冲击对传统生活的掌控、入侵以及对它的抵抗姿态。
“八千岁”的形象与小丑的形象有诸多相似,他是一位靠自己的双手和勤劳肯干发家的小商人,而他吝啬、拘谨的生活方式又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八千岁”身上的对于现代性危机的暗示,最深刻地体现在“大部分米店都已经不用碾子,改用机器轧米了”,“八千岁却还用这种古典的方法生产”。他的行为与其身份错位,是普通人眼中带有一点“疯癫”意味的“傻瓜”,但其并非可笑的“吝啬鬼”本身,而是暗示着一种假定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不存在狂欢节世界的平等、自由与富足,他戴着“吝啬鬼”面具,反映着另一种人即旧世代中被压抑的穷苦百姓的双重性形象,其身上的滑稽可笑,是对社会中掌权阶级的讽刺与挑衅,也是对质朴的传统手工劳动的守旧。
一方势力起来,就有一方势力落败,做买卖的小市民发家了,“宋侉子”、虞家母女、“赵厨房”的日子都是随着旧的官宦贵族势力的衰落而衰败的。
不妨先从夏家祠堂说起,夏家原本是望族,聚族而居的宅子又大又漂亮,如今已经破败不堪了。祠堂的房屋都很高大,现在租给了做生意的“八千岁”做仓库。中国人最信仰的不是佛教道教,而是祖先祖上,可如今夏家已经没有来祭祖的了,这说明旧的礼教已经崩坏。
旧礼教的崩坏是狂欢得以呈现的原因之一,它既解放了一类人民,又难免引发新的危机。正是在这崩坏的旧礼教之下,出了“宋侉子”这样离经叛道的浪子,父母还在世时就把家产挥霍了一半,父母离世后就把田产卖空了。倒不是说他是个不肖子孙,而是旧的那一套不兴了,懂得变通的贵族子弟不得不开始找寻新的出路。虞家母女的命运也暗示了旧官僚秩序的垂暮,不然也不至于让一个盐务道的女儿流落风尘。“赵厨房”也属于手艺人、劳动人民,他原本为官僚阶级做满汉全席,现在则可以为所有人做饭,做满汉全席的那套物什锁在箱子里好多年。在“宋侉子”、虞家母女、“赵厨房”的身上,都因旧制度的坍塌而经历了高贵身份的“脱冕”,得以进入狂欢的生活,在他们身上,藏着旧制度的“死亡”与即将到来的“新秩序”的新生,带有狂欢化的双重性质。
“八舅太爷”是第三股势力,也是当时最霸道、最蛮横的那批人——军阀。“八舅太爷”是战争中的新生势力,但还未完全掌控主导权,因而他的身份也并非绝对高高在上的官方统治者,还没有能力终结狂欢的局面。不过“八舅太爷”身上的狂欢特质也来源于他早期的民间生活,他曾经装过土匪、干过黑帮,还拉过车,体验过那种对于社会制度带有反抗性、颠覆性的放浪生活。“八舅太爷”依旧是两面的,在他的身上,既具有对于权力、制度的挑战与游离,又不乏对于权力的追逐与向往,渴望着从旧社会的“死亡”中走进新秩序的“新生”,并在其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认为,他这样的人物正暗示着时代中虎视眈眈的那一类人,正是危机的缔造者。
在“八舅太爷”的人生经历中,还有关于现代化危机的揭示。“八舅太爷”闯荡的那些年曾去过上海,听见过那些妓女们说“又不是阎瑞生,怕点啥!”那这个阎瑞生是谁呢?妓女们为什么要怕“阎瑞生”?阎瑞生是1920年上海“阎瑞生案”事件主角,上海人阎瑞生是一位恶少,他嗜赌成性,挥金如土,因为赌马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他铤而走险,杀害了名妓“花国总理”王莲英。该事件在1921年就被改编成电影并轰动一时[6]。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正是中国最为繁华的都市,现代化机械的发展造就了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电影、赌博、艳情色彩的谋杀案,这些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带来的冰冷、危险而带有刺激性的产物暗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安因素,这些在小说中是没有明确地提及的,也正因如此,小说中狂欢化的氛围没有被破坏,过去时代的潦倒与新时代的危机以生与死的矛盾形态隐藏在狂欢化的世界中,构成狂欢节世界的两重性,使得小说能够以小见大,在诙谐与幽默中展现出极具包容性、开放性的整体历史意义上的宏伟姿态,这也正是汪曾祺小说的深厚、精妙之处。
五、结语
汪曾祺的写作被视为现代汉语写作的一种革新,他的创作跟随着文学观念发生转变、历史局势不断更迭的时代变迁而不断探索、求新。狂欢化颠覆、包容的特征出现在其小说中也就理所应当了。狂欢理论的文学意义是巨大的,它揭示了狂欢化文学在狂欢表层下隐含的逻辑联系和深层意义,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策略[7]。从狂欢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小说《八千岁》在人物形象、小说内容、语言风格、小说内涵上的特征,便可以看到作者以一种诙谐的、民间性的叙事,揭示了风云变化之际中国社会中潜藏的危机与变化,在微观中展现了一个衰落与希望并存的宏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