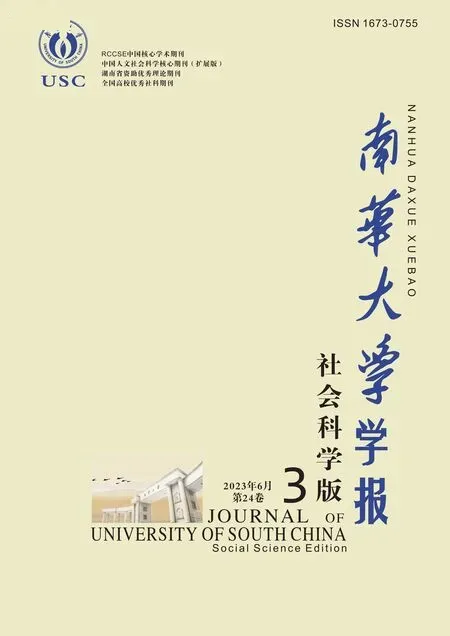沈从文小说中的雾意象
2024-01-07卢晓玉
陈 娟,卢晓玉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在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仿若一幅淡雅而又瑰丽的自然画卷,吸引着人们去阅读和欣赏,而在这个别样的世界中,最缥缈梦幻和最变化莫测的当属雾意象。沈从文笔下的雾具有多重表现形态,并在不同情境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但在对沈从文的研究中,历来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多在其小说的叙事性及乡土情怀方面,而对于小说中频频出现的雾意象则涉及较少。本文主要对沈从文小说中的雾意象进行专门探讨,剖析其具体表现形态,并探究沈从文作品中雾意象的创作成因,以丰富和拓宽现有研究领域。
一 时间之雾:雾起雾落的光影飞逝
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通常出现于晨起与傍晚。山城湘西向来多雾天,在沈从文笔下,对这种晨起与夜暮时间流转之雾有着多样叙写:
首先是代表早晨的时间之雾。在《如蕤》中,沈从文用“晓雾”直接点出时间,在日头的光芒迸出海平面后,又写道:“海面一片银色,为薄雾所包裹。早日正在融解这种薄雾。”[1]143日出意味着雾将转薄,而海面仍旧被雾气包裹着,意味着这是一个充满着朝气、正在苏醒的早晨。在《芸庐纪事·动静》一文中,沈从文从“冬日长晴,山城雾多。整个城市都包裹在一片湿雾里”[2]217写起,这是天还未亮的时候,人们沉醉在梦乡中,雾气笼罩了一切,显得非常静谧。之后山城出现了一些声音,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几个军营的喇叭也按时响了,小商贩的叫卖声也开始闹腾了起来,于是“湿雾迷蒙中却有尖锐的鹰声啼唤”,城镇变得热闹起来。等到“河上湿雾完全消失”时,“大约已将近九点钟”[2]218,这是本城人吃早饭的时间了。晨雾多为湿雾,晨起之时,地冷水暖,从河海中飘荡而来的热空气遇冷凝结,便形成了湿雾。日出而暖,雾到浓时雾转薄,浓重的湿雾在太阳的照射下逐渐稀疏,渐渐消逝。沈从文以细腻之笔攫取了晨雾的状态及变化特点,用雾来点明时间,渲染氛围。
其次是表征夜晚的时间之雾。在《一只船》中,作者写道:“远处水面起了薄薄的白雾,应当是吃饭时候了。”[3]而入夜之时,温度渐渐转凉,水面上的空气遇冷凝结,便形成了雾气。这是傍晚到了,起雾预示着晚饭时间已至,到了日落而息的时间了。《如蕤》中,“将近黄昏时……望一抹轻雾流动于山下平田园村间”[1]163。夕雾轻盈,随风而动,男子与女人便享受在这一片刻的惬意之中。《三个女性》中日行西下的时候,“背了落日的山,已渐渐地在紫色的薄雾里消失了它固有的色彩”[4]111。那刻,夜雾笼罩了山峰,原本翠绿的山在雾的笼罩下渐渐失色,锋利的边缘也逐渐模糊了。在《边城》中,也有对落日时夜雾的描写,“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银色薄雾”[5]120。这里的雾在黄昏日色的装扮下显得更加绚丽多彩。在《夜的空间》一文中,作者写泊船行驶到码头附近,各种载满货物的大船纷纷泊到江中心时,用雾描写了由白日的忙碌转入夜色后的静谧:“在雾里,巨大的船体各画出一长条黑轮廓。”[6]朦朦胧胧的夜雾中,一切都不再明晰,也不需要再像白日般那样明晰了。在沈从文笔下,这样的文本还有很多,如《逃的前一天》中:“太阳一没……仿佛淡牛奶一样的白色东西,流动着,溜泻着,浮在地面,包围了近山的村落,纠缠于林木间。这是雾。”[7]226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雾气在太阳落下后的种种变化,也预示着村落由白天转向夜晚。在《船上岸上》对于月夜的描写:“已全为一种白白薄薄烟雾笼罩,天上是一片青色,有月亮可以看得出了。”[7]156到了夜晚,雾气也逐渐消散,只剩下了白白薄薄的一层。夜雾相比晨雾来说变化更加多端,一是借助于夕阳的变化,雾的色彩也在随着日光的变化而变化;二是在由日入夜、由动转静、由清晰到模糊的转化过程中,夜雾相对晨雾来说,变化的过程更容易被人眼捕捉到,也更易被观察到其确切的形态与色彩。
在沈从文小说中,一般不是直接陈述以点明晨起与夜暮的时间流转,而是经常通过雾气的扩散与凝聚及其出现的浓淡变化来言明,这未尝不是推陈出新的一种有趣表达。在这笔墨缓缓流淌出的自然意蕴中,我们从雾中感受到时间,感受到雾起雾落的光影飞逝,这又何尝不是一番别样的风采呢。
二 地理之雾:雾气弥漫的湘西世界
在沈从文的笔下,雾气不仅在起落转合中昭示着时间,也是对湘西这个独特地理环境的勾绘。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湘西地处三面环山、朝北开口的马蹄形地貌,有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经过,又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湘西多雾的特点。沈从文描写了这个雾气弥漫的湘西世界,不仅有对水面上雾气多样形态的细腻刻画,也有对雾色变化过程的生动描绘。
首先,沈从文极大发挥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原生态的雾都湘西,而其中描写最多的当属水上之雾。沈从文在短篇小说《渔》中写道:“下游远处水面则浮有一层白雾,如淡牛奶,雾中还闪着火光,一点二点。”[8]45在这里,作者将白雾巧喻为淡牛奶,便生动地将雾的颜色、浓度体现了出来。雾本身是凝聚的小水滴聚合在一起的状态,在水面之上的透光程度也不强,于是火光便只是一点二点的闪烁着:“白雾似的成团成饼从海上涌起,包裹了大山与一切建筑。”[1]147用“成团”“成饼”将雾的动态描绘得趣味盎然,既有对雾的动态变化的展现,又准确地将起雾的浓度与强度点出,高密度的雾快速从海上涌起,以至于周围的山和建筑都很快地被包裹了进去。在《阙名故事》中:“这样大的雾,是不常见的雾。雾像一种网,网罩到水面,河岸于是仿佛更阔了。”[8]258在这里沈从文将雾比作网,恰当地描绘出了雾笼河岸之阔大幽美的景象。《芸庐纪事·动静》一文写道:“湿雾照例从河面升起,如一匹轻纱。先是摊成一薄片,浮在水面,渐如被一双看不见的奇异魔手,抓紧又放松。”[2]220这里对雾在水面上变化的描写堪称精彩,先是把雾比作轻纱,以体现其美丽轻俏的形态,接着又将雾的变化形容为“摊成一薄片”,雾气由条状慢慢散成了一大片,其变化如魔法世界中的魔手在操纵一般,时松时紧,变幻多姿。
其次,地理之雾又随着日色的变化而生出多端姿态,这在沈从文笔下有生动描绘,如“面前的海原来已在黄昏中为一片银雾所笼罩,仿佛更近了些。海中的小山已渐渐的模模糊糊,看不出轮廓了”[4]127。这里的雾用颜色表现,不同于一般的白色、灰色,用银色可以更传神地描绘出雾色之美,以展现黄昏中雾气萦绕水光粼闪的美丽画面。而在“轻柔而滚动,缓缓流动,然而方位却始终不见有何变化。颜色由乳白转成浅灰,终于和带紫的暮色混成一气,不可分别”[2]221中,可以看出,作者用了三种颜色来描写雾色的变化,从乳白到浅灰再到带紫,短短几句,便将暮色间雾气的变化过程细致入微和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
湘西是水乡,关于雾的描写一定离不开水,沈从文将雾意象融汇在水的柔美之中,更添其诗意。在日光变幻的过程中,沈从文将雾意象颜色的变化寄托于日色流转,显示出了雾色变化的瑰丽多端。这两种雾色相结合,便构成了沈从文小说中地理之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情感之雾:蕴于雾中的各色情感
情感的寄托在意象的描写中是再常见不过的,沈从文小说中的雾意象也同样如是。人物情感一直是沈从文多加刻画的重点,以至于金介甫曾这样评价他对于人性描写的痴态:“沈对于人性思想,不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古代的或现代的思想,永远是那么朝气蓬勃,而又博采百家、探索追求。”[9]89
(一)人物的孤独、矛盾与隔阂
雾,大部分是白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雾气可以像是白色的屏障一样将人包裹在里面,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切断,而这种隔断正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孤独、矛盾与隔阂。
在《新摘星录》中,沈从文用雾来表现人物当时的孤独:“这紫雾占领了海面同地面,什么也看不见。我感到绝对孤独,生命俨然在向深海下沉,可是并不如何恐怖。”[1]213-214雾气蒙蔽的不仅是当时的海面和地面,还有作者当时的心,雾气将他与他所爱的人隔离开来,生命沉浸于雾中。在《传奇不奇》中,雾则用来表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隔离,主要讲的是凤凰县西部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故事。“一个大雾早上,终于被几个高枧乡下壮汉,充满狩猎的勇敢兴奋,攻占了干洞口。”[10]83满家和田家作为攻守双方,在僵持了17天后,终于进行了下一步的动作——攻占了干洞口后,高枧的汉子们将辣椒与硫磺掺和在一起,朝洞里扇入大量毒烟,不过半天,洞里的人便全被闷死了。满家和田家这两个家族群体,是在凤凰县西部的这个小村落上土生土长起来的,他们并没有接触过外部世界,也没有人来到这个村落里教给他们不好的言行,可是他们仍染上了一堆恶习。大多数作品中,农村群体都是质朴向善的存在,可是在这篇小说中,雾气仿佛给这一出农村恶势力械斗做了掩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隔离透过雾气传达出来。
此外,在《冬的空间》中,雾则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隔阂。女孩玖关心哥哥,临走前还要嘱托他多听医生的话,可是她二哥却并不放在心上。“男子A没有做声,匆匆地向广场走去,把身体消失到乳白的薄雾里。”[8]245薄雾隔绝了男子与女孩玖之间的交流,亲情便也无处可依、无地可着,空空的落了下去。男子A在担心着自己的事情,他周旋于女人之间,在为另一个女性害相思,他完全忽略了妹妹的情绪。乳白色的雾气是哥哥一手拉筑起来的城墙,雾气两端是两颗不能联结的心,一方主动,一方推拒,妹妹遥望着哥哥,哥哥却决绝而去。
白色的雾气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在沈从文小说中,这道雾障变作了人与人之间孤独、矛盾与隔阂的载体,沈从文在对雾气的平缓叙述中道出了剑拔弩张的矛盾以及情感的孤独、阻隔。
(二)生与死的缥缈不定
雾作为生死的象征,体现得最为突出的作品当属《边城》。在《边城》中,雾意象一共出现了四次,而这四次又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烘托着人物不同的情感,象征着生与死的缥缈不定。
第一次是翠翠对于生死存失不定的害怕,“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薄雾。翠翠望到这个景致,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5]120。这个想头是什么呢?是翠翠在担忧爷爷会在什么时候死去。雾本身就有着缥缈不定的意蕴,生死也如是。命运掌握在谁的手中,又会在何时戛然而止,这些都是未知的。翠翠是害怕的,也是迷惘的,她本是一个生长在雾乡里的天真自由的小姑娘,但这时的她却显得心思复杂了起来,她接受不了设想中爷爷的离世,这种淡淡的忧愁萦绕在翠翠心中,也给读者留下了愁绪。第二次,雾的出现发生在祖父将船拉过岸边时,“祖父把手攀引着横缆,注目溪面升起薄雾,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轻轻地吁了一口气”[5]129。此时的祖父在薄雾里看到的,是自己不久于人世后翠翠将来的生活。爷爷希望趁自己还在翠翠身边时,能为她寻求到一个好人家,他希望翠翠未来的人生过得满足快乐。在第三次出现时,雾依旧寄托着爷爷的心绪,“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老船夫心中异常柔和了”[5]167。老船夫想起了翠翠的母亲,想起了她母亲与爱人双双殉情的过往,他不想让翠翠再重蹈覆辙,希望能给她安排一个好的归宿。这之前船总顺顺家里托人来给翠翠说媒,翠翠以为顺顺是她的爱慕对象二老傩送遣来的,不禁害羞得脸红和脖颈全红了,可是说媒的对象却是大老天保,祖父中意的人也是大老。第四次时,翠翠和爷爷来到院子里,坐在月光下的岩石上,“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白雾”[5]188。这时的翠翠与爷爷话着家常,雾气氤氲的溪面也静谧如画。可是平静只是暴风雨前的一时安好,雾气的不定性寓意着生与死的缥缈不定。尽管祖父想要在自己生前为翠翠安排好后路,可是后来,天保出海遇难,祖父在洪水中死去,傩送也外出远行,最后还是只剩下了翠翠孤身一人。翠翠的身世与祖父的命途皆仿佛这一团雾气,生于缥缈,化作虚无。
(三)前途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除了表征生死,沈从文在小说中还经常用雾来象征前途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对于个人而言的前途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在《边城》中有突出表现。傩送背井离乡是否还会回来,甚至是生是死,都是一个未定之数。而翠翠的未来又将寄托在谁人的身上,也是不为人所知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5]224溪面上的薄薄雾气中,掩藏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掩埋着他们的前路。未来将走向何处,就像雾气一样难以捉摸不得而知。每个人的命运都没有定数,但在这个山城中,在这个小姑娘身上,未来的不确定性则以更加矛盾的方式突出表现出来。在爷爷离世后,翠翠已经没有了可以依靠的亲人,她唯一挂念着的人又还未回来,翠翠虽然心里期望着,可实际上也并不知晓傩送是否还会回到她的身边。
其次,是对于集体而言的前途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巧秀与冬生》中写道:“随后却处于一种极离奇情况下,被寒气一压,一齐崩坍下来,展宽成一片一片的乳白色湿雾。再过不多久,这个湿雾便把村子包围了,占领了。”[10]59“离奇”事件开始于巧秀的逃离,结束于冬生的失踪。这一片一片的湿雾将村子里的新生一代困厄其中,逃离变得困难,失踪变得轻松。巧秀的逃离源自她不满意强制的婚配关系,她要去追寻自己的爱情理想。巧秀出走成功了,但她的妈妈却永久的被埋葬在了这个地方。巧秀妈作为一个寡妇,经常被人谩骂欺负,尽管有人利用强迫她,可她仍不屈服。可就在巧秀妈和打虎匠的事情被发现之后,族内之人纷纷指责她,老族长更是直接下了沉潭的决定。他们将巧秀妈剥光了衣服放置在众人面前,任人观看,巧秀妈挂着石坠站在河中央,船摇摇晃晃将翻未翻,这时老族长心狠手辣地走过去掀翻了船。巧秀逃走了半个月,巧秀妈已经长眠潭底15年。这份悲哀是会在巧秀身上延续下去,还是让她侥幸逃脱呢?如果雾气之中愚昧落后的本质不曾改变,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巧秀出现,巧秀的出走或许可能是希望的开始,但绝不会是这份悲剧的结束。
最后,是对于国家而言的前途未来的不确定性。在《芸庐纪事·动静》中,雾代表着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困境。在北方战起后,军团长抱着病躯义无反顾地再次投身了战场。而这时学生们也为他的精神所打动,临别之际争相到水岸边送别他,他们跑着喊着,说“中国万岁,武装同志万岁”!这时间,“河面慢慢的升起了湿雾,逐渐凝结,且逐渐向上升,越来越浓重,黄昏来时,这小山城同往日一样,一切房屋,一切声音,都包裹在夜雾里了。”[2]246小村庄只是一个缩影,被雾气笼住的不止这一个村庄,而是整个中国。1943年的中国仍处在14年抗战之中,人民大众仍旧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战争前景还不明朗,就仿佛一团雾气朦胧了前方的路途,看不清未来。可黑夜终会过去,面前的迷雾终会消散,我们终将迎来胜利,新中国的光明也一定会来到。
四 沈从文小说中雾意象的成因
雾气缭绕的湘西给了沈从文创作雾意象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的熏陶也让他攫取到了雾意象之美,而对雾意象的青睐也符合沈从文的创作偏好,是其写作过程中的主观选择。
(一)生活环境的自然养成
一个作家的长成往往离不开他所成长的这片土地,湘西作为沈从文的家乡,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别样的雾蕴之美。从沈从文自小的生活环境来看,他在小说创作中选取雾意象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
沈从文童年时一直生活在湘西,湘西多雾的环境为沈从文的创作奠定了基本的环境基调。湘西凤凰县地苦多雾,雾气是他惯看的景色,沈从文14岁前一直与家里人住在一起,他的童年一直在湘西多雾的风景人物中浸润着。14岁的他厌倦了学堂,决定跟随地方土著部队当兵,去游历大千世界。6年间,沈从文先后随军经行黔北、川东及湘西边境各县,又行经沅水一带,让他对各处的雾气风景、各色人物都有了深刻的印象。行千里路的同时,他也在读万卷书获取着大量知识。这段远游经历不仅让沈从文大大增长了见识,也给他后来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素材。沈从文十几岁外出在军队游历的这段时间,他见惯了溪上、湖面与山间的雾象,这是他所历经的现实,也是他可以随地取材的用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而也正是在这种环境的浸润中,沈从文能够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看到雾的千变万化、多姿多彩,并用自己充满灵性而又浪漫的笔触将这雾气笼罩下的多情湘西缓缓道来。
(二)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
沈从文幼时在旧时书斋里学习,“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内中有十多本破书,由《包句杂志》《幼学琼林》到《论语》《诗经》《尚书》。通常得背诵”[11]。这段学习经历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字基础。在家里的时候,沈从文因为母亲识字念书,所以能够在其教导下读书认字,而父亲的大书房也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等后来进了部队,他当司书时见到秘书官有两本厚厚的《辞源》,便爱不释手,天天央求着去借各种各样的书。
沈从文博览群书、以书为友,在这种传统诗词文化的学习氛围中,他阅读了大量古诗词。在传统诗美表现格局中,以“雾”为题的古诗词不绝如缕,如李峤的《雾》,“涿鹿妖氛静,丹山霁色明。类烟飞稍重,方雨散还轻”;杜牧的《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李商隐的《碧瓦》,“雾唾香难尽,珠啼冷易销”;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等等。在这众多的作家作品中,沈从文尤爱李商隐,特别爱读李商隐的诗,“喜欢诗意清新……凡是擅长写出真性情,哪怕带点艳情的抒情诗,他都喜欢”[9]93。这些都给沈从文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早早便对雾意象的使用熟稔于心。在后来的学习中,沈从文揣摩旧体诗的遣词造句,也在日常的写作中结合自己的审美体验细腻书写,从而使其笔下的雾意象既不失雅韵,又具有别样之美。
(三)诗意风格的主观选择
沈从文偏爱舒缓诗意的写作风格,而雾作为一种清虚缥缈、浮游而动的意象,显然是符合他的创作取向的。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雾意象的诗意与作家的诗性相结合,使作品呈现出了田园牧歌式的情调,雾意象在沈从文的笔下发挥了独一无二的魅力。
在自传中,沈从文强调他受通俗作品的影响较大,可从他的创作轨迹中看出,沈从文偏向于诗意自然的描写。沈从文在小说中大量使用雾意象,以雾书写晨起与夜暮的时间流转、水光与天色的辉映变幻、孤独与忧愁的情绪蕴含,以及对于隔阂、生死、家国未来的象征等等。在这种对雾意象的细腻摘取和生动描绘中,沈从文也彰显出了自己的诗意之风,在其笔下,诗意如雾气般缓缓流淌,流出了不同的人生,讲述了多彩的故事。可以说,雾意象的田园之风与创作风格的诗意之美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这既符合沈从文的创作偏好,也是其写作过程中的主观选择。
雾笼边城,雾迷人境,沈从文的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关于湘西自然环境、情感体验以及生命品格的美好向往。自发表文章伊始,雾意象便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屡见不鲜,并对其典雅清新的写作风格发挥着重大作用。雾意象的诗性语言与内容的完美融合,是沈从文小说审美价值彰显的必要条件。这片雾气给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带来了诗意与清新,并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启迪着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