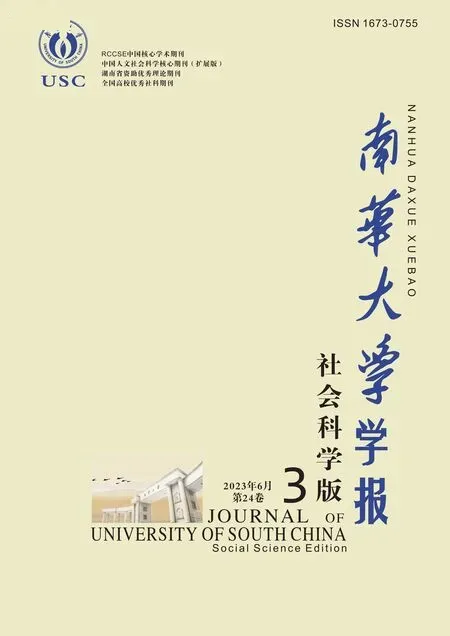延安时期乡愁乌托邦的抒写与建构
——以《黄河大合唱》为例
2024-01-07王俊虎赵文杰
王俊虎,赵文杰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是艺术性、大众性、民族性的高度融合,在现代化过程中影响极为深远,“乡愁乌托邦”是现代性发展的核心概念,是带有中国经验的审美意识形态,其特殊性在于通过回望过去而获取一种抵抗现实困境与建设未来的精神指引。“乡愁乌托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愁,是表达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中,面对被德国、俄国、日本连连侵略的痛苦现实要超越这个阶段的诉求[1]。《黄河大合唱》作为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抗日救亡作品之一,主题深邃浑厚,曲调雄壮有力,充满了雄浑、阳刚、愤慨、悲壮,它是唤醒民众的号角,也是奋勇杀敌的锐器。这部作品对中国的文学史、音乐史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后世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将以这部具有先锋性的文艺作品为核心,从战时语境下空间情感记忆以及乡愁理念书写来分析延安时期乡愁乌托邦的描绘与建构。
一 乡愁理念下的家国关怀
自乡土文学发展以来,乡土社会作为一个蕴含丰富意义的概念,有别于现代社会的城市中心和主流空间。乡愁作为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富有乌托邦层面的意义。乌托邦通过乡愁的形式回望过去,又指向未来,试图以乡愁的反思寻求民族内在的精神力量。乡愁乌托邦作为独特的情感结构贯穿于乡土文学发展进程的始终。
1920年代初,周作人引入乡土文学的概念,他倡导与异域文学对应的“本土文学”,以不同的风土展现不同的民俗。1930年代中期,鲁迅、沈从文、茅盾等著名作家提出乡土小说的理论阐释,鲁迅作为中国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在阐明乡土文学观念的同时着重言明地域色彩、为人生、启蒙主义等关键点;京派代表沈从文开启了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乡土文学世界,认为乡土小说应具有泥土的气息与原始的同情;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乡土小说作家倾向于政治叙事,反映农村现实、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不同于1930年代鲁迅、沈从文、茅盾等作家,1940年代解放区作家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创作乡土题材的作品,提出“赵树理方向”,提倡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强调“农民文学”“农村文学”的概念。1950年代以后乡土文学逐渐走向变异与沉寂,这一时期创作主体提出“农村题材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理论观念。1980年代,乡土文学再度兴起,刘绍棠的创作引发论争,汪曾祺也论述关于“风俗画小说”的观念。1990年代冯骥才等作家将其所描绘的都市民俗小说纳入乡土小说,着力于“乡土形象”的塑造。中国的乡土文学经过引介、分化、沉寂再到复兴发展、理论研究一直在演进拓宽,核心概念“乡愁”得以延续。对于这些本土的主体创作者而言,他们对于乡土小说的理解、故土家园的情感多方面地影响着他们关于乡愁的书写。
最初的“乡愁”蕴含浓厚的怀旧情感,指的是对亲友的思念以及对故时旧景的怀念。古时离乡的游子漂泊在外,由于地域空间上的阻隔思念亲友,牵挂家乡故土,流露出孤独的情绪,表达情感的遥寄。这是中国传统最为典型的文化乡愁形态,这种形态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在过去,中国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的封建时代,家族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束缚了文人的情感指向,极度重视血缘之间的联系与伦理情感的发生,深化了文人落叶归根的乡愁情结,它所表现的文化意蕴、情感抒怀都是传统文化的内在体现。
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乡愁”逐渐从单一个体化的思乡情绪扩张到普遍性层面,过去传统的文化乡愁延续并裂变出新的乡愁形态,即家国乡愁。文化乡愁的延续表征的是对文化状态的关注,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民族文化的归属,此处的乡愁不再囿于地域层面的空间位置,而是文化层面的归依。家国乡愁则是由主体对故土家园、家国的命运忧愁而产生,将乡愁意识上升到了忧国忧民的层面。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霸占中国领土,国家与人民被敌人的铁蹄肆意践踏,四万万同胞弃家而逃、背井离乡,随处可见国人流离失所、客死异乡的惨状,乡愁是这代人普遍的情绪。个体的家园形成国家,乡愁就是国愁。当时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文本层出不穷,主体创作者们以笔为枪,诉说人民与国家的悲惨境遇,表达凄楚悲怆又慷慨激昂的热烈感情。家国乡愁理念下产生的爱国主义不同程度上激励着人民奋起反抗。因家国分裂而产生痛苦惋惜,继而抒发倾诉家国之情,热切期待战争胜利、国家统一,这就指的是乡愁乌托邦下的家国情怀。
不同于以往创作者的乡愁书写,光未然(原名张光年)的创作之路似乎更为艰苦。光未然出生于湖北省光化县老河口镇的一个普通家庭,小学时在东家的影响下开始了旧体诗的创作。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震惊全国,消息传到老河口后,十二岁的光未然毅然加入反帝爱国活动当中,参与进步青年的戏剧演出,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问答》《中国青年》等进步书籍,点亮了他心中的信念。后来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光未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地下联络点暴露以及革命形势恶化,无奈离开老河口。沿江南下后,光未然坚持学习考入武汉中华大学,学习之余正式走上了他的创作之路,他开始以笔名“光未然”发表抗日诗作。一九三七年,光未然在上海的一次歌咏大会上认识了冼星海,二人因共同的创作追求结识为友,为二人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七七事变后,光未然加入了“中国文艺者战地工作团”奔赴抗日前线,因八一三事变爆发,未能行成。一九三九年,光未然前往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光未然的创作之路因战争前行,也受战争羁绊,他的乡愁从最初被迫离乡变成家国大难时中华儿女共同的乡愁。《河边对口曲》中描述了在妻离子散、国破家亡的环境下,两个流离失所的同乡人在异乡相遇,互诉衷肠的场景。他们怒斥家仇国恨,但在痛苦过后痛定思痛,化国仇家恨为斗争力量,投军打仗,保家卫国。诗人用最朴素的言语刻画被压迫者们对故土的刻骨思念,对国家命运的慨叹,受屈辱后的反抗决心以及对家国富强、转危为安的殷切期望,讲述血泪真实的同时抒发对战乱后流离失所的离散者的同情和对家国命运的无尽忧虑。光未然将丧失家园的离愁与别绪倾注在文本中,灌注了乡愁理念下的家国关怀,呈现了战时语境下乡愁与国情的杂糅书写。可见乡愁可以从个体、亲友、故乡、家园延展至国家层面,怀乡思友只是其中的一层,更深层次的表达为对国民的忧患意识化为乌托邦冲动,即借中华儿女内心对于未来美好愿景的渴望,鼓舞人民守卫祖国,直至河清海晏、国家太平。
二 地域空间下的情感记忆
延安素来是文学创作主体关注的中心,黄河更是被反复研究书写。九曲蜿蜒,承载历代文学书写者的袅袅文思。王之涣叙“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之连绵逶迤,刘禹锡抒“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之辽远壮阔,温庭筠歌“黄河怒浪连天来,大响谹谹如殷雷”之汹涌怒涛,现代诗人余光中写“一掬黄河”之沧桑温柔。由此观之,地域空间书写不仅指创作主体所处的客观地理位置,更承载着创作主体的情感记忆、经验以及体验。
著名诗人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旨在颂赞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悠久历史。在他笔下,黄河就是中华民族的乡愁乌托邦。一九三八年秋,武汉沦陷。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继而转入吕梁抗日根据地。翌年一月中旬,抵达延安。在与老友冼星海畅谈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时,光未然思及途中所目睹的黄河船夫们与惊涛骇浪奋勇搏斗的情景,他毅然决定将自己横渡黄河与沿河行军之时的体会化为诗作,诉说满腔激情。黄河于光未然而言,不单是人物主体所处的地域空间,更是承载着他鲜活情感记忆与经验的文化载体。
除却词作者之外,《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一九三五年,冼星海回国参加抗日运动,一九三八年又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一九三九年除夕联欢会上冼星海观看了《黄河吟》的朗诵演出,感动不已。于是,他在延安一座简陋的窑洞里为这部不朽的史诗创作谱曲,终于在三月三十一日这天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作曲[2]。水乡生活是冼星海音乐创作的底色,也是他的情感起源和生活底蕴,故而他谱写出充满力量、鲜活生动的旋律与音符,让人如临其境,神往心驰。
“波澜壮阔的黄河穿过辽阔的宁夏平原,用一泓生生不息的狂涛巨浪,在雄浑连绵的黄土高原上切割出气势磅礴的千里长峡——晋陕峡谷。这里,崖壁峥嵘,河床裂岸,黄流澎湃,烟雾迷蒙,万里长空中轰鸣着如雷的涛声。在这个刀削斧劈般的峡谷南段,有一个水浪冲蚀岩层陷落形成的巨大断崖,中间有一个壶口形状的深槽。当宽阔狂野的河水在这里收束飞泻时,就像一把茶壶倒水,瞬间形成一帘激波飞浪的瀑布。”[3]可见《黄河大合唱》真实复现了黄河之畔狂涛怒吼,声震千里的场景。从《黄河船夫曲》中“波涛啊,高如山!浪花啊,打进船”到《黄河颂》中“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从《黄河之水天上来》中“水上金光迸裂”“河面银光似雪”到《黄水谣》中“奔腾叫啸如虎狼”;从《河边对口曲》中“河边流浪受孤凄”到《黄河怨》中“黄河啊,你不要呜咽”,“洗清我的千重愁来万重冤”;从《保卫黄河》中“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到《怒吼吧,黄河》中“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光未然对于黄河意象的塑造独具匠心,可谓是延安时期的经典之作,他将中华民族的兴亡与黄河的历史紧密结合,为黄河的意象书写赋予了新的生机,多层次的铺垫叙写黄河的性格,将其形象典型化,予以血肉的灵魂。
《黄河船夫曲》以紧张激烈的号子开头,刻画船夫与狂风骇浪搏斗之景,“咳哟!划哟”、“咳!划哟!”齐整接连的号子展现出团结的力量与勇于革命的战斗精神。其后,《黄河颂》里光未然对滚滚黄河之壮美慨叹,吟唱深沉的颂歌,对伟大且坚强的黄河给予无限赞美,民族自信心油然而生。《黄河之水天上来》是诗人对于黄河性格的丰富与深化,它似一条“日行千里的飞龙”,又像一只“疯狂发怒的野兽”,自天而降,千变万化。在这个乐章的朗诵词里,黄河痛诉着中华民族之灾难,见证着中华民族之反抗。唤起悲鸣与反抗,昭示希望与决心,告诫中华儿女们牢记苦难的回忆,谱写壮烈的悲歌。《黄河谣》部分的创作采用今昔对比手法,控诉了日本的入侵给黄河两岸人民带来的沉重苦难,字字真切。《河边对口曲》描述黄河两岸难民相互哭诉,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给底层人民生活带来的苦痛,进而化悲痛于决心,借太行山为全国身处水深火热的同胞们指一条革命斗争的道路。再看《黄河大合唱》中最为低沉惨淡的《黄河怨》,以怨而起,刻画了一个被侵略者凌辱后痛不欲生的妇女形象,她向滔滔河水哭诉、喊叫。然而,她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个体形象呈现,她是备受欺辱的中华民族的缩影。伴随残忍血腥的画面与凄惨凌厉的叫声,中华民族破釜沉舟奋勇向前。层层铺垫,高潮迭起。《保卫黄河》是抗日军民传播最广的主题歌,滔天巨浪,声震寰宇,令侵略者们闻风丧胆。诗人借描绘河岸两边的山岗与高粱隐喻抗日武装日趋成熟,讴歌抗日英雄、游击健儿奋勇杀敌。此时此刻的两岸乡民不再沉浸于痛苦的回忆,而是化为乌托邦冲动的力量,对抗日寇决一死战。《怒吼吧,黄河》作为《黄河大合唱》的终章反复咏叹,展示了怒吼的黄河犹如全国的同胞一起怒吼,万丈波涛,声势浩大。这八个乐章层层深入,高度描摹地域空间,勾勒出一幅中华儿女保家卫国、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宏伟图景。在光未然笔下,黄河是一个凝聚本土记忆的特定空间,超越物理空间的想象限制,它被塑造为一个特定意义之下的乡愁乌托邦,承载着华夏儿女的家国破碎、离恨乡愁。以《黄河大合唱》展示黄河之畔的战乱景象,激励一代代中国人民来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个体无法避免受到战乱的影响。家园破碎、哀鸿遍野所带来的压力、孤独、断裂层见叠出,这使得个体产生强烈的不安定感、漂泊感。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家国故土蕴含着特别的意义,其所带来的乡愁更体现着无数个体内心挥之不去的斑驳情愫,复杂而深刻。或是深山穷谷、萧瑟衰微,故土存封的记忆却弥足珍贵,它为个体的成长赋予精神信仰。现代语境下的乡愁乌托邦是扎根于社会空间、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等因素发生变化后形成的新的情感结构和经验之中的,它不完全等同于古时人们因赶考、天灾、人祸等因素而背井离乡,现代性的乡愁溯源于知识分子自觉的选择,其意义在于他们脑海中所记忆的故土随着多种因素的影响直至消亡,无法获得再体验,而只有借助创作的想象追忆过往,期冀未来。
黄河作为一种抒情象征性的情感投射,是个体精神落魄、萎靡颓唐的避难之所,是治愈离愁苦痛的一剂良药。黄河与中华民族伟大坚强的气质形象连接起来,交互反复地象征着系统与主体的意识建构起深厚的民族认同与民族情感、强烈的归属感与脉脉温情。然而,光未然未曾夸大或者刻意渲染个体内心乡愁的愁苦,而是呈现出抗战危难、家园遭到破坏之时人们顽强抵御的精神力量与担忧家国的情怀,浓浓哀愁伴随惆怅、感伤流入人心,汇入黄河。推而论之,在延安时期的抗战背景下创作主体对于乡愁乌托邦的表达寄生于个体脆弱单薄的生命以及对现实的忧患。他们着眼于现实,结合自身的情感记忆表达对乌托邦化的故土家园的情感体验,忠实地书写艰苦抗争中迸发的民族力量以及人性的真善美。
三 战时语境下的乌托邦书写
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形式与其所处时代下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形势密切相关,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呈现与思想情感表达的载体则更甚。根植于特定时代情境所产生具有标志性的个体记忆交汇重组、共同构建成为时代记忆,这往往在主体创作的过程中再现为独特的时代经验,触动着同时代人的情感。对于创作主体而言,时代经验或隐或显体现于主体的观念、意识、经验中,同时也影响着对文本内容的选择,尤其是在战时语境下,创作所呈现出的个体与时代斑驳交错的经验特征,通过“表征出‘未来’的‘感觉结构’,给人以强大的精神和情感力量。”[4]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产生巨变,战火纷飞导致主体创作者们固有的创作方式、状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走出书斋,或去往城镇、农村,或扎根部队、根据地。他们走进现实,从前线到大后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从“民主、自由”到“为抗战而艺术”“为祖国而歌”。
诗人光未然曾予以自己“革命诗人”的创作身份。所谓“革命诗人”,首先的身份是“革命者”,其次才是“诗人”本身,这是特殊战时语境下“革命”与“文学”相结合的结果。他把文本创作与时代紧密结合,甚至于抒写个人生活、景物也融入了政治情感色彩。他用“革命者”的身份勇敢战斗,拿起“诗人”的笔参与革命,自觉主动地将双重身份融合,以诗为歌投身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据他自述,他在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时,就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光未然心中激荡着革命理想与战斗激情,他在毛泽东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话的指引下积极配合战争时代的需要,写下了既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又表达人民呼声与时代旋律的《黄河大合唱》。《黄河大合唱》表现了人民的情感与时代的精神,以满腔激情呐喊“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口号。这与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革命文艺的地位作用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也相联系,阐明了文艺工作者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社会生活来转变立场,到群众中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文艺道路。特殊的时代赋予光未然独特的创作经验。在“为抗战而艺术”的年代,革命的火种遍洒全国,也埋进了每一个革命者的心中。光未然将目光聚焦时代变迁主题,走出了象牙塔,感受时代变幻,关注国家命运,关注人民疾苦,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大众的情感,走入大众的视野,将艰苦时刻的乡愁上升到乌托邦的层面,使之成为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和依托力量。他的创作情怀无疑展现了崇高的使命感与伟大的责任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名文艺战士在烽火年代的革命热血与战斗激情,这种对革命的追求是战时语境下关于政治意识的自觉表达,也是战争年代主体创作者共同的选择和追求,这与战争对文学生态的影响有莫大的关联。
与此同时,抗战诗歌形式的革新与抗战救亡音乐的发展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诗歌与音乐相结合变成“可歌”的诗,进而发展为抗战文艺的先锋形式,契合了战时语境中为抗战服务的目的。这一独特的文艺形式集合于《黄河大合唱》之中。一九三八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光未然加入其中并负责抗敌宣传的工作,他与音乐家冼星海、张曙同居一室,并与冼星海合作,一人作诗,一人谱曲,为鼓舞民众做出了巨大贡献。二人在延安接连创作《黄河大合唱》这首伟大的颂歌,以昂扬的激情刻画奔腾不息的黄河,颂赞了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憧憬了新中国的未来。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演剧三队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进行《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出,邬析零任指挥[6]。《保卫黄河》是其中最受抗日军民欢迎的一首歌曲,在20世纪40年代初成了工农兵群众大会的必唱歌曲。《黄河大合唱》是诗与乐的珠联璧合,其创作以及后来每一次的演出都是这个时代下个体共同的情感记忆,创作主体的选择是对时代主题的服膺。
现实的家园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遭到冲击,乡愁乌托邦最终指向的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文学的创作将每一个个体联系在一起,构建出具有归属感的共同体,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经由一代又一代人民以生命的代价发展造就而成的,推动着中华民族奋勇向前。生死存亡的时刻,民族精神可以唤起震撼人心的力量,号召、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未来,走向胜利,走向光明。黄河养育了中华儿女,也孕育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它关乎民族的历史与命脉,也昭示着使命与未来,它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乡愁。《黄河大合唱》的产生正值抗战相持阶段,作品的问世彰显出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与必胜信心,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军民与敌寇长久战斗的意志与决心,这是民众的迫切要求,更是主体创作者的迫切愿望。这部作品作为永恒的文艺经典,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起到巨大的作用,无论是从情感的抒发还是受众的情感共鸣,都达到了艺术作品的高标准。
作为战时语境下的乌托邦冲动,《黄河大合唱》将中华民族的精神寄予对未来家园发展的期望上而非沉溺于被损毁破坏的过去,借助“黄河”呼唤出人民群众内心蕴藏的民族情感,呼唤民族的复兴与未来,激励中华儿女争取战斗的胜利,抗击敌军,重建家园,向世界宣告中华崛起之必然趋势。
四 结 语
延安时期乡愁乌托邦的书写以抗日救亡主题创作为主,这一时期文本的特点是把乡愁乌托邦作为在现代化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面对现实生活时的精神力量和情感依托。可以理解的是,现代性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属性介入传统社会结构时,给现代社会带来的断裂、巨变产生了极大的失衡与不安定感。创作主体通过塑造“乡愁乌托邦”来回溯故乡、家园,质疑现代性的介入发展,表达自身在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态度,以及如何对“乡愁乌托邦”进行解构。笔者分析创作主体在反思文化的冲突、知识的重构等社会裂变过程中的定位与认识,同时也思考关于“乡愁乌托邦”的精神困境以及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