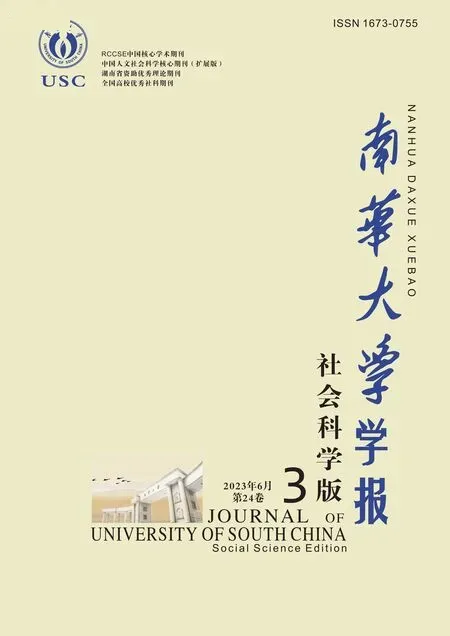发现漏罪或犯新罪后原减刑裁定效力之检视
2024-01-07谭浩乾
周 洁,谭浩乾
(太原科技大学 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刑罚执行期间,对服刑人员做出减刑裁定后,发现漏罪或其又犯新罪的,原减刑裁定是否继续有效不仅关系到刑罚执行制度与刑罚裁量制度在行刑阶段的衔接,还会间接影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行刑时的贯彻,因此原减刑裁定效力应否受罪犯刑罚执行期内的漏罪或新罪的影响而失效在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存在分歧。
一 发现漏罪或犯新罪后原减刑裁定效力之争
【案例一】减刑后发现漏罪案:杨某恩2001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3年被山东省高院减为有期徒刑19年6个月,2014年因新发现的漏罪盗窃罪、拐卖儿童罪,山东省菏泽市中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简称《刑法》)第70条和2012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罪犯因漏罪、新罪数罪并罚时原减刑裁定应如何处理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撤销了原减刑裁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该判决生效后杨某恩向菏泽市中院提出了申诉,认为其漏罪刑罚应与减刑后的原判刑罚并罚。菏泽市中院最终维持了原判决,仍按《意见》规定,以减刑裁定做出前的无期徒刑与漏罪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①。
【案例二】减刑后犯新罪案:徐某荣2006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于2008年、2011年分别被江苏省无锡市中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3年和1年10个月,2012年被假释(考验期至2014年),因假释考验期内犯盗窃罪于2014年被淮安市淮安区法院以原减刑裁定裁减后的原判剩余刑期1年10个月12日与新罪刑罚3年有期徒刑并罚,做出有期徒刑3年的生效判决。2016年淮安区检察院因淮安区法院未按《意见》规定以去掉减刑裁定的未执行刑罚与新罪刑罚并罚而向无锡市中院提起抗诉,经审理,无锡市中院接受了该抗诉意见,撤销了一审法院的数罪并罚部分,否认了所有原减刑裁定效力,用去掉减刑裁定后的未执行刑罚与新罪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②。
案例一为对罪犯减刑后又发现漏罪的情形,案例二为对罪犯减刑后又犯新罪的情形,对于该两种情形,原做出减刑裁定的法院难以预见,面对漏罪、新罪需重新做出裁判的法院如何进行数罪并罚,成了实务中与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对此有必要从学理研讨、最高司法机关的立场和司法实践做法三个层面进行梳理评析。
(一)学界观点论争及检讨
1.学界观点论争
理论界对该问题较一致的观点为,刑罚执行期间罪犯的漏罪或又犯的新罪不应一律使之前的减刑裁定失效,应根据漏罪、新罪反映的罪犯具体情形分别认定。根据对发现漏罪和犯新罪的不同认识,不同学者分析的角度与理据各有不同。
首先,有学者根据发现漏罪是否基于服刑人员的主动交代,犯新罪的时间或犯新罪的主观罪过区分不同情形下原减刑裁定的效力。如:对于减刑后发现漏罪的,根据漏罪发现的时间,持漏罪不影响减刑裁定说的学者认为,减刑裁定做出后发现漏罪的,不对减刑裁定效力产生影响,其理由为如果漏罪影响减刑裁定效力,会变相对罪犯强加无期待可能的主动交代漏罪的义务[1]。根据漏罪发现的不同情形,持主动交代漏罪减刑裁定有效说的学者认为,如果漏罪是因罪犯主动交代而获悉的,原减刑裁定仍有效;持被动交代漏罪减刑裁定无效说的学者认为,如果漏罪是通过其他途径发现的,原减刑裁定失效,其理由为罪犯对漏罪的隐瞒,表明其内心未真正悔改,不符合减刑核心标准[2]。该观点已被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文简称《规定》)采纳。对于服刑期间犯新罪的,从犯新罪的时间角度区分,持减刑前犯新罪减刑裁定无效说的学者认为,罪犯服刑期间在减刑裁定做出前犯新罪的,其减刑裁定因做出了根据错误,应当无效;持减刑后犯新罪减刑裁定有效说的学者认为,在减刑裁定做出后犯新罪的,原减刑裁定仍有效,因为减刑裁定做出的根据不存在错误[3]。从犯新罪的主观罪过层面区分,持故意犯罪原减刑裁定无效说的学者认为,如果新罪为故意犯罪的,原减刑裁定失效;持过失犯罪原减刑裁定部分有效说的学者认为,如果系过失犯罪的,原减刑裁定不应全部失效,其理由为故意犯新罪体现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大于过失犯新罪[4]。该观点也已被《规定》吸收借鉴。
其次,从减刑依据与效果的不同情形出发,持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有效说的学者认为,依据《刑法》第50条“死缓犯的特殊减刑”规定做出的减刑裁定及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裁定(即所有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效力不受漏罪、新罪影响而失效,即认为案例一中应以减刑裁定改变后的有期徒刑与漏罪刑罚并罚,其理由为以上减刑裁定若受漏罪、新罪影响而失效,罪犯事实上会经受两次死刑缓期执行考验期,被判处两次无期徒刑,且维持减刑裁定效力是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5],该观点已部分被《规定》采纳;持应当减刑的减刑裁定部分有效说的学者认为,依据《刑法》第78条“应当减刑”做出的减刑裁定应根据漏罪、新罪所判刑罚情况决定其是否失效,其理由为“应当减刑”的服刑人员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过重大贡献[6];持应当减刑的减刑裁定无效说的学者认为,依“应当减刑”规定做出的减刑裁定过于体现刑罚功利价值,缺少对减刑实质条件的考察,因此其应受漏罪、新罪影响而失效[2];持可以减刑的减刑裁定无效说的学者认为,依《刑法》第78条“可以减刑”做出的减刑裁定可因漏罪、新罪而失效,其理由为该种减刑裁定仅为酌定减刑[6]。
最后,从减刑次数的角度分析,持撤销最近一次减刑裁定说的学者认为,罪犯服刑期内犯的新罪不应使所有减刑裁定失效,仅应通过撤销使最近一次减刑裁定失效,其理由为全部撤销原减刑裁定是对之前减刑工作合理性的间接否定,且不利于罪犯后续改造[7]。
2.学界观点检讨评析
对于漏罪不影响减刑裁定说、主动交代漏罪减刑裁定有效说和被动交代漏罪减刑裁定无效说,笔者认为:漏罪因被动发现而影响原减刑裁定效力的做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罪犯主动交代漏罪,但如漏罪不影响减刑裁定说所说,会对有漏罪的罪犯强加主动交代漏罪的义务,因为该种观点实质上与减刑制度的性质相违背,具有对罪犯的惩罚性与强制性,并且即使该种观点为司法解释采纳,但罪犯不了解相关司法解释,其服刑时一般不知晓交代漏罪的规定,因此不会真正起到促使罪犯主动交代漏罪的作用。对于减刑前犯新罪减刑裁定无效说和减刑后犯新罪减刑裁定有效说,因减刑裁定做出的实质条件为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罪犯于监内犯新罪之事实为减刑裁定做出时的必然依据,因此前一学说具有合理性。对于新罪的故意犯罪原减刑裁定无效说和过失犯罪原减刑裁定部分无效说,二者的内在依据为不同形式新罪体现出的服刑人员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大小不同,笔者认为该两种学说具有合理性,但过失犯新罪不能反映罪犯之前改造效果,不足以否定原减刑裁定做出的依据,笔者认为其不应影响原减刑裁定效力,故意犯新罪说明罪犯存在人身危险性或改造效果不佳,因此其对原减刑裁定效力的影响有合理性,同时考虑减刑制度性质与刑罚执行的刑罚目的,笔者认为应根据故意所犯新罪之轻重与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而部分否认原减刑裁定效力。对于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有效说,笔者认为罪犯有漏罪、新罪时维持原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效力对于实现对漏罪、新罪处罚时的罪责刑相适应,新罪“先减后并”并罚规则的协调有积极意义。对于应当减刑的减刑裁定部分有效说,依“应当减刑”做出的减刑裁定主要体现刑罚功利价值,不具有对减刑实质条件的考察,不利于刑罚预防目的之实现,且其仅具有准予减刑的强制性,无效力维持的强制性与维持前述改变刑种减刑裁定效力的积极意义,笔者认为其可因新罪而失效。对于可以减刑的减刑裁定无效说,依“可以减刑”做出的减刑裁定既无效力维持的强制性,也无做出的强制性,笔者认为其可因新罪而失效。对于撤销最近一次减刑裁定说,结合以上对各学说观点之分析,故意犯新罪表明了此时罪犯人身危险性向改造前状态的反复,实质上是防止再犯的个别预防目的的落空,因此故意犯新罪对原减刑裁定的影响评价范围应为全部。
(二)司法解释立场态度之演变
理论界围绕漏罪、新罪对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影响的研讨实际上影响了最高司法机关对此的立场。2012年之前,理论界对该问题已出现论争,2012年生效的《意见》规定的内容符合了部分学者的观点;2017年生效的《规定》部分吸收了此前理论界对该问题的论争。故司法解释对该问题的立场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完全否定原减刑裁定效力的司法态度。最高法在2012年首次对减刑后发现漏罪和再犯新罪的所有情形做出了全面释明。2012年《意见》对该问题的规定为:因发现漏罪或犯新罪而数罪并罚时,原减刑裁定减去的刑期不计入已执行的刑期,即《意见》认为漏罪、新罪会使之前的减刑裁定失效。
第二阶段,区别情形认可原减刑裁定效力的司法解释立场。2017年《规定》③吸收借鉴之前理论界对该问题的学说,对减刑后发现漏罪和又犯新罪的不同情形,予以进一步细化,在区分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与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的基础上,对漏罪、新罪对减刑裁定的影响做出了不同规定。对于发现漏罪后的减刑裁定,如果是服刑人员主动交代的漏罪,其是否继续有效应由有管辖权的法院重新裁定,予以确认;如果是被动发现的漏罪,则在减刑裁定削减的刑期内酌情重新裁定。对于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规定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的法定减刑裁定除漏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外,事实上仍有效;由死刑缓期执行裁减为无期徒刑后又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裁定及死刑缓期执行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减刑裁定失效,实际执行无期徒刑,同时规定将前判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时至新判生效日执行的刑期在之后减为的有期徒刑内扣减;规定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裁定失效,新判实际执行无期徒刑时,则前判至新判生效时执行的刑期应在第二次减为的有期徒刑内扣减,同时,若漏罪刑罚轻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时,则第二次减为有期徒刑的时间限制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时的一半。即发现漏罪后,四种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中,仅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减刑裁定可不受漏罪影响,其余三种则受漏罪影响并通过“先并后减”的并罚规则失效。
对于犯新罪的,规定所有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不因新罪失效,新罪刑罚与减刑裁定做出后的未执行刑罚并罚;其他情形下,新罪是故意犯罪时,规定原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受新罪影响而失效,新罪是过失犯罪时,原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仍有效。
(三)司法实践适用情形概览
2012年《意见》出台后笔者在北大法宝检索到的适用《意见》的504篇裁判文书④反映的司法实践情况:在2017年《规定》生效适用前,因有明确司法解释作依据,对于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在因漏罪、新罪数罪并罚时,法官均认定原减刑裁定失效;对于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原判刑罚与新罪刑罚并罚时,法官采用承认其效力的变通处理方式,即以裁变后的刑罚与新罪刑罚并罚,原判刑罚与漏罪刑罚并罚时,法官则以裁变前的刑罚与漏罪刑罚并罚,即以“先并后减”的并罚规则使其失效(例如案例一)。2017年《规定》出台后,笔者在北大法宝搜集到的适用了《规定》第33条至37条规定的405篇裁判文书反映的司法实践情况:对罪犯有多个减刑裁定的情形,法官会严格依据《规定》条款,对其效力重新进行评价,依法做出裁判;对于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法官则依据《规定》条款决定其并罚时是否失效;对于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法官一般会同时依据《意见》与《规定》条款决定其并罚时是否失效。
梳理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之演变可发现,2017年以前,原则上减刑裁定受漏罪、新罪影响而无效,《意见》未吸收学界已有观点,坚持实现刑罚的改造功能,将罪犯漏罪、新罪的否定评价扩大到罪犯之前的减刑裁定,表现出了对罪犯悔罪与改造表现的否定。这虽然便于法官之后对减刑裁定的操作与罪犯的持续改造,但该规定之适用也会产生使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结束后未故意犯罪或有重大立功的死缓犯经历两次死刑缓期执行的问题。2017年之后的总体趋势是从完全否定原减刑裁定效力到逐步分情形认可部分原减刑裁定效力,根据发现漏罪的途径及其体现的罪犯人身危险性和改造情况,发现漏罪后的原减刑裁定由以往的全部无效到酌情恢复其效力,并部分维持原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效力。根据新罪反映出的罪犯人身危险性、罪过形式,犯新罪前的减刑裁定由以往的全部无效到维持原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效力,即采纳了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有效说,并明确仅故意犯的新罪影响原减刑裁定效力,即部分采纳了过失犯罪原减刑裁定部分有效说。该种趋势使得对上述问题之裁判应对更加科学合理,兼顾了量刑制度与行刑制度的和谐统一。
《意见》与《规定》的不同之处为是否因罪犯的漏罪、新罪而完全否定原减刑裁定效力,《规定》部分肯定原减刑裁定效力的立场变化,一是对刑罚改造与感化功能的并重,《意见》完全否定原减刑裁定的立场仅是对刑罚改造功能的坚守,未将刑罚感化功能予以重视,《规定》在坚守刑罚改造功能同时,充分重视刑罚感化功能对罪犯监内改造的激励,进一步回应实践中改变刑种减刑裁定的罪犯发现漏罪或犯新罪后的裁判应对问题的同时实现刑罚个别预防目的。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度落实,《意见》完全否定原减刑裁定效力的立场仅对减刑裁定做出后犯新罪的罪犯体现了严格的一面,对减刑裁定做出后未交代漏罪的罪犯未能体现出宽缓的精神,宽严失衡,未能在行刑阶段有效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规定》则明确对死缓犯的特殊减刑裁定与改变无期徒刑的减刑裁定在因罪犯漏罪而无效后相应扣减刑期及放宽之后减刑时限的规定,实现对发现漏罪罪犯与犯新罪罪犯处理的宽严平衡。三是将行刑制度与量刑制度相协调,使实践中法官对发现漏罪罪犯及犯新罪罪犯的减刑裁定处理与《刑法》数罪并罚的三种规定衔接。
二 发现漏罪或犯新罪后维持原减刑裁定效力之正当性辩正
为维护生效刑事裁判的既判力和稳定性,依法做出的减刑裁定之效力应在总体上维持稳定。为鼓励服刑人员持续积极改造,减刑后过失犯新罪不应影响原减刑裁定效力,故意犯新罪应区分不同情形,确认其是否影响原减刑裁定效力。为保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行刑阶段的贯彻落实,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不应因漏罪、新罪而失效。
(一)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坚守
“人权保障是罪刑法定原则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精髓所在。”[8]禁止刑法对犯罪人不利的溯及既往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关注的是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减刑裁定做出后因发现漏罪或犯新罪而失效,不符合上述罪刑法定原则对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同时,对服刑人员的漏罪或新罪的否定评价溯及至之前做出的减刑裁定,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禁止对犯罪人不利的溯及既往派生原则的核心价值。因此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以保障罪犯人权的基本立场出发,原则上应维持做出的减刑裁定效力。
(二)对刑事裁判既判力的维护和确认
学理上认为,依法做出的刑事生效裁判会产生执行力,其属于刑事既判力中的肯定效力,终局的刑事裁判(不包括减刑裁定)是既判力肯定效力的载体。减刑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属于司法管理事务,根据学界主流学说,其不应与刑事既判力相提并论,故减刑的适用不会违背刑事既判力,甚至相反,一定程度上会起到明确刑事既判力肯定效力的作用[9]。减刑裁定作为与判决具有同等地位的有拘束力的司法决定,作为中立的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做出的减刑裁定本身独立于原判决,应当具有与原生效裁判相同的稳定性与权威性。据此,从明确原判决既判力与维护减刑裁定稳定性与权威性的立场出发,笔者认为,减刑裁定做出后,原则上其效力应维持稳定,例外情形下符合一定条件的方可使其失效。
(三)对服刑人员积极改造的肯定和鼓励
学界对减刑性质有权利说与奖励说两种学说,奖励说认为减刑是刑罚执行机关对达到一定改造效果的服刑人员的奖励[10],权利说认为减刑是赋予罪犯的以自己努力缩短刑期的权利[11]。依据《刑法》第78条与2017年《规定》第一条之规定,最高法为《规定》召开的发布会通稿中的释明:“减刑、假释的根本目的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是刑罚执行过程中对积极改造罪犯的一种奖励性措施。”⑤我国减刑的实质条件是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属奖励性质的减刑,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以使其进一步改造自身从而实现顺利复归社会是设立减刑制度的目的。在刑罚执行阶段,预防目的是刑罚首要目的,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中后者又是行刑过程中主要的考量因素,改造与感化是刑罚个别预防具有的功能,其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感化功能间接通过包括减刑在内的行刑制度实现,感化功能实现的同时又能激励罪犯进行改造,实现改造功能。因此,原则上减刑裁定效力应维持稳定,使感化功能持续发挥作用,肯定对罪犯的改造表现,促使罪犯自觉配合改造,最终达成防止再犯的个别预防目的。减刑制度体现奖励性质的同时,也有指引、约束罪犯行为的功能,该功能之发挥同样需稳定性为保障[12]。故维持减刑裁定效力可间接发挥减刑制度正向指引罪犯服从改造,规范狱内行为,矫正原错误思维,重造适应社会人格的功能。
因此,为契合我国减刑制度的奖励性质,激励罪犯监内积极改造,对于学界围绕漏罪的所有学说,笔者认为无论漏罪为何种方式发现,均应维持原减刑裁定效力。对于学界围绕新罪的故意犯罪原减刑裁定无效说与过失犯罪原减刑裁定部分有效说,笔者认为过失犯新罪不应影响原减刑裁定效力,故意犯新罪应根据其性质轻重确认是否维持原减刑裁定效力。对于应当减刑的减刑裁定部分有效说与可以减刑的减刑裁定无效说,依《刑法》第78条做出的减刑裁定,笔者认为维持其效力不具有前述积极意义,因此其可因漏罪、新罪失效。
(四)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和落实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根据分别为报应主义(对已然之罪的惩罚)与功利主义(对未然之罪的预防),通过已然之罪的惩罚预防未然之罪是刑罚设立的根本目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容便包括了刑罚目的[13]。刑罚执行阶段的减刑制度本身就是我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具体体现,罪犯服刑期内犯新罪体现的人身危险性不同于漏罪反映的人身危险性,对原判刑罚依罪犯服刑期内人身危险性变化做相应调整是罪责刑在出现新情况时的应有表现。
根据以上对2017年《规定》的分析,罪犯犯新罪后原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效力不因新罪而失效,但其被发现漏罪后,原改变刑种的四种减刑裁定中的三种减刑裁定(死缓裁减为无期徒刑后又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裁定、死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减刑裁定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裁定)因漏罪而通过《刑法》第70条的并罚规则失效,这三种减刑裁定在受漏罪或新罪影响时的相反结果(即罪犯犯新罪后具有的该三种减刑裁定不会因新罪失效,而其漏罪被发现后具有的该三种减刑裁定会因漏罪失效),使具有以上三种减刑裁定之一的罪犯,犯新罪后所判之刑罚轻于发现漏罪后判处的刑罚,从而导致事实上的罪责刑不相适应,虽然上述死缓犯的特殊减刑裁定与改变无期徒刑的减刑裁定在无效后,《规定》设定了相应扣减刑期与放宽之后减刑时限的奖励,但后者仅对解决前述漏罪、新罪影响下的减刑裁定失效导致的罪责刑不相适应问题具有部分积极作用,事实上的罪责刑不相适应问题依然突出。罪犯服刑期内犯新罪体现的人身危险性高于漏罪反映的人身危险性,对被发现漏罪罪犯的减刑裁定的处理不应严格于犯新罪罪犯的减刑裁定以保证罪责刑相适应,同时基于前述原则上维持做出的减刑裁定立场,被发现漏罪罪犯的改变刑种减刑裁定也应调整为与犯新罪罪犯的改变刑种减刑裁定相同的处理规定,即被发现漏罪罪犯的改变刑种减刑裁定,不因与漏罪刑罚并罚失效。
综上分析,对于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笔者认为维持其效力具有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积极意义,其不应因漏罪、新罪而失效。
三 发现漏罪或犯新罪后原减刑裁定效力之合理检视
结合以上三个角度的分析,罪犯减刑后又发现漏罪的,应维持所有原减刑裁定效力;罪犯减刑后又犯新罪的,应维持所有原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效力,过失犯新罪的,应维持所有原减刑裁定效力,故意犯新罪的,根据新罪罪行的轻重,酌情裁定原减刑裁定效力,例如,新罪应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管制的,应由有管辖权的法院酌情决定原减刑裁定继续有效,新罪应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原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应失效。
(一)发现漏罪或犯新罪后维持原减刑裁定效力的条件
根据上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角度的分析,对于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其效力应不受漏罪、新罪的影响,由裁变后的刑种与漏罪、新罪刑罚并罚,同时《规定》第36条对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在进行数罪并罚后除其漏罪被判为死刑缓期执行外实际执行无期徒刑,此种例外规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法定减刑裁定效力,为发现漏罪时维持原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效力提供了借鉴。据此,笔者认为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减刑裁定和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后又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裁定,原判刑罚与漏罪刑罚并罚时,应将其对原判刑罚裁变后的刑罚与漏罪刑罚按照刑法第70条进行并罚;对于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裁定,同样应将其对原判刑罚裁变后的刑罚与漏罪刑罚并罚,即所有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事实上仍有效。
对于减刑后发现漏罪的情形,由于新罪表现出的人身危险性大于漏罪反映的人身危险性,且新罪发生于刑罚执行期间,实质表明了罪犯改造表现的反弹,故意新罪尤其如此,但漏罪并未发生于服刑期内,仅于此期间获悉,事实上未反映罪犯改造实际,不能成为否定原减刑裁定的合理理由,且如上述漏罪不影响减刑裁定说所说,罪犯主动交代漏罪无期待可能,隐瞒漏罪是常态,因而发现漏罪后,对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也应维持其效力,无需再由有管辖权的法院重新进行裁定。
综上,服刑期内发现漏罪的,无论是改变刑种的减刑裁定,还是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均应维持其效力。即上述案例一中应以减刑裁定裁变后的有期徒刑与新罪刑罚并罚。
(二)罪犯故意犯新罪后原减刑裁定效力须由相关法院结合罪刑轻重参酌确定
减刑裁定做出后罪犯又故意犯罪的,表明其人身危险性仍较高,个别预防的刑罚目的未完全实现,此时需结合新罪应予判处的刑罚轻重,评估其是否符合减刑实质条件。在评估中,对所犯新罪轻重的考虑,认为应以“3年有期徒刑”作为轻罪、重罪界限[14]的理由是:在我国目前刑法学界和实务界,此种界分“有其现实基础,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都具有较强可接受性”⑥。另外,根据笔者在北大法宝搜集到的适用了《规定》第33条的268篇裁判文书载明的故意犯罪种类的整理,发现罪犯故意犯罪的数量居前两位的分别为故意伤害罪(177篇)与破坏监管秩序罪(38篇),《刑法》对该两种罪设定之刑罚均以3年有期徒刑为界,且上述案例中,罪犯触犯的该两种罪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据此,笔者认为,为实现此种情形下罪责刑的适应,兼顾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实践,纠正法定减刑过于偏向功利主义的趋势,在继承2017年《规定》中罪犯犯新罪对原减刑裁定效力影响的规定的基础上,须进一步明确,罪犯故意所犯新罪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时,原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失效;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管制时,则根据其之后的悔改或立功表现,由有管辖权的法院重新确认是否恢复其原削减刑期的减刑裁定。即上述案例二中应由法院酌情考虑将减刑裁定裁减后的有期徒刑与新罪刑罚并罚。
根据上述条件维持原减刑裁定效力,可有效减少上述两案例中申诉与抗诉情形的发生,避免损害法院减刑裁定的稳定性,造成司法资源不必要的浪费,减少司法对抗,释放司法善意,同时也可促使罪犯安心服刑和改造,避免变相导致行刑过程的重刑化倾向。
注释:
①参见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7刑再3号刑事裁定书。
②参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8刑再4号刑事判决书。
③2017年《规定》的第33条至37条对该问题分别进行了规定。
④笔者检索的裁判文书做出的时间是从2012年至2021年。
⑤《最高法院发布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055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1月30日。
⑥我国刑法中的犯罪不仅定性,而且定量。对应这样的整体犯罪门槛,我国的刑罚整体比许多国家的刑罚起点高,相应地,重罪与轻罪的分界线不宜定得过低,否则不适合我国重罪、轻罪划分的目的与性质。如果分界线定得过高,将无法起到对重罪的区别对待、在各项实体法、程序法制度上“重罪重处”的作用。纵观我国刑法分则所有罪名,严重刑事犯罪的量刑起点一般都是3年,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立法对犯罪轻重程度的区分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