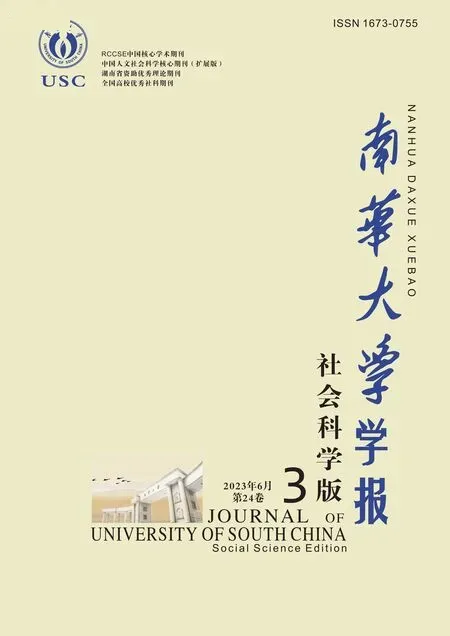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
2024-01-07罗迪江樊慧越
罗迪江,樊慧越
(广西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无论是对语言学转向的现代性诠释,还是对文化转向的后现代性批判,翻译研究总是立足于某种翻译问题“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如此这般的切问近思直接隐含着我们反思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许钧教授曾对亟待关注的翻译价值问题表现出如此的忧患意识:“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程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中国文学、文化怎样能够在‘走出去’过程中得到真实而有效的传播?如何从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平等交流、共同发展这个开放的视野下来认识与理解翻译?如何促使翻译在社会发展、文化建构以及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凸显其应有的价值?”[1]源于对翻译价值的忧患意识,对于当代翻译研究来说,价值论反思不仅需要我们直面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进程中应承担的责任,更需要将我们的思考聚焦于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并在价值论意识中真实而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促使翻译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根本存在方式而凸显其应有的真实价值。“翻译缘起于人类相互交流的需求,交流的结果拓展了人类自我发展的空间……促进文化交流,拓展自我发展空间,仍是当今世界中翻译活动的意义与价值所在。”[2]概而言之,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不仅需要关注翻译的价值问题,更需要强调翻译的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价值问题、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构成了价值论意识的根本内涵。但是,究竟什么是翻译研究应有的价值论意识,目前研究却大多语焉不详。基于此,本文试图就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抛砖引玉,以期深入地理解与把握翻译的价值问题、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
一 翻译的价值问题
翻译研究是在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社会学转向等多个转向的相互纠缠中不断地深入发展的。不论是何种转向,翻译研究既是对翻译事实的客观诠释,更是对翻译价值的多维追求,因为翻译是一种负载人类价值的实践活动,而翻译实践本质上就是价值问题。进而论之,价值总是扎根于翻译实践活动之中,而翻译就是一种价值负载(value-laden)与价值驱动(value-driven)的实践活动。翻译价值就是围绕翻译实践进行具有可珍贵性与可珍惜性的“善好”理念,是基于追求真善美的一种具有翻译精神的“善好”理念。对翻译价值的关注与追求并不是意味着对翻译事实的遮蔽,而是试图超越翻译事实之维,进而为翻译研究注入价值元素且拓展其认识论范畴。值得注意的是,翻译事实与翻译价值是认知与理解翻译研究的双重内涵,但彼此之间又有着明显的区别。“翻译价值问题的探讨是以翻译事实为前提的,翻译价值又以翻译事实为基础。翻译价值也并非只是翻译主体的自我追求而与翻译事实无关,而是在与翻译事实交互耦合的过程中体现翻译价值的优先性。”[3]因此,违背翻译事实的价值评价、价值判断与价值行为,都应该是不合理的,翻译事实对翻译价值具有最终的否决权。翻译价值问题内在隐含着翻译研究对翻译事实的超越,并在这种超越中聚焦于翻译价值的深入探讨。当然,超越翻译事实不是否定翻译价值,而是指翻译研究要站在价值的制高点将其价值论意识突显出来,并以一种合理的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来面对复杂多样的翻译现象,进而洞察翻译的多元性。那么,翻译价值到底是什么呢?要有效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明确三个关键性问题:翻译是什么、翻译意味着什么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
翻译研究是以翻译事实为出发点回答“翻译是什么”的问题。例如,“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4]。基于此,翻译涉及的是符合转换、意义再生与文化交流等关键因素,进而在本体论意义上可将翻译理解为人类存在的根本方式之一。翻译事实之维是反思“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是以“真”或“是”为命题词,关注的是翻译的内在规定,表征的是翻译实践活动对象的“实然形态”[5]。“翻译意味着什么”指向的是翻译在观念层面上的价值认知(value knowing),追问的是翻译对人类文化、社会、文明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翻译应当成为什么”指向的是翻译在实践层面上的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涉及的是如何实现翻译对人类文化、社会、文明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前者是在本体论层面上规定翻译的事实性,后两者是在价值论层面上关联着翻译的价值性。因此,翻译问题总是在翻译研究过程中需要某种事实性解释或价值性诠释而被提出来的。不论如何,“翻译是什么”“翻译意味着什么”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之间并非彼此相互分离,而是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展示出翻译事实与翻译价值的内在联系。换言之,翻译研究既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价值问题,它除了对翻译事实展开本体论与认识论研究之外,还应该包括翻译功能性、需求性与效应性的价值论问题研究。在此意义上,翻译价值可以理解为一种确定“翻译意味着什么”的价值观念与确认“翻译应当成为什么”的价值判断的综合体,它是被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所确定的翻译行为方案而指向翻译行为创造出有意义的、合目的的价值效应(value effects)。因此,翻译价值不是翻译事实呈现的现实性,而是翻译行为创造的效用性。事实上,翻译价值应当被普遍地评价为合理的,或者至少被翻译学界所期待为合理的。只有当行动者具有了实现意图必要的条件,可以卓有成效地干预世界,这种合目的的行为才可称为合理的[6]。翻译活动的合理性是对翻译价值的进一步确认,是翻译价值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的进一步阐释。正是这种合理性,翻译主体就可以卓有成效地干预翻译实践而通达合乎目的的翻译效应,因而翻译实践的价值创造应该警惕与避免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翻译行为,通过价值判断创造出对人类文化交流、社会发展与文明建设具有合理性的价值效应,这就是翻译实践应该选择并创造价值的根本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重大力量,我们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对翻译活动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7]翻译价值问题总是与“翻译意味着什么”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关联在一起的,其核心就在于如何确保翻译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及如何确立翻译价值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它表明了翻译价值既不是单纯主观性的价值判断,也不是纯粹主体性的价值评价,而是存在于翻译实践之中“应当存在”的价值观念与“应当创造”的价值效应。对于“应当存在”来说,价值属于观念层面上的应当存在,它是翻译价值本身的本质属性,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翻译主体的效用性。“应当存在”的价值属于翻译价值的本质,是翻译自身指向价值的合理性,但又不是现实地呈现出来的性质,就其本质而言是应该存在的价值观念,这是对于翻译如其所是地作为一种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的诠释。对于具有内在价值的翻译,我们总是持有特定的价值观念,如果一种价值观念是合理的,那么翻译就具有正面价值;反之,如果是不合理的观念,那么翻译就具有负面价值。如此而来,“应当存在”的翻译价值论就具有如下观点:当且仅当一个翻译行为增加了翻译实践的正面价值或减少了翻译实践的负面价值,它就是合理的;当且仅当一个翻译行为减少了翻译实践的正面价值或增加了翻译实践的负面价值,它就是不合理的。可见,合理性或不合理性构成了我们认识与把握翻译价值的核心问题,其价值化的目标就是翻译实践的正面价值。
二 翻译的价值意识
翻译价值本身就是直接具有内在性质的东西,是如其所是的东西。当翻译价值与翻译合理性取向内在联系时,翻译的价值意识就随之而现。所谓翻译价值意识,就是翻译主体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对翻译价值的观察与思考并努力追求翻译活动的合理性而呈现出的主体意识。根本而言,翻译价值意识是翻译实践活动本质特征的一种体现与内在要求,它所指向的是价值驱动的翻译活动呈现出的意识形态。因此,翻译价值的创造遵循的是合理性,追求的是正面价值,警惕的是负面价值。然而,翻译价值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往往被功利主义行为异化,或者说面临“实用论入侵”(pragmatic encroachment)[8]的挑战而陷入消极的、负面的效应。在翻译实践中,“受文学中‘粗鄙存在观’影响,当前人们的翻译价值观也存在异化的倾向……翻译的经济功能也冲击了人们对翻译社会文化建构功能的重视,罔顾忠实、唯利是图的翻译行为被当作理所当然了。”[9]翻译实践过程中,我们并不是反对翻译的实用性,而是反对将实用性作为翻译的终极目标来考察翻译之用而趋向一种罔顾忠实、唯利是图的功利性翻译行为。功利性翻译行为既减少了翻译实践的正面价值,又增加了翻译实践的负面价值。对此而言,翻译价值意识就应当警惕与避免这种功利性翻译行为,回归到翻译精神上来,进而卓有成效地干预生活世界。“从总体来看,翻译活动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及历史价值,突显了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翻译的本质属性,这正是翻译精神之体现。”[10]这种翻译精神是将翻译作为一种人类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来认识与把握翻译的价值意义,它既显现为翻译主体对这种翻译行为的自我反思,又显现为其对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与历史价值的合理追求。
当我们将翻译价值视为具有合理性时,它意味着我们对翻译价值的判断已经从观念层面(翻译意味着什么)转向实践层面(翻译应当成为什么),那么对翻译价值的认识采用的方式不再是一种“应当存在”而是一种“应当创造”。“应当创造”超越了翻译价值本身而进入到翻译创造价值而变革社会文化的范畴。这就是翻译价值的创造力量,正如“鲁迅始终在‘文艺为人生’这一文化价值观前提下,不遗余力地从事以‘窃得洋火照人间’为翻译价值取向的外国文学翻译,力图达到改变‘人心’,提振民族精神,实现立人立国的终极目的”[11];傅雷先生就是这样的翻译家,“是‘神的口谕’的传达者,是与普罗米修斯一般的窃火者,将异国的文化、思考窃来,开启本国人民的视野与心灵。”[12]这是翻译价值的一种创造力量,它在翻译实践中推动翻译向一种合理性的结果而有意义地创造价值。唯有如此,才能杜绝翻译观念的急功近利与翻译行为的工具主义倾向,也才能有效地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概而言之,翻译价值不仅通过“翻译意味着什么”在观念层面实现其意义,而且通过“翻译应当成为什么”在翻译实践中实现其创造力量,“以助力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国门,实现与他国文学的交融与互通,打破中国翻译文学在西方世界边缘化地位的窠臼,真正促进中国文学切实有效‘走出去’。”[13]
三 翻译的价值担当
翻译价值总会与翻译主体发生内在的关联,在翻译实践中两者的交互作用形成主体性价值观。主体性价值观涉及的不是翻译事实问题,而是翻译主体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价值判断、价值评价、价值担当的态度问题。翻译研究所把握的价值只有与翻译主体相关联时,才能真正在翻译实践中实现自身的创造力量。翻译价值与翻译主体的如此关联,就使得翻译研究的价值问题“翻译意味着什么”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延伸到“我应当做什么”与“我应当期望什么”的问题。于是,翻译价值的问题就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的“成”(being)转向了“我应当做什么”的“做”(doing)。翻译价值之“成”是通过翻译价值之“做”实现的。这是翻译研究对翻译价值在实践层面上的超越,它使翻译回到了“赞天地之化育”之中,展现了“我”在翻译实践中的价值意义、价值意识与价值承担。其中,“我”指向的是翻译主体,“我”之“化育”就是通过自身的翻译活动使“应当成为什么”转化为“应当做什么”,从而合乎翻译主体的合理需要并获得价值意义。“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源于翻译实践活动,它是每个翻译主体在翻译实践活动中都会不断地反思与追问的根本问题。它甚至促使翻译主体做出决策与采取行动,并为翻译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我”来说,价值意识不仅表现了其对于翻译活动的价值感,而且表现了其对于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社会发展、国家形象与文明互鉴的建构作用而具有某种深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就此而言,“我应当做什么”对于翻译活动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是翻译活动的价值呈现及其对翻译价值的判断,而且是“我”这个翻译主体的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的集中体现。“我”的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在翻译研究中被突显出来,“我”总是与翻译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也蕴涵着“我”对翻译价值论意识的建构作用。“我”作为价值主体,“应当做”的是引向正面价值的事情,这不仅要克服“我能够认识什么”对应的认知主体的弊端,即克服认知主体的无限理性能力与工具理性的无限张扬,而且要回归到承载目的设定与坚守的价值理性,彰显价值主体在目的的坚守中蕴含着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取向[14]。在此意义上,能否用人文精神的价值主体反思认知主体,从而使翻译主体性的思想内涵沿着追求真善美的方向不断展开,成为当代翻译主体性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15]。可以说,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自始至终都是翻译行为的价值指引,同时又是对“我能够认识什么”的价值规范与“我应当做什么”的价值指引,这一价值指引不仅对具体翻译实践的价值观念具有包涵能力,而且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价值谱系具有统摄能力。
“我应当做什么”所指向的就是翻译主体对翻译价值的一种认知,它所发生的事情就时间而言是尚未发生但对“我”有规范作用而需要发生的,因而“我应当做什么”是指向未来的。它不是规定、描述与界定真实的翻译“应当什么”,而是翻译实践中缺乏却实际上被需要它“成为什么”而发生的翻译行为。由此而来,“我应当做什么”所指向的“未济状态”是一种“应当到来”的性质,又赋予它一种翻译实践上的创造力量。也就是说,翻译价值就是一个应当如此发生的行为效应,这种效应是通过翻译实践实现“翻译应当成为什么”向“我应当做什么”的转变,即将翻译的“价值存在”转化为“价值创造”。于是,“我”以自己所拥有的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的方式,作为翻译实践者参与到翻译价值的创造之中,使翻译价值获得了具体的意义,并表现和确证“我”作为创造价值而存在的本质力量。质而言之,“翻译应当成为什么”的问题核心是价值的观念问题,通过“我应当做什么”让“应当存在”的价值在翻译实践中呈现出来,对于“我”而言,是翻译主体的行为,其价值担当就是让“应当存在”的价值显现,这才是翻译活动的价值之所在;对于翻译实践而言,是“应当存在”的价值在翻译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通向翻译价值的变革作用。
“我应当做什么”通过翻译实践的价值创造,对于“我”而言,就是一种翻译价值导引的变革作用,这种作用直接介入“我应当期待什么”。“我应当期待什么”问题,实质上也是翻译价值担当的进一步延伸。为了期待,“我”需要关注什么样的翻译行为是“我”作为翻译主体应该期待的价值效应。唯有通过参与翻译价值的建构与塑造,“我”的期待才会具有价值意识,也才会有通过翻译活动创造价值的意识。如果没有翻译活动的价值意识,那么“我”对于“应当做什么”“应当期待什么”就不可能在翻译实践中参与价值建构并创造出合理的价值。应当做什么与应当期待什么,其实不是翻译实践中的真实存在,而是一种价值意识;对于“我”来说,更是一种价值担当。只有当作为翻译主体的“我”拥有了翻译活动的价值意识,才知道自身“应当做什么”;只有当作为翻译主体的“我”拥有了翻译活动的价值担当,才明白自身“应当期待什么”。价值意识的觉醒,就是价值担当的前行,翻译才能是其所是地显现出自身价值,“我”才能如其所是地塑造并创造出可以期待的价值。可以说,探讨“应当成为什么”问题,就直接蕴含着需要唤醒“我”的价值意识,而“我”的价值意识在翻译实践中关涉“应当期待什么”问题时,就自然而然地指向“我”的价值担当。“应当期待什么”问题,内在地蕴含着消解翻译主体的极端主观性,凸显“我”的价值担当,从而奠定翻译价值论意识的基础,为繁杂多变的当代翻译价值观提供一种解决的方案。本质上说,“我”的价值担当就是一种译者之为,“是译者努力超越现实生活、提升自我存在价值的结果,它合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愿望,为人们提供崇高价值的召唤,包含了译者对精神世界的深刻体验和对美好生活的倾情向往。”[16]因此,“翻译应当成为什么”只有与“我应当做什么”“我应当期待什么”发生关联时,译者之为才能体现出翻译的价值意义,而翻译价值才能在翻译实践中进行自我塑造,又在自我塑造中获得创造而显现出来。例如,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建构国家形象的背景下,“我”作为一个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的翻译主体,“不仅要研究传统的以语言作为表达媒介的翻译,更要关注作为国家形象建构之载体的跨文化的翻译和阐释。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用世界通用的语言来讲好中国的故事。”[17]由此,当“我”作为翻译主体承担起翻译实践的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时,显而易见,翻译主体就变成了价值主体,既能摆脱功利性翻译行为的诱惑,又能超越个体价值观的主观性,是对翻译实践活动产生的价值效应与价值后果承担责任的主体。
四 翻译的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
任何翻译活动都存在着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而且两者之间不是孤立割裂的。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需要辩证地看待与审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翻译实践中尽量追求与维护翻译的正面价值,促使翻译活动趋向合理性,同时又要反思负面价值对翻译活动产生的消极作用,并在反思中给予思想上的澄清与引导。“人类所肯定的‘价值’其实具有两重性甚至正反两面性……如果要确立一种‘正面的价值’,那它也必须看到另一面,即‘负面的价值’或‘异化’,从而对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价值问题给予思想理论上的澄清与引导。”[18]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翻译的建构功能与“异族入侵”(intrusion of the alien)[19]。我们在对翻译价值的认识似乎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如果将翻译对本族文化的建构功能视为一种正面价值,那么翻译对本族文化的入侵行为相应地视为一种负面价值。“异族形象”的引入,无疑会打扰、打乱甚至颠覆本族、本土文化的“安宁”,但世界诸多民族或国家形象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却又证明,作为特殊文化表达形式的翻译,往往在这一民族或国家形象建构及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翻译的“异族入侵”行为打扰了本土文化的“安宁”,在某种程度上是消解了本土文化的精神实质而呈现出一种负面价值,然而这种负面价值是一种表层结构的价值体现,但是在其深层结构中却表现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回译”(cultural back-translation)而展现出正面价值的建构作用。因此,价值论意识就是要辩证地审视与探讨翻译活动的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的关系,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寻找如何使负面价值转化为正面价值的途径,透过翻译活动的负面价值去反思翻译价值的多样性以及确认正面价值的合理性。真正的价值论意识不只是关乎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正面价值,而更关注翻译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负面价值以及如何超越负面价值而走向正面价值的确认、维护与创造。
价值本质上是一个关系概念,即某一事物对另一事物“有用”或能够发挥“好”的功能[21]。因此,需要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辨认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认识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过程,进而导向一种对翻译之用的认识与把握。对负面价值的认识,将会涉及翻译批判与价值判断的维度。翻译批评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促使翻译在民族交流、文化传承、语言变革、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翻译事业健康、理性地发展,保证翻译的价值得以实现,从而实现翻译批评自身的价值[22]。对于价值论来说,翻译批评往往是与负面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它所要批评的对象是将翻译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手段来看待而被滥用形成的负面价值。翻译的负面价值主要表现为对翻译功利性的追求,而追求功利性导致的严重后果是翻译工具的滥用与翻译价值的异化,产生诸如翻译市场决定论、粗鄙存在观、唯利是图观、急功近利观等。功利性翻译虽然看到了翻译之用的即时效应,但它为了翻译市场的短期效应与唯利是图进而否定与消解翻译价值的合理性。这就需要我们反思译者主体性的膨胀带来功利主义翻译行为的挑战,以及翻译市场决定论的冒进及其导致翻译价值的丧失,对于当代翻译实践具有十分迫切的意义[23]。归根结底,翻译负面价值产生的根源在于,翻译主体成了翻译行为的主宰者,翻译手段失控而被赋予了操纵功能,翻译行为往往陷入了功利主义倾向,翻译价值的多样性被翻译主体、翻译手段与翻译行为遮蔽了。如果以功利主义价值来指导翻译实践,必然会导致正面价值的遮蔽与扭曲。正是意识到翻译负面价值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立足于翻译负面价值的立场,去澄清、批判与解决翻译负面价值的问题,透过复杂紊乱的价值观来塑造理性的价值批判精神,促使翻译行为回归翻译价值的合理性。在此意义上,翻译主体是驱动与创造翻译价值的承担者,在批评翻译负面价值过程中成了评价主体。评价主体是评价活动的实施者,对于同一价值关系,不同的评价主体往往会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24]。不论如何,评价主体对于负面价值做出的价值判断都应该持否定态度,而一切限制负面价值产生的措施终归要通过价值主体或评价主体在翻译实践中产生的自我约束、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才能得到有效实施。依靠自我约束、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引导与规范翻译实践,是翻译主体“我”的存在方式的独特表现。正因为如此,“我”作为翻译主体、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总是与翻译价值联系在一起,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增强翻译价值意识,承担翻译价值担当,有效地减少翻译的负面价值而增加翻译的正面价值。从时代语境来看,翻译价值始终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密切相关,它总根植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发展历程,关涉对用中国声音向世界讲好中国文化的现代境域中的价值担当的理解,这对于传播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翻译价值担当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 结 语
翻译研究在面向多范式、多维度与多元化的进程中,它不断地面临着新的问题。然而,无论翻译研究如何发展,因“翻译之为翻译”而蕴含的价值论意识,始终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它指向的是对翻译事实之维的反思和对翻译价值之维的关注。以往研究一味追求客观的翻译知识与确定的翻译事实是以翻译价值的丧失为代价的,翻译价值处于翻译实践之中并蕴含着翻译事实。倘若只聚焦于翻译事实,则会使翻译研究陷于抽象状态,无法真正理解翻译的复杂现象,不能回答翻译的价值意义,反倒使人们丧失了对价值问题的关注、价值意识的增强与价值担当的坚守,不再领悟翻译作为人类生存的根本方式这个价值信念,这必然带来翻译价值的消解,使翻译活动陷入工具性与功利性的危险境地。翻译学界意识到,在翻译事实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翻译价值,有必要探讨翻译事实与翻译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探讨翻译事实与翻译价值之间的关系是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的出场方式。这就使得翻译价值能够突破翻译事实的“遮蔽”,从而为翻译研究开启了价值驱动的路径。它本质上就是涉及对翻译价值的思考,是对“翻译之为用大矣哉”[25]的本体思考。它既要关注翻译活动的价值问题——指向的是“翻译意味着什么”与“翻译应当成为什么”,又要强调翻译活动的价值意识与价值担当——指向的是“我应当做什么”与“我应当期待什么”,同时还要正确审视翻译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价值论意识的探讨与进入21世纪以来翻译学界开始重视与思考翻译价值问题是一致的。“这无疑是翻译研究的现代觉醒,也是翻译价值的现代凸显,更是翻译研究在实践层面上的变革”[26]。在思考翻译价值的背后,蕴含着翻译研究具有显著的方法论自觉,它表明了翻译研究逐步认识到翻译事实与翻译价值的区别,也预示着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事实的诠释,还应该关注翻译研究的价值维度,关注翻译价值问题、增强翻译价值意识、承担翻译价值担当。在此意义上,价值论意识的探讨就是试图在翻译事实的基础上避免翻译价值的遮蔽,使翻译的价值意识与价值意义回归翻译研究的基础,为翻译研究的价值论意识找到牢固的依据,这将为目前翻译研究注入“回归价值”的新理念,也将极大地促进当代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