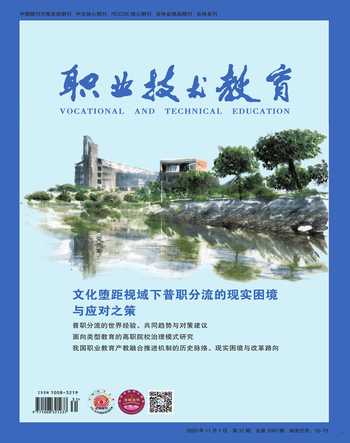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的历史脉络、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向
2024-01-01李阳靳雪瑞
李阳 靳雪瑞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持续改革,重点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之间的权责划分。先后经历了管理职权下放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初步探索阶段、社会力量参与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内涵深化阶段和多元主体协同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发展阶段。作为利益主体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等主体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的效果期待不尽相同,往往会采取各种策略進行博弈。在博弈过程中,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和保持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灵活性的矛盾、不同政府部门多头管理致使政府权威碎片化、地方政府间争取优质教育资源以及“搭便车”行为和官员晋升竞争等问题制约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功能的发挥。为此,应整合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强化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调整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推进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
关键词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市域产教联合体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3)31-0045-07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是指通过政策制定和组织推动,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联结教育、经济、劳动、就业等各个领域,形成教育部门协调、多部门协同、行业企业参与的发展合力,促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多元主体联动机制。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战略任务是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形成“一体两翼”发展格局,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统筹协调权力进一步下沉。202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条件要求,为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提供了实践遵循。为了有效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企业和职业院校进行引导和鼓励,但是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依然存在“学校热、企业冷”的“两张皮”问题[1]。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推进有赖于政府职能的发挥,政府职能需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承担。然而,政府间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有三条线索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二是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三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本研究从这三条线索出发,重点梳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的历史脉络,分析政府之间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指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的改革路向。
一、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的历史脉络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逐渐从产教结合走向产教融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管理职权下放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初步探索阶段、社会力量参与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内涵深化阶段、多元主体协同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发展阶段。
(一)管理职权下放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7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政府主导完成了职业教育发展的两项重要工作:一是恢复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二是大力发展职业高中。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应该考虑扩大各种中专、技校的比例,同时强调教育事业要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在教育与生产结合的内容和方法上要有新的发展[2]。1979年,国家劳动总局颁布《技工学校工作条例(试行)》,指出技工学校的教学应与生产过程相结合,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这是职业教育教学和生产相结合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国家的政策文件中,标志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思想的萌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在各个领域逐渐深化。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简政放权,在坚持中央统筹的基础上,将职业教育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并且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4]。1987年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以及1989年劳动部印发的《关于技工学校深化改革的意见》等文件要求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接纳职业学校学生进入工厂实习和实践,这表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内涵逐渐从生产和教学之间的结合走向企业和学校之间的结合。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指出,应在政府统筹下,加强行业、企业单位办学和各方面联合办学,发挥企业在培养技术工人上的优势,并提倡“产教结合,工学结合”[5],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中出现“产教结合”这一表述,标志着产教融合思想的进一步发展。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兴办多种形式、多层次职业教育的局面,并提倡走联合办学、产教结合的路子[6]。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为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与企业密切联系,培养实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7]。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从政策引导走向法律要求,标志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开始从理念引导走向实践探索。
(二)社会力量参与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内涵深化阶段(1998-2011年)
199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重新成为国务院的下属机构,在教育部的领导下,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职业教育体系逐渐完善[8],开始探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之路。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建立初、中、高衔接的职业教育体系,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9],并要求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走产教结合的道路,调整学校布局,优化资源配置。200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应依靠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企业应与职业院校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确立了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协同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组织布局。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推动产教结合,加强校企合作,积极开展订单式培养,行业企业应积极参与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开创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协同育人的教育模式,在实践中丰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内涵。2005年,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并要求职业院校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建立和完善半工半读制度。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强调要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这一时期,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市场成为重要的职业教育办学主体,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内涵进一步深化,出现了多种产教融合发展模式,这是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选择。
(三)多元主体协同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10],在职业教育管理中,逐步形成政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为主、行业指导、校企合作、社會参与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2013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11]。首次使用“产教融合”这一概念替代“产教结合”,并将深化产教融合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中。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更加全面、准确的概括[12],要求同步规划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明确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原则和校企合作的规则,并提出应发挥企业的办学主体作用。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逐步形成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共同办学、协同育人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第一个关于产教融合的专门性文件,对教育与产业的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要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育人,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并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进行政策激励,突出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协同推进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要求建设产教融合型城市、打造引领产教融合的行业标杆、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法律层面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健康、可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发展保障,也为未来职业教育发展明确了定位。这一时期,我国初步形成了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地位得以确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方式更加多样化,职业教育在经济、科技、创新发展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职业教育在教育链中与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关系更加明确、在产业链中与区域主导产业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创新链中与科学研究和工程教育的结合更加紧密、在人才链中与现场工程师培养的融合更加深入,促进了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二、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的现实困境
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过程中,作为利益主体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的效果期待不尽相同,往往会采取各种策略进行博弈。因此,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间的博弈策略能否实现较好整合,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目标的实现。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动过程中的利益博弈
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中,中央政府主要负责管理全局性、纲领性问题,区域性的、具体性的问题则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由于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责高度同构[13],地方政府的管理活动也是依靠科层组织的层层委托向前推进[14],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下级政府服从上级政府[15]。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改革的过程中改变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偏好、信息与奖励机制,这是央地博弈中地方政府兴起的制度性原因[16]。
1.中央政府通过“计划—审批”的方式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中央政府掌握着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发起权和终止权,通过规则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影响地方政府产教融合发展的实际进程。中央政府通过各种计划和指标来管制和监督地方政府推进产教融合发展的情况,而地方政府则通过领会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来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随着“项目治国”的兴起[17],中央政府通过设立和审批各种项目来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较长的行政距离,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地方性知识”,掌握更多的非对称信息,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央政府“计划—审批”方式的运行。
2.地方政府通过变通执行中央政府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维护自身利益
中央政府的产教融合政策是整体性、全局性的,需要地方政府配合执行。因此,在中央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一些地方政府极力争取对自身有利的政策方案和政策执行条件。在产教融合政策中,很多原则性的规定都是通过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呈现的,这些话语与产教融合政策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其精细化有赖于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阐释。地方政府根据自身对产教融合政策目标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一些原政策目标中所没有的内容或作出不同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精神的解释,使得产教融合政策的适用对象、范围、力度等超过了原政策的界限[18]。
3.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对上负责”的方式执行产教融合政策
当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目标与任务由中央政府委托给地方政府时,“让上级满意”就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追求[19]。在拥有集权惯性的政治体制中,中央政府拥有绝对权威,地方政府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往往等待中央政府的解决方案而不愿或不敢主动作为。同时,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看重个人利益,不愿意付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的成本,也不愿意承担风险,对中央政府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等待观望。在“下管一级”的管理体制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主动迎合上级意志,不顾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规律以及本地区实际情况,机械地执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导致中央政府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失去了应有活力和适用性。
(二)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互动过程中的部门分割
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纵向权力和资源分配关系,而是兼顾纵向和横向权力分割的条块关系,赋予了中央政府在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过程中更多的灵活性[20]。地方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既接受地方政府的领导,也接受中央政府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或领导。在这种架构中,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作为影响产教融合的核心部门,两者之间的互动受到重点关注。
1.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部门化分割
在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几乎掌握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所有重要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质资源以及各种项目设置和评价等办学资源[21]。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过程中,需要处于主导地位的关键部门和辅助部门相互协作。然而,由于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不完善,部门化的分割使得需要跨部门解决的问题较为困难。究其原因:一是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清楚;二是在部门利益的影响下,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会根据利益博弈的效用函数,扩张或者收缩本部门的管辖范围。
2.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多头管理,导致权威碎片化
在“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管理其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人财物,这些部门的上级主管部门则对其业务进行指导。伴随政治体制改革,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不仅是产教融合政策的执行主体,也是独立的、理性的利益主体。因此,各政府部门经常从部门本身角度出发认识和理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政策的具体措施也都局限于以部门为中心,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联性,造成“整体政府”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过程中的缺位和失位[22],当各政府部门利益发生冲突时,各部门将维护部门利益作为首要任务,忽略了部门利益之间的整合,影响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的效果,导致政府权威的碎片化。
3.行业主管部门过度参与削弱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
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职权在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之间交叉,一些原本应该由教育行政部门掌管的职权被其他行业主管部门承担,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23]。行业主管部门以行政化的方式处理专业化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问题,在推进过程中容易引起职业院校的象征性合作。如果教育行政部门在推进产教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不能合理确定,就难以在具体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制定与执行上拥有主动权。同时,在部门权力利益化的情况下,转变行业主管部门的职业教育管理职能经常受到阻碍,甚至会出现行业主管部门在某些利益相关方面进一步集中权力的趋势,导致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顶层设计”难以有效落实。
(三)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互动过程中的府间竞争
中央政府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事务以属地化的形式逐层发包给各级地方政府,并配置一定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然而,优质资源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性资源,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由此产生[24]。同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深受上级政府影响,促发同级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锦标赛”[25]。
1.地方政府之间对优质资源的争取
争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政策试点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是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政策工具,这会导致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为了争取中央政府的认可,一方面,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政策目标的要求制定和完善政策方案;另一方面,则会努力争取上级政府官员的支持。通过特定项目配置资源是专项转移支付的重要方式,因此,一些地方政府经常需要到中央政府及其部委争取项目[26],相对稀缺的职业教育资源必然会引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明确“对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好、重点工作推进有力、改革成效明显的省(区、市)予以倾斜支持”[27]。因此,如果辖区内的职业院校进入“双高计划”名單,地方政府就能够从中获得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助,这成为地方政府争取职业教育资源的重要内驱力。
2.地方政府为节约成本选择“搭便车”
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具体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执行者,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地方政府由于获得了一定的授权而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具有投入高、周期长、见效慢等特点,而且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的收益主要体现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培养质量上,具有较高的流动性[28]。这就导致一些地方政府经常通过政策优惠引进技术技能型人才,通过“搭便车”的方式享受中央政府以及其他地方政府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从而达到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目的。如果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都选择这种“搭便车”的做法,那么就会导致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缺失,使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影响[29]。
3.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
在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面对彼此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激励机制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锦标赛”。在这种晋升模式下,地方政府常常需要被动应对各种资源压力,难以实施长期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计划。为了在晋升竞争中获得成功,政府官员往往会将有限的资源放到其任期内的政绩工程上。地方政府官员不仅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经济竞争,而且很多地方政府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背后也有“土地财政”的影响[30]。为了处理跨区域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问题,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但部分地方政府之间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合作仍然只是围绕区域经济发展亟需的项目进行,而且,这种合作过程经常受到地方政府官员个人偏好的影响。
三、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的改革路向
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需要多元主体的互动协商,而不同主体对产教融合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期望。一方面,中央政府关注的是公共利益,而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关注的是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另一方面,不同的利益诉求导致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猜忌和指责。因此,应调整中央政府、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利益整合的基础上,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
(一)强化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
伴随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部分权力逐渐下放到地方政府。但目前职业教育多头管理的问题仍然存在。各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对于职业教育都有一定的管理职责,并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然而,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过程中却存在很多问题,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导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失真。因此,强化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完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推进机制,是提高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有效性的必然要求。在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之下,各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从公共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以及个体利益出发执行职业教育政策,利益冲突在所难免。面对这些利益冲突,要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中央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促进政府间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前提就是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具有整合的利益[31]。要明确政府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过程中的职责,继续转变政府职能,避免政府权力过多直接介入产教融合管理事务。利用立法、拨款等手段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进行宏观管理,使其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承担起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制定、资源的公平配置、产教融合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和考核等责任,注重为职业院校和企业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使职业院校和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真正意义上的办学主体[32]。
(二)调整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
在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指标的考核制度之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密切相关,致使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对于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在“下管一级”的行政管理体制下,追求上级满意,对上负责是地方政府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着眼点,但考核过程中只有政府参与,缺乏社会公众的参与。基于当下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制度的规约,地方政府常将对经济发展的利益诉求内化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之中,使得职业教育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平衡发生偏离,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实践中,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力图尽可能降低经济支出。因此,要解决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中的唯经济利益至上的问题,就要调整当前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首先,在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的效果实施绩效评价的时候,应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注重政策执行过程中工具性与合法性的协调[33]。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重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所产生的综合效益,要将政策目标群体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支持情况等纳入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之中。其次,应根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跨界性特点制定科学的考核标准,使用恰当的考核方法,通过严格的考核程序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估[34]。对于忠实执行中央政府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地方政府官员给予相应奖励,同时对虚假执行的地方政府官员予以相应惩罚。
(三)完善政府之间的职权划分
要从根本上解决因政府组织间职权划分不当造成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困境。当前,我国已经建立并完善了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但尚未形成政府组织机构编制管理的专项法律,以致于不同政府部门间的管理职能时常交叉。因此,对于政府部门的具体职能划分以及政府组织内部机构设置等,应健全政府组织机构编制的专门法律予以规范,将政府部门的职能配置纳入法治化轨道,使政府部门内部的机构设置有法可依,避免政府部门之间因机构设置不规范而造成的职能交叉以及由此导致的产教融合发展问题[35]。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发挥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办学主体作用,优化行业企业办学职能,压实教育行政部門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第一责任,落实行业主管部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主要责任,推动其他政府部门协同配合,逐步形成教育行政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职责清晰、同向发力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协同推进机制。
(四)推进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
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的重点问题。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探索,也是解决困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两张皮”问题的关键,更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因此,应加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工作,尽快出台国家和地方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办法和条例,从合作协议、权责利明晰、权益保障、风险把控等维度明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管理规范,在法律层面明确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权责利,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提供法律保障。逐步建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委员会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职业教育委员会分级管理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制定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规章,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提供制度保障。成立由政府职能部门组成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领导小组,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组长所在单位,负责具体协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工作,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提供组织保障。允许社会资本以股份制形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组建由政府代表、企业法人和学校法人共同参与的董事会管理职业院校的日常工作,建立社会资本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注册登记、资产管理、产权保护、收益分配等制度,探索公办职业院校和民办职业院校之间相互委托管理的长效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民办院校参与公办职业院校办学,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提供资源保障。
参 考 文 献
[1]李玉倩,陈万明. 产教融合的集体主义困境:交易成本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J].中国高教研究,2019(9):67-73.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04-105.
[3]祁占勇,王羽菲.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变迁与展望[J].中国高教研究,2018(5):40-45+76.
[4]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5(15):467-477.
[5]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1(36):1256-1262.
[6]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J].中国高等教育,1993(4):8-17.
[7]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6(16):624-630.
[8]郅庭瑾.中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82.
[9]石伟平.职业教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2.
[10]侯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
[11]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11-15)[2021-01-06].http://www.scio.gov.cn/zxbd/nd/2013/document/1374228/1374228_1.htm.
[12]张宁娟.从追赶到超越:教育跨越式发展之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77.
[13]李阳.职业教育治理的制度逻辑[J].职业技术教育,2020(36):32-37.
[14]刘祖云.政府间关系:合作博弈与府际治理[J].学海,2007(1):79-87.
[15]吴康宁.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0.
[16]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98.
[17]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 兼论“项目治国”[J].社会,2012(1):1-37.
[18]李阳.控制权分配与职业教育治理模式:政府职业教育治理行动的一个分析框架[J].职业技术教育,2021(31):34-39.
[19]陈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社会支持中政府与民间关系[J].全球教育展望,2014(3):116-123.
[20]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86.
[21]吴康宁.政府部门超强控制:制约教育改革深入推进的一个要害性问题[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6-11.
[22]李阳.职业教育改革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J].职业教育(下旬刊),2020(3):43-51.
[23]李阳,祁占勇.行政管理体制视域下职业教育改革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J].河北职业教育,2020(5):21-25.
[24]张应强,彭红玉.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地方政府竞争与高等教育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9(12):1-16.
[25]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21.
[26]郑世林.中国政府经济治理的项目体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6(2):23-38.
[27]教育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EB/OL].(2019-04-02)[2022-09-3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37/s3876_qt/201904/t20190402_376471.html?authkey=lca153.
[28]李阳,潘海生.变通执行: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一种行动策略[J].职业技术教育,2022(15):48-54.
[29]李阳.职业教育治理机制:挑战与展望[J].职教通讯,2023(2):28-39.
[30]刘云波.发展经济还是追求政绩——地级政府举办高职院校动力的实证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6):85-94.
[31]亓俊国.利益博弈:对我国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0.
[32]李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工具选择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21:52.
[33]李阳,潘海生.工具性与合法性:职业教育政策工具选择模式的一個分析框架[J].职教论坛,2022(6):5-12.
[34]潘海生,李阳.从管理到治理: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的变迁逻辑与未来走向[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5):128-132+138.
[35]金太军.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298.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Current Predicaments and Reform Direction of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Li Yang, Jin Xuerui
Abstract Since the daw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continued to reform, focusing on reforming the division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with their departments. It has experienced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stage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decentralization of management authority, the deepening stage of the connotation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also the stag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multi-subject coordination. As stakeholde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ir departments have different expectations for the effect of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often adopt various strategies to play gam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game, there wer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aintaining the flexi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 fragmentation of government authority caused by multiple management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struggle of local governments for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free rider” behavior and official promotion competition restrict the function of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interests of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trengthen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djust the assessment system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promote the physical operation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romotion mechanism; city-level industry-education union
Author Li Yang, PhD candidate of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350); Jin Xuerui, PhD candidate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作者簡介
李阳(1992- ),男,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社会学,职业教育政策(天津,300350);靳雪瑞(1994- ),女,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谱系图研究”(20JZD055),主持人:潘海生;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现代化进程中职业教育治理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2021YJSB155),主持人: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