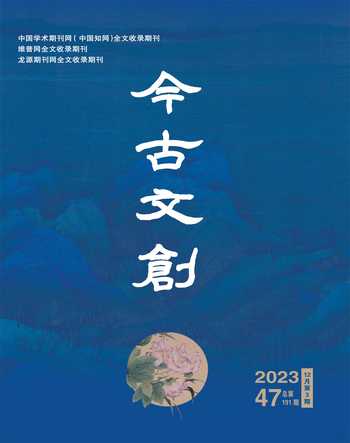祁门县《方氏族谱》土地契约文书探究
2023-12-26邹中强
【摘要】民间契约文书具有独特、重大的研究价值,而收入族谱的契约文书是已订立的契约文书的抄录再现,在族谱中所呈现的诸多契约文书,一方面是向后世子孙及旁人传递宗族族产、祖产等的具体信息以宣告其所有权;另一方面是通过记录这些契约内容以证明其产业合法性,或者在将来可能发生的诉讼纠纷中提供强有力的证据。笔者所见于《方氏族谱》中的契约文书,数量可观,且年份集中于清前中期;这些族谱契约文书具有散件契约文书的一般性特征,包括立契人、中人、代笔人,以及交易物、边界和相关契约术语等。此外,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族谱契约文书中的契约参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些族谱契约文书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了解当时该宗族该地域的土地交易、社会经济及宗族契约秩序等情况。
【关键词】祁门;《方氏族谱》;土地契约文书;内容探究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7-008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7.024
民间历史文献的搜集和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田野考察及广泛收集等研究方法下,以契约文书为代表的民间历史文献越来越多地被发掘出来。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技术手段的完善和研究方法的推进,关于契约文书的搜集与研究成果频出、硕果累累,主要代表作有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该书将土地所有权史研究与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相结合,研究了明清时期的土地制度、契约关系、地权分化、乡村社会经济史、土地所有权史等问题[1]。此外张传玺、周玉英、张小林、郑振满、陈春声、刘志华等诸多学者皆有丰富的契约文书研究著述。
一、祁门县《方氏族谱》及其契约文书情况
本文所用祁门县《方氏族谱》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分别是编号1962同治年修《方氏宗谱》和编号1963光绪年修《方氏宗谱》。“祁邑古属黟,为赤山镇,唐大历初,始析黟之六乡及饶浮梁地而置邑焉。祁山峙其东,阊门巩其南,川谷環抱。”[2]祁门县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地处黄山西麓,西南与江西省浮梁县毗邻,其建县于唐永泰二年(766),因城东北有祁山,西南有阊门而得名;“祁门方姓为祁门望族,乡贤理学代有闻人,心仪而神,企者久之。”[3]祁门方氏有四支,本文所用《方氏族谱》乃是属于赤桥方氏,赤桥方氏始迁祖名方智詠,唐代由浙江严州桐庐白云源迁居祁东赤桥,后来支派繁衍,自赤桥分迁黄杨墩、伟溪、城北、箬坑、稠源、武陵、葛流源、庾岭背、塘坑头及石埭县雷湖等地。[4]族谱记载:“方氏始祖太子雷公食采方山得方为姓……厥后散迁徽、池、饶、信,俱部纷匕著族,大明有鳌峯祥公宦……我来营前见贵宅与柯源、中村三祠合修……”又载,“予祖始祖由禀三公自赤桥徙池阳、石埭、雷湖,复迁祁北六都伟溪,传至十九世祖德五公,自伟溪迁祁南,由柯源迁路公桥至二十八世祖得俊公,由路公桥再迁祁西二十都营前,殆宋以来,人文济美……”[5]由此大概可知祁门赤桥方氏得姓由来及其迁徙情况,初步可以判断来自光绪《方氏宗谱》中的这批契约发生地点位于祁门西南一带,如营前、路公桥、中村等地,作为祁门望族的方氏自古学者名流,代不乏人,其富甲程度历所称道,方氏与其他姓氏存在频繁的土地、山林、坟产等产业交易,尤其是到了清中后期,随着白银的广泛使用、赋役的多样化和市场交易的发达,民间相关产业的交易愈加频繁。这片地区不仅接近祁门文堂陈氏家族聚居地,还与饶州府浮梁县接壤,因此可以发现大量的方氏与文堂陈氏之间的土地契约,以及祁门与浮梁之间的跨地域的土地交易记录。
光绪《方氏宗谱》所载契约文书共计有91份,从时间分布上看,契约文书包括了明洪武至清光绪朝代,洪武1份,正统1份,天启1份,崇祯5份,明代契约份数约占0.08%,可见比例极小;顺治7份,康熙16份,雍正5份,乾隆12份,嘉庆12份,道光11份,咸丰8份,同治6份,光绪4份,清前中期的契约文书份数约占69%,可见该谱契约文书时间集中于清前中期;另有两份年代不详,但可以判断大致属于清代。
此外,根据契约交易内容性质划分,土地、山林、坟产交易契约有71份,可见,方姓无论是与外姓还是与本族成员之间,土地交易占了绝大部分;因土地、坟地等存在私卖、盗砍、划分不清等而产生的合同文约有12份,还有代为收纳收领契约4份,及划分责任所立文约有4份。根据交易对象,方氏与外姓交易的契约文书有82份,与本族成员的交易契约文书有9份。
二、祁门县《方氏族谱》契约文书体例分析
收录于《方氏族谱》中的族谱契约文书日常同散件文书一样,首先会写明卖方为何许人也,其次会寫明所卖土地及其边界详细情况,再交代卖与何人,成交价也会写明收银几何,最后还要做一番说明:“其山地田,未卖之先,与家外人等并无重互交易,来历不明,卖人自理,不干买人之事,自定之后,二名无悔,如违,甘罚契价一半公用,今欲有凭,立此存照”,诸如此类术语,表明交易已完成并且两方皆无异议。在契尾则是写明交易年月日等,卖方画押或签字号;随后便是中见人画押签字。为了说明交易土地等产业,契约后还会附上地图、坟图、祠堂等图示作为辅助,这是散件文书相对缺少的。然而,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契约,从形式上看,其行文都是极其格式化的。[6]如:
文堂陈思翘同弟思恪,今有承祖买受得山一号,坐落五保土名司徒庙下,其山东至山脚吴凰平地,西至汪重保地,南至吴凰山,北至方思禄山。因管业不便,出卖与在城三四都方思禄名下为业,当日面议,时值纹银四两五钱整,在手足讫,所有家外人等并无异说,今恐无凭,立此存照。
内批其山税粮,悉照老额扒税二厘,入三四都方元茂户,供解无辞,翘书。
顺治十三年闰正月初六日 立卖契人陈思翘押 陈思恪号
中见人:陈以環号 可仰号 陈正傅号[7]
从这份契约文书可以看出,契首直接载明卖方是陈思翘和陈思恪,两人乃是兄弟关系,来自文堂陈氏,此外没有写明其年龄、家庭其他信息,开头直接写明卖契人,这也是族谱契约文书的重要特征,同时立契人数也由一个至多个不等。此外,在族谱契约文书中,存在不少买卖双方属于亲戚关系的现象,并且会在契约中写明“卖与戚方××”,在契尾的立卖契人、中见人、代笔人等,往往是其亲属、邻人等谊属。
另外,根据上一章节的统计,可以发现这批方氏族谱契约文书中,买方为方氏族人的契约文书份数占比为76%左右。在清朝,优先购买权在民间已成为一个社会习惯,而在族谱中我们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方氏本宗族成员及其祠堂等是具有优先购买权的,这是族谱契约文书的一个重要特点。相反,外姓人购买土地的契约则少之又少,这便是宗族利益优先原则。
对于交易过程也是一再言明公平自愿,并无意志强加,方氏族谱契约文书虽然格式没有严明统一,但“自情愿”等字眼是一定有的,此外涉及交易价格时,有“时值”字眼,说明价格是符合当时的市场价的,公平合理,也杜绝了日后双方觉得价格过低而产生纠纷的情况。不仅如此,在契尾部分还会加上“与家外人等并无重户交易,来历不明,卖人自理,不干买人之事,自定之后,各不许悔,如违,甘罚契价一半公用,今恐无凭,立此为照”,可谓慎之又慎,这样避免了以后许多争端的出现。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族谱契约文书与日常所见散件契约文书大体相当,族谱契约文书中的买方往往是宗族成员或祠堂,极少有外人,契约参与人如卖方、中见人、代笔人也往往和买方或互相之间存在亲戚或邻居关系。
三、《方氏族谱》契约文书相关内容探究
通过方氏宗族收录的这一批数量可观的族谱契约文书,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方氏宗族在清前中期其宗族所拥有的相关产业,如田地、林地、山地、坟产、树木等等,在91份契约文书中涉及的产业有好几十个,至少可以判断,祁门赤桥方氏这一支在清中期时期宗族产业及个人产业发展壮大,并且明显超过了其附近的诸多姓氏如郑氏、李氏、吴氏等等。这些产业从名称上可以判断分布还是比较广泛的,不仅包括祁门县的,还有邻近浮梁县的;而且类型多样,有祠堂,有水塘,有菜园地,有茶山,有坟地,有风水宝地,有棺椁,亦有钱租。
清初期时,祁门赤桥方氏宗族产业已经开始发展了,陈、汪、李、吴四姓,在祁门都不是小名小姓,方氏有财力从他们手中购买诸多山林土地,可见发展之昌盛。而根据《方氏宗谱》契约文书的统计,与方氏进行交易的姓氏涉及陈、吴、汪、郑、李、冯、刘、程、许、林、胡以及浮梁的揭、章、朱等共计十余姓,可见方氏宗族土地交易人群范围之广。另外,从契约文书内容也可看到这一时期方氏与其他姓氏之间的实力升降,如这份契約:
立从议兴祀合文约人方明德祠秩下麒祯等,崇本祠秩下士云等,缘我十四世祖得五公由北伟溪迁居南乡三四都路公桥柯源,至今历传二十有余,世中有二十三十世祖得俊公以柯源地窄迁于西乡二十都,沿边居住,年远丁繁,递年清明祭扫,德五公等坟墓以向来未有公祀,二祠秩下届期分标,今因祖遗有签业在三四都洪字号,土名张家塅地一块,公同商议出便与郑仆蓄养住基下庇当,得价钱一百六十千文整……
咸丰十年三月初七日[8]
从中可知,方明德祠与方崇本祠两祠因遗留有签业在三四都,遂将其出便与郑仆蓄养,这里把郑氏称呼为仆,可见,当时郑氏有部分族人已经沦落为方氏的佃仆。有清一代,赤桥方氏所展现了强大的土地购买力和经济实力。
中人是土地买卖契约文书中除却买卖双方之外的重要参与者,中人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方氏族谱这些土地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凭中人,有些是一位,也有些是十数位,数量无定数,总体而言数量较多,这与买卖双方交易金额大小及田地数量都无关系,即中见人是必须存在的,但是也有少部分契约并没有中见人记录。中人在交易中是以买卖双方之外的第三人身份参与交易当中,作为中间人,应当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履行连接双方的桥梁作用和监督作用。但实际中,在方氏宗族契约文书中的中人与卖主大多存在着一定的亲属关系,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偏向现象,无法做到公平公正。大部分契约其中见人可从名字判断与卖主属于同一宗族同一字辈之人,可见就算不是堂兄弟,也属于同族兄弟或家长。
另外则是族谱契约文书中的签字画押问题,通常位于契尾,签字画押人通常由立契人、中见人或代笔人等组成,方氏族谱契约文书中,契约部分一般会写明主要的立契人,也有中见人兼任代笔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方氏族谱契约文书中,几乎没有看到由立契人亲笔书写的契约,都是由第三方作为代笔人,而这代笔人有时也是卖主的亲属。除此之外,在这些契约文书中几乎没有看到买方的签字画押,而卖主、中人、代笔人等都是有签字画押的,这就使得这份契约更像是卖方的一分单方面承诺声明,如若日后出现纠纷或纰漏,卖方就会陷入被动与麻烦,而买方则占有十分主动的有利地位。
方氏宗族这批契约文书所属年代主要是清前中期,因此,透过这些契约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现象。清初期的统治者大胆果断地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和相关措施,与民生息,社会繁荣发展,土地流转加快,出现了许多土地交易。徽州自古多山地,耕地稀少,山林田地多碎片化,从契约文书中对于所交易的土地来看,其面积大小不一。此外,还存在土地重复买卖的现象,土地买卖异常活跃。“俗语云: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农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间,已易数主。”[9]同时,民间的这种土地间的随意交易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土地相对集中起来,虽然民间的这样一种土地交易“乱象”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统治者意志,但这种“乱象”帮助了统治者把土地集中化、规模化,有利于稳固社会,安定民心。杨国桢对明清土地买卖结构研究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着地缘与血缘结合的乡族共同体。在乡族共同体内部,个人的活动和对其土地和财产的支配是存在的,亦即有私人土地所有权,但私人的土地权利受到乡族共同体的限制和支配,这在私人土地的继承、让渡、买卖时,表现尤为明显。[10]
关于方氏族谱契约文书交易内容,笔者还关注到在土地交易中买卖双方成交时所使用的货币,主要是白银为主,如时价纹银××两整、××钱整,所用货币皆为白银铜钱,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几份光绪年间的契约文书,其交易所使用的便不是白银,而是英洋即洋錢,契约文书中成交价写作时价英洋××元整、代纳英洋××元。通过这里隐约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自从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涌入中国,欧风美雨深刻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生活,最显著的便是在社会经济方面,商品里出现了洋货,交易对象出现了洋人,契约文书中的交易货币由白银铜钱为主逐渐演化为英洋,这正是一个时代变化的缩影。
四、结语
契约文书是历史学研究重要的文献史料,它记录民间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活动,含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是珍贵史料,对这类史料的保护、搜集与整理是非常重要的。族谱契约文书与散件契约文书相比较,在格式上、书写上、程序上大致是相当的,它们都具备作为契约文书所有的契首、契中、契尾等要素。中人大多是与卖方存在亲属关系的,这使得契约的公平合理性让人质疑;其次很明显的契尾没有买方的画押,这也使得契约让卖方处于极被动的地位。在方氏族谱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买卖交易皆是方氏从他姓购入产业,有方姓出卖亦是由方姓买回,可见这是符合本族经济利益的土地优先购买权。透过这样一批的契约,其背后也反映了一定的大历史背景,要更好地理解这些族谱契约,将其置于当时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我们将会发现契约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内容。
参考文献:
[1]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2](清)周溶修,汪韵珊纂.祁门县志·重修祁门县志序[A]//中国地方志丛书·华中地方[M].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5.
[3]汪廷枢.重修方氏宗谱序[A]//(同治)方氏宗谱[O].上海图书馆.
[4]程成贵主编.祁门通[M].祁门县地方志办公室,1997.
[5]汪怀清.方氏合修宗谱序·营前改公秩下例贡生策撰族谱序[A]//(光绪)方氏宗谱[O].上海图书馆藏.
[6]赵晓耕.身份与契约: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形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19.
[7](光绪)方氏宗谱[O].上海图书馆:253.
[8](光绪)方氏宗谱[O].上海图书馆:1206.
[9](清)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0.
[10]杨国桢.明代土地契约文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作者简介:
邹中强,男,汉族,江西瑞金人,安徽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史、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