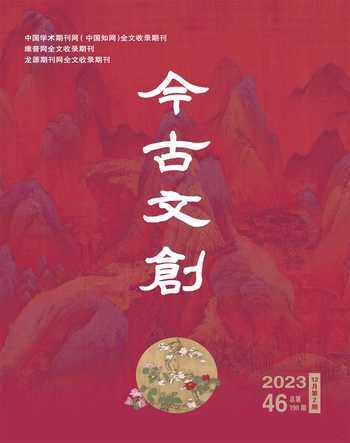布思对存在主义文论的“苔瑟拉” 式修正:个体性的当代转向
2023-12-25陈思
【摘要】第二代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韦恩·C·布思的《小说修辞学》自20世纪下半叶问世以来,即成叙事学与修辞学研究的经典,既探讨了叙事和修辞技巧,又以文学批评为基点,在更深层次上分析了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认为,布思理论中的“第二自我”(the second-self)和“隐含作者”(the implied author)等概念在给予作者更大自由度和个体性的前提下,形成了对存在主义文论中自我与他人问题的“苔瑟拉”(Tessera)式修正,实现了作者个体性和生命性的物质化表达,这种修正折射出的正是个体生命性与物质性的当代转向。
【关键词】韦恩·C·布思;《小说修辞学》;存在主义文论;个体性;“苔瑟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6-006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6.019
布思作为芝加哥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之一,在欧美盛行外部批评的浪潮中复归文本内部,反复探究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与小说艺术的价值。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多次提到包括萨特在内的存在主义文论的观点,并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对其进行批评与修正。存在主义文论自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大地与世界的艺术观以来,经萨特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法国思潮下对自由与生命的独特理解,折射出对自我与他人问题的多重解读。布思基于存在主义文论中对自由的阐发,进一步发展了小说文本的修辞理论,在加深作者客观性的基础上给作者以更大的自由度,实现了对存在主义文论的修正。
本文拟从海德格尔的艺术观入手,进而剖析萨特的文学理论中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映照出布思“苔瑟拉”式修正的方法与效果,最终得到结论,布思的修正背后实则是个体性与生命性的当代性转向。
一、“此”与“彼”:存在主义文论的探索
存在主义文论是20世纪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艺术方面的衍生理论。海德格尔首次将艺术本质与真理相联系,认为艺术的本质即显示真理。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以寻求艺术的本质为起点,对真理的本质进行了详细的存在论分析。他认为真理即与实在相符,实在即处于真理之中(41),言外之意,艺术的本质即显现出真实的本质。根据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本质绝非黑格尔式的形而上的同一性,而是生存论范畴上的存在(Sein und Zeit:19),因而真实的本质即艺术作品的物性因素的存在。物性因素的根本在于实在的存在,海氏认为物性的存在寻根究底是“无蔽”(Aletheia),“对思想者而言,对思想者而言,无蔽乃希腊式此在中遮蔽最深的東西,但同时也是早就开始规定着一切在场者之在场的东西。”(海德格尔:45)海氏之“无蔽”与古希腊哲学始基(arche)一词近似,是最本真的东西,但在日常状态下被遮蔽最深。由此,存在实际上是无蔽在任何情况下的表征,那么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考察则可使我们得到无蔽,得到真理。真理即无蔽状态,实则是双重遮蔽下的否定,对遮蔽的去蔽则源于“澄明”(Lichtung)的双重遮蔽,使得人能够通达非人的存在者,走向我们本身所是的存在者(海德格尔:48)。海德格尔指出,这种澄明在艺术领域则是艺术家所建立起的“世界”,而基础则是遮蔽着无蔽的“大地”,此二者的原始争执(Urstreit)才是艺术作品的本源。世界代表着艺术家的澄明之运思,而大地则是遮蔽着的无蔽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的质料与物,“大地就一味地通过世界而凸现,世界就一味地建基于大地中。”(海德格尔:50),大地是物的封闭的原始形态,而世界是敞开状态,大地以遮蔽的样貌在世界之敞开中显现,而世界则建立在大地的原始形态之上。“作品建立着世界并且制造着大地,作品因之是那种争执的实现过程,在这种争执中,存在者整体之无蔽状态亦即真理被争得了。”(海德格尔:42)作品作为大地与世界之争的表征效果,被争得意味着是无蔽之本质的显现。作品中的真理并非大地的意义,而是世界在大地的基础上以澄明的方式显示出无蔽之本质,换言之,真理被设置入艺术作品之中,并且通过艺术作品确证着自身(Dahlstorm :23)。在世界与大地的冲突中,作品的存在方进入无蔽状态之中。艺术作品以一种新的方式显现出物的本质,也正因如此建立了一个世界,这意味着一种对世界之世界性的存在论上的洞见(Grieder:197)。
总体看来,海德格尔认为,文学作品绝非柏拉图式的理念,而是一场历史性的事件,是世界与大地的冲突,主要指“意义化”的世界和“无意义化”的大地的对立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作品描述的存在者既显示又隐匿地出场,形成真理和本质的双重遮蔽和否定,作品由此而诞生。寻根究底,产生作品的并非作者,而是冲突本身,作者只是这个冲突的中介而已。艺术家所做的是创作,是以大地之遮蔽为质料,将无蔽带入到世界,在世界之澄明中显示出真理与本质。
循着这条线索,萨特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对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揭示。作品是作者以实现自由为目的而创造的他者,但这个他人已经创造出来就脱离了作者的意识控制,成为客观的存在。这一点似与海德格尔艺术是冲突的表征似有相近之处,并将这种表征进一步客体化,形成以自由为基底的存在形式。萨特将存在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自在的存在,即一种与其自身相符合的存在,因而它是僵死的、封闭的、结束了的;另一种是自为的存在,即意识,通过虚无化的自在把虚无引进存在的一种活动过程(祁雅理:103)。写作无疑是自为存在的面向虚无的一种重要活动,最终目的必定是由不是其所是的自为走向是其所是的自在。萨特认为,写作首先就是要将质料变为客体和对象,并与其保持距离,“他要把这个颜色-客体搬到画布上去,他让它受到的唯一改变是把它变成想象的客体。”(Sartre :92)而后,画家本人运用这些质料必将暗含着一种意识层面的动机,即将诸多颜料引向另一集合的理由,这样创造出的客体反映出了画家最深藏不露的意向。作品的形成则意味着无定性的消灭,即本质的取得。此处可见萨特关于艺术本质的观点与海德格尔的差别: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质源于原始冲突,以及无蔽在双重遮蔽下的否定;但萨特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在作者一次次的选择中取得的,因人没有事先规定的本质,是自由的,通过一系列选择实现其本质,此时作品的本质之给定则直接源于人在当前处境下的多重选择,可以说作品是人的处境的直接表征。相比之下,萨特的艺术观点较海德格尔更具人格化的特征,并且将艺术作品以更“人化”和“自由化”的形态呈现。
萨特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是“介入”,他认为,创作与生产最大的区别在于,“作家是与意义打交道的”(萨特:94),文字与语言是作家以一种强大的意向“介入”世界的工具,“介入”后的结果则是作品脱离作者而成为纯粹客观的实在,而这种实在的存在则需要被见证,“书确实不是一个客体,也不是一个行为,甚至不是一个思想:它由一名死者写成,讲述死去的事情……没人理睬它的时候,书就收缩、倒塌……而当批评家使墨渍复活,墨渍就对他谈论他并不怀有的激情,没有对象的怒火,以及死去的恐惧和希望。”(萨特:106)由此,萨特一方面表达了对作品绝对客观性的肯定—他首先指出了作品既成,作者即死的观点;另一方面他指出,作品需要读者而确定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这无疑是对海德格尔艺术观点的细化,既提出了作品的绝对客观性,也指明了读者对于作品的重要意义,这也为后来罗兰·巴特等人的文艺理论提供了灵感。
萨特哲学中自我与他人体现为是显现与被显现、意识与被意识的复杂关系(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67),而萨特的文学理论的对象是作品,是由自我创作出的他人,因而我与他的关系中的“他的自在”的成分形成了一种悖论,即他的内容是我规定的,是我的自为性的表征结果,而他的自在只能通过另一个别人来确证,换言之,虽然他人本应天然地具有生存论范畴上的生命性,而作品作为他者,生命性的实现却只能寄托于读者。也就是说,作品本身生命性的错位导致了作者、作品和读者三方的关系被扭成了一个莫比乌斯带,只有自由的概念可以通行其上。
综上所述,存在主义文论在“此”与“彼”的关系问题上已有了对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在海德格尔到萨特的演进中又体现出作品物质化和客体化的进程,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则是,通行于三者之间的自由到底如何体现?作者本身又该在此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解答此问必须从作者的创作手法切入,这无疑为布思的小说修辞理论提供了充足的论证空间。
二、作者的生命性:布思的多重作者
作为芝加哥学派的第二代理论家与第一代最为显著的差异就在于,这一代的文论更偏向于考虑文本的意图而非作者的意图,在文类规约的作用下,文本内部成分相互关联,组成一个艺术整体,对作者提出要求(Leitch:56),从而突出形式和结构上的完整性和自洽性。换言之,如此做法无疑将作者的意图诉诸文本,使其文本化,进而推进了存在主义文论中作品物质化和客体性的进程。布思的观点与此潮流大体相同,但更注重于读者和作者的交流,并关注在何种手法的修饰下,交流的样态如何(申丹,《修辞性叙事学》:83),这一做法在加强修辞学分析的基础上,亦推动了作者生命性和个体性在文本中的物质化表达。
《小说修辞学》针对作者提出了几个全新的概念,呈现出作者之于作品和读者的生命性和自由性。正如萨特的观点,小说中的任何东西都是作者操纵的表現,布思一开始就否定了纯粹不介入的可能性,同时驳斥了所谓“作者的隐退”的观点,并由此提出“隐含的作者”(the implied author),即小说世界中作者潜在的“自身”,是“第二自我”(the second self)。由此,布思展开了对作者客观性和非人格化观点的批驳。他指出,小说中人物内心的变化和角度的转换并非生活日常所有,小说中的呈现本身就意味着作者的介入,且小说中作者的声音事实上从未消失,小说时刻受到作者的影响(Booth:74)。萨特认为,早期诸种叙事手段均是作者为了使读者注意到作者的存在,而现代小说却以作者身份的隐匿为主要手段,出其不意地将读者带入玄幻之中(Sartre,Situation of the Writer in 1947:169)。布思恰以此为自身辩白,指出所谓隐匿不过是现代小说为达效果的叙事手段而已,事实上,作者的操纵丝毫没有隐匿,“萨特声称每一件事物都是作者操纵的表现信号,这肯定是正确的”(Booth:76)。同时小说中作者的声音是不可能消除的,因为作者的声音是一种选择,在小说创作的一开始就已经深刻地埋入了作品中,并形成了作者的判断,这一点可以伪装,但绝不可能消失,是为“隐含作者”的存在之必然,是作者在创作之时所做出的选择的重要表征。布思认为,为了使自己的选择更贴合作品内容,能够在不引起读者注意的前提下,更好地完成叙事和修饰,作者在创作选择上安排替身走入作品,以更加客观和非人格化的形式完成叙事任务。这些替身实则是不同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作家会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表达自己(Booth:170),借此“第二自我”的形式使得现代小说的作者能够在不引起读者注意的情况下将读者拖进一个未知的世界,是为现代小说创作的创新之处。
布思进一步指出“隐含作者”的精要之处和思想规范的核心,即“风格”(style)、“基调”(tone)和“技巧”(technique),这三个标量使得“隐含作者”能够在作者创作之时真正地忠实于自身的创作意图。换言之,作品之伟大正取决于作者写小说那一刻的选择和决定,这恰恰为“不可靠叙事”创造了空间,当时所做的决定与三种标量的实际效果才是判定作者对作品忠实程度的唯一标准。另外,作者在“第二自我”发挥作用时,有意隐去了观点和立场,这在布思看来并非作者的无中介和纯粹不介入,而是作者有意不打扰读者,为读者留下空间和立场的创作选择,虽是保留,但亦出于主观决定。换言之,所谓“隐含作者”“第二自我”是布思出于对作者和读者之间交流技巧,以及影响如何控制读者的手段的探究(申丹,《作者、文本与读者》:18),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作者本人创作意图文本化和物质化程度和效率的提高,使得小说在复调的形式下为读者营造更丰富的世界。
综上所述,布思以“隐含作者”以及多重叙事声音的概念充分批驳了非人格化作者和纯粹不介入的文论观点,本质上涉及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充分体现出对三者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和实践。在布思看来,非人格化的作者实则面临悖论,作者的主观如果全部消除,作品中的评论则无法实现,反之,则无法解释作者的隐退现象。对此,布思的解决方案无疑是中间道路:分离出作品中的“隐含作者”,形成作品范围内绝对客观的一方,即“第二自我”,使其可以在作品内充分完成创作选择所规定的“风格”“基调”和“技巧”,既保存了作品的主观效果,又使作者能够相对独立地完成对作品这个他者的规定,由此形成的作者与作品、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一种平衡:“隐含作者”游离于这两对关系中间,使得作品既完成了创作意图的显现,又成为相对独立的他者,同时面对读者和作者,这无疑是对存在主义文论的进一步细化与发展,也是对当时流行的非人格作者的强力反击。
三、“苔瑟拉” :修正与个体性
着墨于作者生命性和个体性在文本中的物质化表达,布思的观点实际上是异于外部批评和内部批评主流的第三条道路,在进行精细的内部批评之前,先对身处作品外部的作者进行重新定位。这种定位实则是对作者本身的二重分解,改造了存在主义文论绝对客观的作者,而是从中分化出一部分适应作品环境成分的第二自我。布思的“隐含作者”显然是对存在主义文论的一种修正。不论是萨特还是海德格尔,都强调作品的绝对客观性,以及作为异于作者之外的他者的独立性,因此主张作者在作品的存在应该被彻底消除,使读者在不经意间被带入未知世界,形成現代小说的独特风格。
但布思的问题是,作者在文内的评论既属于作品这个他者的一部分,就绝无可能被彻底抹去,只能将作者对读者的操控由明转暗,将作者名义上的消声诉诸小说本身的修辞技巧,尤其是叙事技巧,方能兼顾作者个体性与作品客观性,进而保证读者的实在体验。
综合看来,布思的方法在立场是延续了存在主义文论,但在演进过程中做出了修正和调整,实则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六种修正比之一——“苔瑟拉”(Tessera)。布鲁姆认为,“所有的阐释都取决于意义之间的对抗关系,而不是取决于一个文本和其意义之间的假设关系。”(A Map of Misreading :79)后辈对前人的“对抗式批评”基于总体概念和意群的对照,形成自身立场下有目的的误读,是为修正。根据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中六种修正比的定义,“苔瑟拉”专指对前人作品的反题和完善式修改(antithetical and completing revision),使得张力加强,根源上是因为前人的观点无法满足当前的论述需求,由此形成的焦虑促使了对前人观点和基本概念的修正,并且以反题和分解的样态出现(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57)。这种反题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并置(juxtaposition),指以平衡的方式将相反概念并置于平行结构中,形成自身的合题和演绎;二是补足(complement),指后人以自身立场和想象对前人概念进行补足,以示修正(66)。拉康对弗洛伊德正是“苔瑟拉”式修正,这种修正在形式上表现为以更细致的概念和思考打磨前人已经磨损了的雕像(the worn out effigy)。
与拉康所做的修正相近,布思对存在主义文论的修正首先在形式上体现为术语和体系的精细化和复杂化演绎,从海德格尔诗意哲学“大地”与“世界”之隐喻、萨特的作者“介入”,到布思“隐含作者”“第二自我”“不可靠叙事”等术语,很鲜明的进程是,作者、读者与作品三者的关系趋于明晰化,同时对作者本身的主客二元化使得三者的关系更加复杂:一方面在作者分化的情形下,作品既是作者创作处境之选择的效果和表征,又在客观的形式中有效地牵引了读者;另一方面,因作者分化出外在于自我的“第二自我”,形成复调多重叙事效果,与读者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为读者留下了批评的中间地带,保证了他者的自为性之可能,是对萨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绝佳实践,同时超越了萨特单纯强调作者客观性而造成的“莫比乌斯环”式悖论,将作者的诉求与对作品和读者两重他者的客体性关切诉诸作者本身的客观性分化,形成作者生命性和个体性在文本中的物质化表达。
布思的“苔瑟拉”式修正带来的实际上是存在主义的当代性表征,是拟于当时外文本批评,对人本身生命性和个体性的复归。这种对作者介入的模糊恰恰实现了作者全身心进入文本的自由度,可看作是解构之后实现的个体化转向,生命性的均衡状态。当代性,罗兰·巴特曾有过这样的总结,“当代,就是不合时宜”,而阿甘本的定义和结论则是:“当代性,就是指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 (Agamben:41)。所谓当代的凝思,总因带有鲜明的“脱节感”,才能在一定的距离外冷静而极具洞见地审视当代,才不会陷入时代的洪流中无法抽身,变成时尚人。而正是这种远离当代的光芒,毋宁躲进黑暗中的距离使得“他对时代的光芒不敏感,而对时代的痛苦、时代的脊骨断裂异常敏感。”(汪民安:11)后工业时代是一个技术发展到了极致,无机与有机的界限、生命和非生命的界限无限模糊的时代,技术的光辉之下,真正的当代人却宁愿躲进阴暗的角落,用一种不被时尚所理解的目光审视这个被技术扭曲而无限数码化的时代。
布思身处20世纪后半叶,对作者生命性和客体性的物质化演绎无疑形成异于时代的前瞻性思考。《小说修辞学》折射出的不仅是文艺理论的时代转型和演进,背后实则是对人本身的深入思考,后工业时代的人在面临外部消解威胁之时,如何保持内部超越性。由此,布思的“隐含作者”成为生命性和个体性内在化建构的绝佳实践,这才是一代理论真正的夺目之处。
参考文献:
[1]Agamben,Giorgio.“What is the Contemporary?”. What is an Apparatus?and Other Essays.Trans.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Sta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Bloom,Harold.A Map of Misreading.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3]Bloom,Harold.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Booth,Wayne C.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
[5]Dahlstorm,Daniel O.The Heidegger Dictionary. London and 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2013.
[6]Grieder,Alfons.“What did Heidegger mean by ‘Essence’?”.Martin Heidegger Critical Assessments. Ed.Christopher Macan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2.
[7]Heidegger,Martin.Sein und Zeit.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1967.
[8]Sartre,Jean-Paul.L’être et le néant:Essai d’ 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Éditions Gallimard,1943.
[9]Sartre,Jean-Paul.“Situation of the Writer in 1947”,What is Literature?Trans.Bernard Frechtman.London:Routledge,2001.
[10]申丹.修辞性叙事学[J].外国文学,2020,(01): 80-95.
[11]申丹.作者、文本与读者:评韦恩·C·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2,(01):16-25.
[12](法)让-保罗·萨特.萨特文论选[M].施康强等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13](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4]汪民安.福柯、本雅明与阿甘本:什么是当代?[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06):10-17.
[15](法)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从柏格森到莱维-施特劳斯[M].吴永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作者简介:
陈思,女,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2021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浪漫主义、媒介哲学与技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