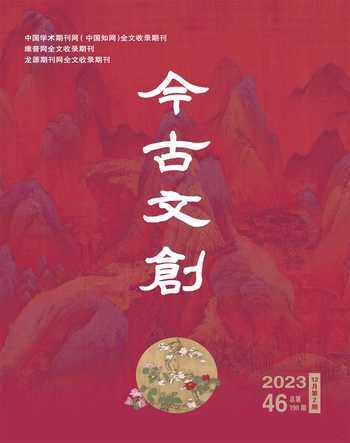平衡与希望之歌
2023-12-25朱希
【摘要】《大地之上》是印度裔加拿大作家罗欣顿·米斯特里的长篇代表作之一,它以英迪拉·甘地宣布紧急状态后的印度为背景,以寡妇迪娜、大学生马内克以及裁缝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什四位主人公的命运为主线,刻画了特殊历史时期之下印度底层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米斯特里将小说命名为《A Fine Balance》,其中的“平衡”一词显然有着特殊的含义,这是一种在苦难中维系生存的韧性,在绝望中怀有希望的力量。米斯特里歌颂这份来自底层的伟大生命力,在人生和社会的双重失衡中,他们始终在命运的缝隙中寻找自己生命的平衡。
【关键词】《大地之上》;罗欣顿·米斯特里;印度;底层人民;平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6-0015-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6.004
《大地之上》是印度裔加拿大作家罗欣顿·米斯特里的长篇代表作之一,它荣获了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吉勒奖、英联邦作家最佳图书奖、洛杉矶时报小说奖等诸多奖项。小说以英迪拉·甘地宣布紧急状态后的印度为背景,以寡妇迪娜、大学生马内克以及裁缝伯侄伊什瓦和翁普拉卡什四位主人公的命运为主线,展现了印度数十年的风云变幻,描绘了一段特殊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苦乐悲欢和他们坚韧的生命力。《大地之上》一书继承了米斯特里惯常的历史与小人物叙事,他表示:“我在这本书中有意识地包含了更多的东西,主要是因为在印度,75%的人居住在乡镇,我想要拥抱更多的印度社会现实。” ①这部小说将批判的笔锋直指印度社会的种种弊病:种姓歧视、宗教冲突、政治腐败……米斯特里以流散者的姿态苛刻地审视着他的母国,又以慈悲的目光观照着那些沉默的人民,以如椽巨笔揭示出被忽视、被掩盖、被隐藏的真实的印度。
米斯特里将这部小说命名为《A Fine Balance》,2015年的第一版中译本将其译为《微妙的平衡》,“平衡(Balance)”一词在书中显然有着特殊的含义。米斯特里借校对员瓦尔米克之口告诉读者:“有时候,人就是要把失败的经历当作成功的垫脚石。要在希望与绝望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归根结底就是保持平衡的问题。” ②
在小说中,几乎所有人都处在被控制、被剥夺、被压迫的失衡状态中:裁缝伯侄伊什瓦和小翁出身低种姓家庭,家人由于反抗种姓制被地主放火烧死,两人来到城里谋生,却在紧急状态法实行的混乱中遭遇一系列祸事,最终身体残疾,沦为乞丐。迪娜自幼丧父,从小被哥哥管控,渴望独立和自由,丈夫不幸去世后,她自谋生路,靠缝纫生意糊口。但随着局势的动荡,她雇佣的裁缝伯侄成了乞丐,房客马内克去了迪拜,她也被房东赶出了公寓,只能回到哥哥家中。大学生马内克乐观善良,在迪娜公寓租住期间,他和裁缝、迪娜一起度过了一段虽有动荡但幸福美好的时光,然而,在目睹着好朋友阿维纳什因参加抗议活动被政府虐待至死、裁缝伯侄失去了双腿和生殖能力、迪娜失去了生意后,他美好的社会理想破灭了,黑暗的现实令他绝望,最终选择了卧轨自杀。“平衡”正是一种在苦难中维系生存的韧性,在绝望中怀有希望的力量。在人生和社会的双重失衡中,他们始终在命运的缝隙中寻找自己生命的平衡。
一、人生的失衡与平衡
(一)迪娜:管控与觉醒
迪娜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帕西族家庭,然而在她十二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她的监护职责落到了哥哥努斯万手里。但努斯万并没有将迪娜视为一个平等的、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待,在他心里,迪娜更多是作为一个附庸者和所有物而存在,他对迪娜的唯一要求就是听话,因而,当迪娜的行事超出了他的设想或不符合他的心意时,他就会暴跳如雷,认为迪娜脱离了他的控制。小说中的努斯万是集中体现了印度男权压迫的典型人物,迪娜的觉醒也来自努斯万对她的层层剥夺。迪娜从小的梦想便是继承父亲的职业当一名医生,然而在努斯万接过了监护她的职责后,她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她的职业梦想也因此夭折。但这并不是唯一,努斯万还禁止她剪短发,这使她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禁止她拜访朋友,这使她失去了人格和尊严。在她长大成人后,努斯万还计划着将她的婚姻作为一次利益交換,将迪娜像物品一样送给那些能给他带来权力、财富、地位的人。而迪娜在一次次的丧失和忍让中,觉醒了她作为女性的独立和反抗意识。
从某种程度上说,迪娜是“新女性”的象征,她拒绝努斯万对她婚姻的操纵,选择了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即使婚后要过清贫的生活,她也决心要脱离努斯万的管控,拿回独立自主的人生。而在丈夫去世后,迪娜在努斯万的金钱威胁之下,意识到女性要在社会中立足必须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她学习缝纫和理发的技术,努力赚钱养活自己。努斯万曾经嘲讽过她:“你已经三十岁了。一旦你人老珠黄,再生孩子可就来不及了。我现在还能帮你找个体面的丈夫。你这么拼命地糊口究竟是为了什么啊?”努斯万不能理解迪娜的选择,他和印度底层的多数人一样,认为女性就是照顾家庭和延续后代的角色。然而迪娜早已认识到了这种依附的后果,她为独立所做出的反抗象征着底层女性逐渐摆脱家庭角色,进入到由男性掌握着话语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
迪娜的觉醒既是其个人的偶然,也是社会的必然。她出生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当时,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发展女性教育。妇女通过教育提升了自身素质,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她们逐步意识到作为人的价值、意识到男女地位的平等,因而有了自我价值实现的诉求③。迪娜接受过良好的初级教育,她对独立人格的追求是长期受到压迫后的必然反抗,也是整个印度社会女性在思想启蒙后的必然觉醒。
(二)伊什瓦和小翁:歧视与反抗
如果说迪娜的觉醒是个人的觉醒,那么伊什瓦和小翁所代表的是一个家族两代人对于种姓制度的斗争。伊什瓦的父亲杜奇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皮匠,和许许多多的低种姓贱民一样忍受着高种姓人的奴役和羞辱,杜奇因为生了两个儿子,遭到了高种姓人家的嫉恨,他只能“极尽所能对人卑躬屈膝。每次在路上遇到高种姓的人,他都是低声下气地趴伏在地上” ④。然而,当杜奇为地主工作了一天,没有收到回报,反而遭到了一顿毒打时,他开始觉醒了,他咒骂高种姓的地主们:“我真恨不得杀了那个塔库尔。他就是个下贱的贼。他……把我们当牲口使唤……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靠他们那些破工作讨生活了。” ⑤他将两个儿子送去了穆斯林的裁缝店里学习缝纫,并且将他们的姓氏改为了“达尔吉”,这是一个穆斯林名字,他试图以这种方式跳出印度教种姓的禁锢。
杜奇是成功的,他的小儿子纳拉扬传承了父亲的斗志,率先在家乡举起了反抗种姓制的旗帜。纳拉扬在学成裁缝手艺回村后公开表示,他的店不仅能为婆罗门做衣服,还能给班吉——这一在贱民中也是最底层的收尸人——做衣服。但他也意识到,单是由皮匠变为裁缝无法改变他们地位依旧低下的事实,他们获得了财富,但在政治参与上依旧是被忽视的人群。他渴望为低种姓人群争取平等的权利,因此他大胆地在议会选举上要求拿到选票,质疑达拉姆西塔库尔操纵选举,但却遭到了灭门之灾。
导致纳拉扬悲剧的是印度农村难以拔除的种姓制的遗毒,虽然勇气可嘉,但终究是以卵击石。而离开了农村的伊什瓦和小翁依旧被贱民的身份毒害着。他们在社会上处于最底层,所遭受的磨难是最多的,所面临的压迫也更令人窒息。他们不像杜奇和纳拉扬那样有明确的抗争对象——村子里高种姓的地主们,他们面对的是无形的制度、规章和法律。因而他们的反抗更多是一种妥协性的自我保全,他们知道自己无法与整体的社会力量抗衡,也无力去改变什么,只能在身不由己的生活中艰难地维持作为主体的人的尊严。他们坚信靠自己双手的劳动能够使自己拥有和他人平等的人格和地位,因而在被警察强行带到灌溉工地做苦力时,伊什瓦一直在向警察强调:他们是裁缝,他们有工作,他们不应该像乞丐一样出现在工地上。即使他们像石子一样被苦难的车轮反复碾压,但伯侄俩从不放弃生活的希望,就像小翁说的:“假如时间是一匹布,我就把所有不好的部分裁掉。裁掉吓人的黑夜,然后把幸福的部分缝起来,这样日子就更好挨一些。然后我就把它像大衣一样穿在身上,永远开开心心的。”他们以乐观对抗苦难,以坚韧对抗磋磨,哪怕是小翁被阉割、伊什瓦失去了双腿,二人沦为乞丐,他们仍选择笑着继续活下去。正如伊什瓦所说:“如果你的脸上满是笑容,就腾不出地方流泪了。” ⑥
(三)马内克:理想与破灭的现实
如果说迪娜和裁缝们是印度底层人民的写照,那么马内克这个人物则在一定程度上是米斯特里的代言人:一个在精神上无家可归,觉醒后又无力改变这个失衡的社会,最后陷入精神崩溃的人物。和迪娜、裁缝们不同,他的人生是一个由平衡走向失衡的过程。马内克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始终处在心灵的漂泊中。他热爱自己的家乡,然而父母却一次又一次地将他送到外面读书,他熟悉的山区也在工程和开发中变得面目全非。家里赖以为生的杂货铺生意凋零,他希望改变小店的经营模式以挽救生意,但父亲的固执己见让马内克无可奈何。在小说的前半段,马内克的言谈中总是充满了对回家的渴望,他想要回到童年时那个乌托邦一样的小镇生活,他坚信,只要自己能拿到家里杂货铺的经营权,就一定能扭转颓势,回到他所眷念的美好时光中,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度过大学生活。在成为迪娜的房客后,他目睹了裁缝伯侄遭受的种种磨难,他自己和迪娜也屡次遭到冲击,但每次动荡后总会迎来幸福的生活,这让他愈发坚信未来是美好的,生活充满希望,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个艰难的世道生存下来。
在完成了一年的学业后,马内克在家人的安排下到迪拜工作,直到八年后才返回印度。在和故土漫长的分别中,他一直保有期待,希望迪娜阿姨和裁缝伯侄此时仍然幸福地生活着,像多年前他们所盼望的那样。然而无情的现实击碎了马内克所有的向往:迪娜失去了她的生意,寄居在努斯万的家里;裁缝们身体残疾,沦为了乞丐;好朋友阿维纳什被政府拘捕后虐待至死,他的三个妹妹也上吊自杀了……他终于看清了,这是一个失衡的社会,是一个个人无法与之抗争的社会,一个个人无力改变的社会⑦。他想帮周围的人摆脱困境,却无能为力,想要反抗,却陷于这个失衡社会的泥沼之中。而他的家乡,他多年来一直渴望回归的地方,在父亲去世后显得如此陌生又疏离,他已经离开家太久了,永远也回不去他想象中的美好时光了。信念崩塌后,心灵也无处寄托,马内克面对的只有深深的绝望,他无法改变这个社会,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更做不到装聋作哑,留给他的只有自杀的结局。
二、社会的失衡与平衡
纵觀全书,四位主人公的一生仿佛陷入了轮回之中,想要逃离哥哥掌控的迪娜最后回到了努斯万的家中,想要逃离贱民身份的伊什瓦和小翁,最后还是无法逃脱贵族的毒手,而渴望回家的马内克绝望地死在了异乡。命运似乎有其既定的轨道,如同俄狄浦斯注定要杀父娶母一样,无论人类如何挣扎,都无法逃离命定的预言。但在《大地之上》中,米斯特里显然无意宣扬宗教的宿命论,他的字里行间都在暗示读者,四位主角的苦难是彻头彻尾的社会悲剧,是英迪拉·甘地和她的紧急状态法所带来的灾难,是种姓歧视、宗教冲突、政治腐败等社会弊病所导向的必然结局。
在小说中,伊什瓦和小翁被地主塔库尔灭门后,却因为贱民身份被报案的警官怒骂,指责他们惹是生非;他们在棚户区的房子被强拆了也无处说理,因为主持这项工作的正是政府的官员和警察;也是这同一批警察,将他们抓到了工地上做苦力。小翁的阉割和伊什瓦的截肢都是计划生育手术的后果,然而警察担心高低种姓之间爆发骚乱,对他们置之不理,负责结扎的官员更是将他们的申诉视作讹钱的伎俩。推动他们人生的从来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他人的意志。
在这个失却了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中,谈个人掌控命运是可笑的,在这个连基本人权都无法保障的时代,被统治者只能任由强权和暴力所宰割。在紧急状态法带来的社会动荡下,底层人民的生命如草芥般脆弱,然而即使紧急状态结束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没有发生变化,马内克1984年回国时,所听到的还是抱怨:“政府还在拆除穷人的房子和棚屋。在乡下,他们说只有结扎人数达标之后才会给村里挖新水井,他们告诉农民,不做结扎手术就不能领肥料。人生在世就是一天接一天的紧急状态。” ⑧正如小说末尾律师对迪娜所说的:“现在毕竟是暴力至上的时代……正义的神庙已经遭到玷污,正义被它的守护者屠杀,横尸其中……而现在,杀死正义的凶手在嘲弄神圣的司法过程,将公平倒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⑨
可以看出,米斯特里在创作《大地之上》时是相当悲观和绝望的,紧急状态法后的印度在他心中如同一个巨大的丑陋的怪物,印度之“根”已经败落、腐烂⑩,而生长于其中的人民只能被动地承受着时代的创伤。
不过,虽然米斯特里笔下的人物总是处在无尽的痛苦与磨难中,但他并不是一味地进行苦难叙事,他以质朴的笔触刻画了底层大众人性中光辉的一面,那些属于底层人民的善意、亲情与梦想,他们的乐观和豁达,他们对生活的希望,都在漆黑绝望的现实面前熠熠生辉。
穆斯林裁缝阿什拉夫是杜奇的朋友,当看到杜奇一家在村子里饱受磨难时,他主动伸出援手,将伊什瓦和纳拉扬收为学徒带出了村子。这一不经意的善举也拯救了阿什拉夫自己。印度独立前,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冲突不断升级,印度教教徒四处屠杀穆斯林,当战火烧到阿什拉夫家里时,是伊什瓦和纳拉扬站出来冒充店铺的主人,在死亡的阴影下掩护了阿什拉夫一家。伊什瓦和小翁刚住进迪娜家时,迪娜对两人始终持有警戒心理,但伯侄俩用他们的质朴和善良慢慢地感动了迪娜,在动荡的生活中,他们蜗居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起做饭、养猫,一起散步和聊天,像家人一样温馨地生活在一起。迪娜在寡居多年后,又一次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温暖和美好,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照顾着马内克和小翁,这份爱子之心让她在面对房东的威胁时,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保护一家人。在艰难的生活面前,这一抹温情足以治愈一切的痛苦和哀伤。
此外,小說中还充满着底层人物幽默风趣的对话和他们对苦难生活的自嘲,他们身处泥淖之中,但仍怀有对生活的乐观心态,伊什瓦总说:“我们的幸运星最终一定会到达正确的位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⑪即使最后沦为乞丐,伯侄俩也会彼此打趣,笑话拉着板车的小翁像一头牛拉着牛车。无论时局多么艰难,他们永远怀有一抹笑,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这一质朴的生活哲学是印度人最本真的生存智慧,一种在苦难中维系自我平衡的力量,米斯特里讴歌这份积极的力量,他向世人揭示了印度最真实的底层生活,也由衷地赞美了这片大地上每一个顽强生存的人,正如他在小说里所说,“希望总是有的——足以平衡我们的绝望。否则我们就彻底迷失了。” ⑫
三、结语
在《大地之上》一书中,米斯特里将目光聚焦于印度的边缘底层人物,书写了他们在紧急状态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动荡生活和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艰难历程。虽然失衡是人生的常态,但平衡的力量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这份力量是印度大地之上千百万底层百姓蓬勃坚韧的生命力,是那充满光辉而永不熄灭的人类精神。米斯特里是批判的,他无情地揭开印度腐烂的疮疤,书写被宏大叙事掩盖的真实历史。但他也是悲悯的,他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真正的苦难,为所有正在努力生存的人,谱写了一曲希望的颂歌。
注释:
①张呈敏:《罗辛顿·米斯垂:流散的印度帕西人》,《世界文化》2016年第9期,第16-17页。
②④⑤⑥⑧⑨⑪⑫(加拿大)罗欣顿·米斯特里著,张亦绮译:《大地之上》,天地出版社2021年版,第258页,第108页,第114页,第501页,第656页,第637页,第205页,第637页。
③杨雅楠:《英属印度殖民教育及其双重效果》,河南大学2011硕士学位论文。
⑦张呈敏:《论〈微妙的平衡〉的底层叙事》,天津外国语大学2017硕士学位论文。
⑩齐园:《边缘人生与失衡的印度——解读罗辛顿·米斯垂〈完美的平衡〉》,《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5年第2期,第39-41页。
参考文献:
[1](加拿大)罗欣顿·米斯特里.大地之上[M].张亦绮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
[2]张呈敏.论《微妙的平衡》的底层叙事[D].天津外国语大学,2017.
[3]杨雅楠.英属印度殖民教育及其双重效果[D].河南大学,2011.
[4]齐园.边缘人生与失衡的印度——解读罗辛顿·米斯垂《完美的平衡》[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5,15(02):39-41.
[5]张呈敏.罗辛顿·米斯垂:流散的印度帕西人[J].世界文化,2016,(09):16-17.
作者简介:
朱希,女,汉族,广东广州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