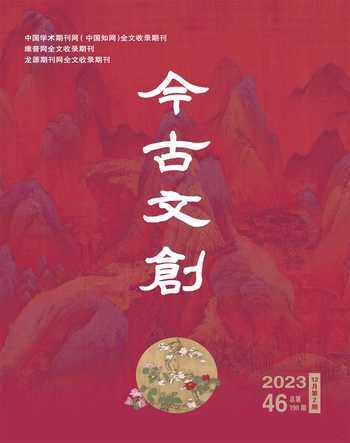从《来生债》看元代经济对 商人形象塑造的影响
2023-12-25顾昕怡
顾昕怡
【摘要】元代商品经济十分繁荣,这对元代戏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影响较为明显地体现在商人形象的塑造上,为进一步探讨经济对于元戏曲的影响,本文以《庞居士误放来生债》为研究对象,从商人形象的转变、人物原型的典型性以及商人佛教思想等方面入手,以求在经济对元代戏曲的影响的研究方面进行不同角度的补充。
【关键词】《来生债》;经济与元代戏曲;商人形象;佛教经济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6-002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6.007
元代的市民经济对市民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戏曲十分繁盛,值得注意的是,在元代以前戏曲中的商人多为负面形象,且多充当配角,而元代戏曲中的商人形象逐渐多样化,甚至有些直接以商人或商业作为作品的核心,例如《东堂老》《老生儿》等等。商人形象的丰富与经济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目前对于《东堂老》《老生儿》以及《看钱奴》等作品中的商人形象研究的较为翔实,但对于《庞居士误放来生债》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完善空间,现有的研究文献有谭伟的《论元杂剧〈庞居士误放来生债〉题材来源及其研究价值》,以及硕士论文《元杂剧当中的富人形象》中的一小段有所提及。一直以来这部作品的研究价值都被低估,但其中的商人形象与元戏曲的其他商人形象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地方,从经济角度对其探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元戏曲商人形象的研究,并从一部作品出发,以便观元代经济对元戏曲的商人形象塑造的整体影响。
一、商人形象的转变
(一)元戏曲中的商人形象
元代戏曲中的商人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在元代之前,商人多是以反面形象出现在观众眼前,例如《琵琶行》里对于商人的描述“商人重利轻别离”,寥寥数字就将商人的形象勾勒出来,元代以后,商人形象出现的较为频繁,甚至商人不再是如《琵琶行》里一样的陪衬,反而一跃成为整部作品的中心。在元代戏曲中,商人形象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虽然仍然以反面形象为主,但也出现了不少正面形象,隐隐有向正面形象过渡的趋势,下面从正反两种形象做进一步介绍。
1.反面形象
元代戏曲里的反面形象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的贾仁、《布袋和尚忍字记》里的刘均佐、《绯衣梦》里的王员外、《玉梳记》里的柳茂英、《云窗梦》里的李多以及《秋胡戏妻》里的李大户等等。他们有的为富不仁,有的吝啬成性,还有的贪得无厌。
《看钱奴》里的贾仁只是偶然借了二十年的富贵日子便开始为富不仁,欺压穷苦人民。在与周秀才进行儿子买卖时,欺负他是个穷人,颠倒黑白,周遭人提醒其应付给周秀才卖儿子的钱财时,贾仁则骂道:“你好没分晓!他因为无饭的养活儿子,才卖与我。如今要在我家吃饭,我不问他要恩养钱,他倒问我要恩养钱?”[1]颠倒是非可见一斑,后续周秀才不愿离开,贾仁这才施舍给他两贯钞,期间在周秀才想要反悔时,贾仁则拿出签订的契约,上面写着反悔之人需赔付一千钞,逼得周秀才只能作罢,商人的奸诈体现无遗。《忍字记》刘均佐出场时,介绍自己“虽然有几文钱,我平日之间一文也不使,半文也不用,若使一贯钱呵,便是挑我身上肉一般。”[2]可见其吝啬程度。
2.正面形象
正面的商人形象直到元杂剧中才第一次出现,如《东堂老劝破家子弟》中的李实。李实由于与赵国器交好,受其临终所托帮他照看自己的儿子扬州奴以及存寄的金银。后扬州奴败光家产,李实不仅使其浪子回头,同时信守承诺,将赵国器存寄的五百两银子归还,“我如今一一交割,如有欠缺,老夫尽行赔还。”[3]成功塑造出一个见财不昧、重情重义、信守承诺的商人形象。
《庞居士误放来生债》中的庞居士也是一个拥有正面形象的商人。他虽放债款,可目的并非是收取高额利息,而是缓解他人燃眉之急,在得知李孝先难还上欠债时,他并未刁难,“我揾了这文书,点个灯来烧了者。本利该四锭银子,都不问你要。”不仅如此,“行钱,再将两锭银子来。孝先,这银子我则这般与你做盘缠。”[4]乐善好施的商人形象跃然纸上。
(二)经济因素对其形象转变的影响
1.经济的繁荣促进商人地位的提高
在元代,商人的地位与其经济的繁荣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元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政权,巩固统治,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促进商贸发展。而商业的繁荣也会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商人态度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上层统治者身上,蒙古贵族大多不善经商,因此他们对于商人十分的信任,甚至提拔一些商人在朝中担任一定的职位,如阿合马、桑哥等人由商人变成了宰相,所谓上行下效,士大夫阶层对商人的态度也有所缓和,同时,元代的商人自身也具备一些品格,例如元末明初的沈万三,经商十分诚信,切决策果断,这也令当时的世人对商人多了一份新的认识。
元代的戏曲在涉及商人时,一是由于其社会地位的提高,难将其作为社会的底层来描写,因此在戏曲中的商人形象逐渐出现了一些转变,例如《东堂老》当中的李实,遵守承诺,见金不昧,再如《来生债》中的庞居士,乐善好施。二是由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更加正面的商人形象,例如沈万三,敏锐的戏曲家们将这些新出现的商人形象吸收到自己的作品当中。
2.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矛盾的出现
随着元代经济的发展,社会上也出现了较多矛盾,由于當时多采用纸币进行交易,难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关于通货膨胀的现象在元代戏曲中同样有所反映,如《酷寒亭》第三折剧中人物对白中的“有新事,一贯钞买一个大烧饼,别的我不知道”[5]这句,就是对当时交钞贬值的社会危机的抨击笔墨。
当然,更严重的是当时的官商勾结,贫富差距过大,商人为富不仁,欺压人民,导致民不聊生。元代的斡脱商人替皇室贵族购取珍异珠宝,以此营利。因此富商与官府勾结的情况时常出现,元代戏曲家们也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反映,如《绯衣梦》里的王员外,与官府勾结欺压平民,使无辜之人锒铛入狱。
元代戏曲家们多对商人进行负面形象的刻画,极尽夸张,力求讽刺当时商人的为富不仁。更有戏曲家开拓思路,用正面形象对现实进行讽刺,例如极尽夸张地写庞居士对钱财的厌恶,将家中所有的欠条烧毁不说,更是将家中的财富汇集在一处,而后将其沉入海中销毁掉,讽刺了当时对钱财过分追求的不良社会风气。
二、人物原型的典型性
(一)庞居士人物原型介绍
庞居士,名蕴,字道玄四。《景德传灯录》卷八本传云庞居士“世以儒为业”,《五灯会元》卷三本传云“世本儒业”,《释氏通鉴》卷九云 “世习儒业”,可知庞居士出身书香门第,有相当高的儒学修养。居士虽出生于书香世家,但从小有佛缘,能够参悟一定的佛法。当时,佛教十分流行,居士便在宅西建让全家修行,后又舍旧宅为寺。居士了悟禅学以后,用船将家中数万珍宝全部沉人湘江(一说洞庭湖)。元和(806——820)中,居士举家北游襄阳,随处而居。最初住在东岩,后来移居襄阳西门外的小舍。以制、卖竹漉篱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计。对庞居士沉宝之事的记载,比较早的是《语录序》,但其记较简, 之后宋本觉《释氏通鉴》卷九亦载有此事,因此沉宝之说也不能说全无依据。
(二)经济对人物原型选取的影响
1.不创新角可提高观众对新剧的接受度
戏曲的繁荣与当时演出的社会化和商业化是分不开关系的,戏曲本是民间艺术,后被统治者所欣赏,于是进入宫廷,由于上层统治者的喜爱和推崇,从而使得戏曲在民间更加盛行,戏曲演出的社会化和商业化必然带来一定的竞争,《蓝采和》杂剧中的“甚杂剧请恩官望着心爱的选,这的是才人书会划新编”[6]一句,可看出当时新编、新改的戏曲在市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因此为了满足当时市场需求,自然少不得需要戏曲家在创作时进行一定的调整。元代也出现了专门从事戏曲写作的作家群体,被称之为“书会”。书会中的戏曲家还会相互竞争,以比赛促创作,以刊刻演出促进经济与文化的繁荣。
在此背景之下,戏曲家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市民的需求,会更倾向于改编从前的作品,或者选取已有的人物形象进行创作,以便提升市民对新戏曲的接受度。《来生债》的作者刘君锡受戏曲商业化的影响,因而在创作作品时,选取了庞居士为原型来加以改编。这也符合李渔在《闲情偶记》演习部中的观点,好的戏曲作品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创新,这样“耳中免生芒刺”,眼角也不会“如悬挂赘疣”。
2.庞居士形象具有一定市民的基础
《来生债》选取庞居士为原型是因为首先他在古代就有着十分的名气,他遁入空门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以他作为原型能够有利于扩大戏曲的受众群体。庞居士曾一度收到文人的追捧,有赞扬其高尚隐逸的,如宋沈遼就有一首诗歌《庞公》专咏庞居士。庞居士放来生债的传说,在元初戏曲中就已出现,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第一折《油葫芦》:“我则待安乐窝中且避乖,争奈我便时未来!……那个似那庞居士可便肯放做来生债?”[7]杨文奎《翠红乡儿女两团圆》第二折《乌夜啼》:“我待学刘员外仗义散家财,我待学庞居士放做了来生债。”[8]无名氏《替杀妻》第二折《倘秀才》:“且休说放钱的庞居士,更压着养剑客的孟尝君,那裹有俺哥哥意分。”[9]庞居士在市民中的流传情况虽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但是从其在诗人笔下以及《来生债》从前的戏曲中出现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庞居士在民间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其次,市民多信仰佛教,而龐蕴是中国佛教的著名居士,作者以他为原型又将巨商的属性放在他的身上,既能够迎合市民对佛教的信仰,吸引市民的关注,又能够达到自己借佛家万物皆空的观点来讽刺社会对名利追逐的目的。
三、元代商人形象与佛教思想的融合
(一)元代佛教经济的兴起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佛教经济在官方的推动下蓬勃发展,上行下效,不论官员还是商人,对于佛教就更加推崇,其中的佛教思想多反映在元代戏曲当中,人物形象也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凸显了更多的佛教思想。
根据《陔馀丛考》卷十八记载,皇庆初给予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外,还有邸店四百间。可见佛教应受统治者推崇,导致寺院数量、人数以及土地面积的增加,由于寺院不用缴纳税款,且多有商人将自己的产业交个寺院从而躲避纳税,因此佛教经济开始蓬勃兴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佛教经济的兴盛,佛教思想开始大量渗透到民间,市民开始不自觉得吸收佛家因果报应等思想,而佛教思想也开始渗透到戏本中,戏曲家们则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进一步表现佛教思想。
(二)元代商人形象中的佛教思想
1.财空观念的突出
按照佛家思想,五蕴皆空,那么钱财也应是一场空。在《来生债》中这中财空的观念往往和恶财相结合。例如“自从灭了无明火,炼得身轻似鹤形……佛说贪财好贿之人似甚么?似小儿在那刀尖上食蜜,贪其甜味,岂防有截舌之患也呵!”[4]以及【混江龙】中这句“我为甚一生潇散不恋那一生钱,大刚来这十年富贵也只是十年运。运去呵,有如那风摇画烛,天散也的这浮云。”[10]其中就提及了若想成佛,需断贪嗔痴,那么首当其冲就应该不贪恋荣华富贵,其次也提到了庞居士认为自己的富贵本是天赐予,到头来终将会消失,这也能体现出财空的观念。
2.因果报应思想的显露
佛家因果报应论,可称为道德因果论。《来生债》当中有许多关于因果报应的思想,如其中“我恰才前后烧香。则听的那牛马做声,那牛便道:我少居士二十两银子,无的还他,做牛来填还他……婆婆,我当初本做善事,谁承望弄巧成拙,都做了来生债也。”[11]以及【满庭芳】中“(做念佛科,唱)我看了他这轮回的路,可则是阴司地府,(云)当初借了我银子,无的还我,今日做驴马众生,来填还我。(做念佛科,唱)哦!方信道还报果无虚”[12]这两段借助牛、马的口吻,直接体现出庞居士有关佛家当中前生债,今生还,今生债,来生还的因果报应思想。
总的来说,元代的经济对于戏曲中商人形象的塑造有着一定的影响,以《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最为典型,元代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商人形象从反面向正面过渡,而且由于元代佛教经济的兴盛而导致了人物形象当中有着大量的佛教思想,从经济角度对其探究能进一步丰富元戏曲商人形象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97.
[2]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59.
[3]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227.
[4]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295.
[5]霍松林,申士尧.中国古代戏曲名著鉴赏辞典[M]. 北京:中国廣播电视出版社,1992:165.
[6]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41.
[7]隋树森.元曲选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18.
[8]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465.
[9]徐沁君校点.新刊元杂剧三十种[Z].北京:中华书局,1980:761.
[10]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296.
[11]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305.
[12]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9:304.
[13]杨军琴.元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01):119-121.
[14]陈贤春.试论元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3):69-73.
[15]关静.元代寺院经济研究[D].河南大学,2010.
[16]曹旅宁.元代的寺产官营问题[J].佛学研究,1996,(00):226-230.
[17]谭伟.论元杂剧《庞居士误放来生债》题材来源及其价值[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3):43-47.
[18]陈小珏.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2.
[19]靳琦华.元杂剧中富人形象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20.
[20]庞居上语录[A]//禅宗集成(14册)[Z].台北:艺文印书社,1968.
[21]张兵.戏曲与社会经济生活[J].学术月刊,2006,(09):100-102.
[22]李桂奎.经济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建构[J].学术月刊,2006,(09):102-105.
[23]赵智旻.《歧路灯》新探[D].南京师范大学,2004.
[24]牛佳玮.李渔戏曲市场观念研究[D].四川音乐学院,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