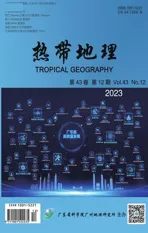跨界治理网络视角下深港跨界区域协同发展研究
2023-12-23沈凤钱申霄媛郭春兰
李 云,沈凤钱,申霄媛,郭春兰
(1.深圳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2.亚热带建筑与城市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640;3.香港中文大学 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香港 999077)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推进,生产模式重组、生产流程重组和全球金融的去监管等变化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这些变化超越了单一行政尺度,延伸至全球范围的区域空间层次,导致全球城市与空间结构的调整。与此同时,与全球化相对应的区域化与经济活动生产本地化的反趋势也不断增强,区域被整合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魏成 等,2011)。在此过程中,跨界区域快速形成,并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急剧增加。跨界区域的形成是多个跨界互动的累积结果,也被视作促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手段(王博祎 等,2016)。近年来,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趋势抬头,大国博弈加剧下的不稳定因素不断冲击着区域和谐发展(范祚军,2023)。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等战略,积极应对国际形势巨变,全面推进区域战略合作,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深港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体系的关键节点和重要跨界发展地区,在“一国两制”的政策框架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下,具备特殊的区域功能优势。从20 世纪80—90 年代的互补探索,到21 世纪00 年代以后的深化合作互动,深港的跨界合作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与规划适应中。随着国际局势变化,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前海合作区的改革、香港北部都会区蓝图的提出,使深港已然出现新的协同发展趋势,有必要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对深港跨界发展进行解析判断。基于此,本文拟从跨界治理网络视角,分析总结深港跨界协同发展的阶段性特点,透视其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以期对新时代边界地区跨界协同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
1.1 跨界区域及其治理的形成与发展
边界是一种划分不同政治实体及其管辖地域的政治地理界线(汤建中 等,2002),跨界区域是由相邻国家或地区的边界空间构成的特殊区域。快速的全球化使经济活动的区位导向呈现外向发展态势,为跨界活动开辟了广阔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需要通过不断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ty)与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ty)进行空间固着与修复(Spatial Fix)。跨界区域可视为一种地域组织,资本依托其进行流通和循环,并完成资本积累(殷洁 等,2013)。可见以往绝大多数针对区域发展的研究都是基于经济一体化的功能性思维。随着功能主义向新功能主义、旧区域主义向新区域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逐渐从经济转移至国家或地方权力上(张虹鸥 等,2018)。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跨界合作政策塑造和机制建设成为区域一体化研究的核心议题(Blatter, 1997;James, 2010)。由非制度化走向制度化成为跨界区域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跨界规划与协同治理随之兴起,中国地方治理形态也逐渐由行政区行政向着跨界区域治理转变(张紧跟,2009;王世福 等,2023)。新世纪以来,中国区域治理实践经历了从直接调整行政区划的刚性模式,到利用尺度工具促进城市群、都市圈等区域合作与规划的柔性治理模式的转型(胡剑双 等, 2020),在此过程中柔性手段逐渐被认为是处理区域治理问题的最优解(刘亚平,2007;骆勇 等,2009;高建华,2010)。
然而在逆全球化趋势日渐严峻的当下,跨界合作与治理逐渐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以欧盟为代表的超国家尺度跨界合作区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面临紧缩危机与区域观调整(贺之杲,2023)、美国霸权主义下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政策为以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区域化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蒋芳菲,2022)。另一方面,中国次国家尺度跨界区域也面临着国家空间战略性选择下的新的区域治理转型探索与深化发展(胡剑双 等,2020)。区域合作成为各地参与全球化、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后疫情时代区域化发展转向与调整,将成为抵御全球化风险的战略选择(许佳 等,2020;张云,2020)。
1.2 理论溯源:政策网络
随着跨组织、跨区域的多重治理理念产生,“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开始成为一种政策分析工具,被广泛地应用于公共政策与管理中(谭羚雁 等,2012;赵德余 等,2021)。它可以被理解为“利益相关者们通过资源依赖关系相互连接而成的集群和综合体”,是一个代表“政治与决策中行为者之间的结构关系、相互依赖和动态”的网络(Rhodes, 1990),常被用于政策制定中,以约束网络中合作成员自利性,引导各方向着共同利益发展。学术界呈现3种不同层次的研究典范,即美国学者强调微观层次下不同机构之间的人际关系互动(Marsh et al., 1998);以Rhodes(1990)为代表的英国学者聚焦于中观层次下部门结构对政策后果的影响,把政府间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德国与荷兰的学者着眼于宏观层面,政策网络被视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方式(石凯 等,2006)。政策网络包含政府、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公民个人等多种参与主体,英国学者Rhodes(1990)将政策网络分为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专业网络(Professional Network)、府际网络(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生产者网络(Producer Network)、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5 种类型。在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对该理论进行持续补充,如Sabatier 等(1993) 的 倡 导 联 盟 框 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ACF)主张将共同的认知和规范性信念作为网络的组成基础,并将政策子系统作为基本分析单元;Blom-Hansen(1997)运用“新制度主义”,主张把政策网络理解为限制和处理多种政策参与者行动的制度,同时,政府也被视作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主导力量(孙柏瑛 等,2008)。构建有效的跨界政策网络被视作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治理转型的重要路径(锁利铭,2014),也是区域治理成功的关键(孙柏瑛 等,2008)。
1.3 范式构建:跨界治理网络
基于“一国两制”这一特色制度,深港跨界协同发展是在次国家层面建立合作关系,因此,本文将聚焦中观层面的网络构建。结合对传统政策网络的反思,提出跨界治理网络理论分析框架(图1),将多层次治理和倡导联盟框架的一些理念和元素纳入新框架,以理解政府主导的跨界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并剖析跨界治理的运作机制和循环过程,从中透视跨界区域治理的特点与转向。

图1 跨界治理网络框架示意Fig.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ross-boundary Governing Network
跨界治理网络是在政策网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政府能力分散为基础的理性决策系统。主要由2 类中观网络组成:政府共商组群与辖域网络。各级政府共商组群由不同层次政府行为体组成,而辖域网络则表示行政单元内政府行为体与其社会行为体组成的集体网络,二者共同表征跨界治理网络中政府能力的实现与调整过程。从本质上讲,跨界治理网络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治理结构,其中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在纵向和横向上分解,并通过相互合作交流形成网络。本文将从3个方面理解和研究该框架:
1)跨界经济发展与跨界治理网络的产生逻辑
在经济地域化过程中,新的经济活动不断引入导致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了维持跨界区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经济社会关系的联系,必须构建相应的权力关系来控制和协调生产网络(张京祥 等,2011)。因此,需从经济地域化与权力尺度重构角度理解跨界治理与跨界治理网络的产生。本文认为,跨界治理网络的功能运作和共识形成并非独立而是嵌入在跨界经济环境中的,随着跨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政府的权力重构必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经济与权力相互耦合,共同推动多尺度治理重组(张衔春 等,2022),并最终以跨界治理网络的形式呈现其衍生的新治理关系(图2)。

图2 政府能力与经济地域化之间的关系Fig.2 The relation between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territorialization
2)多级政府共商组群建设与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方式
政府系统内的重构过程可能会促进或阻碍经济地域化进程和执行力的调整,因此,为了处理跨界区域相关问题,需要建立一个由政府行为体组成的多层次和匹配不同层级的政府共商组群。采用多层次治理方法中的“通用”和“特定任务”的分类,来描述不同系统的政府共商组群,前一种通常基于某种平等的行政地位或跨界问题的外交关系而进行横向互动,而特定任务类型则倾向于处理特定问题或专门的管辖权,基于垂直联系和上下控制。在跨界治理网络中,多级政府协商组群是其运作基础与功能核心;是政府间的资源调动或追逐的机构平台;是影响政府能力实现的重要内部因素,可视作“几个辖域解决特定问题和建立沟通网络以产生有用的结果”的一种运作机制。在其运作下,政府间可以就共同的跨界问题开展官方互动、谈判、政策制定和制度塑造,从而完成区域合作。在中国,国家权力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形成严密的垂直管理体系(张衔春 等,2021),并具备“弹性收放”的动态调整机制(朱力,2022),可以沿着政府间进行重构分散,政府共商组群的运作能力即来自于这种分散。将国家权力进一步结构化,可分为地方代理人执行中央委托人意志的“执行权”和地方代理人能在其领域范围内单方面批准和执行相关活动的“决策权”(Piattoni, 2010)。一方面,由于严密的垂直管理体系的存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持续的不对称关系(Rhodes, 2007),因此,决策权大小决定各政府行为体在跨界治理网络中所处层次,在不同层次政府的纵向依赖与相同层次政府的横向联系下,政府共商组群的多级系统性结构得以形成。另一方面,执行权在很大程度上受不同政府决策权大小及其自身官员效率和运作能力的影响,从而影响整个跨界治理网络的运行效果。
在政府共商组群中,各政府行为体的主要职责是以获取各自利益、实现发展目标为主要目的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决策和政策制定。一般来说,提升在多级政府共商组群中所处级别,从而扩大在网络体系中的话语权,是各政府行为体获取更多权益和资源的重要方法。不同的跨界问题的解决和议题的谈判转向与之匹配的政府共商组群。
跨界治理网络有2个主要的运作过程,即建立伙伴关系和形成共识的过程。从经济地域化的跨界问题的运作目的看,政府行为体采用2种影响战略,即资源依赖战略和话语战略。在政府共商组群和辖域网络之间的桥梁作用下,不同的政府行为体将作为跨界政策形成过程的参与者和各自辖域网络内的“代理人”。由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政府-社会的关系,政府行为体将有选择地在不同的操作过程和影响战略中投入努力。
3)辖域网络内的政府-社会关系对跨界治理网络发展的影响
跨界治理网络中的辖域网络与Rhodes模型中的议题网络类似,是一个覆盖行政管辖范围内所有行为者的中观网络。辖域以行政单元作为基础地理空间单元,具备相对独立性和地方治理完整性,是政府行为体与其对应社会的空间单元载体。辖域网络的形成同样以权力分散作为基础,辖域行政单元内部的政府成员是其各行政管辖范围的主要代理人,不同的辖域网络通过辖域政府权力结构或利益关系相互联系,构成跨界治理网络中一种多层次的尺度逻辑。跨界地区内的活动必须与不同的辖域网络相联系,以获得共同利益或共识。
与政府共商组群的封闭特征和成员要求相比,辖域网络具有相对开放和松散的结构。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共识形成过程,取决于政府能力的实现过程,而政府能力是由政府-社会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模式是影响各政府在社会资源动员等方面能力实现的重要外部因素,通常由政府行为体在辖域内扮演的角色、社会结构特点和社会制度框架所决定。在边界两侧,由于政府-社会关系模式可能有所不同,各地区在政府能力实现上会存在不对称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对跨界双方发展共识的形成过程和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辖域网络提出的话语战略会在各自的辖域网络中孕育出一个获胜联盟,并在政府共商组群中进一步形成执行联盟。有时,一些次国家层面的话语略也可以被提升到更高层次的政府共商组群中。除此之外,由于地方政府可视为辖域内社会与上层政府的中间人和连接点,国家与社会的摩擦将随着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摩擦的扩大而扩大,因此各辖域内的政府-社会关系将影响整个跨界治理网络的稳定发展。
总之,跨界治理网络的概念框架旨在建立一个全面和平衡的方法,以解释政府主导的跨界地区制度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在次国家层面。该框架对政府能力进行阐述,并强调政府行为体的桥梁作用。虽说跨界治理网络弥补了一些传统政策网络的不足,但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在一些概念和逻辑关系的定义上存在模糊之处。由于跨界治理网络受到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显著影响,需进行比较和分析其他跨界实证,以提高对该网络框架的理解。
2 案例演绎:深港跨界治理网络发展构建
在“一国两制”背景下,香港特区与内地的社会政治状况不同,不对称的城市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跨界合作的发展。深港边界既不同于国家间边界,又有别于城市间边界,其所涉及的治理网络结构更为复杂,面临的跨界问题更具挑战。近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来深港跨界协同发展持续推进,2018 年深圳GDP 超越香港后,新的跨界一体化发展趋势已然出现(陈宏胜 等,2022)。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突变,2019 年香港“修例风波”、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深港口岸客运暂停等“黑天鹅事件”不断冲击着深港的稳定发展,在诸如此类偶发“震荡”的影响下,深港跨界治理网络也随之发生全局性变化。
根据跨界治理网络的产生、发展与运作逻辑,本文认为跨界治理网络是一种韧性的治理机制,能根据经济环境与社会情势的变化,通过权力收放下的制度建设与网络结构层次调整及时响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从而有效应对跨界发展过程中不稳定因素带来的挑战。站在香港“由乱转治”、疫情后深港往来全面恢复、深港北部都会区与前海合作区契合演化(周子航 等,2022)的历史转变时期,有必要对深港跨界发展历程及关键事件进行分析,以证明跨界治理网络对维持和促进跨界协同发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基于此,本文将从经济地域化和权力尺度重构对跨界治理网络产生的影响、多级政府共商组群的运作方式、政府-社会关系对跨界治理网络的影响3个关键议题出发,以深港跨界治理网络为例进行分析演绎。
2.1 深港经济地域化与跨界治理网络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经历了从“高度中心化”到“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并存的变革。在权力上,表现为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与回收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国家空间的选择性(张衔春等,2021)。有学者认为,这种国家体制变革和空间干预不仅是对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竞争的被动反应,也是国家在不同空间范围内促进和引导地缘经济重组的一种战略(Brenner et al., 1999)。这种战略一般指对特定地区赋予特殊权力、进行改革试验的“优先经济地域化”。
1978年中国开启了以发展制造业为主的第一轮经济开放,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城市尺度的优先经济地域化方案设立。依靠特区优势,深圳成功吸引香港产业转移,形成深港“前店后厂”的跨界合作发展模式。二者构建起紧密合作关系,在1986—1996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中,港资占比累计达到60%以上(图3)。在香港政府“积极不干预(Positive Non-intervention)”政策下,当时的深港跨界发展呈现市场经济自发驱动下的自下而上特征。Naughton(1997)将此种有别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深度一体化的模式称为“非正式”一体化,主要在跨界经济上表现出强烈的一体化特征,而政府间的合作与制度安排并未出现(Shen, 2003; Yang, 2005)。在该时期,深港在“前店后厂”模式中实现各自地域经济结构的调整。

图3 1986—2020年香港对内地实际投资中深圳占比与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中港资占比Fig.3 Shenzhen's share of foreign capital actually used in the Mainland from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 Macao's share of foreign capital actually used in Shenzhen from 1986 to 2020
香港回归后,随着广东省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之间交流的增加,1998年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制度触发省级政府共商组群出现,标志着深港跨界治理网络进入初级建设阶段。但其时,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等连续打击,使香港政府疲于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危机,另一方面“堡垒香港”(Fortress Hong Kong)政策使香港对跨界合作态度保守,同时受限于省级政府共商组群决策能力,深港跨界一体化发展进程缓慢(Luo et al., 2012)。
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区域逐渐成为国家空间的重要选择(张衔春 等,2021),中央政府的介入打破了深港跨界合作僵局。在中国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二轮经济开放启动后,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作为一种特殊的优先地域化政策出台,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的新一轮经济一体化发展在香港服务功能向内迁移拓展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广东省作为CEPA 试点区,其政府能力得以增强,同时,香港合作态度随着本土经济的复苏而转变,逐渐主动融入跨界发展,由此省级政府共商组群开始在跨界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城市层面,2004年深港合作会议作为城市间合作的正式制度框架建立,跨界治理网络由此形成中央—省—市多级完整结构。此后数十年间,与深港有关的其他多种合作机制持续推进建设,香港对深圳投资起伏变化,但总体上呈增长趋势(见图3),深港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日渐紧密(图4)。

图4 1986—2020年深港进出口贸易依存度变化Fig.4 The interdependencies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during 1986-2020
近年来在国际形势巨变下,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应运而生。随着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成立、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纲要》出台,政府共商组群因中央政府参与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升级,深港跨界治理网络走向湾区尺度。在此背景下,深港跨界治理网络内部的政府联系更加紧密,各辖域网络之间的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水平提高,显著地减少了政策制度差异下的无序竞争与资源消耗,如在合作领域层面,深港双方内嵌式合作议题向着多元化不断推进;在产业创新层面,深港产业创新合作出现以北部都会区建设为代表的深度对接举措与倾向;在人才引进层面,《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的实施细则》《关于进一步便利港澳居民在深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相继出台;在金融合作层面,“跨境理财通”的启动、深圳市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在港成功发行等事件,反映深港双城在金融领域的深化发展。深港跨界合作与双城融合进入新阶段。
从深港跨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地域化是跨界治理网络的建设前提,为了促进经济地域化,中央权力需要向地方进行重构分化,从而为合作制度建立与多级政府共商组群的有效运作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跨界治理网络是一个有效的、由政府主导的、对不断发展的跨界经济地域化与一体化的制度性回应,通过合作论坛、合作备忘录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推动着区域制度一体化的出现(罗小龙 等,2010),促使深港走向深度融合(表1)。因此,在变动的经济环境中,调节和完善跨界治理网络,是引导调控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港方最初保守的合作态度使双方难以通过制度建设回应市场需求,表明市场驱动下的紧密经济联系并不是深港制度一体化发展的充分条件(罗小龙 等,2010),而中央的介入推动了合作制度的强制性变迁(谢宝剑,2013),促使港方态度转变,跨界治理网络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开始从制度层面直接促进深港跨界经济融合。由此可见,在“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在深港跨界合作中扮演着主导作用(沈建法,2002),它们的行为与态度对跨界治理网络的构建至关重要。

表1 深港跨界治理网络发展历程Table 1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Hong Kong cross-boundary governing network
2.2 多级政府共商组群的建设与运作
不同时期的经济表现和地域化都伴随着不同级别政府共商组群制度安排的出现。如前文提到,20世纪90 年代末以来,随着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与CEPA 的签订,广东省政府的权力显著增加。在资源依赖战略下,由粤港两地行政首长共同主持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制度成为香港与内地交流合作的核心平台,奠定了跨界治理网络中以广东省和香港特区政府为中心的省级政府共商组群的主导地位。
尽管省级政府共商组群的形成推进一些省级跨界问题的发展,但在此平台上深港城市级相关问题的讨论与处理缺乏优先权,在省级平台上对市级问题进行谈判是不合理的,因此进展缓慢。与此同时,为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发展,政府扩大了特区政策的范围,深圳经济特区优势不再显著,同香港寻求进一步的战略项目合作成为深圳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此背景下,深港亟待建立城市间沟通平台与制度。由此,“1+8”框架协议签订后,深港合作会议制度被建立。而后在市级政府共商组群的高效运作下,深港双方在教育、医疗、创新建设等方面合作进展显著,以往在省级平台曾提出却未能充分讨论的落马洲河套地区问题也得以推进。以资源依赖战略为起点,“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开发”等试点项目作为城市级发展话语策略被使用,相应的联合专责小组成立。然而,深港合作会议制度的有效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深圳市政府能力的制约,使港方主导的河套项目由于行政管理矛盾、利益分配争议等问题难以持续推进,从而在后续问题层级与平台能力不匹配的情况下陷入长期停滞。
相比河套合作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地方通过话语策略争取优先经济地域化发展权的典范(图5)。在吸取落马洲河套地区的教训后,深圳政府将原本与香港政府直接对接的战略统一过程转向与广东省和中央政府构建战略联盟,使前海项目首先在省级平台提出,从而让经济发展需求与政府共商组群行政能力良好适配。2009年在省级政府共商组群推动下,2010 年国家权力“代理人”介入,使前海从普通的省级跨界问题上移至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在国务院的统筹安排与领导下,前海合作区的建设开始在国家—区域—地方—前海管理局多层级展开,并迅速建立发展制度环境。一方面,部分广东省和深圳市的权力尺度下移到具有计划单列市管理权限的前海管理局层面,使各优惠政策更易于实施,另一方面前海合作区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深港合作会议和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成为前海合作区主要的沟通合作机制,共同承担起深港合作重大决策制定的职能(王博祎 等,2016)。而后在《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广东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2016)《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 等,2019)等文件中,前海和南沙、横琴作为三大重点合作区被不断强调。2021年,为进一步建设前海金融开发示范与试验区,中央政府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中共中央 等,2021),将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 km2扩展至120.56 km2,以扩大深港合作深度。到2022 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 948.7 亿元,其实际利用港资达到56.1亿美元,占实际利用总外资的95.7%,合作成效斐然。
可以看出,一方面,在跨界治理网络中,次国家层面的不同子系统问题必须要一个与之匹配的政府共商组群给予功能支持,该组群需要相关政府提供各自的权力配置和进行有效的参与。另一方面,在具备韧性的跨界治理网络中,政府共商组群需要进行动态的塑造与再塑造,以更好地适应项目的发展,这主要通过权力尺度重构与问题的移交来实现。
2.3 辖域网络内的政府-社会关系的变化与影响
一般来说,共同利益是维持区域合作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除此之外,区域合作也受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共生关系的影响(欧定余 等,2019),政府-社会关系是共生关系突出表现。有研究曾指出,深港之间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不同是深港合作的最大障碍(沈建法,2013),导致深港融合呈现紧密的经济一体化、有限的制度一体化和落后的社会一体化特征(Shen, 2014)。
在内地,政府治理方式较为积极主动,政府-社会关系呈现强烈的国家主义特征,强调以发展为中心,以政府为主导。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产业和城市规划方面都被赋予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高度自主决策和发展控制权,能通过发展战略规划有力地引导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在这种政府-社会关系结构下,内地政府往往能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源和干预地方经济运行。
而受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影响,在处理地方治理与社会关系方面,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将经济主要留给市场调控,其政府定位长期保持为“服务型”。在“自由经济”的原则下,香港特区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管理调控的部分政府能力实际上是由地方社会组织、机构和市场力量完成的。因此,香港政府能力受到复杂的经济-政治关系和辖域网络内社会表现的强力制约(表2)。在《施政报告》(中国政府网,2005)中,香港明确提出“大市场、小政府”的管制原则,在该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香港的政策制定与发展安排需要进行公众参与和咨询,并受到相关机构的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香港特区政府能力的实现效率,导致香港在处理跨界问题时对内地提出的积极建议反应滞后、处理缓慢。例如,在城市空间规划层面,深港都各自提出过跨界区域空间发展的设想,但一直存在深方一头热和港方落实难的问题(王雨等,2022)。又如在落马洲河套合作区的开发过程中,香港社会各方早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就提出希望将该地区开发成为工业区以提升地区制造业竞争力,而香港政府则倾向于将其定位为服务中心,以促进产业转型,但香港立法会认为规划署的远景构想不切实际,部分学者和市民又担心服务业会因此向深方转移。在此背景下,即使深港双方都对边境地区有开发意向,但由于香港一直未能达成辖域网络内部发展共识,一直到2007年以后,河套地区的合作才有了缓慢进展。相比之下,同为深港合作开发区,前海合作区作为位于深圳特区内部的特区,在深方主导下弱化了香港辖域网络社会制度的限制,从而大大提高了项目的推进效率。
近年来,香港逐渐意识到被动的“服务型”政府不再适用于时代发展,反而带来更多社会矛盾。2013年,梁振英上任后提出了政府“适度有为”的集权化转向。在此转变下,香港政府开始尝试利用更多手段干预城市空间发展,北部经济带与新界北作为战略空间被提出。2017年后,林郑月娥政府强调香港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职责。2019年“修例风波”进一步暴露香港政府社会治理的不足与管治功能的失效,随着《国安法》的颁布,在渡过“反中乱港”危机后,香港政府开始着重提高有为政府的能动性。在政府主导的空间策略层面,2021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新界北的基础上提出《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并将首次以强制手段回收土地,以避免民粹运动对新区开发造成的抗辩(周子航 等,2022)。在区域空间结构规划上,北部都会区规划鲜明地指出了深港间空间联系,提出了“双城三圈”的空间结构,突破了深港行政界线。2022年,李家超上任后强调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并将成立相关委员会以推动北部都会区治理体系建设,同时明确提出要超越地理界限限制,与大湾区产生协同效应。可以看出,香港抛弃地方保护主义、主动融入深港跨界协同与国家发展大局的态度越发坚定和明确。此外,2017年深港签署《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重启河套地区的合作,在北部都会区规划下,为了让发展需求与空间相互匹配,落马洲河套合作区通过扩容成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图6)。在此基础上,该区域有望借湾区战略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完成尺度上移,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图6 落马洲河套项目发展历程Fig.6 A brief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LMC Loop
综上,与政府-社会关系模式的不同将导致各辖域内政府能力实现过程不同,从而影响跨界问题的表现与决策。在“一国两制”下,深港之间制度的不同决定其各自政府-社会关系的不同,从而导致二者在跨界问题处理上存在潜在分歧。对于高度自治的香港来说,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矛盾,达成辖域网络内部共识,对整个跨界体系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而近年来,随着香港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香港发展战略与空间选择逐步向深圳方向契合,将推动深港跨界治理网络治理效率的提升与两地经济社会进一步协同发展。
2.4 深港跨界治理网络机制总结
如前文提到,深港地区具有“一国两制”的独特城市构造,正因此,深港跨界治理网络的主体差异矛盾是由于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制度差异,这种差异造就深港之间社会结构、政府能力、办事效率等各方面的不同,从而带来政府沟通、要素流通上的一定阻碍。但另一方面,其在应对冲击挑战时能保持稳健的能力也主要来自于“一国两制”的特征:“两制”促进经济地域化的跨界互补与内嵌,进一步增进辖域差异间的制度对话建设,能为深港高质量发展带来叠加的制度优势,提升区域资源配置能力;“一国”以中央为绝对权力中心,从根本上保证跨界制度建设和网络结构的稳定,能根据国际环境与陆港协同发展需要,通过“两制”的迅速反应对跨界联系进行有效管控。相比之下,其他国家之间的跨界网络常受到国家政体之间的协商的影响,而无法快速形成有效管控,因此缺乏应对风险的韧性。
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国家与次国家的参与情况决定跨界治理网络的扩展升级程度,同时,不同的跨界问题需要诉诸于从国家层面到次国家层面匹配的政府共商组群中的政府间互动。在深港跨界治理实践中,以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为核心参与成员,以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作为核心制度,跨界治理网络逐渐扩展到深港地市一级甚至内地其他地区,为不同的跨界问题提供不同的平台选择,使跨界治理网络逐渐成为深港跨界经济一体化中最有效的政治重组和政府间机构互动类型之一,也促使跨界治理在网络框架下“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孙迎春,2014)。
当然,跨界治理网络并非能够保持绝对稳定与协调。由于制度、规则等差异,深港跨界合作的深化依旧面临诸多阻碍,例如:一些大型基础设施和项目建设长期暂缓,如西部通道规划搁置多年、河套地区开发暂停多年后才于近年重启;科技创新合作领域中存在规则不兼容、标准不衔接、资格不互认等隐形壁垒(岑维 等,2023)。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合理运用“一国两制”的优势,根据发展需求适时调整跨界治理网络结构,优化合作模式,提高网络韧性。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传统政策网络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跨界治理网络分析框架,并针对“一国两制”下深港跨界发展的具体案例,从3个关键议题出发对深港跨界治理网络的建设与运作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深港在协同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跨界治理特征,其经济地域化进程与政府的主动干预和治理密切相关。在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积极参与下,深港跨界治理网络的建设是对经济地域化需求的一种深入的制度回应。2)在“一国两制”下,一方面,香港的立场和态度是跨界治理网络形成的关键。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香港的高度自治、深圳市的特区地位以及CEPA先行先试中广东省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升都是中央发展战略转型中权力合理下放的结果。3)政府共商组群的表现和能力大小由相关政府能力配置决定,因此在处理跨界问题时,问题层级与政府协商组群权力等级相互匹配对问题的快速解决、事项的高效推进至关重要。4)由于政府-社会关系范式的不同,香港与内地存在的不对称的城市治理过程,会对跨界治理网络的有效运作产生一定影响。在发展引导下,近年来香港治理思维逐渐转型,并逐步向与深圳的协同共建靠近。
综上,跨界治理网络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动态系统,在多方共同作用下,这种多层次、系统性的治理方式不断推动着深港跨界区域向着韧性协调的方向深化。在当前越渐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式下,为了推动深港跨界区域向着一体化继续发展、在国家新的空间战略下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群,各级政府共商组群必须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合理调整权力结构以适配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推动完善合作平台建设与制度保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与北部都会区发展的契机,打造强有力的合作联盟,以促进跨界治理网络的有效运作,为区域跨界治理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