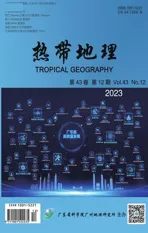休闲环境与态度对休闲行为的影响关系研究
——以广州外地务工人员为例
2023-12-23闫鸿钰毛子丹
赵 莹,闫鸿钰,毛子丹
(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2)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的总数高达3.76 亿,其中乡城流动占比66.3%(国家统计局,2021a)。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外地务工人员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外地务工人员总量为2.86 亿人,其中外地务工人员为1.70 亿(国家统计局,2021b)。大规模的务工人员群体在城市通常从事低端化、长时间的劳动工作,其生活质量与健康耗损广受诟病。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外地务工人员需要获得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才能“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2)。然而,新冠疫情所触发的上海务工人员返乡潮、郑州富士康集体辞职等事件均表明,外地务工人员对生活水平要求已进入到提质升级的新阶段(Wang et al., 2022)。因此,让外地务工人员可以持久快乐且身心健康地参与城市生产生活,直接关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实现。
以住房为基础,以休闲为途径,是新时代外地务工人员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关键问题。住房是外地务工人员安居乐业的基础,已有研究指出外地务工人员住房选择具有租赁房、不稳定、郊区化的特点(黄卓宁,2007;王洋 等,2022),在多渠道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保障下,外地务工人员已部分改变住房条件差的刻板印象,更多发挥主观能动性并追求更优精神生活(刘玉亭 等,2008)。休闲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方式,频繁广泛的休闲参与是实现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宋瑞,2006)。外地务工人员的休闲参与虽然具有部分弱势特征(Naess, 2014;易继红,2015;刘炳献 等,2017;谭磊 等,2019),但休闲态度和理念的积极变化已有所体现(Liu et al., 2020)。推动外地务工人员开展休闲行为需要从环境设施配套的空间政策入手,还是从培育休闲意识的社会政策抓起,仍是人的城镇化的重要难题(林李月 等, 2022) 。
行为地理学与社会心理学从2个学科角度共同关注了自选择效应的理论解释。行为地理学强调环境对行为的影响作用,即建成环境会影响行为开展,如居住环境周边的设施供给会影响居民的行为参与,具体被总结为空间与行为的互动理论(齐兰兰 等,2018)。而社会心理学认为态度和行为相互支持,即人是理性的,个体的态度会有意识地影响行为,具体称为理性行为理论(Fishbein et al.,1977)。两者并非完全割裂并对立,行为地理学的发展中一直保持与心理学的有效沟通,并努力将态度偏好和自由选择的因素纳入日常行为方式的总结(Pred, 1981)。自选择效应指居民可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不同社区的前提下,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行为的影响可能部分归因于居民的态度偏好(Bohte et al.,2009; De Vos et al., 2016; Cheng et al., 2019; Guan et al., 2020),即居民在对居住地进行选择时,会受到自身态度偏好的影响,进而表现出一定的行为特征(Litman et al., 2017)。长期以来,自选择效应被广泛用于探究建成环境与交通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认识环境影响偏差,评估空间政策是否被过高估计(林坚 等,2018)。这类交通行为以工作和通勤的生计性活动占主导,个体居民自由选择范围较小,作为自我选择重要起因的态度因素一直未能得到充分论证(Liu et al., 2020)。
休闲行为不同于交通行为,其充分体现选择自由度和个人意愿性,受个体态度和偏好的影响程度较高,其自选择效应的讨论尚不充分。首先,休闲态度的研究拥有近百年的历史,集中于3 个议题:居民对休闲的内在认知与空间环境和行为方式的关系研究(Gidlow et al., 2019)、居民休闲感知和满意度与休闲参与的关系研究(Naess, 2014)、居民的情感偏好和动机意向研究(Ragheb et al., 1993; Stevens, 2017)。学者们通过大量研究证明了休闲态度存在个体或群体差异 ,且休闲态度会影响居民的休闲参与;同时休闲态度会受空间环境、时代发展、价值转变等因素影响产生改变(Stead et al., 2001;赵莹 等,2020)。其次,休闲环境同样是休闲行为的重要因素,以绿地、公园为代表亲近自然的休闲环境空间成为研究热点。居住地周边的绿地和公园会影响居住选择(Sreetheran et al., 2014; Wu et al.,2022),居民的休闲态度也会影响居住选择,进而影响居民的休闲行为。例如,喜欢公园的人会将居住地选择在公园附近,以享受公园的优越休闲环境(Buckley, 2020);居民居住地选择中对绿地的重视程度,影响绿地感知并由此带来幸福感(Ragheb et al., 1993)。休闲行为研究对态度与环境给予同等重要的关注,但对自选择效应的影响时序、因果关系及复杂机理未有回应。
中国城市具有独特的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自选择效应的实证研究与西方城市表现出差异性。西方相关研究证明了居民对出行的态度偏好会影响居住选择,进而影响居民的出行行为(Cao et al.,2009; Große et al., 2019; Zang et al., 2019)。研究内容包括态度对建成环境和出行行为关系的影响作用、出行行为对建成环境和态度的交互影响作用、态度或建成环境对出行行为的主导影响作用3个方面(Mokhtarian et al., 2008; Lin et al., 2017; Wu et al., 2022)。中国城市自选择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且效应不明显(Xu et al., 2016),认为环境和态度对行为的影响作用差异不显著(Lin et al., 2017; Wang et al., 2019),这可能归因于中国住房制度及非自主选择的因素。在休闲场景下,低碳可持续的步行出行和体力活动是中国城市自选择效应的主要议题(杨文越 等,2018;李智轩 等, 2019),并且研究发现在休闲场景中,个体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会对个体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建成环境影响占主体的结论(黄晓燕 等,2020)不一致。
综上,本文关注外地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与生活质量问题,讨论休闲态度、休闲环境对休闲行为的影响关系。立足于中国城市的本土实践,以广州外地务工人员为例,以自选择效应为理论基础,通过休闲环境与休闲态度的匹配关系分析、休闲行为结构化模型剖析,探究居民休闲态度和居住社区休闲环境对居民休闲行为的影响,挑战已有研究对外地务工人员在居住选择与休闲行为上被动接受的刻板印象(Xu et al., 2016),讨论哪个因素对休闲行为有更重要的影响作用。以期为提高该群体休闲生活体验形成健康生活方式提供科学指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设计
采用统计控制和联合模型2种方法探索休闲情境下态度、环境和行为三者的关系(图1)。已有研究证明建成环境和出行行为之间的关系(张延吉等,2019;杨文越 等,2020),即态度对行为、环境对行为均有主要影响(Cao et al., 2009)。在统计控制方法的部分,重点比较匹配和不匹配人群的休闲行为差异,根据居住空间休闲资源的丰富/稀缺程度、休闲态度的积极/消极程度,建立各社区内匹配人群与不匹配人群的划分;在联合模型方法的部分,基于休闲态度的影响作用建立态度决定模型,基于休闲环境的影响作用建立环境决定模型,基于两者复杂因果关系建立双向影响的非递归模型,探究休闲环境、休闲态度和休闲行为之间的具体影响机制。个体休闲行为的认识采用时间和空间2个维度(刘炳献 等,2017),即通过居民的休闲时间和休闲距离2个角度对居民休闲行为进行刻画,从时空行为角度研究居民的休闲行为。为了更好地验证假设,社会经济属性被控制为外生变量。根据研究模型确定具体变量,具体描述见表1。

表1 休闲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leisure variables

图1 休闲环境-态度-行为影响概念模型Fig.1 Leisure environment-attitude-behavior conceptual model
1.2 变量与数据采集
基于文献调研和专家咨询进行问卷设计,对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一周休闲活动日志和社区休闲设施数量进行调查。在休闲行为方面,通过居民一周平均休闲时间和平均休闲距离刻画居民的休闲行为。通过居民一周休闲活动日志,计算居民一周平均休闲时间和平均休闲距离。在休闲态度方面,通过问卷调查量表得到居民的休闲态度,题项“≥4”表示喜欢休闲,该部分居民为喜爱休闲者;“≤3”表示不喜欢休闲,该部分居民为讨厌休闲者。
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城市之一,是中国代表性的移民城市之一,拥有流动人口约938万①广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1](第六号)——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http://tjj.gz.gov.cn/stats_newtjyw/tjsj/tjgb/glpcgb/content/post_8540184.htm。广州城市移民中较具代表性的外地务工人员群体及他们主要居住的城中村社区,是探索休闲情境下态度-环境-行为关系的合适场域。本文所定义的外地务工人员为:非广州市户口、因工作目的、到广州生活6个月以上的群体(Huang et al.,2018;王洋 等,2022)。因此,调研的实施开展在城中村社区进行,研究对象是以低收入、农村户口为主体的外地务工人员。
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该群体聚居社区的抽样调查,充分体现休闲环境的空间差异性特征。一方面,根据广州市的行政区域划分,通过前期调查评估,在远郊区和老城区涵盖的4个行政区分别抽取1 个移民社区,接着在城乡接合部分布的3 个新城区各抽取2个,保证10个社区基本覆盖广州市全部区域。另一方面,通过社区休闲设施数量刻画休闲环境。根据百度地图社区行政区划范围,利用POI数据,基于社区生活圈设施分布有效阈值研究(罗雪瑶 等,2022),使用休闲设施数量表征社区休闲环境优劣,以实现休闲资源丰富与稀少的全覆盖。社区休闲设施通常包括公共休闲和商业休闲2类,10个社区在公共休闲设施的差异不大,但商业休闲设施的差异明显(图2)。新城区具有较高的商业活力,以健身房、室内娱乐、室内消费为代表的设施数量众多,天河区员村、天河区石牌村和番禺区大山村分别位于珠江河畔、天河区中部和大石中心区,社区内生活设施齐全,社区周边含大型综合市场、百货商场、休闲广场等多样化休闲设施,其休闲娱乐场所POI 数量>100 个,被划定为休闲资源丰富型社区。远郊区的公共和商业休闲设施均相对欠缺,海珠区上涌村、荔湾区坑口村社区内严重缺乏社区绿地、健身设施等,番禺区贝岗村周边为广州高校、社区内部休闲用地匮乏,黄埔区夏园村周边大多为工业用地及工厂、无大型商用休闲设施,其休闲娱乐场所POI数量<50个,被划定为休闲资源稀少型社区。其余越秀区王圣堂社区、白云区棠下村、海珠区下渡村多位于老城,被划定为休闲资源中等型社区(表2)。

表2 社区休闲资源数量Table 2 Statistics of community leisure resources 个

图2 调研地点分布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research sites
第一阶段采用街头拦截和入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问卷调查,保证每个城中村调查100人以上的初步有效样本。问卷调查于2017 年12 月—2018年1月,共收集问卷1 008份,删除未填写一周活动日志、核心数据空缺和数据填写有误的问卷后,得到999份样本进行统计分析。调查样本中,男性略多于女性,以26~45岁的中年人为主,收入普遍较低,受教育程度不高,职业以个体户、工人和服务业为主,95%居民租住,极少部分居民住在自有房(表3)。样本概况体现广州城中村城市外地务工人员的基本特征(朱竑 等,2016)。

表3 广州外地务工人员样本概况Table 3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Guangzhou
为了验证初步结果,研究团队于2022年9月前往休闲资源丰富的石牌村和休闲资源稀少的夏园村开展第二阶段调查。对23位社区租客的休闲生活进行访谈(表4),通过重新采样和补充信息进行的三角验证,进一步确保结果和结论的准确性。

表4 受访者基本信息Table 4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1.3 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初步探究居民在居住空间与休闲态度相匹配或不匹配情况下的行为表现差异;随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探究建成环境、态度和出行行为的复杂关系(Buckley, 2020; Wu et al., 2022)。本文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仅含观测变量,无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的方程为:
式中:Y代表的是NY× 1内生变量向量;X代表的是NX× 1外生变量向量;β是内生变量对其他内生变量的NY×NX直接影响系数矩阵;Γ是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NY×NX直接影响系数矩阵;ζ是NY× 1的误差向量。
根据模型假设,将休闲时间(LT)、休闲距离(LD)、休闲环境(LE)和休闲态度(LA)设定为内生变量,居民社会经济属性设定为外生变量,并将其视作连续变量直接放入结构方程模型(杨文越等,2018)。模型使用Amos 26.0进行估计,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并利用Amos 所提供的修正指标(MI)进行模型修正,分别对态度决定模型、环境决定模型和双向影响的非递归模型进行估计。
以往有关态度偏好与建成环境的研究证明态度与环境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关系(Liu et al.,2020),这会导致本研究中的休闲环境与休闲态度之间存在同时性偏差这一内生性问题(Wu et al.,2022)。因此,本文认为休闲态度和休闲环境之间可能存在非递归关系,并建立双向影响的非递归模型进一步探究二者对休闲行为的影响。
2 结果分析
2.1 基于匹配性的休闲行为分析
基于单因素方差分析,居民休闲行为在不同休闲环境下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表5)。首先,资源丰富型社区居民表现出休闲时间最长、休闲距离中等和休闲态度偏积极的特征。资源丰富型社区居民平均休闲时间最多(2.3 h),休闲时间<1 h 的占比0.99%,在一定程度上,休闲资源丰富型社区会更多地促进居民参与更多的休闲(谭磊 等,2019),“小区附近有丰富的休闲资源,所以喜欢参加休闲活动”(S08)。资源丰富型社区居民的休闲距离排第二(1.62 km),处于中等水平,说明优越的社区休闲环境促使居民更多地利用社区内部及周边的休闲资源进行休闲活动,如石牌村的居民提到“下班就在这里(石牌村幼儿园附近空地)玩一下,然后别的地方也不会去”(S01)。资源丰富型社区有86.84%的居民喜欢休闲,远超过全部社区居民,说明休闲资源越丰富,休闲环境建设越优越的社区居民对休闲的态度越积极,喜爱休闲的居民越多。

表5 不同休闲环境的休闲时间、休闲距离和休闲态度差异Table 5 Differences in leisure time, leisure distance and leisure attitude in different leisure environments
其次,休闲资源中等型社区表现出休闲时间最短、休闲距离最近的特征。休闲资源中等型社区居民休闲时间(2.11 h)比休闲资源稀少型(2.15 h)更少,居民休闲时间在1 h以下的均超过4%。在休闲态度上,中等型社区休闲爱好者(79.39%)比例低于丰富型社区(86.84%)、高于稀少型社区(69.92%),处于中间水平。
最后,休闲资源稀少型社区的休闲距离最长且休闲态度最消极。针对远距离的休闲活动(平均休闲距离“≥5 km”),资源稀少型社区居民比例最多(6.27%),约是资源丰富型社区(3.62%)和中等型社区(3.04%)的2倍。由于社区周边休闲环境建设较差,休闲空间少,居民会更多前往距离较远但休闲资源更多的地区进行休闲(Ettema et al., 2012)。正如S22提到虽然社区内部休闲资源较少,但自己“可以到比较远的地方爬山之类”;S17 提到“这边的商场比较小嘛,那边的(黄埔万达)比较大,就会那边逛”。远距离休闲可能会因为通勤出行等问题降低居民休闲的积极性,进而对居民休闲时间、休闲态度产生消极影响(王新越 等,2019)。休闲资源稀少型社区居民有高达30.08%的居民是休闲讨厌者,如S23认为:“(社区内较少的休闲资源)整体感觉会影响(休闲活动的)积极性”。
进一步基于休闲环境与休闲态度的匹配关系,将居民群体划分为一致型和错位型2种(图3)。可以看出,一致型和错位型居民的休闲行为具有差异。一致型居民平均休闲时间更长,居民普遍在社区“≤1 km”范围内进行休闲,其中休闲资源稀少型社区的不同类型居民的休闲时间未表现出明显差异。这说明居住在休闲资源丰富型社区的居民,休闲态度对休闲时间的影响更显著,而居住在休闲资源稀少型社区的居民,休闲环境对休闲时间的影响更显著。S04 是居住于休闲资源丰富型社区的休闲喜爱者,她表示:“小区里面附近周边的商场都会去逛……也会经常到比较远的商场和朋友一起逛街”。反观错位型居民,约60%每天平均休闲时间“≤2 h”,休闲距离未表现出显著差异。如居住于石牌村的S07“一般不怎么喜欢出去玩,朋友约才去。都是到比较远的地方,这(社区)附近对我没什么影响”;S06是居住于休闲资源丰富型社区的休闲讨厌者,表示自己虽然“不喜欢到外面逛”,但“自己住的房间里面空间很小,空气什么的也不是很好……因为(家附近)有这样一块空地可以乘凉,就会经常到这边来玩”,这体现环境对“错位型”居民休闲行为的影响。总体而言,居住同一社区的不同类型居民的休闲距离有相似性,这说明休闲环境可能对休闲距离存在直接影响。

图3 居住于不同类型社区的休闲爱好者和休闲讨厌者的休闲时间(a)和休闲距离(b)分布Fig.3 Leisure time(a) and Leisure distances(b) for leisure lovers and leisure haters living in different neighborhoods
2.2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休闲环境、态度与行为关系研究
进一步探究休闲环境、态度和休闲行为的影响机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自选择理论,分别对态度决定模型、环境决定模型和双向影响模型进行估计,3 个模型统计检验结果相同,χ²/df为2.035(<0.3),RMSEA为0.33(<0.05),CFI 为0.998(>0.9),模型拟合效果好, 能较好地拟合样本数据(图4)。

图4 自选择模型、环境决定模型和双向影响模型影响路径Fig.4 Self-selection model, environmental determination and two-way influence models
2.2.1 态度决定模型 休闲环境对休闲行为仍有显著的影响(表6),表现为休闲环境对居民平均休闲时间有正向的直接效应,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72,说明社区休闲资源越丰富,居民会花更多的时间参与休闲。“因为他这边(社区公园)给人一种宽敞,很明亮的感觉,会让我更多的出来散心。”(S09)休闲态度同样对休闲行为有显著总效应正向影响,表现为对休闲时间和休闲距离的负向直接效应(-5.434,-2.91),以及通过影响休闲环境,进而转化为对休闲时间和休闲距离的正向间接效应(5.551,2.914)。这说明居民的对休闲的偏好并不会直接促进居民参与休闲活动,而是通过休闲环境的中介调节促使居民参与更多休闲活动。正如S12本身是喜欢休闲的人,在定居后发现小区内有社区公园,就会“没事就出来走走”,并且“也不会到其他地方,就在这个地方(社区公园)逛逛。”而S13 则表示由于自己“喜欢打乒乓球……没有这个地方(社区体育馆)也会去其他地方打”,这也反映休闲态度对休闲行为的积极影响。休闲态度对休闲环境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与假设一致,即居民的休闲行为存在自选择效应(Buckley, 2020)。

表6 内生变量对内生变量之间的标准化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Table 6 Standardized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between endogenous variables on endogenous variables
2.2.2 环境决定模型 社区休闲环境是居民休闲态度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0.111 的正向促进作用(见表6),证实了“环境决定模型”的成立,说明社区休闲环境越好,居民对休闲活动的态度越积极,这与Lin 等(2017)等的研究一致,二阶段访谈的结果也证实以上发现。以S08 和S11 为例:“小区附近有丰富的休闲资源,所以更喜欢参加休闲活动”(S08),体现环境对态度的积极作用;“(以前住的社区)那边有海嘛,然后空间大,可以玩的非常多,这边(现在住的社区)玩的地方很少,没有以前多,就不太爱出去玩了”(S11),体现环境与态度的正相关关系。在环境决定模型中,休闲环境对休闲行为中的休闲距离具有负向的总效应(-0.032),表明休闲环境对休闲距离的负向直接影响(-0.108)大于休闲态度在其中产生的间接调节作用(0.076)。这与前文结果一致,即优越的休闲环境会吸引居民在社区内部进行休闲活动。“对就在这里(石牌村幼儿园)……珠江公园那边都太远了,不愿意去,这个地方刚好可以在一起聊天”(S02)。与此同时,休闲态度与休闲时间正相关(直接效应),这在态度决定模型中表现为负相关,说明社区休闲环境会显著影响居民休闲态度偏好,进而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休闲。
2.2.3 双向影响模型 上述结果证明态度决定模型和环境决定模型均成立,因此休闲态度与休闲环境之间存在非递关系,双向影响模型有效。模型的计算结果(见表5)证明休闲态度与休闲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的、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与Lin 等(2017)的研究相似。一方面,休闲态度显著影响休闲环境:喜欢休闲的人更可能居住在休闲环境优越的社区(直接效应),正如休闲喜爱者S03提到在租房时“考虑过离周边的商场很近然后而且外面也有很多大型的商场”,但此类人群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间接效应),如交通因素(谭磊 等,2019),而无法选择居住在符合自己偏好的社区,“最主要还是离公司近”(S03)。另一方面,休闲环境也对休闲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受其他因素干扰。这充分说明社区良好的休闲环境会培养更多的休闲爱好者,促进居民更加热爱休闲活动。在对休闲行为的影响方面,休闲态度对休闲时间的正向影响减弱,且对休闲距离的影响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影响。休闲环境对休闲行为的影响与环境决定模型一致,表现为仅与休闲距离负相关,说明社区休闲资源越丰富,对居民休闲时间无影响,但会使得居民休闲距离变短。
休闲行为的态度决定模型和环境决定模型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而言,休闲态度与休闲环境呈显著正相关,并通过休闲环境的中介影响居民休闲行为;社区休闲环境对居民休闲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丰富的休闲资源吸引居民开展近距离的社区内休闲。同时,考虑休闲环境与休闲态度偏好相互影响的非递归模型也成立,回应了已有研究(Lin et al., 2017)。进一步地,社区休闲环境与居民休闲态度偏好之间存在直接正向相互影响,即休闲资源越丰富的社区会更好地培养休闲爱好者,同时喜欢休闲的人在选择居住地时,更偏向居住在休闲环境优越的社区。
2.2.4 社会经济属性影响 关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影响,3 个模型具有相似的影响结果(表7)。性别上,男性和女性在休闲时间上不存在差异,但女性休闲距离较男性更远,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在生活中会更多外出参与社交活动与购物活动(许晓霞 等,2012),例如S04 和S17 两位女性都提到:“平时出去逛也是约朋友一起,很多时候也是比较远的商场”(S04),“那边的(市区商场)比较大,就会那边逛”(S17)。年龄对居民休闲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喜欢休闲,回应了两代外地务工人员休闲行为理念与实践的差异(Tang et al., 2020),新生代外地务工人员具有更频繁且丰富的休闲行为,城市空间利用也更为充分。家庭月收入对居民休闲时间和休闲距离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对休闲环境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于这个现象合理的解释是,收入越高的家庭在居住选择上具有较高的自我选择能力,可以选择居住在休闲环境更优越的社区,但其较长的工作时间会导致用于休闲的时间被压缩,进而导致休闲时间减少和休闲距离缩短(宋瑞,2006)。学历上,学历越高的居民更注重休闲生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前往更远的地方参与更多的休闲活动,表明教育水平提高促进外地务工人员休闲行为的开展,由此获得恢复力和工作效率(李萍,2017)。除此以外,家庭月收入在双向影响模型中表现为对休闲态度的负向影响(-3.7),学历在环境决定模型中表现为对休闲环境的负向影响(-0.067),而在其他模型下没有显著相关性。这反映当同时考虑态度和环境2种因素时,家庭月收入会显著影响居民的休闲态度,高收入家庭会更关注自己的休闲生活方式;而学历越高的居民对居住地休闲环境的要求更高,导致其受休闲环境的影响更为敏感。

表7 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的标准化直接效应Table 7 Standardized direct effects of exogenous variables on endogenous variables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自选择理论引入休闲行为研究,通过休闲态度与休闲环境匹配性的分类对比及考虑自选择的休闲行为决策模型,探究了休闲环境、休闲态度和休闲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休闲行为的态度决定模型和环境决定模型均成立,休闲态度与休闲环境存在双向影响关系。2)休闲行为的时间维度(休闲时间)和空间维度(休闲距离)存在差异性的影响机制。休闲态度对休闲时间的影响最为直接,而休闲环境对休闲距离的影响存在复杂的作用机制,如休闲资源丰富和休闲资源中等型的社区居民可能强化的是社区内休闲参与,中等型社区内休闲比例最高;休闲稀缺型社区居民会更多参与社区外休闲,休闲距离最长。3)社会人口经济属性对休闲行为、休闲态度和休闲环境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学历和收入对休闲行为有促进作用,而年龄对休闲行为有限制作用。
本文选择休闲场景,更好地推动了自选择效应与理性行为理论的结合,充分考虑了态度在环境对行为影响机制发挥的作用(Liu et al., 2013; Wu et al., 2022)。已有的自选择效应研究重点讨论了居住环境、态度偏好与交通出行的关系(Wu et al.,2022),交通行为具有功能主义且追求效率的特点,居民自主选择范围和能力有限。而休闲行为的主体决策能力更强,其对态度的依赖与体现更为直接。理性行为理论发展于社会心理学,认为态度和行为互相支持,休闲态度由经验而建立、具有持久稳定性,能更直接影响休闲行为(戴维·迈尔斯,2020),建立起理论对话的桥梁。本文对外地务工人员休闲行为的实证表明,休闲环境的影响固然重要,休闲态度与理念的培育也同样具有意义。
外地务工人员休闲主题的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启示。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深入,休闲已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社会需求,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已成为社会实践的必备部分。休闲可视为对工作的一种补偿,帮助恢复工作消耗的体力与精力(艾泽欧-阿荷拉,2010)。中国快速城镇化中,外地务工人员对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有研究指出外地务工人员在城市留下了青春与健康(陆铭,2016),而未能获得城市居民相等同的优质生活。本文表明,休闲自选择效应可以通过改善社区休闲环境,来提高居民的休闲参与度和生活幸福感,进而有助于缓解外地务工人员的身心压力,以保持身心健康和维持生活质量。鼓励和保障外地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是中国城市社会的重要问题,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在。
围绕外地务工群体认识的多元化趋势正在形成。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这一群体并非是外界习惯认为的形象,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多元化的,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而是发挥着自身主观能动性不断地适应和改变城市生活。休闲态度上,新生代为代表的休闲爱好者会更加主动的选择居住空间,通过参与休闲活动积累城市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Stalker, 2011; Liu et al., 2013)。休闲行为可能成为流动人口实现异地安置的空间粘合剂,促进人的城镇化的完善过程。在居住选择上,应当打破住房无法自我选择的刻板印象。在中国租购并举和租购并权的住房保障体系下,外地务工人员在租房寻求过程中将越来越多的发挥主动权。本文并不否认其在低租金方面的诉求(王洋 等,2022),但访谈中多位受访者也表达了对租房环境的细化需求,休闲态度决定下的居住空间休闲环境需求已有所显露。因此,多元的认识和关怀才能使外地务工人员更好地适应城镇化过程,使其不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朱竑 等,2019)。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外地务工人员的整体生活情况考虑不充分,经济压力、社交联系以及家庭结构均具有影响休闲行为的可能,未来需对社会人口经济属性进行更全面的考虑。其次,引入理性行为理论,作为这一分支最为成熟的计划行为理论具有更为明确的指导意义,由于调查实施及数据限制,未对社会规划、知觉行为控制等变量进行综合考虑,未来需进一步规范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