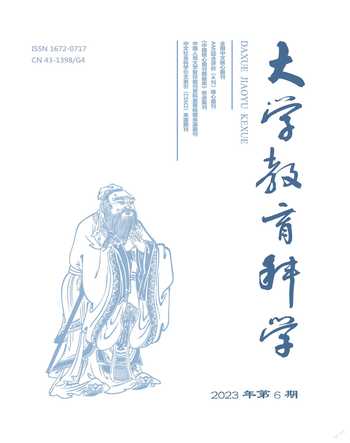分“理”而治:学科治理的本体解读与实践逻辑
2023-12-02陈亮许姝燕
陈亮 许姝燕
摘要:学科治理现代化是可持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全要素驱动创造性成果接续生成的关键保障,分“理”而治为学科治理由粗到细、由抽象到具体的实践转变筑牢了基础。学科治理包含“知识”与“制度”两个维度,知识层面的“天理”“人理”和制度层面的“法理”共同构成了学科之理的三重逻辑。学科冲突寓于学科天赋之理、人赋之理、法定之理之中,且外化于学术组织、学术行为、学术场域三大方面,严重滞碍了学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学科治理中的冲突频发与危机震荡的根源不仅在于学科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不明学科之理,还在于具体的学术制度设计与学科治理行动忽视分理而治。因此,学科治理亟须由“理”明“治”,进而达成分“理”而治,形成顺应学科天理、关照学科人理、完善学科法理的学科治理机制,凝聚学科共生、共在交往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学科观念、制度形态、组织形态三个维度建构起应变机制。
关键词:分理而治;学科治理;本体解读;实践逻辑;现实冲突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3)06-0003-08
学科治理现代化,即学科要实现一流和卓越的学术品性和制度理性,是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可持续培养、驱动创造性成果接续生成的关键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展望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我国陆续出台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旨在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学科治理现代化建设与世界一流学科高质量发展。在国家政策精神的宏观引领下,学界持续开展了学科治理相关研究,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三方面:一是概念属性层面,有学者基于学科在实践、知识、组织层面的基本属性,探讨学科治理与学院治理及大学治理的衍生关系,从而明确学科治理的属性逻辑和本质所在[2];二是作用机理层面,有学者围绕大学社群组织的运行规范,以学科共同体理性治理精神的回归,对学科治理发展的动态机制进行研究[3];三是问题导向层面,有学者论述了学科治理的逻辑体系,审视了学科治理的现实成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学科可持续发展的相关举措[4]。总的来看,当前研究对学科治理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分析已经有所涉及,但缺乏对学科治理本体层面的逻辑解构和实践导向的理路研究,也未从学科治理本体出发观照学科之危,未能深入探讨学科治理现实冲突的本质所在和破解路径。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着眼点逐渐从关注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转向关注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对独特办学理念、强势学科优势、一流教学质量的要求日益突显[5],“高质量发展”也随之成为大学学术治理的主要目标。作为学术治理可持续发展的逻辑旨归,学科治理日益成为教育现代化和现代大学建设的核心关切。然而,学科建设在实践中却成为高校优绩主义竞争和非理性“内卷”的主阵地,并由此诱发了高校学科治理主体权责缺位、资源配置失衡、评价机制固化等问题,阻滞了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为化解学科治理中的顽疾,学科治理亟须由“理”明“治”,进而达成分“理”而治,即针对不同学科门类的属性和特征,对具体问题进行全方面多维度的分析,形成顺应学科天理、观照学科人理、完善学科法理的学科治理机制。学科治理的本体解读和逻辑指向是实现“分‘理’而治”的主要路径,本体解读强调对学科治理本体意义的多重剖析,逻辑指向着重观照学科之危,探寻学科治理的实践机理,共同构成了学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基于此,厘清学科治理的多层结构和内在逻辑,助推学科治理实现由粗到细、由抽象到具体的实践转变,对学科知识和学科制度驾驭系统性、复杂性问题至关重要,也是根治学科治理顽疾、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一、学科之理:学科治理的本体意义
由“理”明“治”,进而达成分“理”而治,构成了理解学科治理本体意义的基本路径。从字面意义来看,“治理”具有统治、管理、整修、处置等含义[6],皆表“治”的动作。而实际上,治理分别由“治”和“理”两部分构成,如果只側重“治”的部分解读,则并不能揭示出“治理”的本真要义。相反,治的对象是“理”,理不同则治不同。显然,要从本体论层面深入理解“治理”,就必须从“理”的部分切入,以“理”明“治”。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治理”由政治话语延伸到更加广泛的领域,譬如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教育治理等,学科治理也是“治理”在学术话语体系下的衍生概念与合意表达。基于此,理解学科之“理”的不同表达,是揭示学科治理本体意义、实现分“理”而治的必要前提,对实现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方位开展学科治理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学科是指人们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系统有序的知识体系”[7]。而学科治理是对知识活动的制度性改革,其本质是知识本性和制度理性间的适应与耦合,这决定了学科治理本体解读的基本逻辑。学科治理包含“知识”与“制度”两个维度,探寻学科之理必然要从“知识之理”与“制度之理”两方面出发。首先,知识的本质是“求真”。“真”意味着真理,即“天理”;而“求”则意味着人类在遵从“人理”基础上探索与验证真理。因此,知识之理涵盖了“天理”与“人理”两大方面。其次,制度本质上具有规范性[8],可以通过对知识活动的规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因此,制度之理即“法理”,是建立稳定学术秩序的重要基础。基于此,知识层面的“天理”“人理”和制度层面的“法理”共同构成了学科之理的三重逻辑。促进学科从“虚空的无”转向“具体的有”,将“天理”“人理”“法理”有机融入学科治理和学科建设之中,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知识真理、满足学科内在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需要[9]、激发学科治理持久生命力的题中之义。
(一)探索知识真理是学科的天赋之理
学科的天赋之“理”是稳定不变的,变化的是“理”的表现形态。天赋之理即自然之理,是深藏于事物背后的底层规律,它不以人的意志和行为而改变,自始至终主宰着自然事物运行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它之所以会发生变化只是表现形式在发生变化。基于此,对自然之理的理解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理不变”,即自然之理是一种规律,是稳定不变、持续存在的;“形易变”,即自然之理的表现形式会发生变化,且变化是多样的、复杂的。学科的天赋之理,即蕴含于自然之理中的学科规律,具备自然之理的基本特征。因此,从“理”和“形”的维度分别解构学科的知识真理,是探明学科本体逻辑的关键。
首先,我们要明确“不变中的理”,即学科的一般规律。学科围绕知识而生,知识生成的最终目标是揭示真理和真相,帮助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演变,知识的本性和其产生的客观规律是不变的;无论学科的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如何变化,学术共同体追求真理的精神信仰是永恒不变的。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知识主体在此信念支持下,以追求真理、探究真问题、讲真话为行为准则,以学术思想传播者的身份在公众知识生活的中心播散希望的学术种子,助推学科治理的稳步运行。
其次,我们须理解“变化中的形”,即学科规律的变化形态。随着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的加深,更深层、更高阶、更精细的规律被发现和揭示,因此学科建设需要适配更复杂、更系统、更高能的知识生产模式。例如,工业社会强调“标准化”和“统一化”,传统的学科制度与工业社会知识生产的方式高度匹配,讲究统一的组织实施和分类标准。而今,现代社会具有“个性化取代标准化”的趋势,知识结构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高深莫测、具有可探究性,学科建设相应地需要在探究、变革中去思索与开拓。
总而言之,在学科治理从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知识生产模式在不断变革,但人们追求的真理始终是知识活动的内在本性和发展规律,并指向学科的高质量发展、高校的可持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运行规律无一不是奉学科知识的真理性为圭臬。那些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研究成果的产生,无一不彰显出真理知识的力量。因此,学科治理要形成一个长期稳定且繁荣的学术生态,必须形成崇尚真相、追求真理的学术信念。这也是维持学术治理“善态”格局,避免偏离学术道德、学术规律的根本所在。
(二)实现社会发展是学科的人赋之理
人赋之理强调学科的社会属性,指明了学科治理不能单纯地追求学术理想,探索知识真理,更要深入到社会的复杂环境,“与环境因子有机结合”[10],进而探求“人赋之理”。“人赋之理”即人理,是人与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道德规约和社会规律。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活动规律也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因此“人理”具备同“天理”一样的自然属性。但又因为人本身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人理”相较于“天理”而言更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故而更为复杂多变。相比于自然规律单一普适的“理”,“人理”主要涵盖“内理”和“公理”兩大方面。前者是人与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尊老、爱幼、兄友、弟恭等道德规约,后者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和遵循的一般规律;前者侧重于“人”,后者着重于“理”。学科的人赋之理,即蕴含于“人理”中的学科规律,主要侧重于对后者“理”的解读。
学科的人赋之理是由知识本身的社会属性和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所决定的。首先,就知识本身的社会属性而言,知识并非只是一种信息、一种缺乏主观信念的客观存在。“知识与信念和投入密切相关,知识所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立场、视角或意图”[11](P47)。因此,学科治理除了要遵循探索知识真理的“天赋之理”,还应被人所信服,为社会所接纳,进而谋求实现社会发展的“人赋之理”。其次,就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而言,知识生产往往与社会物质生产相互促进,相伴而生。例如,原始社会的知识生产方式来源于生存需要和劳动生活中的直观经验,知识还停留在直观层面,物质生产等同于知识生产。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技术环境和经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知识生产方式已从因果线性模式转向复杂多元的共存模式,如由果到因的逆向模式、相关模式、螺旋模式等等[11](P63)。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的相互关系,表明了在历史和社会演进的过程中往往是“物质知识化”和“知识物质化”的不断转化过程。这种转化过程恰恰是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这种逻辑也决定了知识的转化和知识的适用要遵循人和社会的发展。基于此,学科治理要遵循知识本身的社会属性和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在以实现社会发展为目标导向的同时还要规约知识生产的走向,引领社会发展的理性。
(三)维护学术秩序是学科的法定之理
学科的法定之理凸显出学科治理的权力属性,是维护学术秩序的强制规范。法定之理是法理,即交往契约,它不仅仅是法律法规的原理依据,也是各种刚性制度的基本原理。学科的人赋之理是协调人与学科的精神契约,学科的法定之理则是调整学科关系的强制契约。前者是内力,后者是外力,共同构成了学科关系的准则和规范。学科的法定之理是由知识制度的生成逻辑和人与社会的现实需求所决定的。公平公正的学术秩序是学术共同体的基本伦理要求,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12]。知识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要避免知识生产活动的失范风险,当一个社会的知识生产秩序是失范的,则意味着知识主体之间的交往缺乏合理性和信任基础,学术交流与合作则无法开展[13](P78),知识制度也就无法引领社会文明的进步。学术失范的本质是学术行为违背了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律,违背知识的真理本性,这就直接抑制了科学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因此,作为重要知识制度载体的学科也必然担负着保障知识生产、维护学术秩序、引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任务。
学科的法定之理作为规范知识活动的本质所在,必须遵循维护学术秩序这一始终不变的内在要求,维护学科秩序始终是现代化学科治理的基本保障,学术活动、主体利益、交往准则等都需要通过学科秩序进行约定。现代化的学科治理需要重新审视的是:学术活动方式、学术利益分配以及交往规则是否符合新的知识活动要求和知识规律,它们对社会发展是否乃推力而非阻力。信息技术赋能下,知识生产活动越趋频繁与快速,知识传播途径更加多样化、传播速度更为迅捷。学术秩序在这种知识爆炸式增长的环境中呈现出某种异化现象,譬如:学术不端行为频发,隐蔽性更强;学者的学术信仰和话语体系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可能导致学术信仰和学术成果的缺乏。因此,建立公平公正的学科秩序,必然要通过制度对权力的规约去平衡好学术人的权利与义务,使其与知识规律和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相匹配。治理对象和治理目的不同,秩序建构的精神准则亦不同。良好的学科治理秩序,一方面要坚守“法定之理”的稳定内核,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变。这种内外兼通的应对机制,既能保障稳定的学术秩序建立,也可支撑学科治理善态格局的形成;能够促进学术共同体成员在约定俗成的规约下开展学科交往活动,同时也为解决学科发展中出现的诸多失范行为提供方法论指导与实践依据,确保学科治理在合理合法的限度空间高质量、可持续地运行。
二、学科之危:学科治理的现实冲突
随着技术环境的急剧变迁,学科正遭受来自制度与知识的内部冲突以及制度与时代的外部冲突。这两大冲突蕴含于学科治理的全过程之中,并转化为阻碍学科建设的潜在现实危机。学科之危是学科治理内外部环境所遭受的冲突与危机,具体体现为知识生产与学科制度间的失配,即学科制度违背知识生产规律。这在制度层面主要体现为学科制度对知识生产的阻滞妨碍,在时代层面主要体现为学科制度的落后逆施。若不及时对学科治理的现实冲突进行调控和管理,冲突极易从“合理性危机”恶化为“生存性危机”。基于此,从理解学科治理、厘清“学科之理”到直面学科治理,是应对“学科之危”的关键所在。学科治理的本体意义揭示了学科之理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暗含着解构学科之危的基本逻辑。与学科之理本体维度相对应,学科治理的现实冲突也寓于学科天赋之理、人赋之理、法定之理之中,且外化于学术组织忽视学科知识生产规律、学术行为僭越学术主体人文性、学术场域饱受知识活动的权力规约三大方面。
(一)学术组织忽视学科知识生产规律
现代社会正步入知识型社会,学科治理相应从传统化迈向现代化的改革道路。学科治理的变革本质上并非变革知识本身,而是变革生产知识的制度,促使学科制度始终遵循知识本性和学术规律,顺应探索知识真理的学科天赋之理,形塑学科制度理性。此外,学科制度不仅要顺应知识规律,也要充分观照社会规律,深入人的关系属性。学科制度在架构起现代化治理的过程中,必然要通过制度对权力的规约去平衡好学术人的权利范围与责任义务,使其与知识规律和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相匹配。为顺应学科天赋之理,充分观照社会规律,构建具有创新活力和竞争实力的学术生态,学科治理要侧重由内而外的治理方式,同時兼顾由外而内的管理方式,形成松散耦合的关系属性。这一属性蕴含在学科制度建构的理性精神之中,并成为规约学术活动权力范围和关系的重要力量。
目前,我国学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仍未达成,现行科层体系下的学科治理制度结构驱动学科内生性发展乏力。随着社会发展进程加快,个性化需求增多,社会更需要构建开放式政策框架[14]、包容性学科制度,以此推动个性化知识的生产。传统的学科治理体系以科层体系为主,即便今天的现代化改革浪潮推动了很多横向体系和组织建构(交叉学科、未来技术学院以及学科联盟等)的产生,但科层体系的传统惯性仍是支配学科制度设计与治理的主要架构。过去几十年,这种科层体系的高效率和强组织力推动了我国学科的高速度、规模化发展,但同时也凸显出制度僵化、制度失灵甚至制度异化等问题,尤其是学科评价制度如何推动一流学科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体制束缚和结构桎梏。因此,在推进学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要将学科治理现代化的总体部署转化为可供实践的具体方案,就必须以学科治理体系的优化调整为核心,勾勒出一套现代化学科制度架构的逻辑理路,建构起符合知识活动规律的理性学科制度。
(二)学术行为僭越学术主体人文性
学科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是知识分类制度“变易”中的发展与拓展。学术场域中的共同体用理性思辨和因果推理为知识的精深性和专业化倾注力量,知识生产更为多样、复杂,学科制度也从简单的知识分类演变为纵横交错的复杂格局。学科制度在此变革过程中始终以人的力量为观照,不断适应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进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动力。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需要借助学科制度去唤醒学术主体的内在力量,激发人们深层性的变革欲望和创新能力。加之,现代社会中的知识结构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高深莫测、具有可探究性和不确定性的,需要我们在探究、变革中去思索与开拓,在不断修正中发掘不足与改进之处。由此,学科治理必然要引导学术主体自觉的社会责任与自身发展协调共生,形塑学术主体人文性,即沉淀于心的学术道德和精神契约,从而生成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的学术秩序。
然而,在学科治理实践中,学术主体之间由于缺乏信任,合理性交往遭受僭越,个人利益往往凌驾于人文性之上。在优绩主义、狭隘利己主义驱使下,学术成员为把握领域核心利益,将学术资源私人化,垄断学术上升渠道,导致学术人文性缺失、恶性竞争频发。学科建设也逐步呈现出“权力化”“功利化”“指标化”的追逐导向,学科治理秩序紊乱甚至异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滋生的抄袭、造假、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动摇了国人对中国学术的信任,人们开始怀疑真理背后的‘科学’,悼念学术人与‘学术’相处的学术‘礼仪’”[13](P2)。学术失范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主体人文性价值缺失,内在精神契约遭到破坏,加之以法律追责为主要内容的外在惩戒力度不到位。目前,我国仅有较少法律涉及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且仅仅涉及行政责任,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治理尚缺乏充足的法律依据[15]。学术主体间的恶性竞争、制度约束的力度不够,加剧了学术生态的恶化,抑制了学科建设的进程和质量,导致那些具有原创性和变革性的知识生产趋于停滞。因此,学科治理要力求激发学术主体的道德自觉,辅以强有力的惩戒制度加以规约,在公平正义的信任基础之上回应学科卓越发展的美好愿景。
(三)学术场域饱受知识活动的权力规训
学科治理服务于学科知识活动,学科制度设计、实施都应该围绕知识活动的内在规律而开展。学科制度基于知识活动内在规律建立起学术场域内部交往原则与规范,并确立起外部学者与社会的权力关系,因而学科制度所规范的权力关系要以“知识权力”为主。但现实中,制度规范与知识活动之间往往因权力关系而存有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学科制度的权力规范未能遵循知识活动的内在规律,学术场域中的各主体盲目服从权力规训,继而导致“知识固化”下创造性价值乏力、“知识盲从”下价值立场偏向的合理性危机。
首先,学术场域对政治权力的屈从使得知识内在关联的建立受阻,创造性生产日趋困难,“知识固化”在学术场域中趋于主流。大学内部的政治权力往往是自上而下的,通常是一种政治性权力而非民主权利。这种政治权力主导下的学科建设不仅规定了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而且还塑造了知识生产的“产品”内容,以保持固化的大学学科制度开展持久的知识规训。譬如,在大学现存的学术评价指标当中,会出现一种“不可思议”的指标垄断现象,尤其在职称评审中会发现某些学者发表的学术界公认的高级别期刊论文往往无法在本校内部的职称评审中占据同等的同行评价地位。其根本原因是这些校内“高级别”期刊目录的制定者往往是学术生产活动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他们往往既是“学术领袖”“学术守门人”,又是“行政精英”“裁判员”。这个过程中过度的行政权力往往指导着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僭越了学术的内在要求。
其次,学科治理主体行使学术决策权的过程中往往缺乏对国家意志的深入理解和灵活执行,导致学科管理碎片化和学术场域价值立场偏向。其主要原因在于:学术场域中的主体不一定对宏观层面的知识规划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和深入的调查,也不一定能够在结合实际问题的基础上灵活性制定落实举措。如果治理主体缺乏对学术现状和共同体成员的深入调查和研究,往往会导致制度制定和实施的“个别偏向”,即施策权威偏向某些学术权力主体。因为在制度落实和决策制定过程中,学科相关的治理主体占有较大话语权。这些治理主体往往基于权力、绩效和管理的视角解构宏观战略和制度,并对最终的学科制度设计与实施发挥重要影响。然而,学科治理权威赖以维系的基础是公共意志,“在权力的产生中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元素,是人们的共同生活”[16]。因此,学科治理要转变自上而下的绩效管理思维,应减轻学术场域中治理主体对知识活动的权力规训,从而回归集体共同利益,生成敢于质疑权威的学术文化和具有创新活力的学术场域。
三、学科之变:学科治理的实践逻辑
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学科治理需要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形成以新知识和信息技术为基础,注重知识创造价值的卓越集群格局。新时代学科治理要着力关注大学以及学科所处的“后工业”知识社会环境,始终与社会发展情境保持稳定互动,以创新驱动社会发展与服务国家重大现实需要作为学科治理新的增长点和立足点。然而,现实中学科治理冲突频发与危机震荡严重滞碍了学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其根源不仅在于学科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不明学科之“理”,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学术制度设计与学科治理行动中忽视“分理而治”,并由此引发了学术组织、学术主体和学术场域的异化现象。因此,學科治理的实践机理要基于学科之危的根源,在厘清学科之理基础上做到分理而治,理不同则治不同。新时代的学科治理应针对学术组织、学术主体、学术场域三大方面,凝聚学科共生、共在交往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学科观念、制度形态、组织形态三个维度建构起应变机制。
(一)顺应学科天理,实现学科观念转变
“知识分类”的学科布局结构难以适应新时代知识个性化需求,与探索知识真理、顺应知识发展规律、推动知识创新的学科天赋之理相背离。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生长起来的学科意识,在新的知识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临近之际,仍然存留着强大的、泛在的认知惯习。提及“学科”,反映在人们主观意识中的形态往往是“知识的分类体系”这一固化认知。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知识增长的需要决定了学科知识高度分化的发展走向,学科治理格局也高度匹配知识分类结构,形成纵向科层与横向分类的制度体系。在此制度系统结构下,知识具有系统有序、逻辑严密、方向聚焦等特点,高深性与系统性并存,推动了工业社会的高度繁荣。步入后工业社会,人们对物质生活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内涵逐渐从工业时代的标准化、规模化转变为后工业时代的个性化、多样化。随着技术环境的变迁、知识经济社会对知识内涵的拓展,强调“知识分类”的学科布局结构与个性化的社会知识需求形成了较大的矛盾。层层制度化、层层固化的学科布局形塑了强大的知识生产惯习,并进一步阻断了学科与社会的信息通道。学者的工作与社会的需求变得越来越有距离,难以引领社会经济的成功转型。
学科发展应遵循天赋之理,顺应社会变迁,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动力支撑,产出更多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知识和技术生产。当知识的系统程度和严密程度并不成为唯一的社会应用标准时,大学要走在新的时代发展前沿,就必须要思考传统的知识生产体系如何顺应学科天理,实现与现代知识需求的共通共融。而对知识生产体系的重新审视,必然要推动学科意识形态革命性的更新和深化。个性化需求与分类性生产之间的矛盾推动着学科意识形态的转变,新的学科意识形态不再是“知识分类体系”,而应是“群落共生体系”。群落共生体系以整体性思维为着眼点,强调区域内与区域间跨学科的互涉关联与整群融合,有助于推动知识生产应势而变,顺应知识发展规律的“天赋之理”。从“知识分类”到“由分而聚”的学科意识观念更新,是高等教育实现学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之变,有助于推动“因果确定研究”向学科整群合作的范式转变,从而形成顺应知识真理,推动知识创新的新格局。
(二)观照学科人理,推动学科制度形态改变
管理思维下的学科制度形态具有工具性特点,难以深入到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层面建立起基于道德自觉的精神契约。学科治理与学科管理具有不同的权力运行向度:学科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17],学科管理则体现出权力主体“单边性”下达命令的特点。治理“以无为而治为体”,将“由内而外”的疏导协调作为核心主体;管理属“后天有为而为”,以明显的后天干预性为特点,强调“由外而内”的系统化管制[18]。学科治理和学科管理具有不同的权力作用方式,这也决定了学科制度形态建构的不同侧重点。为维持学术场域秩序、提高学科运行效率,学科制度形态往往围绕于以强制性规范塑造学术正义,体现“管理”的色彩。然而,偏重于外在规约和强制手段的“管理”形式并不符合学科治理的人赋之理,愈发难以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需要[19]。人赋之理要求学科治理不能单纯依靠技术、工具去衡量资源和利益的分配,而要深入到人的道德人伦和文化精神层面,进而达成“内圣之理”。“道德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没有它,社会成员就不能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而这类合作恰恰构成了他们共同体的共同生活”[20]。学术共同体的道德信任并非单纯具有维持学术场域稳定,推进学科建设、课题项目进度等工具性目的,更是唤醒学术成员内生自觉、厚植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内在力量。
学科制度形态实现从科学“管理”到人本“治理”的跨越,是学科治理观照学科人赋之理、助推制度形态创新的重要路径。一个能够通过共同的道德规约建立起信任的治理制度,其发展是依靠内在驱动而非通过外力主宰的,这是学科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制度形态改革方向。学科制度形态要摆脱“管理”纯粹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生成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的学术秩序,需要依托学术主体间的道德信任,形成依循学科人理,顺应时代使命,助推社会发展的“柔性治理”。正所谓,“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21]。学科治理需要将制度形态的建构过程融入到社会理性和学科人理之中,从而搭建学科制度螺旋上升的循环链。同时,学科制度形态的发展与创新也为打造学科制度特色、提升制度自信注入生机与活力,有助于推动学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三)完善学科法理,助力学科组织形态重构
学科组织围绕学科知识结构而建立,“知识分类”的结构范式塑造了“分门别类”的学科组织形态,即基于学科划分形成的院校结构。学科组织形态是制度形态的载体,较制度形态更为具体、可视,前者是“形而下”,后者是“形而上”的。“‘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者,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22]形而上是无形的规律,形而下是具体的形态。学科的制度形态侧重学科治理“形而上”的内在规约,即基于道德信任的非正式制度的建立。学科组织形态是“形而下”的,“它是一个由学者、知识信息以及学术物质资料所组成的实体化了的组织体系”[23]。学科组织大多围绕学科知识的分类结构而建立,高等院校的教研室、系、院基本都是工业社会学科知识分类下形成的组织形态。部分大学甚至是基于某一个优势学科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譬如政法大学、外国语大学、经贸大学,它们分别依托法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建构起了各自的学科组织。同时,这些依托学科知识分类建立的学术组织又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了学科知识的划分疆域,在同一个学科专业领域构筑起了牢固的学术研究问题域与解决域。
后工业社会对知识提出了“融合性”要求,学科治理的组织形态也理应在完善学科法理基础上探索学科组织形态的共融共生体系。步入后工业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学术场域中的问题域和研究范式往往需要夹杂融合其他学科。具有单一性特点的“分门别类”学科范式难以适应数字时代对“融合性”学术知识的需要。因此,学科治理亟须打破“分类性”的组织形态桎梏,持续完善学科法理,依托制度与法律规范构建融合共生的学科组织形态,从而激发学者内在研究冲动和热情,使其迈向学术研究的自我升华[24]。具体而言,国家要持续加强政策支持,引导学科自组织、跨学科组织、学科集群等新型学科组织形态的建设与重构;高校要深入开展有关学科联盟、高校联盟的制度建设,为建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学院和学系提供制度性规约。此外,企业、政府、学术组织等要围绕跨知识、跨思维、跨方法、跨视野的理念来进行学科组织制度设计,推动学术组织跨越制度藩篱、打破学科壁垒,从而生成具有创新创造活力的学科组织新样态。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03-13)[2023-02-06]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2] 杨天平,薛长凤.基于学科属性的大学学科治理[J].现代教育管理,2021(07):18-25.
[3] 陈亮.新时代学科治理的发生机理[J].高校教育管理,2022(02):83-91.
[4] 马廷奇,郑政捷.大学学科治理:逻辑意蕴、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10):22-27.
[5] 沈江平,金星宇.把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三重意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4·25重要讲话精神[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4):47-55.
[6] 路丽梅,王群会,江培英.新编汉语辞海:图文珍藏版[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1726.
[7] 周光礼,武建鑫.什么是世界一流学科[J].中国高教研究,2016(01):65-73.
[8] 辛鸣.制度论:关于制度哲学的理论建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
[9] 陈亮,李林霖.中國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要义、本质特征与推进路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42-52.
[10] 赵磊,高树仁.大学教学环境的生态系统及优化策略[J].重庆高教研究,2017(03):59-64.
[11] [日]竹内弘高,野中郁次郎.知识创造的螺旋:知识管理理论与案例研究[M].李萌,译.高飞,校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12] 李建华,江梓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之维[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5):45-52.
[13] 陈亮.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14] 孙蕊,王少洪.共建共治共享开放式社会创新的理论与实践[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22(01):180-187.
[15] 陈恩伦,李亚勍.学术治理现代化的思维转换与路径选择:兼评《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4):59-68.
[16] [德]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58.
[17]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
[18] 熊春锦.东方治理学: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115.
[19] 包水梅,李明芳.一流学科建设:从管理走向治理——兼论我国高校学科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其突破[J].现代教育管理,2021(01):25-30.
[20] [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夏勇,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45.
[2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M].张文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9.
[22] 孔颖达.周易正义[M].李学勤,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92.
[23] 宣勇.论大学学科组织[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2(05):30-33.
[24] 刘晖,张甜甜,张艳芳.困局与破局:大学学术制度构建中学术自由的边界[J].大学教育科学,2022(03):40-46.
收稿日期:2023-07-08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优势学科培育类课题(2023-05-068-BZPK01);陕西省教师发展研究计划专项项目重点项目“陕西师德师风建设的有效机制研究”(SJS2022ZD012)。
作者简介:陈亮(1987-),男,辽宁鞍山人,教育学博士,《当代教师教育》副主编,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许姝燕,陕西师范大学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西安,710062。
Govern by Principles: Ontology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al Logic of Discipline Governance
CHEN Liang XU Shu-yan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discipline governance is a key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cultivation of top innovative talents and the continuous generation of creative achievements driven by all factors. Governing by principle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discipline governance from coarse to fine, and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Discipline governance includes the two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and system. The natural principles and human principles at the knowledge level and the legal principle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triple logic of discipline principles. Disciplinary conflicts are embedded in the principles of disciplinary talent, human endowment, and legal principles, and are externalized in the three major aspects of academic organization, academic behavior, and academic fields, seriously hindering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discipline governance. The root cause of frequent conflicts and crisis shocks in discipline governance is not only that the subjects of discipline governance do not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but also that the specific academic system design and discipline governance actions neglect to govern by principles.Therefore, discipline governance urgently needs to clarify governance by principles, and then achieve governance based on principles, form a discipline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complies with the natural principles of the discipline, takes care of the human principles of the discipline, and improves the legal principles of the discipline, and condenses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for symbiosis and exchange of disciplines.
Key words: divide and rule; discipline governance;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practical logic; realistic conflicts
(責任编辑 陈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