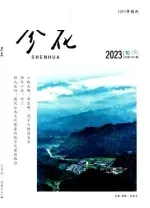论白朴戏剧中人物形象的独特建构
2023-11-15王珏
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白朴是金元易代之际最早以文学名士身份走进杂剧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其剧作具有迥异于同时期其他杂剧作家的多元内涵和复杂的时代特色,突出地表现了白朴作为传统文人在元朝初立时的感慨。通过对其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具体故事情节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对其作品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白朴戏剧作品概述
据钟嗣成《录鬼簿》所记载,白朴写过15部剧本,加上残折共16本。现存完整的、为后人熟知的剧作仅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以下简称《梧桐雨》)《董秀英花月东墙记》《裴少俊墙头马上》(以下简称《墙头马上》)三部。白朴的杂剧题材多取自历史和民间传说,内容多以男女爱情、才人韵事为主。被后人列为“元代四大悲剧”和“元代四大爱情戏”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取材于白居易的著名叙事长诗《长恨歌》和《井底引银瓶》。这两部作品,历来被认为是爱情剧中的成功之作,具有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对后代戏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梧桐雨》——梧桐细雨下的爱情绝唱
《梧桐雨》是一出历史悲剧,此剧取材于白居易《长恨歌》,剧名来自《长恨歌》中的“秋雨梧桐叶落时”这一名句。故事讲的是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李杨之恋”作为一个经典的文学母题,自白居易的《长恨歌》起,此后数朝皆有演绎,以传奇、南戏、杂剧、说唱文学等多种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但相比其他关于“李杨”故事的写作或续写想象,白朴《梧桐雨》的展开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元朝社会风气相对松动,不仅是以白朴为代表的部分文人开始了非常规文学创作,同时亦有观众群体接受度的整体提升,在此前提下,白朴“放浪形骸,期于适意”的人生态度也随之被注入这部作品中,共同叙写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悲欢离合。
(一)杨玉环的时代特性
在对这段旷世之恋的刻画上,最重要的两个角色无非就是爱情的男女主角——李隆基和杨玉环,相比于其他作品的剧情框架,白朴没有沿袭传统文学中对男女主角形象“温情式”的刻板书写,而是在二人的情感线索中增加了安禄山、梅妃等多个元素,并将安史之乱始末与杨贵妃搭建起关联。在人物形象构建上,唐宋的作家们更倾向使用贤良淑德作为后妃的代名词,于是出现了如王昭君、长孙皇后等角色,即便是普通女性形象,也大都拥有诸多优良品质。但《梧桐雨》中白朴却借用了野史对杨玉环的描述,对贵妃进行了轻薄自私的特色化描写,而在刻画作为君王的李隆基时,白朴的描写更是直接冲淡了其权威性。
这样独特的形象构建是具有时代性和个人性的,宋代勾栏、瓦肆等娱乐场所得到发展,及至元代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更是兴盛,结合白朴的个人经历不难推测,其在戏剧生涯中接触了许多风格迥异的女性艺人,这些女性身上不同的性格特征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白朴的创作。而将这些女性群像集中于本该温婉端庄的帝妃身上时,则迸发出更强烈的角色魅力和戏剧影响力,这是白朴对于时代的把握和个人见闻的外化。但过多性格元素的掺入也造成杨贵妃这一角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与男主角相比更显得扁平,这也可能是受元杂剧一人主唱的规定所影响,使末本戏中的女性角色不可避免地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二)李隆基的性格悲剧
作为末本戏主角的正末唐明皇李隆基,其形象也与典型的君王差异较大,白朴笔下的玄宗具有常人般的性格和情绪,而非仅有高高在上的君王气度。首先,在玄宗下令释放安禄山并将其认作义子一段中,可能众多的评论家会将之归结为是玄宗昏庸的表现,但剧中事实却并非如此,张守珪见安禄山骁勇,而将其送往京城“取圣断”,这一行为的初衷本就是守将张守珪希望玄宗可以惜才之名放安禄山生路,结果也是如此,安禄山被免于一死,准其戴罪立功,这种赏罚分明、爱惜人才的做法是开明君主的表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若无引狼入室一举便无安史之乱。而脱去李隆基的黄袍,仅因贵妃喜爱就为安禄山加官晋爵、认为义子的行为,更多的是出于人之常情,凸显了深陷爱情后李隆基的判断受情人感受所左右。无关历史真相,李隆基眼中的杨玉环是“一个晕庞儿画不就,描不成。行的一步步娇,生的一件件撑,一声声似柳外莺。”这完全就是一个陷入热恋的普通男子的真實心态。其次,到马嵬驿赐死贵妃一出,则更直接地表现了君主也似常人般无法挽救自己的爱情和国家,无奈之感笼罩于玄宗和白朴。
(三)李、杨爱情关系的搭建
爱情作为玄宗和贵妃的最深层链接,无疑是《梧桐雨》的核心话题,白朴并未否定李杨二人感情的真实性,在第一折结尾的七夕盟誓足见真心:“长如一双钿盒盛,休似两股金钗另,愿世世姻缘注定。在天呵做鸳鸯常比并,在地呵做连理枝生。月澄澄,银汉无声,说尽千秋万古情。咱各办着志诚,你道谁为显证?有今夜度天河相见女牛星!”可见,即便贵妃与安禄山已然有了“圣人赐予妾为义子,出入宫掖,日久情密”的前提,但月下以金钗钿盒起誓时二人有来有回的提问和回应自是将真情和盘托出,并约定了世世为夫妻、千秋万古情。而因安史之乱玄宗贵妃仓皇出逃至马嵬驿,并经过六军哗变,贵妃被迫自尽、玄宗退位后,在某个寂寥的秋日雨夜,李隆基作为太上皇却又梦到早已离世的贵妃,梧桐夜雨点醒的并非梦境,而是明晰了李隆基对逝去爱人的真切感情。剧中几人感情的复杂并不是对真爱的否定,而是一种真实性的表现,爱、欺骗和遗憾并存的感情完整地表现了杨玉环、李隆基两人脱去身份标志后所拥有的普通人的感情,这也是白朴自身感情观的流露。
盛唐的最后荣光被安史之乱浇熄,梧桐雨也打破了李隆基的残存幻想,这种人物情感和命运的幻灭即是白朴描写的重点,而对李、杨独特的人物形象建构不仅描摹了白朴自身的感受、经历,更营造了山河破碎的氛围感,生于近代的国学大家王国维亦感同身受,于是他由衷地称赞“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冕。”
三、《墙头马上》——喜中衔悲的悲剧化书写
《墙头马上》描写的是一个“志量过人”的女性李千金冲破名教,自择配偶的故事。与《梧桐雨》相比,《墙头马上》有着鲜明的喜剧语言和令人捧腹的科诨,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更加悲剧性的故事因果,以更加辛辣的语言和矛盾尖锐的剧情明显地展示了白朴心中对自由的期盼和渴求,情感与理性的相持让剧中人物呈现出张扬的个性,当时渐为开放的时代思潮也表现在了情与理的缠结中。
(一)李千金的挣扎与妥协
《墙头马上》是元代杂剧中表现爱情的顶尖之作,故事内容大胆革新,活泼的语言、紧凑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李千金这一女性人物形象,但作为矛盾的集中体,李千金身上却有着更明显的、无法逃脱的悲剧性命运。
李千金为爱奋不顾身,她那句“爱别人可舍了自己”的爱情宣言掷地有声,成为经典。就似这句口号,李千金在追求自主婚姻时大胆、勇敢。然而李千金作为女主角承受了剧中绝大多数的压迫,众多的悲剧因子也是由李千金生发而出。《墙头马上》中浓厚的悲剧氛围来源有四,即时间的差错、空间上的阻隔、家族的压力和纲常礼教的束缚。李千金与裴少俊私定终身一起私奔至裴家的后花园,这与双方父母的最初心愿有一致之处,当初李总管、裴尚书都有结亲的心愿,但由于李总管得罪了女皇武氏,宦途直下被贬为洛阳总管,故而耽搁了儿女亲事。李千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个人大事却未被及时提上日程,后偶遇裴少俊来洛阳采办花苗子,一见钟情并相约花好月圆时幽会,被嬷嬷撞破后立即决定私奔,直到这个时候李千金都是勇敢、大胆的,她青春的内心敢于和纲常礼教展开斗争。私奔后的七年中,李、裴二人在后花园中幸福生活并生下一双儿女,后来某日却被公公撞破,在与裴尚书论辩中能够明确亮出自己的观点,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后被休回老家,少俊获隽授官后接她回裴家,她先是不允,但在一番挣扎后只好与之妥协,在这一阶段李千金貌似成功,其实是失败的,因为这种斗争在当时那个时代尚无出路,是唯一选择。
着眼于白朴对李千金的人物塑造,她在追求自主婚姻时是勇敢者,也是胜利者,但她在私奔时似乎从未考虑父母的感受,也未曾在意自己私奔后会造成何种影响,可见她个人是置家族压力于不顾的。随后裴少俊功业有成,前来求和时,她却因为孩子而妥协了,这便是李千金的无奈。在时代以“礼”去要求女性时,李千金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换来的却是父母的早逝、公公的怒骂和丈夫的欺骗。从表面上看,李千金的妥协是因为亲情,但其实质更多的是向夫权妥协。
(二)裴少俊的顺从与无奈
受元杂剧体制影响,裴少俊在旦本戏《墙头马上》中也显现出片面化的现象。相较李千金的复杂性格特征,裴少俊虽也对自由爱情表现出渴求并付诸私奔的实际行动,但其程度远不及李千金,主要性格则外化为对感情的不坚定和顺从父亲。
在白朴的描写中,裴少俊生长在良好的生活环境中,自幼聪颖过人,“三岁能言,五岁识字,七岁草字如云,十岁吟诗应口”,而且才貌双全,在长安城中颇有名声。他的父亲裴行俭,官居工部尚书,对他管教甚严:“年当弱冠,未曾娶妻,不亲酒色。”少俊也以“唯亲诗书,不通女色”自诩。殊不知,他的心中也埋藏着躁动的青春活力,也向往着和谐甜蜜的爱情,因此最终作出了被裴行俭这样有着浓厚礼法观念的老顽固视为“大逆不道”“辱没祖庭”的私奔一事来。
此外,在与李千金的爱情婚姻中,裴少俊除了在初见时出于挑逗的心理主动说出“如此佳丽美人,料他识字,写个简帖儿嘲拨他。张千,将纸笔来,看他理会的么”,并央张千送信过去,其余时候多展现出犹豫的一面,甚至幽会的请求都是由李千金主动提出的。而在幽会时被嬷嬷撞破,虽两人皆与嬷嬷有过周旋,但还是以女方作为事件核心并主张私奔,最后以死相逼才求得嬷嬷放两人离开,在此惊险的过程中裴少俊则作为顺从的一方听从李千金指令。从对搭讪、幽会、私奔的态度看,裴少俊对自由和爱情的渴求远不及李千金。
裴少俊不只是在结合时有过犹豫,私奔回府后更是偏向选择顺从父亲,首先是自身婚姻的身不由己,无论是幼时定亲还是在父亲撞破妻女后被迫写休书,都是家族掌控的产物,而裴少俊的斗争性远不如李千金,即便是与爱人私奔也是情势所迫,裴少俊皆是无法自主选择的。其次是科考的身不由己,裴少俊寒窗苦读多年却无心科举,私奔回家后和李千金在小花园内过了七年秘密的婚姻生活,直到父親强制命令才去参加科考,虽然最后进士及第,但在过程中给家庭造成的创伤是不可逆转的。
四、白朴戏剧中的寄托意识
白朴在创作中融入自身的经历和性格,就如李隆基和裴少俊这两个男性角色都暗含着白朴自己的影子,淡泊名利,将热情投注到感情和生活中,都饱含着对真爱的渴求和对现实的无奈。同时,白朴作为文人的一分子,仍然希望用戏剧这种文学形式去书写时代,以期在情和理之间找到突破口。王国维曾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饜阅者之心,难矣。”可见,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带着对团圆的渴盼。如多数传统文人一样,白朴书写的《梧桐雨》和《墙头马上》也透露着对团圆美满的追求,满足了普通观众对于婚姻和家庭和美的期许。
五、结语
《梧桐雨》与《墙头马上》的题材虽然都源于白居易的诗歌,同为爱情剧,但在风格与文本形式上有着明显差异,一雅一俗,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此可以看出白朴对于不同题材的掌控力。他既能够驾驭传统诗歌以抒情为主的诗化杂剧来营造意境,又能不拘泥于既有的创作习惯,而把握新的文学形式,并通过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来增加杂剧的戏剧效果。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石头记索隐(插图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祖语.《墙头马上》悲剧性的伦理考量[J].戏剧文学,2020(09):124-131.
[4]丁添彩.白朴元曲创作研究[D].河南大学,2015.
(作者简介:王珏,女,硕士研究生在读,吉林艺术学院,研究方向:中国戏剧历史与理论)
(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