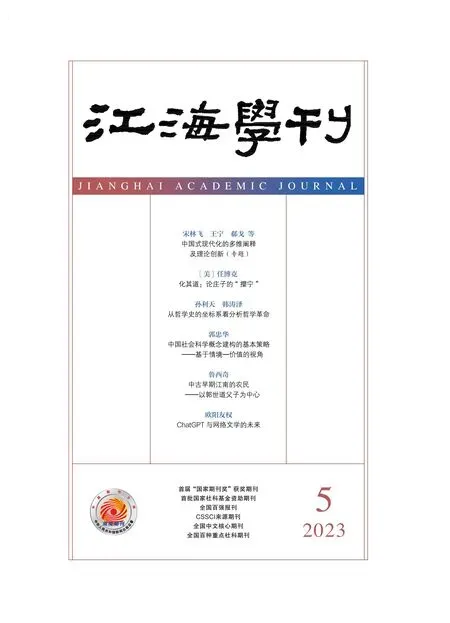中古早期江南的农民
——以郭世道父子为中心
2023-11-01鲁西奇
鲁西奇
“农民”,本义是指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这里的“农业生产”涵义是广义的,包括农耕、游畜牧、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因此,广义的“农民”大致可以界定为,直接依靠自然资源以获取基本生计需求的人。在中国古代,“农民”是“业农之民”,亦即以农耕为业的庶民。《穀梁传·成公元年》载:“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注谓士民为“学习导艺者”,商民是“通四方之货者”,农民是“播殖耕稼者”,工民是“巧心劳手以成器物者”。(1)范宁集解、杨士勋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一三,成公元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417页。《颜氏家训·勉学》:“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义经书。”(2)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卷三《勉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3页。显然,四民的划分,是以生计方式或职业为原则的。其中,“农民”被界定为“播殖耕稼者”或耕稼者,亦即从事农业种植的人,这是狭义的“农民”。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主要是指从事农耕的农民。
孙达人指出:“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农民国家,迄今为止,它还是世界上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研究中国历史虽然应该涉及各色人等和一切方面,不过,无论如何,农民始终应是我国史学主要的研究目标。否则,我们写出来的历史最多也只能是与我国历史主体间接有关的枝节。”农民是中国历史的主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农民创造的,“在中国,假如离开了农民的历史,既无法了解中华的过去,也谈不上认识民族的未来”。(3)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埃里克·范豪特(Eric Vanhaute)说:“在历史上,农民是国家的基石。不论是中华帝国、罗马帝国,还是土耳其帝国、印加帝国,都建立在农民的生产方式和农民劳动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农业的繁荣,它们都难以为继。”(4)[比]埃里克·范豪特:《劳作之中:农民的世界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因此,以农民为主体的历史叙述,应当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核心线索之一。
可是,“农民总是从属于更广阔的社会体制,或被收编(incorporation)、或被同化(assimilation)抑或进行抵抗(resistance)”。(5)[比]埃里克·范豪特:《劳作之中:农民的世界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几乎在所有历史叙述中,农民均处于边缘地位。中国传统史学的“根本弱点在于轻视农民。农民长期被完全排斥在史学的大门之外,没有任何地位可言”。(6)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第5页。因此,要以农民为主体叙述其历史,乃至以农民为核心线索叙述中国历史,就必须“找到”历史上的农民。
《宋书·孝义传》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考察历史上普通农民的珍贵资料。两汉特别是东汉标榜以孝道治天下,故常常表彰、优待孝悌清行之士。华峤《汉后书》首列《孝子传》,范晔《后汉书》略变其例,于《独行》中传列孝友。然华峤、范晔等所述孝子、孝友,皆为士人;魏晋表彰孝义,亦集中于士人;至南朝,始及庶民。《宋书·孝义传》所记,贾恩(会稽诸暨人)、郭世道(会稽永兴人)、严世期(会稽山阴人)、吴逵(吴兴乌程人)、王彭(盱眙直渎人)、孙棘(彭城郡彭城县人)等六人,可以确定是普通编户。其中,有关郭世道父子事迹的记载较为详悉。(7)《宋书》卷九一《孝义传》,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461—2479页,特别是第2464—2467页。郭世道,《南史》卷七三《孝义传》作“郭世通”(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00页)。本文即主要根据《宋书·孝义传》“郭世道”条,结合相关记载,细致考察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地区农民生活的地理空间、生计方式、社会关联及其赋役负担,希望藉此尽可能清晰地认识中古早期江南地区农民的形象及其生存状态,尝试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中古早期江南地区农民,并探讨他们的生存状态。
中古早期江南农民生活的地理空间
《宋书·孝义传》记载的郭世道是会稽郡永兴县人。(8)《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64页。下文凡引用《宋书·孝义传》有关郭世道、原平父子的记载,均见第2464—2467页。《宋书·州郡志》会稽太守“永兴令”条载:“汉旧余暨县,吴更名。”(9)《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第1123页。余暨作为汉旧县,见于《汉书·地理志》与《续汉书·郡国志》。《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余暨”县原注:“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莽曰余衍。”(10)《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1页。《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余暨”县下刘昭补注:“《越绝》曰西施之所出。《谢承书》有涉屋山。《魏都赋》注有萧山,潘水出焉。”(11)《后汉书》志二二《郡国志》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88—3489页。今本《水经注》卷四○《渐江水》云:
浙江又迳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东迳柤塘,谓之柤渎。……有西陵湖,亦谓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东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浙江)又迳永兴县北,县在会稽〔西〕(东)北百二十里,故余暨县也。应劭曰:阖闾弟夫概之所邑,王莽之余衍也。汉末童谣云:“天子当兴东南三余之间。”故孙权改曰永兴。县滨浙江。(12)郦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四○《渐江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3—3304、3324—3325页。
固陵城,胡三省注:“西陵在今越州萧山县西十二里西兴渡是也。吴越王钱镠以西陵非吉语,改曰西兴。”(13)《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纪》二,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下,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356页。其地当在今之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西。永兴县在固陵(西陵)东、山阴(会稽)西北,亦滨浙江,在其南岸。《水经注》又谓浙江过永兴县后,“又东,合浦阳江”。其下文述浦阳江源流,谓其水过诸暨县南之后,“又东北迳永兴县东,与浙江合,谓之浦阳江。《地理志》又云:县有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又疑是浦阳江之别名也,自外无水以应之”。(14)郦道元著,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四○《渐江水》,第3325、3337页。浦阳江(潘水)东北流,经过永兴县东(实为南),东流,合浙江。据此,永兴县治即在浦阳江北、浙江水南,其地当在今杭州市萧山城区或其稍北处。
据《宋书·孝义传》,郭家居于独枫里(元嘉四年以世道之孝行,改名为孝行里,传文不言其所属乡)。传文称郭世道行厚之风,“行于乡党,邻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则其所居在村中。传文又谓其子郭原平为人佣作,日暮受直后“于里中买籴”,归家举爨。则郭家所居之独枫里规模较大,里中有可买米之所。传文又述郭家宅舍,谓:
居宅下湿,绕宅为沟,以通淤水。宅上种少竹,春月夜有盗其笋者,原平偶起见之,盗者奔走坠沟。原平自以不能广施,至使此人颠沛,乃于所植竹处沟上立小桥,令足通行,又采笋置篱外。邻曲惭愧,无复取者。
此亦足证郭家居宅在村里而非城中,于永兴县城附近,属都乡。
郭家所在之地,正当浦阳江下游与浙江水相会之区,其北有浙江,南有浦阳江,西北十余里处是柤渎,正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所以,水上交通应是当地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传文描述说:
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渎不复通船,县官刘僧秀愍其穷老,下渎水与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岂可减溉田之水,以通运瓜之船。”乃步从他道往钱唐货卖。每行来,见人牵埭未过,辄迅楫助之,己自引船,不假旁力。若自船已渡,后人未及,常停住须待,以此为常。尝于县南郭凤埭助人引船……
运瓜往钱唐的水道得称“瓜渎”,既可用于运输,也是灌溉渠道。官府可控制瓜渎的水量,说明渎上已建有控制水量的堰闸。这条渎水,应当流经永兴县城附近,北通浙江;渡过浙江,可到钱唐。钱塘江上建有埭。郭凤埭,在永兴县城南,应是浦阳江上的埭。那么,这条瓜渎,向南当与浦阳江相通。
埭的本义是堤岸。《古今注》卷下《草木》载:“汉郑弘为灵帝文乡啬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酿。于埭逢故旧友人,四顾荒郊,村落绝远,酤酒无处,情抱不伸,乃以钱投十中,依评饮,尽多酣畅,皆得大醉,因更为沈酿川,明旦分首而去。”(15)崔豹:《古今注》卷下《草木第六》,《四部丛刊三编》本(子部二二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6页。沈酿埭处荒郊野外,远离村落,却可以住宿,应是一处渡口设施。《搜神记·吴郡士人》谓:“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于都假还,至曲阿,日暮,引船上,当大埭。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甚美,便呼之留宿。”(16)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卷一八《吴郡士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1—322页。王姓士人的船停靠大埭上,埭上有女子流连,这个埭也当是码头。《宋书·沈攸之传》载:“初,攸之贱时,与吴郡孙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17)《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第2122页。引埭,即藉以拖引船舶的埭,应与江岸相交,伸入江中。

浙江、浦阳江、柤渎等河流上的埭都置有埭吏,负责管理渡口和征税。永明六年(488),时任西陵戍主杜元懿启曰:
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见,日可一倍,盈缩相兼,略计年长百万。浦阳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腹心。
牛埭,是用牛牵引舟船之埭。西陵牛埭,当即钱塘江南岸、西陵戍下的码头。据杜元懿之说,吴兴与会稽间的交通经过西陵戍,西陵牛埭显然是钱塘江上的码头。浦阳南北津,当即浦阳江上的津渡,郭凤埭当是其中之一。针对杜元懿的建议,行会稽郡事顾宪之议曰:
寻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纳税也。当以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胶溺,济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京师航渡,即其例也。而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别道,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而犹责,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格外十条,并蒙停寝。从来喧诉,始得暂弭。案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馑,去之从丰,良由饥棘。或征货贸粒,还拯亲累。或提携老弱,陈力糊口。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19)《南齐书》卷四六《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第893—894页。
埭司,即津埭的管理机构。京师航渡,当指建康长江与秦淮河的渡口。据顾宪之所述,设置埭司的本义,是为了管理渡口设施、航渡运行、救护水难,也负责征收过渡税。从京师到各郡县的津渡皆普遍设有埭司。然监领埭司者,却将征税视为其主要职责,采取各种办法增加税收。埭司垄断水上交通(“禁遏别道”),控制人员货物的流通,正可说明其时水上航行人员往来、货物流通颇为频繁。
《宋书·孝义传》称郭世道“尝与人共于山阴市货物”。山阴为会稽郡治,其“市”在山阴城中。传文又说原平“每出市卖物,人问几钱,裁言其半,如此积时,邑人皆共识悉,辄加本价与之,彼此相让,欲买者稍稍减价,要使微贱,然后取直”。这里的“邑”,是永兴县;“所出之市”,自当在永兴县城中。
综上所考,我们对郭家生活的地理空间遂形成一些基本认识:(1)郭家应当居住在永兴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属独枫里),其宅舍地势较低,四周挖掘了排水沟,上建小桥可供通行。沿排水沟,是竹丛,其外又围有一圈篱笆。宅舍与邻家并不相连,是一处相对独立的住宅。(2)永兴县城大抵即位于今萧山城区或其西北不远处。县城有水道与其南面的浦阳江和北面的浙江水相通。沿此水路,郭世道及其子原平可至永兴县城及其市,然后转赴山阴和钱唐。郭凤埭和西陵牛埭分别是浦阳江和浙江上的重要码头,上建有引埭等设施;置有埭司,负责管理津渡运行和收税。(3)永兴县东有会稽郡(其首县为山阴县),浙江北岸有钱唐县与余杭县,溯江而上有富阳县,永兴县西北境有西陵戍。永兴县即位于山阴、钱唐、富阳共同构成的浙江下游的区域体系中。一个普通农民所生活的地理空间,就以其宅舍为中心,从其所在地村落,通过水网,向永兴县城、西陵戍、山阴市、钱唐县城等地展开来。
中古早期江南农民生计的多样性
郭世道与郭原平的生卒年不详。元嘉四年(427),郭世道以其淳行受到宋文帝的嘉奖,会稽郡榜表其闾门。其时世道父母(继母)均已离世,本人也娶妻生子,早已成年。世道丧父之时,年十四岁。传文记原平守孝三十余载,则世道当卒于元嘉中期。宋文帝驾崩时,原平正当壮年。大明七年(463),原平仍在劳作,而“县官刘僧秀愍其穷老”,元徽元年(473),则卒于家。若以其卒时70岁计,则当生于东晋安帝时。以其出生时世道20岁计,推测世道当生于太元中。世道、原平父子生活的时代,当不出东晋孝武帝到刘宋明帝(376—472)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
据传文所述,郭氏父子的生计手段,主要有佣作、田作与贸易三端。
(1)佣作与十夫客。郭家初无田产。传文叙郭世道年少时“家贫无产业,佣力以养继母”。然世道佣力为生,仍得娶妻生子。世道之佣作,盖非田作。传文记叙世道之子原平“性闲木功,佣赁以给供养”。盖郭家世传木工,世道亦以木工为生计手段。

传文记原平“每为人作匠,取散夫价”。所谓“散夫价”,应当是按日计价。下文又说原平“尤善其事,每至吉岁,求者盈门。原平所赴,必自贫始,既取贱价,又以夫日助之”。(21)《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66页。夫日,也是指按日计算的夫价,即一夫一日的报酬。当时佣赁,无论是作木工还是构冢,都按日付酬。原平为营葬亡父,“自卖十夫,以供众费”。“葬毕,诣所买主,执役无懈,与诸奴分务,每让逸取劳,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暂替。所余私夫,佣赁养母,有余聚以自赎。”原平以“十夫”的身份,与主人家的“诸奴”共同劳作(分务),主人每遣之,因“原平服勤,未曾暂替”,说明“十夫客”的地位高于“诸奴”,大概是居自家,每天前往买主家劳作。十夫客在给主人佣作时,还得有剩余的“私夫”,所余“私夫”,得获报酬,原平用以养母和自赎。
“十夫”,又作“十夫客”。《南齐书·孝义传》载:
吴达之,义兴人也。姨亡无以葬,自卖为十夫客,以营冢椁。从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卖江北,达之有田十亩,货以赎之,与之同财共宅。郡命为主簿,固以让兄。又让世业旧田与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闲废。建元三年,诏表门闾。(22)《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第1063页。
“十夫客”,《南齐书》新校本《校勘记》谓:“《建康实录》卷一六作‘力夫’,《御览》卷五一七引《齐书》作‘十夫佣’,明本《册府》卷八○三《总录部》作‘士夫客’。”(23)《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第1072页。在上引《宋书·孝义传》中,“十夫”与“私夫”相对应,或以“士夫客”为是。东汉桓帝元嘉三年(153)的《郎中王政碑》记王政死后,王家之“门徒士夫”等,“乃相与立石表行”。(24)《隶续》卷一《郎中王政碑》,洪适:《隶释 隶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页。碑文将“士夫”,置于“门徒”之下,当不是“士大夫”之省称,应是指依附王政家的客。因此,所谓“士夫客”,当是如士依附于君或依附于主人的客。郭原平、吴达之自卖为“十夫客”后,仍居自家,亦有自己的户籍,甚至吴达之还拥有“世业旧田”,郭原平亦得自用其“私夫”,但他们必须前往买主家“执役”,与买主家的“诸奴”一起劳动,当是按其劳动量计算工价,并在工价积满卖价后,结束“十夫客”生涯。所以,“十夫客”是预支工钱,然后按工时偿还总价的雇佣方式,其地位盖低于“散夫”,高于“奴”。
佣赁与卖为客,盖为贫穷人家重要的生计方式。除郭世道、原平父子外,《宋书·孝义传》所记吴逵、王彭皆尝以佣赁为生。吴逵,吴兴,乌程人,“经荒饥馑,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独吴逵夫妻存活,“家徒壁立,冬无被绔,昼则庸赁,夜则伐木烧砖”,“朞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邻里嘉其志义,葬日悉出起助”,“逵时逆取邻人夫直,葬毕,众悉以施之,逵一无所受,皆佣力报答焉。”(25)《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68页。吴逵白天为人佣赁,当是日工,故夜里仍得伐木烧砖,为故去的亲人营造墓葬。“逆取邻人夫直”,是指预借邻人钱,以“夫直”作为偿还;邻里表示不用还,吴逵仍“皆佣力报答”。王彭是盱眙直渎人,少丧母,元嘉初,父又丧亡,“家贫力弱,无以营葬,兄弟二人,昼则佣力,夜则号感。乡里并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砖”。(26)《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70—2471页。王彭兄弟二人,白天为人佣力,夜则居自家,也是日工。《南齐书·孝义传》载:
公孙僧远,会稽剡人也。治父丧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谨,年谷饥贵,僧远省飡减食,以供母、伯。弟亡,无以葬,身贩贴与邻里,供敛送之费。躬负土,手种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卖为之成礼。(27)《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第1059页。
“身贩贴与邻里”,《南史·孝义传》作“身自贩贴与邻里”,(28)《南史》卷七三《孝义传》(上),第1818页。当是与郭原平、吴达之“自卖”为“十夫”“十夫客”相同,是以夫力卖与邻里,预取夫费。文中的“自卖”,指僧远自卖为“十夫客”。
然则,东晋南朝时江南地区为人佣工,有日佣(散夫)和自卖为十夫客(士夫客)两种类型,二者均按工时取夫费,前者按日结算,后者预支,按工价偿还。无论散夫还是十夫客(士夫客),都是著籍的编户齐民,于雇主没有强制性人身依附关系。
(2)田作。郭家初有宅,无田产。至原平时,买下田产数十亩。传文称:
及母终,毁瘠弥甚,仅乃免丧。墓前有数十亩田,不属原平,每至农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坟墓,乃贩质家赀,贵买此田。三农之月,辄束带垂泣,躬自耕垦。
贩质,当即典卖。原平贩质的家赀当即田产,故原平此前当已有田产。自汉代以来,田产即可买卖。《三国志·蜀书·张裔传》:“少与犍为杨恭友善,恭早死,遗孤未数岁,裔迎留,与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长大,为之娶妇,买田宅产业,使立门户。”(29)《三国志》卷四一《蜀书·张裔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2页。原平之田,均系买得。郭世道少时,“家贫无产业”,全靠“佣力以养继母”;至原平时,已可一次性买进数十亩田产,此时郭家在经济上已处于上升阶段。
浙江下游两岸种植的农作物,当以水稻为主,但麦菽也应当很普遍。刘宋孝武初年,周朗上书言事,说:“又田非疁水,皆播麦菽;地堪滋养,悉艺纻麻;荫巷缘藩,必树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30)《宋书》卷八二《周朗传》,第2298页。按照周朗的说法,当时南方地区,无论是山地还是水田,到处都种植麦菽纻麻;村落的巷旁篱侧,栽种着桑柘;人家的庭院屋宇边,则种着竹栗。周朗所言,虽是总概,但永兴、山阴、钱唐、富阳间,大抵亦当如是。

子平世居会稽,少有志行,见称于乡曲。事母至孝。扬州辟从事史,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人或问曰:“所利无几,何足为烦?”子平曰:“尊老在东,不办常得生米,何心独飨白粲。”每有赠鲜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则不肯受。(31)《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78页。
何氏本为庐江灊人,南渡居会稽。东晋南朝官吏之月俸为白米,何子平领白米后,即到市场上换粟麦。他做从事史,在建康当差,其母在会稽,故子平称“尊老在东”。从何子平言,知白米比粟麦贵,品质也好。何氏是官宦人家,其父曾任职建安太守。然而即使如何氏,其家也不是总能吃白米,故东晋南朝普通人家,仍当多吃粟麦等。
原平“又以种瓜为业”。《齐民要术·杂说》:
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只如十亩之地,灼然良沃者,选得五亩,二亩半种葱,二亩半种诸杂菜;似校平者种瓜、萝卜。……瓜,二月种;如拟种瓜四亩,留四月种,并锄十遍。(32)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今本《齐民要术》的这一部分《杂说》,一般认为是唐人后补,并非贾思勰原文,所述亦大抵为北方黄河流域的农作经验与技术。但在城郭的郊区,农人多种瓜菜,既供自家食用,又可供出卖,是普遍的情形。郭家除种瓜外,也种各种菜。
(3)贸易。原平所种的瓜进入市场。《宋书·孝义传》载:大明七年(463),大旱,瓜渎不复通船,县官刘僧秀让人下渎水以通运瓜之船,原平拒绝了县官的好意,“步从他道往钱唐货卖”。据此,永兴县民所种之瓜,有相当部分被运往浙江对岸的钱唐去卖。
传文记郭世道“尝与人共于山阴市货物,误得一千钱,当时不觉,分背方悟”,乃“以己钱充数送还之”。原平也经常到市中货卖。传文云:
每出市卖物,人问几钱,裁言其半,如此积时,邑人皆共识悉,辄加本价与之,彼此相让,欲买者稍稍减价,要使微贱,然后取直。
出市卖物,就是到市场上卖自己生产的东西。郭世道到山阴市“货物”,也是去出卖自己家所产之物。《南齐书·孝义传》记会稽陈氏有三女,“遇岁饥,三女相率于西湖采菱,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陈氏三女将采摘的菱、蒪(莼)拿到市上货卖,以换取生活必需的食物等。又,诸暨东洿里的屠氏女,父母生病,移父母远住纻罗,“昼樵采,夜纺织,以供养”。(33)《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第1061—1062页。屠氏女所采之樵、纺织的布,也供货卖。
在所进行的这些交易中,钱的使用很普遍。刘宋孝武初年,周朗曾建议罢用金钱,“以谷帛为赏罚”。他说:“凡自淮以北,万匹为市;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亦不患其难也。今且听市至千钱以还者用钱,余皆用绢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34)《宋书》卷八二《周朗传》,第2297—2298页。周朗建议小宗买卖罢用金钱,而用绢布及米,亦即实物交换,只有达到千钱以上的买卖,才用钱。周朗的建议,正说明其时细民贸易普遍用钱。郭世道及其同伴到山阴市“货物”,误得一千钱,说明小宗买卖,也会超一千钱,周朗的建议,完全没有实行的可能。
综上,我们对郭家的生计状况,可以形成一些大致的认识:(1)郭家原本有自己的住宅,却并无田地。大概到郭原平时,郭家才开始买进田产,其所拥有的一块田,有数十亩,故其全部田产,或超过百亩。郭家所种植作物当以稻为主,但也当有麦菽等;瓜果等物是重要的经济作物。(2)郭世道与郭原平,都为人佣作。其时佣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日佣,即按日取直,大致相当于后世的短工;一是“十夫客”(或“士夫客”),应当是较长时间的雇佣,预付佣直,或一次性结清佣直,相当于后世的“长工”。郭氏父子为人佣作,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木工和营墓。(3)郭世道、郭原平父子经常前往永兴、山阴以及钱唐货物、卖瓜,买卖大都用钱结算。郭氏父子的佣直也大抵用钱结算,故原平可以在拿到日工的佣直后,在本里买米回家做饭。货物交换与钱的使用均非常普遍。
中古早期江南乡村的社会关系
郭家人口不多。世道的父亲两次结婚,只存活世道一个儿子。当父亲在世、世道婚后的郭家由世道父亲、继母与世道夫妻组成,共四口人。世道有两个儿子(原平及其弟)。世道死后,原平和继母、弟弟共同生活,其时原平当已成婚,若其弟未婚,也是四口人。原平有三子,在分家前,当是五口人。所以,世道、原平的家庭,大抵维持在四五口人的规模。
东晋南朝时期,各种原因导致江南地区的人口死亡率高。《宋书·孝义传》说郭世道妇生一男,“夫妻共议曰:‘勤身供养,力犹不足,若养此儿,则所费者大。’乃垂泣瘗之”。其时郭家尚无田产,仅靠佣力为生,无力同时养活儿子和母亲,故而放弃儿子。
贫穷和饥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家庭的规模。据《宋书·孝义传》载,会稽山阴县张迈等三人,各有一子,因“时岁饥俭,虑不相存,欲弃而不举”,赖严世期救助方得养成人。严世期的宗亲严弘、乡人潘伯等十五人,都因荒年饿死而留下孩幼。(35)《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67页。会稽山阴是南方富庶之区,遇饥岁荒年犹有如此众多之人饿死,其他地方只能更为残酷。因饥荒王彭父母双亡,只有兄弟二人相依为生。乌程吴逵“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只剩下吴逵夫妻二人。乌程属富庶之地,吴家一下子死十三口人,疾疫的打击不可谓不重。孙法宗,吴兴人,“父遇乱被害,尸骸不收,母、兄并饿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还。单身勤苦,霜行草宿,营办棺椁,造立冢墓,葬送母兄,俭而有礼。以父丧不测,于部境之内,寻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余年不获,乃缞绖,终身不娶,馈遗无所受”。(36)《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72—2473页。孙法宗本一家四口人,乱离之后,仅余法宗一人。
当农民家庭在动乱、灾疫面前无能为力时,村里地缘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钱唐县某里的范法先一家七口,同时疫死,“唯余法先,病又危笃,丧尸经月不收”,幸赖同里范叔孙“悉备棺器,亲为殡埋”。施渊夫父母、范苗父子,也都是范叔孙帮助营葬。“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丧没,亲邻畏远,莫敢营视。叔孙并殡葬,躬恤病者,并皆得全。”因此,“乡曲贵其义行,莫有呼其名者”。(37)《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73页。该里并不是范姓的单姓村落,范叔孙救济帮助的对象包括施、危二姓之人,其所构成的“乡曲”是地缘性社会,而非血缘性组织。
郭氏父子所生活的独枫里也是一个地缘性社会。《宋书·孝义传》评价郭氏仁厚,受到官府的表彰,其居里也因而改名“孝行里”,但郭氏并未建立起宗族,更未能形成宗族势力。传文中郭原平在父亲死后,“自起两间小屋,以为祠堂”,当是在墓地建立的供祭祀、守墓用的小屋,并非宗祠。
永兴人倪翼之,母亲丁氏,“少丧夫,性仁爱,遭年荒,分赠衣食给里中缺衣少食者,邻里求借,未尝违。同里陈穰父母死,孤单无亲戚,丁氏收养之,及长,为营婚娶。又同里王礼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阴,丁为买棺器,自往敛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断,村里比屋饥饿,丁自出盐米,计口分赋。同里左侨家露四丧,无以葬,丁为办塚槨。有三调不登者,代为输送”。(38)《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第1061页。倪翼之家所在的里,除倪姓外,还有陈、王、左等其他姓氏,并非血缘群体。丁氏抚育孤贫、救助寒弱、周济邻里,发挥着村里领袖的作用。
邻里互助对于贫穷人家具有重要意义。吴逵亲属皆尽,自己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他重病得瘳后,为亲人营葬,“邻里嘉其志义,葬日悉出赴助”。吴逵预支邻人夫直,葬毕,“众悉以施之”(都免除了他当作的夫工),“逵一无所受,皆佣力报答”。(39)《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68页。王彭兄弟父母亡,“乡里并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砖”。(40)《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70页。凡此,都说明邻里互助是形成地缘性社会的基础。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党”也发挥作用。《宋书·孝义传》记义兴许昭先事迹云:
叔父肇之,坐事系狱,七年不判。子侄二十许人,昭先家最贫薄,专独料诉,无日在家。饷馈肇之,莫非珍新,家产既尽,卖宅以充之。肇之诸子倦怠,昭先无有懈息,如是七载。尚书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释。昭先舅夫妻并疫病死亡,家贫无以送,昭先卖衣物以营殡葬。舅子三人并幼,赡护皆得成长。昭先父母皆老病,家无僮役,竭力致养,甘旨必从,宗党嘉其孝行。(41)《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75页。
许昭先叔父系狱,子侄二十许人,而由昭先家专独料诉,盖许氏家族共居,或者同一户头,并未析户。然传文称“昭先家最贫薄”,“昭先父母皆老病,家无僮役,竭力致养,甘旨必从,宗党嘉其孝行”,知许氏各家当分财异爨,组成一个家族。又,昭先出卖衣物营葬舅父舅母,并收养表弟三人,也说明其家庭经济独立。许昭先一家在许氏一族中“最贫薄”,许氏家族中的其他家庭应有僮役,义兴许氏是当地有势力的宗党。
结成宗党的家族一般地位较高。《晋书·隐逸传》载,会稽永兴人夏统(字仲御),“幼孤贫,养亲以孝闻,睦于兄弟”,“雅善谈论”,宗族劝之仕,谓之曰:“卿清亮质直,可作郡纲纪,与府朝接,自当显至,如何甘辛苦于山林,毕性命于海滨也!”(42)《晋书》卷九四《隐逸传》,第2428页。夏氏当是永兴土著的大族。《南齐书·孝义传》记封延伯出自渤海封氏,有学行,仕至豫州长史、带梁郡太守,以疾免,侨居东海,“三世同财,为北州所宗附”。萧齐建元三年(481),遣大使巡行天下,表彰孝义之家,“义兴陈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邵荣兴、文献叔八世同居。东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圣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谭弘宝、衡阳何弘、华阳阳黑头疎从四世同居,并共衣食”。(43)《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第1063页。综观累世同居的家族,都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与较高的社会地位,并非普通庶民人家。
因此,当时普通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地缘性的乡里组织,邻里互助构成其社会关系的基本内涵;只有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家,才形成同居共财的家族、宗党。
郭氏父子似乎并不热衷与士人、官府交往。传文记“原平由来不谒官长”,并举原平因事误为吏所录,县令不相谙悉,将加刑罚之事以为证明。原平与居住在永兴县的士人虽偶有来往,但并不密切。《宋书·孝义传》说:
高阳许瑶之居在永兴,罢建安郡丞还家,以绵一斤遗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复反者前后数十,瑶之乃自往曰:“今岁过寒,而建安绵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许瑶之为许询之后。《陈书·文学传》记有许亨,谓其为高阳新城人,“晋征士询之六世孙也。曾祖珪,历给事中,委桂阳太守,高尚其志,居永兴之究山,即询之所隐也”。(44)《陈书》卷三四《文学传》,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16页。则许家自许询时即居永兴县。许瑶之当与许珪同辈,应是许询的孙辈。许氏以治毛《诗》闻名,是著名的经学世家。许瑶之主动馈送礼物给郭原平,原平推让不受,盖以家境贫寒,不足与士人结交故。
传文还记载了另一个故事:蔡兴宗任会稽太守,对郭原平“深加贵异”,以私米馈原平,并下教道:“永兴郭原平世禀孝德,洞业储灵,深仁绝操,追风旷古,栖贞处约,华耈方严。”故饷以帐下米百斛。原平固让频烦,誓死不受。按:蔡兴宗任会稽太守,在明帝泰始五年(469)六月至后废帝泰豫元年(472)四月间。蔡氏颇重礼仪,《宋书·蔡兴宗传》记:“三吴旧有乡射礼,久不复修,兴宗行之,礼仪甚整。”(45)《宋书》卷五七《蔡廓传》附子《兴宗传》,第1726页。蔡兴宗馈米,皆当出于兴复礼教之旨。而原平拒绝:“府君若以吾义行邪,则无一介之善,不可滥荷此赐。若以其贫老邪,耋齿甚多,屡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原平没有配合太守兴复礼教的行动。在此之前,郭原平已被太守王僧朗举为孝廉,亦不就。甚至长子伯林被举为孝廉,次子灵馥受举为儒林祭酒,皆不就。按:自汉代以来,举孝廉即为庶民进身之要途,郡举孝廉即可补三署(五官署、左署、右署)郎。晋宋南朝,举孝廉后亦得为州郡吏。《宋书·百官志》谓:“江左以丹阳、吴、会稽、吴兴并大郡,岁各举二人。”(46)《宋书》卷四○《百官志》(下),第1364页。《通典·选举》说:“宋制,丹阳、吴、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各一人。凡州举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郭世道、原平、伯林,一门三代,皆被举为孝廉,均不就。
郭世道大概不识字,原平及其子灵馥则粗识文墨。泰始七年(471),会稽太守蔡兴宗试图举原平为太学博士,会兴宗薨,不果行。《晋书·职官志》谓:
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及江左初,减为九人。元帝末,增《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47)《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6页。
原平当然不能治《五经》,但原平既然被举为太学博士,至少识文断字。原平次子灵馥被举为儒林祭酒。这里的太学博士、儒林祭酒都只是荣誉性头衔,郭氏父子“皆不就”,但在乡里的社会地位因之提升,家庭规模渐次扩大,呈现出向家族发展的趋势。
南朝农民的赋役负担
传文称:“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骑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榜表闾门,蠲其税调,改所居独枫里为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袁愉,《校勘记》:“本书卷六四《裴松之传》作‘袁渝’,《建康实录》卷一二、《御览》卷一五七引《宋略》作‘袁瑜’。”《宋书·裴松之传》谓元嘉三年(426),分遣大使,巡行天下,“申令四方,周行邦邑”,“申述志诚,广询治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问所疾”,通直散骑常侍袁渝、司徒左司掾孔邈奉命巡行扬州。(48)《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第1860页。郭世道应当就在此时受到袁愉(渝)“旌举”,得到文帝的嘉奖。会稽太守孟顗随后察举郭世道为孝廉。所以,郭原平称郭家“见异先朝,蒙褒赞之赏”,即是指榜表闾门、蠲免税调以及察举孝廉三事,而其中最要者显然是蠲免税调。
蠲免税调役,是汉晋以来朝廷表彰孝悌品行高尚之人的重要恩典。如汉惠帝四年(前191)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49)《汉书》卷二《惠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0页。南朝彰表孝义,多蠲免税调或租布。据《宋书·孝义传》载,除郭氏外,贾恩得“蠲租布三世”;严世期得“复其身徭役,蠲租税十年”;潘综得“蠲租布三世”;张进之得“在所蠲其徭役”;王彭得“蠲租布三世”;余觉民得“蠲租布,赐其母谷百斛”。(50)《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63、2467、2470、2471、2476页。《南齐书·孝义传》记载公孙僧远等二十三人,“并表门闾,蠲租税”;韩康伯、孙淡、倪翼之得“蠲租税”;蒋俊之得“蠲租赋”;乘公济二子得“复徭役”;陈玄子、邵荣兴等累世同居者,并得“蠲租税”;王续祖、郝道福等累世同爨,得“蠲调役”。(51)《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第1059—1063页。《南史·孝义传》谓元嘉七年(430),南豫州所统西阳县人董阳三世同居,“外无异门,内无异烟”,诏命“蠲一门租布”;益州梓潼人张楚,得“蠲租布三世”。(52)《南史》卷七三《孝义传》(上),第1799、1805页。其中租是田租,即田税;布是调,即户调;役是徭役。东晋南朝时期,编户齐民的赋役负担,主要就是田税、户调和徭役三项。义熙七年(411),刘裕秉政,在江陵下书,要求“凡租税调役,悉以见户为正”。(53)《宋书》卷二《武帝纪》(中),第31页。齐建元四年(482)正月诏书称:“建元以来战亡,赏蠲租布三十年,杂役十年。”战亡者赏,当是指其家户得免纳租布三十年,复除杂役十年。(54)《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第40页。显然,租税、户调、徭役都以户为单位征发。受表彰的孝义多得蠲免租(税)布(调),即指蠲免全户乃至一门的租布(期限则由十年至三世不等);复免徭役则一般是免除其自身个人的徭役。《宋书·孝义传》郭世道受旌表后,得蠲税调,徭役却未得复除。那么,南朝普通编户齐民的赋役负担究竟若何?
我们先来看南朝编户的徭役负担。元嘉六年(429),卫将军王弘上书论役法,说“旧制”(晋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盖“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然“考之见事,犹或未尽”,而“今皇化惟新,四方无事,役召之宜,应存乎消息”,故建议“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宋文帝从之。(55)《宋书》卷四二《王弘传》,第1433—1434页。盖晋宋之制,本以十三岁半役、十六岁全役,至是改为十五岁半役、十七岁全役。《宋书·自序》载元嘉中参征虏军事沈亮启文帝陈西府事,谓其时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而“书制休老以六十为限,役少以十五为制,若力不周务,故当粗存优减”。(56)《宋书》卷一○○《自序》,第2689页。此后,根据制度确定民从十五岁应半役(少役),十七岁应全役,六十岁免役。换言之,普通编户齐民,一生中有四十五年当应征从役。相比《晋书·食货志》所载晋制:“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57)《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90页。知刘宋时期的应役期较之两晋,实有所缩短。
《南齐书·海陵王纪》载:南齐延兴元年(494)九月,因晋安王子懋起兵,内外纂严。十月癸巳的诏书称:“正厨诸役,旧出州郡,征吏民以应其数,公获二旬,私累数朔。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以助淮戍,劳扰为烦,抑亦苞苴是育。今并可长停,别量所出。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58)《南齐书》卷五《海陵王纪》,第85页。《隋书·食货志》述东晋制度,谓:“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59)《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748—749页。海陵王诏书所说的“正厨诸役”“公获二旬”,当即《隋书·食货志》所说每岁二十日之役。正厨诸役由州郡征发,役期每年二旬,但役人来往途中颇费时日,故诏称“私累数朔”。村长、路都,当是乡里役职。诸县征发村长、路都到县城轮值,防守县城,称为“防城直县”。换言之,人丁必须应征的役,包括由州郡征发的正厨诸役和由县邑征发的村长、路都之役。其中,正厨诸役需要离开家乡应役,虽然役期每年只有二十日,但人丁应役,往来则需数月,故负担最重。
虽然制度规定出自州郡的“正厨诸役”每年二十日,但遇有战事发生,按规定征发的役丁不敷使用,就不得不临时加征。如元嘉二十七年(450)秋,宋文帝大起军旅,进行第二次北伐,“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暂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对此,胡三省注称:“三五者,三丁发其一,五丁发其二。”(60)《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纪》七,第4011—4012页。六州民丁,按三丁取一、五丁取二的比例,征发从军,以补兵力不足。沈攸之就在这一年应征入伍。(61)《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第2107页。攸之虽出自吴兴贵族沈氏,然“出自莱亩,寂寥累世”,其时已是普通庶民,故应征从役。《宋书·孝义传》也载:大明五年(461),“发三五丁”,彭城人孙棘弟弟孙萨应从役,但“坐违期不至,依制,军法,人身付狱”,“应依法受戮”。(62)《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76—2477页。孙萨的身份是“甿隶”,应征违期,根据规定要以军法从事,其所应之役也是兵役。《南史·齐本纪》废帝(东昏侯)纪事末综述云:
上自永元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扬、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63)《南史》卷五《齐本纪》(下),第156页。
每遇北魏来伐,或者南朝发生内乱,扬、徐二州人丁都要三人取二,即临时征发兵役。梁武帝普通中(520—526),郭祖深上书言事,谓:
梁兴以来,发人征役,号为三五。及投募将客,主将无恩,存衅失理,多有物故,辄刺叛亡。或有身殒战场,而名在叛目,监符下讨,称为逋叛,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则合村皆空。(64)《南史》卷七○《循吏传》,第1722页。
郭祖深所说“投募将客”,当指投附及招募而来的流民帅所领部曲。郭祖深在此前述及“勋人投化”被南朝任用之后,“皆募部曲”,而“扬、徐之人,逼以众役,多投其募,利其货物”。(65)《南史》卷七○《循吏传》,第1722页。这就是所谓投募将客。萧梁军队,主要由此种“投募将客”构成。若“投募将客”不足,就要“录质家丁”。《宋书·明帝纪》泰始三年(467)五月丙辰,“宣太后崇宁陵禁内坟屋瘗迁徙者,给葬直,蠲复家丁”。(66)《宋书》卷八《明帝纪》,第177页。其所蠲复的“家丁”,当即按家户征发的丁,亦即三五民丁之丁。因此,郭祖深所言“录质家丁”,也就是征用役丁以补充叛亡身殒的“将客”。南朝普通民户都应征服兵役。
上引《隋书·食货志》谓晋时“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宋孝武初年,江州刺史臧质反叛,“豫章太守任荟之、临川内史刘怀之、鄱阳太守杜仲儒并为尽力,发遣郡丁,并送粮运”。(67)《宋书》卷七四《臧质传》,第2101页。所发遣的郡丁,也即应征从事运输的民丁。元徽元年(473)九月壬午诏书称:“国赋氓税,盖有恒品,往属戎难,务先军实,征课之宜,或乖昔准。湘、江二州,粮运偏积,调役既繁,庶徒弥扰。因循权政,容有未革,民单力弊,岁月愈甚。”(68)《宋书》卷九《后废帝纪》,第198—199页。这里所说的“调役”,当即运输之役。齐明帝建武四年(497)正月壬寅诏:“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69)《南齐书》卷六《明帝纪》,第95页。“调役”与“夫役”并称,当分别指运役与工役。
工役(夫役)由郡县征发。《南齐书·王敬则传》记萧齐武帝永明初年,王敬则为会稽太守,“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上许之”。萧子良对此表示反对,说:
臣昔忝会稽,粗闲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桥路须通,均夫订直,民自为用。若甲分毁坏,则年一修改;若乙限坚完,则终岁无役。今郡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致令塘路崩芜,湖源泄散,害民损政,实此为剧。(70)《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第538—539页。
无论士庶都要参与修筑维护塘陂。塘陂之役则根据需要征发,并非固定役使。“均夫订直,民自为用”,盖由民众自发确定夫工的价值(“夫直”),根据工程量确定需用的夫工。相关士庶,亦可按分配的夫工数,根据夫直纳钱,代役,萧子良谓“塘工所上,本不入官”,当即指此。王敬则将维修塘陂的夫工全部折算为钱,由郡县征收,并输纳台库。塘丁盖按户征发,折征夫直后,亦按户征收,故萧子良将之比为户调。萧子良以此举害民损政,建议“塘丁一条,宜还复旧”,然未被采纳。

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是后频年水灾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税米,空悬五十余万斛,尚书褚裒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73)《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第792页。
咸和五年(330),亩税米三升。若仍以每户丁男、次丁男、丁女各一,占田九十五亩计算,则当纳二斛八斗。至哀帝时(362—364),亩收二升。太元二年(377),不再度田收租,而改以口税三斛。至八年,增为口五石。这里的口税三斛与五石,仍指田租。综上,从咸和五年到太元二年(330—377),是度田收税,即履亩征税,税率从亩三升降至二升。太元以后,按口征税米,口三斛至五石。这里的“口”,当是以丁男一口为标准。盖丁男一口,课五十亩,亩收一石,取十税一,故税五石。丁女、次丁男等,则当折合丁男之口。所以,田租(田税)实际上也是按每户当折合的口数征纳。综上,自东晋太元以后,田税、户调按户征发。以标准的丁男户包括丁男一口、丁女一口、次丁男一口计算,每户当纳税九石五斗,调绢三匹、绵三斤。
刘宋时期,制度并用计口输税与度田履税两种。宋孝武初年,周朗上书言事:
又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岂有剥善害民,禁衣恶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农,则宜务削兹法。(74)《宋书》卷八二《周朗传》,第2298页。
根据资产(主要包括田、宅、桑三项)征税,应当是度田履税的扩展;“计人输税”,当即按口纳租,也就是东晋后期制度的“口五石”。根据周朗之说,按照宋的制度规定,应当是计人输税,只是在实行过程中,也采用度田计赀输税之法。《宋书·良吏传》记元嘉三年(426),“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时任始兴太守徐豁上表陈三事,其一曰:
郡大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米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且十三岁儿,未堪田作,或是单迥,无相兼通,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或乃断截支体,产子不养,户口岁减,实此之由。谓宜更量课限,使得存立。今若减其米课,虽有交损,考之将来,理有深益。(75)《宋书》卷九二《良吏传》,第2488页。
“郡大田,武吏”,当是指在郡公田上从事军屯的兵吏。男十六岁输米,十三至十五岁半输,正符合晋宋以来的相关规定。一人课米六十斛,绝无可能输纳,或当作“六斛”(大致相当于六石)。“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是以户为单位、按户内人丁数交纳田税。
计丁课米,当是刘宋(乃至南朝)田税的基本原则。徐豁又述及始兴郡境内的俚民,说:
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寻此县自不出银,又俚民皆巢居鸟语,不闲货易之宜,每至买银,为损已甚。又称两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课甚轻,民以所输为剧。今若听计丁课米,公私兼利。(76)《宋书》卷九二《良吏传》,第2488—2489页。
中宿县的俚民本来是计丁课银,徐豁建议改为计丁课米,其原则一致。萧齐永明二年(484),萧子良说:
建元初,狡虏游魂,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有质卖妻儿,以充此限,道路愁穷,不可闻见。所逋尚多,收上事绝,臣登具启闻,即蒙蠲原。而此年租课,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扰民,实自弊国。(77)《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第539页。
丁税,当即按丁交纳的租课(田税)。丁税一千,当由“口五石”折合而来。永明六年(488),顾宪之行会稽郡事,上书言事,称:
山阴一县,课户二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裁萌,千糵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贵举责,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其可得乎?(78)《南齐书》卷四六《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第894—895页。
近半数民户,赀不满三千。若以家有丁男、丁女、次丁男各一计算,丁税一千,则户纳税当近二千。再加上户调,则倾家荡产,亦不足以纳税调。“三五属官”,当指官府征发三五丁;“百端输调”,是指交纳户调要用多端布帛。贫极的“露户役民”既要按户赀(主要是田、宅)纳租(田税),又要纳户调,应征服役。
《隋书·食货志》综述南朝税课,谓:“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79)《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第748页。租米五石,当即按“口五石”征收的田税。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则当属于户调。“各二丈”当有误,应为“各二匹”。据上引晋户调式,晋时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绢一匹,一般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布、绢各二丈,合计方为一匹。《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461)十二月甲戌,“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80)《宋书》卷六《孝武帝纪》,第139页。布四匹,显然是绢、布各二匹所改。故刘宋时户调,当以丁男绢布各二匹或布四匹为是。此外,丁男还须纳丝、绵合计十一两。两相比较,刘宋时的户调较之晋时,大致持平而略重(以一匹二十五两计,合十一两丝绵,当有三斤六两,较晋时绵三斤,多出六两)。
布、绢、丝、绵皆可折钱交纳。萧齐永明间,萧子良回顾道:
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于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所以每欲优民,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余,其四民所送,犹依旧制。昔为刻上,今为刻下,氓庶空俭,岂不由之。(81)《南齐书》卷二六《王敬则传》,第539页。
据萧子良所言,永初中,官布一匹直千钱,民间输布,折为九百。丁男户的户调,绢、布各二匹,至少要四千钱。再加上丝绵,当在五千钱以上。其时丁税一千,户调负担,远超过田税。元嘉中,布价转低,一束(十匹)六千钱,匹值六百;民户输布一匹,则仅折合五百钱。至永明间,入官好布,仅折合百余钱。民户纳调,仍以原来高价下折合的总钱数为依据,自然需要交纳更多的布。《宋书·沈怀文传》记载,大明中,“斋库上绢,年调钜万匹,绵亦称此。期限严峻,民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亦三四百,贫者卖妻儿,甚者或自缢死”。(82)《宋书》卷八二《沈怀文传》,第2309页。若以丁男户纳绢布各二匹、丝绵十一两计算,至少折合钱一万一千三百至一万六千四百。
郭世道于元嘉四年受到旌表,蠲免税调。其时物价较平稳。如果不蠲免,以郭家有丁男、丁女、次丁男(世道、妻及其子原平)各一口计算,郭家至少应纳田税九石五斗,调绢布八匹、丝绵二斤,折合钱当在一万六千钱上下。郭世道过世后,原平有三子,税调又在不断增加,若不获得蠲免,其应纳的税调或当在三万钱以上。因得到蠲免,郭家每年可以省下这笔钱。原平能够买下数十亩田地,在很大程度上应是获得蠲免税调的缘故。
中古早期江南的农民及其生活
《宋书·孝义传》论曰:“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83)《宋书》卷九一《孝义传》,第2479页。郭世道、原平父子,即出自沟畎之孝义的典型代表。因此,郭氏父子不仅是“被编制”的农民,而且是“被同化”的农民。他们已经自觉地认同王朝国家所宣扬的道德伦理,其言行也得到王朝国家的高度认可。郭氏父子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地位实际上也处于上升状态。通过对《宋书·孝义传》所记郭世道、原平父子事迹的释读,我们得以窥知中古早期普通农民家庭的部分生活图景:
(1)郭世道、原平一家生活的地理空间,以其在永兴县城附近乡村的住宅为中心,通过浦阳江、浙江水、瓜渎等水道,与会稽郡治山阴县、钱唐县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相联系,而且浦阳江、浙江水等河流上已建立起码头设施,通航条件较好,郭家等普通农民均可利用四通八达的水网,来往于山阴、钱唐与永兴之间。
(2)郭家本没有田地,主要靠佣作为生。郭氏父子都善木工,后郭原平又学会营墓。佣作主要有日佣(散夫)和十夫客(士夫客)两种类型,前者当是短工,后者大致相当于长工。郭家在得以免除税调后,每年可以省下至少万余钱,故得以渐次买到数十亩田地。其田地当以稻作为主,但也兼种麦、菽、瓜、菜。郭家经常往永兴、山阴、钱唐的市“货物”,并将所产的瓜等物经水道运往钱唐等地。在各种贸易活动中,广泛地使用钱。
(3)郭世道、原平两代的家庭,大抵维持在四五口人的规模。受到经济条件、赋役负担、社会动乱、灾害疾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古早期普通民户的家庭规模普遍较小,死亡率较高。中古早期江南乡村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阶层差异:普通的乡村民户,在遭遇动乱、灾疫时,主要依靠邻里互助渡难关;其行为品德,也主要由乡曲邻人予以评价。所以,普通乡村民户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以村里为基本单位的地缘性关系。经济条件较好、政治与文化地位较高的地方士人或官员家庭,才会同居甚至共财,形成家族,乃至宗党。两种社会关系之间比较疏离、隔膜,甚至表现出某种对立。少数普通民户(如郭家),随着其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也表现出向家族发展的倾向。
(4)郭家因得到朝廷表彰,得蠲免税调(租布),然未得复除徭役。刘宋时的编户齐民,十五岁(或十三岁)时应半役,十七岁(或十六岁)应全役,至六十岁(或六十六岁)免役。正役役期以每年二十天为原则,实际执行的役期当远超此数。除正役外,民丁还会被临时征发,去前线服兵役,或从事运输、施工等劳役;也会受郡县征发,修护塘坡、沟渠、路桥等,或者在本县邑充当村长、路都,参与防城、直县。其赋税负担,则主要包括田租(税)与户调两项。田税的征收,有计口输税、度田履税两种方式,而以计丁课米为基本原则。户调亦以户为单位交纳。刘宋初年,丁男一口,须交纳的税、调不低于六千钱。若以一户有丁男、丁女、次丁男各一口计算,一户人家的税调负担约在钱一万一千至一万六千之间。
透过这些图景,我们注意到:中古早期江南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被纳入较为广泛的区域经济与政治社会网络之中。他们在从事农耕的同时,普遍开展多种经营(包括从事木工、营墓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种植经济作物等),并通过佣工、采摘捕捞、纺丝织布等,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弥补生活之不足。他们将自己的产出送到市场货卖,并以货币方式结算夫值(佣薪),与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中古时期江南地区的农民,并不是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其所生存的经济环境,也并非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同时,通过乡里与赋役制度,他们也被纳入严密的政府控制体系之中,作为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交纳田租户调,应征从役,并接受王朝国家的教化。当遭遇天灾人祸时,他们很少得到政府的救助,而主要依靠邻里互助,以渡过难关。所以,主要表现为地域联系的村、里组织是其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质言之,中古早期江南地区农民生活的世界,可以区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作为生产生活单位的家庭,二是作为互助单位的村里,三是作为市场网络的区域经济体系,四是作为控制与管理体制的郡县乡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