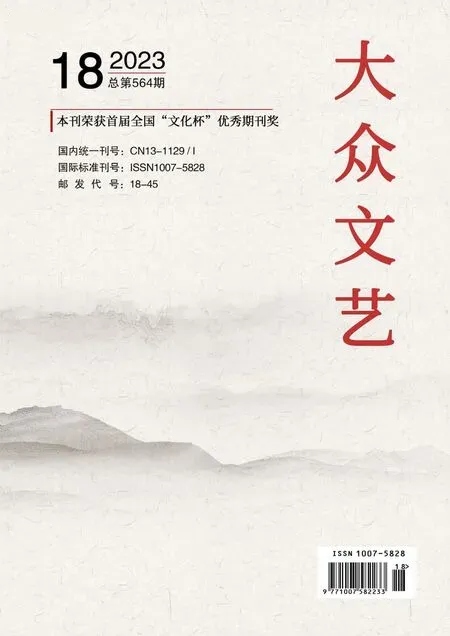“琴僧”对琴学思想发展影响述略*
2023-10-13徐靖松
徐靖松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 225100)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涵盖建筑、美术、书法、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工艺美术等诸多领域,参与佛教艺术的群体有“出家二众”“在家二众”及“佛教四众外围没有信仰或信仰其他宗教的众多研究者及民间从事佛教艺术活动的人群”[1]3-18。在琴学领域,早在唐代就有从事琴乐活动的僧人的记录,但在传统的琴学思想中,琴人群体长期对佛教及“出家二众”(主要指“琴僧”)持明确排斥态度,如田芝翁《太古遗音》有云:“琴本中国贤人君子养性修身之乐,非蛮貊之邦而有也,故丧门不宜于琴。”[2]84-86但从琴学思想发展史来看,佛教思想一直以来都对琴学思想有所渗透,可见“琴”“佛教”与“僧”之关系源流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关于古代琴僧的历史述略,司冰琳在其《中国古代琴僧及其琴学贡献》一文中已有清晰的论述[3]15-17,本文不再赘述。但值得注意的是,琴僧这一群体的诞生是否意味着佛教思想开始影响古琴艺术的发展?换言之,琴僧群体的出现对琴学思想发展的走向影响如何?此问题尚值得探讨。笔者认为,琴僧群体的琴学思想并不能与佛禅琴学思想画等号,对此问题的梳理不能脱离对琴僧群体发展源流中诸多现象的分析。
一、琴僧与琴学关系源流
唐宋以来,禅悦之风盛行。在佛学氛围相对浓厚的时代背景下,唐代出现目前关于“琴僧”的最早文字记录[3]15,但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中仅有“琴僧”弹琴的零星记载,如《听蜀僧浚弹琴》《听颖师弹琴》等,“琴僧”这一时期在琴学思想上的贡献并无明确文字记述。宋元以降,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佛学风气更加高涨,“琴僧”这一群体亦因之呈现出师徒相传的现象,“贯穿着北宋一百多年中,有一个琴僧系统。他们师徒相传、人才辈出,始终在琴界有着重要地位”[4]153。琴僧群体的不断壮大得益于唐宋以来浓厚的佛学氛围,这一时期的僧人文化程度较高,僧人大多是以文人的身份心态参与文艺活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诗僧、书僧、画僧,并在其领域都有所建树,琴僧的出现是时代背景下催生出的必然产物。反观之,这一时期诗僧、画僧等在其从事领域的艺术实践中多多少少践行了佛教的思想主张,从“形而上”的层面影响了其艺术门类的发展,譬如文学领域的意境理论、书画领域的留白理论等。而这一时期,琴僧在琴学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形而下”的“技法”层面,譬如则全的《则全和尚节奏指法》、居月的《琴曲谱录》《琴书类聚》《僧居月制琴》《僧居月造弦法》等,这些论著在琴史上虽具有很大的琴学贡献,但这些琴论大多是对指法、节奏、琴器这一层面的总结和归纳,并未从佛教思想的层面对琴学理论提出强有力的观点和见解,这一时期琴僧琴学贡献的特点是“近乎‘技’而远乎‘道’”;与之相对,这一时期反而是成玉磵这一非“出家二众”的琴人,在琴史上首次提出了“攻琴如参禅”这一具有佛教思想色彩的琴学理论。此外,欧阳修、苏轼等文人群体亦对琴学理论有禅理的思考,如苏轼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5]2534具有以禅喻诗,以诗写琴的特征。这说明宋元时期对琴学理论的佛学书写主要由“在家二众”完成,琴僧则仅仅是兼具“琴人”与“僧人”双重身份性质的群体,且这一群体从佛教思想层面对琴学发展作出的贡献不及“在家二众”。
明清以降,心学盛行,“三教合流”的趋势愈加明显,“文人士大夫与僧人的交往、唱和、弹琴、作诗,都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3]32,“琴僧”群体的数量更为庞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保守琴学思想的影响之下,这一时期“琴人中有一部分士大夫对僧人弹琴所持否定的态度”[3]59,但局部的排斥并不能阻挡琴界对琴僧群体接纳的趋势,琴僧群体的日益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明代的琴僧数量虽多,但这一时期同宋元一样,在琴学理论上卓有建树的琴僧并不多。明代的琴僧以东渡遗民东皋禅师为代表。但就东皋禅师的琴乐主张与审美偏好来看,可以看出其身份虽是佛教徒,但其践行的音乐主张仍然是儒家倡导的音乐观。吴文光先生对此问题有翔实讨论,其认为“无论是以儒见佛,还是从佛入儒,都可以说明在东皋的禅学音乐观中儒学所占的比重和地位。”[6]从东皋禅师的《东皋琴谱》载录的琴曲来看,近70首琴曲中仅有一首《释谈章》为佛教琴曲,其他大多为琴歌,具有浓厚的入世情怀,可见东皋禅师的琴乐观念受儒家思想影响更为深刻。明代的琴僧数量虽多,但有突出琴学贡献者仅有东皋禅师等寥寥数人,且明代琴僧从佛学角度对琴学进行理论书写者更不见其人。同宋元一样,明代对琴学理论的佛学书写亦主要由“在家二众”完成。这一时期琴学理论的佛学书写仍是由“在家二众”完成。如李贽在禅宗思想影响下提出“声音之道可与禅通”的命题,钱棻在《大还阁琴谱》的序文中“空界生声,情界生音”“以笔墨求画则失画,以义学求禅则失禅”“果可语言文字取乎?青山幸为我再下一转语。”[7]310等具有禅宗思辨色彩的言论,均说明这一观点。
有清一代,琴学重心由虞山派转移到广陵派,但较之前不同的是,由于清代扬州地区经济富庶,思想包容开放,再加之扬州佛寺林立,信徒众多,具有浓郁的佛学氛围,广陵琴派对琴僧则持接纳的态度。在广陵琴学源流之中,琴僧系统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清中叶以后,琴僧与居士一脉成为广陵琴派发展的中坚力量。从清代琴学重镇——广陵琴派的谱本来看,琴界的“排佛”思想仍有遗存,如《孔毓圻序》:
甚且和以人声,俚歌梵呗,阑入其中,名为雅而实流于郑。譬诸儒者不儒其行而儒其服,其得谓之儒矣乎?[8]12
孔毓圻作为孔子后人,袭第六十七世衍圣公,自然要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但除孔氏有此论外,广陵琴学谱本中几乎再无相似观点,这说明广陵琴人群体已经很少有人在主观意愿上排斥琴僧群了。与孔氏之论相反的是,广陵琴派谱系中,出现了清晰的琴僧传承脉络。据《扬州画舫录·小秦淮录》载:
武生吴仕柏,居董子祠,善鼓琴,日与徐锦堂、沈江门、吴重光、僧宝月游,夜则操缦,三更弗缀。[9]207
这是关于广陵琴人与琴僧的最早文献记载。吴灴、徐锦堂,沈江门、吴重光皆善操缦,虽然目前没有充足的史料证明僧宝月琴艺如何以及其师承何处,但就他们四人“夜则操缦,三更弗缀”的情形来看,宝月和尚操缦风格也很可能受徐锦堂与吴灴的广陵琴风影响并与之相近。广陵琴派对于琴僧以及佛家思想的明确接纳肇始于吴灴与其《自远堂琴谱》时期。吴灴是当时广陵琴派的集大成者,他弟子众多,且僧俗皆传,自吴灴开始,琴僧群体开始正式参与到广陵琴派的谱系传承中来,并且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同源二流的发展脉络,图示如下:

广陵琴学僧俗传承谱系[10]
二、广陵“琴僧”对琴学发展的意义
清代广陵琴派的“琴僧”与前代不同,开始“援佛入琴”,从琴曲创作与理论书写两方面对琴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第一,广陵琴僧从音乐题材的角度对琴乐进行扩充,大胆创作、移植、改编佛教题材的琴乐。在琴乐发展的历程中,由于“排佛思想”的限制,古琴艺术中几乎看不到佛教音乐的踪影。目前,最早可见的佛教题材琴曲为《释谈章》,载录于《三教同声》(1592年刊)谱,其曲为佛咒移植,后被删节为《普庵咒》。除《释谈章》(《普庵咒》)之外,佛教题材的古琴音乐另有琴曲《色空诀》,该曲见于《太音希声》(1625年刊)谱,该曲词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该曲的音乐为作者自己根据吟诵的调子创作,但该曲仅有《大音希声》一谱收录,且流传度不高,实无多少影响。可见在广陵琴僧扩充佛教琴曲之前,与佛教题材相关的琴曲仅有《释谈章》(《普庵咒》)《色空诀》寥寥几曲。
广陵琴僧释空尘在其琴乐实践中创作、改编、移植了多首与佛教相关的琴乐。据《枯木禅琴谱》,该谱收录的三十二首琴曲中,除去二十五首广陵派传统曲目,还有七首释空尘自己创作的琴曲:《独鹤与飞》《云水吟》《那罗法曲》《枯木吟》《思贤操》《怀古吟》和《莲社引》,除《思贤操》与《怀古曲》外,其余五首琴曲均与佛教相关。此五首琴曲中,《莲社引》为《归去来曲》原调,释空尘对其改编了歌词,曲词中不乏“万法俱寂,一真独存”[11]144此类的禅语。《那罗法曲》为释空尘根据北京旃檀寺喇嘛吟诵的梵呗所移植:“闲步旃檀寺,听喇嘛齐歌梵呗,音声清和……而后抚弦和之,得谱成曲”[11]139,此曲母体即是佛教梵呗。《独鹤与飞》《枯木吟》《云水吟》三首琴曲为释空尘根据自己多年的佛法体悟所创作,各曲均有不同的禅学旨向,在音乐上均有明显的禅悟意味,是典型的佛教题材琴曲。广陵琴僧释空尘的这一琴乐实践一方面弥补了传统琴曲佛教题材琴乐数量少的缺憾,另一方面为后世琴人积极开拓琴乐的内容提供了参考的模范,其佛曲创作对古琴音乐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广陵琴僧从佛教思想特别是禅宗思想的角度出发,对琴学作出理论书写,尤其是对“琴禅论”的阐释,具有一定的理论范式意义。以《枯木禅琴谱》为例,该谱提出了“以琴说法”的主张。释竹禅从本体论角度在序文为“以琴说法”理论的可行性作出解释:
大道无相,闻声而入。衣钵流传,因人说法。
今云闲上人,深悟琴学三昧,其住世行道,得教外别传之旨,更于琴中音律指法,究竟精妙……上人所授可谓共命之学,两头一音。复于京都聚首,以手著琴曲出示,爰题“以琴说法”四字,不异禅宗之有语录流传,以共同好云耳。[8]213
禅宗讲究“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对佛法的把握不能依赖语言文字,要通过“顿悟”的方法论实现“见性成佛”的目的。琴乐作为一种音乐艺术,亦“不立文字”,在表情达意上具有抽象性,即其所云之“大道无相,闻声而入”,此为琴乐与禅宗同构性之一。再者,古琴音乐因其特殊性往往晦涩难懂,琴乐活动的参与者对琴曲的理解亦需通过“顿悟”性质的方法论来达成,此为琴乐与禅宗同构性之二。基于此,竹禅认为释空尘同时对两个“共命”之学有深厚的造诣,其将禅学与琴学相结合的实践需赖以“以琴说法”这一琴乐功能指向来实现。对于此论,释德辉与之相同,并提出了“合琴与禅为一致”[8]217的主张。释空尘在其自序中,对“以琴说法”的合理性亦做了阐释:
而我教中之蒲团禅板何非修身养性之道?证之琴德,奚有二哉。自梵僧居月善琴,继以颖诗、聪师、维公、义公,咸以琴理喻禅,见于旧简者不可数计。[8]224
释空尘与欧阳述与释竹禅的琴乐功能论观点相一致,认为禅宗与琴乐均有修身养性的功能。同时,其从功能论角度对“儒释之辩”的问题进行调和,即琴乐既能够“以助治理”,亦能够“以琴理喻禅”,二者是不矛盾的。释空尘将古琴作为参禅悟道的工具,并以之弘扬佛法,将“以琴说法”从实践上开辟为“琴禅论”思想中新的功能指向。由此,可视《枯木禅琴谱》中“以琴说法”的琴禅论思想是对北宋成玉磵“攻琴如参禅”琴禅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成玉磵在其《琴论》中对“攻琴如参禅”的阐释如下:
攻琴如参禅,岁月磨炼,瞥然省悟,则无所不通。纵横妙用,而尝若有馀,至于未悟,虽用力寻求,终无妙处。[12]207
成氏此论强调禅学对于习琴的方法论意义,援“顿悟”之方法入琴学,高扬琴之“妙”境。《枯木禅琴谱》中“以琴说法”的琴学主张则是在此基础上,扩充了琴禅论思想的功能论意义,如徐熙在序文中所论:“琴以谱传,禅从琴寄。作一花以供养,结缘瞿夷;比半果以研磨,功成阿育”[8]200,“以琴说法”的主张,将古琴音乐“律身”“修心”的功能进一步开拓出“传法”的功能,实现琴乐由“渡己”到“渡人”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以琴说法”的功能并非传统儒家琴学观念中“教化”功能的变体,前者以“顿悟”为方法论,强调审美主体自我意识的反省及对真如佛性的关照,重心在审美主体的个性上,是超脱的;后者则强调通过琴乐培养审美主体的儒家文化语境中的标准人格,重心在对伦理秩序的服从,二者是有本质不同的。可见,“以琴说法”的功能论主张乃是《枯木禅琴谱》琴禅论思想的一大贡献。
要之,“琴人”“文人”“僧人”以及“琴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清代之前,“琴僧”往往以“非僧人”的心态参与琴乐活动,而诸多文人群体则以佛禅思想为指导,对琴学思想进行佛学书写,“琴”与“僧”的结合并不意味着佛学思想对琴学思想的渗透。而自广陵琴派对琴僧群体接纳之后,琴僧开始实质性地将佛学思想援入琴学思想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大胆扩充了佛教题材的琴曲,另一方面发展了“攻琴如参禅”的思想,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以琴说法”。从主观上对僧人群体的接纳,到琴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佛教琴谱《枯木禅琴谱》的诞生,可见清代末期广陵琴僧的琴学实践真正意义在琴学领域实现了“琴”“僧”“论”三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