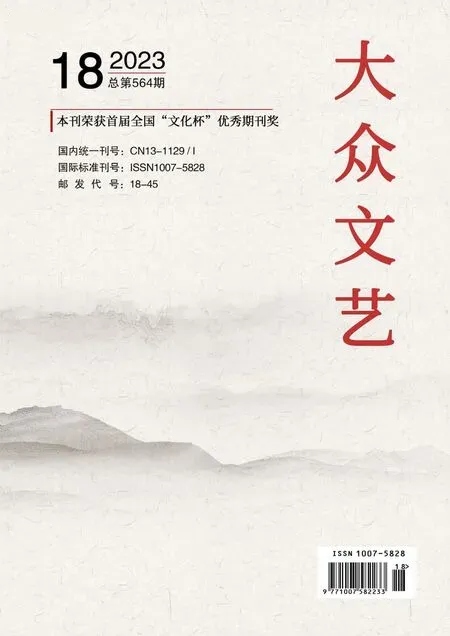“宫崎骏现象”:幻想王国与现实关怀
2023-11-15李尤
李 尤
(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广西南宁 530031)
八十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来,宫崎骏的动画作品风靡世界,受到全球观众的热烈追捧,他所领衔的吉卜力工作室也崛起为足以与好莱坞的迪士尼分庭抗礼的动画王国,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就像人们常常用“村上春树现象”“渡边淳一”现象来形容他们作品的广泛流行一样,宫崎骏受关注的程度无疑也是现象级的(毕竟,《千与千寻》至今保持日本电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观看宫崎骏的影片,我们可以徜徉在他精心打造的幻想王国里,插上想象的翅膀恣意翱翔。与此同时,宫崎骏对民族、历史乃至全人类生存境况充满忧患意识的观照又把我们拉回地面,让我们睁大双眼直面身处的世界。本文就从幻想与现实关怀这两个维度出发,以日本现代史为背景,探讨宫崎骏作品的独特魅力与“宫崎骏现象”的文化内涵。
一、盛世危言与乌托邦
八十年代的日本,达到了其战后崛起的顶峰。在东京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其总值是当时世界股票市场的40%以上,一些统计甚至表明,东京市总地产价值已经高于整个美国的房地产价[1]。这一时期,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傅高义的著作《日本第一》在日本畅销,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日本有史以来最畅销的非小说类翻译作品。总之,八十年代的日本正逢盛世,整个民族显得生机勃勃,进取心和自我满足几乎膨胀到了傲慢的边缘。
从这样的背景出发,《风之谷》(1984)显得相当不合时宜:影片充满了悲观的情绪,甚至是对人类的厌恶。甫一开场,浓浓的末世气息就扑面而来,人类文明早已被虫族毁灭,快速扩散的“腐海”蚕食着硕果仅存的人类家园。这种对灾难的想象贯穿宫崎骏的多部作品。而《风之谷》中的腐海无疑是对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的一种投射。早在50年代,伴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起飞,出现了一连串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水俣和新潟发生的水银中毒,富山县发生的镉中毒,三重县发生的空气污染引发的哮喘,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四大公害病。在70年代,虽然法庭对上述公害病的案例做出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判决,使政府及企业担负赔偿责任,但类似的问题仍然像不时飘过头顶的乌云,给日本平民的生活笼罩上一层阴影,甚至直至近年仍然不时出现在公众视野中。2016年上映的原一男导演的纪录片《日本国vs泉南石棉村》讲述的就是泉南地区罹患肺病的石棉工人对政府责任的追究。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影像作品中对灾难的想象或许植根于日本人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日本列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火山活动、地震和海啸频发,地震的年爆发率最高达到1500次,从20世纪至今,就发生过三次严重的地震[2]。这种对自然灾害的恐惧与危机感,深刻影响了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
事实上,《风之谷》之于宫崎骏作品序列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奠定了一系列内容表达上的母题,这些母题在之后的作品中仍然不断出现。除了对灾难的想象,另一重要母题便是对战争的批判反思。影片中的国家多鲁美奇亚四处征伐侵略,声称要整合边境各国,建立一方乐土,明显地指涉了“二战”中日本以实现“大东亚共荣”为名实施的侵略行径。战争期间出生的宫崎骏一直对军国主义的历史及其残存的幽灵持坚定的批判态度。1986年上映的《天空之城》正延续了这一母题,片中野心巨大的反派穆斯卡试图利用天空之城的发达科技统治世界,其形象无疑是对军国主义势力的影射[3]。而巴兹与希达最后念出毁灭咒语“巴鲁斯”,正是呼唤和平,告别战争的最强音。
宫崎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持续探讨也由《风之谷》开启。影片中腐海的扩张和王虫的愤怒都是人类一心征服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的结果,而贪婪的本性又使人类不断陷入混战与斗争。这种“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裹挟着一股愤怒的厌世情绪,仿佛只有人类彻底灭亡之后世界才能恢复原有的秩序。然而,宫崎骏还是让心怀赤子之心的娜乌西卡协调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最终在末日的边缘拯救了世界。纯粹的赤子之心向来是宫崎骏的主角们最可爱的地方,只不过他们在种种危机面前所能有的作为一直在发生变化,他们的身份地位也有其发展轨迹:《风之谷》里的娜乌西卡是有着皇室血统的基督式的救世主,到了《千与千寻》,荻野千寻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邻家女孩。
宫崎骏的自然观就如日本的生态环境一样,一方面透过地震、海啸和火山这样的灾难毫不宽容地让人类葬身其中,另一方面又温柔地让物产丰收,慈悲地让人们安居乐业,于是就有了《龙猫》(1988)。这部昭和末年的作品散发着乌托邦的氛围,田园牧歌的祥和远离了无休止的征战和一切灾难破坏,最迫切的烦恼似乎只是生老病死而已。如果说《天空之城》里的拉普达也有着乌托邦色彩,那确乎是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不可能存在的地方。那么《龙猫》的乌托邦则是“就在身旁”的奇异世界。《龙猫》的整个故事背景是全然本土化的,跟前两部作品都不同,主角们终于用上了日本名字,生活场景也是平日可见的日本乡间。基于这一背景,宫崎骏提出:“早已遗忘的东西,未曾注意的东西,以为早就失去的东西,但是我相信那些东西都还在,所以提出《龙猫》这个案子[4]。”所谓“早已遗忘的东西,未曾注意的东西”,正是日本自然观中的神灵。这种自然观,可以看作某种万物有灵论。日本人也许不相信组织上、教义上的宗教,但却怀有信仰某种万物有灵论的心。此种信仰,实践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感应着无所不在的佛与神的力量,从动物、植物、大自然和无机物等森罗万象当中,感应灵魂与生命的征兆。因此,我们就看到了《龙猫》里寄居在废弃房屋里的煤球精灵,遇到了沉睡在森林身处的龙猫家族,然后和龙猫一起,见证月夜下疯狂生长的参天樟树。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对自然的恐惧或敬畏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当中,众多的神灵正是无意识的显影,是民众对自然的诸种敬畏和企盼的混合体。
二、赞美与忧患
随着日本进入平成年代,长期以来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宣告终止。在整个八十年代,宫崎骏都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一共推出了四部长片,进入九十年代,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宫崎骏也进入了创作低潮,到世纪末为止只亲自指导了两部作品。1992年的《红猪》延续了反战立场的表达,在主角波鲁克身上,宫崎骏投射了自己作为反战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难堪境地——身为日本人,但不愿与军国主义势力同流合污。因此,主角波鲁克就从人变成了猪,通过这样的变形实现自我放逐,逃离所有的国家立场和民族身份,这位痛恨战争的孤独者就成了一个西部片式的赏金猎人,在亚得里亚海上空与空贼周旋,赚取赏金度日。影片吸收了些许美国西部片的元素和桥段,台词中也直言不讳地指涉了西部片,但更有意味的是,影片还是一曲女性的赞歌。宫崎骏的多数作品都以女性为主角,在他眼里,女孩特有的纯真特性使得她们更接近自然,平凡、弱小的她们承载的是勇敢与不屈的宝贵精神。《红猪》中的那家机械制造厂里,男人们因为战争的原因都被征召入伍,工厂里的员工清一色是女性。18岁的菲奥是这些工作女性的出色代表,她独立设计了波鲁克的新飞艇,完工之前一直昼夜不停地赶工校准每一个细节,飞艇建造的其他所有环节也由家族的其他女性完成。[5]事实上,宫崎骏在前作《魔女宅急便》(1989)中就已开始关注相似议题,13岁的女主角琪琪来到异乡打工,在陌生的环境下面临重重困难,甚至于一度失去了与生俱来的法力,但她最终凭借自己的善良和勤劳完成了一项又一项成长中必经的功课。从两位女主角的年龄上看,《红猪》里的菲奥正是琪琪的完美延续,她在新的起点上开启实现自我价值的新篇章。
1997年的《幽灵公主》也用一定篇幅承接这一女性赞歌的母题:达达拉城的女性是工作的主力军,负责制造武器,同时还担负起城防的任务。有意思的是,女性的领袖幻姬在年龄上恰好比18岁的菲奥又年长一些。九十年代的日本因为陷入经济萧条,又正逢生育率下跌,政府出台了相应法案推动就业平等,鼓励女性参加工作,以应对人力短缺的问题。1999年,《男女共同参划社会基本法》在国会通过,承诺未来会加强立法给予男女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的平等地位。此后,重要的性别平等措施陆续出现,不少已婚妇女仍然留在工作岗位上,女性担任管理层职位的比例也有所增加。[6]另一方面,《幽灵公主》是一部充满了忧患意识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九十年代的“时代精神”。片中被斩首的山兽神愤怒的呼号,全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流出黑色的浓稠液体,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人与自然的激烈冲突都在此刻达到顶点,男女主角充满张力的互动也是这种冲突的绝佳载体。此外,片中诸神如山兽神、猪神、狼神、树精比《龙猫》更进一步地刻画万物有灵的世界,这在下一部作品《千与千寻》中又继续着更生动的描绘。
三、新世纪的“变形”
进入新千年后,宫崎骏推出的第一部作品《千与千寻》(2001)就创造了日本动画的票房奇迹,拿下了290亿日元,至今仍保持着日本电影史上最高的票房纪录。影片的日文片名直译过来是“千与千寻的神隐”,所谓神隐,是日本的一个民俗概念,指孩子突然收到超自然力量的感召而从日常生活中隐匿,在异世界经过一场历练之后再返回生活世界的现象。影片中,我们跟着主角千寻进入了一个“百鬼夜行”的世界,在这里,宫崎骏最为生动地构筑了一个万物有灵的小宇宙:千寻的主管是以日本传说中“大天狗”为原型的“汤婆婆”,帮助千寻坐电梯的白萝卜客人脱胎于农神萝卜神,追击白龙的纸鸟则是源于日本人偶崇拜的传统,白龙本身又是河神之子。还有《龙猫》里出现过的煤球精灵也再次登场,它们胆怯怕人,喜欢藏在古宅的墙缝中安家。然而,“百鬼夜行”所折射出的并不是关于人与自然的议题,而似乎是一个关于职场生活的寓言。影片伊始,千寻一家进入那个废弃的游乐场,似在指涉仍未走出经济萧条的日本社会,此后出现的那个幽暗的异世界散发出恐怖片的气氛,在千寻贪吃的父母变成猪之后达到顶点。此后的千寻为了拯救父母,留在这个世界当中辛苦地工作,她受尽了汤婆婆的训斥苛责,干遍了脏活累活,还一度失去了自己原来的名字。最后,千寻终于凭借着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善良温柔的心性完成了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拯救了父母,同时找回了自己的名字。“不要忘记自己的名字”似乎是宫崎骏送给所有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的箴言。“巨婴”,压榨,贪婪,面对这些成人社会的怪力乱神,似乎只有怀抱着原初的心性,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保持最纯真的自我。
就像白龙由龙变成人形,千寻忘记自己的名字也可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异化”或“变形”,接下来的两部作品里也延续了这一“变形”主题:《哈尔的移动城堡》(2004)里变成黑鸟的哈尔和变成老太太的苏菲,《悬崖上的金鱼姬》(2008)里变成人类的波妞。另一方面,从《千与千寻》开始,宫崎骏的主角们都很平凡,或者最终变得平凡。千寻只是一个十几岁的邻家女孩,没有任何技能特长。苏菲也只是个普通的衣帽匠学徒,没有半点法力,但靠着自己纯净的心灵,苏菲最终救了哈尔,破除了稻草人的魔法。波妞本来是大海里的金鱼公主,法力强大,但最后为了宗介,她甘愿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事实上,在《千与千寻》之后,宫崎骏的作品内化了故事中的矛盾冲突,早期作品里激烈曲折的情节不再是人物行动的燃料,人物内心深处做出的选择才是引导影片走向的指针。人物从“变形”到“还原”正是他们勇敢面对自我后实现的升华,同时也寄寓着宫崎骏在访谈中多次表达过的信念:只有纯真的孩子才能让这个糟糕的世界变得好一点,也只有心存赤子之心才能在这个糟糕的世界更好地生存下去。
结语
2013年末上映的集大成之作《起风了》是宫崎骏迄今为止现实关怀最强烈的作品:首先影片以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传记为题材,这在宫崎骏的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影片天然地限制了以往作品中那种幻想王国里的恣意纵横,不能出现超越现实生活的元素。但宫崎骏在这种限制下仍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的长项,在掘越二郎的梦境里,他与意大利飞机设计师卡普罗尼相遇,在梦的国度里畅谈理想,环游世界。另外,这部影片也最直接地面对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国族的命运:大正年间的关东大地震,“一战”后萧条的经济,走上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直至最终迎来毁灭性的战败。这也是宫崎骏第一部具有悲剧内核的影片。主角掘越二郎是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只能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为军国主义的日本设计战斗机。然而到了影片结尾的时候,他的爱人死去,他的国家战败,他心爱的作品悉数毁于战场,正如卡普罗尼对他说的:“飞行是被诅咒的梦想。”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梦想坠入地狱。有意味的是,“飞行”也是宫崎骏本人最钟爱的母题,他对于各种机械装置也近乎迷恋,而侵略战争的历史似乎使“飞行”的梦带上原罪,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从《风之谷》到《悬崖上的金鱼姬》,心怀赤子之心的主角们总能在最可怕的危机中拯救世界,但在《起风了》的结尾,宫崎骏对此不再相信了,整个世界并没有重新焕发生机,也并不充满希望,只留下背对观众的主角在战后的废墟上挣扎着生存下去。不难发现,影片展开的几大主题都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只有生存这一主题面向未来敞开。此时的宫崎骏是何等悲观,消解了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母题具有的意义,但是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对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仍然借着掘越二郎的最后一句台词说了声“谢谢,谢谢”。生存似乎才是宫崎骏最终极的关切,纵然命运风雨飘摇,这个世界仍然值得我们生存。就像影片开头引用的瓦莱里的诗句:“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至于要如何在这个并不充满希望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即将上映的作品《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也许会为我们呈现更进一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