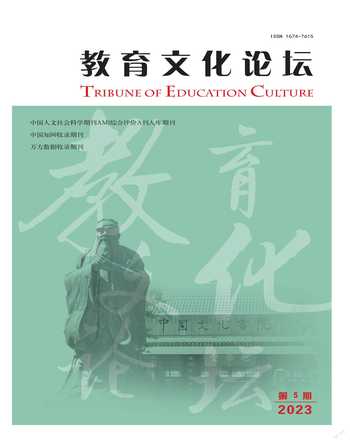面向文化治理的大学人文教育:何以与何为
2023-08-25何佩航
何佩航
摘 要: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方向,文化治理显现出国家、社会、公民三种话语力量的动态博弈过程。但随着当代中国文化治理格局中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暴露,对文化治理的主体追问使大学人文教育应需而入场。大学人文教育作为培育时代新人的关键场域与青年话语汇集之地,应以人文渗透的育人过程、人文产出的形式与数字人文的实践情境助推文化行动,提升话语力量,促进文化治理中共同体“有为”的实现。
关键词:文化治理;人文教育;主体性;话语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615(2023)05-0001-10
DOI: 10-15958/j-cnki-jywhlt-2023-05-001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建设日益受到各界关注。随之而来的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方向,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文化治理呈现出隐性与柔性结合的特征,潜移默化却深远持久地影响着整个社会中的权力、制度与关系;另一方面,文化治理以文化为载体贯穿了整个社会的权力、制度、关系结构,是调整社会矛盾、回应社会诉求、稳定社会结构的内部逻辑。文化治理天生具有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旨在平衡人、社会、国家三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之间的文明互动关系[1]。但无法否认的是,“文化既是秩序的工具,又是失序的动因”[2]。在经济全球化、信息高速化、风险流动化的今天,中国文化面临着国家间争端的风险与文化分层的落差等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化治理的价值进一步凸显,有必要思考如何在危机之中实现这一治理模式转型。随着实践的推进,我国文化治理实践中的结构性问题引发了各界对文化治理的主体追问,这使大学人文教育应需而入场。因此,基于大学人文教育面向文化治理的应然价值与时代意义,更基于大学人文教育助推文化治理的实践可能,本文将以文化治理的三维格局为指引,探讨大学人文教育如何为推进文化治理作出切实可行的贡献,助力国家治理模式转型。
一、 入场:文化治理与大学人文教育
(一)应然: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三维格局
文化治理这一概念来自西方。米歇尔·福柯对“治理性”、安东尼奥·葛兰西对“文 化霸权”以及托尼·本尼特对“文化治理”的研究,使文化治理的理论逐渐成熟[3]。在文化治理视域之下,文化与权力相联系。福柯指出,各种知识、话语等形式是广义的政治支配性权力结构的表现,“控制的技术”将走向社会大众“自我的技术”[4],并以“社会技术”对社会大众进行行为引导与观念塑造,即政府治理可以借助文化来实现。因此,文化不单单只是“文化”,而是表现为“权力弥散于文化结构”“言词形式的领导权使群众、政党、领导集团紧密联系”[5]。文化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统一意志使社会大众、政党、领导集团形成复合体并达成集体行动。但文化不仅仅是领导权的单向表达,“文化总是一种在场,并且是第一位的,存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实践中,还从内部建构它们”[6]206。在文化治理视域下,社会作为一种文化有机体,需要形成“现代性共容”的文化土壤与文化治理场域,去适应、回应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并形成文化、权力和市场的合理性关系[7],从而促成文化、权力、社会间的有机互动,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协同推进的应然图景。
立足中国语境考察文化治理,从历朝历代的文化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化管理再到当代的文化治理来看,我国文化治理的转向,从侧面反映了国家权力的限缩趋势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文化治理于当代中国之所以重要,不仅由于文化治理自身的价值,也由当下特殊的国内外环境所造就。从文化治理的价值来说,文化是治理的手段、过程与目标的集合体,涉及意义生产、话语权建构乃至资源分配,不仅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理念与规训教化,还涵盖了民众的文化权利以及背后的政治、社会权利方面的话语[8]。从国内外环境而言,我国面临的竞争不仅是政治、经济竞争,更是人才竞争与文化软实力竞争。伴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内部发展诉求以及外部竞争压力都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深化与转型。
基于文化治理的现实价值,学界对文化治理的理论格局与结构进行了深入思考。从我国政策话语与相关学术研究来看,文化治理的三维格局逐渐明晰,包括政府维度、市场维度和公民维度[9]。其中,政府维度体现国家意志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为政治认同的国家话语[10];市场维度体现资源分配与要素流动,呈现为价值多元的社会话语;公民维度指向公民意志与主体性构建,呈现为自我赋权的公民话语。基于此,文化治理格局下的国家维度关乎文化的目标与取向,是文化治理的前提;社会维度关乎文化的价值与选择,是文化治理的过程性保障;公民维度则关乎文化的诉求与表达,是文化治理在场的主体性回应。而这应然格局中三维对应的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公民话语所代表的力量,则反映了我国文化治理的格局结构是否合理[10]。应然层面的文化治理格局意在使公民真正成为文化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形成和谐互动的三维结构,达成真正的合作共治,从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模式的转型。
(二)实然: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主体追问
在我国文化治理的推进过程中,国家话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诚然,强势的国家话语有利于体现国家的“家长责任”与“文化监护”,有助于构建以独有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文化中轴作为社会的稳压器,从而潜移默化地使民众心中生成具有民族特征、時代意义的“集体意识”。但随着文化治理实践的推进,当代中国文化治理格局中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暴露。由于家长式政府所带来的路径依赖,公民在文化治理中存在习惯性接受、被动性参与、主体性缺失等问题,在文化治理在场中很难发挥应有作用。因此,在文化治理的背景之下,有必要发问:如何使公民真正成为文化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如何实现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回应?如何达成文化治理在场中真正意义上的共治与善治?有学者指出,公众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积极表达意见是公民在文化治理中达成共治与善治的高阶表现[9]。在强势国家话语的历史背景下,公民话语的有效表达,一方面需要突破国家主导的惯性话语机制;另一方面还需要激活公民的主体性,促使其主动行使权利,进行有效的话语表达与积极的文化行动。
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全面渗透,公民的文化需求已然呈现出爆发式增长,需求异质性越发凸显,这有利于使公民话语作为一种反抗性力量推动文化治理格局下三种话语的再博弈;另一方面,我国在改革中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文化相对被忽视,多种类型亚文化的悄然渗透和扩张使我国文化矛盾在个体间、阶层间显化[7],这使我国政府更加重视文化的功用,关注公民的主体价值。托尼·本尼特指出,文化的功用将“有利于在人们中培养一种自愿的自我控制力”[6]239,话语将“使我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对我们自身的管理与监督之中,并促进我们自身的发展”[6]206。但“文化建构形成的谨慎的主体不是拥有一套信仰的主体——这样的主体能通过赞同现存的权力而使其永存——而是作为一个行动者,通过要过一种新生活的行动实现权力运作的职能”[6]258。这意味着,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回应并不是对领导权能的单纯顺应与赞同,而是以文化行动“作用于社会以调节社会,同时作为形成一种观念即国家权力从属于批判的理性形式的手段而发挥功能”[6]336。
一言以蔽之,文化治理的顺利推进必依赖于公民的主体地位及其主体性回应,并在某种意义上达成公民文化自觉与行为自觉的某种治理性结果[7],由此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在对话交往中实现公民赋能,在文化治理中实现互动与回应,从而达成共治共享的理想局面。
(三)使然:文化治理下大学人文教育的入场
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之下,文化治理的推进一方面更加凸显出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意义。主体性是培养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根基,这也意味着当代我国对人的培养应当重在人的主体性建构;其次,主体性也是社会共识和秩序凝结的内在纽带[11],是达成文化自觉与行为自觉的养成性基础。另一方面,主体性也是公民表达文化诉求等活动的参与基础,是汇聚多方话语从而达成公民话语再博弈、实现共治共享的实践性基础。因此,文化治理格局下的主体追问使大学人文教育应需而入场,并力图以其在文化、育人、治理方面的功用回应文化治理。
首先,从历史视角来看,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人文文化特质:一是强调以人为本,要求保持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独立性;二是主张礼乐教化,强调自我管理,让人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12]。文化本身就具有教育的意味,既是教育的工具,也是教育的目标,具有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的教育作用。“文化是一种道德教育学,将会解放我们每个人身上潜在的理想或集体的自我,使得我们能够与政治公民的身份相称,这样的自我在国家的普遍范畴中得到最高表现。”[13]其次,教育是建构文化、革新文化、再生文化的重要场域,其中人文教育作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与方式[14],由里及外地存在于国家文明、社会生活以及育人场域三个层次中,而这恰与文化治理的三维格局相对应。历史的经验也表明,展现人之主体性的人文教育使公民具有与治理相匹配的素养,是把人从自然状态解放出来的必由路径,是社会治理最坚实、最持久、最本真的人文基石[15]。此外,文化和知识分子空间——类似大学的场所,将在发展和传播社会与文化批判的特殊形式上发挥首要作用[6]336。知识分子具有“典范效应”,能以行动启蒙社会大众、关怀文化生活并推动社会发展。
基于此,大学人文教育作为人文素养培育与主体性建构、文化传承以及话语表达的重要推手,将助力文化治理中各方回應与互动的实现。对于人文教育,托尼·本尼特指出:“人文学科需要重新定位,它们应该对现有的社会、学术、政治争论和手段做出切实可行的有益贡献。”[16]但基于大学人文教育对文化治理的应有之义,不应将其局限于对人文学科的重新定位,而应当基于时代背景,从目标、过程以及特有价值上与我国文化治理动态相呼应,从而探寻教育与治理的结合点,为全面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奠定坚实的“软支持”。
二、 何以:文化治理下大学人文教育的“三为”面向
在当代中国文化治理格局下,大学人文教育与文化治理在目标、过程与价值上呈现出高度的耦合与呼应,并表现为主体性赋能的个体之为、以文育人的行动之为以及话语表达与权力的治理之为。需要明晰的是,本文所指的大学人文教育并非人文主义教育或者狭义的大学人文学科,而是广义上以人文育人理念提升青年大学生的人文认知以及人文素养水平的教育。因此,大学人文教育关注个体的自我修为与文化品性,意在使青年大学生能够认识自我、真正“成人”[17],从而促进“人的主体性建构并实现文化治理中的主体性回应”这一理想的实现。
(一)主体之为:主体性赋能与德性培育
在文化治理视域下,公民话语的主体性表达之基础必然与其主体性能力(抑或素养)密切相关,大学生作为具有“典范效应”的知识分子群体,更应具备较高的自我修为与道德素养。因此,当大学生作为文化治理格局中公民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文化治理目标与大学人文教育目标不谋而合。
从文化的主体之为来看,一是关注人的主体自我修为,实现人与自我统一;二是关注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在文化公共层面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使人与社会相通[18]。正如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人文教育的第一要义即实现人与自我的统一,只有在人与自我统一的基础上,个体才能真正亲身参与、投入实践从而进行社会创造。但人的主体性不仅是理性自我的充分显现,个体有限性与无限性的通达可以转化为个体向其他个体、群体和历史的延续[11]。这意味着个体的主体性不仅体现于其自身,也体现于个体之间。也即,个体主体性的生成必然发生于社会之中,而个体与社会的共通正是文化治理的主体之为之一。这与人文教育在培养理性自我基础之上欲达成的公共理性相耦合,也是达成群体认同与形成集体行动的基础。
基于此,大学人文教育应致力于个体的主体性赋能与德性培育,从而塑造具有较高自我主体修为与德性氛围的公民群体,继而实现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互通与共融。一方面,大学人文教育的主体性赋能应当使大学生具有与文化治理相匹配的素养,从而具有对话与发声的能力。大学生的主体自我修为不仅仅体现为人文认知水平,更体现其在公共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我认知、理性思考与价值判断等能力上。另一方面,大学人文教育的德性培育应超越私德,关注公共德性的内化,使大学生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将个体发展融入共同体发展。个体只有在自有、自发、自在的基础之上,才能达成自觉、自为的治理结果。赋之以能力并唤醒其自发认同,才能使大学生确立顺应时代潮流、坚守民族灵魂、符合国家价值的精神追求,从而实现个体与自我的统一、个体与社会的相通。
(二)行动之为:文化的动态建构与柔性塑造
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多元文化交流已成为常态。只有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19]。这意味着,只有坚实的人文基础才能使我们在日益动态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坚守本心并理解他者。
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对民族、历史、制度、文化等的认识之可能性都是基于自己的创造,而正是基于这种亲身参与、亲身创造的同质性,人才有可能从内部去认识、重构和理解社会历史文化[20],并在认识、重构与理解文化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塑造与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化认识的异质性日益凸显,文化也逐渐呈现出多元而动态发展的特点,这使文化的功用逐渐从纵向的时间维度转向横向的空间维度。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认识、重构与理解本土文化,还要在文化市场化、文化全球化中建构与理解新的文化。这意味着,文化的革新與发展往往源于作为文化行动者的“我们”,而文化行动的发生又以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为诱因。个体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脱离并再嵌入群体,并以文化产出的形式向外界传播影响,而其他主体对客体性文化产出的理解或再造又意味着新一轮文化动态建构的开始。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在这个动态建构过程中得到充分显现,个体行动者既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对象;个体行动者不仅需要“自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互识”,从而“再塑我者”,获得“他者认同”。因此,只有具备较高的人文基础,才能实现“自识”与“他识”的动态交互,并在文化动态建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塑造与发展。
基于此,大学人文教育将以学校体系的方式实现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人文内化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人文坚守,从而帮助大学生在“自识”与“他识”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对话与交往。一方面,大学人文教育的过程正是认识自己文化的传承过程,是对主体人文性与生命性的塑造。经典文化是人文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本土文化的人文积淀是文化治理中主体能够认识、重构、理解自己历史文化的前提。另一方面,大学人文教育的发生过程也是动态建构的过程,表现出主体交互性。大学人文教育的作用方式正是主体之间的动态交互,是教与学中的互相影响与互相成就,而非单向的师授生听方式。此外,大学人文教育的作用体现在个体行动的过程中,表现出包容性与共通性。大学人文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对文化进行选择与判断,也即进行文化心智模式的转换;另一方面,在面对多元文化环境时,也有助于大学生学习从个体到群体的文化对话及交往过程[21]。
(三)治理之为:话语权力与文化共同体
在文化治理视域下,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过程必然意味着言语对话的产生,并在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权力的博弈。但在我国历史进程中,国家话语体系之下的公民多表现为“沉默”或“失语”状态,成为话语权弱势群体,亟需一种一致性的力量使之形成行动共同体。一方面,由于具有强势地位的国家话语以知识性文化输送着价值体系,以“知识——权力”操纵文化治理机制中的具体规则,意在使社会公民中形成以专门知识建构社会的意识形态安全底线[22],但却相对削弱了公民话语的声音。另一方面,随着文化市场的涌动,新媒体逐渐在市场话语中变成另一种“强势话语”,具有弥散性和广泛性的新兴媒体话语伴随着话语失度与失真,携带外来文化的价值冲击[23],进一步消解了公民的话语权力。在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影响下,公民的“沉默”逐渐演化为一种惯习。这意味着,作为新生代公民的大学生群体,不仅需要提升主体性能力,以主体的身份进入文化治理的场域;还需要超越“惯习”,以共同体的身份凝练新的行为方式与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文化动力应对市场话语的冲击,张扬公民话语的价值。
因此,大学人文教育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体发展之上,也同时彰显于其构筑青年共同体的责任之上。共同的人文内核与价值观将有利于大学生群体形成一致性追求,凝聚共识、合力行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从而以新生代的力量去破解公民话语困境。从个体层面看,大学人文教育着力于提升大学生个体的主体性修为与德性,从而成为“能为”的个体;从群体层面看,大学人文教育致力于提升大学生群体共同的人文情怀与价值认同,从而形成“自为”的状态;从共同体层面看,人文教育旨在使大学生群体达成一致性追求与积极行动,从而实现“有为”的理想。正如托尼·本尼特的看法,“批判理性”与“积极实践”是文化治理格局中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想姿态。大学作为培育知识分子群体的场地,需以人文教育作为其“教育底色”,以知识赋能大学生,以人文联结大学生,以话语赋权大学生,从而使大学生群体主动摆脱“沉默”的面具,以行动的共同体参与文化治理并投身社会主义治理实践。因此,大学人文教育之于治理的价值,正是彰显于培育大学生这一青年群体的主体性之上,从而联结个体并形成共同体,有效增强公民话语力量。由此,文化治理格局下的三种话语力量才有可能实现结构性优化,继而推动共治共享局面的实现。
三、 何为:文化治理下大学人文教育的行动路向
基于大学人文教育与文化治理的耦合关系,以及大学这一育人的关键场域,大学人文教育不仅具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传统意义,也肩负个体主体性赋能、话语权彰显的时代责任,更是凝结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因此,从育人的视角来看,大学人文教育仍需探索将人文渗透育人全过程的路径,从而实现个体的主体性赋能与德性培育,以个体“能为”推进文化治理;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大学人文教育还需探索推动文化认同的路径,从而凝练核心价值的文化内核,以群体“自为”推进文化治理;从治理的视角来看,大学人文教育更需探索实现文化行动的路径,从而打破公民话语的沉默惯习,以共同体“有为”推进文化治理。
(一)能为:以人文渗透的育人过程实现主体性赋能
基于文化治理的目标,大学人文教育应当在育人过程中体现人文渗透的特点,并在课程思政等政策引领之下构建起人文学科集群,通过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集群,复归人文学科的共通与互融,从而超越学科的局限性,使青年大学生能够站在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去审视自身并实现个体的主体性赋能[24]。
一方面,大学人文教育应当以个体的主体性赋能作为目标,关注育人过程中的人文渗透。主体性赋能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将人文渗透育人的全过程,才能使个体在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环境中发展。但反观现实,大学人文教育尚未实现全过程的人文渗透,甚至对人文教育的目标与过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读。其一,大学人文教育的主体性赋能不仅仅是对人文知识传授的单向度关注。知识输送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育成,学生的主体性往往被工具化评价体系所隐蔽。事实上,大学生的主体性表现为以人文认知水平为基础的自我认知、理性思考与价值判断等综合能力,并体现为与治理相匹配的个体素养。其二,大学人文教育的德性培育不应局限于对政治德性的单向度关注,继而异化为任务性的思政课程。无可否认,德育是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基于立德树人这一大学的根本任务,大学人文教育需实现全方位的德性培育,促成公共德性的内化。在当前课程思政的政策东风之下,课程思政的推进为人文滲透课程提供了有益思路。由于课程思政建设与通识教育人文课程具有深层次的内在契合性,因此,以课程思政建设为指引[25],将人文特质与思政内容同步渗透、正向关联。这是因为通识教育人文课程内容本身就具有人文特质,通过各类通识课程之中的人文渗透与思政互动,有利于使青年大学生的德性生成与人文认知提升融为一体,从而实现人文认知与德性的共生。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文渗透应当因课而化、常态推进,并在内容与方法上进行主体性设计,在评价上避免功利性倾向。
另一方面,大学人文教育应当突破学科间的壁垒,实现学科间的人文渗透。从当下教育环境看,大学人文学科边缘化现象严重,极不利于时代新人的主体性建构。大学对专业化的追求使人文教育日渐式微,人文学科的细分使学科间被架构起人为的隔膜,学科竞争甚至使部分人文学科日益萎缩。例如,北京大学近年来以“专业+项目”的方式探索出古典文学、思想与社会、汉语国际教育等跨学科人文教育课程体系,有益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其人文思维。因此,乘着新文科的政策东风,大学人文教育应当注重学科间的人文渗透,从而构建起人文学科集群,实现协同共育的教育生态。通过建构人文学科集群,不仅有利于集聚学科资源,实现学科间的互相支撑;更能以文化集群的形式发挥溢出效应,以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生态全方位提升个体的素养,从而助力个体“能为”的实现。
(二)自为:以人文产出的形式凝练文化核心价值
文化作为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其必定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并由某种文化形式承载。因此,大学人文教育应当反思如何通过人文产出凝练核心价值,以顺应时代潮流的形式承载核心价值并扩散影响,从而构建起文化治理格局中稳定、包容的中轴力量。
大学人文教育要回应时代需求,增强其在文化市场中的话语影响力。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学一直承担着文化传承与知识生产的重任,但大学人文教育的人文产出形式相对固化,主要体现为论文、报告等形式,这使人文产出在现实中常常被等同于学术生产。论文、报告等确有学术价值,但其话语表达不易被大众接纳。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技术发展全面改写了文化的传播形式与速度。技术的自反性建构起知识的“定价”体系,变现的压力使思辨传统和人文理论研究被明显边缘化[26]。这也意味着大学人文教育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与财政投入,以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
大学人文教育需肩负时代责任,传播中华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类文化在技术逻辑的影响下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建构、转换,逐渐演绎出了更亲近民众的话语表达。但对形式的过度关注,往往意味着对实质内容的相对忽视,当下市场中部分“亲民”形式的文化实际携载着对核心价值的解构冲击。碎片化文化、数字信息漫灌以及各类亚文化的冲击使大学生群体更需要一种牢固的内心力量,以提升共同的人文情怀与价值认同,从而用人文的力量平衡当下市场话语的浮躁与功利,在“自识”的基础上达成“互识”。
大学人文教育应积极供给优质精神文化产品,提升其人文产出水平。大学人文教育的产出形式不应拘泥于学术研究,可尝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时代新意相结合,并以顺应时代潮流的文化形式承载之。例如,在部分文化产出中利用新传媒途径,或者以大学生群体容易接受的流行话语、生活话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阐发和创新,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亲和力[22]。例如,云南大学的学术史话剧《魁阁时代》,以跨学科协同、师生构作的方式将人文、学术与传媒融为一体,取得了较好的育人效果与示范效果。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在亲民话语形式下的文化产品中,有利于极大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使国家话语、主流话语逐渐融入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精神入脑入心。由此,大学生群体方能逐渐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为转化,从而以共同的人文情怀与价值认同投身于文化治理与社会主义实践之中。
(三)有为:以数字人文的实践情境铸牢文化共同体
当下,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文化建构了新的虚拟空间,大学人文教育需探寻文化治理中数字技术与人文坚守的平衡点,为大学生群体创设数字人文的实践情境,从而促使其以一致性追求形成行动,实现共同体“有为”。以上海大学的“上大元宇宙”平台为例,其集学术、讲座、展览、社交等功能于一体,学生们乐于在虚拟空间进行数字化学习、社交与生活,初步实现了虚拟技术下的真实共情与人文交往,这为数字人文的实践情境提供了推进基础。
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以大学数字人文实现人文培育、学术生产以及综合实践等功能的一体化,助力大学生的文化实践。大学数字人文是对大学人文教育的坚守与延伸,这意味着大学生群体人文素养的培育过程不仅发生在传统教育情境之下,也将进行数字情境下的转化,例如学习方式的数字化、学习资料的数字化以及教学技术的数字化。此外,大学数字人文应当突破传统大学人文教育的局限,为学术生产创造具有强大包容性的学术版图[27]。人文学科的交叉与合作,有利于培育大学生跨学科思维,并以多元化的人文学术产出为大学生群体营造文化内核坚实且包容多元文化的环境。
另一方面,关注人文转化,注重大学数字人文作为文化情境性机制的功能。当下,虚拟空间意味着文化作用的延伸与解构将同时存在,这使文化的动态建构更容易且更频繁。然而,虚拟空间也意味着文化价值的多元与叛离将同时存在,这使话语的权力博弈更激烈且更分散。这表明,在数字技术逻辑的加持下,公民话语的异质性在虚拟空间中得到凸显与放大。但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蔓延也使公民话语分散,并出现表达失度与失序现象,这说明数字时代更需要人文柔性逻辑的坚守。在此背景之下,大学生作为虚拟空间的活跃分子,一方面需要促进人文素养的数字转化,做虚拟空间的文化典范;另一方面也需积极参与虚拟空间的文化实践,拒绝沉默与匿名。因此,大学数字人文应当以数字化技术促进人文转化,从而激励行动者有意识地在不同制度情境中转变文化策略,并有效实现集体行动动员[28]。大学数字人文可尝试以数字项目式研究作为实践单元,以协同性、合作性的团队实践形式,使大学生群体在虚拟空间中为了一致的目标而行动。由此,大学生群体将以利益共同、责任同担、积极行动的行为方式增强其话语力量,从而促进共同体“有为”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施雪华,禄琼.当前中国文化治理的意义、进程与思路[J].学术界,2017(1):53-62.
[2] 齐格蒙特·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M].郑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
[3] 李艳丰.走向文化治理:托尼·本尼特文化研究理论范式的转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68-177+192.
[4] 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
[5]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姜丽,张跣,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342.
[6] 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M].王杰,强东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 张鸿雁.“文化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建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J].社会科学,2015(3):3-10.
[8] 张良.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治理[J].社会主义研究,2017(4):73-79.
[9] 柯尊清.公共文化治理的理论维度、过程逻辑与实现路径[J].理论月刊,2021(1):105-112.
[10] 廖胜华.文化治理分析的政策视角[J].学术研究,2015(5):39-43.
[11] 張鲲.新时代“时代新人”之主体性建构[J].思想教育研究,2018(10):24-28.
[12] 楼宇杰.中国文化的精神根基[M].北京:中华书局,2016:7.
[13] 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8.
[14] 王兆璟.新时代人文教育场域之突围与再造[J].社会科学战线,2019(8):228-233.
[15] 刘建军,邓理.基于人文教育的人文治理——理论建构及实践进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2(2):60-73+194.
[16] 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M].王杰,强东红,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225.
[17] 马智芳.论人文教育的三种内涵及其现实危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32(25):16-20.
[18] 徐椿梁.认知·实践·主体:价值在文化存在中的三重意义[J].求索,2020(6):77-83.
[19] 刘谦.学校育人过程中文化自觉性的培养[J].教育研究,2011,32(3):13-16+20.
[20] 牛文君,张小勇.人文与诠释——维柯人文科学奠基的诠释学理解进路[J].社会科学战线,2021(5):52-59+281.
[21] 廖文伟.文化自觉与社会行动者[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6(6):17-24.
[22] 刘莉.从“生命政治”到“文化治理”:对公共文化的一种定位与解构[J].思想战线,2020,46(6):72-78.
[23] 肖薇薇,陈文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年认同的话语赋能[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35(1):39-46.
[24] 李伟群,朱白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域中的高校人文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16(9):86-89.
[25] 祝浩涵.论以课程思政建设推动通识教育人文课程质量提升[J].教育文化论坛,2022,14(6):79-83.
[26] 刘超.数字化与主体性: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J].探索与争鸣,2021(3):22-25.
[27] 孟建,胡学峰.数字人文:媒介驱动的学术生产方式变革[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4):24-28+54.
[28] 魏海涛.集体行动的形成:一个文化视角的理论模型[J].社会学评论,2019,7(4):75-87.
University Humanistic Education for Cultural Governance: Approaches and Targets
HE Peiha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715)
Abstract:
As a direction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l, cultural governance reveals a dynamic game process among the three discourse forces of the state, society and citizens. However, as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in the patter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e gradually revealed, the inquiry of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governance has introduced the humanistic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need. As a key field for cultivating new talents of the times and a place where young people's discourse converges, university humanistic education should promote cultural action through the nurturing process of humanistic penetration, the form of humanistic outputs, and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humanistic, so as to enhance discourse power and help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gain achievements.
Key words:
cultural governance; humanistic education; subjectivity; discourse
(责任编辑:梁昱坤 郭 芸)